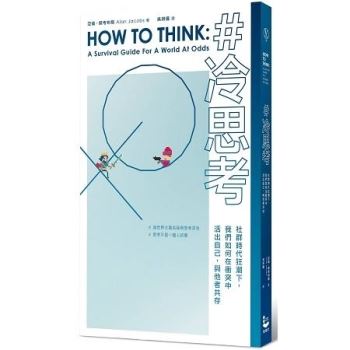(節錄部分)
可能是巧合,或是共時性(synchronicity)、命運使然,但有些時候,你正在讀的和你需要的之間會出現一種幸運的趨同現象。幾個月前,為了某個與本書無關的理由,我讀了兩位睿智作家—瑪麗蓮.羅賓遜,以及T.S.艾略特(T. S. Eliot)的文章。當時我正巧在認真重新評估我的上網時間,尤其是花在社群媒體上的時間。然後,寫這本書的點子開始在我腦袋裡連結起來。
羅賓遜在發表於一九九四年的〈清教徒與假道學〉一文裡,挑戰了許多人對清教徒的輕蔑態度(如今,「清教徒」不過是一種侮辱之詞),並對於他們所想的事、那些思考背後的理由,提出較寬容而準確的說明。下筆時,她突然想到,「我們談論或想起清教徒的方式,在我看來是一種可以用來討論所謂『清教徒主義』這個現象許多重要面向的模型。」也就是說,被我們說成是「清教徒式」的種種特徵—死板、心胸狹窄、愛下判斷—正是大家每次談起清教徒時所展現的特質。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大家對清教徒的態度是這麼的「清教徒」?「答案很簡單。」羅賓遜寫道。「這是個絕佳範例,指出我們有一種集體渴望—在缺乏相關知識或訊息的狀況下,去貶抑受人貶抑的事物—藉此得到回饋,也就是共享一種我們自知會得到社會認同的態度,並從中享受到快感。」這意思是說,我們譴責清教徒主義,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交談的對象會共享這種對清教徒的貶抑態度,也會贊同我們喚起這種感受。使用這個詞彙時,它和清教徒的行動、信念所代表的真相到底有無任何顯著關連性,一點都不重要。在這種狀況下,清教徒一詞不具任何意義,肯定也不符合史實。這個詞彙比較像是進入俱樂部的通關密語。
羅賓遜進一步評論說,這種使用方式「讓我們看到,這樣的共識可以多麼有效地封鎖對某個主題的探究」—這有可能是通篇最重要的論點。一個詞彙越能夠有效展現我得到某個團體的接納,我就越懶得再去檢驗我對這個詞彙的用法從任何一種標準來看到底算不算正當。所以,喜歡指控別人「像清教徒一樣」,會認真地力求盡可能不去理解真正的清教徒—也就是說,致力於不去思考。
羅賓遜的分析很敏銳,而且考量到這篇文章是在網路變成跨文化現象之前所寫的,更是難能可貴。思考讓人類無法「分享我們自知會得到社會認同的態度」—特別是在網路環境下,靠著「喜歡」、「讚」、「追蹤」和「加好友」,個人的態度要得到社會認可實在容易得多,而且馬上就能得到—既然如此,人為什麼要思考?
羅賓遜以一席提神醒腦的嚴肅評論來總結她的反省:在這種環境下,「未獲認可的觀點實際上會遭受不被理解的懲罰」。這不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人人有心刻意打壓異端的社會裡(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是確實如此),「反而只是追求共識的本能過度肥大所造成的後果」。如果你想要思考,你就必須縮減「過度肥大的追求共識本能」。然而,考量到那種本能之強大,親愛的讀者,你非常有可能不想去惹這個麻煩。
那種追求共識的本能,在我們的時代裡更加發揚光大,因為我們每天都在處理號稱是資訊、卻通常都是廢話的混亂洪流。這不是什麼新鮮事。T.S.艾略特在幾乎一個世紀前寫到一種現象,而他相信那是十九世紀的產物:「在這個時代,有這麼多事要去了解,又有這麼多知識領域以不同的意義來使用相同的字詞,每個人對於一大堆事情又都只了解一點點,以至於對任何人來說,我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說出口的話有幾分真實,都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讓我用不同字體來強調艾略特的結論——「在我們不了解或是了解得不夠多的時候,我們傾向總是用情緒來取代思維。」
這是另一種看來更加尖銳的想法。與其說它符合發言當時的狀況,不如說是更適合我們這個時代的診斷。而且這個想法跟羅賓遜的分析吻合得讓人心驚。致力於不去了解、不去思考某些事,以便「共享一種我們自知會得到社會認同的態度,並從中享受到快感」的人,在其追求共識的本能得到滿足時,會欣喜若狂—當這種本能受挫時,就會心生憤怒。社會紐結(Social bonding)是透過共同分享的情緒所鞏固,共享的情緒又會滋生社會紐結。這是一個排除反省的回饋循環。羅賓遜與艾略特解釋了許多線上持續不斷的狂亂激憤(agita)。在我看來,離線的生活也越來越相似了。
任何自稱沒被這些力量影響、形塑的人,幾乎可以確定是在自欺欺人。人類的天生構造,就是無法對社交世界的波折和波動淡然處之。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對於隨波逐流還有一丁點的不情願。真心想要思考的人,必須發展出一些策略來辨識最微妙的社會壓力,對抗來自內團體(ingroup)的牽引,以及對於外團體(outgroup)的厭惡。想要思考的人必須練習保持耐性,還要駕馭恐懼。
◎隸屬多重社群
我相信我可以幫助想要改善思考的人,但是—在更進一步以前,我得先說—不,這不是因為我來自學術界。我的學術界同僚,整體而言,也跟教育程度沒那麼高的普通路人一樣,不情願從事真正的省思。學術界人士一向具有異常嚴重的順應期待問題;你要證明自己配得上學術圈,主要辦法之一就是拿到非常好的成績,而你要是不說些指導教授愛聽的話,你就拿不到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不,學術生活對人的思考沒多大幫助,或至少沒有幫到我推薦的那種「思考」。學術生活幫助人累積一套知識,讓人學習並使用某些經過認可的修辭策略,它需要很好的記性、智性靈活度之類的東西,但學術生活裡沒多少事情會要求你質疑自己的衝動反應—即使你的學術生涯就是在研究衝動反應也一樣,如同前面康納曼所說的。
然而,身為老師,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在大學教書已經三十年以上,整體而言,大學教育就是個絕佳的思考實驗室。我的大多數學生都知道自己相信什麼,也想為其辯護,但他們也明白自己還有很多要學(世人普遍以為,大學生是一群自以為無所不知、其實是朽木不可雕的傲慢屁孩—這和我的教學經驗有相當大出入。我知道有這種人,但不常見,而且現在這種人不會比我剛入行的時候還來得多)。向學生們證明他們的信念不必然是錯的,只是他們沒能好好為其辯護、沒有了解自己最根本的邏輯、沒有掌握到向「可疑的他者」推薦自身觀點時怎麼做會最好,是非常值回票價的事。我估計我至今大概批改過一萬五千篇的學生作業,應該有資格說我見識過怎麼正確論證和論證出錯的所有方式。
這種長期累積的經驗在思考「思考」這件事之上確實很寶貴,更加寶貴的是我參與過各種社群,而這些社群經常彼此意見不同。我是個學者,卻也是個基督徒。聽到學者談論基督徒的時候,我的典型感想是:不是這樣的,我不相信你了解那些你自認為不同意的那些人。而當我聽到基督徒談論學者的時候,也有完全一樣的想法。我花了幾十年注意這些非常普遍的誤解,設法搞清楚它們是怎麼產生的,並尋求辦法來糾正這些錯誤。
三十年前,人類學家蘇珊.佛蘭德.哈定(Susan Friend Harding)開始認真研究美國基督教的基要主義派(Fundamentalism)。這個研究最後成就了一份卓越的報導:《傑瑞.法威爾之書:基要主義派的語言與政治》。然後她發現,她的同僚對她的研究興趣非常不解:怎麼會有人想要研究一群如此怪異又顯然不討喜的人?哈定寫道:「實際上,一直不斷有人問我:妳現在是或曾經是『重生的基督徒』嗎?」相信有許多讀者可以看出來哈定在狡黠地呼應一九五○年代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問過數百人的那個問題:「你現在是或曾經是共產黨員嗎?」
一九九一年,哈定針對這個現象出版了一篇力道強勁的論文。她提問,人類學家不是本來就應該對跟自己不同的文化結構與習俗感興趣嗎?那麼,當這種「不同」就在你家隔壁、可以跟你一起在同一場選舉裡投票,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類學家排斥研究它?哈定的論文標題是〈再現基要主義派:「令人反感的文化他者」問題〉。我們在接下來的內容裡,將會有理由使用「令人反感的文化他者」(Repugnant Cultural Other)一詞。事實上,這個詞彙出現的次數頻繁到最好給它一個首字母略稱:RCO。
正如我先前所暗示的,如果基要主義派或福音教派基督徒對於世俗的學界人士來說,很容易被當成RCO,反過來說也一樣。自從我成年以來,一直在這種互相猜疑之中努力向前航行。如今,我生活中的政治環境,整體來說,已經承襲了過去我在那些彼此敵對的較小型社群裡經常看到的可悲特徵:刻意的不求甚解、有毒性的疑心。現在每個人似乎都有個RCO,而每個人的RCO都在社群媒體上的某處。我們也許能夠躲開、不去傾聽我們的RCO,但我們都必須面對這個領悟:他或她就在那裡,可能就在兩個房間之外向我們叫囂著。
這種狀況極端不健康,因為它妨礙我們去體認其他人是我們的同胞—甚至當他們是我們名符其實的鄰人時也一樣。「那邊那個人既是個他者,又令人反感」,如果我滿腦子都在想著這種事,可能永遠不會發覺我最愛的電視節目也是他的最愛;我們喜歡的書有些是一樣的,雖然理由不盡然相同;我們都知道照顧長期臥病的心愛之人是什麼感覺……這一切都表示,我可能太容易就忘記政治、社會與宗教差異並非人類經驗的全部。RCO冰冷的分裂邏輯讓我們所有人變得貧乏,使我們更接近政治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那種「每個人對抗每個人」的原始狀態。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應該做得更好。我也相信我幫得上忙,這有部分要歸功於我在互相敵對的社群之間調停多年的經驗。我知道要跟在某些方面迥異於我的人為共同的理想而奮鬥是什麼感覺;我知道這樣的經驗能夠怎麼擴展我對世界的了解;我知道它們能夠如何逼使我去對抗我狹隘的視野,以及我簡化思考過程(有時根本想都不想)的傾向。還有,在此要向康納曼致歉,我是真心相信我這些年來在思考方面有長足的進步,而且我不想獨善其身。
◎迂迴勝於直接
接下來在 本書中所談的,有許多只是診斷性質,也有很好的理由如此。許多年前,我有過一次胸痛的經驗,好幾個醫生都沒辦法確定問題出在哪裡。我規律運動,心臟似乎也很健康,沒什麼地方明顯不對勁。但那種痛一直反覆發作,把我嚇壞了。最後,有個醫生進一步追究,發現我在胸痛開始之前,有過拖很久的嚴重咳嗽問題。看來那陣子的咳嗽拉傷了我胸部的一條肌肉,胸痛的來源就在這裡,而我開始擔憂這種痛楚之後導致的焦慮又使得肌肉更緊張,因此加強了痛楚,然後又讓我更焦慮。
這是典型的惡性循環強化。當我問醫生他覺得哪種療法最好,他回答:「診斷本身就是治療。現在你知道你沒有危及生命的疾病,你就不會那麼擔心,心裡的壓力減輕,意思是胸部肌肉的壓力也會比較少,於是這些肌肉就有機會痊癒了。」
同樣的道理,儘管我會在接下來的篇章提供積極的處方,但事實上,光是知道有哪些力量在我們身上起作用,使我們逃避真正進行反省、對自身狀況作精確診斷,就是治療的第一道程序了。
此外,我也很樂意提供你一套恆常不變的指導原則,讓你可以一步步遵循,變成更善於思考的人—但思考不是這樣一回事。我再強調一次,科學是我們的朋友,但思考在本質上是一門藝術,而藝術素有不受規則束縛的「惡名」—但仍有一些有效的舉措可以遵循,而我會在接下的內容裡介紹這些舉措(說實話,在說明買車這件事的時候,我幾乎已全都暗示在其中了)。總之,不論誰最先說出「快樂不是我們能夠直接追求的目標,只能靠著專注於其他美好事物來達成」這番話,把它套用到「思考」上也一樣正確。
音樂家布萊安.伊諾(Brian Eno)和藝術家彼得.史密特(Peter Schmidt)在一九七五年創造了一套奇特的工具。那是一組包含獨特指示的卡片:「將錯誤視為你的潛藏意圖」、「問你的身體」、「改變樂曲的速度」等。這些字卡的用意,是要幫助在工作上碰到瓶頸的藝術家(尤其是音樂家)。伊諾和史密特把他們的牌卡稱為「迂迴策略卡」(Oblique Strategies),因為他們知道當藝術家卡住的時候,直接去解決問題,每每無異於提油救火。同樣地,有時候只有把注意力轉向思考以外的事物,你才能更善於思考。所以,接下來的內容,有時是軼事趣聞,有時迂迴纏繞—但最後我們總是會繞回糟糕的思考會採取哪些形式,並發掘可以幫助我們更精通於養成此一最棘手藝術的習慣。這不是容易的事—問題有一部分就在於此。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辦到。
可能是巧合,或是共時性(synchronicity)、命運使然,但有些時候,你正在讀的和你需要的之間會出現一種幸運的趨同現象。幾個月前,為了某個與本書無關的理由,我讀了兩位睿智作家—瑪麗蓮.羅賓遜,以及T.S.艾略特(T. S. Eliot)的文章。當時我正巧在認真重新評估我的上網時間,尤其是花在社群媒體上的時間。然後,寫這本書的點子開始在我腦袋裡連結起來。
羅賓遜在發表於一九九四年的〈清教徒與假道學〉一文裡,挑戰了許多人對清教徒的輕蔑態度(如今,「清教徒」不過是一種侮辱之詞),並對於他們所想的事、那些思考背後的理由,提出較寬容而準確的說明。下筆時,她突然想到,「我們談論或想起清教徒的方式,在我看來是一種可以用來討論所謂『清教徒主義』這個現象許多重要面向的模型。」也就是說,被我們說成是「清教徒式」的種種特徵—死板、心胸狹窄、愛下判斷—正是大家每次談起清教徒時所展現的特質。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大家對清教徒的態度是這麼的「清教徒」?「答案很簡單。」羅賓遜寫道。「這是個絕佳範例,指出我們有一種集體渴望—在缺乏相關知識或訊息的狀況下,去貶抑受人貶抑的事物—藉此得到回饋,也就是共享一種我們自知會得到社會認同的態度,並從中享受到快感。」這意思是說,我們譴責清教徒主義,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交談的對象會共享這種對清教徒的貶抑態度,也會贊同我們喚起這種感受。使用這個詞彙時,它和清教徒的行動、信念所代表的真相到底有無任何顯著關連性,一點都不重要。在這種狀況下,清教徒一詞不具任何意義,肯定也不符合史實。這個詞彙比較像是進入俱樂部的通關密語。
羅賓遜進一步評論說,這種使用方式「讓我們看到,這樣的共識可以多麼有效地封鎖對某個主題的探究」—這有可能是通篇最重要的論點。一個詞彙越能夠有效展現我得到某個團體的接納,我就越懶得再去檢驗我對這個詞彙的用法從任何一種標準來看到底算不算正當。所以,喜歡指控別人「像清教徒一樣」,會認真地力求盡可能不去理解真正的清教徒—也就是說,致力於不去思考。
羅賓遜的分析很敏銳,而且考量到這篇文章是在網路變成跨文化現象之前所寫的,更是難能可貴。思考讓人類無法「分享我們自知會得到社會認同的態度」—特別是在網路環境下,靠著「喜歡」、「讚」、「追蹤」和「加好友」,個人的態度要得到社會認可實在容易得多,而且馬上就能得到—既然如此,人為什麼要思考?
羅賓遜以一席提神醒腦的嚴肅評論來總結她的反省:在這種環境下,「未獲認可的觀點實際上會遭受不被理解的懲罰」。這不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人人有心刻意打壓異端的社會裡(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是確實如此),「反而只是追求共識的本能過度肥大所造成的後果」。如果你想要思考,你就必須縮減「過度肥大的追求共識本能」。然而,考量到那種本能之強大,親愛的讀者,你非常有可能不想去惹這個麻煩。
那種追求共識的本能,在我們的時代裡更加發揚光大,因為我們每天都在處理號稱是資訊、卻通常都是廢話的混亂洪流。這不是什麼新鮮事。T.S.艾略特在幾乎一個世紀前寫到一種現象,而他相信那是十九世紀的產物:「在這個時代,有這麼多事要去了解,又有這麼多知識領域以不同的意義來使用相同的字詞,每個人對於一大堆事情又都只了解一點點,以至於對任何人來說,我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說出口的話有幾分真實,都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讓我用不同字體來強調艾略特的結論——「在我們不了解或是了解得不夠多的時候,我們傾向總是用情緒來取代思維。」
這是另一種看來更加尖銳的想法。與其說它符合發言當時的狀況,不如說是更適合我們這個時代的診斷。而且這個想法跟羅賓遜的分析吻合得讓人心驚。致力於不去了解、不去思考某些事,以便「共享一種我們自知會得到社會認同的態度,並從中享受到快感」的人,在其追求共識的本能得到滿足時,會欣喜若狂—當這種本能受挫時,就會心生憤怒。社會紐結(Social bonding)是透過共同分享的情緒所鞏固,共享的情緒又會滋生社會紐結。這是一個排除反省的回饋循環。羅賓遜與艾略特解釋了許多線上持續不斷的狂亂激憤(agita)。在我看來,離線的生活也越來越相似了。
任何自稱沒被這些力量影響、形塑的人,幾乎可以確定是在自欺欺人。人類的天生構造,就是無法對社交世界的波折和波動淡然處之。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對於隨波逐流還有一丁點的不情願。真心想要思考的人,必須發展出一些策略來辨識最微妙的社會壓力,對抗來自內團體(ingroup)的牽引,以及對於外團體(outgroup)的厭惡。想要思考的人必須練習保持耐性,還要駕馭恐懼。
◎隸屬多重社群
我相信我可以幫助想要改善思考的人,但是—在更進一步以前,我得先說—不,這不是因為我來自學術界。我的學術界同僚,整體而言,也跟教育程度沒那麼高的普通路人一樣,不情願從事真正的省思。學術界人士一向具有異常嚴重的順應期待問題;你要證明自己配得上學術圈,主要辦法之一就是拿到非常好的成績,而你要是不說些指導教授愛聽的話,你就拿不到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不,學術生活對人的思考沒多大幫助,或至少沒有幫到我推薦的那種「思考」。學術生活幫助人累積一套知識,讓人學習並使用某些經過認可的修辭策略,它需要很好的記性、智性靈活度之類的東西,但學術生活裡沒多少事情會要求你質疑自己的衝動反應—即使你的學術生涯就是在研究衝動反應也一樣,如同前面康納曼所說的。
然而,身為老師,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在大學教書已經三十年以上,整體而言,大學教育就是個絕佳的思考實驗室。我的大多數學生都知道自己相信什麼,也想為其辯護,但他們也明白自己還有很多要學(世人普遍以為,大學生是一群自以為無所不知、其實是朽木不可雕的傲慢屁孩—這和我的教學經驗有相當大出入。我知道有這種人,但不常見,而且現在這種人不會比我剛入行的時候還來得多)。向學生們證明他們的信念不必然是錯的,只是他們沒能好好為其辯護、沒有了解自己最根本的邏輯、沒有掌握到向「可疑的他者」推薦自身觀點時怎麼做會最好,是非常值回票價的事。我估計我至今大概批改過一萬五千篇的學生作業,應該有資格說我見識過怎麼正確論證和論證出錯的所有方式。
這種長期累積的經驗在思考「思考」這件事之上確實很寶貴,更加寶貴的是我參與過各種社群,而這些社群經常彼此意見不同。我是個學者,卻也是個基督徒。聽到學者談論基督徒的時候,我的典型感想是:不是這樣的,我不相信你了解那些你自認為不同意的那些人。而當我聽到基督徒談論學者的時候,也有完全一樣的想法。我花了幾十年注意這些非常普遍的誤解,設法搞清楚它們是怎麼產生的,並尋求辦法來糾正這些錯誤。
三十年前,人類學家蘇珊.佛蘭德.哈定(Susan Friend Harding)開始認真研究美國基督教的基要主義派(Fundamentalism)。這個研究最後成就了一份卓越的報導:《傑瑞.法威爾之書:基要主義派的語言與政治》。然後她發現,她的同僚對她的研究興趣非常不解:怎麼會有人想要研究一群如此怪異又顯然不討喜的人?哈定寫道:「實際上,一直不斷有人問我:妳現在是或曾經是『重生的基督徒』嗎?」相信有許多讀者可以看出來哈定在狡黠地呼應一九五○年代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問過數百人的那個問題:「你現在是或曾經是共產黨員嗎?」
一九九一年,哈定針對這個現象出版了一篇力道強勁的論文。她提問,人類學家不是本來就應該對跟自己不同的文化結構與習俗感興趣嗎?那麼,當這種「不同」就在你家隔壁、可以跟你一起在同一場選舉裡投票,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類學家排斥研究它?哈定的論文標題是〈再現基要主義派:「令人反感的文化他者」問題〉。我們在接下來的內容裡,將會有理由使用「令人反感的文化他者」(Repugnant Cultural Other)一詞。事實上,這個詞彙出現的次數頻繁到最好給它一個首字母略稱:RCO。
正如我先前所暗示的,如果基要主義派或福音教派基督徒對於世俗的學界人士來說,很容易被當成RCO,反過來說也一樣。自從我成年以來,一直在這種互相猜疑之中努力向前航行。如今,我生活中的政治環境,整體來說,已經承襲了過去我在那些彼此敵對的較小型社群裡經常看到的可悲特徵:刻意的不求甚解、有毒性的疑心。現在每個人似乎都有個RCO,而每個人的RCO都在社群媒體上的某處。我們也許能夠躲開、不去傾聽我們的RCO,但我們都必須面對這個領悟:他或她就在那裡,可能就在兩個房間之外向我們叫囂著。
這種狀況極端不健康,因為它妨礙我們去體認其他人是我們的同胞—甚至當他們是我們名符其實的鄰人時也一樣。「那邊那個人既是個他者,又令人反感」,如果我滿腦子都在想著這種事,可能永遠不會發覺我最愛的電視節目也是他的最愛;我們喜歡的書有些是一樣的,雖然理由不盡然相同;我們都知道照顧長期臥病的心愛之人是什麼感覺……這一切都表示,我可能太容易就忘記政治、社會與宗教差異並非人類經驗的全部。RCO冰冷的分裂邏輯讓我們所有人變得貧乏,使我們更接近政治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那種「每個人對抗每個人」的原始狀態。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應該做得更好。我也相信我幫得上忙,這有部分要歸功於我在互相敵對的社群之間調停多年的經驗。我知道要跟在某些方面迥異於我的人為共同的理想而奮鬥是什麼感覺;我知道這樣的經驗能夠怎麼擴展我對世界的了解;我知道它們能夠如何逼使我去對抗我狹隘的視野,以及我簡化思考過程(有時根本想都不想)的傾向。還有,在此要向康納曼致歉,我是真心相信我這些年來在思考方面有長足的進步,而且我不想獨善其身。
◎迂迴勝於直接
接下來在 本書中所談的,有許多只是診斷性質,也有很好的理由如此。許多年前,我有過一次胸痛的經驗,好幾個醫生都沒辦法確定問題出在哪裡。我規律運動,心臟似乎也很健康,沒什麼地方明顯不對勁。但那種痛一直反覆發作,把我嚇壞了。最後,有個醫生進一步追究,發現我在胸痛開始之前,有過拖很久的嚴重咳嗽問題。看來那陣子的咳嗽拉傷了我胸部的一條肌肉,胸痛的來源就在這裡,而我開始擔憂這種痛楚之後導致的焦慮又使得肌肉更緊張,因此加強了痛楚,然後又讓我更焦慮。
這是典型的惡性循環強化。當我問醫生他覺得哪種療法最好,他回答:「診斷本身就是治療。現在你知道你沒有危及生命的疾病,你就不會那麼擔心,心裡的壓力減輕,意思是胸部肌肉的壓力也會比較少,於是這些肌肉就有機會痊癒了。」
同樣的道理,儘管我會在接下來的篇章提供積極的處方,但事實上,光是知道有哪些力量在我們身上起作用,使我們逃避真正進行反省、對自身狀況作精確診斷,就是治療的第一道程序了。
此外,我也很樂意提供你一套恆常不變的指導原則,讓你可以一步步遵循,變成更善於思考的人—但思考不是這樣一回事。我再強調一次,科學是我們的朋友,但思考在本質上是一門藝術,而藝術素有不受規則束縛的「惡名」—但仍有一些有效的舉措可以遵循,而我會在接下的內容裡介紹這些舉措(說實話,在說明買車這件事的時候,我幾乎已全都暗示在其中了)。總之,不論誰最先說出「快樂不是我們能夠直接追求的目標,只能靠著專注於其他美好事物來達成」這番話,把它套用到「思考」上也一樣正確。
音樂家布萊安.伊諾(Brian Eno)和藝術家彼得.史密特(Peter Schmidt)在一九七五年創造了一套奇特的工具。那是一組包含獨特指示的卡片:「將錯誤視為你的潛藏意圖」、「問你的身體」、「改變樂曲的速度」等。這些字卡的用意,是要幫助在工作上碰到瓶頸的藝術家(尤其是音樂家)。伊諾和史密特把他們的牌卡稱為「迂迴策略卡」(Oblique Strategies),因為他們知道當藝術家卡住的時候,直接去解決問題,每每無異於提油救火。同樣地,有時候只有把注意力轉向思考以外的事物,你才能更善於思考。所以,接下來的內容,有時是軼事趣聞,有時迂迴纏繞—但最後我們總是會繞回糟糕的思考會採取哪些形式,並發掘可以幫助我們更精通於養成此一最棘手藝術的習慣。這不是容易的事—問題有一部分就在於此。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