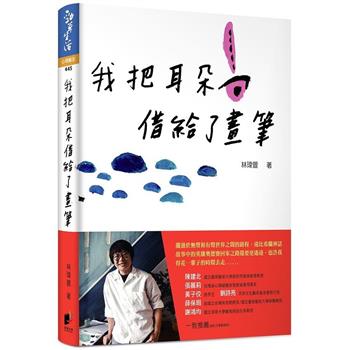Chapter1 消失的85%分貝
1-1 我家的柏拉圖洞穴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經說過一個洞穴的比喻,這是一個關於追求真知的比喻,故事是這樣的:有一群囚犯在洞穴裡,每一個人的雙手和雙腳都被縛,背對著洞穴出口,只能往前面看。前方有座牆壁,而在他們後面有枝蠟燭,映射出來的光源投在牆上,出現了影子。但因為每個人都被束縛著無法回頭,久而久之竟然以為牆上投射出的影子是真實的世界。直到有一天,有一個囚犯掙脫了,回頭一看,走出洞穴接觸到陽光。
這個故事令我想到的是在父母的保護之下形成的安全洞穴,讓我們在生活上無憂無慮,不被外界真實的現實樣貌影響,生活太封閉也是會欺騙我們對外面的認知,這讓我對所謂的「真實」世界感到好奇,也許柏拉圖有他想闡述的理型世界,但對我來說,縱使身在洞穴內,我也不害怕,更不想麻痺自己的感官,因為尋找自己和家人,擁有真實的接觸,就必須先走出封閉的狀態。
︱繞著我轉呀轉的母親︱
媽媽是一個對婚姻和家庭充滿憧憬的女孩,正值青春年華的二十歲, 與爸爸相識戀愛進而結婚, 住在苗栗縣南庄鄉的大家庭。我,是爺爺家的第一個孫女,整個大家庭非常開心,我也備受呵護。在一歲時,家人發現我安靜不語,直到醫生宣告我聽不見的消息,更讓全家人深受打擊,媽媽問醫生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我們家族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例子。有好長一段時間,媽媽不斷地自責與愧疚,一直回想懷孕過程有沒有忽略任何該注意的細節,但仍找不出原因。在醫療資訊尚未精密化的年代,爸媽努力去打聽資源,尋求更積極的做法,甚至求神問卜,盡一切補救我的聽力。聽說「穿耳洞」就可以聽得見聲音,彷彿找到一線希望,抱著試試看的祈求心情,帶我去穿耳洞。但依舊聽不見,卻多了金圓形的耳環,看起來很美,卻又是沉重的失望! 記得那時的我很討厭戴耳環,想盡辦法要把耳環弄掉,媽媽看起來很生氣,被臭罵了一頓。小小的我卻不知道原來是有原因的,不知道家人為什麼會如此地生氣。
父母真真切切愛的聲音,無情的在空氣中消失。
之後,弟弟妹妹相繼出生。爸爸因為在海上工作,正值壯年的生命連接的是世界上各大貿易港口。媽媽都是一個人照顧我們四個小孩,一邊持家、一邊等待爸爸的歸來,是心力強大的女人。
打從有記憶以來,除了與母親相依偎,身邊總有許多親人照顧我、陪我玩,姑姑、表哥、表姊、堂姐等,唯獨爸爸,也許當時的他正在巴拿馬運河的某處,或是正在模里西斯的港口補給,所以小時候對爸爸的回憶一直很模糊。爸爸帶來滿足物質上的欲望,在生活上卻是遙遠的距離,少少參與我的世界,但回憶爸爸卻是很快樂的,因為和各種舶來品相連結。
在生活上,媽媽不僅要扮演父親嚴厲的角色,更要適時溫柔地安撫孩子,這對一個先生不在身邊,獨立養育孩子的母親來說,的確很不容易。每次想起媽媽一個人在生活上面對我們四個孩子的辛勞與照顧,十分揪心,充滿疼惜與感激。在醫療資訊尚未發達的年代,沒有人告訴我的父母,該怎樣養育一個聽障孩子? 要怎麼知道我想要什麼或需要什麼? 要怎麼知道我半夜哭又或是那裡不舒服呢? 還有要怎麼告訴我,我是爸媽的寶貝呢? 這對父母來說是多麼艱難的功課,無法想像,在照顧我的這段歲月裡,又是怎麼樣堅持的信念,一路養育我到長大。爸媽緊緊地擁著我,我雖聽不見愛的呢喃,但在爸媽臉上那真切的疼惜,便深刻地表現出對我的愛,這就是「擁抱的語言」,讓我感受到在父母的懷抱裡是多麼地溫暖,得到無比的安全感。而我從小與媽媽非常親密,常常撫觸媽媽的聲帶,感受聲音的振幅,閱讀嘴唇,想像字型。蔣勳說:「身體的記憶,影響於無形,卻久遠而深刻。」
︱航海家父親︱
從小到大一直覺得爸爸的工作很酷, 很羨慕他可以環遊世界。在世界知名海運公司擔任輪機長,走環球航線,常年都在海外, 一年回國一、兩次, 若有放長假就會回來家裡待上幾個星期。有時,工作繁多忙碌而無法下船回家,媽媽就會帶著我們去基隆港或者高雄港,到港埠與父親相見。一整列的貨櫃以及正在吊卸的起重機場景在我面前展開,我最喜歡看機台把綠色長方形的貨櫃移動組合、排列, 像在堆樂高玩具般, 堆疊得高高的。爸爸帶著我們走上細細長長的舷梯到甲板上的白色正方形建築物裡,讓我們一探艙內,裡頭有分層,最上面的是駕駛艙,另外還有機艙的控制室、廚房和餐廳等等。艙裡空間的走廊既狹窄又彎曲,每一間的門又長得很像,小小的我們深怕會迷路,一路緊緊地跟著爸爸到房間。 裡頭有沙發、辦公桌、浴室、床和喝不完的可樂,還有黑邊橢圓形的窗戶,可以看到大海,這是獨一無二的海景套房。
爸爸那次還在浴缸裡倒有貼芝麻街大鳥圖案的泡泡浴精,神奇地在水面上直冒出綿白色的泡沫,令我和妹妹看得入神,興奮地跳進浴缸裡讓泡沫覆蓋著全身、把泡泡堆在頭上,在裡面玩很久直到媽媽不斷地催促才起身。
父親在海外的生活經驗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也造就了我喜歡探索、喜歡新奇的性格。長大之後仍繼續保持好奇心,發掘未知的事物並樂在其中,即使面對未知仍帶點不安的心理,但我喜歡享受新鮮事物帶來的趣味多於熟悉的事物。同時也深切影響我在繪畫中不斷的創新,關注我所喜歡的主題,研究線條、筆觸要怎麼畫等等,在繪畫的領域裡,流著航海家父親的血液去冒險和追尋那未知的可能。雖然在畫布上,當要下第一筆時非常困難,會猶豫很久,這時我要解決的第一件事,就是克服「習慣」的安逸心理,我相信最終還是會畫出來,我需要做的是去振動想像力的翅膀。事物有時候不一定是「新」的,它可能是一直存在的事情,所以是自己沒有注意到的部分,從熟悉之處不厭其煩地再去發掘,搶在未曾接觸之前多些體驗。
聽人家說國外的月亮很圓又很大,爸爸是否也會站在甲板上靜靜地看著海面上的月亮呢? 在浩瀚無垠的天空,布滿了閃耀般的星星,閃閃的光亮只有在黑暗的夜裡才會出現,流星劃過天際到海裡的消逝也看到了嗎? 是否也看見海豚在天空下滾著海浪跳躍著? 遇到狂風暴雨的大浪把船弄得搖搖晃晃,不知道爸爸的心情是什麼樣的呢? 對爸爸的印象是一個在大海盡頭很遙遠的航海家。
︱「吾愛」航空信與巧克力︱
爸爸在不同國家時常稍來淡藍色條紋的航空信件給媽媽。媽媽說信封要坐好久的飛機,要一周的時間,有時十天半個月、甚至更長才能送達我們手上。我們聽著媽媽說爸爸在國外看到的風景與近況,以及對我們的關心問候。記得媽媽的信上讀的第一個開頭字是「吾愛」,覺得很美,字裏行間透露出愛情的甜蜜!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擁有自己的信呢,一份屬於我跟爸爸的祕密。
當我上小學讀書識字時,爸爸特別寫信給我,我喜出望外地打開信,紙上的注音符號穿插簡單的文字,努力地讓我直接和他有生活上的連接,感受到爸爸把滿溢的思念寄託在沉甸甸的藍色信件裡。書信往返雖然耗時且紙幅有限,但正因為有所限制,更顯珍貴。
爸爸每次回家,我們像是久久一次看到聖誕老公公般地開心,爸爸總是帶回很多當時非常炫的玩具,以及各國各式口味的巧克力做為我們小時候的零食。包裝盒外散發出濃濃的巧克力香味,聞起來好香,我們總迫不及待拆開包裝,爭先恐後地挑選喜歡的造型;甜甜的,吃起來有香甜潤滑的口感,濃郁的可可味再加上堅果、葡萄乾和牛奶香,一口接一口,很令人意猶未盡的甜點。這是我們全家人快樂的來源,令人充滿活力,沒有人能抗拒巧克力的魅力,而且常很快地便在一兩天內吃完。爸爸每次買就一打,深怕滿足不了嘴饞的我們。如今在商店架上看到各式各樣的巧克力,總是勾起爸爸買給我們的童年回憶,心裡有如巧克力的幸福濃化開來,後來常跟朋友分享我的事情,忍不住想炫耀小時候有吃過國外這個或那個牌子的巧克力。我能體會為何記憶會歷久彌新,就如同扇貝型的海綿蛋糕「瑪德蓮」 * 也曾勾起普魯斯特的童年追憶,這種包含味蕾的記憶一經召喚,眼前會馬上浮出一幕幕的影像呢!
在生活物質上,可以感受到父親的分享與愛,滿足了我們對甜點、玩具的想像並且還能擁有它們。
1-2 洋式style的惠美教育
「在聲音尚未開啟之前,我的世界是安靜。」
︱移動的風景︱
1979 年,一歲的我正值牙牙學語的階段,父母察覺到我對周遭聲音毫無反應,尤其被放鞭炮的紙片如雪花紛飛的畫面吸引定住,沒有立即摀住耳朵迅速地躲在一旁,和一般小孩的反應有所不同。隨即帶我去台北榮總及台北鐵路醫院做聽力檢查。爸媽知道我聽不到聲音後並沒有沮喪太久,收拾心情後開始不斷地尋找任何一個能讓我有機會與這世界溝通連接的可能。多次徵詢醫生何處有對聽力受損兒童合適的教學單位時,鐵路醫院建議小孩四歲以後由於腦神經發育較好了,可至台北「惠美聽力語言中心」上課,他們有提供口語訓練及讀唇教學。 爸媽對惠美教育的理念十分認同與支持,唇語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教學方式,所以不論多遠、多難、多貴,都堅持帶我去接受聽力語言中心的指導,讓我能夠學會聽與說的技巧。惠美聽力語言中心是由李郭惠美院長在民國56 年所創立,教授口語並訓練聽障兒童。創設的主因是院長的兒子本身也是聽障,之前居住美國,有感於台灣聽障兒童教育資源貧乏,因此回台設立語言中心,希望推動學前教育,鼓勵聽障兒童接受口語訓練,之後能夠回歸主流教育體制內,進入普通班上課學習,也能順利地與一般人對話,持續練習讀唇與發音說話。
在惠美上課之前,爸媽竭盡所能地尋求任何補救的機會,這段時間都先在家裡自己教導,一邊摸索教材、一邊和我說說話,鼓勵我發出聲音。一字一字地灌溉我那寂靜的耳朵,直到聲音的光劃破了沉默。爸爸回憶說,說來也真神奇,我去惠美上課的第一天就會叫爸爸、媽媽了。我說的話對家人來說是多麼地平常,卻是遙不可及的期盼,讓家人覺得當時自學教育的方式是正確的。等到我4歲時,才去惠美語言中心接受教育,為了方便就讀,第一年借住台北親戚家,第二年有了妹妹,我們就搬回新竹縣的外婆家,妹妹托給外婆照顧,我和媽媽則每天一大早六點出門,從新竹縣搭火車到台北上課,中午下課回到外婆家已經是下午兩點後,風雨無阻地不放棄任何一次學習。
鄉下的清晨,微光暗色的天空,從外婆家騎一段鄉間小路到竹北火車站,這是個很小的站,我們搭乘固定的班次且是有藍色車體和白色線條的復興號,復古綠的雙人長椅,窗戶則是從下方一扣就可以往上拉開的設計,走道上方有一排電扇,夏天時一直轉動。喜歡趴著窗邊吹著風,看著兩旁風景被時速的推進而移動,刷拋到後面消失。有時不小心睡著,醒來就已經到台北車站了,我們在後站下車,當時的惠美語言訓練中心就在中山北路的那段路上,放眼望去全面延伸的是正在擴建新鐵路和新馬路的景象。媽媽緊抓著我的小手沿著舊鐵軌旁走一小段之後,再拐進小巷子裡就到惠美中心。
整棟建築分為一樓小班、二樓中大班, 一班約有10 個人,桌椅分成前後兩排成環型狀,這樣的設計是為了讓我們都能閱讀到老師唇形和發音的字詞;我們胸前掛著像盒子一樣的口袋型接收器,端口連接Y 型線耳罩式的耳機蓋住耳朵,搭配老師的麥克風,盒子將聲音輸出送至耳罩式耳機,把接收外面的聲音轉成電子訊號以類比式電路放大輸出。
家人則是坐在後面,除了陪伴以外,也觀摩老師如何教我們發音的方式,惠美希望除了上課時間之外,日常生活裡也能持續有互動式的交談,聽障孩童是透過不斷地模仿才會記住發音。
︱視覺至上——用眼睛去學說話︱
在還沒有開始戴助聽器前,一直是帶著眼睛去了解這世界。
在惠美語言中心上口語訓練之前,媽媽試著找方法教我發音,對著我說話。直到上課後,就將所教的內容及技巧幫助我積極地應用在日常生活裡,引用更多的詞彙,從家人「爸爸」 、 「媽媽」的單字,以及周遭的物體,如:「電冰箱」 、 「電燈」 、 「光」 、 「門」等等的名稱。聽力正常的人只要聽過一次就會記得,但我得對著物體,重覆朗誦好幾次才能記得住,媽媽花很多時間與耐心陪著我,在書上和生活的事物中學習認識,加強我的記憶。若不積極地發聲說話與對話,會讓我的聲帶退化及認知能力淡化,如此一來就得要重頭開始學習。爸媽看著我從可以用簡單的句子清楚表達,並且能夠選擇正確的字詞來表達個人的重點,到能夠完整講出一句話,進一步與家人建立對話的關係,讓他們感到十分欣慰。
在惠美語言中心的課堂上,老師是先教我們認識在黑板上寫的注音符號的字形,「看」老師嘴型發出來的字來「讀」取字的意思。常常覺得難以置信,我們是如何從不會說一個字到可以開口並說話到長大呢? 我還記得老師上課講話的嘴型是誇張的,那是因為我們要透過嘴形、面部肌肉和舌頭動作去閱讀來了解唇形的張力會牽動五官的那些表情,有滑稽、有趣、扭曲……等。如同默劇,猜想對方是要表達什麼意思。
媽媽一再地告訴我,如果上課時聽不清楚老師說什麼的話要舉手發問,或者別人說話時聽不懂,要直接地告訴對方我聽不見,請對方再說一次。利用預習和複習,以及溝通技巧的訓練,奠定我往後在求學與社交的環境適應力。 剛開始從不會說話、不會聽,到現在能聽會說的成果,這些過程點滴在心頭。母親所給予我最珍貴的,就是放手,讓我學會獨立。
「聲音」對小小的我來說是很遙遠的星球,老師試著引導我去依循著聲波,找尋聲音的存在,並把它放到我前面。噢! 原來,聲音是一直存在,是用「眼睛」去觀看並專注它所帶來的振動與張力。
透過眼睛觀看,我學會了「感.受」。
37 個注音符號「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ㄐ ㄑ ㄒㄓ 彳 ㄕ ㄖ ㄗ ㄘ ㄙ ㄚ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ㄢ ㄣ ㄤ ㄥ ㄦ ㄧ ㄨㄩ 」有幾個音對我來說不易發音,且同時要讀唇語,有時候覺得兩個器官沒辦法同時一起用。「ㄐ 、ㄑ、 ㄒ、 ㄓ、 彳、 ㄕ、 ㄗ、 ㄘ、ㄙ、 ㄩ」這些字音的聲音很細又很小聲,嘴形的樣子幾乎差不多,很難辨別, 無法順利讀出它的音, 也聽不出來它的音是什麼。時常覺得這遙遠星球的聲音很陌生,不知道要怎麼試著模仿它的聲音。至今,仍是抓不住它的音準,經常被媽媽糾正。如「ㄅ、ㄆ、ㄇ、ㄈ 」的音比較大聲,嘴形上的張力也比較大,所以看幾次就模仿發音幾次,在練習之下就能抓住這個音。爸媽為了讓我順利地發音,窮盡一切辦法使出戲劇化的手勢、誇張的嘴形和借助其它的工具,如「ㄎ」就喝了不少水來練習,在嘴裡念「ㄎ」,氣則會把嘴裡的水噴出來,像是「ㄍ」 ,媽媽會拉我的手摸她的喉嚨,用手去感受媽媽的喉嚨裡發出的聲音。運用視覺和觸覺的感知去強化我對注音符號的記憶,並不停地講話,講到對的音,家人會突然說「對! 就是這樣的發音。」持續地逼練口腔內的舌頭、牙齒且反覆練習達到自動化的記住。在過程中,時間是緩慢的,常常無法順利流暢地讀唇和說話。
1-1 我家的柏拉圖洞穴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經說過一個洞穴的比喻,這是一個關於追求真知的比喻,故事是這樣的:有一群囚犯在洞穴裡,每一個人的雙手和雙腳都被縛,背對著洞穴出口,只能往前面看。前方有座牆壁,而在他們後面有枝蠟燭,映射出來的光源投在牆上,出現了影子。但因為每個人都被束縛著無法回頭,久而久之竟然以為牆上投射出的影子是真實的世界。直到有一天,有一個囚犯掙脫了,回頭一看,走出洞穴接觸到陽光。
這個故事令我想到的是在父母的保護之下形成的安全洞穴,讓我們在生活上無憂無慮,不被外界真實的現實樣貌影響,生活太封閉也是會欺騙我們對外面的認知,這讓我對所謂的「真實」世界感到好奇,也許柏拉圖有他想闡述的理型世界,但對我來說,縱使身在洞穴內,我也不害怕,更不想麻痺自己的感官,因為尋找自己和家人,擁有真實的接觸,就必須先走出封閉的狀態。
︱繞著我轉呀轉的母親︱
媽媽是一個對婚姻和家庭充滿憧憬的女孩,正值青春年華的二十歲, 與爸爸相識戀愛進而結婚, 住在苗栗縣南庄鄉的大家庭。我,是爺爺家的第一個孫女,整個大家庭非常開心,我也備受呵護。在一歲時,家人發現我安靜不語,直到醫生宣告我聽不見的消息,更讓全家人深受打擊,媽媽問醫生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我們家族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例子。有好長一段時間,媽媽不斷地自責與愧疚,一直回想懷孕過程有沒有忽略任何該注意的細節,但仍找不出原因。在醫療資訊尚未精密化的年代,爸媽努力去打聽資源,尋求更積極的做法,甚至求神問卜,盡一切補救我的聽力。聽說「穿耳洞」就可以聽得見聲音,彷彿找到一線希望,抱著試試看的祈求心情,帶我去穿耳洞。但依舊聽不見,卻多了金圓形的耳環,看起來很美,卻又是沉重的失望! 記得那時的我很討厭戴耳環,想盡辦法要把耳環弄掉,媽媽看起來很生氣,被臭罵了一頓。小小的我卻不知道原來是有原因的,不知道家人為什麼會如此地生氣。
父母真真切切愛的聲音,無情的在空氣中消失。
之後,弟弟妹妹相繼出生。爸爸因為在海上工作,正值壯年的生命連接的是世界上各大貿易港口。媽媽都是一個人照顧我們四個小孩,一邊持家、一邊等待爸爸的歸來,是心力強大的女人。
打從有記憶以來,除了與母親相依偎,身邊總有許多親人照顧我、陪我玩,姑姑、表哥、表姊、堂姐等,唯獨爸爸,也許當時的他正在巴拿馬運河的某處,或是正在模里西斯的港口補給,所以小時候對爸爸的回憶一直很模糊。爸爸帶來滿足物質上的欲望,在生活上卻是遙遠的距離,少少參與我的世界,但回憶爸爸卻是很快樂的,因為和各種舶來品相連結。
在生活上,媽媽不僅要扮演父親嚴厲的角色,更要適時溫柔地安撫孩子,這對一個先生不在身邊,獨立養育孩子的母親來說,的確很不容易。每次想起媽媽一個人在生活上面對我們四個孩子的辛勞與照顧,十分揪心,充滿疼惜與感激。在醫療資訊尚未發達的年代,沒有人告訴我的父母,該怎樣養育一個聽障孩子? 要怎麼知道我想要什麼或需要什麼? 要怎麼知道我半夜哭又或是那裡不舒服呢? 還有要怎麼告訴我,我是爸媽的寶貝呢? 這對父母來說是多麼艱難的功課,無法想像,在照顧我的這段歲月裡,又是怎麼樣堅持的信念,一路養育我到長大。爸媽緊緊地擁著我,我雖聽不見愛的呢喃,但在爸媽臉上那真切的疼惜,便深刻地表現出對我的愛,這就是「擁抱的語言」,讓我感受到在父母的懷抱裡是多麼地溫暖,得到無比的安全感。而我從小與媽媽非常親密,常常撫觸媽媽的聲帶,感受聲音的振幅,閱讀嘴唇,想像字型。蔣勳說:「身體的記憶,影響於無形,卻久遠而深刻。」
︱航海家父親︱
從小到大一直覺得爸爸的工作很酷, 很羨慕他可以環遊世界。在世界知名海運公司擔任輪機長,走環球航線,常年都在海外, 一年回國一、兩次, 若有放長假就會回來家裡待上幾個星期。有時,工作繁多忙碌而無法下船回家,媽媽就會帶著我們去基隆港或者高雄港,到港埠與父親相見。一整列的貨櫃以及正在吊卸的起重機場景在我面前展開,我最喜歡看機台把綠色長方形的貨櫃移動組合、排列, 像在堆樂高玩具般, 堆疊得高高的。爸爸帶著我們走上細細長長的舷梯到甲板上的白色正方形建築物裡,讓我們一探艙內,裡頭有分層,最上面的是駕駛艙,另外還有機艙的控制室、廚房和餐廳等等。艙裡空間的走廊既狹窄又彎曲,每一間的門又長得很像,小小的我們深怕會迷路,一路緊緊地跟著爸爸到房間。 裡頭有沙發、辦公桌、浴室、床和喝不完的可樂,還有黑邊橢圓形的窗戶,可以看到大海,這是獨一無二的海景套房。
爸爸那次還在浴缸裡倒有貼芝麻街大鳥圖案的泡泡浴精,神奇地在水面上直冒出綿白色的泡沫,令我和妹妹看得入神,興奮地跳進浴缸裡讓泡沫覆蓋著全身、把泡泡堆在頭上,在裡面玩很久直到媽媽不斷地催促才起身。
父親在海外的生活經驗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也造就了我喜歡探索、喜歡新奇的性格。長大之後仍繼續保持好奇心,發掘未知的事物並樂在其中,即使面對未知仍帶點不安的心理,但我喜歡享受新鮮事物帶來的趣味多於熟悉的事物。同時也深切影響我在繪畫中不斷的創新,關注我所喜歡的主題,研究線條、筆觸要怎麼畫等等,在繪畫的領域裡,流著航海家父親的血液去冒險和追尋那未知的可能。雖然在畫布上,當要下第一筆時非常困難,會猶豫很久,這時我要解決的第一件事,就是克服「習慣」的安逸心理,我相信最終還是會畫出來,我需要做的是去振動想像力的翅膀。事物有時候不一定是「新」的,它可能是一直存在的事情,所以是自己沒有注意到的部分,從熟悉之處不厭其煩地再去發掘,搶在未曾接觸之前多些體驗。
聽人家說國外的月亮很圓又很大,爸爸是否也會站在甲板上靜靜地看著海面上的月亮呢? 在浩瀚無垠的天空,布滿了閃耀般的星星,閃閃的光亮只有在黑暗的夜裡才會出現,流星劃過天際到海裡的消逝也看到了嗎? 是否也看見海豚在天空下滾著海浪跳躍著? 遇到狂風暴雨的大浪把船弄得搖搖晃晃,不知道爸爸的心情是什麼樣的呢? 對爸爸的印象是一個在大海盡頭很遙遠的航海家。
︱「吾愛」航空信與巧克力︱
爸爸在不同國家時常稍來淡藍色條紋的航空信件給媽媽。媽媽說信封要坐好久的飛機,要一周的時間,有時十天半個月、甚至更長才能送達我們手上。我們聽著媽媽說爸爸在國外看到的風景與近況,以及對我們的關心問候。記得媽媽的信上讀的第一個開頭字是「吾愛」,覺得很美,字裏行間透露出愛情的甜蜜!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擁有自己的信呢,一份屬於我跟爸爸的祕密。
當我上小學讀書識字時,爸爸特別寫信給我,我喜出望外地打開信,紙上的注音符號穿插簡單的文字,努力地讓我直接和他有生活上的連接,感受到爸爸把滿溢的思念寄託在沉甸甸的藍色信件裡。書信往返雖然耗時且紙幅有限,但正因為有所限制,更顯珍貴。
爸爸每次回家,我們像是久久一次看到聖誕老公公般地開心,爸爸總是帶回很多當時非常炫的玩具,以及各國各式口味的巧克力做為我們小時候的零食。包裝盒外散發出濃濃的巧克力香味,聞起來好香,我們總迫不及待拆開包裝,爭先恐後地挑選喜歡的造型;甜甜的,吃起來有香甜潤滑的口感,濃郁的可可味再加上堅果、葡萄乾和牛奶香,一口接一口,很令人意猶未盡的甜點。這是我們全家人快樂的來源,令人充滿活力,沒有人能抗拒巧克力的魅力,而且常很快地便在一兩天內吃完。爸爸每次買就一打,深怕滿足不了嘴饞的我們。如今在商店架上看到各式各樣的巧克力,總是勾起爸爸買給我們的童年回憶,心裡有如巧克力的幸福濃化開來,後來常跟朋友分享我的事情,忍不住想炫耀小時候有吃過國外這個或那個牌子的巧克力。我能體會為何記憶會歷久彌新,就如同扇貝型的海綿蛋糕「瑪德蓮」 * 也曾勾起普魯斯特的童年追憶,這種包含味蕾的記憶一經召喚,眼前會馬上浮出一幕幕的影像呢!
在生活物質上,可以感受到父親的分享與愛,滿足了我們對甜點、玩具的想像並且還能擁有它們。
1-2 洋式style的惠美教育
「在聲音尚未開啟之前,我的世界是安靜。」
︱移動的風景︱
1979 年,一歲的我正值牙牙學語的階段,父母察覺到我對周遭聲音毫無反應,尤其被放鞭炮的紙片如雪花紛飛的畫面吸引定住,沒有立即摀住耳朵迅速地躲在一旁,和一般小孩的反應有所不同。隨即帶我去台北榮總及台北鐵路醫院做聽力檢查。爸媽知道我聽不到聲音後並沒有沮喪太久,收拾心情後開始不斷地尋找任何一個能讓我有機會與這世界溝通連接的可能。多次徵詢醫生何處有對聽力受損兒童合適的教學單位時,鐵路醫院建議小孩四歲以後由於腦神經發育較好了,可至台北「惠美聽力語言中心」上課,他們有提供口語訓練及讀唇教學。 爸媽對惠美教育的理念十分認同與支持,唇語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教學方式,所以不論多遠、多難、多貴,都堅持帶我去接受聽力語言中心的指導,讓我能夠學會聽與說的技巧。惠美聽力語言中心是由李郭惠美院長在民國56 年所創立,教授口語並訓練聽障兒童。創設的主因是院長的兒子本身也是聽障,之前居住美國,有感於台灣聽障兒童教育資源貧乏,因此回台設立語言中心,希望推動學前教育,鼓勵聽障兒童接受口語訓練,之後能夠回歸主流教育體制內,進入普通班上課學習,也能順利地與一般人對話,持續練習讀唇與發音說話。
在惠美上課之前,爸媽竭盡所能地尋求任何補救的機會,這段時間都先在家裡自己教導,一邊摸索教材、一邊和我說說話,鼓勵我發出聲音。一字一字地灌溉我那寂靜的耳朵,直到聲音的光劃破了沉默。爸爸回憶說,說來也真神奇,我去惠美上課的第一天就會叫爸爸、媽媽了。我說的話對家人來說是多麼地平常,卻是遙不可及的期盼,讓家人覺得當時自學教育的方式是正確的。等到我4歲時,才去惠美語言中心接受教育,為了方便就讀,第一年借住台北親戚家,第二年有了妹妹,我們就搬回新竹縣的外婆家,妹妹托給外婆照顧,我和媽媽則每天一大早六點出門,從新竹縣搭火車到台北上課,中午下課回到外婆家已經是下午兩點後,風雨無阻地不放棄任何一次學習。
鄉下的清晨,微光暗色的天空,從外婆家騎一段鄉間小路到竹北火車站,這是個很小的站,我們搭乘固定的班次且是有藍色車體和白色線條的復興號,復古綠的雙人長椅,窗戶則是從下方一扣就可以往上拉開的設計,走道上方有一排電扇,夏天時一直轉動。喜歡趴著窗邊吹著風,看著兩旁風景被時速的推進而移動,刷拋到後面消失。有時不小心睡著,醒來就已經到台北車站了,我們在後站下車,當時的惠美語言訓練中心就在中山北路的那段路上,放眼望去全面延伸的是正在擴建新鐵路和新馬路的景象。媽媽緊抓著我的小手沿著舊鐵軌旁走一小段之後,再拐進小巷子裡就到惠美中心。
整棟建築分為一樓小班、二樓中大班, 一班約有10 個人,桌椅分成前後兩排成環型狀,這樣的設計是為了讓我們都能閱讀到老師唇形和發音的字詞;我們胸前掛著像盒子一樣的口袋型接收器,端口連接Y 型線耳罩式的耳機蓋住耳朵,搭配老師的麥克風,盒子將聲音輸出送至耳罩式耳機,把接收外面的聲音轉成電子訊號以類比式電路放大輸出。
家人則是坐在後面,除了陪伴以外,也觀摩老師如何教我們發音的方式,惠美希望除了上課時間之外,日常生活裡也能持續有互動式的交談,聽障孩童是透過不斷地模仿才會記住發音。
︱視覺至上——用眼睛去學說話︱
在還沒有開始戴助聽器前,一直是帶著眼睛去了解這世界。
在惠美語言中心上口語訓練之前,媽媽試著找方法教我發音,對著我說話。直到上課後,就將所教的內容及技巧幫助我積極地應用在日常生活裡,引用更多的詞彙,從家人「爸爸」 、 「媽媽」的單字,以及周遭的物體,如:「電冰箱」 、 「電燈」 、 「光」 、 「門」等等的名稱。聽力正常的人只要聽過一次就會記得,但我得對著物體,重覆朗誦好幾次才能記得住,媽媽花很多時間與耐心陪著我,在書上和生活的事物中學習認識,加強我的記憶。若不積極地發聲說話與對話,會讓我的聲帶退化及認知能力淡化,如此一來就得要重頭開始學習。爸媽看著我從可以用簡單的句子清楚表達,並且能夠選擇正確的字詞來表達個人的重點,到能夠完整講出一句話,進一步與家人建立對話的關係,讓他們感到十分欣慰。
在惠美語言中心的課堂上,老師是先教我們認識在黑板上寫的注音符號的字形,「看」老師嘴型發出來的字來「讀」取字的意思。常常覺得難以置信,我們是如何從不會說一個字到可以開口並說話到長大呢? 我還記得老師上課講話的嘴型是誇張的,那是因為我們要透過嘴形、面部肌肉和舌頭動作去閱讀來了解唇形的張力會牽動五官的那些表情,有滑稽、有趣、扭曲……等。如同默劇,猜想對方是要表達什麼意思。
媽媽一再地告訴我,如果上課時聽不清楚老師說什麼的話要舉手發問,或者別人說話時聽不懂,要直接地告訴對方我聽不見,請對方再說一次。利用預習和複習,以及溝通技巧的訓練,奠定我往後在求學與社交的環境適應力。 剛開始從不會說話、不會聽,到現在能聽會說的成果,這些過程點滴在心頭。母親所給予我最珍貴的,就是放手,讓我學會獨立。
「聲音」對小小的我來說是很遙遠的星球,老師試著引導我去依循著聲波,找尋聲音的存在,並把它放到我前面。噢! 原來,聲音是一直存在,是用「眼睛」去觀看並專注它所帶來的振動與張力。
透過眼睛觀看,我學會了「感.受」。
37 個注音符號「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ㄐ ㄑ ㄒㄓ 彳 ㄕ ㄖ ㄗ ㄘ ㄙ ㄚ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ㄢ ㄣ ㄤ ㄥ ㄦ ㄧ ㄨㄩ 」有幾個音對我來說不易發音,且同時要讀唇語,有時候覺得兩個器官沒辦法同時一起用。「ㄐ 、ㄑ、 ㄒ、 ㄓ、 彳、 ㄕ、 ㄗ、 ㄘ、ㄙ、 ㄩ」這些字音的聲音很細又很小聲,嘴形的樣子幾乎差不多,很難辨別, 無法順利讀出它的音, 也聽不出來它的音是什麼。時常覺得這遙遠星球的聲音很陌生,不知道要怎麼試著模仿它的聲音。至今,仍是抓不住它的音準,經常被媽媽糾正。如「ㄅ、ㄆ、ㄇ、ㄈ 」的音比較大聲,嘴形上的張力也比較大,所以看幾次就模仿發音幾次,在練習之下就能抓住這個音。爸媽為了讓我順利地發音,窮盡一切辦法使出戲劇化的手勢、誇張的嘴形和借助其它的工具,如「ㄎ」就喝了不少水來練習,在嘴裡念「ㄎ」,氣則會把嘴裡的水噴出來,像是「ㄍ」 ,媽媽會拉我的手摸她的喉嚨,用手去感受媽媽的喉嚨裡發出的聲音。運用視覺和觸覺的感知去強化我對注音符號的記憶,並不停地講話,講到對的音,家人會突然說「對! 就是這樣的發音。」持續地逼練口腔內的舌頭、牙齒且反覆練習達到自動化的記住。在過程中,時間是緩慢的,常常無法順利流暢地讀唇和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