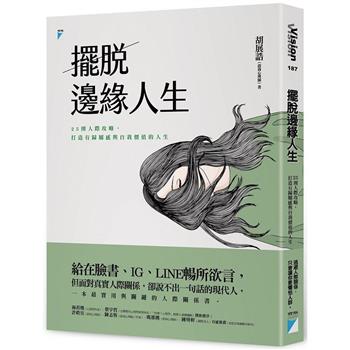遲來的理解──長期被漠視的選擇性緘默症
「我到底做錯什麼了?為什麼彤彤總是不和我說話?難道孩子這麼討厭我嗎?」珍妮老師有些自責,向主任說出自己的困惑。「我想,是否讓彤彤轉個班,或許讓其他老師來帶,對她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珍妮,你也知道在幼兒園,如果孩子動不動就換班級、換老師,這真的會給我帶來很大的困擾,因為其他家長也容易有樣學樣,到那個時候,我其他事情就都不用做了,每天來處理這些事情就好了。更何況,班上其他的孩子,你不是都帶得好好的嗎?我看你們長頸鹿班,整個上課氣氛非常的歡樂,有說有笑,而且班上小朋友的家長,也都對你讚譽有加。今天只是一個小女孩不說話,你真的不需要當作一回事啊!」
珍妮老師心裡遲疑了一下。其實,主任說的也挺有道理的。只是,自己這麼多年來,在教學上,還是非常在乎孩子和自己的關係。
「主任,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你說說看,只要我幫得上忙。」
「我想,是否讓彤彤有幾節課到別的教室裡試試?或是請其他老師來我們班上,帶幾個活動也行。」
「你這麼做的想法是⋯⋯」主任有些疑惑。
「我是想⋯⋯」珍妮老師說得有點吞吞吐吐,「或許,有機會讓我知道,彤彤在其他老師的班上,是否也是一樣不開口?」
「珍妮,你真的是好老師無誤。現在的老師只會頭痛、煩惱班上那些吵得半死,讓自己的課上不下去的孩子。哪有人還想要把安安靜靜、乖乖巧巧的孩子送出去?你啊,負責任是很好,但是,不要把許多的事情都攬在自己身上。很多事情不見得都是因為你的因素。」
「我想比較簡單的做法,就是請河馬班的潔西卡老師來你們班上,帶幾個活動交流交流,就當作跨班級一起上課,你也不要再想怎麼換老師、換班級。至於你想要觀察彤彤的說話,是否有所轉變。這一點,你倒是可以試試。」
珍妮稍微鬆了一口氣,也感謝主任的應允,讓自己有機會釐清自己和彤彤的關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是,自己也很擔心一種狀況,假如潔西卡老師來上課,但卻讓彤彤輕輕鬆鬆的開口說話了,那到時,自己就真的是尷尬、難堪了。
意中心理師說選擇性緘默症
選擇性緘默症是一種發生在兒童、青少年,屬於焦慮的一種疾病,並不是單純的害羞、內向、文靜就可以解釋。關於選擇性緘默症,在生活中、校園裡,這樣的孩子依然長期被漠視。對於許多人來說,選擇性緘默症這字眼,可能連聽過都沒聽過,或存在著偏見──認為是孩子自己不說話,相信時間久了,他應該自然而然就會開口說話。
我與選擇性緘默症的第一次接觸
十年多前,我第一次遇見選擇性緘默症孩子,只是,當年這名詞在臨床工作上很少被提及,更別說在校園裡被認識與關注。
那一天,一對父母帶著就讀幼兒園的女孩前來醫院,是經由醫師轉介過來,我準備為女孩進行智力測驗,以評估發展狀況。在施測前,我看著這女孩默默的蹲在治療室裡面,不說一句話。她的表情漠然、肢體僵硬,一動也不動。我明顯可以感受到女孩的焦慮與畏縮。
經驗法則告訴我,當下的智力測驗,女孩無法進行施測。縱使,勉為其難的施測,也一定會低估女孩的表現。
我當時得知女孩在家裡說話自然,但在幼兒園卻不開口。
我因此和父母先溝通,並說明需要先暫停智力測驗,而改採其他方式的理由,我也建議優先處理女孩的不說話行為。
幸運的是,當時女孩的父母對於早期療育有充分的概念,且非常的積極,對於我所設定的治療目標也欣然同意,並且對於後續建議的執行,也相當具有行動力。這些條件的組合,對女孩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與關鍵。
然而,有些案例卻往往因為父母或老師並不認為孩子在學校不說話,有什麼問題,而疏忽了這問題的嚴重性。讓許多緘默的孩子,錯過了早期療育介入的黃金時刻。
但我不忍苛責這些家長與老師,因為他們對於選擇性緘默症並不了解。畢竟長期以來,這樣的診斷名稱,許多人從未聽聞過,更何況是了解。
我很希望透過自己的臨床實務工作、校園服務、書寫與演講,讓選擇性緘默症的孩子能夠受到應有的關注。
只要每多一個人知道,每多一個人看見,那麼,就有機會讓這些孩子在教室裡的緘默行為被合理對待。當孩子的焦慮化解了,他們自然能開口說話。
留意能力的低估現象
面對選擇性緘默症孩子,在進行相關智力測驗的評估,或是其他需要開口說話的施測,施測者一定要有一種認知,也就是在施測過程中,我們很有可能低估了孩子實際的能力。
這一點,對於第一線實務工作者,無論是心評老師、資源班老師、治療師、心理師或醫師,都是需要具備的基本判斷。我們必須考量的是,在施測過程中,我們所面對的是,孩子可能因為焦慮,而無法真正表現出自己的能力。
較為輕微的選擇性緘默症,在施測過程中,或許在非語言的項目上,他還可以理解你的提問,並且按照時間、速度,做出應有的反應。但是,對於需要口語表達的項目,這時,很明顯的,孩子無法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或是回應出來的內容,相對簡短。
這就像是同一道測驗題目,在現場施測,你問孩子,孩子答不出來,或答得較為簡短,但是回到家,或在孩子比較自在的情境裡,他卻可以回答的非常的完整。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真正要施測的是孩子的能力,而不是測出一種因受限於他的焦慮,而低估的能力。
因此,請自我提醒,應避免為了施測而施測。
同時,對於嚴重的選擇性緘默症,你會發現不只口語的施測很難搜集資料,連非語言的部分,甚至於都無法順利進行。這時,你可以想像,自己硬是要搜集的施測資料是沒有太多意義的,甚至於,就怕對孩子的能力造成錯誤的解釋。
這也是在書中我將會提到如何避免將選擇性緘默症與智能障礙、認知發展遲緩孩子混淆。
鳳毛麟角的關注
在我兩千多場的演講場合中,每一次的演講主題,大部分都由主辦單位決定。而在這麼多場演講裡,主辦單位選擇討論選擇性緘默症,真的是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雖然有時在分享情緒行為障礙的議題中,選擇性緘默症也是其中一小部分。
因此,每當有主辦單位,機關、團體、學校提出想談論選擇性緘默症這議題時,我都是身懷感激的。因為,每多一次的分享,就有機會讓現場聽眾們多一些了解,這一群長時間被遺忘在教室角落裡的孩子。
當然,演講主題可遇不可求,因此,為了讓更多人能夠更加的熟悉、了解選擇性緘默症,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來書寫這本書的目的之一。
解開心中的困惑
「心理師,你終於解開我十幾年以來的困惑。原本,我以為我和這個孩子的關係怎麼這麼糟糕,到底是我做錯了什麼,不然,她為什麼都不跟我開口說話。我的心裡總是有著深深的罪惡感,一直到今天,聽完這場演講,我終於了解原來這孩子,她可能有選擇性緘默症的問題。雖然,這讓我心裡釋懷了許多。但是,我還是為這孩子感到心疼。」一位資深的幼兒園老師,在我演講後,對我分享著。
我想,這也是我這些年在各地進行演講的目的。我期待讓現場聽眾們多一些了解不同孩子的機會。
對於有些老師來說,以往他們面對教室裡不說話的孩子,有時會認為是否是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導致和這個孩子關係惡劣,讓孩子討厭自己、害怕自己,以至於不敢和自己說話。
但在釐清觀念後,未來,當他們再次面對選擇性緘默症孩子,因為有了基礎的認識與概念,或許,他們能多一些陪伴的方式、對應的技巧,不至於讓這樣的孩子,對於說話這件事更加感到害怕、畏懼、退縮,老師也不至於愈幫愈忙,適得其反。
「我到底做錯什麼了?為什麼彤彤總是不和我說話?難道孩子這麼討厭我嗎?」珍妮老師有些自責,向主任說出自己的困惑。「我想,是否讓彤彤轉個班,或許讓其他老師來帶,對她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珍妮,你也知道在幼兒園,如果孩子動不動就換班級、換老師,這真的會給我帶來很大的困擾,因為其他家長也容易有樣學樣,到那個時候,我其他事情就都不用做了,每天來處理這些事情就好了。更何況,班上其他的孩子,你不是都帶得好好的嗎?我看你們長頸鹿班,整個上課氣氛非常的歡樂,有說有笑,而且班上小朋友的家長,也都對你讚譽有加。今天只是一個小女孩不說話,你真的不需要當作一回事啊!」
珍妮老師心裡遲疑了一下。其實,主任說的也挺有道理的。只是,自己這麼多年來,在教學上,還是非常在乎孩子和自己的關係。
「主任,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你說說看,只要我幫得上忙。」
「我想,是否讓彤彤有幾節課到別的教室裡試試?或是請其他老師來我們班上,帶幾個活動也行。」
「你這麼做的想法是⋯⋯」主任有些疑惑。
「我是想⋯⋯」珍妮老師說得有點吞吞吐吐,「或許,有機會讓我知道,彤彤在其他老師的班上,是否也是一樣不開口?」
「珍妮,你真的是好老師無誤。現在的老師只會頭痛、煩惱班上那些吵得半死,讓自己的課上不下去的孩子。哪有人還想要把安安靜靜、乖乖巧巧的孩子送出去?你啊,負責任是很好,但是,不要把許多的事情都攬在自己身上。很多事情不見得都是因為你的因素。」
「我想比較簡單的做法,就是請河馬班的潔西卡老師來你們班上,帶幾個活動交流交流,就當作跨班級一起上課,你也不要再想怎麼換老師、換班級。至於你想要觀察彤彤的說話,是否有所轉變。這一點,你倒是可以試試。」
珍妮稍微鬆了一口氣,也感謝主任的應允,讓自己有機會釐清自己和彤彤的關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是,自己也很擔心一種狀況,假如潔西卡老師來上課,但卻讓彤彤輕輕鬆鬆的開口說話了,那到時,自己就真的是尷尬、難堪了。
意中心理師說選擇性緘默症
選擇性緘默症是一種發生在兒童、青少年,屬於焦慮的一種疾病,並不是單純的害羞、內向、文靜就可以解釋。關於選擇性緘默症,在生活中、校園裡,這樣的孩子依然長期被漠視。對於許多人來說,選擇性緘默症這字眼,可能連聽過都沒聽過,或存在著偏見──認為是孩子自己不說話,相信時間久了,他應該自然而然就會開口說話。
我與選擇性緘默症的第一次接觸
十年多前,我第一次遇見選擇性緘默症孩子,只是,當年這名詞在臨床工作上很少被提及,更別說在校園裡被認識與關注。
那一天,一對父母帶著就讀幼兒園的女孩前來醫院,是經由醫師轉介過來,我準備為女孩進行智力測驗,以評估發展狀況。在施測前,我看著這女孩默默的蹲在治療室裡面,不說一句話。她的表情漠然、肢體僵硬,一動也不動。我明顯可以感受到女孩的焦慮與畏縮。
經驗法則告訴我,當下的智力測驗,女孩無法進行施測。縱使,勉為其難的施測,也一定會低估女孩的表現。
我當時得知女孩在家裡說話自然,但在幼兒園卻不開口。
我因此和父母先溝通,並說明需要先暫停智力測驗,而改採其他方式的理由,我也建議優先處理女孩的不說話行為。
幸運的是,當時女孩的父母對於早期療育有充分的概念,且非常的積極,對於我所設定的治療目標也欣然同意,並且對於後續建議的執行,也相當具有行動力。這些條件的組合,對女孩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與關鍵。
然而,有些案例卻往往因為父母或老師並不認為孩子在學校不說話,有什麼問題,而疏忽了這問題的嚴重性。讓許多緘默的孩子,錯過了早期療育介入的黃金時刻。
但我不忍苛責這些家長與老師,因為他們對於選擇性緘默症並不了解。畢竟長期以來,這樣的診斷名稱,許多人從未聽聞過,更何況是了解。
我很希望透過自己的臨床實務工作、校園服務、書寫與演講,讓選擇性緘默症的孩子能夠受到應有的關注。
只要每多一個人知道,每多一個人看見,那麼,就有機會讓這些孩子在教室裡的緘默行為被合理對待。當孩子的焦慮化解了,他們自然能開口說話。
留意能力的低估現象
面對選擇性緘默症孩子,在進行相關智力測驗的評估,或是其他需要開口說話的施測,施測者一定要有一種認知,也就是在施測過程中,我們很有可能低估了孩子實際的能力。
這一點,對於第一線實務工作者,無論是心評老師、資源班老師、治療師、心理師或醫師,都是需要具備的基本判斷。我們必須考量的是,在施測過程中,我們所面對的是,孩子可能因為焦慮,而無法真正表現出自己的能力。
較為輕微的選擇性緘默症,在施測過程中,或許在非語言的項目上,他還可以理解你的提問,並且按照時間、速度,做出應有的反應。但是,對於需要口語表達的項目,這時,很明顯的,孩子無法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或是回應出來的內容,相對簡短。
這就像是同一道測驗題目,在現場施測,你問孩子,孩子答不出來,或答得較為簡短,但是回到家,或在孩子比較自在的情境裡,他卻可以回答的非常的完整。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真正要施測的是孩子的能力,而不是測出一種因受限於他的焦慮,而低估的能力。
因此,請自我提醒,應避免為了施測而施測。
同時,對於嚴重的選擇性緘默症,你會發現不只口語的施測很難搜集資料,連非語言的部分,甚至於都無法順利進行。這時,你可以想像,自己硬是要搜集的施測資料是沒有太多意義的,甚至於,就怕對孩子的能力造成錯誤的解釋。
這也是在書中我將會提到如何避免將選擇性緘默症與智能障礙、認知發展遲緩孩子混淆。
鳳毛麟角的關注
在我兩千多場的演講場合中,每一次的演講主題,大部分都由主辦單位決定。而在這麼多場演講裡,主辦單位選擇討論選擇性緘默症,真的是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雖然有時在分享情緒行為障礙的議題中,選擇性緘默症也是其中一小部分。
因此,每當有主辦單位,機關、團體、學校提出想談論選擇性緘默症這議題時,我都是身懷感激的。因為,每多一次的分享,就有機會讓現場聽眾們多一些了解,這一群長時間被遺忘在教室角落裡的孩子。
當然,演講主題可遇不可求,因此,為了讓更多人能夠更加的熟悉、了解選擇性緘默症,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來書寫這本書的目的之一。
解開心中的困惑
「心理師,你終於解開我十幾年以來的困惑。原本,我以為我和這個孩子的關係怎麼這麼糟糕,到底是我做錯了什麼,不然,她為什麼都不跟我開口說話。我的心裡總是有著深深的罪惡感,一直到今天,聽完這場演講,我終於了解原來這孩子,她可能有選擇性緘默症的問題。雖然,這讓我心裡釋懷了許多。但是,我還是為這孩子感到心疼。」一位資深的幼兒園老師,在我演講後,對我分享著。
我想,這也是我這些年在各地進行演講的目的。我期待讓現場聽眾們多一些了解不同孩子的機會。
對於有些老師來說,以往他們面對教室裡不說話的孩子,有時會認為是否是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導致和這個孩子關係惡劣,讓孩子討厭自己、害怕自己,以至於不敢和自己說話。
但在釐清觀念後,未來,當他們再次面對選擇性緘默症孩子,因為有了基礎的認識與概念,或許,他們能多一些陪伴的方式、對應的技巧,不至於讓這樣的孩子,對於說話這件事更加感到害怕、畏懼、退縮,老師也不至於愈幫愈忙,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