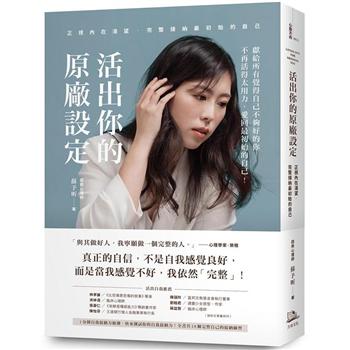▌想更完美前我們先談那些心中魔獸
人生中總有某些時刻、某段經歷,會讓你下定決心:「我絕不要成為『那種人』!」因此,某部分的自己,從此被割下來,丟進那陰暗的、你再也不想去整理的小房間裡。
我的國中班導曾在聯絡簿上寫道:「予昕,班上同學都希望你多點『女人味』」。先撇開這句話偏頗的性別刻板印象,的確,在青少年時期,我一直都給人很強勢、自傲的形象;不但得理不饒人,還處處要爭個你輸我贏,當時,我以為這就叫做「自信」,什麼都得贏,才能有自信呀!
可惜,這樣的「自信」並沒有帶給我太多愉快的感受,我記得國二那年參加一場演說比賽,得到第二名,明明應該開心地享受得獎的歡愉,我卻選擇請假在家、把自己鎖在房間,不吃不喝大哭了一整天,氣憤地怒吼:「第二名跟最後一名有什麼不一樣?」而這句話幾乎成為我三十歲前的基調。好像非得是第一,我才有資格得到別人的肯定、才有資格被喜歡、才不會被隱形。
直到三十歲的某一天,我的伴侶問我:「你還要贏過誰,才能快樂?」我不加思索地脫口而出:「美國總統吧!」接著,我安靜了下來,我聽見自己的荒謬。那永無止盡的比較與競爭,我相信我就算真當上美國總統,也無法平息。因為這已和輸贏無關,而是我內心的某個被壓抑已久的騷動,它,有話要說。
我問自己:「贏,到底是為了什麼?」
因緣際會下我進入心理諮商的領域深造,過程中不免要進行千百次的自我探索,我才從一次兒時經驗回顧得到答案。
國小三年級下學期,我因搬家轉到另一間小學就讀,當時媽媽還動用關係讓我進入所謂的「人情班」(班上同學皆是學校老師、主任或員工的兒女,反正就是「達官顯貴」聚集地,班導通常是能讓班級成績特別好或特別嚴格的角色),一開始同學們紛紛對我展現善意,一個說要帶我去校園巡禮、一個說我的洋裝好漂亮,看似一團融洽,也讓本來就開朗的我很快地融入大家。
可惜好景不常,過了幾個禮拜,我開始發現自己不明究理地背上一些莫須有黑鍋─像是花盆破了或外掃區沒掃乾淨。每天總會有些新罪名「自動找上我」,讓我被老師在升旗典禮或午休時罰站,即使我努力解釋這些都不是我做的,老師依然不相信。 後來,我被分配和一位學校老師的小孩同座,當時課桌還是兩人一桌的「連體嬰」,我與這位同學不得不共用抽屜,然而他的抽屜卻始終凌亂不堪,抽屜裡總會出現沒喝完的牛奶及成堆的垃圾。
某天,在我最愛的作文課上,當我正振筆疾書地寫著文章,他卻已早早寫完,一時心血來潮想整理抽屜,瞬間便把抽屜裡所有髒亂物品通通堆上桌,甚至越過城池,侵略到我的作文紙上。我當時跟他說了一句:「請別這麼自私,我還在寫耶!」他就氣憤地衝出教室。
過不到五分鐘,他和他的媽媽─學校的A老師,就出現在教室門口,他媽媽當著全班的面對我大罵:「我家小孩才不要跟『那種人』坐在一起!」背上的黑鍋多到可以開火鍋店的我,老師更是問也不問,直接叫我起身,坐到垃圾桶旁的位子。
當時我低著頭、咬著牙,心裡一直想:「我到底是『哪種人』?」不意外地,我的功課跟著一落千丈,在班上也常跟同學發生衝突,更加坐實了「壞學生」的位置;甚至班導在我請假的那一天,在班上舉行了「最差人緣獎」投票,你們猜猜獎落誰家?哇喔∼就是我呢!(女明星式搧眼淚)
這種每天被罰站的生活足足過了一整個學期,直到國小四年級上學期,學校徵求每班要派兩位同學參加校內的朗讀比賽,當時班上只有一位主任的孩子自告奮勇,另一個位置從缺。
班導看了看大家,就戲謔地說:「既然沒人想去,那就派最吵鬧的蘇予昕去好啦!」惹來同學一陣訕笑,我也就這麼硬著頭皮去參加了。
比賽那天,我戰戰兢兢地走上台,朗誦出手中的文章,評審們一雙雙閃著光芒的眼眸,帶著無法忽視地笑意,就像挖掘到什麼奇世珍寶般,直直地盯著我看。比賽結果出爐,出乎眾人的意料,那個被戲謔為最吵鬧的學生─我,得了第一。
從此,我的人生有了轉捩點,我開始受到學校的關注,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的比賽,也拿下了冠軍,甚至連校長都因此記功嘉獎,我也間接成為了某種「校長的麻吉」。
在這之後的某天,當我在走廊上再次遇到那位──在教室大聲咆哮,對著全班宣告:「我們家小孩才不要跟『那種人』坐在一起!」的A老師,他竟一改長久以來把我當空氣的態度,主動向我打招呼,甚至揚起殷勤的聲線,過來拉住我說:「哎呦,予昕啊!聽說你得了全國第一名,真是太了不起了!不知道你能不
此刻,就像對一個十歲孩子注射一劑成長激素,瞬間嚐到這世界的某種殘酷跟某種優越混合在一起的複雜滋味,痛恨著這張勢利透頂的臉同時,我也將「當你是第一名,就能讓所有人在乎你」這個信念,深深種下。
但是,無論是不是第一,我都不快樂,內在價值隨著外在評價浮浮沉沉,既自傲、又自卑。我花了三十年,用盡全力讓自己看起來光鮮亮麗,又用盡全力假裝小房間裡的魔獸不存在:一隻肯定會惹大家討厭的勢利魔獸;一隻恨不得大家都失敗的嫉妒魔獸;還有一隻徬徨無助的脆弱魔獸,瑟縮在角落發抖。
我花了好久好久的時間,才能向自己承認:「是的,我有勢利眼;是的,我有嫉妒;是的,我有脆弱。」
心理學大師榮格統稱這些魔獸為「陰影」(Shadow),那些你內心最想否認的特質、樣貌,你不想被你的伴侶、父母、朋友、老闆看見的,甚至你自己都不想承認的,那個你。
也許你會將它們深藏在潛意識的地窖中,以為早已拋開了,但它們仍有能力發出一些訊息讓你感覺它們的存在:「我爛透了」、「根本沒人愛我」、「我就是個魯蛇」、「他看清我之後一定會討厭我」……
你也許不曉得,正是這些躲在暗處的魔獸,主導了(或是你會覺得是阻礙了)我們的人生劇碼,所以是時候了!讓我們拿回主導權、走進小房間,好好地和魔獸來場對話。
▌為了被喜歡而戴上面具,卻阻礙了你的命運?
其實我有時候挺羨慕算命師的,總能鐵口直斷地告訴來訪者:「你就是命中帶煞,所以註定碰到這種事」、「你上輩子欠他的,所以這輩子你要來還債」。我這顆天生麻瓜,在諮商中若被個案問道:「心理師,我的命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一直遇到這種人/事?」
我也只能聳聳肩,老實地告訴你──我不曉得;但,即使我們不曉得是不是上輩子跟他結仇,我們依然可以透過陰影魔獸了解這些重複出現的「命運劇碼」,進而停止舊戲重播,開始執導新的篇章。
現在請你幫我幻想一個情境:
你因某些傑出成就獲頒一個獎項,在你上台前主持人將會對觀眾述說一段有關你的描述,在台下等待的你想聽到怎麼樣的形容詞呢?是勤奮努力、聰明絕頂、關懷他人、無私奉獻、耀眼迷人、充滿熱忱、無人能敵、意志堅定還是默默耕耘? 在榮格心理學中,有個和「陰影」相對的名詞叫做「人格面具」(Persona),它指的是我們渴望這個社會看見的那一面,通常我們會竭盡全力地讓這一面發揚光大,而這一面也非常受到我們自己的接納,因此當我們把以上情境想到的形容詞念出來的時候(例如:我是勤奮努力的人),不但不會被「電到」,反倒令我們熱血沸騰。
人格面具有著非常重要的存在價值,它協助我們融入社會、適應制度與禮俗、建立親密關係、追求成就與目標,可說是我們「打造人生藍圖」的必要條件,但,如果我們誤以為面具就是完整的我,那鐵定會出大問題。
當你過度認同勤奮努力,你就可能對享樂放鬆感到罪惡;當你過度認同無私奉獻,你就可能對自我照顧感到不安;當你過度認同耀眼迷人,你就可能對卸下光環的自己無法容忍;當你過度認同意志堅定,你就可能對徬徨無助的自己深惡痛絕……。
此時,人格面具下的陰影魔獸,已悄悄成了命運的主宰,讓我們不禁仰天哀嘆「人生好難!」
紐約資深編輯──莎拉.奈特(Sarah Knight)在其著作《改變人生的魔法:管它去死》(The Life Changing Magic of Not Giving A F*ck)裡描述,曾就讀哈佛大學的莎拉是眾人眼中的資優生,父母、親友給的幾乎都是讚美、誇獎,這卻差點摧毀她前半輩子的人生。
因為她為了達到這些讚美的標準,不容許自己犯錯、不容許自己偷懶,畢業後在競爭激烈的紐約出版界打拚十五年,無論薪水、職位、名聲都相當過人,但在得到一切的此刻卻迎來人生最憂鬱的低谷時期,無論待在家、去工作、或是上班途中的一分一秒,都令她痛苦到難以呼吸。
最後莎拉決定離職,拒絕繼續活出別人期待的樣子,開始活出自己。這些巨變也使她發現,我們都需要一些「管它去死」的精神,才有心靈的餘裕感受快樂、體驗生命。
我認識不少像莎拉奈特這樣成就非凡、極度努力的個案,若論客觀條件,真的沒什麼好抱怨的,但他們卻有一個共通點──難以感受到快樂,總是憤憤不平地問:「我都這麼努力了,為什麼就是不快樂?」很多人都曾在某些時刻出現這個聲音,但其實,對於「過度努力的完美主義者」而言,這份「不快樂」真是來得恰到好處!我常笑說,我總是一邊痛苦、一邊感謝自己的感冒時刻,如果沒有感冒,我不知道還要繼續逼迫我的身體到哪裡去,一旦感冒,就只能乖乖就範,躺下來,和身體在一起。
同理可證,當我們怎麼努力都無法感到幸福,這份憂鬱正在盡責地提醒:親愛的,是時候卸下你的人格面具,好好喘息一番吧!
你也有「過度努力」的症頭嗎?想知道自己有沒有不小心戴上完美主義者的人格面具,以下三個問題,邀請你真誠地問問自己:
你是否容易受他人評價的影響?
你是否曾把重要的事拖到最後一刻,或遲遲不肯開始?
你是否永遠為自己設定更高的目標,進而停不下來?
▌關於你所痛恨的那些「負面」情緒
有很長一段時間,好勝的性格讓我極容易和他人比較,也使我不願意向自己承認──我在嫉妒,因為嫉妒就輸了嘛!我怎麼能讓這種令人難堪又丟臉的情緒存在呢!這個情緒並沒有因為我的否認而減弱,反而日益強烈,直到多年前的某天,無預警地爆發開來。
那是一個有著和煦陽光的初夏午後,還在念研究所的我剛剛完成出一份厚重的期末報告,心情瞬間輕盈許多,一個勁兒地往床上躺,沒事做了呢!無意識地拿起手機,點開Facebook,用大拇指往上滑了幾下;突然,一張照片吸住了我的目光,我像是被定格一樣盯住照片不放,然後,從胸口湧出一股強烈的酸意。
照片中,我的某位女性臉友身處一家高級的米其林餐廳,用甜美幸福的笑容看著鏡頭,她的右邊是她事業有成的丈夫,她手上抱著的是剛滿周歲的孩子,桌上擺著兩個名牌鉑金包(粗估價值約台幣百餘萬元),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無法動彈、腦袋一片空白了不知道多久,接著我感覺到臉頰熱呼呼地,滾下好幾行淚,我怎麼了?我好生氣、我也好難過,我好……嫉妒!我怎麼可以嫉妒?欸,蘇予昕,難道你是這種無法祝福別人、見不得別人好的小人嗎?
十幾分鐘後,澎湃的情緒漸漸趨於平靜,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溫暖的聲音:「要不要關心一下,『嫉妒』它想表達什麼?」我打開電腦,開啟一個空白word檔,把手放在鍵盤上,讓手指像是有自主意識一般,自由地表達──
「我不懂,我是嫉妒那兩個鉑金包嗎?還是嫉妒她有個疼愛她的老公?」 「當然,有人送我鉑金包我會開心收下啦,但這不是我此刻渴望的東西,我也擁有一位非常合拍的伴侶,那我到底在意的點是什麼呢?」
讓心的語言流淌了一會兒,我突然體悟到,原來,我渴望的是這位女性臉友呈現出來的「人生勝利組感」,就像一個名牌包那麼惹眼。而我因為學習帶來的滿足感再怎麼豐沛,卻沒辦法被別人具體的看見,尤其,身為一個沒有生產力、沒錢賺的學生,很容易失去價值、忘記自己的意義在哪裡。
但這也讓我和自己重新核對,「正在行走的這條路,是否真的通往我所渴望的方向?」我的答案是,「即使暫時沒辦法被他人認可,我已經在正確的道路上了!」想到這裡,剛剛的酸楚逐漸從胸口離開,升起一股堅定、平靜的感受。
以上是我個人因為「嫉妒」而引發的一段心理風暴,雖然這一生中不知出現過多少次嫉妒的感覺,但這一次我沒有否認、沒有逃跑,反而正面迎上嫉妒,想跟它來場對話,因此發生了和以往與嫉妒交手後截然不同的結局:與嫉妒和好,並且重新確認了自己最深的渴望。
通常個案有不舒服的情緒時,很愛問我:「心理師,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些『負面』情緒啊!它讓我好難受,怎麼沒有一個按鈕可以把它們關掉呢?」是啊,這麼痛苦的感覺卻一直出現,對於天性「趨樂避苦」的人類來說,這實在太反常了不是嗎?
但請你想像一下幾十萬年前的地球上,人類祖先第一次遇到老虎的那天,如果這個祖先的情緒本能沒辦法讓他心跳加速、發抖、流汗,直覺地拿起身邊的石頭攻擊老虎,或拔腿就跑(fight or flight),你認為他的下場是什麼?啊呣,被老虎一口吃掉!他的基因也無法一傳再傳,傳到正在讀這本書的你我身上。
所以,情緒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確保我們的「生存」,讓我們好好活著,雖然現今已經不會隨便在路上遇到老虎了,但這個動盪的世界仍充斥著各種危機,包含天災人禍、人際衝突、職場困境、感情糾葛、內在的孤獨、自卑感等等,全部都可能比老虎的威脅性更強、更猛,所以情緒沒有被演化淘汰,是因為我們可能比過往更需要它的指引,它像個忠心的衛兵,提醒著我們「注意!有什麼事不對勁了!」 不過,有點感慨的是,大部份人聽到衛兵的警告時,不是先去搞清楚發生什麼,而是選擇充耳不聞、封鎖城門,任由衛兵在外頭苦苦叩門,我們以為「不要去感覺、不要去想,時間過了就會沒事了」。就像心理學家陳永儀教授在TED的演講中所述:「情緒就像痛覺,沒有人喜歡痛,但如果今天我們不小心把手放在熱爐上面,沒有痛的感覺,我們就不知道要把手抽回來……」
當我們有不舒服的情緒時,我們可能會像「吞一個止痛藥」般去阻絕感受,也許是透過喝酒、打電玩、追劇、大吃大喝、過度的運動……只要能讓我們感受不到情緒的事就瘋狂地做;但沒有痛覺,病就痊癒了嗎?通常不是的,更可能的是因為忽略而惡化,所以對於情緒這個「心理上的痛覺」(這是真的,心痛的時候腦的痛覺區會跟著啟動),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溫暖、關懷的溝通管道,邀請情緒現身、對自己說說話。
所以嫉妒真的那麼不好嗎?其實每一種我們痛恨的情緒都有它獨特的功能,如果這世界沒有嫉妒,我猜我們可能還停留在石器時代,我覺得,哇∼你的石器很棒呦,你也覺得我的石器挺不賴,卻無法因為看到你的石器更銳利更好用,而讓我心生「嗯,那我也要!」的欲望,更大膽地說,人類之所以擁有現在的文明發展,嫉妒真是功不可沒!
情緒本身沒有正與負、對與錯、好與壞,就是一種主觀的個人感受而已。我想大聲告訴你,你對任何人事物,產生任何情緒,都是OK的,重點是我們如何有建設性的表達、展現情緒。當我感受到嫉妒,我可以選擇去毀掉讓我嫉妒的人,我也可以選擇回到內在探索渴望,進而活得更貼近自己,這兩種選擇下的人生開展肯定截然不同。
我常在路邊看到一些家長,對著正在鬧脾氣的孩子說:「這有什麼好生氣的!你不許生氣!」引用陳永儀教授的比喻:「這就像是我說『我好冷喔!』,你回我『欸,你不應該這麼冷欸!』」
人生中總有某些時刻、某段經歷,會讓你下定決心:「我絕不要成為『那種人』!」因此,某部分的自己,從此被割下來,丟進那陰暗的、你再也不想去整理的小房間裡。
我的國中班導曾在聯絡簿上寫道:「予昕,班上同學都希望你多點『女人味』」。先撇開這句話偏頗的性別刻板印象,的確,在青少年時期,我一直都給人很強勢、自傲的形象;不但得理不饒人,還處處要爭個你輸我贏,當時,我以為這就叫做「自信」,什麼都得贏,才能有自信呀!
可惜,這樣的「自信」並沒有帶給我太多愉快的感受,我記得國二那年參加一場演說比賽,得到第二名,明明應該開心地享受得獎的歡愉,我卻選擇請假在家、把自己鎖在房間,不吃不喝大哭了一整天,氣憤地怒吼:「第二名跟最後一名有什麼不一樣?」而這句話幾乎成為我三十歲前的基調。好像非得是第一,我才有資格得到別人的肯定、才有資格被喜歡、才不會被隱形。
直到三十歲的某一天,我的伴侶問我:「你還要贏過誰,才能快樂?」我不加思索地脫口而出:「美國總統吧!」接著,我安靜了下來,我聽見自己的荒謬。那永無止盡的比較與競爭,我相信我就算真當上美國總統,也無法平息。因為這已和輸贏無關,而是我內心的某個被壓抑已久的騷動,它,有話要說。
我問自己:「贏,到底是為了什麼?」
因緣際會下我進入心理諮商的領域深造,過程中不免要進行千百次的自我探索,我才從一次兒時經驗回顧得到答案。
國小三年級下學期,我因搬家轉到另一間小學就讀,當時媽媽還動用關係讓我進入所謂的「人情班」(班上同學皆是學校老師、主任或員工的兒女,反正就是「達官顯貴」聚集地,班導通常是能讓班級成績特別好或特別嚴格的角色),一開始同學們紛紛對我展現善意,一個說要帶我去校園巡禮、一個說我的洋裝好漂亮,看似一團融洽,也讓本來就開朗的我很快地融入大家。
可惜好景不常,過了幾個禮拜,我開始發現自己不明究理地背上一些莫須有黑鍋─像是花盆破了或外掃區沒掃乾淨。每天總會有些新罪名「自動找上我」,讓我被老師在升旗典禮或午休時罰站,即使我努力解釋這些都不是我做的,老師依然不相信。 後來,我被分配和一位學校老師的小孩同座,當時課桌還是兩人一桌的「連體嬰」,我與這位同學不得不共用抽屜,然而他的抽屜卻始終凌亂不堪,抽屜裡總會出現沒喝完的牛奶及成堆的垃圾。
某天,在我最愛的作文課上,當我正振筆疾書地寫著文章,他卻已早早寫完,一時心血來潮想整理抽屜,瞬間便把抽屜裡所有髒亂物品通通堆上桌,甚至越過城池,侵略到我的作文紙上。我當時跟他說了一句:「請別這麼自私,我還在寫耶!」他就氣憤地衝出教室。
過不到五分鐘,他和他的媽媽─學校的A老師,就出現在教室門口,他媽媽當著全班的面對我大罵:「我家小孩才不要跟『那種人』坐在一起!」背上的黑鍋多到可以開火鍋店的我,老師更是問也不問,直接叫我起身,坐到垃圾桶旁的位子。
當時我低著頭、咬著牙,心裡一直想:「我到底是『哪種人』?」不意外地,我的功課跟著一落千丈,在班上也常跟同學發生衝突,更加坐實了「壞學生」的位置;甚至班導在我請假的那一天,在班上舉行了「最差人緣獎」投票,你們猜猜獎落誰家?哇喔∼就是我呢!(女明星式搧眼淚)
這種每天被罰站的生活足足過了一整個學期,直到國小四年級上學期,學校徵求每班要派兩位同學參加校內的朗讀比賽,當時班上只有一位主任的孩子自告奮勇,另一個位置從缺。
班導看了看大家,就戲謔地說:「既然沒人想去,那就派最吵鬧的蘇予昕去好啦!」惹來同學一陣訕笑,我也就這麼硬著頭皮去參加了。
比賽那天,我戰戰兢兢地走上台,朗誦出手中的文章,評審們一雙雙閃著光芒的眼眸,帶著無法忽視地笑意,就像挖掘到什麼奇世珍寶般,直直地盯著我看。比賽結果出爐,出乎眾人的意料,那個被戲謔為最吵鬧的學生─我,得了第一。
從此,我的人生有了轉捩點,我開始受到學校的關注,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的比賽,也拿下了冠軍,甚至連校長都因此記功嘉獎,我也間接成為了某種「校長的麻吉」。
在這之後的某天,當我在走廊上再次遇到那位──在教室大聲咆哮,對著全班宣告:「我們家小孩才不要跟『那種人』坐在一起!」的A老師,他竟一改長久以來把我當空氣的態度,主動向我打招呼,甚至揚起殷勤的聲線,過來拉住我說:「哎呦,予昕啊!聽說你得了全國第一名,真是太了不起了!不知道你能不
此刻,就像對一個十歲孩子注射一劑成長激素,瞬間嚐到這世界的某種殘酷跟某種優越混合在一起的複雜滋味,痛恨著這張勢利透頂的臉同時,我也將「當你是第一名,就能讓所有人在乎你」這個信念,深深種下。
但是,無論是不是第一,我都不快樂,內在價值隨著外在評價浮浮沉沉,既自傲、又自卑。我花了三十年,用盡全力讓自己看起來光鮮亮麗,又用盡全力假裝小房間裡的魔獸不存在:一隻肯定會惹大家討厭的勢利魔獸;一隻恨不得大家都失敗的嫉妒魔獸;還有一隻徬徨無助的脆弱魔獸,瑟縮在角落發抖。
我花了好久好久的時間,才能向自己承認:「是的,我有勢利眼;是的,我有嫉妒;是的,我有脆弱。」
心理學大師榮格統稱這些魔獸為「陰影」(Shadow),那些你內心最想否認的特質、樣貌,你不想被你的伴侶、父母、朋友、老闆看見的,甚至你自己都不想承認的,那個你。
也許你會將它們深藏在潛意識的地窖中,以為早已拋開了,但它們仍有能力發出一些訊息讓你感覺它們的存在:「我爛透了」、「根本沒人愛我」、「我就是個魯蛇」、「他看清我之後一定會討厭我」……
你也許不曉得,正是這些躲在暗處的魔獸,主導了(或是你會覺得是阻礙了)我們的人生劇碼,所以是時候了!讓我們拿回主導權、走進小房間,好好地和魔獸來場對話。
▌為了被喜歡而戴上面具,卻阻礙了你的命運?
其實我有時候挺羨慕算命師的,總能鐵口直斷地告訴來訪者:「你就是命中帶煞,所以註定碰到這種事」、「你上輩子欠他的,所以這輩子你要來還債」。我這顆天生麻瓜,在諮商中若被個案問道:「心理師,我的命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一直遇到這種人/事?」
我也只能聳聳肩,老實地告訴你──我不曉得;但,即使我們不曉得是不是上輩子跟他結仇,我們依然可以透過陰影魔獸了解這些重複出現的「命運劇碼」,進而停止舊戲重播,開始執導新的篇章。
現在請你幫我幻想一個情境:
你因某些傑出成就獲頒一個獎項,在你上台前主持人將會對觀眾述說一段有關你的描述,在台下等待的你想聽到怎麼樣的形容詞呢?是勤奮努力、聰明絕頂、關懷他人、無私奉獻、耀眼迷人、充滿熱忱、無人能敵、意志堅定還是默默耕耘? 在榮格心理學中,有個和「陰影」相對的名詞叫做「人格面具」(Persona),它指的是我們渴望這個社會看見的那一面,通常我們會竭盡全力地讓這一面發揚光大,而這一面也非常受到我們自己的接納,因此當我們把以上情境想到的形容詞念出來的時候(例如:我是勤奮努力的人),不但不會被「電到」,反倒令我們熱血沸騰。
人格面具有著非常重要的存在價值,它協助我們融入社會、適應制度與禮俗、建立親密關係、追求成就與目標,可說是我們「打造人生藍圖」的必要條件,但,如果我們誤以為面具就是完整的我,那鐵定會出大問題。
當你過度認同勤奮努力,你就可能對享樂放鬆感到罪惡;當你過度認同無私奉獻,你就可能對自我照顧感到不安;當你過度認同耀眼迷人,你就可能對卸下光環的自己無法容忍;當你過度認同意志堅定,你就可能對徬徨無助的自己深惡痛絕……。
此時,人格面具下的陰影魔獸,已悄悄成了命運的主宰,讓我們不禁仰天哀嘆「人生好難!」
紐約資深編輯──莎拉.奈特(Sarah Knight)在其著作《改變人生的魔法:管它去死》(The Life Changing Magic of Not Giving A F*ck)裡描述,曾就讀哈佛大學的莎拉是眾人眼中的資優生,父母、親友給的幾乎都是讚美、誇獎,這卻差點摧毀她前半輩子的人生。
因為她為了達到這些讚美的標準,不容許自己犯錯、不容許自己偷懶,畢業後在競爭激烈的紐約出版界打拚十五年,無論薪水、職位、名聲都相當過人,但在得到一切的此刻卻迎來人生最憂鬱的低谷時期,無論待在家、去工作、或是上班途中的一分一秒,都令她痛苦到難以呼吸。
最後莎拉決定離職,拒絕繼續活出別人期待的樣子,開始活出自己。這些巨變也使她發現,我們都需要一些「管它去死」的精神,才有心靈的餘裕感受快樂、體驗生命。
我認識不少像莎拉奈特這樣成就非凡、極度努力的個案,若論客觀條件,真的沒什麼好抱怨的,但他們卻有一個共通點──難以感受到快樂,總是憤憤不平地問:「我都這麼努力了,為什麼就是不快樂?」很多人都曾在某些時刻出現這個聲音,但其實,對於「過度努力的完美主義者」而言,這份「不快樂」真是來得恰到好處!我常笑說,我總是一邊痛苦、一邊感謝自己的感冒時刻,如果沒有感冒,我不知道還要繼續逼迫我的身體到哪裡去,一旦感冒,就只能乖乖就範,躺下來,和身體在一起。
同理可證,當我們怎麼努力都無法感到幸福,這份憂鬱正在盡責地提醒:親愛的,是時候卸下你的人格面具,好好喘息一番吧!
你也有「過度努力」的症頭嗎?想知道自己有沒有不小心戴上完美主義者的人格面具,以下三個問題,邀請你真誠地問問自己:
你是否容易受他人評價的影響?
你是否曾把重要的事拖到最後一刻,或遲遲不肯開始?
你是否永遠為自己設定更高的目標,進而停不下來?
▌關於你所痛恨的那些「負面」情緒
有很長一段時間,好勝的性格讓我極容易和他人比較,也使我不願意向自己承認──我在嫉妒,因為嫉妒就輸了嘛!我怎麼能讓這種令人難堪又丟臉的情緒存在呢!這個情緒並沒有因為我的否認而減弱,反而日益強烈,直到多年前的某天,無預警地爆發開來。
那是一個有著和煦陽光的初夏午後,還在念研究所的我剛剛完成出一份厚重的期末報告,心情瞬間輕盈許多,一個勁兒地往床上躺,沒事做了呢!無意識地拿起手機,點開Facebook,用大拇指往上滑了幾下;突然,一張照片吸住了我的目光,我像是被定格一樣盯住照片不放,然後,從胸口湧出一股強烈的酸意。
照片中,我的某位女性臉友身處一家高級的米其林餐廳,用甜美幸福的笑容看著鏡頭,她的右邊是她事業有成的丈夫,她手上抱著的是剛滿周歲的孩子,桌上擺著兩個名牌鉑金包(粗估價值約台幣百餘萬元),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無法動彈、腦袋一片空白了不知道多久,接著我感覺到臉頰熱呼呼地,滾下好幾行淚,我怎麼了?我好生氣、我也好難過,我好……嫉妒!我怎麼可以嫉妒?欸,蘇予昕,難道你是這種無法祝福別人、見不得別人好的小人嗎?
十幾分鐘後,澎湃的情緒漸漸趨於平靜,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溫暖的聲音:「要不要關心一下,『嫉妒』它想表達什麼?」我打開電腦,開啟一個空白word檔,把手放在鍵盤上,讓手指像是有自主意識一般,自由地表達──
「我不懂,我是嫉妒那兩個鉑金包嗎?還是嫉妒她有個疼愛她的老公?」 「當然,有人送我鉑金包我會開心收下啦,但這不是我此刻渴望的東西,我也擁有一位非常合拍的伴侶,那我到底在意的點是什麼呢?」
讓心的語言流淌了一會兒,我突然體悟到,原來,我渴望的是這位女性臉友呈現出來的「人生勝利組感」,就像一個名牌包那麼惹眼。而我因為學習帶來的滿足感再怎麼豐沛,卻沒辦法被別人具體的看見,尤其,身為一個沒有生產力、沒錢賺的學生,很容易失去價值、忘記自己的意義在哪裡。
但這也讓我和自己重新核對,「正在行走的這條路,是否真的通往我所渴望的方向?」我的答案是,「即使暫時沒辦法被他人認可,我已經在正確的道路上了!」想到這裡,剛剛的酸楚逐漸從胸口離開,升起一股堅定、平靜的感受。
以上是我個人因為「嫉妒」而引發的一段心理風暴,雖然這一生中不知出現過多少次嫉妒的感覺,但這一次我沒有否認、沒有逃跑,反而正面迎上嫉妒,想跟它來場對話,因此發生了和以往與嫉妒交手後截然不同的結局:與嫉妒和好,並且重新確認了自己最深的渴望。
通常個案有不舒服的情緒時,很愛問我:「心理師,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些『負面』情緒啊!它讓我好難受,怎麼沒有一個按鈕可以把它們關掉呢?」是啊,這麼痛苦的感覺卻一直出現,對於天性「趨樂避苦」的人類來說,這實在太反常了不是嗎?
但請你想像一下幾十萬年前的地球上,人類祖先第一次遇到老虎的那天,如果這個祖先的情緒本能沒辦法讓他心跳加速、發抖、流汗,直覺地拿起身邊的石頭攻擊老虎,或拔腿就跑(fight or flight),你認為他的下場是什麼?啊呣,被老虎一口吃掉!他的基因也無法一傳再傳,傳到正在讀這本書的你我身上。
所以,情緒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確保我們的「生存」,讓我們好好活著,雖然現今已經不會隨便在路上遇到老虎了,但這個動盪的世界仍充斥著各種危機,包含天災人禍、人際衝突、職場困境、感情糾葛、內在的孤獨、自卑感等等,全部都可能比老虎的威脅性更強、更猛,所以情緒沒有被演化淘汰,是因為我們可能比過往更需要它的指引,它像個忠心的衛兵,提醒著我們「注意!有什麼事不對勁了!」 不過,有點感慨的是,大部份人聽到衛兵的警告時,不是先去搞清楚發生什麼,而是選擇充耳不聞、封鎖城門,任由衛兵在外頭苦苦叩門,我們以為「不要去感覺、不要去想,時間過了就會沒事了」。就像心理學家陳永儀教授在TED的演講中所述:「情緒就像痛覺,沒有人喜歡痛,但如果今天我們不小心把手放在熱爐上面,沒有痛的感覺,我們就不知道要把手抽回來……」
當我們有不舒服的情緒時,我們可能會像「吞一個止痛藥」般去阻絕感受,也許是透過喝酒、打電玩、追劇、大吃大喝、過度的運動……只要能讓我們感受不到情緒的事就瘋狂地做;但沒有痛覺,病就痊癒了嗎?通常不是的,更可能的是因為忽略而惡化,所以對於情緒這個「心理上的痛覺」(這是真的,心痛的時候腦的痛覺區會跟著啟動),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溫暖、關懷的溝通管道,邀請情緒現身、對自己說說話。
所以嫉妒真的那麼不好嗎?其實每一種我們痛恨的情緒都有它獨特的功能,如果這世界沒有嫉妒,我猜我們可能還停留在石器時代,我覺得,哇∼你的石器很棒呦,你也覺得我的石器挺不賴,卻無法因為看到你的石器更銳利更好用,而讓我心生「嗯,那我也要!」的欲望,更大膽地說,人類之所以擁有現在的文明發展,嫉妒真是功不可沒!
情緒本身沒有正與負、對與錯、好與壞,就是一種主觀的個人感受而已。我想大聲告訴你,你對任何人事物,產生任何情緒,都是OK的,重點是我們如何有建設性的表達、展現情緒。當我感受到嫉妒,我可以選擇去毀掉讓我嫉妒的人,我也可以選擇回到內在探索渴望,進而活得更貼近自己,這兩種選擇下的人生開展肯定截然不同。
我常在路邊看到一些家長,對著正在鬧脾氣的孩子說:「這有什麼好生氣的!你不許生氣!」引用陳永儀教授的比喻:「這就像是我說『我好冷喔!』,你回我『欸,你不應該這麼冷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