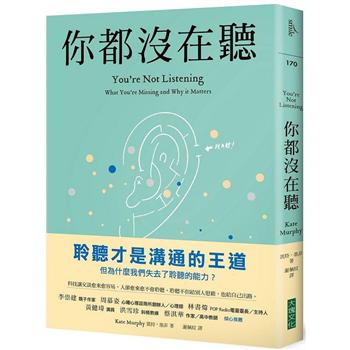1 當周圍的人不再傾聽
我坐在臥房的衣櫃裡訪問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因為公寓對面正在施工,衣櫃就成了我能找到最安靜的地方。因此我才會盤著腿坐在黑暗中,把掛在衣架上的裙子和褲腳從耳機上的小麥克風撥開,跟世界知名的神經學家及作家通話。薩克斯最家喻戶曉的作品是《睡人》(Awakenings)這本回憶錄,後來還拍成電影,由羅賓‧威廉斯和勞勃‧狄尼諾主演。
這次訪談是為了我在《紐約時報》週日評論的一個小專欄,想請他談談他最喜歡的書和電影。但後來我們把波特萊爾拋到腦後,熱烈討論起幻覺、白日夢,還有其他影響薩克斯饒富詩意稱為「心靈氣候」的現象。當我的狗抓著衣櫥門時,薩克斯正在跟我描述他的心靈氣候。有時候,他的心靈因為辨別不出人臉而烏雲密布,包括他映照在鏡中的臉。此外,他也毫無方向感,連短短散個步都可能迷路,回不了家。
那天,我們兩人的時間都很緊。除了手上的專欄,我還有一篇報導要交給《紐約時報》。薩克斯則是在看診、教書、演講的中間,抽空接受我的訪談。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談得很深入,甚至交換了用天氣比喻心靈狀態的用語,比方外表陽光燦爛、霧濛濛的理解力、閃電般的靈感、創造力乾旱、欲望洪流。我也許坐在漆黑的衣櫥裡,但聽他說話時,我不時有醍醐灌頂、感同身受、擊節讚賞,以及靈感或幽默感閃現的瞬間。薩克斯在二○一五年過世,離那次訪談已經過了幾年,但那場對話對我來說卻恍如昨日。
因為長期為《紐約時報》撰稿,偶爾也擔任其他新聞媒體的特派員,我才有幸聽到奧立佛‧薩克斯這樣傑出的思想家說話,還有許多較不知名、但同樣見解獨到的各行各業人士,從時裝設計師到建築工人都有。無一例外,他們擴展了我的視野,增進我對世界的理解,其中很多人深深感動了我。在一般人眼中,我可以跟任何人說話,實際情況是——我可以傾聽任何人說話。這對我的記者生涯很有幫助。我最好的新聞構想經常來自與別人不經意的對話,或許是在街道底下裝設光纖電纜的工人、牙醫診所的助理,或是壽司店遇到、轉行去開牧場的金融家。
我為《紐約時報》撰寫的多篇報導,登上了轉寄次數或點閱率最高的排行榜。原因不是我修理了哪個權貴或揭發了什麼醜聞,而是因為他人談起他們的悲歡喜惡、煩惱困惑時,我用心傾聽之後,盡其所能呈現他們的說法,然後再向外擴展。這其實跟設計一件成功商品、提供消費者一流的服務、留住最好的員工,或賣東西之前要做的準備並無不同。這同樣也是當一個好朋友和好伴侶所需的條件。一切都要回到傾聽這件事。
在我寫的好幾百篇報導中,每一篇或許都引用了四、五種說法,每一個出處我都要跟十幾二十人求證事實、詢問背景資訊或審查資料。但就像我跟奧立佛‧薩克斯的衣櫥對話,其中最深刻難忘、最耐人尋味的訪談,並非破題或扣緊主題的對話,反而是那些談起個人經驗的離題閒聊,或許是一段關係、虔誠的信仰、對某事物的恐懼,或是影響深遠的事件。也就是當一個人說,「我從沒告訴過任何人」或「說出來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是這樣想」的時刻。
有時候對方吐露的事太過私密,我成了當事者以外唯一知情的人,或許至今仍是。而當事人聽到自己說出的話,似乎跟我一樣震驚。我們雙方都不知道怎麼會說到這裡,但是都感覺到此刻重要無比、神聖不可侵犯。那是一種共享的頓悟時刻,只有彼此才知道的祕密感動且改變了我們。是傾聽創造了這樣的機會,成為一種催化劑。
現代生活讓這樣的時刻愈來愈稀少。以前的人會坐在門廊下或營火邊聽彼此說話。現代人不是太忙,就是一心多用,沒時間深入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密西西比大學的歷史和南方學教授查爾斯‧雷根‧威爾森(Charles Reagan Wilson),
記得他曾問過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家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為什麼南方出了這麼多偉大的作家。她回答:「親愛的,我們除了坐在門廊上聊天也沒別的事可做,後來有些人就把聊天內容寫了下來。」
現代住家的門廊多半成了門前的車庫,在忙碌不堪的一天過後將屋主的汽車吞沒。要不就是住在各自獨立的公寓或集合住宅裡,在電梯遇到也不聞不問。這年頭在住宅區裡散步,不太可能會有人靠在欄杆上招手跟你攀談。唯一看得出有人居住的跡象,就是電腦或電視從樓上窗戶透出的藍光。過去我們會個別且面對面地跟親朋好友聊近況,現在則多半透過簡訊、推特或社群媒體聯絡交流。現今你可以同時敲幾十、幾百、幾千,甚至幾百萬人,但是你多常有空或有心跟親朋好友進行面對面、既深且廣的對話?
在社交場合上,我們傳看著手機裡的照片,而不是描述我們的所見所感。我們不再尋求對話中能讓彼此會心一笑的幽默,而是分享在網路上爆紅的人事物或YouTube影片。假如雙方意見分歧,Google就是裁判。要是有人講一件事超過三十秒,大家的頭就紛紛低下來,不是低下來沉思,而是讀訊息、看球賽比數,或是網路新潮流。傾聽的能力日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把所有人擋在門外的能力,尤其是跟我們意見相左或說話拖泥帶水、不直接說重點的人。
訪談的時候,無論我的訪問對象是街頭遊民、企業執行長或名人,我常感覺到他們不太習慣有人傾聽他們說話,彷彿這是一種新奇的經驗。當我對他們所說的事真心感到興趣,並鼓勵他們多說一些時,他們都很驚訝。一旦確認我沒有要催趕、打斷他們或偷瞄手機之後,看得出來他們的身體放鬆下來,思考時更認真投入,回答也更詳細。我猜想這就是很多人最後願意與我分享內心想法的原因,即使我沒有如此要求,話題本身也跟我要寫的文章完全無關。他們在我身上發現一個終於願意傾聽他們說話的人。
人之所以覺得寂寞,就是因為不被傾聽。心理學和社會學學者提醒大眾,寂寞在美國有快速蔓延之勢。專家稱之為公共衛生危機,因為孤立感和疏離感會增加早夭的風險,也讓肥胖和酗酒的人口增加。這對健康的負面影響,比一天抽十四根菸還大。確實,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寂寞跟心臟病、中風、失智和免疫力下降都有關係。
嗅出現今的寂寞礦坑暗藏危險的金絲雀,大概是二○○四年的一位無名網友。當時網路革命正值風起雲湧之際,此人在某個鮮為人知的線上聊天室貼了一句「我好寂寞,有人願意跟我說話嗎?」。這句發自內心的吶喊在網路上快速蔓延,累積大量的回應和媒體關注,很多人群起仿效,留下類似的貼文,至今在不同的線上論壇仍可看見。
看這些文章你會發現一件事。很多人之所以寂寞(lonely)不是因為孤單(alone)。有人寫道:「我每天身邊都圍繞著很多人,我卻感覺跟他們很疏離。」寂寞的人沒有可以分享想法和感受的人,同樣重要的是,也沒有人跟他們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原來那句貼文的用意是希望有人跟貼文者說話,他不是想跟人說話,而是想聽別人說話。建立連結必然是一種雙向過程,雙方都要傾聽並理解對方想說什麼。
從二○○四年那篇貼文開始,感覺自己孤立又孤單的人快速增加。二○一八年對兩萬名美國人所做的調查發現,將近一半表示他們不是每天都進行面對面、有意義的社交互動,例如跟朋友長談。約有同樣比例的人說,他們常在周圍有人時感到寂寞、被忽略。一九八○年代也做過類似的研究,當時只有二○%的受訪者表示有這種感覺。現今,美國的自殺率達到三十年來最高,自一九九九年以來增加了三○%。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如今也因為自殺、酗酒、鴉片類藥物上癮及其他跟寂寞相關的情緒問題,開始縮短。
不只美國如此,寂寞是全世界的現象。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近四十五年來,全球的自殺率增加了六○%。二○一八年,英國更進一步任命「寂寞部長」,幫助九百萬(根據二○一七年政府委託的調查報告)時常或總是感到寂寞的人。在日本,Family Romance這類的公司愈來愈多,讓寂寞的人雇用演員扮演自己的朋友、家人或伴侶。這類服務並不包含性交易,顧客只是付錢租借家人。例如,一個母親跟兒子疏遠,所以就租個兒子來探望她。或者單身漢可能租個太太問他今天過得如何、何時到家。
寂寞不分男女老少。最近有個研究指出,說到疏離感,男、女或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不大。然而,研究確實發現,Z世代(第一個看著螢幕長大的世代)最容易感到寂寞,而且自稱健康狀況比其他世代都要差,包括年長者。從二○○八年至今,學齡兒童和青少年因有自殺念頭或試圖自殺而入院治療者,已經增加一倍有餘。很多文章探討現今青少年為何比較不容易約會、跟朋友出去、考上駕照,甚至沒有父母陪同獨自出門。他們獨處的時間愈來愈長,因此心情和外表都很「藍」(blue,亦指憂鬱)——因為螢幕反射的藍光。研究指出,面對螢幕的時間愈長,人就愈不快樂。沉迷於社群媒體的八年級生,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比一般人高二七%。比起在臉書、YouTube、Instagram之類的平台花較少時間的同儕,他們說自己不開心的機率高出五六%。同樣地,針對有打電玩習慣的青少年所做的研究綜合分析發現,他們更容易有焦慮和憂鬱的問題。
為了趕走寂寞,我們多半會鼓勵人「走出去」參加社團、從事某項運動、去當志工、邀朋友共進晚餐、加入教會等等。說穿了就是別掛在臉書上,與人「面對面」。但就像之前說的,人在其他人面前常覺得寂寞。一旦「走出去」和人「面對面」,你要怎麼跟人產生連結?藉由傾聽。做起來可不像說起來那麼簡單。真正傾聽他人,是一種很多人似乎都已遺忘、甚至從沒學會過的技巧。
(未完)
4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用偏見把耳朵塞住
「我說的你都沒在聽!」
「先讓我說完!」
「我哪有這麼說!」
在「我愛你」之後,這些是親密關係中最常反覆出現的話。或許你以為比起陌生人,你更願意傾聽伴侶的話,事實往往相反。心理學家朱蒂斯‧寇奇(Judith Coche)對這種現象再熟悉不過。她是公認的夫妻團體治療權威,由羅莉‧亞伯拉罕(Laurie Abraham)執筆的《夫妻俱樂部》(The Husbands and Wives Club)一書,
記錄了她如何成功挽救看似無可救藥的婚姻。
某天傍晚,我到寇奇位於費城市區的辦公室找她。不久前才離開的夫妻團體留下一堆凌亂變形的抱枕,椅子和沙發仍留有餘溫。我到那裡是為了請教她,為什麼人常常覺得伴侶不聽他們說話,甚至誤解他們的話。寇奇的回答很簡單:關係久了就會對彼此失去好奇心。不一定是冷漠,只是覺得彼此已經熟得不能再熟了。不聽對方說話,是因為自以為知道對方要說什麼。
寇奇舉了夫妻替對方回答問題或做決定的例子。夫妻也可能送了對方根本不想要的禮物,讓對方感到失望或受傷。父母同樣會犯類似的錯誤,自以為瞭解小孩的喜好、知道他們會做或不會做什麼。無論是誰,其實都很容易預設自己瞭解伴侶、家人的想法。這叫作親密溝通偏見。親密關係雖然美好,但也會讓我們自滿,高估自己理解最親近的人在想什麼的能力。
威廉士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的研究都證實了這點。研究員讓兩對互不相識的夫妻圍坐成一圈,背對著彼此,像在玩遊戲一樣。每個人都要輪流說幾句日常對話會用到、但具有多重意義的話。接著,伴侶說出他們猜想另一半想表達的意思,另一對陌生夫妻再提出他們的猜測。例如「你今天看起來不太一樣」,可能表示「你看起來好糟」、「看吧,我有注意你的外表」、「嘿,我喜歡你的新造型!」,或是「呃,我覺得有哪裡不一樣,但又說不上來是什麼」。受試者以為另一半比陌生人瞭解他們,結果非但沒有,有時甚至還不如陌生人。
另一個類似的實驗證明,好朋友也會高估對彼此的理解程度。研究員先後將受試者跟好友和陌生人配對,請受試者引導對方去拿大箱子裡的東西。箱子分成一格一格,裡頭有各式同名的物品,例如電腦滑鼠和老鼠布偶(英文都是mouse)。有些格子只有一個人看得見,有些兩個人都看得見。朋友之間的親密關係製造出兩人同心的假象,讓他們更容易以為朋友看到的跟他們看到的一樣。跟陌生人就比較不會犯這種錯誤。也就是說,由陌生人引導時,他們比較會直接伸手去拿兩人都看得見的正確標的。「『我的認知跟你的不同』這種想法,是有效溝通不可缺的元素。」肯尼斯‧薩維斯基(Kenneth Savitsky)說。他是威廉士學院的心理學教授,也是該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那對指導、教學或一般對話都很必要。但是當對象是好朋友或另一半時,這個原則就很難掌握。」
那就好像一旦你跟一個人建立關係,你會以為關係永遠存在。可是我們每天跟人的互動和從事的活動持續塑造著我們,一點一滴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所以沒有人跟昨天一樣,今天的我也不會跟明天的我一模一樣。看法、態度和信念隨時在改變。無論你們認識多久、自認為多瞭解對方,只要停止傾聽,最終會失去對他人的理解,對彼此愈來愈陌生。
靠過去的印象去理解現在的人,注定會失敗。法國作家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曾說:「幸福的婚姻是一場漫長、但永遠嫌太短的對話。」如果一個人堅持把你當作初相識的那個你對待,你會想跟他長相廝守嗎?不只愛情關係如此,所有關係都是。連幼童都不想被當成兩個月前的小嬰兒一樣對待。堅持要幫一個兩歲小孩做他已經學會的事,他可能生氣地說:「我來弄!」生命變動不居,傾聽是我們跟彼此保持連結的方法。
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英國人類學家及進化心理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的文章。他告訴我,維持友誼的主要方式就是透過「日常對話」。那表示,詢問對方「你好嗎?」,並用心傾聽對方的答案。他最有名的是提出「鄧巴數」,亦即在社群網路上實際交往的人最多在一百五十人上下。你只能跟這麼多人熟識,在酒吧巧遇時一起喝一杯也不會尷尬。超過這個數字就超出了腦袋和情緒的負荷,無法建立有意義的連結。
不過鄧巴也強調,根據你花在這一百五十個人身上的時間,可以分出不同的「友誼等級」。就像婚禮蛋糕,最上層只有一、兩個人(另一半和最好的朋友),那是你最親密且天天互動的人。下一層最多可以容納四個人,是你很親密、喜愛且關心的人,這個等級的朋友大概需要每週都有互動才能維持。接下來就是跟你較少見面的普通朋友,彼此的關係也較薄弱,因為沒有經常接觸,很容易變成泛泛之交。雙方雖然友善,但不是真正的朋友,因為沒有跟上對方的各種變化。儘管可以跟他們喝一杯,但你不會特別想念他們,甚至不會發現他們已經搬到別的地方,他們也不會想念你。
一個例外或許是某些你多年沒聯絡、卻絲毫不覺得疏遠的朋友。鄧巴認為,這些通常是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曾透過既多且深的傾聽跟你建立友誼的朋友,多半是情緒動盪的時期,像是上大學、剛成年或遭遇困境時,如生病或離婚。那很像事先累積了大量的傾聽,日後即使長期分開,也有互相理解和聯繫的基礎。換句話說,過去常常用心聽一個人說話,之後即使雙方因為距離或冷戰而不再聯絡,也能很快重拾過去的默契。
坐在朱蒂斯‧寇奇辦公室裡,周圍都是皺巴巴的抱枕,我發現重修舊好並不是一個快速或簡單的過程,至少對參加她的治療團體的夫妻並不是。她要求他們參加一整年的課程,每個月參與長達四小時的團體治療,外加一個週末的閉關。此外,寇奇會先仔細調查夫妻的狀況,才決定要不要讓他們加入。她說她要確定他們「已經準備好且有能力做這種功課」。意思就是準備好傾聽,不光是傾聽另一半,還有團體裡的其他成員。
我坐在臥房的衣櫃裡訪問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因為公寓對面正在施工,衣櫃就成了我能找到最安靜的地方。因此我才會盤著腿坐在黑暗中,把掛在衣架上的裙子和褲腳從耳機上的小麥克風撥開,跟世界知名的神經學家及作家通話。薩克斯最家喻戶曉的作品是《睡人》(Awakenings)這本回憶錄,後來還拍成電影,由羅賓‧威廉斯和勞勃‧狄尼諾主演。
這次訪談是為了我在《紐約時報》週日評論的一個小專欄,想請他談談他最喜歡的書和電影。但後來我們把波特萊爾拋到腦後,熱烈討論起幻覺、白日夢,還有其他影響薩克斯饒富詩意稱為「心靈氣候」的現象。當我的狗抓著衣櫥門時,薩克斯正在跟我描述他的心靈氣候。有時候,他的心靈因為辨別不出人臉而烏雲密布,包括他映照在鏡中的臉。此外,他也毫無方向感,連短短散個步都可能迷路,回不了家。
那天,我們兩人的時間都很緊。除了手上的專欄,我還有一篇報導要交給《紐約時報》。薩克斯則是在看診、教書、演講的中間,抽空接受我的訪談。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談得很深入,甚至交換了用天氣比喻心靈狀態的用語,比方外表陽光燦爛、霧濛濛的理解力、閃電般的靈感、創造力乾旱、欲望洪流。我也許坐在漆黑的衣櫥裡,但聽他說話時,我不時有醍醐灌頂、感同身受、擊節讚賞,以及靈感或幽默感閃現的瞬間。薩克斯在二○一五年過世,離那次訪談已經過了幾年,但那場對話對我來說卻恍如昨日。
因為長期為《紐約時報》撰稿,偶爾也擔任其他新聞媒體的特派員,我才有幸聽到奧立佛‧薩克斯這樣傑出的思想家說話,還有許多較不知名、但同樣見解獨到的各行各業人士,從時裝設計師到建築工人都有。無一例外,他們擴展了我的視野,增進我對世界的理解,其中很多人深深感動了我。在一般人眼中,我可以跟任何人說話,實際情況是——我可以傾聽任何人說話。這對我的記者生涯很有幫助。我最好的新聞構想經常來自與別人不經意的對話,或許是在街道底下裝設光纖電纜的工人、牙醫診所的助理,或是壽司店遇到、轉行去開牧場的金融家。
我為《紐約時報》撰寫的多篇報導,登上了轉寄次數或點閱率最高的排行榜。原因不是我修理了哪個權貴或揭發了什麼醜聞,而是因為他人談起他們的悲歡喜惡、煩惱困惑時,我用心傾聽之後,盡其所能呈現他們的說法,然後再向外擴展。這其實跟設計一件成功商品、提供消費者一流的服務、留住最好的員工,或賣東西之前要做的準備並無不同。這同樣也是當一個好朋友和好伴侶所需的條件。一切都要回到傾聽這件事。
在我寫的好幾百篇報導中,每一篇或許都引用了四、五種說法,每一個出處我都要跟十幾二十人求證事實、詢問背景資訊或審查資料。但就像我跟奧立佛‧薩克斯的衣櫥對話,其中最深刻難忘、最耐人尋味的訪談,並非破題或扣緊主題的對話,反而是那些談起個人經驗的離題閒聊,或許是一段關係、虔誠的信仰、對某事物的恐懼,或是影響深遠的事件。也就是當一個人說,「我從沒告訴過任何人」或「說出來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是這樣想」的時刻。
有時候對方吐露的事太過私密,我成了當事者以外唯一知情的人,或許至今仍是。而當事人聽到自己說出的話,似乎跟我一樣震驚。我們雙方都不知道怎麼會說到這裡,但是都感覺到此刻重要無比、神聖不可侵犯。那是一種共享的頓悟時刻,只有彼此才知道的祕密感動且改變了我們。是傾聽創造了這樣的機會,成為一種催化劑。
現代生活讓這樣的時刻愈來愈稀少。以前的人會坐在門廊下或營火邊聽彼此說話。現代人不是太忙,就是一心多用,沒時間深入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密西西比大學的歷史和南方學教授查爾斯‧雷根‧威爾森(Charles Reagan Wilson),
記得他曾問過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家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為什麼南方出了這麼多偉大的作家。她回答:「親愛的,我們除了坐在門廊上聊天也沒別的事可做,後來有些人就把聊天內容寫了下來。」
現代住家的門廊多半成了門前的車庫,在忙碌不堪的一天過後將屋主的汽車吞沒。要不就是住在各自獨立的公寓或集合住宅裡,在電梯遇到也不聞不問。這年頭在住宅區裡散步,不太可能會有人靠在欄杆上招手跟你攀談。唯一看得出有人居住的跡象,就是電腦或電視從樓上窗戶透出的藍光。過去我們會個別且面對面地跟親朋好友聊近況,現在則多半透過簡訊、推特或社群媒體聯絡交流。現今你可以同時敲幾十、幾百、幾千,甚至幾百萬人,但是你多常有空或有心跟親朋好友進行面對面、既深且廣的對話?
在社交場合上,我們傳看著手機裡的照片,而不是描述我們的所見所感。我們不再尋求對話中能讓彼此會心一笑的幽默,而是分享在網路上爆紅的人事物或YouTube影片。假如雙方意見分歧,Google就是裁判。要是有人講一件事超過三十秒,大家的頭就紛紛低下來,不是低下來沉思,而是讀訊息、看球賽比數,或是網路新潮流。傾聽的能力日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把所有人擋在門外的能力,尤其是跟我們意見相左或說話拖泥帶水、不直接說重點的人。
訪談的時候,無論我的訪問對象是街頭遊民、企業執行長或名人,我常感覺到他們不太習慣有人傾聽他們說話,彷彿這是一種新奇的經驗。當我對他們所說的事真心感到興趣,並鼓勵他們多說一些時,他們都很驚訝。一旦確認我沒有要催趕、打斷他們或偷瞄手機之後,看得出來他們的身體放鬆下來,思考時更認真投入,回答也更詳細。我猜想這就是很多人最後願意與我分享內心想法的原因,即使我沒有如此要求,話題本身也跟我要寫的文章完全無關。他們在我身上發現一個終於願意傾聽他們說話的人。
人之所以覺得寂寞,就是因為不被傾聽。心理學和社會學學者提醒大眾,寂寞在美國有快速蔓延之勢。專家稱之為公共衛生危機,因為孤立感和疏離感會增加早夭的風險,也讓肥胖和酗酒的人口增加。這對健康的負面影響,比一天抽十四根菸還大。確實,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寂寞跟心臟病、中風、失智和免疫力下降都有關係。
嗅出現今的寂寞礦坑暗藏危險的金絲雀,大概是二○○四年的一位無名網友。當時網路革命正值風起雲湧之際,此人在某個鮮為人知的線上聊天室貼了一句「我好寂寞,有人願意跟我說話嗎?」。這句發自內心的吶喊在網路上快速蔓延,累積大量的回應和媒體關注,很多人群起仿效,留下類似的貼文,至今在不同的線上論壇仍可看見。
看這些文章你會發現一件事。很多人之所以寂寞(lonely)不是因為孤單(alone)。有人寫道:「我每天身邊都圍繞著很多人,我卻感覺跟他們很疏離。」寂寞的人沒有可以分享想法和感受的人,同樣重要的是,也沒有人跟他們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原來那句貼文的用意是希望有人跟貼文者說話,他不是想跟人說話,而是想聽別人說話。建立連結必然是一種雙向過程,雙方都要傾聽並理解對方想說什麼。
從二○○四年那篇貼文開始,感覺自己孤立又孤單的人快速增加。二○一八年對兩萬名美國人所做的調查發現,將近一半表示他們不是每天都進行面對面、有意義的社交互動,例如跟朋友長談。約有同樣比例的人說,他們常在周圍有人時感到寂寞、被忽略。一九八○年代也做過類似的研究,當時只有二○%的受訪者表示有這種感覺。現今,美國的自殺率達到三十年來最高,自一九九九年以來增加了三○%。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如今也因為自殺、酗酒、鴉片類藥物上癮及其他跟寂寞相關的情緒問題,開始縮短。
不只美國如此,寂寞是全世界的現象。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近四十五年來,全球的自殺率增加了六○%。二○一八年,英國更進一步任命「寂寞部長」,幫助九百萬(根據二○一七年政府委託的調查報告)時常或總是感到寂寞的人。在日本,Family Romance這類的公司愈來愈多,讓寂寞的人雇用演員扮演自己的朋友、家人或伴侶。這類服務並不包含性交易,顧客只是付錢租借家人。例如,一個母親跟兒子疏遠,所以就租個兒子來探望她。或者單身漢可能租個太太問他今天過得如何、何時到家。
寂寞不分男女老少。最近有個研究指出,說到疏離感,男、女或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不大。然而,研究確實發現,Z世代(第一個看著螢幕長大的世代)最容易感到寂寞,而且自稱健康狀況比其他世代都要差,包括年長者。從二○○八年至今,學齡兒童和青少年因有自殺念頭或試圖自殺而入院治療者,已經增加一倍有餘。很多文章探討現今青少年為何比較不容易約會、跟朋友出去、考上駕照,甚至沒有父母陪同獨自出門。他們獨處的時間愈來愈長,因此心情和外表都很「藍」(blue,亦指憂鬱)——因為螢幕反射的藍光。研究指出,面對螢幕的時間愈長,人就愈不快樂。沉迷於社群媒體的八年級生,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比一般人高二七%。比起在臉書、YouTube、Instagram之類的平台花較少時間的同儕,他們說自己不開心的機率高出五六%。同樣地,針對有打電玩習慣的青少年所做的研究綜合分析發現,他們更容易有焦慮和憂鬱的問題。
為了趕走寂寞,我們多半會鼓勵人「走出去」參加社團、從事某項運動、去當志工、邀朋友共進晚餐、加入教會等等。說穿了就是別掛在臉書上,與人「面對面」。但就像之前說的,人在其他人面前常覺得寂寞。一旦「走出去」和人「面對面」,你要怎麼跟人產生連結?藉由傾聽。做起來可不像說起來那麼簡單。真正傾聽他人,是一種很多人似乎都已遺忘、甚至從沒學會過的技巧。
(未完)
4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用偏見把耳朵塞住
「我說的你都沒在聽!」
「先讓我說完!」
「我哪有這麼說!」
在「我愛你」之後,這些是親密關係中最常反覆出現的話。或許你以為比起陌生人,你更願意傾聽伴侶的話,事實往往相反。心理學家朱蒂斯‧寇奇(Judith Coche)對這種現象再熟悉不過。她是公認的夫妻團體治療權威,由羅莉‧亞伯拉罕(Laurie Abraham)執筆的《夫妻俱樂部》(The Husbands and Wives Club)一書,
記錄了她如何成功挽救看似無可救藥的婚姻。
某天傍晚,我到寇奇位於費城市區的辦公室找她。不久前才離開的夫妻團體留下一堆凌亂變形的抱枕,椅子和沙發仍留有餘溫。我到那裡是為了請教她,為什麼人常常覺得伴侶不聽他們說話,甚至誤解他們的話。寇奇的回答很簡單:關係久了就會對彼此失去好奇心。不一定是冷漠,只是覺得彼此已經熟得不能再熟了。不聽對方說話,是因為自以為知道對方要說什麼。
寇奇舉了夫妻替對方回答問題或做決定的例子。夫妻也可能送了對方根本不想要的禮物,讓對方感到失望或受傷。父母同樣會犯類似的錯誤,自以為瞭解小孩的喜好、知道他們會做或不會做什麼。無論是誰,其實都很容易預設自己瞭解伴侶、家人的想法。這叫作親密溝通偏見。親密關係雖然美好,但也會讓我們自滿,高估自己理解最親近的人在想什麼的能力。
威廉士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的研究都證實了這點。研究員讓兩對互不相識的夫妻圍坐成一圈,背對著彼此,像在玩遊戲一樣。每個人都要輪流說幾句日常對話會用到、但具有多重意義的話。接著,伴侶說出他們猜想另一半想表達的意思,另一對陌生夫妻再提出他們的猜測。例如「你今天看起來不太一樣」,可能表示「你看起來好糟」、「看吧,我有注意你的外表」、「嘿,我喜歡你的新造型!」,或是「呃,我覺得有哪裡不一樣,但又說不上來是什麼」。受試者以為另一半比陌生人瞭解他們,結果非但沒有,有時甚至還不如陌生人。
另一個類似的實驗證明,好朋友也會高估對彼此的理解程度。研究員先後將受試者跟好友和陌生人配對,請受試者引導對方去拿大箱子裡的東西。箱子分成一格一格,裡頭有各式同名的物品,例如電腦滑鼠和老鼠布偶(英文都是mouse)。有些格子只有一個人看得見,有些兩個人都看得見。朋友之間的親密關係製造出兩人同心的假象,讓他們更容易以為朋友看到的跟他們看到的一樣。跟陌生人就比較不會犯這種錯誤。也就是說,由陌生人引導時,他們比較會直接伸手去拿兩人都看得見的正確標的。「『我的認知跟你的不同』這種想法,是有效溝通不可缺的元素。」肯尼斯‧薩維斯基(Kenneth Savitsky)說。他是威廉士學院的心理學教授,也是該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那對指導、教學或一般對話都很必要。但是當對象是好朋友或另一半時,這個原則就很難掌握。」
那就好像一旦你跟一個人建立關係,你會以為關係永遠存在。可是我們每天跟人的互動和從事的活動持續塑造著我們,一點一滴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所以沒有人跟昨天一樣,今天的我也不會跟明天的我一模一樣。看法、態度和信念隨時在改變。無論你們認識多久、自認為多瞭解對方,只要停止傾聽,最終會失去對他人的理解,對彼此愈來愈陌生。
靠過去的印象去理解現在的人,注定會失敗。法國作家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曾說:「幸福的婚姻是一場漫長、但永遠嫌太短的對話。」如果一個人堅持把你當作初相識的那個你對待,你會想跟他長相廝守嗎?不只愛情關係如此,所有關係都是。連幼童都不想被當成兩個月前的小嬰兒一樣對待。堅持要幫一個兩歲小孩做他已經學會的事,他可能生氣地說:「我來弄!」生命變動不居,傾聽是我們跟彼此保持連結的方法。
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英國人類學家及進化心理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的文章。他告訴我,維持友誼的主要方式就是透過「日常對話」。那表示,詢問對方「你好嗎?」,並用心傾聽對方的答案。他最有名的是提出「鄧巴數」,亦即在社群網路上實際交往的人最多在一百五十人上下。你只能跟這麼多人熟識,在酒吧巧遇時一起喝一杯也不會尷尬。超過這個數字就超出了腦袋和情緒的負荷,無法建立有意義的連結。
不過鄧巴也強調,根據你花在這一百五十個人身上的時間,可以分出不同的「友誼等級」。就像婚禮蛋糕,最上層只有一、兩個人(另一半和最好的朋友),那是你最親密且天天互動的人。下一層最多可以容納四個人,是你很親密、喜愛且關心的人,這個等級的朋友大概需要每週都有互動才能維持。接下來就是跟你較少見面的普通朋友,彼此的關係也較薄弱,因為沒有經常接觸,很容易變成泛泛之交。雙方雖然友善,但不是真正的朋友,因為沒有跟上對方的各種變化。儘管可以跟他們喝一杯,但你不會特別想念他們,甚至不會發現他們已經搬到別的地方,他們也不會想念你。
一個例外或許是某些你多年沒聯絡、卻絲毫不覺得疏遠的朋友。鄧巴認為,這些通常是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曾透過既多且深的傾聽跟你建立友誼的朋友,多半是情緒動盪的時期,像是上大學、剛成年或遭遇困境時,如生病或離婚。那很像事先累積了大量的傾聽,日後即使長期分開,也有互相理解和聯繫的基礎。換句話說,過去常常用心聽一個人說話,之後即使雙方因為距離或冷戰而不再聯絡,也能很快重拾過去的默契。
坐在朱蒂斯‧寇奇辦公室裡,周圍都是皺巴巴的抱枕,我發現重修舊好並不是一個快速或簡單的過程,至少對參加她的治療團體的夫妻並不是。她要求他們參加一整年的課程,每個月參與長達四小時的團體治療,外加一個週末的閉關。此外,寇奇會先仔細調查夫妻的狀況,才決定要不要讓他們加入。她說她要確定他們「已經準備好且有能力做這種功課」。意思就是準備好傾聽,不光是傾聽另一半,還有團體裡的其他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