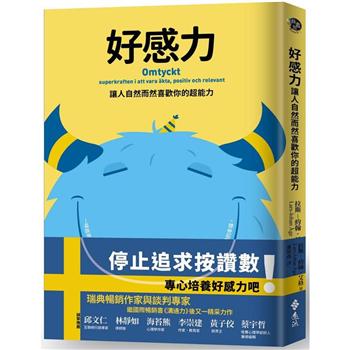1 為何大家都渴望人氣?
人氣在大腦內引發的化學作用
澳洲有位名叫克里斯.戴維斯(Chris Davis)的教授曾經做過一個頗受矚目的實驗。他要那些自願參加實驗的人觀看一些陌生人的照片,並寫下他們對每一個人的喜好度,然後再告訴他們照片裡的人當中有哪幾位也喜歡他們(照片裡的人事先已經看過那些受試者的照片)。受試者身上都戴著連接到磁振造影設備的儀器,藉以測量他們的大腦活動。當受試者聽到有人喜歡他們時,他們大腦內的獎賞中樞就會立即產生反應。
這種反應攸關我們的發育與成長,因為它開始向我們發出訊號,要我們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並試著掙脫我們和父母之間的緊密關係,轉而尋求同儕的認可與關注。為了確保我們會持續努力脫離對父母的依附,尋求他人的認可,大腦會分泌兩種特定的物質—─催產素與多巴胺—─以活化獎賞中樞內的相關受體,讓我們感到愉悅。因此,我們之所以追求人氣並藉此獲得認可,乃是催產素和多巴胺這兩種效果強大的化學物質聯手作用的結果。
如今,當我看到有人對我在臉書或 Instagram 上所發布的訊息按讚時,之所以會開心,也是由同樣的化學作用所導致。這時,如果你剛好坐在我身邊,問我在做什麼,我甚至可能答不出來。有些研究確實顯示:這種追求大腦獎賞的行為都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進行的。
因此,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提昇覺察能力著手。
我們喜歡和別人比較
身為一個研究談判技巧的人,我很清楚一件事:如果我們知道別人所拿到的東西比我們少,就比較有可能會接受對方的提議。同樣的,我們可能也會因為別人所得到的東西比我們好,而向對方說「不!」。這是因為人們總是喜歡拿別人來和自己做比較。換句話說,我們總是不斷地在做「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追求人氣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會比較」有兩種形式。一種叫做「向下比較」(downward comparison)。當賣方因為其他人所出的價錢都比較少而接受某人的投標時,他(她)就是在進行「向下比較」。向下比較
我們可以用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後所出現的一種新式電影為例,來說明何謂「向下比較」。這種電影的內容就是描寫其他國家的窮人如何受到剝削,有時也被稱為「震驚紀錄片」(shockumentary)。這類影片的目的就是迎合人們在面臨經濟危機時的心理需求,讓那些生活艱辛的人感覺好過一些。它們往往把非洲或印尼的原始部落人民描寫成兇殘、粗野且生活條件極其惡劣的野蠻人,其效果就是讓一個或許剛剛失業的人只要花一張電影票的錢,就可以提昇他對自身生活的幸福感與滿意度,因為發現世上還有人過得比他更慘。
我們很可能會認為這類「向下比較」會讓我們感覺好過一些,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使我們剛開始時會因此而產生幸福感,但就長期而言,它的效果卻是負面的。舉例來說,有一群研究人員就做過一項調查。他們問一群警察是否認為當警察的人大致上要比當警衛的人優秀。結果他們發現:愈是認真比較兩者差異的警察,自尊心愈低,對自己的生活也愈不滿意。
研究人員所做的解釋是:當這些警察開始和他人做比較時,雖然他們是占優勢的一方,但這會讓他們開始藉由跟他人比較,來建立自己的自尊心並肯定自我的價值。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稍後我將會回過頭來再談談這種自我評價方式,因為社會比較是否具有建設性,關鍵就在於我們如何評價自我。另一種常見的社會比較方式就是所謂的「向上比較」。簡而言之,它指的就是把自己拿來和那些更優秀或者過得更好的人做比較。不久前我在社區的網球場上所經歷的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向上比較
話說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球友一起去網球場打球(我們每個星期打一次)。我們抵達時,剛好遇到一個之前曾和我的那位球友一起打球的人。當時他是一個人去,目的是要練習發球技巧。由於網球場上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別人,於是在開打之前,我們便邀請他和我們一起暖身。
我不認識那個人,但從開打前我的球友和他的對話中,我約略得知他是個網球高手,而且之前還是某個俱樂部的男子網球隊的選手。他第一次發球時,我光是聽那球拍發出的聲音就知道他果然是個高手,因為純粹為了健身而打球的人是不可能有那種架勢的。他必然已經練了很多年,而且可能還經過專業教練的調教。我意識到這一點時,起初非常振奮,因為我沒想到自己能碰上這樣的對手。這些年,我都是為了運動而打球,而且一直都是和同一個人打。現在我終於有機會領教真正的高手有多麼厲害,並藉此評估自己的球技了。
之前我的程度始終不曾達到足以代表網球俱樂部去比賽的水準,但現在我卻可以透過和這位高手過招,來間接達成參賽的夢想。
然而,才打了十分鐘,我就發現我和對方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距。總而言之,他打得就是比我好。
通常我打完球後心情都會很好,但這天晚上我卻沒有很開心,因為和那個高手比起來,我顯然還是不太行。原本我覺得自己打得還不錯,但如今看來我的球技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好。當那位高手離開後,我便一直沉浸在這樣的情緒中。可想而知,我後來和我的那位球友打球時,成績自然也不太理想。事實上,那一晚接下來的時間,我一直都為自己的網球夢的幻滅而耿耿於懷。
有意識的社會比較
身為一個喜愛建構模型的研究人員,我在做研究時向來都是使用所謂的「連續比較」(continual comparison)。這個名詞聽起來可能不太好懂,但實際上它的意思就是:當我發現某個有趣的現象時,就會把它拿來和已知的現象做比較,看看兩者之間有何異同,如此便能對我的研究素材有更多的認識。
這個過程其實和社會比較沒有太大的不同。早在一九五四年時,社會心理學家黎昂.費思汀格(Leon Festinger)就已經指出:社會比較的真正目的是要讓我們更認識自己,並且促進我們的成長與發展,就像我透過比較的方式來加深我對我的研究素材的理解一般。只可惜大多數人都不是這麼做。且容我再次以那個打網球的例子,來說明我們的意識與覺察在社會比較中所扮演的角色。
理論上,我其實可以透過和對手的比較得到許多有用的訊息,以便了解自己球技水準如何。比方說,開打二十秒鐘後,我就發現那人擊球的方式和我完全不同,拍子碰到球時所發出的聲音也更明顯。這時候,我與其去思考「誰打得比較好?」,倒不如分析他擊球的方式好在哪裡。他揮拍之前,我看到他的手腕甩了一下,或許那是原因之一?如果我當時問他,他或許能夠給我一些指點,因為他很可能已經在揮拍和擊球方面下了許多工夫。或許他甚至會教我該如何為網球拍穿線,讓我能以更適合我的步法的方式去擊球。
我當時如果能以更有意識的方式來做比較,就能使自己的球技得到提昇。然而,因為我沒有這麼做,最後只是搞得自己一整個晚上自信全失。當事情關係到自己時,我為什麼就不能像往常那樣做建設性的比較?
這是因為其中涉及我的自我價值。
如果說我當時對自己的價值突然沒了把握,這聽起來或許太過戲劇化,但我的意思是:我再也無法確定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件我認為很重要、而且也相信自己很擅長的事了。由於那次打球的經驗讓我的自我價值面臨危機,於是我就失去了做建設性比較的能力。這都是因為我太急切地想要證明自己夠好,而這正是我們很難以有建設性的方式進行社會比較的原因。大體上來說,如果你在做社會比較時,在意的是你的自我價值感,就必然會產生負面的情緒,而且很諷刺的是,你的自我價值感也幾乎必然會因此而降低。
關於社群媒體
談到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人氣這件事,我們就很難不提到社群媒體。社群媒體讓我們有機會彼此互動、保持聯絡,並對那些需要支持的人表達支持。這是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見的現象。然而,現代人之所以會普遍追求人氣,其原因也和社群媒體的存在有直接的關連,因為從這些媒體上得到認可時,我們的大腦會分泌出催產素、多巴胺,並使腦內的獎賞中樞產生其他一些化學反應,讓我們產生快感。此外,社群媒體的架構使我們得以控制並關注他人(以及群體)的行為。這也是這些媒體的大多數行銷策略背後的基本原則。最後一點,也是很重要的一點:社群媒體是我們進行社會比較(尤其是無意識的社會比較)最主要的一個場所。
在社群媒體上這種情況特別嚴重。我們在瀏覽社群媒體時往往處於某種「自動駕駛」(autopilot)狀態,此時我們的行為多少都有一些無意識的成分。由於我們不太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和他人比較,因此有可能會導致自我價值降低。對某些人而言,後果還不僅止於此。
研究顯示,愈需要增強自我價值的人愈會進行社會比較,但這卻使得他們的自我價值更加低落,因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還有一個例子也顯示出動機的重要性:有人原本想在社群媒體上尋求支持(這是社群媒體很善於提供的東西),沒想到卻反而不自覺地開始和別人比較起來。這種情況是很有可能發生的,因為社群媒體設計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我們進入這樣的情境。既然社群媒體會讓人落入社會比較的陷阱,無法自拔,我們似乎應該敬而遠之才對。事實上,有許多人也呼籲大眾應該減少使用社群媒體,以免危害自身的幸福與健康。
但既然我們喜愛社群媒體,而且它們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並不認為我們應該予以捨棄。事實上,有些研究也支持這樣的觀點。這些研究顯示,如果我們在使用時能更有自覺,社群媒體其實可以讓我們更加快樂。所以重點在於我們如何看待社群媒體的核心:社會比較。誠如我們所知,這類比較可能對我們有所幫助,但也可能對我們產生危害。
因此,如果在社群媒體上與人互動時,不去做這類無意識的社會比較,那麼在這些媒體上看到的正向貼文就會感染我們,對我們產生建設性的影響,而不會造成壓力。
因此,解決問題的方式並非不使用社群媒體,也不做社會比較,而是剛好相反。我們唯有更積極地關注自己的社會比較行為,才能實現社會比較的初衷:幫助我們發展自我,並且激勵我們變得更好。
人氣在大腦內引發的化學作用
澳洲有位名叫克里斯.戴維斯(Chris Davis)的教授曾經做過一個頗受矚目的實驗。他要那些自願參加實驗的人觀看一些陌生人的照片,並寫下他們對每一個人的喜好度,然後再告訴他們照片裡的人當中有哪幾位也喜歡他們(照片裡的人事先已經看過那些受試者的照片)。受試者身上都戴著連接到磁振造影設備的儀器,藉以測量他們的大腦活動。當受試者聽到有人喜歡他們時,他們大腦內的獎賞中樞就會立即產生反應。
這種反應攸關我們的發育與成長,因為它開始向我們發出訊號,要我們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並試著掙脫我們和父母之間的緊密關係,轉而尋求同儕的認可與關注。為了確保我們會持續努力脫離對父母的依附,尋求他人的認可,大腦會分泌兩種特定的物質—─催產素與多巴胺—─以活化獎賞中樞內的相關受體,讓我們感到愉悅。因此,我們之所以追求人氣並藉此獲得認可,乃是催產素和多巴胺這兩種效果強大的化學物質聯手作用的結果。
如今,當我看到有人對我在臉書或 Instagram 上所發布的訊息按讚時,之所以會開心,也是由同樣的化學作用所導致。這時,如果你剛好坐在我身邊,問我在做什麼,我甚至可能答不出來。有些研究確實顯示:這種追求大腦獎賞的行為都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進行的。
因此,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提昇覺察能力著手。
我們喜歡和別人比較
身為一個研究談判技巧的人,我很清楚一件事:如果我們知道別人所拿到的東西比我們少,就比較有可能會接受對方的提議。同樣的,我們可能也會因為別人所得到的東西比我們好,而向對方說「不!」。這是因為人們總是喜歡拿別人來和自己做比較。換句話說,我們總是不斷地在做「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追求人氣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會比較」有兩種形式。一種叫做「向下比較」(downward comparison)。當賣方因為其他人所出的價錢都比較少而接受某人的投標時,他(她)就是在進行「向下比較」。向下比較
我們可以用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後所出現的一種新式電影為例,來說明何謂「向下比較」。這種電影的內容就是描寫其他國家的窮人如何受到剝削,有時也被稱為「震驚紀錄片」(shockumentary)。這類影片的目的就是迎合人們在面臨經濟危機時的心理需求,讓那些生活艱辛的人感覺好過一些。它們往往把非洲或印尼的原始部落人民描寫成兇殘、粗野且生活條件極其惡劣的野蠻人,其效果就是讓一個或許剛剛失業的人只要花一張電影票的錢,就可以提昇他對自身生活的幸福感與滿意度,因為發現世上還有人過得比他更慘。
我們很可能會認為這類「向下比較」會讓我們感覺好過一些,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使我們剛開始時會因此而產生幸福感,但就長期而言,它的效果卻是負面的。舉例來說,有一群研究人員就做過一項調查。他們問一群警察是否認為當警察的人大致上要比當警衛的人優秀。結果他們發現:愈是認真比較兩者差異的警察,自尊心愈低,對自己的生活也愈不滿意。
研究人員所做的解釋是:當這些警察開始和他人做比較時,雖然他們是占優勢的一方,但這會讓他們開始藉由跟他人比較,來建立自己的自尊心並肯定自我的價值。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稍後我將會回過頭來再談談這種自我評價方式,因為社會比較是否具有建設性,關鍵就在於我們如何評價自我。另一種常見的社會比較方式就是所謂的「向上比較」。簡而言之,它指的就是把自己拿來和那些更優秀或者過得更好的人做比較。不久前我在社區的網球場上所經歷的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向上比較
話說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球友一起去網球場打球(我們每個星期打一次)。我們抵達時,剛好遇到一個之前曾和我的那位球友一起打球的人。當時他是一個人去,目的是要練習發球技巧。由於網球場上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別人,於是在開打之前,我們便邀請他和我們一起暖身。
我不認識那個人,但從開打前我的球友和他的對話中,我約略得知他是個網球高手,而且之前還是某個俱樂部的男子網球隊的選手。他第一次發球時,我光是聽那球拍發出的聲音就知道他果然是個高手,因為純粹為了健身而打球的人是不可能有那種架勢的。他必然已經練了很多年,而且可能還經過專業教練的調教。我意識到這一點時,起初非常振奮,因為我沒想到自己能碰上這樣的對手。這些年,我都是為了運動而打球,而且一直都是和同一個人打。現在我終於有機會領教真正的高手有多麼厲害,並藉此評估自己的球技了。
之前我的程度始終不曾達到足以代表網球俱樂部去比賽的水準,但現在我卻可以透過和這位高手過招,來間接達成參賽的夢想。
然而,才打了十分鐘,我就發現我和對方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距。總而言之,他打得就是比我好。
通常我打完球後心情都會很好,但這天晚上我卻沒有很開心,因為和那個高手比起來,我顯然還是不太行。原本我覺得自己打得還不錯,但如今看來我的球技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好。當那位高手離開後,我便一直沉浸在這樣的情緒中。可想而知,我後來和我的那位球友打球時,成績自然也不太理想。事實上,那一晚接下來的時間,我一直都為自己的網球夢的幻滅而耿耿於懷。
有意識的社會比較
身為一個喜愛建構模型的研究人員,我在做研究時向來都是使用所謂的「連續比較」(continual comparison)。這個名詞聽起來可能不太好懂,但實際上它的意思就是:當我發現某個有趣的現象時,就會把它拿來和已知的現象做比較,看看兩者之間有何異同,如此便能對我的研究素材有更多的認識。
這個過程其實和社會比較沒有太大的不同。早在一九五四年時,社會心理學家黎昂.費思汀格(Leon Festinger)就已經指出:社會比較的真正目的是要讓我們更認識自己,並且促進我們的成長與發展,就像我透過比較的方式來加深我對我的研究素材的理解一般。只可惜大多數人都不是這麼做。且容我再次以那個打網球的例子,來說明我們的意識與覺察在社會比較中所扮演的角色。
理論上,我其實可以透過和對手的比較得到許多有用的訊息,以便了解自己球技水準如何。比方說,開打二十秒鐘後,我就發現那人擊球的方式和我完全不同,拍子碰到球時所發出的聲音也更明顯。這時候,我與其去思考「誰打得比較好?」,倒不如分析他擊球的方式好在哪裡。他揮拍之前,我看到他的手腕甩了一下,或許那是原因之一?如果我當時問他,他或許能夠給我一些指點,因為他很可能已經在揮拍和擊球方面下了許多工夫。或許他甚至會教我該如何為網球拍穿線,讓我能以更適合我的步法的方式去擊球。
我當時如果能以更有意識的方式來做比較,就能使自己的球技得到提昇。然而,因為我沒有這麼做,最後只是搞得自己一整個晚上自信全失。當事情關係到自己時,我為什麼就不能像往常那樣做建設性的比較?
這是因為其中涉及我的自我價值。
如果說我當時對自己的價值突然沒了把握,這聽起來或許太過戲劇化,但我的意思是:我再也無法確定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件我認為很重要、而且也相信自己很擅長的事了。由於那次打球的經驗讓我的自我價值面臨危機,於是我就失去了做建設性比較的能力。這都是因為我太急切地想要證明自己夠好,而這正是我們很難以有建設性的方式進行社會比較的原因。大體上來說,如果你在做社會比較時,在意的是你的自我價值感,就必然會產生負面的情緒,而且很諷刺的是,你的自我價值感也幾乎必然會因此而降低。
關於社群媒體
談到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人氣這件事,我們就很難不提到社群媒體。社群媒體讓我們有機會彼此互動、保持聯絡,並對那些需要支持的人表達支持。這是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見的現象。然而,現代人之所以會普遍追求人氣,其原因也和社群媒體的存在有直接的關連,因為從這些媒體上得到認可時,我們的大腦會分泌出催產素、多巴胺,並使腦內的獎賞中樞產生其他一些化學反應,讓我們產生快感。此外,社群媒體的架構使我們得以控制並關注他人(以及群體)的行為。這也是這些媒體的大多數行銷策略背後的基本原則。最後一點,也是很重要的一點:社群媒體是我們進行社會比較(尤其是無意識的社會比較)最主要的一個場所。
在社群媒體上這種情況特別嚴重。我們在瀏覽社群媒體時往往處於某種「自動駕駛」(autopilot)狀態,此時我們的行為多少都有一些無意識的成分。由於我們不太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和他人比較,因此有可能會導致自我價值降低。對某些人而言,後果還不僅止於此。
研究顯示,愈需要增強自我價值的人愈會進行社會比較,但這卻使得他們的自我價值更加低落,因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還有一個例子也顯示出動機的重要性:有人原本想在社群媒體上尋求支持(這是社群媒體很善於提供的東西),沒想到卻反而不自覺地開始和別人比較起來。這種情況是很有可能發生的,因為社群媒體設計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我們進入這樣的情境。既然社群媒體會讓人落入社會比較的陷阱,無法自拔,我們似乎應該敬而遠之才對。事實上,有許多人也呼籲大眾應該減少使用社群媒體,以免危害自身的幸福與健康。
但既然我們喜愛社群媒體,而且它們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並不認為我們應該予以捨棄。事實上,有些研究也支持這樣的觀點。這些研究顯示,如果我們在使用時能更有自覺,社群媒體其實可以讓我們更加快樂。所以重點在於我們如何看待社群媒體的核心:社會比較。誠如我們所知,這類比較可能對我們有所幫助,但也可能對我們產生危害。
因此,如果在社群媒體上與人互動時,不去做這類無意識的社會比較,那麼在這些媒體上看到的正向貼文就會感染我們,對我們產生建設性的影響,而不會造成壓力。
因此,解決問題的方式並非不使用社群媒體,也不做社會比較,而是剛好相反。我們唯有更積極地關注自己的社會比較行為,才能實現社會比較的初衷:幫助我們發展自我,並且激勵我們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