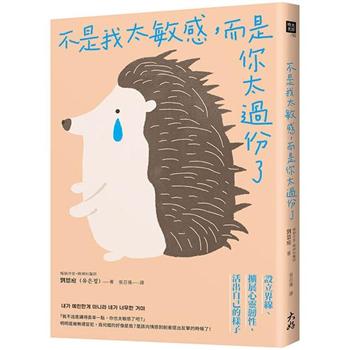◎連你也幸福的話我會很難熬,所以希望你過得不幸
觀察前來接受諮商者,會發現他們有幾個自我攻擊的修飾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敏感」這樣的表現。「敏感的人」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與生俱來,在性格上「敏感的人」(sensitive person);第二種是由於周邊環境、狀況或是面臨的問題,因此不得不變得尖銳的「處於敏感狀態者」(sensitive condition)。
本書所提到的「敏感」,指的不是與生俱來的個性,而是打算談一談上述的第二種情況,亦即突然接到對方不經意扔過來的球:「你為什麼因為一點小事那麼敏感」,卻還要高喊著「沒錯」的時候。因為這是情緒暴力的加害者與內心受創的被害人,兩者角色遭到互換的戲劇性瞬間。
◆行動來自習慣,話語反映人性;面由心生,觀相知人
在久違的大學同學會上,二十多歲的女孩宣荷經歷了相當荒唐的場面。當時她正和朋友們聊天,在家鄉和她就讀同一所國中、高中的好朋友,卻突然將宣荷的居住環境拿來當作話題。
「宣荷從鄉下上來後,住在考試院生活耶!不覺得很厲害嗎?我覺得超恐怖,我絕對沒辦法住在考、試、院。」
在那一瞬間,宣荷感受到莫大的羞愧感。住在考試院並不是問題,而是自己的情況在未經同意下就被洩露出去,因此無可厚非地升起那樣的情緒。高喊著沒辦法住在考試院的朋友,目前寄居在首爾的阿姨家。
相識十五年的那位朋友,在宣荷率先進到理想的公司任職時,就開始對她進行情緒方面的攻擊;甚至在她談戀愛之後,不分青紅皂白的進犯又變得更加嚴重。
朋友會看著文具迷宣荷蒐集來的原子筆,勸說道:「蒐集那些原子筆是要用在哪裡啊?換個成熟一點的興趣如何?」看到宣荷打算和男友一起欣賞而預購音樂劇票,她會感嘆地說:「怎麼現在才要去看啊?」當得知宣荷正在上語學院時,又會說「那間補習班不怎麼樣」,然後告訴她自己所掌握到的高級情報。
現在,就讓我們反過來分析看看,這位「極度」為宣荷著想的朋友所說的話:她用「成熟一點的興趣」來貶低宣荷蒐集文具的嗜好;對期待觀賞音樂劇而興奮不已的宣荷,她以失落感來顛覆那純粹的幸福;不僅如此,連宣荷努力打聽後報名的語學院,她也用「那間補習班不怎麼樣」,讓宣荷對自己的選擇產生懷疑。藉由「那點東西」、「我覺得不怎麼樣」、「不過才……」、「唉唷」等幾句嘆息的話,毀壞宣荷的情緒領地,這就是經常被提到的「友情勒索」。
「邏輯性的對策」、「合理的懷疑」、「真正的安慰」,那些人在耳邊嘀嘀咕咕的所謂「知心話」,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
「如果連你也變得幸福的話,我不就太難熬了嘛!所以不管他人怎樣,至少你不可以比我幸福。若你能一直這麼不幸就好了。」
一個人的行動源自於習慣,話語則反映了人性,正所謂面由心生,觀相可以知人。
◆另一種狗與狼的時間──友敵
最近在診療室遇見的來談者,有很多人都吐露了關於「友敵」(frenemy)的煩惱。所謂的「友敵」,是由朋友(friend)與敵人(enemy)兩個詞組合而成,使用在不知道身邊的人是為自己祈求好運的真正朋友,或只是假借「朋友」名義卻胡亂眼紅、嫉妒的人。我個人想要這樣定義:友敵不是為了證明朋友確實存在,而是想要否定朋友存在之人。
友敵大部分是情感的剝削者,也是情感的掠食者,以一句話概括可以稱之為「情感吸血鬼」。他們就像宣荷的朋友一樣,隱約地顯露出敵意,破壞他人的心情,然後當對方為了自我防禦和自我保護,表現出「你越線了」的時候,就生氣地嚷著「你是不是有點奇怪」、「會不會太敏感了啊」。明明先侵犯他人的領域,卻在對方要求遵守禮儀時大發脾氣,連在表達歉意時也過於理直氣壯,反倒讓接受道歉的人覺得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事。
情感吸血鬼的目標只有一個:犧牲對方來降低自身的劣等感,並藉此確認自己處於優勢地位。因此,他們不斷地去動搖對方,試圖增加其不安與恐懼。他們躺在灰塵滿布的房間地板上,透過嫉妒、憤怒、同情、憐憫等,想盡辦法讓對方和自己一樣跌入谷底;他們牢牢抓住努力邁出步伐之人的腳踝,嘲諷道:「談戀愛之後整個人都變了呀」、「房價漲了就耀武揚威啦」、「出生在好人家,生活過得真是愜意呢」,用帶著挑釁的話語和行動,不斷刺激對方使其變得敏感。若對方覺得生氣,他們就會解釋「自己說的話沒有惡意」,打算一笑置之。
自己的本陣受到襲擊,沒有一位選手還可以處之泰然地繼續進行比賽。在防禦時變得極度敏感是很正常的事,若對方不喜歡我變得敏感,那麼一開始就不應該越線。
關鍵就在這裡:沒有惡意的話語和行動!我很想問問這些人:到底想要從事什麼?有什麼樣的生活目標?是否曾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奮力奔跑過?有沒有真心對待過他人,並且對自己的分內之事全力以赴?因為自己無法順心如意,就想讓拚命掙扎的人嘗到失落感,將他人推入倦怠的深淵,這種悲觀的理論究竟是從哪裡學來的呢?即使做不到去鼓勵、稱讚用心生活的人,也不應該將之貶低為「只是單純地運氣好」。
此外,更重要的是,像宣荷這樣的被剝削者,必須懂得讓情感吸血鬼停止突然地跳進圍牆裡來,在自己的前院享受野餐。他們二十四小時佔據了你的時間或情感,以便在自己需要時可以任意開門進入。若對於這種毫無預兆的突襲感到倦怠,忍不住對他們說:「不好意思,今天可不可以請你先回去?」他們就會回嘴道:「你平常都不會這樣,今天特別敏感耶!」、「真是沒有幽默感」、「感性的傢伙」、「認真鬼」等等。因為是朋友、因為是家人,是出於信任才找上門的,怎麼可以如此傷人呢?他們一邊這麼說,一邊將自己無禮和冒犯的責任,反過來推到你身上。
每次宣荷只要與那位朋友見面,就總是會變得敏感,心情也跟著低落,我對著不清楚原因為何的她這麼說:
「宣荷,你並不是無緣無故變得敏感,那位朋友不經大腦的話語和行動總是刺激到你,讓你的感覺變得尖銳。並不是宣荷你過於敏感,而是那位朋友太過份了。」
◆現在,你需要具備三種覺悟
如果厭倦了「單方面付出,卻總是受傷」的情況,從現在開始,就要懂得培養守護自己情緒領地的力量。「會不會顯得過於敏感?」、「我會不會看起來太刻薄?」、「是不是有可能被冷落?」無論如何,都沒有必要因為這些擔心而疏於保護自己,或者對守衛自己的情緒領地趨於消極。我真的很厭惡那種明知道對方會受傷,卻不肯多加小心,還把自己的漫不經心與無禮歸咎為對方太過敏感,並對此窮追猛打的人。
若想把侵略情緒領地,還坐在那假裝自己是主人的情感吸血鬼趕出去,首先必須具備積極主動的態度。也就是說,現在是時候拋棄熟悉的關係與被動的心態所帶來的安全感了,而這樣的你,只需要做到以下三項:
第一,要有「決心」恢復自己被侵略的情緒領地;第二,「冷靜」地區分我的基準和你的基準不同;最後,必須要具備能夠加以靈活分辨的「決斷力」──在不安的氣氛中,一步步朝我走近的黑影,究竟是平時可以信任且依靠的忠犬,還是打算前來傷害我自尊心的野狼?
來吧,現在「狼與狗」的時間開始了!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展開戰鬥吧!
◎以「為了你」開頭的話,為什麼最後變成「為了我」
繼千禧世代(一九八○年代中期至一九九○年代中期出生者)之後,Z世代(一九九○年代中期至二○○○年代中期出生者)的出現為韓國社會帶來了全新衝擊。約佔人口百分之十五的Z世代族群中,大約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持有智慧型手機,因為從小接觸的數位及媒體影響,他們對於IT擁有敏銳的觸角,而且對趨勢變化相當敏感。比起線下的世界,他們更熟悉網路生態,因此又被稱為「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
如果說以前的世代偏於理想主義,那麼Z世代族群則獨立性強、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優先看重經濟方面的價值,並且追求公正的遊戲規則與報酬。上述為媒體所定義的九○年代出生者的特徵,此外,「沒教養」、「自私」、「斤斤計較」、「個人主義」、「追求合理」等,是和九○年代出生者一起在職場工作過的人,共同做出的評價。◆有「惡婆婆症候群」的前輩們
雖然擁有創世以來最好的資歷,但是卻被要求不斷努力的Z世代。這個世代的族群,格外被賦予許多華麗的修飾語,然而,這樣的「標籤化」對當事者來說,也有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暴力。因為隱隱約約將Z世代「他者化」(讓特定對象看起來與眾不同,刻意用話語或行動強調其為遭受分離的存在)的社會氛圍,很可能被當事者解讀成是要求「保持距離」的信號。
而Z世代與年長一輩的人之間的矛盾,幾乎已到達戰爭的程度,這也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在下班的二十~三十分鐘前就開始換衣服、補妝,大概是覺得沒有準時下班就算權益受損……一定就是九○年生,九○年生的才會那樣。」
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確實可能為此感到不滿。然而,在這句話裡面,似乎也藏有惡婆婆症候群:「這段時間我受了多少苦,就你一個人想過得輕鬆嗎」、「既然把我寶貝的兒子帶走了,當然也要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啊」。在諮商的過程中,我也曾被Z世代獨特的思考方式嚇一跳,不過,對此我只覺得是相當新穎的世代衝擊,並不至於劃線將他們歸類為「與我們不同的種族」。
或許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吧?「就算你認為很合理,但社會生活不是這樣過的」、「我是為了你著想才這麼說的……」、「想當年我們……」,以這些句子為開頭的忠告,很多時候並不是為了對方設想,而是說話的人替自己在做盤算。不然的話,「為了你著想才這麼說的……」,最後卻變成「為了我、為了團隊、為了公司,請你務必要這麼做」,這樣的結尾又該如何解釋呢?
◆源自原始型態關係的誤解
從演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對於陌生且未知的事物,自動會將其視為「怪物」,這是幾近於本能的反應。由於大腦是為了生存而組成的集合體,因此會對「初次見到且陌生的事物」發出警告訊號,在認清對方的真面目之前保持一定距離,並盡可能在確保安全之前不過於靠近對方。
如果我們的先祖看到老虎,就因為好奇心而毫無保留地撲上去,那麼說不定現在就沒有人類的存在了。因此,九○年代出生者與既存世代的衝突,可以說是源自於「無法好好了解彼此」的原始型態關係。至今為止,在診療室中遇見的九○年代出生者,和過去的世代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依舊比任何人更想擁有美麗的外貌,希望有智慧地解決與父母之間的矛盾,也期盼從長期應考生活導致的孤立感中脫離。
當然,解決引發心理問題的環境,處理方式的確會與以往不同,但我想說的是:他們的個人主義只是因應時代變化而來的特質,並非是弱點或是需要改善的部分。
◆「問題很多的九○年代生」VS. 「總是倚老賣老的上一代」
若想接納與自己個性不同的人,就要努力將其視為「個別的存在」,而非「一個特定的世代」。現在,就試著將「問題很多的九○年代生」與「總是倚老賣老的上一代」這樣的範疇劃分,個體化為「○○○組長」和「○○○組員」吧,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核心。
不久前,有一位來談者表示自己領養了狗,當時我預估大約是馬爾濟斯那樣的程度。沒想到,在照片中露出燦笑的狗狗,是因為「桑根」而廣為人知的大白熊犬(Great Pyrenees)。大白熊犬也屬於「狗」的範疇,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牠和小型犬馬爾濟斯就變成了同一類別,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理解他人時,「個體化」會變得至關重要。
社會學家們表示,比起個人的價值觀,必須要更重視集體的價值觀才能讓社會和諧地運轉。但是,現在的我們必須接受「各自謀生」已成為一種日常的新形態(New Normal),隱密的集權主義不再有立足之地。
最後,就像社會或老一輩的人用「九○年代生」來綑綁和稱呼年輕人,很有可能會淪為情緒暴力一般,新世代的年輕人將前輩一概歸類為「老古板」,這點也同樣需要注意。此外,所謂的「老古板」說的話,也不一定全都是毫無價值的嘮叨,一定也會有不少對當事人有幫助的意見。倘若被侷限在「老一輩=老古板」的框架裡,那麼錯過這些建言肯定是種損失。
而其中的關鍵在於主觀和獨斷是不同的,主觀為提出個人獨到的見解和看法,而獨斷則是無視客觀性的依據,自己單方面地判斷或決斷事務。我們雖然需要具備明智的主觀意識,卻也同時要小心落於危險的獨斷專行。在診療室裡,有些人覺得獲取的建言對自己有益,就會拚命地想牢牢把握住;相對的,有些人無論我提出什麼樣必要的建議,他也絲毫聽不進去半句。當然,通常前者的癒後情況會較為良好。唯有一點需要注意,就像前文所提到的,以「我是為了你著想……」做為開頭的忠告,結尾卻變成「為了我……」、「為了我們……」的話,那麼果敢地忽略這樣的建議也無所謂,因為那些言語,才真正是毫無用處的「倚老賣老」。
觀察前來接受諮商者,會發現他們有幾個自我攻擊的修飾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敏感」這樣的表現。「敏感的人」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與生俱來,在性格上「敏感的人」(sensitive person);第二種是由於周邊環境、狀況或是面臨的問題,因此不得不變得尖銳的「處於敏感狀態者」(sensitive condition)。
本書所提到的「敏感」,指的不是與生俱來的個性,而是打算談一談上述的第二種情況,亦即突然接到對方不經意扔過來的球:「你為什麼因為一點小事那麼敏感」,卻還要高喊著「沒錯」的時候。因為這是情緒暴力的加害者與內心受創的被害人,兩者角色遭到互換的戲劇性瞬間。
◆行動來自習慣,話語反映人性;面由心生,觀相知人
在久違的大學同學會上,二十多歲的女孩宣荷經歷了相當荒唐的場面。當時她正和朋友們聊天,在家鄉和她就讀同一所國中、高中的好朋友,卻突然將宣荷的居住環境拿來當作話題。
「宣荷從鄉下上來後,住在考試院生活耶!不覺得很厲害嗎?我覺得超恐怖,我絕對沒辦法住在考、試、院。」
在那一瞬間,宣荷感受到莫大的羞愧感。住在考試院並不是問題,而是自己的情況在未經同意下就被洩露出去,因此無可厚非地升起那樣的情緒。高喊著沒辦法住在考試院的朋友,目前寄居在首爾的阿姨家。
相識十五年的那位朋友,在宣荷率先進到理想的公司任職時,就開始對她進行情緒方面的攻擊;甚至在她談戀愛之後,不分青紅皂白的進犯又變得更加嚴重。
朋友會看著文具迷宣荷蒐集來的原子筆,勸說道:「蒐集那些原子筆是要用在哪裡啊?換個成熟一點的興趣如何?」看到宣荷打算和男友一起欣賞而預購音樂劇票,她會感嘆地說:「怎麼現在才要去看啊?」當得知宣荷正在上語學院時,又會說「那間補習班不怎麼樣」,然後告訴她自己所掌握到的高級情報。
現在,就讓我們反過來分析看看,這位「極度」為宣荷著想的朋友所說的話:她用「成熟一點的興趣」來貶低宣荷蒐集文具的嗜好;對期待觀賞音樂劇而興奮不已的宣荷,她以失落感來顛覆那純粹的幸福;不僅如此,連宣荷努力打聽後報名的語學院,她也用「那間補習班不怎麼樣」,讓宣荷對自己的選擇產生懷疑。藉由「那點東西」、「我覺得不怎麼樣」、「不過才……」、「唉唷」等幾句嘆息的話,毀壞宣荷的情緒領地,這就是經常被提到的「友情勒索」。
「邏輯性的對策」、「合理的懷疑」、「真正的安慰」,那些人在耳邊嘀嘀咕咕的所謂「知心話」,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
「如果連你也變得幸福的話,我不就太難熬了嘛!所以不管他人怎樣,至少你不可以比我幸福。若你能一直這麼不幸就好了。」
一個人的行動源自於習慣,話語則反映了人性,正所謂面由心生,觀相可以知人。
◆另一種狗與狼的時間──友敵
最近在診療室遇見的來談者,有很多人都吐露了關於「友敵」(frenemy)的煩惱。所謂的「友敵」,是由朋友(friend)與敵人(enemy)兩個詞組合而成,使用在不知道身邊的人是為自己祈求好運的真正朋友,或只是假借「朋友」名義卻胡亂眼紅、嫉妒的人。我個人想要這樣定義:友敵不是為了證明朋友確實存在,而是想要否定朋友存在之人。
友敵大部分是情感的剝削者,也是情感的掠食者,以一句話概括可以稱之為「情感吸血鬼」。他們就像宣荷的朋友一樣,隱約地顯露出敵意,破壞他人的心情,然後當對方為了自我防禦和自我保護,表現出「你越線了」的時候,就生氣地嚷著「你是不是有點奇怪」、「會不會太敏感了啊」。明明先侵犯他人的領域,卻在對方要求遵守禮儀時大發脾氣,連在表達歉意時也過於理直氣壯,反倒讓接受道歉的人覺得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事。
情感吸血鬼的目標只有一個:犧牲對方來降低自身的劣等感,並藉此確認自己處於優勢地位。因此,他們不斷地去動搖對方,試圖增加其不安與恐懼。他們躺在灰塵滿布的房間地板上,透過嫉妒、憤怒、同情、憐憫等,想盡辦法讓對方和自己一樣跌入谷底;他們牢牢抓住努力邁出步伐之人的腳踝,嘲諷道:「談戀愛之後整個人都變了呀」、「房價漲了就耀武揚威啦」、「出生在好人家,生活過得真是愜意呢」,用帶著挑釁的話語和行動,不斷刺激對方使其變得敏感。若對方覺得生氣,他們就會解釋「自己說的話沒有惡意」,打算一笑置之。
自己的本陣受到襲擊,沒有一位選手還可以處之泰然地繼續進行比賽。在防禦時變得極度敏感是很正常的事,若對方不喜歡我變得敏感,那麼一開始就不應該越線。
關鍵就在這裡:沒有惡意的話語和行動!我很想問問這些人:到底想要從事什麼?有什麼樣的生活目標?是否曾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奮力奔跑過?有沒有真心對待過他人,並且對自己的分內之事全力以赴?因為自己無法順心如意,就想讓拚命掙扎的人嘗到失落感,將他人推入倦怠的深淵,這種悲觀的理論究竟是從哪裡學來的呢?即使做不到去鼓勵、稱讚用心生活的人,也不應該將之貶低為「只是單純地運氣好」。
此外,更重要的是,像宣荷這樣的被剝削者,必須懂得讓情感吸血鬼停止突然地跳進圍牆裡來,在自己的前院享受野餐。他們二十四小時佔據了你的時間或情感,以便在自己需要時可以任意開門進入。若對於這種毫無預兆的突襲感到倦怠,忍不住對他們說:「不好意思,今天可不可以請你先回去?」他們就會回嘴道:「你平常都不會這樣,今天特別敏感耶!」、「真是沒有幽默感」、「感性的傢伙」、「認真鬼」等等。因為是朋友、因為是家人,是出於信任才找上門的,怎麼可以如此傷人呢?他們一邊這麼說,一邊將自己無禮和冒犯的責任,反過來推到你身上。
每次宣荷只要與那位朋友見面,就總是會變得敏感,心情也跟著低落,我對著不清楚原因為何的她這麼說:
「宣荷,你並不是無緣無故變得敏感,那位朋友不經大腦的話語和行動總是刺激到你,讓你的感覺變得尖銳。並不是宣荷你過於敏感,而是那位朋友太過份了。」
◆現在,你需要具備三種覺悟
如果厭倦了「單方面付出,卻總是受傷」的情況,從現在開始,就要懂得培養守護自己情緒領地的力量。「會不會顯得過於敏感?」、「我會不會看起來太刻薄?」、「是不是有可能被冷落?」無論如何,都沒有必要因為這些擔心而疏於保護自己,或者對守衛自己的情緒領地趨於消極。我真的很厭惡那種明知道對方會受傷,卻不肯多加小心,還把自己的漫不經心與無禮歸咎為對方太過敏感,並對此窮追猛打的人。
若想把侵略情緒領地,還坐在那假裝自己是主人的情感吸血鬼趕出去,首先必須具備積極主動的態度。也就是說,現在是時候拋棄熟悉的關係與被動的心態所帶來的安全感了,而這樣的你,只需要做到以下三項:
第一,要有「決心」恢復自己被侵略的情緒領地;第二,「冷靜」地區分我的基準和你的基準不同;最後,必須要具備能夠加以靈活分辨的「決斷力」──在不安的氣氛中,一步步朝我走近的黑影,究竟是平時可以信任且依靠的忠犬,還是打算前來傷害我自尊心的野狼?
來吧,現在「狼與狗」的時間開始了!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展開戰鬥吧!
◎以「為了你」開頭的話,為什麼最後變成「為了我」
繼千禧世代(一九八○年代中期至一九九○年代中期出生者)之後,Z世代(一九九○年代中期至二○○○年代中期出生者)的出現為韓國社會帶來了全新衝擊。約佔人口百分之十五的Z世代族群中,大約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持有智慧型手機,因為從小接觸的數位及媒體影響,他們對於IT擁有敏銳的觸角,而且對趨勢變化相當敏感。比起線下的世界,他們更熟悉網路生態,因此又被稱為「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
如果說以前的世代偏於理想主義,那麼Z世代族群則獨立性強、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優先看重經濟方面的價值,並且追求公正的遊戲規則與報酬。上述為媒體所定義的九○年代出生者的特徵,此外,「沒教養」、「自私」、「斤斤計較」、「個人主義」、「追求合理」等,是和九○年代出生者一起在職場工作過的人,共同做出的評價。◆有「惡婆婆症候群」的前輩們
雖然擁有創世以來最好的資歷,但是卻被要求不斷努力的Z世代。這個世代的族群,格外被賦予許多華麗的修飾語,然而,這樣的「標籤化」對當事者來說,也有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暴力。因為隱隱約約將Z世代「他者化」(讓特定對象看起來與眾不同,刻意用話語或行動強調其為遭受分離的存在)的社會氛圍,很可能被當事者解讀成是要求「保持距離」的信號。
而Z世代與年長一輩的人之間的矛盾,幾乎已到達戰爭的程度,這也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在下班的二十~三十分鐘前就開始換衣服、補妝,大概是覺得沒有準時下班就算權益受損……一定就是九○年生,九○年生的才會那樣。」
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確實可能為此感到不滿。然而,在這句話裡面,似乎也藏有惡婆婆症候群:「這段時間我受了多少苦,就你一個人想過得輕鬆嗎」、「既然把我寶貝的兒子帶走了,當然也要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啊」。在諮商的過程中,我也曾被Z世代獨特的思考方式嚇一跳,不過,對此我只覺得是相當新穎的世代衝擊,並不至於劃線將他們歸類為「與我們不同的種族」。
或許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吧?「就算你認為很合理,但社會生活不是這樣過的」、「我是為了你著想才這麼說的……」、「想當年我們……」,以這些句子為開頭的忠告,很多時候並不是為了對方設想,而是說話的人替自己在做盤算。不然的話,「為了你著想才這麼說的……」,最後卻變成「為了我、為了團隊、為了公司,請你務必要這麼做」,這樣的結尾又該如何解釋呢?
◆源自原始型態關係的誤解
從演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對於陌生且未知的事物,自動會將其視為「怪物」,這是幾近於本能的反應。由於大腦是為了生存而組成的集合體,因此會對「初次見到且陌生的事物」發出警告訊號,在認清對方的真面目之前保持一定距離,並盡可能在確保安全之前不過於靠近對方。
如果我們的先祖看到老虎,就因為好奇心而毫無保留地撲上去,那麼說不定現在就沒有人類的存在了。因此,九○年代出生者與既存世代的衝突,可以說是源自於「無法好好了解彼此」的原始型態關係。至今為止,在診療室中遇見的九○年代出生者,和過去的世代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依舊比任何人更想擁有美麗的外貌,希望有智慧地解決與父母之間的矛盾,也期盼從長期應考生活導致的孤立感中脫離。
當然,解決引發心理問題的環境,處理方式的確會與以往不同,但我想說的是:他們的個人主義只是因應時代變化而來的特質,並非是弱點或是需要改善的部分。
◆「問題很多的九○年代生」VS. 「總是倚老賣老的上一代」
若想接納與自己個性不同的人,就要努力將其視為「個別的存在」,而非「一個特定的世代」。現在,就試著將「問題很多的九○年代生」與「總是倚老賣老的上一代」這樣的範疇劃分,個體化為「○○○組長」和「○○○組員」吧,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核心。
不久前,有一位來談者表示自己領養了狗,當時我預估大約是馬爾濟斯那樣的程度。沒想到,在照片中露出燦笑的狗狗,是因為「桑根」而廣為人知的大白熊犬(Great Pyrenees)。大白熊犬也屬於「狗」的範疇,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牠和小型犬馬爾濟斯就變成了同一類別,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理解他人時,「個體化」會變得至關重要。
社會學家們表示,比起個人的價值觀,必須要更重視集體的價值觀才能讓社會和諧地運轉。但是,現在的我們必須接受「各自謀生」已成為一種日常的新形態(New Normal),隱密的集權主義不再有立足之地。
最後,就像社會或老一輩的人用「九○年代生」來綑綁和稱呼年輕人,很有可能會淪為情緒暴力一般,新世代的年輕人將前輩一概歸類為「老古板」,這點也同樣需要注意。此外,所謂的「老古板」說的話,也不一定全都是毫無價值的嘮叨,一定也會有不少對當事人有幫助的意見。倘若被侷限在「老一輩=老古板」的框架裡,那麼錯過這些建言肯定是種損失。
而其中的關鍵在於主觀和獨斷是不同的,主觀為提出個人獨到的見解和看法,而獨斷則是無視客觀性的依據,自己單方面地判斷或決斷事務。我們雖然需要具備明智的主觀意識,卻也同時要小心落於危險的獨斷專行。在診療室裡,有些人覺得獲取的建言對自己有益,就會拚命地想牢牢把握住;相對的,有些人無論我提出什麼樣必要的建議,他也絲毫聽不進去半句。當然,通常前者的癒後情況會較為良好。唯有一點需要注意,就像前文所提到的,以「我是為了你著想……」做為開頭的忠告,結尾卻變成「為了我……」、「為了我們……」的話,那麼果敢地忽略這樣的建議也無所謂,因為那些言語,才真正是毫無用處的「倚老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