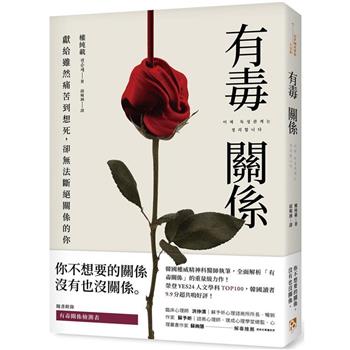※試閱範圍為摘錄。
Chapter1
摧毀存在的有毒關係——有毒關係的主導者、協力者、犧牲者
*有毒關係不知不覺就開始了
患者K來找身為身心科醫生的我就醫
來到診療室的男性患者K是位三十五歲左右的牙科醫生。身材消瘦,穿著端莊的休閒式正裝,給人乾淨俐落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他看起來也極度敏感且有氣無力。混濁眼鏡鏡片後的雙眼,也如鏡片一樣模糊不清。即使說句客套話,也無法說他這樣的形象會帶給人好感。
K的個性誠實細心,從未在服務的醫院中惹過麻煩,但大家對他的評價仍舊不太好。雖然他個性不是親切且善於社交,但也不會隨便對待身邊的人或病人。整體而言,他彬彬有禮,即使面對年紀比自己小的人也會使用尊稱。事情發生在公司聚餐時,一位一起共事的年輕口腔衛生師對他的穿著開了玩笑,他突然站起來咆哮道:
「對我指指點點的,你算老幾?你就那麼了不起嗎?我知道你平常就瞧不起我!」
在場的人當然全都僵住了,因為他的能力或社會地位並不到會被瞧不起的程度,而且那位同事說的話在其他人聽來也不構成什麼問題,甚至更像是親密友好的表現。但K的怒火無法平息,最後年輕同事哭著跑了出去。K逃亡似地逃離了突然散場的局,回到家後在浴室裡用蓮蓬頭水管捆住自己的脖子,要不是他的老婆察覺到後趕緊勸阻,差點就要發生可怕的憾事。
其實K不是第一次這樣因為別人的話而勃然大怒了。雖然他看起來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人,但不經意的一句話就能讓他發脾氣。大部分K身邊的人並不知道他為何生氣,只是開始與他疏遠,K也不打算為此多做解釋。問題在於K生氣之後的心理狀態,每當碰上這樣的夜晚,K便會深陷在悲慘與羞恥的情緒中。雖然他很後悔自己發了脾氣,但聽到那些話的當下確實感到自己被侮辱與瞧不起。
我這麼問他:
「所以你也不理解自己為什麼會在那種情況下感到受侮辱和生氣吧?」
他回答道:
「不是的,醫生,我知道我為什麼生氣,以及這憤怒和受侮辱的感覺從何而來,就是因為我和我父親之間的關係。但儘管如此,我還是改變不了。我想知道的是結束這痛苦關係的方法。」
意外的是,K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問題。他的行為是如何惡化他的社會立場、為什麼他會這麼容易感覺被他人侮辱,以及這樣的問題如何搞砸自己的人生,這些問題他都可以條理分明地說明,讓精神醫學科醫師都感到驚訝。他對自身問題的優異洞察說明了他不斷努力與反省以擺脫自己的問題,但他依舊痛苦纏身,無論多麼深思自己的問題,多麼努力原諒自己,他和帶給他痛苦的父親之間的關係始終沒有改變,甚至問題到現在都還持續。我明白,K仍被折磨自己一輩子的有毒關係所束縛並痛苦著。
那天,K不知為何就成了有毒關係的犧牲者
K和父親的有毒關係可以追溯到他結束高中三年的宿舍生活,開始念大學的時候。K出生於雙親從商的家庭,度過相對平凡的青少年時期。K高中的時候是優秀的學生,但也常聽人家說他不知變通。他總是死板地遵守校規,因此受到同學們的嫌惡,不過整體而言,他是家裡的驕傲,無論別人或他自己,都相信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大學入學考試以優異成績考上牙醫大學後,就像多數大學生一樣,他搬到學校附近開始獨立生活。
那年,K 離開鬱悶的宿舍,陶醉在二十歲大學生自由之中。他的父母在郊區做生意,並住在附近的公寓。三月,他暌違一個月後回到父母居住的家。那是他獨立生活後的一個月,坐在餐廳的K 興高采烈地訴說成年男性的大學新生故事,但過了一會後他才察覺到不對勁,父母一直看也不看他一眼,也不回應他的話。這時,K 的父親突然憤憤地開口了:
「你瘋了嗎?」
K 傻住了,突然襲來的咒罵就像插上胸口的匕首,但他連感到疼痛的時間都沒有,只有臉變得通紅。比起痛,他更感到羞愧。因為不知道被罵的原因是什麼,K本能地開始回想自己的行為有什麼問題,肯定有什麼他不知道的原因,但他就是不明白。他好像成了不懂事的孩子,因為自己的愚蠢行為而陷入困境。本來保持沉默的K 父親丟下筷子就走了,理由是沒胃口。K 雖然嚇傻了,但還是吞下口中咀嚼的飯粒。這時的羞愧感從此折磨了他一輩子。
K在自己的房裡休息時,他母親叫他去主臥室,讓父親消氣。他進到臥室,父親還是看也不看他一眼,就這樣三十分鐘過去,不自在與不安的感覺讓他就快窒息了(此後,K患上嚴重的恐慌症)。就跟吃飯時一樣,K的父親不悅地開口了:
「你回來幹嘛?」
雖然是毫無頭緒的問題,但他還是回答自己是回來探望父母,並問了父親是不是心情不好。無論如何,都得要讓父親消氣才行。父親卻開始瞪著他。
「嘖!」
一瞬間,K 的眼前一片空白。回過神時,只有臉上燙傷般的疼痛感,他被賞了一巴掌。K 的父親以前也經常打他,但那只會在K說謊之類,明確犯錯的時候。因為有明確的形式和原因,因此也有宣告結束的某種程序。然而,剛剛的疼痛卻是出自個人的,那並不是一種程序,而是個人的報仇或暴力。像是國中生走在暗巷被高中生施暴搶錢一樣,不知道會以什麼方式進行,也不知道何時會結束,K 當時就像那樣,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他未曾想過要抵抗父親,於是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K 的思考就停滯了。在此同時,K 的父親一邊喝著啤酒,一邊看著電視上的高爾夫球比賽,然後突然問了K:
「你不知道你做錯了什麼嗎?」
K 不記得自己當時回答了什麼,只記得在毫無防備下,被父親踹了胸口而在地上打滾。那天他所受到的衝擊,讓他這十多年間沒有一天不想起。然而,當時的K 還想像不到,這樣的關係在十多年間的每週反覆上演。那天有毒關係開始,徹底摧毀了K 的靈魂。
*有毒關係一旦形成,便逐漸具有破壞性及不斷強化
K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就是有毒關係的典型樣貌。無論是發生於家庭或職場,所有有毒關係都有幾項共同特徵。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我將關係中的對象分為兩種。主導有毒關係,給對方造成有毒影響、試圖操縱對方的人,稱為「主導者」;而從屬於有毒關係、被這種關係操縱並因此受害的人,則稱之為「犧牲者」。
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壓倒性的力量差異
有毒關係發生於力量有著壓倒性差異的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即父母與子女、師長與徒弟、前輩與後輩、上司與下屬等。有毒關係越是持續,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的力量差距就會越來越大。必須留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力量差異,不僅僅是物理性的力量差異;例如讓主導者K 的父親與犧牲者K之間形成有毒關係的力量差異,就不是物理性的力量差異。當時的K 或許稱不上是健壯,但大致上算是健康、體力達平均標準的普通年輕人,所以即使是充斥著毆打、謾罵、人格侮辱的有毒關係,K的體力也絕不會抵抗不了邁入老年期的父親。然而,人與人之間,社會經濟地位遠比物理性的力量更具影響力。大學時期的K 除了課餘時間的打工之外,並沒有其他收入。雖然就年齡看來他已是成年人,但就社會經濟層面而言,他並不是可以獨立自主的成年人。相反地,主導者K 的父親在社會上是受人尊敬的有錢人,更重要的是,他具備了豐富經驗所鍛鍊出來的純熟社會技能與歷練,以及可以動搖許多人的手腕與影響力。
當K試圖以力量對抗父親的那瞬間,K在社會上就成了對父母施暴的絕世逆子而受世人指責,並被斷絕了所有經濟上的支援。儘管K年輕而且力氣較大,但他能夠戰勝父親的機率連百分之一都不到。他們都在本能上清楚知道兩人之間的力量差距,K其實也曾在父親的暴力之下,為了保護自己的身體舉起拳頭,但他鼓起勇氣舉起的拳頭,卻因為父親大聲喝斥:「你竟敢想對我動手?」而無力地放下了。雖然K和父親之間的有毒關係所帶來的影響,對當事者K而言是破壞了他整個人生的驚人大事,但諷刺的是,在K當時生活的韓國社會裡,這只是無法被定罪的瑣碎小事。
就算是夫妻、同學、手足等名義上看似平等的關係,若仔細觀察這些關係就會發現,在形成有毒關係之前,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有著壓倒性力量差異是很常見的。父權文化普遍存在,於是在婚姻生活或家庭失和被無條件認為是女人責任的社會裡,夫妻之間就很容易產生有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或社會偏見等要素,就是在主導者與犧牲者的有毒關係中,明確區分力量優劣的重要因素。若好好觀察看似平等的國、高中同班同學之間發生的有毒關係,會發現他們生活其中並稱之為班級的這種特定組織裡,經常可見主導者擁有比犧牲者更具壓倒性影響力的情況。這樣的力量優劣非常堅固,無法輕易被推翻。
有毒關係一旦形成便會不斷強化
有毒關係具有強烈的持續性與逐漸嚴重的破壞性。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心理方面的優劣,當關係中發生虐待、惡言等破壞性行為時,人與人之間便會產生某種心理動態,也就是流動與模式。一旦心的流動固定下來,就會漸漸形成某種固定的形態,形成固定形態的有毒關係會抗拒改變,於是不平衡且具破壞性的流動便會繼續維持。
剛滿二十歲的K 並沒有意識到有毒關係開始了。因此,他把父親突然對自己的人格侮辱與暴力,僅僅當作是父親一時的反覆無常。然而,父親毫無理由(但他自認為理由充分)行使暴力的那天,還只是個開始而已。隨著時間過去,拳頭之後動粗口、罵完之後動拳頭、人格侮辱、把K 當成隱形人,這些都只是根據不同情況改變形態而已,暴力仍然持續。而且可怕的是,這對K 的父親,甚至對K而言,都逐漸變成理所當然的事。
K 漸漸開始害怕週末的到來,只要K回到家,父親無論理由為何,都會理所當然地對他發怒,無論那憤怒是起因於K、他自己的壓力或是其他理由。K也一樣,起初,他還會感到奇怪,努力想找出原因,了解父親為什麼對他發火、自己為什麼要持續遭受這種可怕的對待,但隨著時間過去,這樣的有毒關係對K而言也變成理所當然的了。很少人會思考風為什麼會吹、蘋果為什麼會從樹上掉下來。K 寧願忍受痛苦,也放棄對這種關係提出疑問。
有毒關係越是持續,暴力程度就越嚴重,手段也越多樣。長時間施行暴力到成了常態的話,就會改為變成拷問(torture)的形態。人對他人行使暴力時,施暴的一方心裡存在著一種類似馬奇諾防線的堡壘,讓他們的施暴無法超過一定的程度。這堡壘是複合而成的,其中包含釋出惡意及破壞性行為時產生的罪惡感,以及對方和自己同樣生而為人、自然而然會去想像「如果我也被那樣打的話,應該也很痛吧?」的同理與同情。
用手指捏死螞蟻的時候,我們很難想像螞蟻全身被壓扁、生命即將消失的感受,但是看到血腥電影裡人的手腳被砍斷時,因為對方和自己太過相似,便會產生反感。然而,長時間持續的有毒關係會稀釋主導者心裡的馬奇諾防線,甚至讓防線消失。結果就是,人類對人類施加的暴力程度強化,方式變得過於殘忍。此外,並不只有暴力的物理性程度強化了,暴力的多樣性也增加了。從K 遭受到的非物理性暴力來看,最具代表性的是「無視」。每個週末家人一起用餐時,K怎麼樣也插不上話。K無論說什麼話,父親都毫不理會;晚餐期間,K 的父親徹底把K 當作不存在,但儘管如此,他還是會被指責吃飯的時候什麼話都不說,而且這成了K被暴力對待的藉口。這種一個人的語言訊息與他的非語言訊息不一致的情況,在心理學中被稱作雙重束縛(double bind)。最終,K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父親的話,他難以逃離這種怎麼做都不對的情況,和家人用餐的時間總是讓K 感受嚴重的不安與混亂。
暴力的多樣性已經擴大到傷害K的基本人權。基本人權指的是居住遷移自由、表達自由、思想自由等為了維持人類生活,必須且基本的自我決定權。K 的父親以語言、非語言侵害的方式,對K 想住的地方、婚姻生活、未來計畫等,這些身為人類的K 所能決定且應該享受的基本生活權利施加暴力。
有毒關係在封閉的情況下會牢牢鞏固
有毒關係具有強烈的孤立性,並且這種孤立性會使犧牲者無法獲得外界的援助,因而感到嚴重的無力感。雖然韓國在近年來改善許多,但傳統上依然有一種氛圍,就是不希望所有場所都適用於統一的規則。也就是說,在社會、家庭、軍隊、男女之間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規則。在社會中,蓄意損傷他人的身體是可能被判刑入獄的重罪,但在家庭裡,這卻是一種訓誡的方式。雖然勞動契約裡,規範下班後公司不得干預員工的生活,但許多公司仍將參加聚餐等活動,視為組織配合度的重要指標,因此連下班後的生活都會被主管影響。除此之外,這類每個組織都不太一樣的規則,有時甚至侵害了人的基本權利,讓隸屬於封閉組織內的當事人無從抵抗。有毒關係就存在於這樣的縫隙當中。
幾年前引起軒然大波的「第二十八步兵師團醫務兵殺人事件」,也就是「尹士兵事件」,即是軍隊中有毒關係的駭人事件。在尹士兵事件中,包含李兵長在內的四名軍隊學長是有毒關係的主導者,他們在和尹士兵一起吃冷凍食品時,集體將他毆打致死。在尹士兵失去意識昏倒後,這幾位主導者仍殘忍地繼續對他施暴。經過深入調查後得知,包括李兵長在內的這群人,長達四個月對犧牲者尹士兵行使物理性與言語性的暴力。
重要的是這起事件的環境因素。只要建立起孤立的環境,絕對無法想像會發生在現實社會中的暴力就會變得漫長且殘忍。
基本上,雖然這是因為封閉環境而產生的有毒關係,但有毒關係的主導者們為了維持這種關係的孤立性進而採取的行動,也值得關注。加害者們為了盡可能防止對尹士兵施暴的事實曝光,因此更改尹士兵的勤務,甚至阻止他和家人會面。假如他們堅信自己殘酷的行為是正當的,就不會有這些為了維持關係孤立性而產生的行動,所以他們是清楚知道,他們的行為可怕到就算是對戰俘,也不會輕易出現這些行為。但即使如此,他們仍保持關係的孤立性,並沒有停止他們的這種行為。這是典型有毒關係的特性。
整理一下,(1)在關係明確的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具有力量優劣或社會和心理性位階的差異,(2)發生了在其他正常關係中無法被接受的孤立性與暴力關係,以及(3)暴力越來越強烈與多樣化,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有毒關係」。然而,上述的三項特徵只是構成有毒關係的外在特性而已,兩人之間內在隱密的心理交流則會形成某種病態關係,並使有毒關係持續。下一章,我們將探討構成有毒關係的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發生的心理特徵。
Chapter1
摧毀存在的有毒關係——有毒關係的主導者、協力者、犧牲者
*有毒關係不知不覺就開始了
患者K來找身為身心科醫生的我就醫
來到診療室的男性患者K是位三十五歲左右的牙科醫生。身材消瘦,穿著端莊的休閒式正裝,給人乾淨俐落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他看起來也極度敏感且有氣無力。混濁眼鏡鏡片後的雙眼,也如鏡片一樣模糊不清。即使說句客套話,也無法說他這樣的形象會帶給人好感。
K的個性誠實細心,從未在服務的醫院中惹過麻煩,但大家對他的評價仍舊不太好。雖然他個性不是親切且善於社交,但也不會隨便對待身邊的人或病人。整體而言,他彬彬有禮,即使面對年紀比自己小的人也會使用尊稱。事情發生在公司聚餐時,一位一起共事的年輕口腔衛生師對他的穿著開了玩笑,他突然站起來咆哮道:
「對我指指點點的,你算老幾?你就那麼了不起嗎?我知道你平常就瞧不起我!」
在場的人當然全都僵住了,因為他的能力或社會地位並不到會被瞧不起的程度,而且那位同事說的話在其他人聽來也不構成什麼問題,甚至更像是親密友好的表現。但K的怒火無法平息,最後年輕同事哭著跑了出去。K逃亡似地逃離了突然散場的局,回到家後在浴室裡用蓮蓬頭水管捆住自己的脖子,要不是他的老婆察覺到後趕緊勸阻,差點就要發生可怕的憾事。
其實K不是第一次這樣因為別人的話而勃然大怒了。雖然他看起來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人,但不經意的一句話就能讓他發脾氣。大部分K身邊的人並不知道他為何生氣,只是開始與他疏遠,K也不打算為此多做解釋。問題在於K生氣之後的心理狀態,每當碰上這樣的夜晚,K便會深陷在悲慘與羞恥的情緒中。雖然他很後悔自己發了脾氣,但聽到那些話的當下確實感到自己被侮辱與瞧不起。
我這麼問他:
「所以你也不理解自己為什麼會在那種情況下感到受侮辱和生氣吧?」
他回答道:
「不是的,醫生,我知道我為什麼生氣,以及這憤怒和受侮辱的感覺從何而來,就是因為我和我父親之間的關係。但儘管如此,我還是改變不了。我想知道的是結束這痛苦關係的方法。」
意外的是,K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問題。他的行為是如何惡化他的社會立場、為什麼他會這麼容易感覺被他人侮辱,以及這樣的問題如何搞砸自己的人生,這些問題他都可以條理分明地說明,讓精神醫學科醫師都感到驚訝。他對自身問題的優異洞察說明了他不斷努力與反省以擺脫自己的問題,但他依舊痛苦纏身,無論多麼深思自己的問題,多麼努力原諒自己,他和帶給他痛苦的父親之間的關係始終沒有改變,甚至問題到現在都還持續。我明白,K仍被折磨自己一輩子的有毒關係所束縛並痛苦著。
那天,K不知為何就成了有毒關係的犧牲者
K和父親的有毒關係可以追溯到他結束高中三年的宿舍生活,開始念大學的時候。K出生於雙親從商的家庭,度過相對平凡的青少年時期。K高中的時候是優秀的學生,但也常聽人家說他不知變通。他總是死板地遵守校規,因此受到同學們的嫌惡,不過整體而言,他是家裡的驕傲,無論別人或他自己,都相信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大學入學考試以優異成績考上牙醫大學後,就像多數大學生一樣,他搬到學校附近開始獨立生活。
那年,K 離開鬱悶的宿舍,陶醉在二十歲大學生自由之中。他的父母在郊區做生意,並住在附近的公寓。三月,他暌違一個月後回到父母居住的家。那是他獨立生活後的一個月,坐在餐廳的K 興高采烈地訴說成年男性的大學新生故事,但過了一會後他才察覺到不對勁,父母一直看也不看他一眼,也不回應他的話。這時,K 的父親突然憤憤地開口了:
「你瘋了嗎?」
K 傻住了,突然襲來的咒罵就像插上胸口的匕首,但他連感到疼痛的時間都沒有,只有臉變得通紅。比起痛,他更感到羞愧。因為不知道被罵的原因是什麼,K本能地開始回想自己的行為有什麼問題,肯定有什麼他不知道的原因,但他就是不明白。他好像成了不懂事的孩子,因為自己的愚蠢行為而陷入困境。本來保持沉默的K 父親丟下筷子就走了,理由是沒胃口。K 雖然嚇傻了,但還是吞下口中咀嚼的飯粒。這時的羞愧感從此折磨了他一輩子。
K在自己的房裡休息時,他母親叫他去主臥室,讓父親消氣。他進到臥室,父親還是看也不看他一眼,就這樣三十分鐘過去,不自在與不安的感覺讓他就快窒息了(此後,K患上嚴重的恐慌症)。就跟吃飯時一樣,K的父親不悅地開口了:
「你回來幹嘛?」
雖然是毫無頭緒的問題,但他還是回答自己是回來探望父母,並問了父親是不是心情不好。無論如何,都得要讓父親消氣才行。父親卻開始瞪著他。
「嘖!」
一瞬間,K 的眼前一片空白。回過神時,只有臉上燙傷般的疼痛感,他被賞了一巴掌。K 的父親以前也經常打他,但那只會在K說謊之類,明確犯錯的時候。因為有明確的形式和原因,因此也有宣告結束的某種程序。然而,剛剛的疼痛卻是出自個人的,那並不是一種程序,而是個人的報仇或暴力。像是國中生走在暗巷被高中生施暴搶錢一樣,不知道會以什麼方式進行,也不知道何時會結束,K 當時就像那樣,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他未曾想過要抵抗父親,於是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K 的思考就停滯了。在此同時,K 的父親一邊喝著啤酒,一邊看著電視上的高爾夫球比賽,然後突然問了K:
「你不知道你做錯了什麼嗎?」
K 不記得自己當時回答了什麼,只記得在毫無防備下,被父親踹了胸口而在地上打滾。那天他所受到的衝擊,讓他這十多年間沒有一天不想起。然而,當時的K 還想像不到,這樣的關係在十多年間的每週反覆上演。那天有毒關係開始,徹底摧毀了K 的靈魂。
*有毒關係一旦形成,便逐漸具有破壞性及不斷強化
K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就是有毒關係的典型樣貌。無論是發生於家庭或職場,所有有毒關係都有幾項共同特徵。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我將關係中的對象分為兩種。主導有毒關係,給對方造成有毒影響、試圖操縱對方的人,稱為「主導者」;而從屬於有毒關係、被這種關係操縱並因此受害的人,則稱之為「犧牲者」。
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壓倒性的力量差異
有毒關係發生於力量有著壓倒性差異的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即父母與子女、師長與徒弟、前輩與後輩、上司與下屬等。有毒關係越是持續,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的力量差距就會越來越大。必須留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力量差異,不僅僅是物理性的力量差異;例如讓主導者K 的父親與犧牲者K之間形成有毒關係的力量差異,就不是物理性的力量差異。當時的K 或許稱不上是健壯,但大致上算是健康、體力達平均標準的普通年輕人,所以即使是充斥著毆打、謾罵、人格侮辱的有毒關係,K的體力也絕不會抵抗不了邁入老年期的父親。然而,人與人之間,社會經濟地位遠比物理性的力量更具影響力。大學時期的K 除了課餘時間的打工之外,並沒有其他收入。雖然就年齡看來他已是成年人,但就社會經濟層面而言,他並不是可以獨立自主的成年人。相反地,主導者K 的父親在社會上是受人尊敬的有錢人,更重要的是,他具備了豐富經驗所鍛鍊出來的純熟社會技能與歷練,以及可以動搖許多人的手腕與影響力。
當K試圖以力量對抗父親的那瞬間,K在社會上就成了對父母施暴的絕世逆子而受世人指責,並被斷絕了所有經濟上的支援。儘管K年輕而且力氣較大,但他能夠戰勝父親的機率連百分之一都不到。他們都在本能上清楚知道兩人之間的力量差距,K其實也曾在父親的暴力之下,為了保護自己的身體舉起拳頭,但他鼓起勇氣舉起的拳頭,卻因為父親大聲喝斥:「你竟敢想對我動手?」而無力地放下了。雖然K和父親之間的有毒關係所帶來的影響,對當事者K而言是破壞了他整個人生的驚人大事,但諷刺的是,在K當時生活的韓國社會裡,這只是無法被定罪的瑣碎小事。
就算是夫妻、同學、手足等名義上看似平等的關係,若仔細觀察這些關係就會發現,在形成有毒關係之前,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有著壓倒性力量差異是很常見的。父權文化普遍存在,於是在婚姻生活或家庭失和被無條件認為是女人責任的社會裡,夫妻之間就很容易產生有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或社會偏見等要素,就是在主導者與犧牲者的有毒關係中,明確區分力量優劣的重要因素。若好好觀察看似平等的國、高中同班同學之間發生的有毒關係,會發現他們生活其中並稱之為班級的這種特定組織裡,經常可見主導者擁有比犧牲者更具壓倒性影響力的情況。這樣的力量優劣非常堅固,無法輕易被推翻。
有毒關係一旦形成便會不斷強化
有毒關係具有強烈的持續性與逐漸嚴重的破壞性。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心理方面的優劣,當關係中發生虐待、惡言等破壞性行為時,人與人之間便會產生某種心理動態,也就是流動與模式。一旦心的流動固定下來,就會漸漸形成某種固定的形態,形成固定形態的有毒關係會抗拒改變,於是不平衡且具破壞性的流動便會繼續維持。
剛滿二十歲的K 並沒有意識到有毒關係開始了。因此,他把父親突然對自己的人格侮辱與暴力,僅僅當作是父親一時的反覆無常。然而,父親毫無理由(但他自認為理由充分)行使暴力的那天,還只是個開始而已。隨著時間過去,拳頭之後動粗口、罵完之後動拳頭、人格侮辱、把K 當成隱形人,這些都只是根據不同情況改變形態而已,暴力仍然持續。而且可怕的是,這對K 的父親,甚至對K而言,都逐漸變成理所當然的事。
K 漸漸開始害怕週末的到來,只要K回到家,父親無論理由為何,都會理所當然地對他發怒,無論那憤怒是起因於K、他自己的壓力或是其他理由。K也一樣,起初,他還會感到奇怪,努力想找出原因,了解父親為什麼對他發火、自己為什麼要持續遭受這種可怕的對待,但隨著時間過去,這樣的有毒關係對K而言也變成理所當然的了。很少人會思考風為什麼會吹、蘋果為什麼會從樹上掉下來。K 寧願忍受痛苦,也放棄對這種關係提出疑問。
有毒關係越是持續,暴力程度就越嚴重,手段也越多樣。長時間施行暴力到成了常態的話,就會改為變成拷問(torture)的形態。人對他人行使暴力時,施暴的一方心裡存在著一種類似馬奇諾防線的堡壘,讓他們的施暴無法超過一定的程度。這堡壘是複合而成的,其中包含釋出惡意及破壞性行為時產生的罪惡感,以及對方和自己同樣生而為人、自然而然會去想像「如果我也被那樣打的話,應該也很痛吧?」的同理與同情。
用手指捏死螞蟻的時候,我們很難想像螞蟻全身被壓扁、生命即將消失的感受,但是看到血腥電影裡人的手腳被砍斷時,因為對方和自己太過相似,便會產生反感。然而,長時間持續的有毒關係會稀釋主導者心裡的馬奇諾防線,甚至讓防線消失。結果就是,人類對人類施加的暴力程度強化,方式變得過於殘忍。此外,並不只有暴力的物理性程度強化了,暴力的多樣性也增加了。從K 遭受到的非物理性暴力來看,最具代表性的是「無視」。每個週末家人一起用餐時,K怎麼樣也插不上話。K無論說什麼話,父親都毫不理會;晚餐期間,K 的父親徹底把K 當作不存在,但儘管如此,他還是會被指責吃飯的時候什麼話都不說,而且這成了K被暴力對待的藉口。這種一個人的語言訊息與他的非語言訊息不一致的情況,在心理學中被稱作雙重束縛(double bind)。最終,K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父親的話,他難以逃離這種怎麼做都不對的情況,和家人用餐的時間總是讓K 感受嚴重的不安與混亂。
暴力的多樣性已經擴大到傷害K的基本人權。基本人權指的是居住遷移自由、表達自由、思想自由等為了維持人類生活,必須且基本的自我決定權。K 的父親以語言、非語言侵害的方式,對K 想住的地方、婚姻生活、未來計畫等,這些身為人類的K 所能決定且應該享受的基本生活權利施加暴力。
有毒關係在封閉的情況下會牢牢鞏固
有毒關係具有強烈的孤立性,並且這種孤立性會使犧牲者無法獲得外界的援助,因而感到嚴重的無力感。雖然韓國在近年來改善許多,但傳統上依然有一種氛圍,就是不希望所有場所都適用於統一的規則。也就是說,在社會、家庭、軍隊、男女之間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規則。在社會中,蓄意損傷他人的身體是可能被判刑入獄的重罪,但在家庭裡,這卻是一種訓誡的方式。雖然勞動契約裡,規範下班後公司不得干預員工的生活,但許多公司仍將參加聚餐等活動,視為組織配合度的重要指標,因此連下班後的生活都會被主管影響。除此之外,這類每個組織都不太一樣的規則,有時甚至侵害了人的基本權利,讓隸屬於封閉組織內的當事人無從抵抗。有毒關係就存在於這樣的縫隙當中。
幾年前引起軒然大波的「第二十八步兵師團醫務兵殺人事件」,也就是「尹士兵事件」,即是軍隊中有毒關係的駭人事件。在尹士兵事件中,包含李兵長在內的四名軍隊學長是有毒關係的主導者,他們在和尹士兵一起吃冷凍食品時,集體將他毆打致死。在尹士兵失去意識昏倒後,這幾位主導者仍殘忍地繼續對他施暴。經過深入調查後得知,包括李兵長在內的這群人,長達四個月對犧牲者尹士兵行使物理性與言語性的暴力。
重要的是這起事件的環境因素。只要建立起孤立的環境,絕對無法想像會發生在現實社會中的暴力就會變得漫長且殘忍。
基本上,雖然這是因為封閉環境而產生的有毒關係,但有毒關係的主導者們為了維持這種關係的孤立性進而採取的行動,也值得關注。加害者們為了盡可能防止對尹士兵施暴的事實曝光,因此更改尹士兵的勤務,甚至阻止他和家人會面。假如他們堅信自己殘酷的行為是正當的,就不會有這些為了維持關係孤立性而產生的行動,所以他們是清楚知道,他們的行為可怕到就算是對戰俘,也不會輕易出現這些行為。但即使如此,他們仍保持關係的孤立性,並沒有停止他們的這種行為。這是典型有毒關係的特性。
整理一下,(1)在關係明確的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具有力量優劣或社會和心理性位階的差異,(2)發生了在其他正常關係中無法被接受的孤立性與暴力關係,以及(3)暴力越來越強烈與多樣化,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有毒關係」。然而,上述的三項特徵只是構成有毒關係的外在特性而已,兩人之間內在隱密的心理交流則會形成某種病態關係,並使有毒關係持續。下一章,我們將探討構成有毒關係的主導者與犧牲者之間發生的心理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