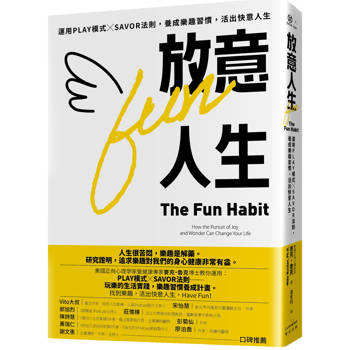1 樂趣是解藥
「我一生中曾有一段時間,認為自己擁有一切──萬貫家財、豪宅、汽車、華服、美女,以及任何你能想像到的各種物質東西,而我現在只求平靜。」
────美國演員李察・普瑞爾(Richard Pryor)
亞利桑納州鳳凰城某個乾旱如常的冬日,一位名叫威爾・諾瓦克的男子收到一封電子郵件,信中邀請他參加單身派對。聽起來很好玩啊:在佛蒙特州滑雪,度過一個狂野週末。派對是八◯年代的主題,有燒烤和義大利美食、啤酒、美麗的初雪。只有一個小小問題,派對主角是新郎安傑羅,威爾根本沒聽過他,也不認識他的任何伴郎;一定有人發錯了邀請函。(值得注意的是,有個伴郎叫比爾・諾瓦克,而比爾是威廉的小名。)不過,讀到這封電子郵件讓威爾心情很好,身為一個十個月大嬰兒的父親,無疑很需要放鬆。
他自顧自地笑了起來,寫了回函:「他媽的也算我一個!從邀請函內容看來,安傑羅聽起來棒極了,我想幫他好好地告別單身,我希望他的新娘(或新郎)非常棒。」他還附上了他的T恤尺寸。
他從沒想過會收到回音,他只是向宇宙丟出石子,這顆石子卻激起了些漣漪。伴郎們認為威爾很有趣────他太搞笑了,一定會為派對加分。威爾很快得到回覆:「如果你是認真的,我們也是認真的,那就來吧。」
威爾愣住了。他真的要去嗎?這趟旅行要花一千美元,家裡還有妻小要顧,加上翻修房子經濟上已經很窘迫。而且……對方都是陌生人。但另一方面,他從十四歲起就沒有再去滑雪過。他的生活雖然充實,但就像大多數新手父母一樣,生活充滿爆炸多的尿布和睡眠不足,打個小盹都算冒險。
因此他不想拒絕,而是加倍努力。他在GoFundMe平台發起募款活動,訴求「幫我參加陌生人的單身派對。」這可是重要的事,為了一個睡眠嚴重不足的新手爸爸,為了一群隨性策畫派對的兄弟團。一開始只有幾十人支持,到最後有數百人跳上來贊助,這些人在當天沒有做其他更正經的事,都到GoFundMe平台上投幾塊錢。當天還沒到募款結束,威廉的旅行資金就已全部到位。到最後共有兩百二十四人捐了四千六百一十五美元,這項募款活動轉發六千三百次。(超出旅費之外的錢以準新郎和新娘的名義捐給一個名為「大學/食品/玩具/任何所需」的兒童慈善基金會。)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太荒唐了,請暫時站在威廉的立場思考,設想一下這是一種如何的體驗:
將錯就錯的大玩笑。
因冒險激發出的腎上腺素大爆發。
從平凡躍入非凡的純粹喜悅。
隨性而至的旅行帶來的刺激感和玩樂的可能性。
結交新朋友的獎勵。
以健康形式逃避現實的機會。
威爾的故事在去蕪存菁之後是存粹的樂趣。在老婆的祝福下,他登上飛機,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創造終生難忘的回憶。對其他人來說,他成了傳奇。等到有一天,他的孩子會看到這些照片,難以置信地大笑,因為他的父親竟做出如此性之所至的事情。
我說這個故事的目的並不是說你應該效仿威爾,要你拋開每日行程轉去做別的事。這並不是本書的重點。歸根究柢,故事的重點根本不是威爾,而是所有在場外為他的冒險鼓勵歡呼的人,這些如病毒般散布的熱情是有啟發性的。人們資助威爾的募款活動或贊助網路上其他好玩的事都是有原因的(當然你也可以說那些是「毫無意義」的無聊事):
我們生活在極度缺乏樂趣的世界,我們無法自己找樂子,就只能敲幾個按鍵,把找樂子的事託付給像威爾這樣的人。
所以玩樂是──或說應該是──人人都能獲得的基本物品。如果人生必定有失望、痛苦和失落,玩樂就是神奇的膏藥,就算巨石襲來、利箭穿身,只要好玩就能讓命運無情的折磨變得可以忍受。
從出生開始,玩樂對於人類大腦的發育至關重要,如利用「躲貓貓」這樣簡單遊戲讓我們埋下理解世界的種子。孩童的玩樂有助於發展基本的社交和運動技能,建立界線也測試極限,定義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我們利用玩樂來探索生活,找尋是什麼人事物會帶給我們快樂。我們經歷不同角色和身分,最終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識。(以喜劇動畫《南方四賤客》(South Park)裡大廚(Chef)的名言來說,就是「有段時間、有個地方是為所有事做準備,那就是大學。」)
當我們慢慢進入成年,生活可能變得更複雜,玩樂成為豐富人生的工具,也成為卸除生活壓力的排氣閥,同時也維持我們的健康:因為玩樂帶來的歡笑和幽默感可以減少焦慮、減輕壓力、增強自尊、自我激勵。玩樂帶來的趣味可以改善呼吸和循環,降低脈搏和血壓,有助於將腦內啡釋放到血液中。玩樂可以緩解孤獨和無聊。當年齡增長,玩樂是保持活力的關鍵。
這就是玩樂的真相和潛力,至少應該是這樣的。但可悲的現實是,我們多半在剛成年時就放棄了它,因為「我們總有一天會長大,對吧?」《華爾街日報》曾有一篇文章〈衰老過程中被忽視的技能:如何享受樂趣〉,作家克萊兒・安斯貝里(Clare Ansberry)在文中表示,在整個成年過程中,我們多半都忘記了如何玩樂。我們讓這個重要技能被削弱,因為我們錯誤地認為它幾乎沒有什麼價值,而事實是,「歡笑、放鬆、享樂、消遣────這些都可作為壓力、憂鬱和焦慮的解藥。」1
親愛的讀者,你既然買了這本書,很可能對我們缺乏樂趣的人生感到懷疑。若是如此,你很特別。很多人都認為玩樂是幼稚的、沒有必要的、分散專注力的,甚至是危險的。我知道,因為當我告訴別人我正在寫一本讓人重新正視玩樂的書時,我看到他們的反應充滿疑惑。有人緊張地扭頭看別的地方,有人輕聲低笑轉移話題,還有人雖熱情點頭,卻只是等待時機,想證明為什麼在他們的情況下玩樂不能優先考慮。
在重視生產力高於一切的社會,我們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觀念:玩樂是「有,也不錯」。玩樂並不出現在日常的重要時刻,而是規畫在一年一度的度假時間裡。如果幸運的話,也許週末還能來一趟一次性的冒險行動。根據人力資源公司Zenefits的調查資料,美國的帶薪休假時間是已開發國家中最少的,但許多美國雇員必須在公司的督促下才會使用帶薪休假。2日復一日,我們不管在精神上或身體上都綁在辦公桌前,只能對著待辦清單生悶氣。在身心俱疲之下,我們既然無法選擇在生活中來次冒險,只好透過像威廉這樣的人替我們滿足需求。他們像是出來搞笑的甘草人物,不時出現在我們的社群消息中。
當我說「選擇去冒險」,我並不是指要去跨州旅行和陌生人聚會,也不是去做什麼其他更激進的事。我的意思是:用心生活,有意識地把日子慢慢過成能享受樂趣的日子────就從現在的生活開始,而不是幻想明天。這概念我稱之為「玩樂的生活實踐,養成樂趣習慣」。
要想在生活中實踐玩樂並養成習慣,首先要徹底重新認知什麼是「樂趣」,以及它為什麼是健康、幸福、成功的關鍵,甚至它的重要性比我們想的更重要。
只有工作,沒有玩樂
我們是如何來到這裡的?在美國和歐洲,人們多半接受古老基督新教對職業道德的詮釋,這是美國夢的精神軟肋:努力工作是一種美德。對清教徒來說,成功不僅定義了人的自我價值,也定義了我們的精神價值。如此,真正的靈魂才會處於平衡。在這樣的背景下,工作是否努力以及工作的產出就變成非常嚴肅的事了!
如果工作是神聖的,那干擾工作的事────又名玩樂────不僅毫無價值,更是邪惡的。
遵循同一福音的教導,要想創造財富和實現美國夢,只要努力工作就夠了────儘管現代社會學表示,貧窮與個人的關係要複雜得多。記者兼社會評議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她的著作《我的底層生活》(Nickel and Dimed)3中描述她如何只靠一份最低工資的工作謀生,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簡單做結論:在沒有個人儲蓄或有意義的社會安全網下,做最底層工作的人連勉強餬口也嚴重地無能為力,努力工作根本不足以克服困境。
儘管如此,由工作衍生的各種觀念(在各層面上)仍然根深蒂固。我們的自我價值感隨著個人的生產力上升或下降。暢銷書作者拉哈芙・哈弗斯(Rahaf Harfoush)在《未來、工作、你》(Hustle & Float)4一書中強調,工作是一種美德────無論它與快樂、意義或勞動成果有多麼悖離────因為工業革命將工作細分為瑣碎的小任務,且藉由測量來最佳化小任務的產值,在此過程中工作努力很有幫助。這是所謂的「演算法工作」(algorithmic work),工作內容可由一定的順序模式重複進行,這是過去許多人的謀生形式。5就如我的祖父,他在奧克拉荷馬州有一家鑄造廠,他和同事每天早上同一時間進廠工作,每一天,每個人都知道別人對他的期望是什麼。這種工作耗費的體力非常繁重,所以沒有熬夜這回事。你知道該做什麼,也做了該做的事,更得到了報酬,工作以外的剩餘時間都是你自己的。
到了一九七◯年代,迎來了資訊時代。許多工人不再製造小零件,而是在新興的「知識工作」領域進行交易。智慧財產和創新成為工作產品,我們不再是產線上的工人,操作裝著鏈輪與齒輪的機器;我們自己就是鏈輪和齒輪,我們的執行能力就像生產線上的設備一樣,被人利用,過度提升。我們現在就是機器,輸出商品,為他人創造利潤。
更複雜的是,近年來生產力變得越來越難以衡量。與生產線不同,創造性工作是由非線性思維和流程驅動的,因此不再遵循一致的模式,結果是我們的工作沒有明確的終點線。如果不像演算法工作那樣提供明確目標,我們就只能模糊判斷自己是否在辦公室度過誠實的一天。因為急著賺錢謀生,只好讓自己永遠處在「開機」狀態。同時,新的通訊方式使我們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溝通,問題因此變得更複雜。到現在,我們多在家工作,但工作似乎永無止境。不管工作、吃飯、睡覺,所有行動都在同一個物理空間,因此沒有明顯的過渡期告訴大腦我們已經「下班」了,只能一直回覆電子郵件直到頭撞到枕頭上。
近年來,「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觸角進一步打破這種平衡。對於那些依靠Uber、Lyft、Fiverr、Instacart、DoorDash和Upwork等平台謀生的人來說,生活的每個角落都擠滿了工作。零工工作者被工作可以自理的虛假承諾所吸引,往往沒有意識到有股強大力量讓他們辛苦創造的大部分價值都流向他人。更糟的是,這些平台的運作機制從設計之初就在誆騙零工工作者,讓他們以越來越少的工資做越來越多的工作。如果你是零工工作者,簡單搜尋一下網路就會找到許多軟體開發人員的告白,為他們把技術用在操縱運作規則上而感到內疚。
零工經濟受到應用程式的支援而出現了一種錯覺,認為可對旗下工作者進行有效控制和有意識的操縱,這錯覺很極端但絕非唯一。除非你是自己的雇主,不然很少會有雇主把最高原則全部透明公開;所謂的最高原則就是盡可能利用一切資源(包括人力),能擠出多少是多少。這種企業手段在Slate線上雜誌的一篇文章中看得一清二楚,文章是〈我的公司在做企業健康管理app,但請看我恐怖的工作配額〉(My Disturbing Stint on a Corporate Wellness App),作者安・拉森(Ann Larson)曾在管理企業健康的軟體公司工作,據她推測,公司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將低薪與過勞的不良影響從雇主肩上轉移到員工身上,她也因此必須從事更多、更長時間的體力勞動。6確實有些公司是以與員工分享財富為其創業使命,但這種公司並不常見。
工作和生活沒有界線,「付出一一◯%!」全新且惡毒的工作意義出現了。美國各類勞工的過勞情形處於歷史最高峰。公司雇用當紅的激勵大師發出精神喊話,蓋瑞・范納洽(Gary Vaynerchuk)堅持認為你需要「撩落去7」 ,葛蘭特・卡爾登(Grant Cardone)宣稱榮耀屬於那些為工作付出「十倍力」(10X)的人。8這些話語在舞台上聽來很棒,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揭示,接受這些訊息且起而立行的人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史丹佛大學商學院組織行為學教授傑弗里・菲弗(Jeffrey Pfeffer)在他的《為薪水而死》(Dying for a Paycheck)一書中概述現況,他認為現代工作場域「永遠待命」的要求對我們造成嚴重傷害。9而後,在史丹佛商學院《洞見》(Insights)網站的一篇訪問中,菲弗稱讚西班牙IESE商學院的教授努里雅・欽奇莉亞(Nuria Chinchilla),認為她將這些適應不良的行為稱為「社會污染」很對。10這種工作優先的概念是一種侵入性的傷害,不僅破壞了友誼和家庭關係,且真實地正在殺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結果,二◯一六年,長時間工作導致七十四萬五千人死亡,比二◯◯◯年調查的數據增加了二十九%。11
讓工人為組織生產更多產品並不是新概念,管理大師菲德烈・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在一九一一年的著作《科學化的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中就提出這樣的想法,泰勒在書中闡述他如何利用提高工資和嚴格管理工作節奏等方法,讓鐵工廠工人的日產量從十二噸提高到四十七噸。儘管我們的經濟型態發生了如前所述的巨大變化,這個故事在今天仍然豐富了管理學理論和實務。(但是泰勒毫不掩飾地鄙視這類勞工,他表示:「這些人是如此愚蠢和遲鈍,以致心理構造比其他類型的人都更像牛。」)12我還記得我念博士時學過「目標設定理論」(goal-setting theory)13,此理論在一九六◯年代中期,由組織行為研究的先驅愛德溫・洛克(Edwin Locke)和蓋瑞・萊瑟姆(Gary Latham)確立,他們也將此方法用在改善工人生產而聞名。在在顯示,將人類最佳化為工作機器是一種進化過程,並且有著悠久歷史。最近企業正向我們推銷如下訊息:「咬牙忍耐」是一種榮譽徽章。但事實上,它是有毒的。
讓我們面對現實吧,如果你沒有不顧一切努力;如果你沒有連在上廁所時都在回電子郵件;如果你沒有日行一萬步……那麼你一定是個懶惰鬼,是吧?老實說,這些資訊蒙蔽我們理智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這種犧牲會讓我們付出可怕代價。玩樂、遊戲和休閒才是我們幸福感的來源,才是人生活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現代生活已經侵蝕了我們享受它們的機會。
跳出幸福的陷阱
正如我在前言中說的,很多人都將「追求幸福快樂」當成努力不懈的目標,我也是對這壓力鍋做出回應的其中一人。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我也像許多人一樣踏入量化這個願望的陷阱,我會把帶來快樂體驗的各個層面量化。舉個例子,我喜歡冥想。為了「增進」我的冥想體驗,我買了一台能測出神經反應的設備,這樣我就可以測知我的冥想有多「好」。然而,這種體驗很快就變質了,因為裝置軟體不斷督促我進行改善,而不是讓我簡單享受冥想體驗。就如現今人類做很多活動,但我們都受到鼓勵使用app和小工具來追蹤生活的各層面,從睡眠、運動,到與愛人親密的天數等私密事情都要計算一下。14
我們不是按照自己方式享受這些活動,而是將它們轉化為可供分析的統計數據。我們將今天的自己與昨天的自己比較,同時也將自己與隔壁的老王比較。我們糾結在當前狀態與偶然欲望之間的差距,但這些差距很可能只是偶然的問題。但若我們想走向真正能滋養我們、能幫助我們成長的有意義經歷時,幸福變成了海市蜃樓,遠遠地看還滿清楚的,可一旦我們到達,就會發現那裡什麼都沒有,只能再次從地平線上搜尋,最後變成無限循環。
這不是你的錯:科學表示,情況對我們不利。我們的大腦程式從一開始就設計成專注於現況與期待幸福之間的差距。學術界用來描述快樂體驗的專業術語是「享樂」(hedonic)這個字,當我們談論享樂體驗時,通常有兩個組成要素────預期的快樂和最終的快樂。過去的科學認為,人類行動的主要動力是為了追求完美的愉悅────這是把人類追求幸福的目的界定為「為了讓自己感覺爽」的奇妙說法。但現在科學已經認識到,真正驅使我們追求快樂的,往往不是讓我們感覺良好的事件本身,而是追求快樂可能得到的潛在獎勵或正面回饋,以及當我們的期待沒有落空時,隨之而來的良好感覺。原因有三:
一、我們會期待。如果你之前讀過幸福相關的文章,很可能聽過多巴胺(dopamine)這個物質。多巴胺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它有個更常見的別名「快樂荷爾蒙」,因為發現之初就認為它可以幫助我們體驗到愉悅、快感。但正如神經學家布萊克・波特(Black Porter)在回答我的採訪時所說,「多巴胺快感的故事在目前的神經學領域幾乎快消失了。」科學家研究多巴胺時注意到一些讓人驚訝的事:多巴胺激增的時刻是在我們做快樂的事之前。我們曾認為要體驗快樂和愉悅,多巴胺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現在我們知道,那種強烈感覺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因為我們期待。15事實上,期待與快樂感受根本沒有必然連結。現今科學家認為,多巴胺的演化目的是在提高你的興奮程度,讓你為意想不到的事做準備。至於「這件事情」本身的品質如何?多巴胺不在乎。現在,多巴胺也被認為與追求目標有關,它為我們衝向終點提供動力。
在多巴胺的推動下,我們興之所至地追求幸福,而不是真正享受幸福本身這個禮物。16在設計上,想緩解這種渴望本來就被設定為不可能。因此,我們覺得自己就像坐在倉鼠跑步輪上,科學恰如其分地把它稱之為「享樂跑步機」。類似的相關術語還包括:享樂適應(hedonic adaptation)、享樂相對性(hedonic relativism、幸福設定點或幸福原點(happiness set point)。這些概念在在顯示,生活變化和事件會對我們的幸福感受產生影響,而我們傾向高估這些影響。通常情況下,一旦改變的事物變成熟悉的事物,我們的幸福感就會回到我們各自設定的「原點」────與改變之前我們既有的幸福水準相同。我們並不比以前更快樂,所以我們又開始追求更多東西。
在享樂跑步機上還有另外兩個「欺騙人類的花招」,讓幸福變得更加難以捉摸。
二、我們會適應。人生中的任何結果,無論好壞,通常影響有限,對我們主觀認定的幸福感受都是暫時的。當我們自以為抓住幸福的時候,幸福就會溜走。幾十年來科學界一直用「適應水準理論」(applying adaptation-level theory)來探知為什麼美好事物不會持久,但真正引起關注的是社會心理學家在一九七八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研究者布里曼(Philip Brickman)、科茨(Dan Coates)和賈諾夫-布爾曼(Ronnie Janoff-Bulman)針對彩券中獎者做了一番研究。17他們發現,人生可能出現某些讓人驚奇、意想不到的經歷────例如中樂透,當下生活會暫時充滿興奮感。但我們有適應的傾向,最終會適應新的現實,回到我們最初習慣的幸福預設水平。事實上,當我們不以理性思考的態度面對不斷變化的境遇時,我們依然會變得不快樂,只要新的併發症出現了(例如,中樂透之後出現了想要分一杯羹的朋友和家人),或出現了新的問題要處理(就像饒舌歌手Notorious B.I.G. 唱的,「mo money,mo problems────沒錢,沒麻煩)。 好消息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對於樂透中獎者來說,也不會失去所有希望。如果我們能夠有效地吸收好運,我們確實可以提高生活滿意度。18如果你中了樂透,只要有正確的工具,仍然可以「智取」適應水平。
三、我們會比較。快樂感受往往與我們的實際經驗關係不大,卻與我們與他人經驗比較後出現的認知有關。
我們對幸福的看法絕大部分取決於共同經驗。以此看來,幸福就像集體幻覺。無論何時何地,共識現實出現的當下,我們就會把自己經驗的現實與他人經驗的現實進行比較。
例如,法國做過一項社會人口學研究指出,如果人有選擇,他們通常要的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更多」,而是比周圍的人擁有更多。研究人員詢問研究參與者希望選擇下列哪一項:一種是自己的智商為一百一十,而周遭他人的平均智商為九十;另一種情形是自己的智商為一百三十,但他人的智商則為一百五十。研究參與者多半選擇第一項,儘管自己的智商較低。其他狀況也是一樣的,若問參與者想要有幾週假期,一種情形是當別人放假兩週時,自己放假四週;另種情況是自己可以有六週假期,但別人卻有八週假期,研究參與者多會選擇四週假期。19
進化機制根生蒂固在人類身上,讓我們偏好選擇享樂跑步機。你終於休假了,但休假並沒有像你想的那麼快樂,因為它沒有達到羨煞眾人的效果。你終於獲得晉升,但隨著你適應新角色,你的喜悅逐漸消失。更糟的是,你發現那根本不是你期待的。你的孩子享受著節日禮物帶來的興奮,但當他們將自己的好運與表弟比較、發現運氣更好的表弟恰巧收到更酷禮物,他們的世界就會崩潰。經驗的正向感受是短暫的,我們會回到原來的狀態,那個令人討厭的幸福設定點,甚至會讓你感覺更糟。
輸入空虛
你看過電影《大魔域》(The Neverending Story)嗎?故事講述魔法世界「幻想國」(Fantasia)正被一種名為「空虛」(The Nothing)的強大惡勢力吞噬,最後只留下缺乏想像力的「真實」世界,僅存一片淒涼的空虛。這就是我對使用腦殘媒體、參與空心活動的看法────一種看似勢不可擋的空虛力量,將會吸走生活中的快樂和意義……如果我們允許它這樣做。
就以使用社群媒體為例,你可以在社群平台上立即找到有點興趣的東西、很快建構起與他人的聯繫、勾起記憶、緬懷往事。我當然喜歡與人交流做線上分享,我並不想妖魔化這些工具。但重要的是要記住,這些應用程式本來就是為了侵占我們的休閒而設計的。它們透過人為參與擴大吸引我們的注意力,程式會不時提醒我們要對某事做社群性的獎勵,所以我們也慢慢學會透過留言與按讚建立我們的排序,在此狀況下,因經驗產生的內在優點反而不是重點。
這樣的遊戲規則讓我們對平台產生黏著性,很可能會導致意想不到的行為改變,一點一滴,積沙成塔,最後得到快樂的是「Gram」 ,而不是我們自己。我們放棄真實情境上的親密關係,透過替代性行為轉移且淡化它。當我們的網友追蹤者越來越多,但核准與否都來自外部:來自一支空虛軍隊────但他們只是陌生人,對我們自身福祉鮮少關心甚至根本沒有興趣。
經驗本身不再是目的,所謂的經驗變成利用奇怪的虛擬貨幣來獲取地位的手段,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些虛擬貨幣幾乎沒有任何價值、沒有任何好處。看到點讚數又上升了,多巴胺釋放了,暫時感到滿足。這種滿足感來得快去得快,但它容易獲得也容易讓人愉悅,所以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回去以獲取更多。這聽起來有點像毒品上癮的初期症狀,不是嗎?沒錯,它就是。近期的科學研究表明,這些行為正在改變我們的大腦結構,使我們更容易抑鬱和焦慮。20事實上科學家認為,自殺和憂鬱症的統計數字上升趨勢,與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的統計數據上升趨勢呈現一致。21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尚・瑪麗・溫特格(Jean Marie Twenge)對此議題做了研究,特別指出智慧手機正破壞人們的心理健康。儘管有人批評她的詮釋過於負面,但研究的確顯示,社交媒體可能對我們的幸福感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22
《愉悅的祕密:解開人類成癮之謎》(The Compass of Pleasure)23全書主旨在以科學知識陳述人類愉悅感的來源,作者大衛・林登(David J. Linden)指出,痛苦曾經認為是快樂的對立面,直到我們開始研究專門騙人的多巴胺,並發現痛苦也可以啟動我們的獎勵迴路(reward circuit)。我們現在了解,快樂的反義詞是無聊(ennui,或說無聊到極致帶來的萎靡感),一種缺乏刺激和充實感的不滿足。若說無聊是樂趣的敵人,那麼空虛就是毀滅樂趣的終極惡霸。
樂趣的祕密武器,催產素
以往我們相信能保有快樂的方法,現在則證實與豐富人生無關,只是努力迷失在空虛中。我們努力讓自己快樂,卻得不到持久回報,當快樂捉摸不定,我們就會想知道為什麼。
對於這一切,玩樂是解藥──不管從真實意義層面還是從神經化學的角度來看,它都是解藥。是的,與他人共享玩樂與一種重要的荷爾蒙有關,但我們談得不夠多,它是第二種會讓我們感覺愉悅的荷爾蒙:催產素(oxytocin)。我們可透過親社會互動(prosocial interaction,又稱利社會互動)以及與他人的相處經驗得到催產素。打個比方,催產素帶給我們的是超出我們想像、真正的糖,而多巴胺則是糖精,只是讓我們感覺不錯。
若不經過有意管控,我們自己的時間很容易就被別人占據了,接著是被綁住的無力感,因為我們知道事情不該是這樣。我們忽視了人有自己行動、自主掌控的原始渴望,只好透過捐款給威爾的冒險,或者發佈#tbt懷舊照片 ,看著按讚次數持續升高,心裡的那一塊渴望好像就被安撫了。問題是,這並不是真正的交流聯繫。我們按著按鍵,卻忽略了與我們一起吃飯的人,然後說,虛擬交流也是社會參與。但內心深處卻有種感覺低語著,生活正與我們擦肩而過,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是把生命片段投入空虛中。
當我們想去玩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收回控制權。當我們著重在分享真實細膩的經驗,當我們想透過玩樂積極尋求有他人參與且有意義的社交互動時,我們就不再需要多巴胺靜脈注射。因此,玩樂就是享樂跑步機的解方,它豐富我們的生活,而不會壓抑我們要感覺活著、我們要感覺與他人連結的真實需求。
催產素的作用似乎不只在讓人愉悅,研究顯示它可以保護我們免受自己負面衝動的影響。德國呂貝克大學的沃克・奧特(Volker Ott)博士和同事做過一個實驗,他們給二十名健康男性注射催產素後,這些男性的自我克制能力增強,零食攝入量減少。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催產素對控制與獎賞相關的行為有顯著效果。24如果我們優先要做的都是那些能補充催產素、滿足樂趣需求的活動,我們就會把自己裝備得更好,把那些速食滿足拋在腦後,為我們的時間分配和精力投資做出更好的選擇。鼓勵催產素的釋放,就能更深入體會同理心,也就更支持了人際連結的維繫。如此,我們就能從餵養空虛,變成餵養我們自己和那些我們真正關心的人。催產素的存在,讓我們表現得更加親社會、更加利他,更能認知玩樂這件事無關乎自己或與他人比較,而是一種互相支持、一起邁向更好未來的狀態。25
請注意:催產素和多巴胺等荷爾蒙與行為間的關係是真實且經過研究的。科學正在蒐集謎團的各部分線索,但必須承認它們在體內運作的全貌比我們目前理解的要複雜得多。神經傳導物質並非「不是這樣就是那樣」,而是關聯共生的關係,在身體上產生各種不同用途。因此,雖然上述並不能完整闡述催產素vs.多巴胺對大腦的作用────事實上,它們更像是彼此需要的玩伴────但上述所說可作為我們該重視什麼,以及為什麼該重視的隱喻。
「我一生中曾有一段時間,認為自己擁有一切──萬貫家財、豪宅、汽車、華服、美女,以及任何你能想像到的各種物質東西,而我現在只求平靜。」
────美國演員李察・普瑞爾(Richard Pryor)
亞利桑納州鳳凰城某個乾旱如常的冬日,一位名叫威爾・諾瓦克的男子收到一封電子郵件,信中邀請他參加單身派對。聽起來很好玩啊:在佛蒙特州滑雪,度過一個狂野週末。派對是八◯年代的主題,有燒烤和義大利美食、啤酒、美麗的初雪。只有一個小小問題,派對主角是新郎安傑羅,威爾根本沒聽過他,也不認識他的任何伴郎;一定有人發錯了邀請函。(值得注意的是,有個伴郎叫比爾・諾瓦克,而比爾是威廉的小名。)不過,讀到這封電子郵件讓威爾心情很好,身為一個十個月大嬰兒的父親,無疑很需要放鬆。
他自顧自地笑了起來,寫了回函:「他媽的也算我一個!從邀請函內容看來,安傑羅聽起來棒極了,我想幫他好好地告別單身,我希望他的新娘(或新郎)非常棒。」他還附上了他的T恤尺寸。
他從沒想過會收到回音,他只是向宇宙丟出石子,這顆石子卻激起了些漣漪。伴郎們認為威爾很有趣────他太搞笑了,一定會為派對加分。威爾很快得到回覆:「如果你是認真的,我們也是認真的,那就來吧。」
威爾愣住了。他真的要去嗎?這趟旅行要花一千美元,家裡還有妻小要顧,加上翻修房子經濟上已經很窘迫。而且……對方都是陌生人。但另一方面,他從十四歲起就沒有再去滑雪過。他的生活雖然充實,但就像大多數新手父母一樣,生活充滿爆炸多的尿布和睡眠不足,打個小盹都算冒險。
因此他不想拒絕,而是加倍努力。他在GoFundMe平台發起募款活動,訴求「幫我參加陌生人的單身派對。」這可是重要的事,為了一個睡眠嚴重不足的新手爸爸,為了一群隨性策畫派對的兄弟團。一開始只有幾十人支持,到最後有數百人跳上來贊助,這些人在當天沒有做其他更正經的事,都到GoFundMe平台上投幾塊錢。當天還沒到募款結束,威廉的旅行資金就已全部到位。到最後共有兩百二十四人捐了四千六百一十五美元,這項募款活動轉發六千三百次。(超出旅費之外的錢以準新郎和新娘的名義捐給一個名為「大學/食品/玩具/任何所需」的兒童慈善基金會。)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太荒唐了,請暫時站在威廉的立場思考,設想一下這是一種如何的體驗:
將錯就錯的大玩笑。
因冒險激發出的腎上腺素大爆發。
從平凡躍入非凡的純粹喜悅。
隨性而至的旅行帶來的刺激感和玩樂的可能性。
結交新朋友的獎勵。
以健康形式逃避現實的機會。
威爾的故事在去蕪存菁之後是存粹的樂趣。在老婆的祝福下,他登上飛機,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創造終生難忘的回憶。對其他人來說,他成了傳奇。等到有一天,他的孩子會看到這些照片,難以置信地大笑,因為他的父親竟做出如此性之所至的事情。
我說這個故事的目的並不是說你應該效仿威爾,要你拋開每日行程轉去做別的事。這並不是本書的重點。歸根究柢,故事的重點根本不是威爾,而是所有在場外為他的冒險鼓勵歡呼的人,這些如病毒般散布的熱情是有啟發性的。人們資助威爾的募款活動或贊助網路上其他好玩的事都是有原因的(當然你也可以說那些是「毫無意義」的無聊事):
我們生活在極度缺乏樂趣的世界,我們無法自己找樂子,就只能敲幾個按鍵,把找樂子的事託付給像威爾這樣的人。
所以玩樂是──或說應該是──人人都能獲得的基本物品。如果人生必定有失望、痛苦和失落,玩樂就是神奇的膏藥,就算巨石襲來、利箭穿身,只要好玩就能讓命運無情的折磨變得可以忍受。
從出生開始,玩樂對於人類大腦的發育至關重要,如利用「躲貓貓」這樣簡單遊戲讓我們埋下理解世界的種子。孩童的玩樂有助於發展基本的社交和運動技能,建立界線也測試極限,定義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我們利用玩樂來探索生活,找尋是什麼人事物會帶給我們快樂。我們經歷不同角色和身分,最終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識。(以喜劇動畫《南方四賤客》(South Park)裡大廚(Chef)的名言來說,就是「有段時間、有個地方是為所有事做準備,那就是大學。」)
當我們慢慢進入成年,生活可能變得更複雜,玩樂成為豐富人生的工具,也成為卸除生活壓力的排氣閥,同時也維持我們的健康:因為玩樂帶來的歡笑和幽默感可以減少焦慮、減輕壓力、增強自尊、自我激勵。玩樂帶來的趣味可以改善呼吸和循環,降低脈搏和血壓,有助於將腦內啡釋放到血液中。玩樂可以緩解孤獨和無聊。當年齡增長,玩樂是保持活力的關鍵。
這就是玩樂的真相和潛力,至少應該是這樣的。但可悲的現實是,我們多半在剛成年時就放棄了它,因為「我們總有一天會長大,對吧?」《華爾街日報》曾有一篇文章〈衰老過程中被忽視的技能:如何享受樂趣〉,作家克萊兒・安斯貝里(Clare Ansberry)在文中表示,在整個成年過程中,我們多半都忘記了如何玩樂。我們讓這個重要技能被削弱,因為我們錯誤地認為它幾乎沒有什麼價值,而事實是,「歡笑、放鬆、享樂、消遣────這些都可作為壓力、憂鬱和焦慮的解藥。」1
親愛的讀者,你既然買了這本書,很可能對我們缺乏樂趣的人生感到懷疑。若是如此,你很特別。很多人都認為玩樂是幼稚的、沒有必要的、分散專注力的,甚至是危險的。我知道,因為當我告訴別人我正在寫一本讓人重新正視玩樂的書時,我看到他們的反應充滿疑惑。有人緊張地扭頭看別的地方,有人輕聲低笑轉移話題,還有人雖熱情點頭,卻只是等待時機,想證明為什麼在他們的情況下玩樂不能優先考慮。
在重視生產力高於一切的社會,我們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觀念:玩樂是「有,也不錯」。玩樂並不出現在日常的重要時刻,而是規畫在一年一度的度假時間裡。如果幸運的話,也許週末還能來一趟一次性的冒險行動。根據人力資源公司Zenefits的調查資料,美國的帶薪休假時間是已開發國家中最少的,但許多美國雇員必須在公司的督促下才會使用帶薪休假。2日復一日,我們不管在精神上或身體上都綁在辦公桌前,只能對著待辦清單生悶氣。在身心俱疲之下,我們既然無法選擇在生活中來次冒險,只好透過像威廉這樣的人替我們滿足需求。他們像是出來搞笑的甘草人物,不時出現在我們的社群消息中。
當我說「選擇去冒險」,我並不是指要去跨州旅行和陌生人聚會,也不是去做什麼其他更激進的事。我的意思是:用心生活,有意識地把日子慢慢過成能享受樂趣的日子────就從現在的生活開始,而不是幻想明天。這概念我稱之為「玩樂的生活實踐,養成樂趣習慣」。
要想在生活中實踐玩樂並養成習慣,首先要徹底重新認知什麼是「樂趣」,以及它為什麼是健康、幸福、成功的關鍵,甚至它的重要性比我們想的更重要。
只有工作,沒有玩樂
我們是如何來到這裡的?在美國和歐洲,人們多半接受古老基督新教對職業道德的詮釋,這是美國夢的精神軟肋:努力工作是一種美德。對清教徒來說,成功不僅定義了人的自我價值,也定義了我們的精神價值。如此,真正的靈魂才會處於平衡。在這樣的背景下,工作是否努力以及工作的產出就變成非常嚴肅的事了!
如果工作是神聖的,那干擾工作的事────又名玩樂────不僅毫無價值,更是邪惡的。
遵循同一福音的教導,要想創造財富和實現美國夢,只要努力工作就夠了────儘管現代社會學表示,貧窮與個人的關係要複雜得多。記者兼社會評議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她的著作《我的底層生活》(Nickel and Dimed)3中描述她如何只靠一份最低工資的工作謀生,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簡單做結論:在沒有個人儲蓄或有意義的社會安全網下,做最底層工作的人連勉強餬口也嚴重地無能為力,努力工作根本不足以克服困境。
儘管如此,由工作衍生的各種觀念(在各層面上)仍然根深蒂固。我們的自我價值感隨著個人的生產力上升或下降。暢銷書作者拉哈芙・哈弗斯(Rahaf Harfoush)在《未來、工作、你》(Hustle & Float)4一書中強調,工作是一種美德────無論它與快樂、意義或勞動成果有多麼悖離────因為工業革命將工作細分為瑣碎的小任務,且藉由測量來最佳化小任務的產值,在此過程中工作努力很有幫助。這是所謂的「演算法工作」(algorithmic work),工作內容可由一定的順序模式重複進行,這是過去許多人的謀生形式。5就如我的祖父,他在奧克拉荷馬州有一家鑄造廠,他和同事每天早上同一時間進廠工作,每一天,每個人都知道別人對他的期望是什麼。這種工作耗費的體力非常繁重,所以沒有熬夜這回事。你知道該做什麼,也做了該做的事,更得到了報酬,工作以外的剩餘時間都是你自己的。
到了一九七◯年代,迎來了資訊時代。許多工人不再製造小零件,而是在新興的「知識工作」領域進行交易。智慧財產和創新成為工作產品,我們不再是產線上的工人,操作裝著鏈輪與齒輪的機器;我們自己就是鏈輪和齒輪,我們的執行能力就像生產線上的設備一樣,被人利用,過度提升。我們現在就是機器,輸出商品,為他人創造利潤。
更複雜的是,近年來生產力變得越來越難以衡量。與生產線不同,創造性工作是由非線性思維和流程驅動的,因此不再遵循一致的模式,結果是我們的工作沒有明確的終點線。如果不像演算法工作那樣提供明確目標,我們就只能模糊判斷自己是否在辦公室度過誠實的一天。因為急著賺錢謀生,只好讓自己永遠處在「開機」狀態。同時,新的通訊方式使我們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溝通,問題因此變得更複雜。到現在,我們多在家工作,但工作似乎永無止境。不管工作、吃飯、睡覺,所有行動都在同一個物理空間,因此沒有明顯的過渡期告訴大腦我們已經「下班」了,只能一直回覆電子郵件直到頭撞到枕頭上。
近年來,「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觸角進一步打破這種平衡。對於那些依靠Uber、Lyft、Fiverr、Instacart、DoorDash和Upwork等平台謀生的人來說,生活的每個角落都擠滿了工作。零工工作者被工作可以自理的虛假承諾所吸引,往往沒有意識到有股強大力量讓他們辛苦創造的大部分價值都流向他人。更糟的是,這些平台的運作機制從設計之初就在誆騙零工工作者,讓他們以越來越少的工資做越來越多的工作。如果你是零工工作者,簡單搜尋一下網路就會找到許多軟體開發人員的告白,為他們把技術用在操縱運作規則上而感到內疚。
零工經濟受到應用程式的支援而出現了一種錯覺,認為可對旗下工作者進行有效控制和有意識的操縱,這錯覺很極端但絕非唯一。除非你是自己的雇主,不然很少會有雇主把最高原則全部透明公開;所謂的最高原則就是盡可能利用一切資源(包括人力),能擠出多少是多少。這種企業手段在Slate線上雜誌的一篇文章中看得一清二楚,文章是〈我的公司在做企業健康管理app,但請看我恐怖的工作配額〉(My Disturbing Stint on a Corporate Wellness App),作者安・拉森(Ann Larson)曾在管理企業健康的軟體公司工作,據她推測,公司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將低薪與過勞的不良影響從雇主肩上轉移到員工身上,她也因此必須從事更多、更長時間的體力勞動。6確實有些公司是以與員工分享財富為其創業使命,但這種公司並不常見。
工作和生活沒有界線,「付出一一◯%!」全新且惡毒的工作意義出現了。美國各類勞工的過勞情形處於歷史最高峰。公司雇用當紅的激勵大師發出精神喊話,蓋瑞・范納洽(Gary Vaynerchuk)堅持認為你需要「撩落去7」 ,葛蘭特・卡爾登(Grant Cardone)宣稱榮耀屬於那些為工作付出「十倍力」(10X)的人。8這些話語在舞台上聽來很棒,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揭示,接受這些訊息且起而立行的人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史丹佛大學商學院組織行為學教授傑弗里・菲弗(Jeffrey Pfeffer)在他的《為薪水而死》(Dying for a Paycheck)一書中概述現況,他認為現代工作場域「永遠待命」的要求對我們造成嚴重傷害。9而後,在史丹佛商學院《洞見》(Insights)網站的一篇訪問中,菲弗稱讚西班牙IESE商學院的教授努里雅・欽奇莉亞(Nuria Chinchilla),認為她將這些適應不良的行為稱為「社會污染」很對。10這種工作優先的概念是一種侵入性的傷害,不僅破壞了友誼和家庭關係,且真實地正在殺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結果,二◯一六年,長時間工作導致七十四萬五千人死亡,比二◯◯◯年調查的數據增加了二十九%。11
讓工人為組織生產更多產品並不是新概念,管理大師菲德烈・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在一九一一年的著作《科學化的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中就提出這樣的想法,泰勒在書中闡述他如何利用提高工資和嚴格管理工作節奏等方法,讓鐵工廠工人的日產量從十二噸提高到四十七噸。儘管我們的經濟型態發生了如前所述的巨大變化,這個故事在今天仍然豐富了管理學理論和實務。(但是泰勒毫不掩飾地鄙視這類勞工,他表示:「這些人是如此愚蠢和遲鈍,以致心理構造比其他類型的人都更像牛。」)12我還記得我念博士時學過「目標設定理論」(goal-setting theory)13,此理論在一九六◯年代中期,由組織行為研究的先驅愛德溫・洛克(Edwin Locke)和蓋瑞・萊瑟姆(Gary Latham)確立,他們也將此方法用在改善工人生產而聞名。在在顯示,將人類最佳化為工作機器是一種進化過程,並且有著悠久歷史。最近企業正向我們推銷如下訊息:「咬牙忍耐」是一種榮譽徽章。但事實上,它是有毒的。
讓我們面對現實吧,如果你沒有不顧一切努力;如果你沒有連在上廁所時都在回電子郵件;如果你沒有日行一萬步……那麼你一定是個懶惰鬼,是吧?老實說,這些資訊蒙蔽我們理智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這種犧牲會讓我們付出可怕代價。玩樂、遊戲和休閒才是我們幸福感的來源,才是人生活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現代生活已經侵蝕了我們享受它們的機會。
跳出幸福的陷阱
正如我在前言中說的,很多人都將「追求幸福快樂」當成努力不懈的目標,我也是對這壓力鍋做出回應的其中一人。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我也像許多人一樣踏入量化這個願望的陷阱,我會把帶來快樂體驗的各個層面量化。舉個例子,我喜歡冥想。為了「增進」我的冥想體驗,我買了一台能測出神經反應的設備,這樣我就可以測知我的冥想有多「好」。然而,這種體驗很快就變質了,因為裝置軟體不斷督促我進行改善,而不是讓我簡單享受冥想體驗。就如現今人類做很多活動,但我們都受到鼓勵使用app和小工具來追蹤生活的各層面,從睡眠、運動,到與愛人親密的天數等私密事情都要計算一下。14
我們不是按照自己方式享受這些活動,而是將它們轉化為可供分析的統計數據。我們將今天的自己與昨天的自己比較,同時也將自己與隔壁的老王比較。我們糾結在當前狀態與偶然欲望之間的差距,但這些差距很可能只是偶然的問題。但若我們想走向真正能滋養我們、能幫助我們成長的有意義經歷時,幸福變成了海市蜃樓,遠遠地看還滿清楚的,可一旦我們到達,就會發現那裡什麼都沒有,只能再次從地平線上搜尋,最後變成無限循環。
這不是你的錯:科學表示,情況對我們不利。我們的大腦程式從一開始就設計成專注於現況與期待幸福之間的差距。學術界用來描述快樂體驗的專業術語是「享樂」(hedonic)這個字,當我們談論享樂體驗時,通常有兩個組成要素────預期的快樂和最終的快樂。過去的科學認為,人類行動的主要動力是為了追求完美的愉悅────這是把人類追求幸福的目的界定為「為了讓自己感覺爽」的奇妙說法。但現在科學已經認識到,真正驅使我們追求快樂的,往往不是讓我們感覺良好的事件本身,而是追求快樂可能得到的潛在獎勵或正面回饋,以及當我們的期待沒有落空時,隨之而來的良好感覺。原因有三:
一、我們會期待。如果你之前讀過幸福相關的文章,很可能聽過多巴胺(dopamine)這個物質。多巴胺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它有個更常見的別名「快樂荷爾蒙」,因為發現之初就認為它可以幫助我們體驗到愉悅、快感。但正如神經學家布萊克・波特(Black Porter)在回答我的採訪時所說,「多巴胺快感的故事在目前的神經學領域幾乎快消失了。」科學家研究多巴胺時注意到一些讓人驚訝的事:多巴胺激增的時刻是在我們做快樂的事之前。我們曾認為要體驗快樂和愉悅,多巴胺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現在我們知道,那種強烈感覺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因為我們期待。15事實上,期待與快樂感受根本沒有必然連結。現今科學家認為,多巴胺的演化目的是在提高你的興奮程度,讓你為意想不到的事做準備。至於「這件事情」本身的品質如何?多巴胺不在乎。現在,多巴胺也被認為與追求目標有關,它為我們衝向終點提供動力。
在多巴胺的推動下,我們興之所至地追求幸福,而不是真正享受幸福本身這個禮物。16在設計上,想緩解這種渴望本來就被設定為不可能。因此,我們覺得自己就像坐在倉鼠跑步輪上,科學恰如其分地把它稱之為「享樂跑步機」。類似的相關術語還包括:享樂適應(hedonic adaptation)、享樂相對性(hedonic relativism、幸福設定點或幸福原點(happiness set point)。這些概念在在顯示,生活變化和事件會對我們的幸福感受產生影響,而我們傾向高估這些影響。通常情況下,一旦改變的事物變成熟悉的事物,我們的幸福感就會回到我們各自設定的「原點」────與改變之前我們既有的幸福水準相同。我們並不比以前更快樂,所以我們又開始追求更多東西。
在享樂跑步機上還有另外兩個「欺騙人類的花招」,讓幸福變得更加難以捉摸。
二、我們會適應。人生中的任何結果,無論好壞,通常影響有限,對我們主觀認定的幸福感受都是暫時的。當我們自以為抓住幸福的時候,幸福就會溜走。幾十年來科學界一直用「適應水準理論」(applying adaptation-level theory)來探知為什麼美好事物不會持久,但真正引起關注的是社會心理學家在一九七八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研究者布里曼(Philip Brickman)、科茨(Dan Coates)和賈諾夫-布爾曼(Ronnie Janoff-Bulman)針對彩券中獎者做了一番研究。17他們發現,人生可能出現某些讓人驚奇、意想不到的經歷────例如中樂透,當下生活會暫時充滿興奮感。但我們有適應的傾向,最終會適應新的現實,回到我們最初習慣的幸福預設水平。事實上,當我們不以理性思考的態度面對不斷變化的境遇時,我們依然會變得不快樂,只要新的併發症出現了(例如,中樂透之後出現了想要分一杯羹的朋友和家人),或出現了新的問題要處理(就像饒舌歌手Notorious B.I.G. 唱的,「mo money,mo problems────沒錢,沒麻煩)。 好消息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對於樂透中獎者來說,也不會失去所有希望。如果我們能夠有效地吸收好運,我們確實可以提高生活滿意度。18如果你中了樂透,只要有正確的工具,仍然可以「智取」適應水平。
三、我們會比較。快樂感受往往與我們的實際經驗關係不大,卻與我們與他人經驗比較後出現的認知有關。
我們對幸福的看法絕大部分取決於共同經驗。以此看來,幸福就像集體幻覺。無論何時何地,共識現實出現的當下,我們就會把自己經驗的現實與他人經驗的現實進行比較。
例如,法國做過一項社會人口學研究指出,如果人有選擇,他們通常要的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更多」,而是比周圍的人擁有更多。研究人員詢問研究參與者希望選擇下列哪一項:一種是自己的智商為一百一十,而周遭他人的平均智商為九十;另一種情形是自己的智商為一百三十,但他人的智商則為一百五十。研究參與者多半選擇第一項,儘管自己的智商較低。其他狀況也是一樣的,若問參與者想要有幾週假期,一種情形是當別人放假兩週時,自己放假四週;另種情況是自己可以有六週假期,但別人卻有八週假期,研究參與者多會選擇四週假期。19
進化機制根生蒂固在人類身上,讓我們偏好選擇享樂跑步機。你終於休假了,但休假並沒有像你想的那麼快樂,因為它沒有達到羨煞眾人的效果。你終於獲得晉升,但隨著你適應新角色,你的喜悅逐漸消失。更糟的是,你發現那根本不是你期待的。你的孩子享受著節日禮物帶來的興奮,但當他們將自己的好運與表弟比較、發現運氣更好的表弟恰巧收到更酷禮物,他們的世界就會崩潰。經驗的正向感受是短暫的,我們會回到原來的狀態,那個令人討厭的幸福設定點,甚至會讓你感覺更糟。
輸入空虛
你看過電影《大魔域》(The Neverending Story)嗎?故事講述魔法世界「幻想國」(Fantasia)正被一種名為「空虛」(The Nothing)的強大惡勢力吞噬,最後只留下缺乏想像力的「真實」世界,僅存一片淒涼的空虛。這就是我對使用腦殘媒體、參與空心活動的看法────一種看似勢不可擋的空虛力量,將會吸走生活中的快樂和意義……如果我們允許它這樣做。
就以使用社群媒體為例,你可以在社群平台上立即找到有點興趣的東西、很快建構起與他人的聯繫、勾起記憶、緬懷往事。我當然喜歡與人交流做線上分享,我並不想妖魔化這些工具。但重要的是要記住,這些應用程式本來就是為了侵占我們的休閒而設計的。它們透過人為參與擴大吸引我們的注意力,程式會不時提醒我們要對某事做社群性的獎勵,所以我們也慢慢學會透過留言與按讚建立我們的排序,在此狀況下,因經驗產生的內在優點反而不是重點。
這樣的遊戲規則讓我們對平台產生黏著性,很可能會導致意想不到的行為改變,一點一滴,積沙成塔,最後得到快樂的是「Gram」 ,而不是我們自己。我們放棄真實情境上的親密關係,透過替代性行為轉移且淡化它。當我們的網友追蹤者越來越多,但核准與否都來自外部:來自一支空虛軍隊────但他們只是陌生人,對我們自身福祉鮮少關心甚至根本沒有興趣。
經驗本身不再是目的,所謂的經驗變成利用奇怪的虛擬貨幣來獲取地位的手段,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些虛擬貨幣幾乎沒有任何價值、沒有任何好處。看到點讚數又上升了,多巴胺釋放了,暫時感到滿足。這種滿足感來得快去得快,但它容易獲得也容易讓人愉悅,所以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回去以獲取更多。這聽起來有點像毒品上癮的初期症狀,不是嗎?沒錯,它就是。近期的科學研究表明,這些行為正在改變我們的大腦結構,使我們更容易抑鬱和焦慮。20事實上科學家認為,自殺和憂鬱症的統計數字上升趨勢,與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的統計數據上升趨勢呈現一致。21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尚・瑪麗・溫特格(Jean Marie Twenge)對此議題做了研究,特別指出智慧手機正破壞人們的心理健康。儘管有人批評她的詮釋過於負面,但研究的確顯示,社交媒體可能對我們的幸福感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22
《愉悅的祕密:解開人類成癮之謎》(The Compass of Pleasure)23全書主旨在以科學知識陳述人類愉悅感的來源,作者大衛・林登(David J. Linden)指出,痛苦曾經認為是快樂的對立面,直到我們開始研究專門騙人的多巴胺,並發現痛苦也可以啟動我們的獎勵迴路(reward circuit)。我們現在了解,快樂的反義詞是無聊(ennui,或說無聊到極致帶來的萎靡感),一種缺乏刺激和充實感的不滿足。若說無聊是樂趣的敵人,那麼空虛就是毀滅樂趣的終極惡霸。
樂趣的祕密武器,催產素
以往我們相信能保有快樂的方法,現在則證實與豐富人生無關,只是努力迷失在空虛中。我們努力讓自己快樂,卻得不到持久回報,當快樂捉摸不定,我們就會想知道為什麼。
對於這一切,玩樂是解藥──不管從真實意義層面還是從神經化學的角度來看,它都是解藥。是的,與他人共享玩樂與一種重要的荷爾蒙有關,但我們談得不夠多,它是第二種會讓我們感覺愉悅的荷爾蒙:催產素(oxytocin)。我們可透過親社會互動(prosocial interaction,又稱利社會互動)以及與他人的相處經驗得到催產素。打個比方,催產素帶給我們的是超出我們想像、真正的糖,而多巴胺則是糖精,只是讓我們感覺不錯。
若不經過有意管控,我們自己的時間很容易就被別人占據了,接著是被綁住的無力感,因為我們知道事情不該是這樣。我們忽視了人有自己行動、自主掌控的原始渴望,只好透過捐款給威爾的冒險,或者發佈#tbt懷舊照片 ,看著按讚次數持續升高,心裡的那一塊渴望好像就被安撫了。問題是,這並不是真正的交流聯繫。我們按著按鍵,卻忽略了與我們一起吃飯的人,然後說,虛擬交流也是社會參與。但內心深處卻有種感覺低語著,生活正與我們擦肩而過,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是把生命片段投入空虛中。
當我們想去玩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收回控制權。當我們著重在分享真實細膩的經驗,當我們想透過玩樂積極尋求有他人參與且有意義的社交互動時,我們就不再需要多巴胺靜脈注射。因此,玩樂就是享樂跑步機的解方,它豐富我們的生活,而不會壓抑我們要感覺活著、我們要感覺與他人連結的真實需求。
催產素的作用似乎不只在讓人愉悅,研究顯示它可以保護我們免受自己負面衝動的影響。德國呂貝克大學的沃克・奧特(Volker Ott)博士和同事做過一個實驗,他們給二十名健康男性注射催產素後,這些男性的自我克制能力增強,零食攝入量減少。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催產素對控制與獎賞相關的行為有顯著效果。24如果我們優先要做的都是那些能補充催產素、滿足樂趣需求的活動,我們就會把自己裝備得更好,把那些速食滿足拋在腦後,為我們的時間分配和精力投資做出更好的選擇。鼓勵催產素的釋放,就能更深入體會同理心,也就更支持了人際連結的維繫。如此,我們就能從餵養空虛,變成餵養我們自己和那些我們真正關心的人。催產素的存在,讓我們表現得更加親社會、更加利他,更能認知玩樂這件事無關乎自己或與他人比較,而是一種互相支持、一起邁向更好未來的狀態。25
請注意:催產素和多巴胺等荷爾蒙與行為間的關係是真實且經過研究的。科學正在蒐集謎團的各部分線索,但必須承認它們在體內運作的全貌比我們目前理解的要複雜得多。神經傳導物質並非「不是這樣就是那樣」,而是關聯共生的關係,在身體上產生各種不同用途。因此,雖然上述並不能完整闡述催產素vs.多巴胺對大腦的作用────事實上,它們更像是彼此需要的玩伴────但上述所說可作為我們該重視什麼,以及為什麼該重視的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