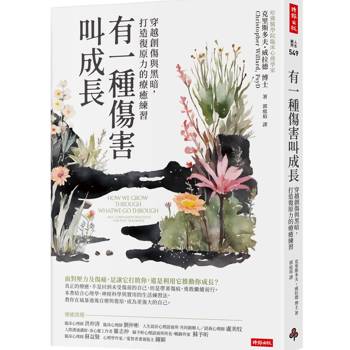01.我們天生就有復原力
創傷會改變一切,從我們的身體和大腦,到我們與他人和世界的關係,無一例外。遭受嚴重的心理、情緒或身體傷害時,我們會用洞察力、成長與學習的機會來換取自身安全--至少暫時會這樣。
百分之六十的人會經歷「創傷後成長」
幾乎所有人與天地間的萬物生靈都會在某個時刻經歷某種創傷,而其反應與療癒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研究報告指出,男性遭遇創傷的機率高於女性,但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因創傷而產生併發症,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弱勢族群(指在不平等社會中的邊緣人或被排擠者)更有可能受到創傷及其複合效應衝擊,獲得療癒資源的管道也比較少。此外,對某些人來說,身體對創傷的反應會逐漸消失;對另一些人來說,這類反應則會刻進骨子裡,久久無法平復。但無論經歷過什麼,我們都有能力成長和改變。
令人訝異的是,研究發現,雖然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會遭遇創傷,但只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的人會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百分之六十的人則會經歷創傷後成長。這是相當不錯的比例。更棒的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創傷後成長可以同時發生,兩者並不互斥。神經科學的觀點就跟大多數靈性與哲學傳統所主張的一樣:成長與痛苦是並存的。
有一點必須先說清楚,創傷及之後的復原過程充滿磨難和煎熬,不僅步調極為緩慢、難以預測,而且絕非線性發展,沒有任何事物能持續且完全緩解及撫慰我們的傷痛。朋友提供的小撇步、心理師的建議或迷因梗圖,可能永遠都無法「修復」我們,讓我們回復到之前的狀態。或許我們無法完全理解彼此的痛苦,但我們可以認同並見證這些傷痛。
也就是說,我們無須修復創傷,或希望創傷被修復,更不是試圖修復自己,而是看見、並與我們的痛苦同在。當我們擁有適當的工具來管理與調節創傷的反應時,更能輕鬆接納自己,在他人需要時給予支持,也能做到全然地陪伴與關注。
你可能會自問,你的痛苦是否嚴重到足以稱為創傷?「創傷是對異常事件的正常反應」,這個說法雖是陳腔濫調,卻再正確不過。由於「正常」與「異常」都是主觀概念,因此,創傷對各人的影響不盡相同。
創傷隱藏在神經系統裡
我們內建的壓力和創傷反應系統,會在經歷痛苦時與事過之後保護我們,以免我們將來再度受創。而期間接收到的感官訊息,也會儲存在大腦裡,每當遇上那些依舊被神經系統視為「危險」的地方或人事物,就會觸發創傷記憶與感受。一旦這種反應隨著時間逐漸失靈,變成無意識的自動化行為,就會被貼上「失調」的標籤。但事實上,我們的神經系統只是嘗試在混亂中創造秩序罷了。
與其爭論何謂創傷,不如將這本書當成一種工具或方法,能用來關注、善待、重置與重新調節你失調的神經系統。
我們在面對威脅時會啟動防禦機制,這是很正常的反應,也是演化而來的結果,這些反應幫助了我們的祖先,也是我們得以生存的關鍵。然而,威脅越嚴重,或持續的時間越長,大腦受這些機制影響和重塑的程度就越高。無論威脅實際存在與否,只要感知到威脅,我們就會出現這類反應。
我再強調一次:無論威脅實際存在與否,只要感知到威脅,我們就會出現這些反應。
02.本能的「四F求生策略」
接下來,我們來探討面對壓力和創傷時的典型反應。這些反應都是人類祖先留下的遺緒。
遠古的生活環境乍看單純,但其實比現代世界危險多了。在人類尚處於逐漸進化的動物狀態時,對我們的祖先而言,什麼會是創傷?想像有隻獅子正在追你,為了生存,你能怎麼做?
我曾在德州問過觀眾這個問題,那時台下恰巧有位訓練獅子的馴獸師。說真的,她的自我調節能力都強到可以讓她進籠和猛獅待在一起了,我不懂她幹嘛還來上我的正念課!如果你也是馴獸師,或許可以跳過這一篇文章繼續往下讀。
過度警醒V.S低度警醒
面對獅子的攻擊,我們可以用四種方式來回應,每一種都會讓神經系統趨於活躍,採取過度警醒(hyperarousal)或低度警醒(hypoarousal)的求生策略。
過度警醒
一、戰鬥(Fight):抵抗,與攻擊者正面對決。
遇到野生動物窮追不捨,這種反應的確有嚇阻的效果。但若所謂的「威脅」是塞車、討厭的同事,或某個讓你想起心中「內在獅子」的事物,這種反應就沒那麼管用了。
一旦進入戰鬥狀態,我們會變得暴躁易怒,甚或發動肢體或言語攻擊。有時,如果對抗的是自己(自責),這種反應可能會轉化成自我攻擊,進而出現自傷或其他危險行為。
二、逃跑(Flee):躲避或逃離攻擊。
如果那隻獅子動作很慢,或是你跑得很快,那這種反應就很棒。
不過,要是每次遇到令人不舒服或不安的情況,我們都選擇逃避,那就不太妙了。逃避可能會隨著時間演變成持續焦慮、恐慌、特定場所畏懼症(agoraphobia)等,抑或表現為追求強烈刺激、癮症和強迫行為。
低度警醒
三、僵住不動(Freeze):隱藏或偽裝自己,盡量不引起對方注意,例如裝死或放棄抵抗,默默等待攻擊結束。
低度警醒狀態可能會隨時間逐漸發展成蓄意逃避或無意識的解離。對許多弱勢族群來說,引人注目可能讓人覺得、或的確會格外危險,而僵住不動的反應,確實有助於保護身體、情緒,甚至是財物安全。
四、管他去死(Fuck it):好吧,我承認,其實目前臨床上還沒有人提出這樣的說法!
這種反應亦可稱為「昏厥或放棄」(faint or flop)。放棄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自我保護不致持續受創傷所苦。這種「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是自覺無法掌控或凌駕命運的無力感,長期下來可能會使大腦陷入憂鬱,讓我們慢慢放棄自己、放棄世界,或是採取逃避策略,例如濫用物質成癮,藉此淡化創傷經驗等等。
創傷會改變一切,從我們的身體和大腦,到我們與他人和世界的關係,無一例外。遭受嚴重的心理、情緒或身體傷害時,我們會用洞察力、成長與學習的機會來換取自身安全--至少暫時會這樣。
百分之六十的人會經歷「創傷後成長」
幾乎所有人與天地間的萬物生靈都會在某個時刻經歷某種創傷,而其反應與療癒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研究報告指出,男性遭遇創傷的機率高於女性,但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因創傷而產生併發症,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弱勢族群(指在不平等社會中的邊緣人或被排擠者)更有可能受到創傷及其複合效應衝擊,獲得療癒資源的管道也比較少。此外,對某些人來說,身體對創傷的反應會逐漸消失;對另一些人來說,這類反應則會刻進骨子裡,久久無法平復。但無論經歷過什麼,我們都有能力成長和改變。
令人訝異的是,研究發現,雖然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會遭遇創傷,但只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的人會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百分之六十的人則會經歷創傷後成長。這是相當不錯的比例。更棒的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創傷後成長可以同時發生,兩者並不互斥。神經科學的觀點就跟大多數靈性與哲學傳統所主張的一樣:成長與痛苦是並存的。
有一點必須先說清楚,創傷及之後的復原過程充滿磨難和煎熬,不僅步調極為緩慢、難以預測,而且絕非線性發展,沒有任何事物能持續且完全緩解及撫慰我們的傷痛。朋友提供的小撇步、心理師的建議或迷因梗圖,可能永遠都無法「修復」我們,讓我們回復到之前的狀態。或許我們無法完全理解彼此的痛苦,但我們可以認同並見證這些傷痛。
也就是說,我們無須修復創傷,或希望創傷被修復,更不是試圖修復自己,而是看見、並與我們的痛苦同在。當我們擁有適當的工具來管理與調節創傷的反應時,更能輕鬆接納自己,在他人需要時給予支持,也能做到全然地陪伴與關注。
你可能會自問,你的痛苦是否嚴重到足以稱為創傷?「創傷是對異常事件的正常反應」,這個說法雖是陳腔濫調,卻再正確不過。由於「正常」與「異常」都是主觀概念,因此,創傷對各人的影響不盡相同。
創傷隱藏在神經系統裡
我們內建的壓力和創傷反應系統,會在經歷痛苦時與事過之後保護我們,以免我們將來再度受創。而期間接收到的感官訊息,也會儲存在大腦裡,每當遇上那些依舊被神經系統視為「危險」的地方或人事物,就會觸發創傷記憶與感受。一旦這種反應隨著時間逐漸失靈,變成無意識的自動化行為,就會被貼上「失調」的標籤。但事實上,我們的神經系統只是嘗試在混亂中創造秩序罷了。
與其爭論何謂創傷,不如將這本書當成一種工具或方法,能用來關注、善待、重置與重新調節你失調的神經系統。
我們在面對威脅時會啟動防禦機制,這是很正常的反應,也是演化而來的結果,這些反應幫助了我們的祖先,也是我們得以生存的關鍵。然而,威脅越嚴重,或持續的時間越長,大腦受這些機制影響和重塑的程度就越高。無論威脅實際存在與否,只要感知到威脅,我們就會出現這類反應。
我再強調一次:無論威脅實際存在與否,只要感知到威脅,我們就會出現這些反應。
02.本能的「四F求生策略」
接下來,我們來探討面對壓力和創傷時的典型反應。這些反應都是人類祖先留下的遺緒。
遠古的生活環境乍看單純,但其實比現代世界危險多了。在人類尚處於逐漸進化的動物狀態時,對我們的祖先而言,什麼會是創傷?想像有隻獅子正在追你,為了生存,你能怎麼做?
我曾在德州問過觀眾這個問題,那時台下恰巧有位訓練獅子的馴獸師。說真的,她的自我調節能力都強到可以讓她進籠和猛獅待在一起了,我不懂她幹嘛還來上我的正念課!如果你也是馴獸師,或許可以跳過這一篇文章繼續往下讀。
過度警醒V.S低度警醒
面對獅子的攻擊,我們可以用四種方式來回應,每一種都會讓神經系統趨於活躍,採取過度警醒(hyperarousal)或低度警醒(hypoarousal)的求生策略。
過度警醒
一、戰鬥(Fight):抵抗,與攻擊者正面對決。
遇到野生動物窮追不捨,這種反應的確有嚇阻的效果。但若所謂的「威脅」是塞車、討厭的同事,或某個讓你想起心中「內在獅子」的事物,這種反應就沒那麼管用了。
一旦進入戰鬥狀態,我們會變得暴躁易怒,甚或發動肢體或言語攻擊。有時,如果對抗的是自己(自責),這種反應可能會轉化成自我攻擊,進而出現自傷或其他危險行為。
二、逃跑(Flee):躲避或逃離攻擊。
如果那隻獅子動作很慢,或是你跑得很快,那這種反應就很棒。
不過,要是每次遇到令人不舒服或不安的情況,我們都選擇逃避,那就不太妙了。逃避可能會隨著時間演變成持續焦慮、恐慌、特定場所畏懼症(agoraphobia)等,抑或表現為追求強烈刺激、癮症和強迫行為。
低度警醒
三、僵住不動(Freeze):隱藏或偽裝自己,盡量不引起對方注意,例如裝死或放棄抵抗,默默等待攻擊結束。
低度警醒狀態可能會隨時間逐漸發展成蓄意逃避或無意識的解離。對許多弱勢族群來說,引人注目可能讓人覺得、或的確會格外危險,而僵住不動的反應,確實有助於保護身體、情緒,甚至是財物安全。
四、管他去死(Fuck it):好吧,我承認,其實目前臨床上還沒有人提出這樣的說法!
這種反應亦可稱為「昏厥或放棄」(faint or flop)。放棄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自我保護不致持續受創傷所苦。這種「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是自覺無法掌控或凌駕命運的無力感,長期下來可能會使大腦陷入憂鬱,讓我們慢慢放棄自己、放棄世界,或是採取逃避策略,例如濫用物質成癮,藉此淡化創傷經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