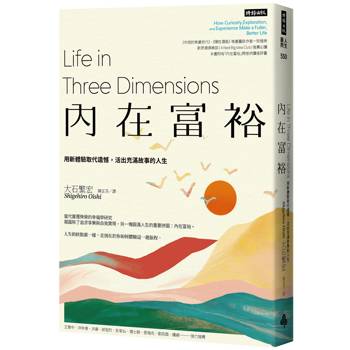第1章 該留還是該走? 如果我走,會遇上麻煩; 如果我留,麻煩只會翻倍。 ──衝擊合唱團(The Clash) 1. 安適的人生 阿義出生在日本九州的小山村,一個以生產綠茶和蜜柑知名的地方。阿義就像他的父親、祖父和在他之前的所有男性祖先,一輩子住在那裡,種稻米和茶為生,他才上了一年的農業高校就選擇輟學務農,走上這條老路。二十七歲那年,阿義娶了鄰鎮的女孩,有了三個孩子,他參加街坊組成的壘球隊,一直打到五十幾歲,每年會跟鄰居結伴到各地的溫泉暢遊。至今他依舊住在這座小鎮,還是同一位妻子,親近的友人還是那幾個從小學就認識的,阿義選擇遵循先人的足跡,他與祖先不僅血脈相連,就連職業、住所、期待和生活方式都緊緊相繫。 阿義是我父親,而我是他遠在天邊的兒子。我剛過完十八歲生日後,花了整整十八天才從我住的小山村來到東京上大學。大四那年,我獲得國際扶輪社(Rotary International)的獎學金,到緬因州留學。留學的課程開始前,我先到紐約市的史泰登島(Staten Island)去參加暑期英語課程,當時我剛和東京的女友分手,對談戀愛心灰意冷,只想把英文讀好,但我認識了一位韓國學生並墜入愛河,當時她即將前往波士頓讀研究所,我則是即將去緬因州的劉易斯頓(Lewiston)留學一年。一九九一至九二年的那個學年間,我每週末搭灰狗巴士去波士頓看她,到了五月,我必須回東京,儘管我在留學前的生涯規劃是去日本的文部省工作,全然沒有打算在美國念研究所,但那時我已下定決心要回美國。一九九三年六月畢業後,我離開日本,從此不再回去,之後流轉於紐約市、伊利諾州香檳市(Champaign)、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里斯市(Minneapolis)、維吉尼亞州夏洛特鎮(Charlottesville)等地,最後在芝加哥落腳。在這過程中,我娶了在史泰登島認識的韓國女孩,我們的兩個孩子分別出生在兩個不同的城市。我已經多年沒有和任何一位兒時的友人見面。 離開家鄉三十年後,隨著年紀增長,加上試著維持家族的情感聯繫,我經常納悶著我的人生怎麼會與父親的人生差距如此之大,我想知道為何他有機會卻不離開家鄉,相反地,我也想知道自己為何如此漂泊。 父親的人生安定、熟悉且舒適。春季的年度賞櫻會,夏季的盆踴祭典,秋季的賞楓之旅,冬季的溫泉。安適美好的人生。相反地,我的人生一點也不安定、一點也不熟悉,承受著更多壓力,來自授課、批改成績和寫作截止日期,當中混雜著無數次被拒之門外的經驗(例如:申請經費、論文、書籍企劃提案、應徵工作等)。雖然我多半時間熱愛著自己的工作,但有時我真心忌妒父親那單純、怡然自得的生活,希望每個禮拜能有個晚上跟老朋友喝個小酒,回憶學生時代,聊聊農事,但老實說,我知道自己不可能過那樣的生活,因為我極度渴望見識外面的世界,渴望到無法遵循祖先一路走來的一成不變的生活。 2. 幸福、意義及其他 我回想在高中畢業時,面對衝擊合唱團(The Clash)那句不朽歌詞的提問:「我該留還是該走」,那時答案很簡單,走就對了。但隨著年紀增長,這問題也愈來愈難回答,幾十年來,它已經成為我個人生活和學術研究的核心。我猜想大部分的讀者也曾經問過自己相同的問題,不只一、兩次,而是很多很多次。你們之中的一些人或許就像我父親那樣,忠誠、謹慎且念舊,將安定列為人生的優先;有些人或許比較像我,對外界的變化敏感、異想天開、愛冒險,擁抱大膽探險的人生。當然,安定和變動的人生;單純與高潮迭起的人生;舒適和挑戰的人生;傳統與非傳統的人生,這之間存在著利弊得失,但是,哪一種才能讓我們更接近「美好」的人生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會汲取我數十年來的心理科學研究,輔以現有文學、電影、哲學著作中的案例資料,但我們首先要問的是,究竟什麼是美好的人生? 當《金翅雀》(The Goldfinch)的作者唐娜.塔特(Donna Tartt)被問到她在這本小說中想探討什麼問題時,她回答:「什麼是美好的人生……是讓自己感到幸福?是屬於個人的幸福?還是哪怕犧牲自己的幸福也要讓別人幸福?」塔特的提問值得深思。我們是否應該努力追求幸福?還是先努力使他人幸福,然後才想到自己? 首先,什麼是個人的幸福?什麼使你幸福?是能夠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還是追求並完成事業目標?又或是到海邊玩耍或是做spa?我在人生中曾經做過很多自私的決定,包括在我兒子們還就讀初高中時搬到紐約,到一所聲譽卓著的學校工作,儘管兒子不想離開家鄉和他們的朋友,我還是選擇使個人的幸福極大化,而到頭來,我並不覺得自己更幸福。相反地,我父親則決定留在家鄉,或許是為了使我母親和其他人幸福而犧牲了他自己。如果搬到縣內另一個熱鬧的城市,他賺的錢大概會多很多。諷刺的是多年後,他對當初決定的滿意程度似乎高於我,這聽起來像是什麼中國諺語的故事,卻闡釋了一個更大的真理:心理學的研究顯示,試圖使他人幸福將使你幸福,而試圖使自己幸福,卻往往無法如願。心理學家發現,利他目標的花費、寫感謝信、懷抱知足心態(也就是安於所有),都能提升幸福的程度,父親如此幸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調整自己的期望,珍惜在田裡的每一天,享受老伴在身邊的小確幸。 父親的美好人生,關鍵或許在他決定將他人(包括我母親和家族傳統)的需求置於自己的需求之上,話雖如此,以自我犧牲與美德為主軸的人生--或許可以被稱為「有意義的人生」--是無怨無悔的人生嗎?人會為最近做過的事後悔,後悔說了不該說的話或是做了不該做的事,然而從長遠來說,人會為自己沒有做的事後悔,像是沒有說出「我愛你」,或沒有回學校繼續進修,有些人過著自我犧牲與美德的人生,卻錯過種種機會,最終招致更多的遺憾和悔恨;自我犧牲確實令人敬佩,但是把自我犧牲擺第一位,可能會使你看不見自己的渴望和理想,直到感覺人生不再真實。法國哲學家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會將之稱為「自欺」(bad faith)的人生,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說《秀拉》(Sula)中就出現了這樣的例子,書中的妮爾.萊特(Nel Wright)擱置了兒時的冒險」夢想,按著家人的期待扮演完美妻子與母親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