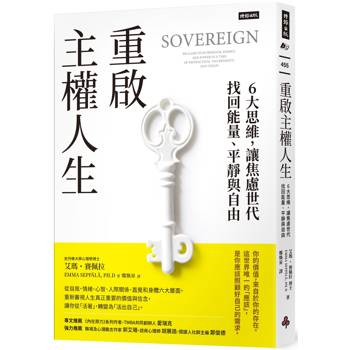第二章 成為自我的主人
有個星期六,我預定要在一場線上會議擔任開場講者。但我鮮少在週六工作,所以那天我想都沒想,就帶著小孩出門,到離家四十五分鐘的一個公園。
就在孩子們往湖裡扔石頭玩時,我收到一條簡訊:「妳無法登入嗎?」我這才猛然想起——專題演講!我完全忘得一乾二淨。這是我們籌備了半年多的活動,結果我在最後一刻讓夥伴們失望了。
我羞愧至極,無地自容,整個人蜷縮起來,感覺自己就像穿了一件上面大大寫著「丟臉」二字的衣服。
你知道什麼叫「史詩級的失敗」嗎?你知道什麼叫「想挖個地洞鑽進去嗎」?你知道什麼叫「徹底搞砸」嗎?現在,花點時間回想最近一次令你尷尬的失誤或窘境,還有在事發當下你對自己是怎麼說的。我給你五秒鐘。
我曾拿這個問題問過數千名學生與企業管理階層,他們的回答多半是:
你怎麼會這麼白癡。
你還真是蠢。
你根本沒資格在這裡。
你到底在想什麼?
你老是這樣!
你真是一團糟。
把這些傷人的話再讀一遍,記住它們給你的感受。這些正是人類用來自我折磨的惡毒語言。
本章要探討的,是我們如何與自己相處。我們與自己的關係可以束縛住我們,也可以帶領我們走向「自主的自我」。
「討厭自己」這種病
我在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高階主管課程從事教學工作,每年指導數以百計的企業高管。我發現阻擋這些管理階層在發展之路上的最大障礙,往往就是他們與自己的關係。
某天,一位在《財富》世界500強(Fortune Global 500)企業任職的中年女性領導者,在課後跟我說:「我在領導能力上是個可以拿A的主管,但在教養孩子上卻是只能拿D的媽媽。」她的傷心也讓我心碎。
「我不夠好」這句話,已經成為大部分人大腦中的「病毒程式」。百分之八十的千禧世代都認同「我不夠好」這句話適用於自己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百分之八十耶!比起好事,我們的大腦更容易看到壞事,這就是知名的「負面偏誤」(negativity bias),而這也解釋了何以在績效評估或任何類型的評論中,九個人喊讚也抵不過一個人的批判。我們無法欣然接受那九個人的肯定,因為我們會把全副精力用在思考投反對票的那個人到底哪裡不滿意,繼而讓情緒跌到谷底。
「自我厭惡」是跟自己的有毒關係
我們常聽到「有毒關係」這個詞,卻沒有意識到,許多人跟自己的關係也有毒,而這也是我們被束縛,困在死結裡無法掙脫的原因。
這種與自己敵對的關係,會掏空你、拖垮你、限制你發揮最大的潛能,也是所謂的自我厭惡。你可能認為:「我才沒有討厭自己呢!」但換個角度想想:你是否總覺得自己不夠好,對自己太過苛責呢?從心理學的觀點,自我批判就是自我厭惡的表現。
讀到這裡你可能會想:且慢,適度的自我批判難道不是滿健康的事情嗎?人不就是要懂得反躬自省才能有所進步嗎?難道我們不該對自己嚴格一點,以免在競爭中落後,或是無法全力以赴嗎?
在這裡,我們必須學著區分什麼是自我批判,什麼又是自我覺察。
自我批判:針對失誤與缺點感到自責。它會譴責你未達標,讓你羞愧難當,極具傷害性。
自我覺察:只是單純意識到自己需要改進之處,但既不批判也不自責,不會引發罪惡感、羞愧或不安全感等負面情緒。
比方說,我的統計學知識還不夠好。如果是自我批判,那我就會(在腦海中)狠狠打自己一頓屁股。但如果是自我覺察,那我就會承認自己的確需要更多專業知識,並邀請統計學家參加我的研究團隊──而這也確實是我採取的做法。
習慣性自責,就是內心住著恐怖份子
我們總是如此嚴苛地對待自己,而身邊也一堆嚴以待己的人,這是不是很有趣了?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在自我虐待。
自我厭惡是一種傳播廣泛的病毒──我會稱它為「病毒」,是因為:一、它很常見;二、它具有傳染性,會在家庭與社會之間傳播;三、它具有強大的破壞力。研究也顯示,自我批判是焦慮、憂鬱與飲食失調等症狀的「維護因子」(maintenance factor)。
想像現在有個恐怖份子,手持武器走進房間威脅你。你的交感神經系統──即「戰或逃或僵住」的模式──會被啟動,伴隨而來的是恐懼、焦慮、心跳加速、血壓升高和恐慌。
你內在的批評者就像那名恐怖份子,只不過這個恐怖份子住在你心裡,折磨著你。在讓你心跳加速與各種交感神經活動亢奮的同時,逐漸耗損你的身心健康。
打敗我們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苛刻的自責。抵在你太陽穴的那把槍就是羞愧,讓你的自我價值感一落千丈,榨乾你的能量,讓你身心枯竭。
諷刺的是,你一人分飾兩角:你既是迫害者(恐怖份子),同時也是受害者(你那可憐的自我)。看到了嗎?讓你受困和束縛的,正是你自己。這就像我們被設定了要自我毀滅的程式,根本說不通。
沒有一種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強烈
自我批判是一種在家庭、群體與文化傳承之間的社會制約,既然大家都是這麼做,你自然也會耳濡目染。這一切已經變得如此「正常」,你根本不會去質疑它。
但話說回來,自我厭惡並非普世的現象。在某些文化中,像是印度教、耆那教與佛教文化,它們相信輪迴的存在,信徒明白能生而為人是多麼難得。你就像中了頭獎,此生才能投胎為人。畢竟,你也可以生來是一條蟲!所以你能擁有人的身體、自由意志,以及學習、成長與做出貢獻的機會,真的非常幸運。
有個例子可以說明我們是何等深植於自我厭惡的設定中──或者説我們跟這種設定究竟有著何等的孽緣:
在我為企業主管所開設的一門課程中,我請參加者向他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索取關於自己的反饋,而且是僅限於正面、積極的評價。
猜猜怎麼樣?這些主管根本無法接受這個要求,甚至一想到要做這項任務的前一晚還會焦慮到失眠!我不禁好奇,請別人給自己一點正面的回饋有那麼難嗎?當我問他們是不是寧願請求負面回饋時,得到了一致的答案:「當然!」
為什麼我們可以接受自我批判來打擊自己,也可以接受別人批判性的回饋意見,卻無法接受自我肯定與別人讚美?這真是非常奇怪。
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如果你不去質疑,特別是質疑那些對你有害的事,你將無法擺脫束縛。深入思考,揭開面紗,然後捫心自問:「為什麼我要信這一套?」只有透過提出質疑,你才能開始拆解那些控制你生活的破壞性習慣與制約。
此外,即使你不是為了自己去拆除這種自我厭惡,也請為了你的孩子或任何一個以你為榜樣的人去做。對此我能舉出最揪心的例子,就是我曾聽到我大兒子用充滿自我否定的語氣談論他自己,只因為他曾聽過我用同樣的語氣聊到我自己:當時他弟弟剛出生,而我正處於產後憂鬱期,他內化了那些他聽到的感受,就像所有的小孩都會做的那樣。於是我下定決心,不能再把這種負能量傳到下一代。
如果有什麼是我想要傳承給我孩子的,那就是希望他們能成為擁有自主權的人,那是一種肯定生命、尊重自我的態度。
擁有歸屬感,比做自己更重要?
除了自我批判之外,我們加諸自身的另一種枷鎖,是認為他人的肯定、讚譽和欽佩會讓我們感受到被愛。然而,我們常為了追求這些肯定而把自己搞到焦頭爛額。
感受「被愛」,才會有歸屬感
耶魯是一所極其競爭的學府,每年的錄取率也就百分之三到五。來自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莘莘學子,都夢想能進入這所菁英薈萃之地就讀。所以,當有一群科學研究員問及耶魯大學的同學,對於終於擠進這個窄門有什麼感想時,一般人想像的答案可能是「自豪」、「榮幸」、「開心」。對吧?畢竟他們美夢成真了。
並沒有。
這些衝衝衝,衝進了耶魯的資優生,給出了兩種答案:「壓力很大」、「累死了」。
這些回答聽了真讓人洩氣。
接著,研究員又問這些學生:「你最想感受到什麼樣的情緒?」
再往下讀之前,請先花一分鐘想想你的答案。滿足?快樂?功成名就?
不。是「被愛」。被愛!
所有這些努力不懈,還有那種種的壓力與疲累,都代表我們拼了命在追求被愛。
渴望獲得外界的肯定,並不是耶魯學生的專利,而是世上最常見的事情,這也是很多人為什麼都曾或多或少犧牲自己的需求,也要追尋歸屬感的原因。
當然,歸屬感的需求是根深柢固、出於本能、自然且健康的。在人類歷史上,我們一直生活在家庭、團體和社會中。從出生到老去,我們與他人建立聯繫,對於生存至關重要。我們需要彼此來獲得人身安全、心理健康、社群支持與情感連結。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成為異類或被排擠多半就相當於被宣判死刑。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進化到覺得被拒絕是件很痛苦的事──它會觸發身體疼痛時,腦部所感知到的類似區域。
研究人員發現,除了食物與住所之外,我們最重要的需求就是積極的社會連結,這有利於我們的身心健康。能與他人保持緊密聯繫的人,陷入焦慮與憂鬱的比例更低,壽命會延長百分之五十,免疫系統更強大,生病更快復原,即使罹患大病的存活率也會提升。
我們天生就會尋求社會認可,甚至四個月大的嬰兒就更喜歡被肯定而不愛被拒絕的聲音。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融入家庭、學校、朋友群體和社區。成年後,我們會持續調整自身的行為,去適應戀人、朋友圈、社區與職場。無論是否有意識到,我們都會自我調適以因應性別、國籍、宗教、社區與文化等規範。
再叛逆的人,也會遵守某種規範。譬如很多重機俱樂部就會奉行自由與反抗的價值觀,如同一些典型標語上所寫的:「成為騎士吧!讓他們知道自己錯了」、「不能騎車,毋寧死」。但這些社團也往往有著嚴格的行為守則、明確的階級制度,以及期望成員遵守的團體規範。他們騎的機車跟身上的刺青或許看似叛逆,但其實那是種統一的制服。但凡是人──不論他們看起來有多兇狠多強硬──都有同一種軟肋:渴望歸屬感,和耶魯大學生一樣都渴望被愛。
偽裝,就是逼自己討厭人生
然而,這種渴望融入群體而不想被排擠的強烈願望,可能會導致人們「變形」,也就是把自身的需求、偏好、信念拋諸腦後,呈現出他們認為更容易被接納的模樣。
我大學畢業後就搬到中國生活,當時我並不會說中文,所以感覺分外孤單。我渴望人際接觸,再陽春的都好,像是能接到老家打來的電話就很不錯。有天我正在洗澡時,電話鈴響了,我渾身溼答答地就跑出來接。管它毛巾不毛巾的,我才不要漏接這通電話(當年並沒有什麼FaceTime之類的視訊功能,所以你光著身子講電話也無妨!)。在跟老媽聊了十分鐘之後,光溜溜站在那兒發抖的我才注意到窗戶外有些動靜。(上海因為空間有限和人口過密,建築物都靠得很近)就在離我只有一英尺遠的地方,窗外站著三位上海男人,他們正把身體探出陽台,看我看得很過癮。
你或許不曾經歷過渾身滴著水,還充當裸體模特兒的情況,但你應該能體會在最赤裸、最尷尬的時刻被人看到的羞恥感,你的臉頰會因為覺得無比丟臉而漲紅。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極力維持表面上的體面,以免丟臉。這也是何以那麼多人會死也不肯上台演講,因為他們不想有任何被嘲笑的機會,而被嘲笑就代表不被認可。按照這種邏輯,我們當然會改變自己的模樣以贏得他人的肯定。然而,為了迎合別人而改變自己,其實也是種拒絕,而且拒絕你的還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人——你自己。
我一個同事的姐姐莎拉,被診斷出一種罹患疾病,醫療人員建議可以藉由更健康、更有機的飲食加以改善。但她卻拒絕這個建議,因為這代表她會因為改變飲食選擇,而在她的社區裡成為異類,不是個「正常人」。看到了嗎?對莎拉而言,歸屬感比活下去更重要。普天下的人類為了融入群體有多不擇手段,由此可見一斑。
看不見的情緒假面
偽裝自己呈現出與自我不符的樣貌,對你來說就是一種束縛,因為那會讓你耗盡精力,痛苦不堪。你會感覺到:
恐懼:畢竟,不是出於本心的人設,隨時都有應聲倒塌的風險。一旦人設被拆穿,旁人發現你真正的樣子,你就可能被排擠。
IG的前網紅克拉拉‧達勒(Clara Dollar),曾為《紐約時報》寫過一篇讓人怵目驚心的文章。她描述自己是如何在戀愛關係中裝出一副高冷的酷樣,只因為她覺得那就是自己的「品牌形象」,而對方愛上的就是自己在IG上的這種人設。果不其然,她的下場就是失去對方的愛,而那其實才是她真正在乎的事情。如今,她已經取消IG帳號了。
憂鬱:諾拉‧文森(Norah Vincent)曾喬成男人,進行為期一年的實驗,然後將這場實驗寫成了一本暢銷書《自製男人》(Self-Made Man)。雖然她在超陽剛的圈子裡都成功地沒被識破,但長時間偽裝的壓力導致她嚴重憂鬱,甚至住進精神病院療養。
內耗:勉強自己去配合別人,明明不想答應卻說「Yes」,或是說出違心之論,都是違背自身的需求與慾望,會讓你感到筋疲力竭。
這就像是中國古代會讓有錢人家的女子裹小腳的做法。這些女性無法正常走路,說好聽是「婀娜多姿」,其實是一瘸一拐地痛苦行走。她們幾乎失去了自身的力量,而這種束縛正是她們自己造成的。
假裝合群的代價,是失去真正的你
人會為了歸屬感而順從社會期望和習俗行事,這是很正常的,社會傳統就是這麼建立起來的(這樣也可以避免完全的無政府狀態和無法無天)。但如果這種做法會導致你為了遷就旁人與世俗眼光而拋棄自我,包括放棄自己的本性、願望、想法,甚至是基本需求,那就不正常了。
我人生第一次失戀,是在十六歲。我初戀時因為太過投入,忽略他人,結果失去了很多朋友,所以分手後非常絕望、孤單。我還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我以本色示人留不住愛,那我就只好成為別人期望的樣子。我想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而所謂的「好人」在我的想像裡,就是要順從和被動,(盡可能)隨時準備好配合別人的需求。於是,我留起了長髮,戒掉咬指甲的壞習慣,為的是培養所謂的「女人味」。我還開始節食──彷彿這樣做可以消除我主觀上自認為的「不可愛」,但其實那只是埋下我日後飲食失調的種子。
在試著讓自己改頭換面,以便(一廂情願地)討好旁人的同時,我漸漸失去自我。我配合旁人的順從態度,到了讓人討厭的程度,就是當被問到「你想做什麼嗎?」我的回答會是「隨便啊,那你想做什麼?」有個朋友曾這麼對我說:「我覺得你甚至為了自己的存在而感到抱歉。」
我當然希望你能比青少年時期的我做出更正向積極的決定,但在許多方面,我們都曾依照外在的期待,忽略自身的需求,放棄真實的自我。我們都曾在明知該拒絕的時候答應對方的請求,多數情況下,這種行為的影響微不足道,就如同你因為出於禮貌而吃了道不想吃的前菜般,無傷大雅。但有些時候,這個結果卻足以影響你的人生,譬如你可能因為回答一句「沒問題」,就做了份工作,買了間房子,或進入一段婚姻,但這些一開始就是顯而易見的錯誤行為。面對旁人,你可以假裝無辜;但事後仔細回想,如果你對自己夠誠實,自然心裡有數:其實你一直都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但你就是說不出那個「不」字。而你之所以不敢拒絕,為的就是那份歸屬感。
有個星期六,我預定要在一場線上會議擔任開場講者。但我鮮少在週六工作,所以那天我想都沒想,就帶著小孩出門,到離家四十五分鐘的一個公園。
就在孩子們往湖裡扔石頭玩時,我收到一條簡訊:「妳無法登入嗎?」我這才猛然想起——專題演講!我完全忘得一乾二淨。這是我們籌備了半年多的活動,結果我在最後一刻讓夥伴們失望了。
我羞愧至極,無地自容,整個人蜷縮起來,感覺自己就像穿了一件上面大大寫著「丟臉」二字的衣服。
你知道什麼叫「史詩級的失敗」嗎?你知道什麼叫「想挖個地洞鑽進去嗎」?你知道什麼叫「徹底搞砸」嗎?現在,花點時間回想最近一次令你尷尬的失誤或窘境,還有在事發當下你對自己是怎麼說的。我給你五秒鐘。
我曾拿這個問題問過數千名學生與企業管理階層,他們的回答多半是:
你怎麼會這麼白癡。
你還真是蠢。
你根本沒資格在這裡。
你到底在想什麼?
你老是這樣!
你真是一團糟。
把這些傷人的話再讀一遍,記住它們給你的感受。這些正是人類用來自我折磨的惡毒語言。
本章要探討的,是我們如何與自己相處。我們與自己的關係可以束縛住我們,也可以帶領我們走向「自主的自我」。
「討厭自己」這種病
我在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高階主管課程從事教學工作,每年指導數以百計的企業高管。我發現阻擋這些管理階層在發展之路上的最大障礙,往往就是他們與自己的關係。
某天,一位在《財富》世界500強(Fortune Global 500)企業任職的中年女性領導者,在課後跟我說:「我在領導能力上是個可以拿A的主管,但在教養孩子上卻是只能拿D的媽媽。」她的傷心也讓我心碎。
「我不夠好」這句話,已經成為大部分人大腦中的「病毒程式」。百分之八十的千禧世代都認同「我不夠好」這句話適用於自己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百分之八十耶!比起好事,我們的大腦更容易看到壞事,這就是知名的「負面偏誤」(negativity bias),而這也解釋了何以在績效評估或任何類型的評論中,九個人喊讚也抵不過一個人的批判。我們無法欣然接受那九個人的肯定,因為我們會把全副精力用在思考投反對票的那個人到底哪裡不滿意,繼而讓情緒跌到谷底。
「自我厭惡」是跟自己的有毒關係
我們常聽到「有毒關係」這個詞,卻沒有意識到,許多人跟自己的關係也有毒,而這也是我們被束縛,困在死結裡無法掙脫的原因。
這種與自己敵對的關係,會掏空你、拖垮你、限制你發揮最大的潛能,也是所謂的自我厭惡。你可能認為:「我才沒有討厭自己呢!」但換個角度想想:你是否總覺得自己不夠好,對自己太過苛責呢?從心理學的觀點,自我批判就是自我厭惡的表現。
讀到這裡你可能會想:且慢,適度的自我批判難道不是滿健康的事情嗎?人不就是要懂得反躬自省才能有所進步嗎?難道我們不該對自己嚴格一點,以免在競爭中落後,或是無法全力以赴嗎?
在這裡,我們必須學著區分什麼是自我批判,什麼又是自我覺察。
自我批判:針對失誤與缺點感到自責。它會譴責你未達標,讓你羞愧難當,極具傷害性。
自我覺察:只是單純意識到自己需要改進之處,但既不批判也不自責,不會引發罪惡感、羞愧或不安全感等負面情緒。
比方說,我的統計學知識還不夠好。如果是自我批判,那我就會(在腦海中)狠狠打自己一頓屁股。但如果是自我覺察,那我就會承認自己的確需要更多專業知識,並邀請統計學家參加我的研究團隊──而這也確實是我採取的做法。
習慣性自責,就是內心住著恐怖份子
我們總是如此嚴苛地對待自己,而身邊也一堆嚴以待己的人,這是不是很有趣了?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在自我虐待。
自我厭惡是一種傳播廣泛的病毒──我會稱它為「病毒」,是因為:一、它很常見;二、它具有傳染性,會在家庭與社會之間傳播;三、它具有強大的破壞力。研究也顯示,自我批判是焦慮、憂鬱與飲食失調等症狀的「維護因子」(maintenance factor)。
想像現在有個恐怖份子,手持武器走進房間威脅你。你的交感神經系統──即「戰或逃或僵住」的模式──會被啟動,伴隨而來的是恐懼、焦慮、心跳加速、血壓升高和恐慌。
你內在的批評者就像那名恐怖份子,只不過這個恐怖份子住在你心裡,折磨著你。在讓你心跳加速與各種交感神經活動亢奮的同時,逐漸耗損你的身心健康。
打敗我們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苛刻的自責。抵在你太陽穴的那把槍就是羞愧,讓你的自我價值感一落千丈,榨乾你的能量,讓你身心枯竭。
諷刺的是,你一人分飾兩角:你既是迫害者(恐怖份子),同時也是受害者(你那可憐的自我)。看到了嗎?讓你受困和束縛的,正是你自己。這就像我們被設定了要自我毀滅的程式,根本說不通。
沒有一種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強烈
自我批判是一種在家庭、群體與文化傳承之間的社會制約,既然大家都是這麼做,你自然也會耳濡目染。這一切已經變得如此「正常」,你根本不會去質疑它。
但話說回來,自我厭惡並非普世的現象。在某些文化中,像是印度教、耆那教與佛教文化,它們相信輪迴的存在,信徒明白能生而為人是多麼難得。你就像中了頭獎,此生才能投胎為人。畢竟,你也可以生來是一條蟲!所以你能擁有人的身體、自由意志,以及學習、成長與做出貢獻的機會,真的非常幸運。
有個例子可以說明我們是何等深植於自我厭惡的設定中──或者説我們跟這種設定究竟有著何等的孽緣:
在我為企業主管所開設的一門課程中,我請參加者向他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索取關於自己的反饋,而且是僅限於正面、積極的評價。
猜猜怎麼樣?這些主管根本無法接受這個要求,甚至一想到要做這項任務的前一晚還會焦慮到失眠!我不禁好奇,請別人給自己一點正面的回饋有那麼難嗎?當我問他們是不是寧願請求負面回饋時,得到了一致的答案:「當然!」
為什麼我們可以接受自我批判來打擊自己,也可以接受別人批判性的回饋意見,卻無法接受自我肯定與別人讚美?這真是非常奇怪。
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如果你不去質疑,特別是質疑那些對你有害的事,你將無法擺脫束縛。深入思考,揭開面紗,然後捫心自問:「為什麼我要信這一套?」只有透過提出質疑,你才能開始拆解那些控制你生活的破壞性習慣與制約。
此外,即使你不是為了自己去拆除這種自我厭惡,也請為了你的孩子或任何一個以你為榜樣的人去做。對此我能舉出最揪心的例子,就是我曾聽到我大兒子用充滿自我否定的語氣談論他自己,只因為他曾聽過我用同樣的語氣聊到我自己:當時他弟弟剛出生,而我正處於產後憂鬱期,他內化了那些他聽到的感受,就像所有的小孩都會做的那樣。於是我下定決心,不能再把這種負能量傳到下一代。
如果有什麼是我想要傳承給我孩子的,那就是希望他們能成為擁有自主權的人,那是一種肯定生命、尊重自我的態度。
擁有歸屬感,比做自己更重要?
除了自我批判之外,我們加諸自身的另一種枷鎖,是認為他人的肯定、讚譽和欽佩會讓我們感受到被愛。然而,我們常為了追求這些肯定而把自己搞到焦頭爛額。
感受「被愛」,才會有歸屬感
耶魯是一所極其競爭的學府,每年的錄取率也就百分之三到五。來自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莘莘學子,都夢想能進入這所菁英薈萃之地就讀。所以,當有一群科學研究員問及耶魯大學的同學,對於終於擠進這個窄門有什麼感想時,一般人想像的答案可能是「自豪」、「榮幸」、「開心」。對吧?畢竟他們美夢成真了。
並沒有。
這些衝衝衝,衝進了耶魯的資優生,給出了兩種答案:「壓力很大」、「累死了」。
這些回答聽了真讓人洩氣。
接著,研究員又問這些學生:「你最想感受到什麼樣的情緒?」
再往下讀之前,請先花一分鐘想想你的答案。滿足?快樂?功成名就?
不。是「被愛」。被愛!
所有這些努力不懈,還有那種種的壓力與疲累,都代表我們拼了命在追求被愛。
渴望獲得外界的肯定,並不是耶魯學生的專利,而是世上最常見的事情,這也是很多人為什麼都曾或多或少犧牲自己的需求,也要追尋歸屬感的原因。
當然,歸屬感的需求是根深柢固、出於本能、自然且健康的。在人類歷史上,我們一直生活在家庭、團體和社會中。從出生到老去,我們與他人建立聯繫,對於生存至關重要。我們需要彼此來獲得人身安全、心理健康、社群支持與情感連結。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成為異類或被排擠多半就相當於被宣判死刑。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進化到覺得被拒絕是件很痛苦的事──它會觸發身體疼痛時,腦部所感知到的類似區域。
研究人員發現,除了食物與住所之外,我們最重要的需求就是積極的社會連結,這有利於我們的身心健康。能與他人保持緊密聯繫的人,陷入焦慮與憂鬱的比例更低,壽命會延長百分之五十,免疫系統更強大,生病更快復原,即使罹患大病的存活率也會提升。
我們天生就會尋求社會認可,甚至四個月大的嬰兒就更喜歡被肯定而不愛被拒絕的聲音。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融入家庭、學校、朋友群體和社區。成年後,我們會持續調整自身的行為,去適應戀人、朋友圈、社區與職場。無論是否有意識到,我們都會自我調適以因應性別、國籍、宗教、社區與文化等規範。
再叛逆的人,也會遵守某種規範。譬如很多重機俱樂部就會奉行自由與反抗的價值觀,如同一些典型標語上所寫的:「成為騎士吧!讓他們知道自己錯了」、「不能騎車,毋寧死」。但這些社團也往往有著嚴格的行為守則、明確的階級制度,以及期望成員遵守的團體規範。他們騎的機車跟身上的刺青或許看似叛逆,但其實那是種統一的制服。但凡是人──不論他們看起來有多兇狠多強硬──都有同一種軟肋:渴望歸屬感,和耶魯大學生一樣都渴望被愛。
偽裝,就是逼自己討厭人生
然而,這種渴望融入群體而不想被排擠的強烈願望,可能會導致人們「變形」,也就是把自身的需求、偏好、信念拋諸腦後,呈現出他們認為更容易被接納的模樣。
我大學畢業後就搬到中國生活,當時我並不會說中文,所以感覺分外孤單。我渴望人際接觸,再陽春的都好,像是能接到老家打來的電話就很不錯。有天我正在洗澡時,電話鈴響了,我渾身溼答答地就跑出來接。管它毛巾不毛巾的,我才不要漏接這通電話(當年並沒有什麼FaceTime之類的視訊功能,所以你光著身子講電話也無妨!)。在跟老媽聊了十分鐘之後,光溜溜站在那兒發抖的我才注意到窗戶外有些動靜。(上海因為空間有限和人口過密,建築物都靠得很近)就在離我只有一英尺遠的地方,窗外站著三位上海男人,他們正把身體探出陽台,看我看得很過癮。
你或許不曾經歷過渾身滴著水,還充當裸體模特兒的情況,但你應該能體會在最赤裸、最尷尬的時刻被人看到的羞恥感,你的臉頰會因為覺得無比丟臉而漲紅。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極力維持表面上的體面,以免丟臉。這也是何以那麼多人會死也不肯上台演講,因為他們不想有任何被嘲笑的機會,而被嘲笑就代表不被認可。按照這種邏輯,我們當然會改變自己的模樣以贏得他人的肯定。然而,為了迎合別人而改變自己,其實也是種拒絕,而且拒絕你的還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人——你自己。
我一個同事的姐姐莎拉,被診斷出一種罹患疾病,醫療人員建議可以藉由更健康、更有機的飲食加以改善。但她卻拒絕這個建議,因為這代表她會因為改變飲食選擇,而在她的社區裡成為異類,不是個「正常人」。看到了嗎?對莎拉而言,歸屬感比活下去更重要。普天下的人類為了融入群體有多不擇手段,由此可見一斑。
看不見的情緒假面
偽裝自己呈現出與自我不符的樣貌,對你來說就是一種束縛,因為那會讓你耗盡精力,痛苦不堪。你會感覺到:
恐懼:畢竟,不是出於本心的人設,隨時都有應聲倒塌的風險。一旦人設被拆穿,旁人發現你真正的樣子,你就可能被排擠。
IG的前網紅克拉拉‧達勒(Clara Dollar),曾為《紐約時報》寫過一篇讓人怵目驚心的文章。她描述自己是如何在戀愛關係中裝出一副高冷的酷樣,只因為她覺得那就是自己的「品牌形象」,而對方愛上的就是自己在IG上的這種人設。果不其然,她的下場就是失去對方的愛,而那其實才是她真正在乎的事情。如今,她已經取消IG帳號了。
憂鬱:諾拉‧文森(Norah Vincent)曾喬成男人,進行為期一年的實驗,然後將這場實驗寫成了一本暢銷書《自製男人》(Self-Made Man)。雖然她在超陽剛的圈子裡都成功地沒被識破,但長時間偽裝的壓力導致她嚴重憂鬱,甚至住進精神病院療養。
內耗:勉強自己去配合別人,明明不想答應卻說「Yes」,或是說出違心之論,都是違背自身的需求與慾望,會讓你感到筋疲力竭。
這就像是中國古代會讓有錢人家的女子裹小腳的做法。這些女性無法正常走路,說好聽是「婀娜多姿」,其實是一瘸一拐地痛苦行走。她們幾乎失去了自身的力量,而這種束縛正是她們自己造成的。
假裝合群的代價,是失去真正的你
人會為了歸屬感而順從社會期望和習俗行事,這是很正常的,社會傳統就是這麼建立起來的(這樣也可以避免完全的無政府狀態和無法無天)。但如果這種做法會導致你為了遷就旁人與世俗眼光而拋棄自我,包括放棄自己的本性、願望、想法,甚至是基本需求,那就不正常了。
我人生第一次失戀,是在十六歲。我初戀時因為太過投入,忽略他人,結果失去了很多朋友,所以分手後非常絕望、孤單。我還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我以本色示人留不住愛,那我就只好成為別人期望的樣子。我想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而所謂的「好人」在我的想像裡,就是要順從和被動,(盡可能)隨時準備好配合別人的需求。於是,我留起了長髮,戒掉咬指甲的壞習慣,為的是培養所謂的「女人味」。我還開始節食──彷彿這樣做可以消除我主觀上自認為的「不可愛」,但其實那只是埋下我日後飲食失調的種子。
在試著讓自己改頭換面,以便(一廂情願地)討好旁人的同時,我漸漸失去自我。我配合旁人的順從態度,到了讓人討厭的程度,就是當被問到「你想做什麼嗎?」我的回答會是「隨便啊,那你想做什麼?」有個朋友曾這麼對我說:「我覺得你甚至為了自己的存在而感到抱歉。」
我當然希望你能比青少年時期的我做出更正向積極的決定,但在許多方面,我們都曾依照外在的期待,忽略自身的需求,放棄真實的自我。我們都曾在明知該拒絕的時候答應對方的請求,多數情況下,這種行為的影響微不足道,就如同你因為出於禮貌而吃了道不想吃的前菜般,無傷大雅。但有些時候,這個結果卻足以影響你的人生,譬如你可能因為回答一句「沒問題」,就做了份工作,買了間房子,或進入一段婚姻,但這些一開始就是顯而易見的錯誤行為。面對旁人,你可以假裝無辜;但事後仔細回想,如果你對自己夠誠實,自然心裡有數:其實你一直都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但你就是說不出那個「不」字。而你之所以不敢拒絕,為的就是那份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