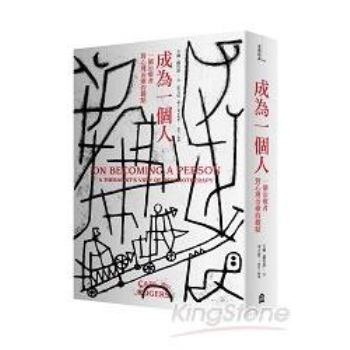第一章這就是我
■我學到的幾個重要的心得
我的學習是經過數千個小時,和那些滿懷憂戚、困擾的一個個人,密切地在一起工作而得以學會的。我要很坦白地說:這些對我而言特別有意義,我不知對你們是不是也一樣重要。我無意把這些體驗說成什麼人生的導引。不過,我倒是發現:任何別人要是願意把他自己內在的方向說出來給我聽的話,那都會對我很有價值。以下,我將把我學到的東西介紹給各位。
‧在我和他人的關係中,我發現:我若有意地想表現一些非本然的我自己,那將是毫無助益的。如果實際上我在生氣而且滿懷批評之意,那麼,刻意表現得很平靜或很愉快,就毫無用處。如果實際上我一無所知,卻要表現得好像知道答案,那也是沒用的。如果有些時候我懷著敵意,但卻表現得像個充滿關愛的人,那是沒有用的。如果實際上我正在擔驚受怕、滿腹疑慮,卻要裝得好像信心十足的樣子,那對我才真是一無是處。我相信:在我希望和另一個人建立一種有建設性的關係時,那種表裡不一的情形最是使我無法成功。
‧我發現:在我能夠很接納地聽我自己、做我自己的時候,我才是個比較有效的治療者。我覺得,這許多年來,我才充分學會聆聽我自己;我也因此比以往更能充分地知曉我在任何時刻中真正的感覺──我能明瞭我真的在生氣,或真的正在拒絕一個人;或者我能感覺我對一個人是否有足夠的溫暖和關愛;或者我是否對眼前發生的事情感到厭煩、沒趣;或者我是否急切想瞭解這個人,或者我是否在和這個人的關係中感到慌亂和害怕。我還可以這麼說:我因此變得更能完全地讓我做我自己。我也因此變得更容易接納自己之為一個決不完善的人,而這個人並不是永遠都能夠運作自如的。
‧我發現:能允許自己去瞭解他人,實在具有無比的價值。對於別人向我們所作的陳述,我們最常有的反應乃是立刻去評價、判斷而不是去瞭解。當別人表示了他的一些感覺、態度或信仰時,我們通常會脫口而出地說:「對對對」或「真笨」或「不正常」、「不像話」、「不對」或「那樣真不好」。我們很難得允許自己去正確地瞭解他所說的話對他究竟有什麼意義。我相信那是因為:瞭解是很冒險的。如果我讓自己確實地瞭解別人,我可能會因那種瞭解而發生改變,而我們都害怕改變。
‧我發現:若果我能打開一些管道,讓別人可由之而向我傳達他們的感覺和他們個人所體驗的世界,那將會豐富我的體驗。因為瞭解總能令人感到欣慰,所以我喜歡減少別人和我之間的障礙,這麼一來,如果他們想要的話,才能夠更充分地展露自己。在治療的關係中,我可以用好些方法使案主更容易表達他自己。我可以用自己的態度在關係中創造出安全感,使這種表達變得更可能些。至於用敏感的瞭解,能看待他就像他待自己一樣,而且也能接納他之具有那些知識和感覺,這樣也很有幫助。
‧我發現:當我能接納他人時,我會感到無比的欣慰。我真的能允許別人對我心懷敵意嗎?我能接納他的憤怒,並視之為他自己的真實而又正當的一部分嗎?我能否接納一個對生命和種種問題的看法都和我迥然不同的人?我能否接納這樣的一個人──非常肯定我,仰慕我,乃至想把自己塑造成像我一樣?所有這些都包含在「接納」之中,但那是不容易的。每一個人對他自己而言都是一座孤島,而且真實不二;而假若他想向其他諸島搭架橋樑,他必須首先要能願意做他自己、允許成為自己。所以,我發現:當我能接納他人,就是接納那些情感、態度、信仰,並視之為那個人之中的真實而又有活力的部分,然後我才能肯定我是在協助他去成為一個人:而在我看來,能這樣做,其中的價值深厚無比。
‧我愈是能夠向我自己以及他人內在的真實而展開時,我愈能發現自己不會急忙地想鑽進「固守的據點」中。當我試圖聆聽我自己正在經歷著的體驗時,或當我愈是試圖把這同樣的聆聽態度延伸到另一個人身上時,我愈是能尊重我所感受到的這種生命之複雜的過程。所以我變得愈來愈不願意急急忙忙衝進那個固守的據點──去確定目標,去塑造別人,去操縱或催促別人走上我要他們走的道路。更容易令我滿足的,毋寧是讓我做我自己,而讓別人去做他自己。
‧我能夠信任我自己的體驗。當我覺得一件事好像很有價值或值得去做時,那它就是值得去做。換句話說,我學到的是:對於一個處境,我的整個有機體的感覺比我的智識更值得信賴。我的整個專業生涯的走向在別人看來有許多是愚不可及的,而我自己難免有許多懷疑。但我對於自己能向「覺得很對」的方向走去,這一點我是從不後悔的,即使在當時我也確常覺得自己很傻、很寂寞。我發現,當我能信任我的一些內在的,非智性的感覺時,我在那當中就可找到智慧。事實上我也發現,在我執意遵循這條不同尋常的道路,經過五年、十年之後,許多人加入我的行列成為我的同僚,我也因此而不再覺得孤單。
‧別人對我的評價並不能引導我。我可以說,別人的種種判斷,總是該聽聽,該弄清楚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那卻永遠不會引導我。我記得在早年的時候,有位飽學而好深思的先生告訴我,一個心理學專家對心理治療發生興趣簡直是件錯謬的事情。我聽了之後感到震撼不已。可是,那種話卻無法引領我到任何地方去,而且如果我只認定自己是個心理學專家,我就根本不會有機會練習做心理治療。在爾後幾年中,我聽到別人對我的種種批評,也時常使我信心動搖。他們是怎麼說的呢?說我是個騙子、沒有執照卻敢行醫的傢伙、是個專寫些膚淺而有害的治療法的作家、是個追求權力慾的人、是個神秘主義者等等。而同時有些極端的讚譽之辭也使我一樣感到困擾。但我對這些都不太關心,因為後來我覺得只有一個人可以曉得我做的種種究竟是誠實、完整、開放、健全,或是虛偽、防衛而不健全的,而那個人就是我自己。
‧對我而言,體驗本身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效度的準繩就在於我自己的體驗。任何別人的觀念,以及我自己的觀念,都比不上我的體驗那麼有權威。為了發現真理,我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到體驗之中,而這個使我逼近真理的過程和我之成為我自己的過程是一樣的。所以,不論是《聖經》或是先知,不論是佛洛伊德或是實徵研究,不論是神的啟示或人的啟示,都不能超過我所直接體驗到的,而取得優先的決定權。我的體驗並不是因為不會犯錯而具有權威性,相反的,乃是因為它在整個權威性階層的最底層,可以不斷地用新的、基本的方式去檢查它。正因此故,體驗即使經常有失誤或會犯錯,卻永遠都是開放著,以迎接必要的修正。
‧我很喜歡在體驗之中發現秩序。我好像總是難免要在一大堆的體驗之中尋出它的意義、秩序或法則。正因為我有這樣的好奇心,我在追尋之中感到十分滿足,也因此而使我能逐一地作出我的主要理論。所以,我把科學研究和理論建構兩者都看成是有意義的體驗向一種內在的秩序奔去的過程。研究乃是一種持續而又有訓練的努力,其目的在於為主觀體驗的現象理出個頭緒,並且把它的意義說出來。這個世界若能看來很有秩序而令人滿意,那麼它存在的理由便自在其中;另一個理由是,當一個人能理解自然之中有秩序的種種關係時,這種理解自會引發出許多令人欣慰的成果。
‧事實總是友善的。有很多心理治療師(尤其是精神分析師)一直在拒絕為他們自己所實施的心理治療作些科學的評鑑,而且也不讓別人去作。我可以瞭解這種反應,因為我曾經體驗過,我會把事實看成潛在的寇讎,或看成災源禍水。也許我有點遲鈍而不能很早就看出:事實本當永遠都是友善的。人只要獲得哪怕是一點點證據,不管是屬於哪方面的,都可以把人向真理推近恰如其分的那麼多。而接近真理決不會對人有傷害、有危險或是令人不滿的事情。所以,儘管我仍然討厭去調整我的思考方式,仍然討厭放棄舊的知覺和概念,然而在一些較深的層次上,我卻已經相當能夠理解:這些痛苦的調整和重組過程正是我的學習;同時,雖然痛苦,這些學習的經驗也總是能引出更能令人滿足的(因它是更為正確的)人生觀
‧但凡是最屬乎個人的,便也是最為普遍的。有好幾次,我和學生或同事交談,或在我的寫作中,我都曾以非常個人的方式來表達我自己,我甚至會覺得這種表達的態度可能沒人能聽懂,因為我所表達的是最為私己的、個人的、而且也可能是最不易讓他人理解的感覺,結果卻每次都激起最多的迴響。因此我才逐漸相信:每個人之最私己的、獨特的體驗(如果能表達出來、與人分享的話),可能就是最能說進人心深處的因子。我也因此而得以更瞭解藝術家和詩人──這些人正是敢於將他們自己之中最獨特的部分表達出來的人。
‧我的體驗告訴我說:人都具有一個基本上是積極的方向。我在作治療時,和我有最深刻接觸的案主,包括那些帶來最多困擾的人,那些行為最反社會的人,那些具有最不正常感覺的人在內,結果我發現這樣的信念都很真確。當我能很敏感地瞭解他們所表達的感覺,當我能以他們的立場去接納他們,承認他們有權利和別人不同,然後,我才發現他們都會願意朝某些方向去改變。我不希望別人以此而誤解我的意思。我對於人的本性所持的並不是「快樂小天使」式的樂天觀點。我很能看出:人在重重防衛以及潛隱的恐懼之下,會表現而且已經表現過很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殘暴、恐怖的破壞、不成熟、退化、反社會、傷害等等行為。不過,我的經驗中最能令人振奮的部分也就是和這些人一起作治療,然後發現:在他們之中(就如同在我們每一個人之中一樣)有些最深的層次裡,也潛伏著非常積極的方向。
‧人的生命,在最好的狀況下,乃是個流動、變化的過程,其中沒有什麼是固著不變的。不論是在我的案主或在我自己,我發現:生命在最豐富而又最有價值的時刻,一定是個流動的過程。但要體會這一點的話,一方面是很能令人著迷;但另一方面也有點可怕。在我能讓我的體驗之流載我流向前去,流向我才剛能模模糊糊意識到的目標而去的時候,我通常就是在我的最佳狀態中。我的體驗之流極其錯綜複雜,但當我能在其中載沉載浮,而且還能同時一直嘗試去瞭解那變動不居的複雜性的話,那麼,其中不會有任何定點讓我停留。當我能在如此的過程之中時,很顯然的,我不會持有一個封閉的信仰體系,也不會有一套永遠不變的原則。能引導生命的乃是對於體驗能不斷瞭解、不斷闡釋的那個過程本身。所以生命就是一直在形成(becoming)的過程之中。
■我學到的幾個重要的心得
我的學習是經過數千個小時,和那些滿懷憂戚、困擾的一個個人,密切地在一起工作而得以學會的。我要很坦白地說:這些對我而言特別有意義,我不知對你們是不是也一樣重要。我無意把這些體驗說成什麼人生的導引。不過,我倒是發現:任何別人要是願意把他自己內在的方向說出來給我聽的話,那都會對我很有價值。以下,我將把我學到的東西介紹給各位。
‧在我和他人的關係中,我發現:我若有意地想表現一些非本然的我自己,那將是毫無助益的。如果實際上我在生氣而且滿懷批評之意,那麼,刻意表現得很平靜或很愉快,就毫無用處。如果實際上我一無所知,卻要表現得好像知道答案,那也是沒用的。如果有些時候我懷著敵意,但卻表現得像個充滿關愛的人,那是沒有用的。如果實際上我正在擔驚受怕、滿腹疑慮,卻要裝得好像信心十足的樣子,那對我才真是一無是處。我相信:在我希望和另一個人建立一種有建設性的關係時,那種表裡不一的情形最是使我無法成功。
‧我發現:在我能夠很接納地聽我自己、做我自己的時候,我才是個比較有效的治療者。我覺得,這許多年來,我才充分學會聆聽我自己;我也因此比以往更能充分地知曉我在任何時刻中真正的感覺──我能明瞭我真的在生氣,或真的正在拒絕一個人;或者我能感覺我對一個人是否有足夠的溫暖和關愛;或者我是否對眼前發生的事情感到厭煩、沒趣;或者我是否急切想瞭解這個人,或者我是否在和這個人的關係中感到慌亂和害怕。我還可以這麼說:我因此變得更能完全地讓我做我自己。我也因此變得更容易接納自己之為一個決不完善的人,而這個人並不是永遠都能夠運作自如的。
‧我發現:能允許自己去瞭解他人,實在具有無比的價值。對於別人向我們所作的陳述,我們最常有的反應乃是立刻去評價、判斷而不是去瞭解。當別人表示了他的一些感覺、態度或信仰時,我們通常會脫口而出地說:「對對對」或「真笨」或「不正常」、「不像話」、「不對」或「那樣真不好」。我們很難得允許自己去正確地瞭解他所說的話對他究竟有什麼意義。我相信那是因為:瞭解是很冒險的。如果我讓自己確實地瞭解別人,我可能會因那種瞭解而發生改變,而我們都害怕改變。
‧我發現:若果我能打開一些管道,讓別人可由之而向我傳達他們的感覺和他們個人所體驗的世界,那將會豐富我的體驗。因為瞭解總能令人感到欣慰,所以我喜歡減少別人和我之間的障礙,這麼一來,如果他們想要的話,才能夠更充分地展露自己。在治療的關係中,我可以用好些方法使案主更容易表達他自己。我可以用自己的態度在關係中創造出安全感,使這種表達變得更可能些。至於用敏感的瞭解,能看待他就像他待自己一樣,而且也能接納他之具有那些知識和感覺,這樣也很有幫助。
‧我發現:當我能接納他人時,我會感到無比的欣慰。我真的能允許別人對我心懷敵意嗎?我能接納他的憤怒,並視之為他自己的真實而又正當的一部分嗎?我能否接納一個對生命和種種問題的看法都和我迥然不同的人?我能否接納這樣的一個人──非常肯定我,仰慕我,乃至想把自己塑造成像我一樣?所有這些都包含在「接納」之中,但那是不容易的。每一個人對他自己而言都是一座孤島,而且真實不二;而假若他想向其他諸島搭架橋樑,他必須首先要能願意做他自己、允許成為自己。所以,我發現:當我能接納他人,就是接納那些情感、態度、信仰,並視之為那個人之中的真實而又有活力的部分,然後我才能肯定我是在協助他去成為一個人:而在我看來,能這樣做,其中的價值深厚無比。
‧我愈是能夠向我自己以及他人內在的真實而展開時,我愈能發現自己不會急忙地想鑽進「固守的據點」中。當我試圖聆聽我自己正在經歷著的體驗時,或當我愈是試圖把這同樣的聆聽態度延伸到另一個人身上時,我愈是能尊重我所感受到的這種生命之複雜的過程。所以我變得愈來愈不願意急急忙忙衝進那個固守的據點──去確定目標,去塑造別人,去操縱或催促別人走上我要他們走的道路。更容易令我滿足的,毋寧是讓我做我自己,而讓別人去做他自己。
‧我能夠信任我自己的體驗。當我覺得一件事好像很有價值或值得去做時,那它就是值得去做。換句話說,我學到的是:對於一個處境,我的整個有機體的感覺比我的智識更值得信賴。我的整個專業生涯的走向在別人看來有許多是愚不可及的,而我自己難免有許多懷疑。但我對於自己能向「覺得很對」的方向走去,這一點我是從不後悔的,即使在當時我也確常覺得自己很傻、很寂寞。我發現,當我能信任我的一些內在的,非智性的感覺時,我在那當中就可找到智慧。事實上我也發現,在我執意遵循這條不同尋常的道路,經過五年、十年之後,許多人加入我的行列成為我的同僚,我也因此而不再覺得孤單。
‧別人對我的評價並不能引導我。我可以說,別人的種種判斷,總是該聽聽,該弄清楚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那卻永遠不會引導我。我記得在早年的時候,有位飽學而好深思的先生告訴我,一個心理學專家對心理治療發生興趣簡直是件錯謬的事情。我聽了之後感到震撼不已。可是,那種話卻無法引領我到任何地方去,而且如果我只認定自己是個心理學專家,我就根本不會有機會練習做心理治療。在爾後幾年中,我聽到別人對我的種種批評,也時常使我信心動搖。他們是怎麼說的呢?說我是個騙子、沒有執照卻敢行醫的傢伙、是個專寫些膚淺而有害的治療法的作家、是個追求權力慾的人、是個神秘主義者等等。而同時有些極端的讚譽之辭也使我一樣感到困擾。但我對這些都不太關心,因為後來我覺得只有一個人可以曉得我做的種種究竟是誠實、完整、開放、健全,或是虛偽、防衛而不健全的,而那個人就是我自己。
‧對我而言,體驗本身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效度的準繩就在於我自己的體驗。任何別人的觀念,以及我自己的觀念,都比不上我的體驗那麼有權威。為了發現真理,我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到體驗之中,而這個使我逼近真理的過程和我之成為我自己的過程是一樣的。所以,不論是《聖經》或是先知,不論是佛洛伊德或是實徵研究,不論是神的啟示或人的啟示,都不能超過我所直接體驗到的,而取得優先的決定權。我的體驗並不是因為不會犯錯而具有權威性,相反的,乃是因為它在整個權威性階層的最底層,可以不斷地用新的、基本的方式去檢查它。正因此故,體驗即使經常有失誤或會犯錯,卻永遠都是開放著,以迎接必要的修正。
‧我很喜歡在體驗之中發現秩序。我好像總是難免要在一大堆的體驗之中尋出它的意義、秩序或法則。正因為我有這樣的好奇心,我在追尋之中感到十分滿足,也因此而使我能逐一地作出我的主要理論。所以,我把科學研究和理論建構兩者都看成是有意義的體驗向一種內在的秩序奔去的過程。研究乃是一種持續而又有訓練的努力,其目的在於為主觀體驗的現象理出個頭緒,並且把它的意義說出來。這個世界若能看來很有秩序而令人滿意,那麼它存在的理由便自在其中;另一個理由是,當一個人能理解自然之中有秩序的種種關係時,這種理解自會引發出許多令人欣慰的成果。
‧事實總是友善的。有很多心理治療師(尤其是精神分析師)一直在拒絕為他們自己所實施的心理治療作些科學的評鑑,而且也不讓別人去作。我可以瞭解這種反應,因為我曾經體驗過,我會把事實看成潛在的寇讎,或看成災源禍水。也許我有點遲鈍而不能很早就看出:事實本當永遠都是友善的。人只要獲得哪怕是一點點證據,不管是屬於哪方面的,都可以把人向真理推近恰如其分的那麼多。而接近真理決不會對人有傷害、有危險或是令人不滿的事情。所以,儘管我仍然討厭去調整我的思考方式,仍然討厭放棄舊的知覺和概念,然而在一些較深的層次上,我卻已經相當能夠理解:這些痛苦的調整和重組過程正是我的學習;同時,雖然痛苦,這些學習的經驗也總是能引出更能令人滿足的(因它是更為正確的)人生觀
‧但凡是最屬乎個人的,便也是最為普遍的。有好幾次,我和學生或同事交談,或在我的寫作中,我都曾以非常個人的方式來表達我自己,我甚至會覺得這種表達的態度可能沒人能聽懂,因為我所表達的是最為私己的、個人的、而且也可能是最不易讓他人理解的感覺,結果卻每次都激起最多的迴響。因此我才逐漸相信:每個人之最私己的、獨特的體驗(如果能表達出來、與人分享的話),可能就是最能說進人心深處的因子。我也因此而得以更瞭解藝術家和詩人──這些人正是敢於將他們自己之中最獨特的部分表達出來的人。
‧我的體驗告訴我說:人都具有一個基本上是積極的方向。我在作治療時,和我有最深刻接觸的案主,包括那些帶來最多困擾的人,那些行為最反社會的人,那些具有最不正常感覺的人在內,結果我發現這樣的信念都很真確。當我能很敏感地瞭解他們所表達的感覺,當我能以他們的立場去接納他們,承認他們有權利和別人不同,然後,我才發現他們都會願意朝某些方向去改變。我不希望別人以此而誤解我的意思。我對於人的本性所持的並不是「快樂小天使」式的樂天觀點。我很能看出:人在重重防衛以及潛隱的恐懼之下,會表現而且已經表現過很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殘暴、恐怖的破壞、不成熟、退化、反社會、傷害等等行為。不過,我的經驗中最能令人振奮的部分也就是和這些人一起作治療,然後發現:在他們之中(就如同在我們每一個人之中一樣)有些最深的層次裡,也潛伏著非常積極的方向。
‧人的生命,在最好的狀況下,乃是個流動、變化的過程,其中沒有什麼是固著不變的。不論是在我的案主或在我自己,我發現:生命在最豐富而又最有價值的時刻,一定是個流動的過程。但要體會這一點的話,一方面是很能令人著迷;但另一方面也有點可怕。在我能讓我的體驗之流載我流向前去,流向我才剛能模模糊糊意識到的目標而去的時候,我通常就是在我的最佳狀態中。我的體驗之流極其錯綜複雜,但當我能在其中載沉載浮,而且還能同時一直嘗試去瞭解那變動不居的複雜性的話,那麼,其中不會有任何定點讓我停留。當我能在如此的過程之中時,很顯然的,我不會持有一個封閉的信仰體系,也不會有一套永遠不變的原則。能引導生命的乃是對於體驗能不斷瞭解、不斷闡釋的那個過程本身。所以生命就是一直在形成(becoming)的過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