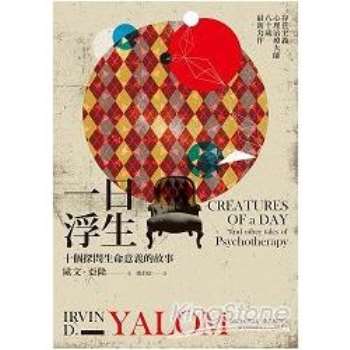1 扭曲的治療The Crooked Cure
亞隆醫師,我很想跟您談談。讀了您的小說,
《當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心想,不知道
您是否願意見一個碰到了寫作瓶頸的作家同行。
──保羅‧安德魯
想也知道,保羅的電子信無非是要引起我的興趣。他顯然成功了。我這個人,從來不拒絕作家同行。至於寫作瓶頸嘛,託天之幸,我倒是沒碰到過這樣的人,還真想幫他一把看看。十天之後,保羅應約而來。基於某些理由,我以為來者會是一個中年作家,有點輕佻,有點煩惱。殊不知,進我診療室來的竟是一個皺巴巴的老先生,腰彎得彷彿在地板上找東西。看著他經過走道,寸步慢行,心想,我這診療室高居在舊金山近郊的俄羅斯山(Russian Hill)頂,他是怎麼上來的。幾乎連他關節的噼啪作響都聽得見,我趕緊接過他手上沉重破舊的公文包,攙扶著他,帶到他坐的位子。
「感恩,感恩,年輕人,多大年紀啦?」
「八十。」我回他。
「啊──怎麼也八十了。」
「你呢?高壽多少了?」
「八十四。對,沒錯,八十四。我知道,一定嚇著你了。大部分人都猜我三十多歲。」
我端詳著他,好一會兒,彼此的目光鎖住。我被他調皮的眼睛和游移在嘴唇上玩耍的微笑迷住了。一語不發,坐著對望了好一陣子,沉浸在老人情誼特有的那種溫暖中,我把我們想像成同一條船上的旅客,一個寒冷起霧的夜晚,在甲板上聊起來,結果發現我們竟是在同一個社區長大,而且馬上認出了彼此。我們的父母都熬過大蕭條的苦日子,我們見證過迪馬喬(DiMaggio)與泰迪威廉(Ted William)之間的決鬥傳奇,也都記得牛油與汽油配給卡、歐戰勝利日,以及史坦貝克(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和法雷爾(Farrel)的《史塔茲‧勞尼艮》(Studs Lonigan)。我們什麼都一樣,彼此都覺得放心,那就更不在話下了。既然如此,可以開始工作了。
「所以,保羅,我們不妨就用名字互稱吧──」
他點了點頭:「當然。」
「我對你的認識,全都來自你那封短短的電子信,你說,你也是作家,讀過我的尼采小說,現在碰到了寫作瓶頸。」
「是的,但我只想做一次諮商。就一次。我的收入固定,多的付不起。」
「我會盡力而為。那我們就開始吧,盡量有效率一點。說說看你的瓶頸吧。」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談談自己的經歷。」
「那很好呀。」
「我得回到我學校畢業的那段日子。我在普林斯頓念哲學,寫博士論文,談的是尼采的決定論與他的擁護自我轉化互不相容。但我沒辦法完成。我老是讓一些事情搞得分心,譬如說尼采那些很不尋常的書信,特別是寫給朋友及同行作家,像史特林堡(Strinberg)之類的。漸漸地,我對他的哲學完全失去了興趣,反而比較推崇他的藝術成就,我把尼采看作是個詩人,是史上最有力量的聲音,聲音宏亮到連他的理念都為之黯然失色,沒多久,我就沒什麼搞頭了,只好轉系,不弄哲學,去念文學博士。時間就這樣過去,我的研究進行順利,但就是寫不出來。最後,我把自己搞到了一個狀況,那就是一個藝術家唯有透過藝術才能表現自己,於是,我把寫論文的計畫整個放棄,寫起有關尼采的小說來。但寫東西的瓶頸依然,一點都不受我計畫改變的影響,唬嚨不了它,嚇阻也不管用,照樣力量強大,不動如山。就這樣,一點進展都沒有,一直持續到今天。」
我這一驚,非同小可。保羅現在八十四歲。他開始寫論文應該是二十幾歲的時候,六十年前。以前我聽說過有職業學生,以念書為業,但一念六十年?他的人生凍結了六十年?啊,不,但願不是,那不可能的。
「保羅,講一點大學以後的生活吧。」
「沒什麼好講的。當然啦,大學最後確定我逾期了,鐘聲響起,我的學籍遭到註銷。但書都在我的血液裡,我從來沒丟下。在一家州立大學找了一份工作,當圖書管理員,一直幹到退休,那麼多年下來都還試著在寫,沒有結果。就這些啦,我的人生。講完了。」(待續)「再多講一點。你的家庭?生命中有那些人?」
保羅看起來有點不耐煩,噼哩啪啦地把話吐出來:「兄弟姊妹沒半個,婚結兩次離兩次,短命婚姻,但還好短。沒有孩子,感謝上帝。」
事情變得怪怪的,我心裡想。剛開始那麼親切,現在卻好像不想再跟我多談下去了。接下去呢?
我不放棄。「你的計畫是寫有關尼采的小說,在電子信裡還提到,說你讀過我的小說《當尼采哭泣》。這一方面,可以多談談嗎?」
「我不懂你要問的是哪一方面。」
「關於我的小說,你有什麼感覺?」
「一開始有一點慢,但後來有了氣力,儘管用詞精簡,對話自成一格,別有所見,但整體來說,讀來並不引人入勝。」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說,你,你自己,一直拚命想要寫有關尼采的小說,對於我那本小說的出現,你有什麼反應。這件事你應該會有些感觸吧?」
保羅搖著頭,一副連答都懶得答的神氣。無奈之餘,我只好繼續下去。
「說來聽聽,你怎麼會找上我呢?你挑選我做諮商,理由是不是我的小說?」
「啊,管他理由是什麼,我人都已經在這裡了。」
這下子,事情愈來愈詭異,我心裡想。但若要給他有幫助的諮商,就絕對需要多了解他一些。我只好轉而請出「老辦法」,一個屢試不爽又可以帶出一堆材料來的要求:「我需要了解你更多,保羅。就你平常過的日子,只要讓我詳細了解一天二十四小時你是怎麼過的,我相信我們今天就能搞定。就這個星期過去的那幾天吧,隨便挑一天,從你早晨醒來說起。」諮商的時候,我幾乎每次都會提出這個要求,儘管帶出來的都是一些病人各個生活領域的雞毛蒜皮──睡眠啦,夢啦,吃和工作模式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我了解了病人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保羅卻絲毫感覺不到我的探究熱情,就只是輕輕搖頭,像是在抹掉我的要求。「我們要討論的,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許多年來,我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克勞德‧穆勒(Claude Mueller)教授,有過很長的通信。你讀過他的東西嗎?」
「啊,他寫的尼采傳我很熟,非常棒的作品。」
「好,非常好。你這樣想,我格外高興。」保羅一邊說著,一邊把手伸進他的公文包,抽出厚厚一疊的活頁資料夾。「好吧,我把這些通信都帶來了,希望你能看一看。」
「什麼時候?你是說現在?」
「沒錯,我們這次諮商,沒有比這更重要的。」
我看了看我的手錶。「但我們只有這麼一個回合,光讀這些怕就要花掉一、兩個小時,我們還有比這更要的──」
「亞隆醫師,相信我,我清楚自己在要求什麼。開始吧,請。」
我有點不知所措。怎麼辦?他顯然心意已決。我提醒過他,我們的時間有限,他也十分清楚自己只有這麼一次會晤。但話又說回來,保羅或許真有他自己的把握,又或許,他深信不疑這些通信的確可以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材料。是了,是了,我越想越覺得有道理:一定就是這樣。
「保羅,我把你說的整理了一下,你是說,這些通信可以提供一切有關你的必要材料?」
「如果你是想問『是否非讀它不可、不然就沒有用』——那麼,答案是肯定的。」
簡直是反了。一對一對談是我的專業,我的診療室是我的地盤。在這裡,我永遠都自自在在的,但這一次對談總覺得一切都倒過來了,全亂了套。或許我大可不必那麼認真,隨他去便了。畢竟,時間是他的。而我的時間,他可是要付費的。我覺得有點遲疑,但還是勉強接受了,伸手接下他遞過來的手稿。
保羅一邊把厚厚的三孔活頁資料夾交給我,一邊告訴我,通信一共經歷了四十五個年頭,直到二○○二年穆勒教授去世為止。我開始瀏覽,好讓自己進入情況。花在這本活頁夾上的心思還真不少。看來保羅把他們之間的往返,不論是偶發的短便條或是長篇大論的討論書函,從保存、索引到日期,一切都做得齊齊備備了。穆勒教授的信,連結尾的署名都整整齊齊打出來,規規矩矩的老式作風,至於保羅的信,無論是早期複寫紙複印的或後來影印的,結尾都只一個字母P。
保羅朝我點點頭。「請開始吧。」(待續)讀了前面幾封信,發現封封典雅迷人。穆勒博士顯然十分尊重保羅,但卻責備他喜歡玩詞弄字。第一封信裡面他就說:「我看你是在和文字談戀愛,安德魯先生。喜歡和他們翩然起舞。但文字只是符號。構成旋律的是理念。為我們人生打造結構的是理念。」
「我承認我有這種毛病。」在接下來的信裡,保羅駁回去:「我是沒有好好消化和吸收他們,就是喜歡和他們跳舞,這個毛病我還真希望自己永遠都犯。」後來的幾封信,儘管有角色和半個世紀的年齡區隔,他們卻都放棄了正式稱謂「先生」與「教授」,互相稱起名字來:保羅與克勞德。
在另一封信裡,保羅寫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我老是把朋友弄得困惑不已。」所以,以前有朋友。保羅繼續寫到:「從此,我就得永遠擁抱孤獨。我以為別人都和我一樣,對文字的力量有著同樣的熱情,我知道自己錯了,知道自己是在強人所難。所以你不難想像,只要我一走近,大家就一哄而散。」聽起來,這滿重要的,我心裡想。「擁抱孤獨」是神來一筆,為此添了幾分詩意,但我想像得到,一個非常孤獨的老人。
接下來,兩封信之後,我可真是發現了「大驚奇」,有一段文字有可能為這整樁超現實的治療提供了解的鑰匙。保羅寫道:「所以,你明白了吧,克勞德,就我而言,剩下來的,無非就是去尋找一個至為輕靈、至為高貴的心靈,懂得欣賞我的感性,欣賞我對詩的熱愛,一個銳利而又大膽的心靈加入我的對話。克勞德,我的用詞遣字,可有加速了你的脈搏?這舞,我需要一個雙腳輕靈的舞伴。你會賜予我這份榮幸嗎?」
這一了解,無異霹靂。現在,我總算明白保羅堅持要我讀信的原因了。事情再清楚不過,我怎麼可以不讀呢?穆勒走了十二年了,保羅現在四處晃蕩,就是要尋找另一個舞伴!而我的尼采小說,剛好就這樣插了進來!這下好了,我整個人都給弄糊塗了。心想,本來是我約談他的,事實上呢?倒是他在約談我了。一定就是這樣,錯不了。
望著天花板好一陣子,琢磨著要怎麼樣把自己洞燭了他的心機講出來,保羅卻打斷了我的沉思,指著他的手錶強調:「拜託,亞隆醫師,我們的時間在跑耶,請繼續讀下去。」我順他的意,這些信實在精彩,我樂得一頭栽進去。
前十二封信,很明白的就是師生關係。克勞德經常會派功課,譬如:「保羅,我希望你寫篇東西,比較尼采的厭女症與史特林堡的厭女症。」這一類的功課我推斷保羅都交了,但並沒有在信中看見進一步提到,想來他們都是面對面討論了。但漸漸地,那一年過半,師生的角色開始消失。很少再提到功課,有的時候,甚至不太容易分得清誰是老師誰是學生。克勞德拿了幾首自己的詩,希望保羅發表看法。保羅的回應卻沒什麼好話,而是叫克勞德少些理智,多在意內在感情的衝擊。克勞德則剛好相反,批評保羅的詩徒有感情卻不知所云。
隨著每封書信的往返,他們的關係逐漸親密,感情日益深刻。我心想,難不成我手裡的這一握灰燼竟是保羅一生的最愛,甚或唯一的愛。長久以來,保羅或許一直陷在無法自拔的哀傷中。沒錯,沒錯,一定是這樣的。他要我讀這些寫給往者的信,無非就是要告訴我這些。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接著一個的假設在我腦海裡興起,我雖然覺得有趣,但終究沒有一個可以提供我想要的充分解釋。讀得愈多,我的疑問愈滾愈大。保羅來找我的目的究竟何在?他先前說寫作瓶頸是主要的問題,但為什麼現在他一點也沒表現出要探討寫作瓶頸的興趣?他為什麼拒絕透露自己的生活細節?為什麼堅持非要把我們的時間全都花在讀這些許久以前的書信上?我們得理個頭緒出來才行。我下定決心,不把這幾個問題跟保羅弄清楚絕不罷休。(待續)接著,我看到一封回信,把我給拉住了。「保羅,你對純粹經驗的過度推崇走偏走到一個危險的方向去了,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你蘇格拉底的告誡:人生不經檢視,活著也是白活。」
說得好,克勞德!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完全認同你督促保羅檢視他自己的人生。
但在下一封信裡,保羅馬上毫不客氣地反駁:「若要我在活著與檢視之間做個選擇,任何一天我都選擇活著。解釋這種病,我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我勸你最好也跟我學。解釋的趨勢是現代思想的流行病,其主要的帶原體則是今天的治療師:我遇到的精神科醫師,每個都有這種病,而且是會上癮,會傳染的。解釋根本就是一種錯覺,一種妄想,一種建構,一種安慰性的催眠。解釋並不存在。說穿了,不過是懦夫面對絕對存在的無常、冷漠與變遷因恐懼顫慄而採取的一種防衛。」這一段話,我讀之再三,但覺心旌動搖。心裡醞釀的想法,原本已經決定要搬出來的,這一來,也猶豫起來。我知道,保羅接受我邀舞的機會根本就是零。
每當抬起目光,就看到保羅的眼睛緊緊咬住我,我的反應一個也不放過,提醒我繼續讀下去。但到最後,我一看時間只剩下十分鐘,便闔上夾子,取回主導權。
「保羅,我們剩的時間不多了,而我還有幾件事情要跟你討論。我滿不痛快的,因為已經到了要結束的時候,我居然還沒能真正談到你來找我的理由──你的主要問題,你的寫作瓶頸。」
「我可沒說過。」
「但在你給我的電子信裡面,你說……這裡,我列印出來了……」我打開自己的夾子,但還沒等我把它擺出來,保羅已經回了過來:
「我自己寫的我知道:『我很想跟您談談。我讀了您的小說,《當尼采哭泣》,心想,不知道您是否願意見一個碰到了寫作瓶頸的作家同行。』」
我瞧著他,期待一個傻笑,但他卻一本正經。他是說過寫作瓶頸,但並沒有明指那就是他要我幫忙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一個文字陷阱。覺得自己被玩弄了,我大為不爽,反擊回去:「我一貫都是幫助別人解決問題,這是治療師的本分。所以,我會這樣的推斷,誰都想得到。」
「我完全理解。」
「那就對了,讓我們重新開始吧。告訴我,我要怎樣才能幫你?」
「你對那些信有什麼看法?」
「可不可以說得更具體一點?好讓我把要講的東西理個架構出來。」
「隨便什麼看法,對我全都是最有幫助的。」
「好吧。」我打開筆記本翻頁。「你是知道的,我的時間只夠看一小部分,但整個來說,我非常喜歡,裡面滿是第一流的才情與學問。角色的轉移令人印象深刻。開始的時候,你是學生,他是老師。但很顯然的,你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學生,不過幾個月,年輕學生與知名教授就平起平坐通起信來。毫無疑問的,他十分尊重你的看法與判斷,欣賞你的文章,看重你對他作品的批評。想也知道,他花在你身上的時間和精神一定遠遠超過他所能提供給一般學生的。還有,你們的通信既然能夠在你失去學生資格後還延續那麼久,當然,毫無疑問的,你們相互之間的重要性確實非比尋常。」
我注意看著保羅。他一動不動,含淚坐著,狂飲我的每一句話,顯然還渴望更多。終於,終於,我們碰頭了。終於,我給了他一些東西。我為一件對保羅格外重要的事情做了見證。我,而且只有我,證明世間確有一位大人物高度肯定保羅‧安德魯的重要性。但這位大人物去世多年,保羅隨著年歲增加,心理愈趨脆弱,如今再也無法獨自承受這一事實。他需要一個見證人,某個有社會地位的人,而我剛好被他挑中,填補了這個角色。沒錯,我絲毫不懷疑這一點。這種看法散發出強烈的真相氣息。
現在,若把這些看法中的某部分傳達出去,對保羅應屬有利。回顧起來,我透過觀察所得到的了解還不少,但剩下的時間又不到幾分鐘,當從何處開始,我真有點拿不定主意。最後,我決定還是從最顯著的地方著手:「保羅,關於你們的通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和穆勒教授之間既強烈又溫柔的關係,這是一種極深摯的愛。他的過世對你而言,定然難以承受。我猜想,這種失落之痛久久不得平息正是你要尋求諮商的原因。你認為呢?」
保羅沒作聲,只是伸手要拿書信,我回遞給他。他打開公事包,把書信夾子放妥了,拉上拉鍊封口。
「對或不對,保羅?」
「我會來找你諮商,是因為我需要。現在,我已經做了,也得到了我想要的。你做的很有幫助,非常非常有幫助。我別無所求了。謝謝你。」
「保羅,暫請留步。我始終覺得,了解一下自己幫助了患者什麼也很重要。你從我這裡得到了些什麼,可以麻煩你花幾分鐘說明一下嗎?我相信,對這方面做更進一步的釐清,對你將來會有好處,對我以及我未來的客戶也大有助益。」
「歐老,給你留下那麼多的謎團,我很遺憾,但我怕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起身的時候,他幾乎站不穩,我及時抓住他的手肘穩住他。等站穩了,他伸手和我握手,然後,步子輕快,邁出我的診療室。(待續)10 一日浮生
進了我的諮商室,傑若逕自走向自己的位子,意興闌珊,也不招呼我。我呢,也是顧我自己,沒搭理他。
望著窗外雪白羊毛般的成串紫羅蘭,他說:「歐老,我要懺悔。」欲言又止,然後突然掉過頭來面對著我說:「有個女的,艾莉西亞……我提過她的,你還記得嗎?」
「艾莉西亞?當然,瑪麗亞我們倒是談過不少,但艾莉西亞,不記得了,不妨再說來聽聽吧。」
「好吧,艾莉西亞,是另外一個女的啦,事情是這樣的……呃……艾莉西亞以為我要跟她結婚。」
「哇,我這可糊塗了。傑若,從頭說起,把話講明白。」
「好吧,昨天下午,瑪麗亞和我一起,跟你的凱薩琳會面做伴侶療程,事情爆開來了。一開始,瑪麗亞就打開她的皮包,抽出一疊──厚厚一疊──電子信,罪證確鑿,我和艾莉西亞討論過結婚的電子信。所以我今天決定,還是爽快一點的好。我寧願親口告訴你,不希望透過凱薩琳讓你知道,當然啦,如果她已經跟你說了,那就另當別論了。」
我大吃一驚。傑若,一個皮膚科醫師,三十二歲。這一年裡面,我和他不時會晤,密切關注他瑪麗亞之間的感情關係,他們已經同居九個月。儘管口口聲聲說愛她,他卻始終怯於給她一個承諾。「為什麼一定要給?」他不止一次說。「把我這僅有的一生押到這上面?」
到目前為止,我的感覺是治療的進展雖然穩定但很慢。傑若在大學裡主修過哲學,最初,他之所以會找上我,是因為讀過我的哲學小說,確信自己找對了治療師。開始合作的第一個月,他總是堅持透過抽象的哲學討論來做治療。但最近幾個星期以來,我比較少看到他這樣,態度似乎愈來愈認真,愈來愈願意與人分享內心世界。但即使這樣,他最急迫的問題,亦即他和瑪麗亞之間出了問題的感情關係並沒有改變。我明白,兩個人的功課,單治療一個人是沒有效果的,於是我在幾個星期前,建議他和瑪麗亞去看一個傑出的伴侶治療師,凱薩琳‧佛斯特醫師,但沒料到,今天,只要是提到凱薩琳,他開口閉口都是「你的凱薩琳」。
傑若的懺悔該如何回應呢?他和瑪麗亞的危機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他讓兩個女人都以為他要和自己結婚;他對瑪麗亞侵入自己的電子郵件的反應;還有,他口中的我的凱薩琳,以及那底下的胡思亂想。但所有這些都可以暫時擺到一邊。我以為,眼前的首要之務應該放到我們的治療關係上,那才是當務之急。
「傑若,我們回到原點,討論一下你的第一句話,你說你要懺悔的那句話。很明顯地,對於我們的合作,你保留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沒講,而你之所以今天才講
,是因為你以為凱薩琳,我的凱薩琳,會告訴我。」
該死,我實在不該把我的凱薩琳這幾個字搬出來,我知道,那會節外生枝,但還是攔不住,蹦了出來。
「沒錯,我道歉,關於那個凱薩琳的俏皮話,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怎麼來的。」
「是在暗示什麼嗎?」
「不確定。我想,那只是因為你很欣賞她,又把她的能力誇上了天。更何況,她確實是美到不可方物。」
「所以,你就以為凱薩琳和我有什麼了?」
「也不全然是啦。我的意思是說,別的不說,光是年齡就有很大的差距。你說過的,她是你的學生,大約三十年前。我上網搜尋過,知道她嫁給一個心理學家,也是你的學生……所以呢……呃……歐老,為什麼會那樣說,我真的不知道。」(待續)「或許,你心裡是這樣希望的,希望我和你是一丘之貉,跟你一個樣,也搞不倫之戀。」
「可笑。」
「可笑?」
「可笑,但……」傑若自顧自地點了點頭。「可笑,但也可能沒錯。我承認,今天我走進來的時候,就覺得形單影隻,在風中飄搖不定。」
「所以你想有個伴?希望我們狼狽為奸?」
「我想是吧。有道理。沒錯,如果你是精神病那才是有道理。老天爺,這還真是尷尬,你搞得讓我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十歲小孩。」
「我知道這很難堪,傑若,但不要逃避。你用『懺悔』那樣的字眼,我就恨詫異。對你,對我,那代表什麼意思?」
「啊,說的無非是罪惡,說自己做了什麼羞於承認的事吧。不管什麼事,只要是有損於你對我的看法,我都盡量不讓你知道。我是十分尊敬你的……這你是知道的……我非常希望,你對我,能夠維持一個不會改變的……呃……不會改變的形象。」
「什麼樣的形象?你希望歐文‧亞隆怎麼看傑若‧赫爾西?來,我們花一點時間,變個場景出來,讓我好好端詳一下你的形象。」
「什麼啦?我可不會。」傑若又是扮鬼臉又是搖頭,彷彿急著擺脫自己惹來的一身腥。「我們到底在搞什麼名堂?離題太遠了吧,為什麼不談重要的事情──我和艾莉西亞及瑪麗亞的困境呢?」
「那當然重要,馬上就談。但先遷就我一下,繼續討論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夠了,我真的受不了了,這就是你們所謂的『抗拒』吧?」
「說對了。我知道,這感覺起來滿冒險的,但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就告訴過你,每一次諮商都是一次冒險,這一點很重要,你還記得吧?現在正是如此!試試看,冒個險吧。」
傑若閉上眼睛,臉轉向天花板。「好吧,來吧……我看到你在這間諮商室裡面,坐在那邊。」他轉過來,眼睛仍然閉著,臉朝向我的桌子,我諮商室的另一頭。「你正忙著寫東西,因為某些原因,我的形象湧進了你的心裡。你講的是這個意思吧?」
「正確,別停下來。」
「你閉上了眼睛,你在心裡看我的形象,看得很久。」
「很好,繼續。現在,我看的是你的臉,想像一下我在想什麼?」
「你心裡在想,啊,那是傑若,我在看著他……」沉入到幻象之中,他看起來比較放鬆。「沒錯,那是傑若,多好的一個傢伙呀。滿聰明的,又有學問。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人。有深度,有想法。」
「繼續。我還想了些什麼?」
「你在想,『他多麼有品格,多麼正直呀……我所見過最優秀最善良的人……一個值得懷念的人』,就這一類的吧。」
「再講再講,你在我心目中有這樣的形象對你有多重要。」
「超超超級重要。」
「你找我諮商的目的本來是要我幫助你改變,但就我看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才是比較重要的。」
傑若搖頭,有點洩氣。「照今天的發展來看,這還真他媽的難以反駁。」
「沒錯,如果你對我有所保留,就像你和艾莉西亞的感情那樣,那就一定會這樣。」
「了解。說真的,我的行徑之荒唐也明目張膽了。」
傑若癱到椅子上,我們短暫沉默相對。
「講講看,現在心裡想些什麼?」
「可恥。真的可恥。想到要跟你承認我可能無法和瑪麗亞結婚,你……我們……在瑪麗亞診斷出來癌症及乳房切除之後,那樣辛苦地過來,我就覺得可恥。」
「繼續。」
「我是說,一個女人得了癌症,那會是什麼樣的痛?一個女人失去了乳房,就背叛遺棄她,還算個男人嗎?可恥。非常可恥。更渾蛋的是,我還是個醫生,我應該是要照顧別人的。」(待續) 我開始有點為傑若難過起來,感覺到一股衝動在我裡面發酵,保護他不受到自責的怒火灼傷。我想要提醒他,他和瑪麗亞的感情早在她診斷出癌症之前就已經有了問題,但他現在正處在危機的關頭,我擔心,不管我說什麼,他都會當成我是在給他出主意。在這種狀況下,遷怒為他們做決定的人,包括他們的治療師,這種病人我看得太多了。事實上,在我看來,傑若根本就是存心挑唆瑪麗亞,讓她決心斷絕他們的關係。畢竟,她是怎麼會發現那些電子信的呢?他一定是在無意識間跟她透露了什麼,若不然,大可把那些信丟到垃圾桶或刪除掉。
「那麼,艾莉西亞呢?」我問。「你跟她,可以跟我講一些嗎?」
「我認識她有幾個月了。在健身房碰到的。」
「然後呢?」
「每個星期見面兩次,都在白天。」
「啊,可以跟我少講一點嗎?」
有點不知所措,傑若抬起眼睛看著我,注意到了我在笑,也笑了起來。「我知道,我知道……」
「你一定覺得很難啟齒。這兩難還真是既尷尬又痛苦。你來找我幫忙,卻又不願意老實講出來。」
「說『不願意』還算客氣的,我根本就是打死了也不想談。」
「怕會影響到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是的,是因為形象。」
傑若的話我琢磨了一會兒,決定採取一個非正規的策略──我不太在治療過程中用到的。
「傑若,最近我正好在讀馬可‧奧里略(Marcus Aurelius),我想讀一點他的東西給你聽聽,跟我們討論的東西有關。你知道他的作品嗎?」
傑若的眼裡馬上充滿了興致。對這暫停他表示歡迎。「我讀過。我在大學主修過一段時間古典文學,讀過他的《沉思錄》(Meditations),但那以後就沒有再碰過他了。」
我走到書桌,拿起那本奧利略的《沉思錄》,開始翻弄書頁。過去幾天,我一直都在讀這本書,對文章印象深刻,主要是因為和另一個病人安德魯的不尋常互動。在前一個星期的療程中,安德魯對於自己一輩子都耗在沒有意義的工作上備感苦悶,他這樣已經好多次了。身為高薪的廣告主管,他恨透了向身穿加利亞諾(Galliano)晚裝的女人推銷勞斯萊斯轎車那種毫無意義的工作目標。但他覺得別無選擇:肺氣腫很有可能縮短他的工作歲月,支付四個孩子的大學學費、照顧生病的父母,他都需要錢。建議安德魯讀奧里略的《沉思錄》,連我自己都感到訝異,因為我已經多年沒碰這本書,只記得他和安德魯的情形頗有一點類似:馬柯斯‧奧里略也是身不由己,所從事的行業並非出於自己選擇。他想做個哲學家,但卻身為羅馬皇帝的養子,最後被推選為父親的繼承人。因此,無緣於思與學的人生,他大半生都在做他的皇帝,為保護羅馬帝國的邊界而戰。然而,為了維持內心的寧靜,在希臘,奧里略把自己的哲學沉思口述給一個希臘奴隸,逐日記載,僅供皇帝本人過目。
在那個療程之後,我突然想到安德魯很勤勉,毫無疑問,他一定會認真地閱讀奧里略。因此,我也必須馬上讓自己重溫《沉思錄》,上個星期便把大部分的空閒時間,都放在這位西元二世紀羅馬皇帝的身上,品味他力道十足的犀利文字,並為自己準備安德魯的下一個療程──就在看完傑若之後不久。
和傑若會面時,這就是我的心理背景,當他表示希望自己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遠不會改變時,我就不斷說服自己,奧里略的某些理念也有可能對他造成轉化。同一時間,我對自己的一廂情願卻也興起了疑問:我多次注意到,每讀到偉大的人生哲學家時,我總覺得他們跟我正在看診的許多病人大有關係,忍不住會引述某些自己剛讀到的觀念或章節。有的時候有效,但也經常失靈。(待續)傑若一邊待著,有點不耐煩,我則匆匆翻閱著自己劃的重點。「只要幾分鐘,傑若,我保證,這裡確實有些話是對你有價值的。啊,有了:『不久,你將忘記一切,不久,一切都將把你遺忘。』
「還有這一段,正是我心裡想的。」我大聲朗讀出來,傑若閉著眼睛,看得出來很專心。「『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全都只是暫時的──記憶與被憶亦然。等時候到了,你將忘記一切;等時候到了,所有的人也都將忘記你。總要時時記得,不多久,你將一無所是,你將不知所終。』」
「還有這也是:『一轉眼間,一切為人記憶的均將埋葬於永恆的鴻溝。』」
我把書放下。「有沒有切中要害的?」
「『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那一句開頭的一段怎麼說的?」
我打開書,再念一遍:
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全都只是暫時的──記憶與被憶亦然。等時候到了,你將忘記一切;等時候到了,所有的人也都將忘記你。總要時時記得,不多久,你將一無所是,你將不知所終。
「不知道為什麼,但背脊骨感到一陣哆嗦。」傑若說。
賓果!我開心極了。這正是我所期待的。看來這次的中途轉移還真是神來之筆。「傑若,把別的心思都放到一邊,專注到那股涼意上。聽它說些什麼。」
傑若閉上眼睛,像是進入了夢境。經過幾分鐘的沉寂,我又慫恿他。「反芻一下這句話: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
眼睛仍然閉著,傑若緩緩回答:「這一刻,我生平第一次與馬可‧奧里略接觸的記憶清晰有如水晶……那是我在達特茅斯(Dartmouth)大二的時候,約拿但‧霍爾教授的課。他要我針對《沉思錄》的第一部說出感想,我提出一個問題,使他頗感驚訝與興趣,問題是:『馬可‧奧里略心目中有沒有讀者?』據說他根本沒有要把自己的話語讓別人閱讀的意思,又說他的話語所表達的都是他早已經爛熟於胸的東西,既然如此,他又是寫給誰的呢?我還記得,我的問題在班上激起了漫長而興致高昂的討論。」
真是煩人,非常煩人。又來了,傑若存心要把我拖下水,捲入一場有趣卻轉移焦點的討論。他仍然想要美化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但按照過去一年跟他合作的經驗我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好不要去挑戰他,反而應該直接回應他的問題,然後再婉轉地將他引回正題。
「據我所知,根據學者的研究,奧里略會不斷溫習這些章節,主要是把它當成一種日課,強化自己的決心,規範自己的生活。」
傑若點點頭。這是他表示滿意的身體語言,我則繼續說道:「但還是讓我們回到我引述過的段落吧。你說,開頭的那句話讓你深受感動: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
「我有說過我深受感動嗎?或許那時候有吧,但因為某種原因,現在它卻讓我冷了下來。說真的,此時此刻,實話實說,我不明白這怎麼跟我扯得上關係。」
「也許我可以幫你回憶一下整個過程。你瞧,十到十五分鐘之前,你解釋著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對你來說很重要,這才讓我想到,奧里略的文章可能會給你帶來一些啟發。」
「但是怎樣的啟發呢?」
真是氣人!傑若今天似乎特別不開竅──平常他可是靈光得很。我本來考慮就他的抗拒說一些重話,但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相信他一定又會狡辯,結果只會使我們進展得更慢。我繼續慫恿他。「因為你很在乎我對你的印象,所以才叫我再念一遍那個段落開頭的那一句:『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待續)傑若搖頭。「我知道你試著要幫我,但這些高貴的宣言似乎完全搭不上邊,而且十足的蒼白、虛無。沒錯,當然,我們都只不過是一日浮生。當然,萬物不過一瞬。當然,我們都將消失於無形。這一切都再明白不過,有誰能夠否認?但這又有什麼幫助呢?」
「試試看這個,傑若,記住這個句子:『不久,一切都將把你遺忘。』另一方面,想一想你卻把自己那麼在乎的形象寄託在我這顆心上,一顆行將死去、將要凋零、八十一歲蒼老的心上。」
「歐老,我無意冒犯,但是你的論點並不一致……」
我看到傑若的眼裡閃爍火花,期待著一場知性的辯論,他以一副如魚得水的模樣繼續說道:「聽著,我可不是要和你爭。我承認萬物皆在一瞬,不會自命不凡或自以為能長生不死。如同馬可‧奧里略,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前,已有億萬年流逝,在我棄生之後,仍有億萬年前來。但這對我寄希望於一個我敬重的人,那就是你,於陽光之下,在我短暫的有生之年給我一個好的評價又有什麼幫助呢?」
哎唷喂呀!嘗試這個方法實在是大錯特錯。我聽到時間滴答流逝。這一回合的討論把我們的整個療程都消耗掉了,我非得設法搶救一部分我們共處的時間才行。我常教學生,在療程中碰到麻煩時,有一招可以幫忙脫困,而且屢試不爽,那就是「程序阻斷」,也就是停止動作,並開始探索自己與病人之間的關係。我決定接受自己的忠告。
「傑若,我們暫停一下,把焦點轉移到你和我之間的現況上,好嗎?過去的十五分鐘,你覺得怎麼樣?」
「我認為我們表現得好得不得了。這麼多年來,這可是最有趣的一次療程。」
「你和我都享受了一次知性的辯論,但我卻懷疑自己今天對你有什麼助益。我原本指望,這些沉思中的某些篇章可以帶來一點啟發,對你希望你在我心目中有個正面形象的重要性有所幫助,但我此刻認為你是對的,我的這種想法顯然有欠考慮。我建議,我們就此放下,用今天還剩下來的一點時間,處理你所面對的你和瑪麗亞及艾莉西亞的危機。」
「我不同意那是欠考慮。我認為你是對的。只是我的話太多以致思慮不周而已。」
「就算這樣,我們還是回頭來看你和瑪麗亞現在的情況吧。」
「瑪麗亞會怎麼做我不太確定。所有這一切都是今天上午才發生的,等這個療程一結束,她就必須回實驗室去開研究會議。至少她是這樣說的。有的時候,我認為她根本是在找藉口不來談。」
「但談談這個吧:你希望你們兩個之間會怎麼走下去?」
「我不認為這是我能決定的。事情鬧成了這個樣子,現在該叫牌的是她。」
「或許是你不想叫牌。我們來做個動腦實驗:如果現在你必須決定,你希望事情會怎麼走下去?」
「走一步是一步。我也不知道。」
傑若緩緩搖頭,我們無言相對,坐完最後的幾分鐘。
收拾東西時,我慎重其事地說:「我還想抓住這最後的時刻,不妨放在心裡,我的問題是:你連自己想要的是什麼都不知道,這表示什麼?下個療程我們就從這個問題開始。還有傑若,有個想法或許你也可以在這個星期裡好好思考:我有種感覺,一方面,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另一方面,你強烈希望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會改變,這兩者之間有著關聯,或許是一種極為強烈的關聯。」
傑若起身離去時,我又加了幾句:「你現在事情滿多的,我不能保證幫得上忙,但如果你覺得有壓力,打電話給我,我會在這個星期找時間跟你見面。」
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照講,傑若的困擾是可以理解的。他在緊急關頭找上門來,我卻跟他吊書袋,自命不凡,念一個公元二世紀哲學家的玄學給他聽。簡直就是業餘才會犯的毛病!我到底在指望些什麼?單單念馬可‧奧里略的文句就可以神奇地啟發他,快速地改變他嗎?真正重要的是他自己心目中對自己的形象,是他自己的自重,而不是我心目中對他的形象,這一點他會馬上明白嗎?我到底在想些什麼?我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而他呢,離去時一定比來時更加困惑吧。
(本文未完,全文詳見《一日浮生:十個探問生命意義的故事》第十章〈一日浮生〉)
亞隆醫師,我很想跟您談談。讀了您的小說,
《當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心想,不知道
您是否願意見一個碰到了寫作瓶頸的作家同行。
──保羅‧安德魯
想也知道,保羅的電子信無非是要引起我的興趣。他顯然成功了。我這個人,從來不拒絕作家同行。至於寫作瓶頸嘛,託天之幸,我倒是沒碰到過這樣的人,還真想幫他一把看看。十天之後,保羅應約而來。基於某些理由,我以為來者會是一個中年作家,有點輕佻,有點煩惱。殊不知,進我診療室來的竟是一個皺巴巴的老先生,腰彎得彷彿在地板上找東西。看著他經過走道,寸步慢行,心想,我這診療室高居在舊金山近郊的俄羅斯山(Russian Hill)頂,他是怎麼上來的。幾乎連他關節的噼啪作響都聽得見,我趕緊接過他手上沉重破舊的公文包,攙扶著他,帶到他坐的位子。
「感恩,感恩,年輕人,多大年紀啦?」
「八十。」我回他。
「啊──怎麼也八十了。」
「你呢?高壽多少了?」
「八十四。對,沒錯,八十四。我知道,一定嚇著你了。大部分人都猜我三十多歲。」
我端詳著他,好一會兒,彼此的目光鎖住。我被他調皮的眼睛和游移在嘴唇上玩耍的微笑迷住了。一語不發,坐著對望了好一陣子,沉浸在老人情誼特有的那種溫暖中,我把我們想像成同一條船上的旅客,一個寒冷起霧的夜晚,在甲板上聊起來,結果發現我們竟是在同一個社區長大,而且馬上認出了彼此。我們的父母都熬過大蕭條的苦日子,我們見證過迪馬喬(DiMaggio)與泰迪威廉(Ted William)之間的決鬥傳奇,也都記得牛油與汽油配給卡、歐戰勝利日,以及史坦貝克(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和法雷爾(Farrel)的《史塔茲‧勞尼艮》(Studs Lonigan)。我們什麼都一樣,彼此都覺得放心,那就更不在話下了。既然如此,可以開始工作了。
「所以,保羅,我們不妨就用名字互稱吧──」
他點了點頭:「當然。」
「我對你的認識,全都來自你那封短短的電子信,你說,你也是作家,讀過我的尼采小說,現在碰到了寫作瓶頸。」
「是的,但我只想做一次諮商。就一次。我的收入固定,多的付不起。」
「我會盡力而為。那我們就開始吧,盡量有效率一點。說說看你的瓶頸吧。」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談談自己的經歷。」
「那很好呀。」
「我得回到我學校畢業的那段日子。我在普林斯頓念哲學,寫博士論文,談的是尼采的決定論與他的擁護自我轉化互不相容。但我沒辦法完成。我老是讓一些事情搞得分心,譬如說尼采那些很不尋常的書信,特別是寫給朋友及同行作家,像史特林堡(Strinberg)之類的。漸漸地,我對他的哲學完全失去了興趣,反而比較推崇他的藝術成就,我把尼采看作是個詩人,是史上最有力量的聲音,聲音宏亮到連他的理念都為之黯然失色,沒多久,我就沒什麼搞頭了,只好轉系,不弄哲學,去念文學博士。時間就這樣過去,我的研究進行順利,但就是寫不出來。最後,我把自己搞到了一個狀況,那就是一個藝術家唯有透過藝術才能表現自己,於是,我把寫論文的計畫整個放棄,寫起有關尼采的小說來。但寫東西的瓶頸依然,一點都不受我計畫改變的影響,唬嚨不了它,嚇阻也不管用,照樣力量強大,不動如山。就這樣,一點進展都沒有,一直持續到今天。」
我這一驚,非同小可。保羅現在八十四歲。他開始寫論文應該是二十幾歲的時候,六十年前。以前我聽說過有職業學生,以念書為業,但一念六十年?他的人生凍結了六十年?啊,不,但願不是,那不可能的。
「保羅,講一點大學以後的生活吧。」
「沒什麼好講的。當然啦,大學最後確定我逾期了,鐘聲響起,我的學籍遭到註銷。但書都在我的血液裡,我從來沒丟下。在一家州立大學找了一份工作,當圖書管理員,一直幹到退休,那麼多年下來都還試著在寫,沒有結果。就這些啦,我的人生。講完了。」(待續)「再多講一點。你的家庭?生命中有那些人?」
保羅看起來有點不耐煩,噼哩啪啦地把話吐出來:「兄弟姊妹沒半個,婚結兩次離兩次,短命婚姻,但還好短。沒有孩子,感謝上帝。」
事情變得怪怪的,我心裡想。剛開始那麼親切,現在卻好像不想再跟我多談下去了。接下去呢?
我不放棄。「你的計畫是寫有關尼采的小說,在電子信裡還提到,說你讀過我的小說《當尼采哭泣》。這一方面,可以多談談嗎?」
「我不懂你要問的是哪一方面。」
「關於我的小說,你有什麼感覺?」
「一開始有一點慢,但後來有了氣力,儘管用詞精簡,對話自成一格,別有所見,但整體來說,讀來並不引人入勝。」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說,你,你自己,一直拚命想要寫有關尼采的小說,對於我那本小說的出現,你有什麼反應。這件事你應該會有些感觸吧?」
保羅搖著頭,一副連答都懶得答的神氣。無奈之餘,我只好繼續下去。
「說來聽聽,你怎麼會找上我呢?你挑選我做諮商,理由是不是我的小說?」
「啊,管他理由是什麼,我人都已經在這裡了。」
這下子,事情愈來愈詭異,我心裡想。但若要給他有幫助的諮商,就絕對需要多了解他一些。我只好轉而請出「老辦法」,一個屢試不爽又可以帶出一堆材料來的要求:「我需要了解你更多,保羅。就你平常過的日子,只要讓我詳細了解一天二十四小時你是怎麼過的,我相信我們今天就能搞定。就這個星期過去的那幾天吧,隨便挑一天,從你早晨醒來說起。」諮商的時候,我幾乎每次都會提出這個要求,儘管帶出來的都是一些病人各個生活領域的雞毛蒜皮──睡眠啦,夢啦,吃和工作模式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我了解了病人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保羅卻絲毫感覺不到我的探究熱情,就只是輕輕搖頭,像是在抹掉我的要求。「我們要討論的,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許多年來,我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克勞德‧穆勒(Claude Mueller)教授,有過很長的通信。你讀過他的東西嗎?」
「啊,他寫的尼采傳我很熟,非常棒的作品。」
「好,非常好。你這樣想,我格外高興。」保羅一邊說著,一邊把手伸進他的公文包,抽出厚厚一疊的活頁資料夾。「好吧,我把這些通信都帶來了,希望你能看一看。」
「什麼時候?你是說現在?」
「沒錯,我們這次諮商,沒有比這更重要的。」
我看了看我的手錶。「但我們只有這麼一個回合,光讀這些怕就要花掉一、兩個小時,我們還有比這更要的──」
「亞隆醫師,相信我,我清楚自己在要求什麼。開始吧,請。」
我有點不知所措。怎麼辦?他顯然心意已決。我提醒過他,我們的時間有限,他也十分清楚自己只有這麼一次會晤。但話又說回來,保羅或許真有他自己的把握,又或許,他深信不疑這些通信的確可以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材料。是了,是了,我越想越覺得有道理:一定就是這樣。
「保羅,我把你說的整理了一下,你是說,這些通信可以提供一切有關你的必要材料?」
「如果你是想問『是否非讀它不可、不然就沒有用』——那麼,答案是肯定的。」
簡直是反了。一對一對談是我的專業,我的診療室是我的地盤。在這裡,我永遠都自自在在的,但這一次對談總覺得一切都倒過來了,全亂了套。或許我大可不必那麼認真,隨他去便了。畢竟,時間是他的。而我的時間,他可是要付費的。我覺得有點遲疑,但還是勉強接受了,伸手接下他遞過來的手稿。
保羅一邊把厚厚的三孔活頁資料夾交給我,一邊告訴我,通信一共經歷了四十五個年頭,直到二○○二年穆勒教授去世為止。我開始瀏覽,好讓自己進入情況。花在這本活頁夾上的心思還真不少。看來保羅把他們之間的往返,不論是偶發的短便條或是長篇大論的討論書函,從保存、索引到日期,一切都做得齊齊備備了。穆勒教授的信,連結尾的署名都整整齊齊打出來,規規矩矩的老式作風,至於保羅的信,無論是早期複寫紙複印的或後來影印的,結尾都只一個字母P。
保羅朝我點點頭。「請開始吧。」(待續)讀了前面幾封信,發現封封典雅迷人。穆勒博士顯然十分尊重保羅,但卻責備他喜歡玩詞弄字。第一封信裡面他就說:「我看你是在和文字談戀愛,安德魯先生。喜歡和他們翩然起舞。但文字只是符號。構成旋律的是理念。為我們人生打造結構的是理念。」
「我承認我有這種毛病。」在接下來的信裡,保羅駁回去:「我是沒有好好消化和吸收他們,就是喜歡和他們跳舞,這個毛病我還真希望自己永遠都犯。」後來的幾封信,儘管有角色和半個世紀的年齡區隔,他們卻都放棄了正式稱謂「先生」與「教授」,互相稱起名字來:保羅與克勞德。
在另一封信裡,保羅寫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我老是把朋友弄得困惑不已。」所以,以前有朋友。保羅繼續寫到:「從此,我就得永遠擁抱孤獨。我以為別人都和我一樣,對文字的力量有著同樣的熱情,我知道自己錯了,知道自己是在強人所難。所以你不難想像,只要我一走近,大家就一哄而散。」聽起來,這滿重要的,我心裡想。「擁抱孤獨」是神來一筆,為此添了幾分詩意,但我想像得到,一個非常孤獨的老人。
接下來,兩封信之後,我可真是發現了「大驚奇」,有一段文字有可能為這整樁超現實的治療提供了解的鑰匙。保羅寫道:「所以,你明白了吧,克勞德,就我而言,剩下來的,無非就是去尋找一個至為輕靈、至為高貴的心靈,懂得欣賞我的感性,欣賞我對詩的熱愛,一個銳利而又大膽的心靈加入我的對話。克勞德,我的用詞遣字,可有加速了你的脈搏?這舞,我需要一個雙腳輕靈的舞伴。你會賜予我這份榮幸嗎?」
這一了解,無異霹靂。現在,我總算明白保羅堅持要我讀信的原因了。事情再清楚不過,我怎麼可以不讀呢?穆勒走了十二年了,保羅現在四處晃蕩,就是要尋找另一個舞伴!而我的尼采小說,剛好就這樣插了進來!這下好了,我整個人都給弄糊塗了。心想,本來是我約談他的,事實上呢?倒是他在約談我了。一定就是這樣,錯不了。
望著天花板好一陣子,琢磨著要怎麼樣把自己洞燭了他的心機講出來,保羅卻打斷了我的沉思,指著他的手錶強調:「拜託,亞隆醫師,我們的時間在跑耶,請繼續讀下去。」我順他的意,這些信實在精彩,我樂得一頭栽進去。
前十二封信,很明白的就是師生關係。克勞德經常會派功課,譬如:「保羅,我希望你寫篇東西,比較尼采的厭女症與史特林堡的厭女症。」這一類的功課我推斷保羅都交了,但並沒有在信中看見進一步提到,想來他們都是面對面討論了。但漸漸地,那一年過半,師生的角色開始消失。很少再提到功課,有的時候,甚至不太容易分得清誰是老師誰是學生。克勞德拿了幾首自己的詩,希望保羅發表看法。保羅的回應卻沒什麼好話,而是叫克勞德少些理智,多在意內在感情的衝擊。克勞德則剛好相反,批評保羅的詩徒有感情卻不知所云。
隨著每封書信的往返,他們的關係逐漸親密,感情日益深刻。我心想,難不成我手裡的這一握灰燼竟是保羅一生的最愛,甚或唯一的愛。長久以來,保羅或許一直陷在無法自拔的哀傷中。沒錯,沒錯,一定是這樣的。他要我讀這些寫給往者的信,無非就是要告訴我這些。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接著一個的假設在我腦海裡興起,我雖然覺得有趣,但終究沒有一個可以提供我想要的充分解釋。讀得愈多,我的疑問愈滾愈大。保羅來找我的目的究竟何在?他先前說寫作瓶頸是主要的問題,但為什麼現在他一點也沒表現出要探討寫作瓶頸的興趣?他為什麼拒絕透露自己的生活細節?為什麼堅持非要把我們的時間全都花在讀這些許久以前的書信上?我們得理個頭緒出來才行。我下定決心,不把這幾個問題跟保羅弄清楚絕不罷休。(待續)接著,我看到一封回信,把我給拉住了。「保羅,你對純粹經驗的過度推崇走偏走到一個危險的方向去了,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你蘇格拉底的告誡:人生不經檢視,活著也是白活。」
說得好,克勞德!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完全認同你督促保羅檢視他自己的人生。
但在下一封信裡,保羅馬上毫不客氣地反駁:「若要我在活著與檢視之間做個選擇,任何一天我都選擇活著。解釋這種病,我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我勸你最好也跟我學。解釋的趨勢是現代思想的流行病,其主要的帶原體則是今天的治療師:我遇到的精神科醫師,每個都有這種病,而且是會上癮,會傳染的。解釋根本就是一種錯覺,一種妄想,一種建構,一種安慰性的催眠。解釋並不存在。說穿了,不過是懦夫面對絕對存在的無常、冷漠與變遷因恐懼顫慄而採取的一種防衛。」這一段話,我讀之再三,但覺心旌動搖。心裡醞釀的想法,原本已經決定要搬出來的,這一來,也猶豫起來。我知道,保羅接受我邀舞的機會根本就是零。
每當抬起目光,就看到保羅的眼睛緊緊咬住我,我的反應一個也不放過,提醒我繼續讀下去。但到最後,我一看時間只剩下十分鐘,便闔上夾子,取回主導權。
「保羅,我們剩的時間不多了,而我還有幾件事情要跟你討論。我滿不痛快的,因為已經到了要結束的時候,我居然還沒能真正談到你來找我的理由──你的主要問題,你的寫作瓶頸。」
「我可沒說過。」
「但在你給我的電子信裡面,你說……這裡,我列印出來了……」我打開自己的夾子,但還沒等我把它擺出來,保羅已經回了過來:
「我自己寫的我知道:『我很想跟您談談。我讀了您的小說,《當尼采哭泣》,心想,不知道您是否願意見一個碰到了寫作瓶頸的作家同行。』」
我瞧著他,期待一個傻笑,但他卻一本正經。他是說過寫作瓶頸,但並沒有明指那就是他要我幫忙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一個文字陷阱。覺得自己被玩弄了,我大為不爽,反擊回去:「我一貫都是幫助別人解決問題,這是治療師的本分。所以,我會這樣的推斷,誰都想得到。」
「我完全理解。」
「那就對了,讓我們重新開始吧。告訴我,我要怎樣才能幫你?」
「你對那些信有什麼看法?」
「可不可以說得更具體一點?好讓我把要講的東西理個架構出來。」
「隨便什麼看法,對我全都是最有幫助的。」
「好吧。」我打開筆記本翻頁。「你是知道的,我的時間只夠看一小部分,但整個來說,我非常喜歡,裡面滿是第一流的才情與學問。角色的轉移令人印象深刻。開始的時候,你是學生,他是老師。但很顯然的,你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學生,不過幾個月,年輕學生與知名教授就平起平坐通起信來。毫無疑問的,他十分尊重你的看法與判斷,欣賞你的文章,看重你對他作品的批評。想也知道,他花在你身上的時間和精神一定遠遠超過他所能提供給一般學生的。還有,你們的通信既然能夠在你失去學生資格後還延續那麼久,當然,毫無疑問的,你們相互之間的重要性確實非比尋常。」
我注意看著保羅。他一動不動,含淚坐著,狂飲我的每一句話,顯然還渴望更多。終於,終於,我們碰頭了。終於,我給了他一些東西。我為一件對保羅格外重要的事情做了見證。我,而且只有我,證明世間確有一位大人物高度肯定保羅‧安德魯的重要性。但這位大人物去世多年,保羅隨著年歲增加,心理愈趨脆弱,如今再也無法獨自承受這一事實。他需要一個見證人,某個有社會地位的人,而我剛好被他挑中,填補了這個角色。沒錯,我絲毫不懷疑這一點。這種看法散發出強烈的真相氣息。
現在,若把這些看法中的某部分傳達出去,對保羅應屬有利。回顧起來,我透過觀察所得到的了解還不少,但剩下的時間又不到幾分鐘,當從何處開始,我真有點拿不定主意。最後,我決定還是從最顯著的地方著手:「保羅,關於你們的通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和穆勒教授之間既強烈又溫柔的關係,這是一種極深摯的愛。他的過世對你而言,定然難以承受。我猜想,這種失落之痛久久不得平息正是你要尋求諮商的原因。你認為呢?」
保羅沒作聲,只是伸手要拿書信,我回遞給他。他打開公事包,把書信夾子放妥了,拉上拉鍊封口。
「對或不對,保羅?」
「我會來找你諮商,是因為我需要。現在,我已經做了,也得到了我想要的。你做的很有幫助,非常非常有幫助。我別無所求了。謝謝你。」
「保羅,暫請留步。我始終覺得,了解一下自己幫助了患者什麼也很重要。你從我這裡得到了些什麼,可以麻煩你花幾分鐘說明一下嗎?我相信,對這方面做更進一步的釐清,對你將來會有好處,對我以及我未來的客戶也大有助益。」
「歐老,給你留下那麼多的謎團,我很遺憾,但我怕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起身的時候,他幾乎站不穩,我及時抓住他的手肘穩住他。等站穩了,他伸手和我握手,然後,步子輕快,邁出我的診療室。(待續)10 一日浮生
進了我的諮商室,傑若逕自走向自己的位子,意興闌珊,也不招呼我。我呢,也是顧我自己,沒搭理他。
望著窗外雪白羊毛般的成串紫羅蘭,他說:「歐老,我要懺悔。」欲言又止,然後突然掉過頭來面對著我說:「有個女的,艾莉西亞……我提過她的,你還記得嗎?」
「艾莉西亞?當然,瑪麗亞我們倒是談過不少,但艾莉西亞,不記得了,不妨再說來聽聽吧。」
「好吧,艾莉西亞,是另外一個女的啦,事情是這樣的……呃……艾莉西亞以為我要跟她結婚。」
「哇,我這可糊塗了。傑若,從頭說起,把話講明白。」
「好吧,昨天下午,瑪麗亞和我一起,跟你的凱薩琳會面做伴侶療程,事情爆開來了。一開始,瑪麗亞就打開她的皮包,抽出一疊──厚厚一疊──電子信,罪證確鑿,我和艾莉西亞討論過結婚的電子信。所以我今天決定,還是爽快一點的好。我寧願親口告訴你,不希望透過凱薩琳讓你知道,當然啦,如果她已經跟你說了,那就另當別論了。」
我大吃一驚。傑若,一個皮膚科醫師,三十二歲。這一年裡面,我和他不時會晤,密切關注他瑪麗亞之間的感情關係,他們已經同居九個月。儘管口口聲聲說愛她,他卻始終怯於給她一個承諾。「為什麼一定要給?」他不止一次說。「把我這僅有的一生押到這上面?」
到目前為止,我的感覺是治療的進展雖然穩定但很慢。傑若在大學裡主修過哲學,最初,他之所以會找上我,是因為讀過我的哲學小說,確信自己找對了治療師。開始合作的第一個月,他總是堅持透過抽象的哲學討論來做治療。但最近幾個星期以來,我比較少看到他這樣,態度似乎愈來愈認真,愈來愈願意與人分享內心世界。但即使這樣,他最急迫的問題,亦即他和瑪麗亞之間出了問題的感情關係並沒有改變。我明白,兩個人的功課,單治療一個人是沒有效果的,於是我在幾個星期前,建議他和瑪麗亞去看一個傑出的伴侶治療師,凱薩琳‧佛斯特醫師,但沒料到,今天,只要是提到凱薩琳,他開口閉口都是「你的凱薩琳」。
傑若的懺悔該如何回應呢?他和瑪麗亞的危機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他讓兩個女人都以為他要和自己結婚;他對瑪麗亞侵入自己的電子郵件的反應;還有,他口中的我的凱薩琳,以及那底下的胡思亂想。但所有這些都可以暫時擺到一邊。我以為,眼前的首要之務應該放到我們的治療關係上,那才是當務之急。
「傑若,我們回到原點,討論一下你的第一句話,你說你要懺悔的那句話。很明顯地,對於我們的合作,你保留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沒講,而你之所以今天才講
,是因為你以為凱薩琳,我的凱薩琳,會告訴我。」
該死,我實在不該把我的凱薩琳這幾個字搬出來,我知道,那會節外生枝,但還是攔不住,蹦了出來。
「沒錯,我道歉,關於那個凱薩琳的俏皮話,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怎麼來的。」
「是在暗示什麼嗎?」
「不確定。我想,那只是因為你很欣賞她,又把她的能力誇上了天。更何況,她確實是美到不可方物。」
「所以,你就以為凱薩琳和我有什麼了?」
「也不全然是啦。我的意思是說,別的不說,光是年齡就有很大的差距。你說過的,她是你的學生,大約三十年前。我上網搜尋過,知道她嫁給一個心理學家,也是你的學生……所以呢……呃……歐老,為什麼會那樣說,我真的不知道。」(待續)「或許,你心裡是這樣希望的,希望我和你是一丘之貉,跟你一個樣,也搞不倫之戀。」
「可笑。」
「可笑?」
「可笑,但……」傑若自顧自地點了點頭。「可笑,但也可能沒錯。我承認,今天我走進來的時候,就覺得形單影隻,在風中飄搖不定。」
「所以你想有個伴?希望我們狼狽為奸?」
「我想是吧。有道理。沒錯,如果你是精神病那才是有道理。老天爺,這還真是尷尬,你搞得讓我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十歲小孩。」
「我知道這很難堪,傑若,但不要逃避。你用『懺悔』那樣的字眼,我就恨詫異。對你,對我,那代表什麼意思?」
「啊,說的無非是罪惡,說自己做了什麼羞於承認的事吧。不管什麼事,只要是有損於你對我的看法,我都盡量不讓你知道。我是十分尊敬你的……這你是知道的……我非常希望,你對我,能夠維持一個不會改變的……呃……不會改變的形象。」
「什麼樣的形象?你希望歐文‧亞隆怎麼看傑若‧赫爾西?來,我們花一點時間,變個場景出來,讓我好好端詳一下你的形象。」
「什麼啦?我可不會。」傑若又是扮鬼臉又是搖頭,彷彿急著擺脫自己惹來的一身腥。「我們到底在搞什麼名堂?離題太遠了吧,為什麼不談重要的事情──我和艾莉西亞及瑪麗亞的困境呢?」
「那當然重要,馬上就談。但先遷就我一下,繼續討論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夠了,我真的受不了了,這就是你們所謂的『抗拒』吧?」
「說對了。我知道,這感覺起來滿冒險的,但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就告訴過你,每一次諮商都是一次冒險,這一點很重要,你還記得吧?現在正是如此!試試看,冒個險吧。」
傑若閉上眼睛,臉轉向天花板。「好吧,來吧……我看到你在這間諮商室裡面,坐在那邊。」他轉過來,眼睛仍然閉著,臉朝向我的桌子,我諮商室的另一頭。「你正忙著寫東西,因為某些原因,我的形象湧進了你的心裡。你講的是這個意思吧?」
「正確,別停下來。」
「你閉上了眼睛,你在心裡看我的形象,看得很久。」
「很好,繼續。現在,我看的是你的臉,想像一下我在想什麼?」
「你心裡在想,啊,那是傑若,我在看著他……」沉入到幻象之中,他看起來比較放鬆。「沒錯,那是傑若,多好的一個傢伙呀。滿聰明的,又有學問。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人。有深度,有想法。」
「繼續。我還想了些什麼?」
「你在想,『他多麼有品格,多麼正直呀……我所見過最優秀最善良的人……一個值得懷念的人』,就這一類的吧。」
「再講再講,你在我心目中有這樣的形象對你有多重要。」
「超超超級重要。」
「你找我諮商的目的本來是要我幫助你改變,但就我看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才是比較重要的。」
傑若搖頭,有點洩氣。「照今天的發展來看,這還真他媽的難以反駁。」
「沒錯,如果你對我有所保留,就像你和艾莉西亞的感情那樣,那就一定會這樣。」
「了解。說真的,我的行徑之荒唐也明目張膽了。」
傑若癱到椅子上,我們短暫沉默相對。
「講講看,現在心裡想些什麼?」
「可恥。真的可恥。想到要跟你承認我可能無法和瑪麗亞結婚,你……我們……在瑪麗亞診斷出來癌症及乳房切除之後,那樣辛苦地過來,我就覺得可恥。」
「繼續。」
「我是說,一個女人得了癌症,那會是什麼樣的痛?一個女人失去了乳房,就背叛遺棄她,還算個男人嗎?可恥。非常可恥。更渾蛋的是,我還是個醫生,我應該是要照顧別人的。」(待續) 我開始有點為傑若難過起來,感覺到一股衝動在我裡面發酵,保護他不受到自責的怒火灼傷。我想要提醒他,他和瑪麗亞的感情早在她診斷出癌症之前就已經有了問題,但他現在正處在危機的關頭,我擔心,不管我說什麼,他都會當成我是在給他出主意。在這種狀況下,遷怒為他們做決定的人,包括他們的治療師,這種病人我看得太多了。事實上,在我看來,傑若根本就是存心挑唆瑪麗亞,讓她決心斷絕他們的關係。畢竟,她是怎麼會發現那些電子信的呢?他一定是在無意識間跟她透露了什麼,若不然,大可把那些信丟到垃圾桶或刪除掉。
「那麼,艾莉西亞呢?」我問。「你跟她,可以跟我講一些嗎?」
「我認識她有幾個月了。在健身房碰到的。」
「然後呢?」
「每個星期見面兩次,都在白天。」
「啊,可以跟我少講一點嗎?」
有點不知所措,傑若抬起眼睛看著我,注意到了我在笑,也笑了起來。「我知道,我知道……」
「你一定覺得很難啟齒。這兩難還真是既尷尬又痛苦。你來找我幫忙,卻又不願意老實講出來。」
「說『不願意』還算客氣的,我根本就是打死了也不想談。」
「怕會影響到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是的,是因為形象。」
傑若的話我琢磨了一會兒,決定採取一個非正規的策略──我不太在治療過程中用到的。
「傑若,最近我正好在讀馬可‧奧里略(Marcus Aurelius),我想讀一點他的東西給你聽聽,跟我們討論的東西有關。你知道他的作品嗎?」
傑若的眼裡馬上充滿了興致。對這暫停他表示歡迎。「我讀過。我在大學主修過一段時間古典文學,讀過他的《沉思錄》(Meditations),但那以後就沒有再碰過他了。」
我走到書桌,拿起那本奧利略的《沉思錄》,開始翻弄書頁。過去幾天,我一直都在讀這本書,對文章印象深刻,主要是因為和另一個病人安德魯的不尋常互動。在前一個星期的療程中,安德魯對於自己一輩子都耗在沒有意義的工作上備感苦悶,他這樣已經好多次了。身為高薪的廣告主管,他恨透了向身穿加利亞諾(Galliano)晚裝的女人推銷勞斯萊斯轎車那種毫無意義的工作目標。但他覺得別無選擇:肺氣腫很有可能縮短他的工作歲月,支付四個孩子的大學學費、照顧生病的父母,他都需要錢。建議安德魯讀奧里略的《沉思錄》,連我自己都感到訝異,因為我已經多年沒碰這本書,只記得他和安德魯的情形頗有一點類似:馬柯斯‧奧里略也是身不由己,所從事的行業並非出於自己選擇。他想做個哲學家,但卻身為羅馬皇帝的養子,最後被推選為父親的繼承人。因此,無緣於思與學的人生,他大半生都在做他的皇帝,為保護羅馬帝國的邊界而戰。然而,為了維持內心的寧靜,在希臘,奧里略把自己的哲學沉思口述給一個希臘奴隸,逐日記載,僅供皇帝本人過目。
在那個療程之後,我突然想到安德魯很勤勉,毫無疑問,他一定會認真地閱讀奧里略。因此,我也必須馬上讓自己重溫《沉思錄》,上個星期便把大部分的空閒時間,都放在這位西元二世紀羅馬皇帝的身上,品味他力道十足的犀利文字,並為自己準備安德魯的下一個療程──就在看完傑若之後不久。
和傑若會面時,這就是我的心理背景,當他表示希望自己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遠不會改變時,我就不斷說服自己,奧里略的某些理念也有可能對他造成轉化。同一時間,我對自己的一廂情願卻也興起了疑問:我多次注意到,每讀到偉大的人生哲學家時,我總覺得他們跟我正在看診的許多病人大有關係,忍不住會引述某些自己剛讀到的觀念或章節。有的時候有效,但也經常失靈。(待續)傑若一邊待著,有點不耐煩,我則匆匆翻閱著自己劃的重點。「只要幾分鐘,傑若,我保證,這裡確實有些話是對你有價值的。啊,有了:『不久,你將忘記一切,不久,一切都將把你遺忘。』
「還有這一段,正是我心裡想的。」我大聲朗讀出來,傑若閉著眼睛,看得出來很專心。「『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全都只是暫時的──記憶與被憶亦然。等時候到了,你將忘記一切;等時候到了,所有的人也都將忘記你。總要時時記得,不多久,你將一無所是,你將不知所終。』」
「還有這也是:『一轉眼間,一切為人記憶的均將埋葬於永恆的鴻溝。』」
我把書放下。「有沒有切中要害的?」
「『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那一句開頭的一段怎麼說的?」
我打開書,再念一遍:
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全都只是暫時的──記憶與被憶亦然。等時候到了,你將忘記一切;等時候到了,所有的人也都將忘記你。總要時時記得,不多久,你將一無所是,你將不知所終。
「不知道為什麼,但背脊骨感到一陣哆嗦。」傑若說。
賓果!我開心極了。這正是我所期待的。看來這次的中途轉移還真是神來之筆。「傑若,把別的心思都放到一邊,專注到那股涼意上。聽它說些什麼。」
傑若閉上眼睛,像是進入了夢境。經過幾分鐘的沉寂,我又慫恿他。「反芻一下這句話: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
眼睛仍然閉著,傑若緩緩回答:「這一刻,我生平第一次與馬可‧奧里略接觸的記憶清晰有如水晶……那是我在達特茅斯(Dartmouth)大二的時候,約拿但‧霍爾教授的課。他要我針對《沉思錄》的第一部說出感想,我提出一個問題,使他頗感驚訝與興趣,問題是:『馬可‧奧里略心目中有沒有讀者?』據說他根本沒有要把自己的話語讓別人閱讀的意思,又說他的話語所表達的都是他早已經爛熟於胸的東西,既然如此,他又是寫給誰的呢?我還記得,我的問題在班上激起了漫長而興致高昂的討論。」
真是煩人,非常煩人。又來了,傑若存心要把我拖下水,捲入一場有趣卻轉移焦點的討論。他仍然想要美化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但按照過去一年跟他合作的經驗我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好不要去挑戰他,反而應該直接回應他的問題,然後再婉轉地將他引回正題。
「據我所知,根據學者的研究,奧里略會不斷溫習這些章節,主要是把它當成一種日課,強化自己的決心,規範自己的生活。」
傑若點點頭。這是他表示滿意的身體語言,我則繼續說道:「但還是讓我們回到我引述過的段落吧。你說,開頭的那句話讓你深受感動: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
「我有說過我深受感動嗎?或許那時候有吧,但因為某種原因,現在它卻讓我冷了下來。說真的,此時此刻,實話實說,我不明白這怎麼跟我扯得上關係。」
「也許我可以幫你回憶一下整個過程。你瞧,十到十五分鐘之前,你解釋著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對你來說很重要,這才讓我想到,奧里略的文章可能會給你帶來一些啟發。」
「但是怎樣的啟發呢?」
真是氣人!傑若今天似乎特別不開竅──平常他可是靈光得很。我本來考慮就他的抗拒說一些重話,但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相信他一定又會狡辯,結果只會使我們進展得更慢。我繼續慫恿他。「因為你很在乎我對你的印象,所以才叫我再念一遍那個段落開頭的那一句:『我們全都是一日浮生;記人者與被記者都是。』」(待續)傑若搖頭。「我知道你試著要幫我,但這些高貴的宣言似乎完全搭不上邊,而且十足的蒼白、虛無。沒錯,當然,我們都只不過是一日浮生。當然,萬物不過一瞬。當然,我們都將消失於無形。這一切都再明白不過,有誰能夠否認?但這又有什麼幫助呢?」
「試試看這個,傑若,記住這個句子:『不久,一切都將把你遺忘。』另一方面,想一想你卻把自己那麼在乎的形象寄託在我這顆心上,一顆行將死去、將要凋零、八十一歲蒼老的心上。」
「歐老,我無意冒犯,但是你的論點並不一致……」
我看到傑若的眼裡閃爍火花,期待著一場知性的辯論,他以一副如魚得水的模樣繼續說道:「聽著,我可不是要和你爭。我承認萬物皆在一瞬,不會自命不凡或自以為能長生不死。如同馬可‧奧里略,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前,已有億萬年流逝,在我棄生之後,仍有億萬年前來。但這對我寄希望於一個我敬重的人,那就是你,於陽光之下,在我短暫的有生之年給我一個好的評價又有什麼幫助呢?」
哎唷喂呀!嘗試這個方法實在是大錯特錯。我聽到時間滴答流逝。這一回合的討論把我們的整個療程都消耗掉了,我非得設法搶救一部分我們共處的時間才行。我常教學生,在療程中碰到麻煩時,有一招可以幫忙脫困,而且屢試不爽,那就是「程序阻斷」,也就是停止動作,並開始探索自己與病人之間的關係。我決定接受自己的忠告。
「傑若,我們暫停一下,把焦點轉移到你和我之間的現況上,好嗎?過去的十五分鐘,你覺得怎麼樣?」
「我認為我們表現得好得不得了。這麼多年來,這可是最有趣的一次療程。」
「你和我都享受了一次知性的辯論,但我卻懷疑自己今天對你有什麼助益。我原本指望,這些沉思中的某些篇章可以帶來一點啟發,對你希望你在我心目中有個正面形象的重要性有所幫助,但我此刻認為你是對的,我的這種想法顯然有欠考慮。我建議,我們就此放下,用今天還剩下來的一點時間,處理你所面對的你和瑪麗亞及艾莉西亞的危機。」
「我不同意那是欠考慮。我認為你是對的。只是我的話太多以致思慮不周而已。」
「就算這樣,我們還是回頭來看你和瑪麗亞現在的情況吧。」
「瑪麗亞會怎麼做我不太確定。所有這一切都是今天上午才發生的,等這個療程一結束,她就必須回實驗室去開研究會議。至少她是這樣說的。有的時候,我認為她根本是在找藉口不來談。」
「但談談這個吧:你希望你們兩個之間會怎麼走下去?」
「我不認為這是我能決定的。事情鬧成了這個樣子,現在該叫牌的是她。」
「或許是你不想叫牌。我們來做個動腦實驗:如果現在你必須決定,你希望事情會怎麼走下去?」
「走一步是一步。我也不知道。」
傑若緩緩搖頭,我們無言相對,坐完最後的幾分鐘。
收拾東西時,我慎重其事地說:「我還想抓住這最後的時刻,不妨放在心裡,我的問題是:你連自己想要的是什麼都不知道,這表示什麼?下個療程我們就從這個問題開始。還有傑若,有個想法或許你也可以在這個星期裡好好思考:我有種感覺,一方面,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另一方面,你強烈希望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會改變,這兩者之間有著關聯,或許是一種極為強烈的關聯。」
傑若起身離去時,我又加了幾句:「你現在事情滿多的,我不能保證幫得上忙,但如果你覺得有壓力,打電話給我,我會在這個星期找時間跟你見面。」
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照講,傑若的困擾是可以理解的。他在緊急關頭找上門來,我卻跟他吊書袋,自命不凡,念一個公元二世紀哲學家的玄學給他聽。簡直就是業餘才會犯的毛病!我到底在指望些什麼?單單念馬可‧奧里略的文句就可以神奇地啟發他,快速地改變他嗎?真正重要的是他自己心目中對自己的形象,是他自己的自重,而不是我心目中對他的形象,這一點他會馬上明白嗎?我到底在想些什麼?我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而他呢,離去時一定比來時更加困惑吧。
(本文未完,全文詳見《一日浮生:十個探問生命意義的故事》第十章〈一日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