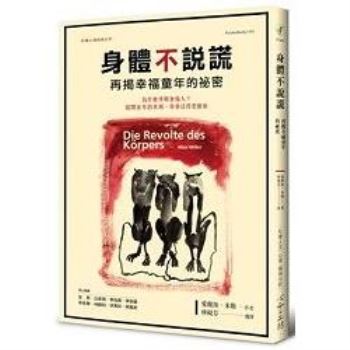1) 「孝敬父母」的戒律,為何無法讓人真正愛自己?:「知情見證者」之必要
當孩子出生時,他們最需要從父母得到的是愛──我指的是慈愛、關注、照顧、和藹以及交流的意願等。如果這些需求被滿足了,孩子的身體將會得到關愛照顧的美好記憶,日後長大成人之後也會將同樣形式的愛繼續傳遞給下一代。但如果這些需求沒有被滿足,那麼他將一輩子渴望能滿足最初始(也是最重要)的需求。在日後的人生中,這種渴望將會轉嫁給其他人。比較起來,越常被剝奪愛,或是越常被以「教養」之名而遭受否定或虐待的孩子,他們在成年之後就越離不開父母(或替代父母的其他人),他們期待獲得以前父母在關鍵性的時刻未按其所需給予的一切。這是身體的正常反應。身體知道它缺少了什麼,它忘不掉那些匱乏。匱乏或空洞一直都在那裡,等待被填滿。
當年紀越大,就越難從別人身上獲得父母拒絕給予的愛。但身體的期待卻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停止──而且完全相反!期望只會轉嫁給其他人,通常的對象就是自己的兒孫。離開這種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能對這種機制有所自覺,並藉由消解「壓抑與否認」的過程,竭盡所能地認清我們的童年真相。我們能在自己身上創造出可以滿足這些需求的人,給予從我們出生以來或更早以前就等著填滿的需求。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給自己未曾從父母獲得的重視、尊重、對自身情緒的理解、必要的保護,以及無條件的愛。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們需要一個特殊的經驗:去愛童年的自己。沒有這種愛的經驗,我們就不會知道愛是什麼。如果我們想藉由心理治療的幫助學會這種經驗,就需要一位可以給予保護、尊重、同理心與陪伴的治療師,這位治療師能接受我們的模樣,能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為什麼會變成現在的樣子。這種基本經驗是不可或缺的,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為曾經受忽視的孩子披上父母的角色。
我們不需要想為我們「做些方案」的教育家,也不需要在面對個案的童年創傷時力求保持中立並將分析對象的敘說詮釋為幻想的精神分析師。不,我們需要的正是完全相反的人:也就是一個偏心的(parteiischen)陪伴者,一個當我們的情緒在他與我們面前一步一步地揭露童年曾承受過什麼,以及過去必須忍受些什麼時,這位陪伴者可以陪我們一起經驗驚懼與憤怒;當我們還是小孩,身心在為生命奮戰時,一直是孤孤單單的,生命長年累月地處在持續的危險之中。
我們需要這樣的一個陪伴者──我稱之為「知情見證者」(Wissenden Zeugen)──如果我們得到這種陪伴,從此刻開始去幫助我們心中的那個孩子,去理解他的身體語言、去探究他的需求,而不是像我們的父母一直以來忽視這些需求。
我在這裡描述的內容絕對是實際可行的。人們可以在這種偏心的、不中立(nicht nuetralen)的治療陪伴下找到自己的真相。人們可以在這樣的過程中解除自己的病症、擺脫抑鬱、重獲人生樂趣、脫離筋疲力竭的狀態,而且一旦不再需要將精力耗費在壓抑自身的真相後,他的能量就會滋長了。重點在於,每當我們壓抑自己的強烈情緒,並且企圖輕視、忽視身體的記憶時,抑鬱特有的疲倦感就會來臨。
為什麼比較少發生這種正面進展的機會呢?為什麼大多數人(包括所謂的「專家」)寧願相信藥物的力量,而不是讓儲存在身體的所知去導引呢?身體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們需要什麼、被拒絕了什麼、承受不了什麼、對什麼會有過敏反應等。但多數人卻寧可尋求藥物、毒品或酒精等的協助,這些物品只會讓通往真相的道路更加受阻。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是因為知道真相後會痛苦?痛苦是必然的。但這種痛苦只是暫時的。在適當的治療陪伴下,可以忍受得了。我相信最主要的問題就出在缺乏這種專業的陪伴。在我稱為「助人的專業者」(helfenden berufe)的人士之中,多數人似乎都受到自身道德系統的強烈阻礙,使他們無法幫助曾受虐的孩子,以及看清早年的傷害所帶來的後果。規定人們要敬愛自己父母的第四誡,它的威力完全壓制了這些專業人士,第四誡說:「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很明顯,這條戒律妨礙了早年傷痕的療癒。截至目前為止,該事實都未曾被公開發言和探討,這點並不奇怪。這條戒律的影響範圍與力量是難以衡量的,因為幼小的孩童自然地會依附他們的父母,所以一再助長了第四誡。就連最偉大的哲學家與作家都不敢抨擊這條戒律。尼采 雖然犀利地批判了基督教的道德規範,但他無法將批判擴及自己的家庭。當任何一個曾受虐的成年人企圖違抗父母的行為時,心中都暗藏著那個小小孩對父母會施加懲罰的恐懼。不過這種恐懼只會潛伏在無意識裡。一旦有意識地經驗到了,恐懼就會隨著時間漸漸消散。
支持第四誡的道德規範與我們童年的期望互相結合,導致絕大多數治療師會對尋求幫助的病患,提出和他們接受的教養同樣一套規範。許多這類治療師本身就和父母有數不清的牽纏。他們稱這種擺脫不了的牽纏是「愛」,並試著將這種形式的「愛」提供給他人作為解決之道。他們傳播寬恕是癒療的途徑,顯然並不明白這條路是個圈套,他們自己就身陷其中。寬恕從來沒有療癒的效果(Alice Miller, 1990; 2003)
很特別的一點是,我們幾千年來都與這條戒律生活在一起,幾乎無人質疑它,只因為它支撐了一項生理現實:所有孩子,無論受過虐待與否,都一直愛著他們的父母。只有成年人,才有辦法選擇。但我們的行為卻表現得猶如仍是小孩,不可以對自己父母的戒律提出質疑。然而,身為有意識的成年人,我們擁有質疑的權力,即便我們知道這些對兒時的質疑可能會讓父母非常震驚。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導論「身體與道德」,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26-31。)
2) 直視「我是為你好!」的施虐痕跡:受傷的內在小孩,身體需要傾聽。
在我所有的著作裡,我試著用不同的方式以及脈絡,闡述我所謂的「黑色教育」(Schwarzen Pädagogik)童年經歷會在日後如何限制我們的活力,並大幅損害甚或扼殺我們究竟是誰、我們有什麼感覺、我們需要什麼感覺等。「黑色教育」的養育之道會教養出適應良好的個體,只會信任他們被強迫戴上的面具,因為他們童年一直生活在害怕被處罰的長期恐懼之中。這種教育方式的最高原則是:「我這樣教你,是為了你好,即便我毆打你或用言語折磨、傷害你,都只會對你有好處。」
匈牙利作家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惹‧卡爾特斯在他著名的小說《非關命運》中,提到了他進入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景況。當時他還只是一個年僅十五歲的男孩,他鉅細靡遺地告訴讀者,他如何試著將在集中營遇見很多費解而殘忍的事情解釋為正面的、對他有好處。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他無法在死亡的恐懼下倖存下來。
或許每個受虐兒為了求生,都必須接受這種態度。這些孩子重新詮釋他們的感知,在局外觀察者一致認定是明顯的犯罪行為之中看見「善行」。孩子沒有選擇。如果沒有「協助見證者」(Helfenden Zeuge)在一旁扭轉情況或幫忙揭露施暴者,受虐兒就必須要去壓抑真正的感覺。日後他們長大成人之後,如果有幸遇到了「知情見證者」,他們才有了選擇。他們可以進入真相,不用再去同情、「理解」施暴者,停止試圖去感覺他們無力支撐的、分離的情緒,並可以徹底地揭露曾被施暴的情況。這一步意味著身體卸下了重負。長大成人的當事者不用一再地強迫憶起孩提時的悲慘歷史。一旦這個成年人願意認清自己的所有真相,他的身體就會感覺被理解、被尊重與被保護。
我稱這種暴力形式的「教養」(Erziehung )是虐待(Mißhandlung),不只是因為孩子被否定了他身為人類所應得的尊嚴與尊重的權力,同時也建立起一種極權體制,使孩子完全無法感知所遭遇到的屈辱、貶抑與蔑視,更遑論起而反抗了。這種童年的模式必然會被受害者複製了,用在他們的伴侶與孩子身上,用在工作場域與政治領域裡,用在任何恐懼和焦慮滋生之處,不讓極度缺乏安全感的孩童得到外部力量的協助。獨裁者就是透過這種方式生的;這些人在內心深處蔑視任何人,他們在孩童時期不曾受到尊重,日後便試圖用強大的權力迫取尊敬。
我們可以在政治領域裡觀察到,對權力與認同的飢渴是從未止息。那是永無饜足,也不可能全然被滿足的。人們擁有的權力越大,就越驅使在強迫性的重複驅力下行動,而他們企圖逃離的舊有無力感會再度出現:在地堡裡的希特勒、在自己偏執狂的恐懼之中的史達林、後來被人民反對的毛澤東、被放逐的拿破崙、在監獄裡的米洛塞維奇,以及躲在地洞裡權力不再的海珊。
是什麼驅使這些人這般濫用他們獲得的權力,導致他們最後傾覆在無力感之中呢?我認為是他們的身體。他們的身體清楚知道所有在童年時期的無力感;他們將這種無力感鎖進了自己的細胞裡,他們想驅使這種無力感的「擁有者」被人看見。然而,這些獨裁者全都非常害怕自己童年的現實,他們寧願毀掉整個民族、讓幾百萬人死去,也不願去感覺真相。
雖然我覺得研究獨裁者的生平非常據有說服力,但在這本書裡我不會繼續關注這些獨裁者的動機。我要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同樣接受黑色教育長大,但不覺得需要獲取無窮權力的人或變成獨裁者。相較之下,他們並未將壓抑的怒氣與憤恨施加於他人身上,而是毀滅性地轉向自己。他們生了病、罹患各種症狀,並且很早辭世。這些人當中最具天分的,會成為作家或藝術家。他們雖然能在文學或藝術上呈現出他們的真相,但呈現的永遠只是個人人生的分裂部分。這種分裂則讓他們用病痛付出了代價。我將在本書的第一部提出這類悲劇性人生的案例。
聖地牙哥的一個研究團隊,曾在一九九0年代針對平均年齡五十七歲的一萬七千人,詢問他們的童年概況以及一生當中有哪些疾病紀錄。結果顯示童年曾受虐者,比童年未受虐、沒有以「為了他們好」的理由而被責打的人,日後罹患重症多了數倍。
後者在日後的人生中不會抱怨病痛的問題。這篇研究短文的標題是〈如何點金成石」〉(Wie man aus Gold Blei macht)。作者把這篇文章寄給我,他對這項發現的評論是:結果一目了然、極具說服力,但同時卻沒人看見、被人掩蓋了。
為什麼被人掩蓋了呢?因為公布結果時不可能不譴責施虐的父母。我們的社會依然禁止譴責父母,事實上如今反而更嚴重了。這是由於專家們越來越力挺的觀點,是將成年人心靈上的苦痛歸咎於基因遺傳,而不是來自童年明確的傷害、被父母排斥。就連七0年代有關思覺失調患者童年的研究,除了發表在專業雜誌以外,也不被大眾所知。深信基因論者依然是勝利的一方。
英國廣受重視的臨床心理學家奧利佛‧詹姆斯在《他們毀了你》(They F*** You Up)一書裡,談的就是這種觀點。雖然這本出版於二00三年的著作,留下了矛盾的印象(因為作者對於自己理解的結論感到恐懼,甚至明確地警告不要把孩子的苦痛認為是父母的責任),但該書還是利用很多研究結果與文獻很有說服力地證明了,除了遺傳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在心理疾病的發展上其實並未扮演什麼重要角色。
因此,很多當今的心理治療很小心地迴避童年這個議題(Alice Miller, 2001)。的確,在一開始會鼓勵病患表達出他們的強烈情緒。但隨著情緒浮現的往往是被壓抑的童年記憶,也就是遭受虐待、剝削、羞辱與傷害的記憶;這些事情對心理治療師來說,常常都超過了他們的能力負荷。如果治療師沒有親自走過這條路的話,並無法應付這一切。曾走過這條路的治療師並不多見。所以大部分的治療師給個案的建議依然是黑色教育的老調重彈,也就是最初導致他們生病的同一套道德規範。
身體根本不懂這種道德規範;第四誡對身體來說毫無意義,身體也不像我們的心智會被言語蒙蔽。身體是真相的守護者,因為它背負著我們一輩子的經歷,並負責讓我們能和我們有機體的真相生活在一起。透過病症迫使我們讓真相也能進入意識之中,藉此讓我們能和那個曾經被忽視、羞辱,而一直在我們心中的孩子和諧地溝通。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導論「身體與道德」,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33-40。)
3) 席勒:書寫反抗權威的偉大劇作家vs.受軍事化教養折磨的兒子。
席勒一直都因身體不同器官的嚴重痙攣所苦。四十歲時他染上重病,以致他不斷地與死神拔河。還伴隨有精神失常的症狀,致使他在四十六歲時與世長辭。
對我而言,席勒的這種嚴重痙攣絕對可以歸咎於他童年時期頻繁的體罰以及青年時的嚴苛紀律。確切地說,他的囚禁狀態早在進入軍校前,在他父親身邊時就已經開始了。他的父親在席勒童年時系統化地克制快樂的感覺,他父親同時也如此對待自己,並稱之為自律。例如,規定孩子一旦在用餐時感到愉悅,就必須立刻停止進食並離開餐桌。席勒的父親也會這麼做。或許席勒父親是一種特例,他採取的古怪模式,壓抑了所有我們可能稱為「生活品質」的天性。但軍校制度在當時卻是廣泛被使用的,而且被視為普魯士的嚴格教養。很少有人會去反思這種教養的後果。
這些軍事學校所採取的嚴酷監視系統,會讓人聯想到某些與納粹集中營相關的描述。當然集中營裡由國家組織起來的虐待行徑,比起軍校絕對更加歹毒與殘忍,不過集中營和之前幾百年盛行的教育體制有相同的根源(Alice Miller, 1980)。這種計畫性的殘忍行為,無論是發令者還是執行者,他們小時候都曾經歷過責打與其他各式各樣施加於其身的羞辱方式。他們完全學會了將來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不帶罪惡感也不加反省地施加在臣服於他們力量之下的其他人身上,例如孩童或囚犯。席勒沒有把自己曾承受過的恐怖統治報復在他人身上。不過,他的身體終其一生都承受著童年必須忍耐的殘暴行徑帶來的後果。
當然,席勒並非特例。孩提時代上過這種學校的人有數百萬,如果不想受到重罰或甚至被奪去性命,他們就必須學習沉默地服從權威的力量。這種經驗使他們對第四誡肅然起敬,並嚴厲叮囑下一代也絕對不得質疑權威。因此即使到了今天,他們的子子孫孫依舊堅信責打不會帶來任何傷害,這也就見怪不怪了。
然而,席勒就這方面而言卻是個例外。從《強盜》到《威廉.退爾》等,他所有的作品都不斷地反抗權威施行的盲目暴力,經由他不凡的文筆在許多人心中播下希望的種子,期許這種抗爭有朝一日能勝利。不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席勒不知道的是,他反抗不合理的權威命令,能量是來自於他身體儲存的早年經歷。他為父親那令人費解又驚恐的權力執行模式所苦,致使他開始寫作,但他不可能察覺寫作欲望之下的動機。他只想寫出優美而偉大的文學作品。
他利用歷史人物試圖說出真相,而他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只是有關父親帶給他的苦痛,即便到了他早逝的那一天,他對這所有的真相都隻字未提。這對他與社會來說依舊是個祕密,我們的社會幾百年來都相當讚賞席勒,許多戲迷和讀者視他為典範,因為他在作品中為了自由與真相奮鬥。不過真相僅止於社會可以接受的真相。
如果有人對席勒說:「你不需要尊敬你的父親。對於曾經那樣傷害過你的人,並不值得你的愛或尊敬,即便他們是你的父母亦然。為了這種孝順的奉獻,你已經用你身體上極至的苦痛付出了代價。只要你不再遵從第四誡,你就有機會解放自己。」如果聽到這番話,勇敢的席勒將會多麼震驚啊!他又會怎麼回應呢?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第一部「訴說與遮掩」,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61
4) 對母親,我能不恨嗎?寬恕無須勉強,獲知真相才是通往長大成人之路。
能夠保護我們不會受到重複驅力侵害的,只有承認真相―─承認全部的真相以及它的所有意涵。只有當我們盡可能地了解父母對我們做過什麼,我們才不會有重複那些惡行的危險;否則,我們會自動地重複父母的行為,並且極力反抗一種想法:當我們長大成人且想要平靜地建立屬於自己的人生時,我們就能夠―─且必須─―解開童年與施虐父母的連結。童年的迷惘起因於我們從前努力要去理解虐待,並由虐待中推論出意義。但我們必須放下這種迷惘。身為成年人,我們可以停止迷惘;也可以學會了解在心理治療時,道德會如何妨礙傷口的復原。
下面的例子可以具體地說明覺察是如何發生的。有一位心灰意冷的年輕女子,她認為自己無論在工作或兩性關係上都是個失敗者,她寫道:
我母親越是對我說,我是個微不足道的人、我什麼也做不成,我就越會四處碰壁。我並不想恨我的母親,我希望與她和平相處,想原諒她,讓我最後能夠擺脫我的恨意。但我卻辦不到。在恨之中我覺得被她所傷,猶如她也恨我一樣不過這是不可能的。我究竟做錯了什麼呢?我知道如果我沒辦法原諒她,我將會很痛苦。我的心理治療師告訴我,如果我和父母對抗,這就宛如我在對抗自己一樣。我當然知道如果無法發自內心深處原諒的話,就不是真正的原諒。我覺得非常困惑,因為有些時候我可以原諒父母,並且感覺我同情他們。但一想到他們曾對我做過的事,我就會突然生氣,然後完全不想看到他們。我其實想過我自己的生活,平靜下來,不要一直想過去他們是怎麼打我、羞辱我、以及那些幾乎算是酷刑的虐待了。
這女人相信,當她認真看待自己的記憶並且忠於自己的身體時,就是在與父母對抗,同時也等於對抗自己。這是心理治療師告訴她的。但這種說法的後果卻是,這個女人完全無法區分她自己的生活以及父母的生活,她完全沒有自我意識,只能將自己理解為父母的一部分。心理治療師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呢?我不知道。但我認為在這樣的陳述中可以感覺到這位心理治療師對自己父母的恐懼,而個案則被這種恐懼與迷惘感染了。結果是她不敢揭開自己的童年故事,讓自己的身體能和真相生活在一起。
在另外一個案例中,一個非常聰明的女人寫道,她不想對自己的父母做出一
概而論的評價,而是要把事情分開來看。因為無論她小時候被打還是被性侵,她還是與父母一起度過了一些美好時光。她的心理治療師肯定她應該去權衡美好與不好的時光,而且身為成年人必須了解不可能有完美的父母,所有父母都會犯錯。然而重點並不在此。重點是現在已然成年的這位女子必須發展出對那個小女孩的同理心,沒有人看見那個小女孩的苦痛,她被求取自身利益的父母利用了,多虧了她洋溢的才華,她可以完美地滿足父母的利益。如果她現在已經能去感覺那個小女孩的苦痛,並且去陪伴內在小孩,那麼她就不應讓美好的時光與不好的時光互相抵銷。這麼一來,她又會披上那個小女孩的角色,這個小女孩想去滿足父母的心願:愛他們、原諒他們、記住美好時光等。
這個孩子不斷地嘗試這麼做,希望能理解她遭遇到的那些來自於父母的自相矛盾的訊息及行為。但這種內在的「工作」只會更強化她的困惑。這個孩子不可能理解她的母親也身處在一個內心的防空洞裡,建築著對抗自己感覺的防禦工事,以至於沒有任何理解孩子需求的感受力。她應該根據自己的感覺來行動,這些感覺永遠像所有情緒一樣是主觀的:「在我小時候是什麼使我痛苦的呢?什麼是我以前完全不能去感覺的呢?」
問這些問題,並不是要一概而論地批判父母,而是為了要找出那個受苦、說不出話的孩子的觀點,以及放下在我看來是破壞性的依附關係。誠如我之前所說的,這種依附的組成是感激、同情、否認、渴望、粉飾,以及無數始終無法圓滿而且注定無法圓滿的期望。對曾忍受過的殘暴行徑表達出寬容的態度,並不會打開通往長大成人的道路。能打開那條路的是獲知自己的真相,以及滋長出對那個受虐兒的同理心。看清虐待如何阻礙了成年人的整個人生,以及摧毀了多少可能性,同時又有多少不幸被不經意地傳給了下一代。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第二部「心理治療中的傳統道德與身體的知識」,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181-184。)
5) 親子間的真正溝通:站在孩子這邊,看見童年真相。(已重新下標)
同樣讓心理治療師感到棘手的是治療過動兒童的症狀。如果這些孩子的情況
被視為與遺傳有關,或是應該加以矯正的壞習慣,這些孩子要怎麼融入家庭呢?
而所有真正的病因都將成為祕密?但如果我們準備好去看清這些情緒其實有現
實的基礎,反映了他們缺乏照料、遭受虐待,或尤其是缺乏情緒滋養(nährender
Kommunikation),我們眼中就不會再看到無意義地到處吵鬧的孩子,而是承受著痛苦的孩子,是不能知道受苦之因的孩子。如果我們能接受這些,就能幫助自己與他們。也許我們(和他們)便不會那麼害怕情緒、痛楚、恐懼與憤怒,而是理解我們的父母究竟對我們做過什麼。
多數心理治療師支持的(道德)義務,是無論如何都不對父母追究責任的態
度,導致了對疾病之因不自覺的漠視,同時也影響了治療疾病的機會。現代的大腦科學家在幾年前便已知道,出生的第一個月到三歲期間,如果與母親之間缺乏良好且可信賴的依附,腦中將會留下影響重大的痕跡,並導致嚴重的失調。或許早是讓這種知識在心理治療師的訓練中傳播開來的時候了,如此一來,他們接受的傳統教養所造成的傷害性影響,也許會稍微減弱。因為禁止我們過問父母行為的,常常就是我們自身的教養,也就是相信黑色教育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傳統道德、宗教規條,以及某些精神分析理論,都導致了連兒童心理治療師也對於指出父母的責任一事躊躇不前。他們害怕這麼做會造成父母的罪惡感,而如此一來這些父母可能會傷害孩子。
我深信情況會是相反的。一旦建立起治療的關係,說出真相是可以喚醒個案
的。當然,兒童心理治療師無法去改變「問題」兒童的父母,但如果他將必要的知識傳達給他們,那麼基本上就能協助改善父母與孩子的關係。舉例而言,如果告知父母真正溝通的情緒滋養意義,並且幫助他使用這方面的知識,就會為父母打開一扇通往全新體驗的大門。父母拒絕與孩子溝通,常常並非出於惡意,而是因為他們自己在小時候也沒有經歷過這種形式的情感關懷照顧,他們完全不知道這種東西存在。父母可以與孩子一同學習如何有意義地溝通,但前提是這些孩子獲得心理治療師全然的支持,而這位心理治療師自己已經擺脫了黑色教育,也就是完全站在孩子這邊。
有這樣的治療師提供知情見證者的支持,鼓勵過動(或承受著其他苦痛)的孩子去感覺他的不安,而非發洩他的不安,並且對父母表達他的感覺,而不是害怕感覺並與感覺分離。如此一來,父母會從孩子身上學到,人可以擁有感覺,而無須害怕感覺將導致惡果,感覺反而可以讓人得到依靠並且創造互信。
我知道有位母親很感謝她的孩子拯救她擺脫了她對父母的毀滅性依附。這位母親小時候曾遭到父母嚴重的虐待,她接受了許多年的心理治療,依然努力去看父母好的一面。她由於女兒的過動症以及具攻擊性的情緒爆發行為而深感痛苦,她的女兒自出生以來就不斷地接受醫生治療。這種狀態幾年下來都沒有改善。她帶著孩子去看醫生,給孩子吃不同的藥,定期造訪自己的心理治療師,但卻一再地為自己的父母辯護。在意識層面上,她從未認為自己是因為父母而受苦,而只意識到孩子讓她痛苦。
直到有一天她,她終於經由一位新的心理治療師而承認她三十年來對父母積壓在心中的怒火,因此勃然大怒。此時奇蹟發生了(雖然這根本不是奇蹟):在短短幾天之內,她的女兒開始用正常的方式玩耍,過動的病症都消失了,會提出疑問並且明確地回答。這位母親猶如從厚重迷霧裡走出來,像是她現在第一次看見她的孩子。而這樣一個不被利用來當成投射對象的孩子,便可以安靜地玩耍,不需要像發瘋似的跑來跑去。她不用再去完成拯救媽媽的無望任務,或至少是用她自己的「失調」來讓媽媽面對真相。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第三部「厭食症:對真正溝通的渴望」,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200-203。)
當孩子出生時,他們最需要從父母得到的是愛──我指的是慈愛、關注、照顧、和藹以及交流的意願等。如果這些需求被滿足了,孩子的身體將會得到關愛照顧的美好記憶,日後長大成人之後也會將同樣形式的愛繼續傳遞給下一代。但如果這些需求沒有被滿足,那麼他將一輩子渴望能滿足最初始(也是最重要)的需求。在日後的人生中,這種渴望將會轉嫁給其他人。比較起來,越常被剝奪愛,或是越常被以「教養」之名而遭受否定或虐待的孩子,他們在成年之後就越離不開父母(或替代父母的其他人),他們期待獲得以前父母在關鍵性的時刻未按其所需給予的一切。這是身體的正常反應。身體知道它缺少了什麼,它忘不掉那些匱乏。匱乏或空洞一直都在那裡,等待被填滿。
當年紀越大,就越難從別人身上獲得父母拒絕給予的愛。但身體的期待卻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停止──而且完全相反!期望只會轉嫁給其他人,通常的對象就是自己的兒孫。離開這種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能對這種機制有所自覺,並藉由消解「壓抑與否認」的過程,竭盡所能地認清我們的童年真相。我們能在自己身上創造出可以滿足這些需求的人,給予從我們出生以來或更早以前就等著填滿的需求。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給自己未曾從父母獲得的重視、尊重、對自身情緒的理解、必要的保護,以及無條件的愛。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們需要一個特殊的經驗:去愛童年的自己。沒有這種愛的經驗,我們就不會知道愛是什麼。如果我們想藉由心理治療的幫助學會這種經驗,就需要一位可以給予保護、尊重、同理心與陪伴的治療師,這位治療師能接受我們的模樣,能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為什麼會變成現在的樣子。這種基本經驗是不可或缺的,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為曾經受忽視的孩子披上父母的角色。
我們不需要想為我們「做些方案」的教育家,也不需要在面對個案的童年創傷時力求保持中立並將分析對象的敘說詮釋為幻想的精神分析師。不,我們需要的正是完全相反的人:也就是一個偏心的(parteiischen)陪伴者,一個當我們的情緒在他與我們面前一步一步地揭露童年曾承受過什麼,以及過去必須忍受些什麼時,這位陪伴者可以陪我們一起經驗驚懼與憤怒;當我們還是小孩,身心在為生命奮戰時,一直是孤孤單單的,生命長年累月地處在持續的危險之中。
我們需要這樣的一個陪伴者──我稱之為「知情見證者」(Wissenden Zeugen)──如果我們得到這種陪伴,從此刻開始去幫助我們心中的那個孩子,去理解他的身體語言、去探究他的需求,而不是像我們的父母一直以來忽視這些需求。
我在這裡描述的內容絕對是實際可行的。人們可以在這種偏心的、不中立(nicht nuetralen)的治療陪伴下找到自己的真相。人們可以在這樣的過程中解除自己的病症、擺脫抑鬱、重獲人生樂趣、脫離筋疲力竭的狀態,而且一旦不再需要將精力耗費在壓抑自身的真相後,他的能量就會滋長了。重點在於,每當我們壓抑自己的強烈情緒,並且企圖輕視、忽視身體的記憶時,抑鬱特有的疲倦感就會來臨。
為什麼比較少發生這種正面進展的機會呢?為什麼大多數人(包括所謂的「專家」)寧願相信藥物的力量,而不是讓儲存在身體的所知去導引呢?身體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們需要什麼、被拒絕了什麼、承受不了什麼、對什麼會有過敏反應等。但多數人卻寧可尋求藥物、毒品或酒精等的協助,這些物品只會讓通往真相的道路更加受阻。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是因為知道真相後會痛苦?痛苦是必然的。但這種痛苦只是暫時的。在適當的治療陪伴下,可以忍受得了。我相信最主要的問題就出在缺乏這種專業的陪伴。在我稱為「助人的專業者」(helfenden berufe)的人士之中,多數人似乎都受到自身道德系統的強烈阻礙,使他們無法幫助曾受虐的孩子,以及看清早年的傷害所帶來的後果。規定人們要敬愛自己父母的第四誡,它的威力完全壓制了這些專業人士,第四誡說:「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很明顯,這條戒律妨礙了早年傷痕的療癒。截至目前為止,該事實都未曾被公開發言和探討,這點並不奇怪。這條戒律的影響範圍與力量是難以衡量的,因為幼小的孩童自然地會依附他們的父母,所以一再助長了第四誡。就連最偉大的哲學家與作家都不敢抨擊這條戒律。尼采 雖然犀利地批判了基督教的道德規範,但他無法將批判擴及自己的家庭。當任何一個曾受虐的成年人企圖違抗父母的行為時,心中都暗藏著那個小小孩對父母會施加懲罰的恐懼。不過這種恐懼只會潛伏在無意識裡。一旦有意識地經驗到了,恐懼就會隨著時間漸漸消散。
支持第四誡的道德規範與我們童年的期望互相結合,導致絕大多數治療師會對尋求幫助的病患,提出和他們接受的教養同樣一套規範。許多這類治療師本身就和父母有數不清的牽纏。他們稱這種擺脫不了的牽纏是「愛」,並試著將這種形式的「愛」提供給他人作為解決之道。他們傳播寬恕是癒療的途徑,顯然並不明白這條路是個圈套,他們自己就身陷其中。寬恕從來沒有療癒的效果(Alice Miller, 1990; 2003)
很特別的一點是,我們幾千年來都與這條戒律生活在一起,幾乎無人質疑它,只因為它支撐了一項生理現實:所有孩子,無論受過虐待與否,都一直愛著他們的父母。只有成年人,才有辦法選擇。但我們的行為卻表現得猶如仍是小孩,不可以對自己父母的戒律提出質疑。然而,身為有意識的成年人,我們擁有質疑的權力,即便我們知道這些對兒時的質疑可能會讓父母非常震驚。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導論「身體與道德」,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26-31。)
2) 直視「我是為你好!」的施虐痕跡:受傷的內在小孩,身體需要傾聽。
在我所有的著作裡,我試著用不同的方式以及脈絡,闡述我所謂的「黑色教育」(Schwarzen Pädagogik)童年經歷會在日後如何限制我們的活力,並大幅損害甚或扼殺我們究竟是誰、我們有什麼感覺、我們需要什麼感覺等。「黑色教育」的養育之道會教養出適應良好的個體,只會信任他們被強迫戴上的面具,因為他們童年一直生活在害怕被處罰的長期恐懼之中。這種教育方式的最高原則是:「我這樣教你,是為了你好,即便我毆打你或用言語折磨、傷害你,都只會對你有好處。」
匈牙利作家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惹‧卡爾特斯在他著名的小說《非關命運》中,提到了他進入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景況。當時他還只是一個年僅十五歲的男孩,他鉅細靡遺地告訴讀者,他如何試著將在集中營遇見很多費解而殘忍的事情解釋為正面的、對他有好處。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他無法在死亡的恐懼下倖存下來。
或許每個受虐兒為了求生,都必須接受這種態度。這些孩子重新詮釋他們的感知,在局外觀察者一致認定是明顯的犯罪行為之中看見「善行」。孩子沒有選擇。如果沒有「協助見證者」(Helfenden Zeuge)在一旁扭轉情況或幫忙揭露施暴者,受虐兒就必須要去壓抑真正的感覺。日後他們長大成人之後,如果有幸遇到了「知情見證者」,他們才有了選擇。他們可以進入真相,不用再去同情、「理解」施暴者,停止試圖去感覺他們無力支撐的、分離的情緒,並可以徹底地揭露曾被施暴的情況。這一步意味著身體卸下了重負。長大成人的當事者不用一再地強迫憶起孩提時的悲慘歷史。一旦這個成年人願意認清自己的所有真相,他的身體就會感覺被理解、被尊重與被保護。
我稱這種暴力形式的「教養」(Erziehung )是虐待(Mißhandlung),不只是因為孩子被否定了他身為人類所應得的尊嚴與尊重的權力,同時也建立起一種極權體制,使孩子完全無法感知所遭遇到的屈辱、貶抑與蔑視,更遑論起而反抗了。這種童年的模式必然會被受害者複製了,用在他們的伴侶與孩子身上,用在工作場域與政治領域裡,用在任何恐懼和焦慮滋生之處,不讓極度缺乏安全感的孩童得到外部力量的協助。獨裁者就是透過這種方式生的;這些人在內心深處蔑視任何人,他們在孩童時期不曾受到尊重,日後便試圖用強大的權力迫取尊敬。
我們可以在政治領域裡觀察到,對權力與認同的飢渴是從未止息。那是永無饜足,也不可能全然被滿足的。人們擁有的權力越大,就越驅使在強迫性的重複驅力下行動,而他們企圖逃離的舊有無力感會再度出現:在地堡裡的希特勒、在自己偏執狂的恐懼之中的史達林、後來被人民反對的毛澤東、被放逐的拿破崙、在監獄裡的米洛塞維奇,以及躲在地洞裡權力不再的海珊。
是什麼驅使這些人這般濫用他們獲得的權力,導致他們最後傾覆在無力感之中呢?我認為是他們的身體。他們的身體清楚知道所有在童年時期的無力感;他們將這種無力感鎖進了自己的細胞裡,他們想驅使這種無力感的「擁有者」被人看見。然而,這些獨裁者全都非常害怕自己童年的現實,他們寧願毀掉整個民族、讓幾百萬人死去,也不願去感覺真相。
雖然我覺得研究獨裁者的生平非常據有說服力,但在這本書裡我不會繼續關注這些獨裁者的動機。我要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同樣接受黑色教育長大,但不覺得需要獲取無窮權力的人或變成獨裁者。相較之下,他們並未將壓抑的怒氣與憤恨施加於他人身上,而是毀滅性地轉向自己。他們生了病、罹患各種症狀,並且很早辭世。這些人當中最具天分的,會成為作家或藝術家。他們雖然能在文學或藝術上呈現出他們的真相,但呈現的永遠只是個人人生的分裂部分。這種分裂則讓他們用病痛付出了代價。我將在本書的第一部提出這類悲劇性人生的案例。
聖地牙哥的一個研究團隊,曾在一九九0年代針對平均年齡五十七歲的一萬七千人,詢問他們的童年概況以及一生當中有哪些疾病紀錄。結果顯示童年曾受虐者,比童年未受虐、沒有以「為了他們好」的理由而被責打的人,日後罹患重症多了數倍。
後者在日後的人生中不會抱怨病痛的問題。這篇研究短文的標題是〈如何點金成石」〉(Wie man aus Gold Blei macht)。作者把這篇文章寄給我,他對這項發現的評論是:結果一目了然、極具說服力,但同時卻沒人看見、被人掩蓋了。
為什麼被人掩蓋了呢?因為公布結果時不可能不譴責施虐的父母。我們的社會依然禁止譴責父母,事實上如今反而更嚴重了。這是由於專家們越來越力挺的觀點,是將成年人心靈上的苦痛歸咎於基因遺傳,而不是來自童年明確的傷害、被父母排斥。就連七0年代有關思覺失調患者童年的研究,除了發表在專業雜誌以外,也不被大眾所知。深信基因論者依然是勝利的一方。
英國廣受重視的臨床心理學家奧利佛‧詹姆斯在《他們毀了你》(They F*** You Up)一書裡,談的就是這種觀點。雖然這本出版於二00三年的著作,留下了矛盾的印象(因為作者對於自己理解的結論感到恐懼,甚至明確地警告不要把孩子的苦痛認為是父母的責任),但該書還是利用很多研究結果與文獻很有說服力地證明了,除了遺傳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在心理疾病的發展上其實並未扮演什麼重要角色。
因此,很多當今的心理治療很小心地迴避童年這個議題(Alice Miller, 2001)。的確,在一開始會鼓勵病患表達出他們的強烈情緒。但隨著情緒浮現的往往是被壓抑的童年記憶,也就是遭受虐待、剝削、羞辱與傷害的記憶;這些事情對心理治療師來說,常常都超過了他們的能力負荷。如果治療師沒有親自走過這條路的話,並無法應付這一切。曾走過這條路的治療師並不多見。所以大部分的治療師給個案的建議依然是黑色教育的老調重彈,也就是最初導致他們生病的同一套道德規範。
身體根本不懂這種道德規範;第四誡對身體來說毫無意義,身體也不像我們的心智會被言語蒙蔽。身體是真相的守護者,因為它背負著我們一輩子的經歷,並負責讓我們能和我們有機體的真相生活在一起。透過病症迫使我們讓真相也能進入意識之中,藉此讓我們能和那個曾經被忽視、羞辱,而一直在我們心中的孩子和諧地溝通。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導論「身體與道德」,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33-40。)
3) 席勒:書寫反抗權威的偉大劇作家vs.受軍事化教養折磨的兒子。
席勒一直都因身體不同器官的嚴重痙攣所苦。四十歲時他染上重病,以致他不斷地與死神拔河。還伴隨有精神失常的症狀,致使他在四十六歲時與世長辭。
對我而言,席勒的這種嚴重痙攣絕對可以歸咎於他童年時期頻繁的體罰以及青年時的嚴苛紀律。確切地說,他的囚禁狀態早在進入軍校前,在他父親身邊時就已經開始了。他的父親在席勒童年時系統化地克制快樂的感覺,他父親同時也如此對待自己,並稱之為自律。例如,規定孩子一旦在用餐時感到愉悅,就必須立刻停止進食並離開餐桌。席勒的父親也會這麼做。或許席勒父親是一種特例,他採取的古怪模式,壓抑了所有我們可能稱為「生活品質」的天性。但軍校制度在當時卻是廣泛被使用的,而且被視為普魯士的嚴格教養。很少有人會去反思這種教養的後果。
這些軍事學校所採取的嚴酷監視系統,會讓人聯想到某些與納粹集中營相關的描述。當然集中營裡由國家組織起來的虐待行徑,比起軍校絕對更加歹毒與殘忍,不過集中營和之前幾百年盛行的教育體制有相同的根源(Alice Miller, 1980)。這種計畫性的殘忍行為,無論是發令者還是執行者,他們小時候都曾經歷過責打與其他各式各樣施加於其身的羞辱方式。他們完全學會了將來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不帶罪惡感也不加反省地施加在臣服於他們力量之下的其他人身上,例如孩童或囚犯。席勒沒有把自己曾承受過的恐怖統治報復在他人身上。不過,他的身體終其一生都承受著童年必須忍耐的殘暴行徑帶來的後果。
當然,席勒並非特例。孩提時代上過這種學校的人有數百萬,如果不想受到重罰或甚至被奪去性命,他們就必須學習沉默地服從權威的力量。這種經驗使他們對第四誡肅然起敬,並嚴厲叮囑下一代也絕對不得質疑權威。因此即使到了今天,他們的子子孫孫依舊堅信責打不會帶來任何傷害,這也就見怪不怪了。
然而,席勒就這方面而言卻是個例外。從《強盜》到《威廉.退爾》等,他所有的作品都不斷地反抗權威施行的盲目暴力,經由他不凡的文筆在許多人心中播下希望的種子,期許這種抗爭有朝一日能勝利。不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席勒不知道的是,他反抗不合理的權威命令,能量是來自於他身體儲存的早年經歷。他為父親那令人費解又驚恐的權力執行模式所苦,致使他開始寫作,但他不可能察覺寫作欲望之下的動機。他只想寫出優美而偉大的文學作品。
他利用歷史人物試圖說出真相,而他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只是有關父親帶給他的苦痛,即便到了他早逝的那一天,他對這所有的真相都隻字未提。這對他與社會來說依舊是個祕密,我們的社會幾百年來都相當讚賞席勒,許多戲迷和讀者視他為典範,因為他在作品中為了自由與真相奮鬥。不過真相僅止於社會可以接受的真相。
如果有人對席勒說:「你不需要尊敬你的父親。對於曾經那樣傷害過你的人,並不值得你的愛或尊敬,即便他們是你的父母亦然。為了這種孝順的奉獻,你已經用你身體上極至的苦痛付出了代價。只要你不再遵從第四誡,你就有機會解放自己。」如果聽到這番話,勇敢的席勒將會多麼震驚啊!他又會怎麼回應呢?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第一部「訴說與遮掩」,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61
4) 對母親,我能不恨嗎?寬恕無須勉強,獲知真相才是通往長大成人之路。
能夠保護我們不會受到重複驅力侵害的,只有承認真相―─承認全部的真相以及它的所有意涵。只有當我們盡可能地了解父母對我們做過什麼,我們才不會有重複那些惡行的危險;否則,我們會自動地重複父母的行為,並且極力反抗一種想法:當我們長大成人且想要平靜地建立屬於自己的人生時,我們就能夠―─且必須─―解開童年與施虐父母的連結。童年的迷惘起因於我們從前努力要去理解虐待,並由虐待中推論出意義。但我們必須放下這種迷惘。身為成年人,我們可以停止迷惘;也可以學會了解在心理治療時,道德會如何妨礙傷口的復原。
下面的例子可以具體地說明覺察是如何發生的。有一位心灰意冷的年輕女子,她認為自己無論在工作或兩性關係上都是個失敗者,她寫道:
我母親越是對我說,我是個微不足道的人、我什麼也做不成,我就越會四處碰壁。我並不想恨我的母親,我希望與她和平相處,想原諒她,讓我最後能夠擺脫我的恨意。但我卻辦不到。在恨之中我覺得被她所傷,猶如她也恨我一樣不過這是不可能的。我究竟做錯了什麼呢?我知道如果我沒辦法原諒她,我將會很痛苦。我的心理治療師告訴我,如果我和父母對抗,這就宛如我在對抗自己一樣。我當然知道如果無法發自內心深處原諒的話,就不是真正的原諒。我覺得非常困惑,因為有些時候我可以原諒父母,並且感覺我同情他們。但一想到他們曾對我做過的事,我就會突然生氣,然後完全不想看到他們。我其實想過我自己的生活,平靜下來,不要一直想過去他們是怎麼打我、羞辱我、以及那些幾乎算是酷刑的虐待了。
這女人相信,當她認真看待自己的記憶並且忠於自己的身體時,就是在與父母對抗,同時也等於對抗自己。這是心理治療師告訴她的。但這種說法的後果卻是,這個女人完全無法區分她自己的生活以及父母的生活,她完全沒有自我意識,只能將自己理解為父母的一部分。心理治療師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呢?我不知道。但我認為在這樣的陳述中可以感覺到這位心理治療師對自己父母的恐懼,而個案則被這種恐懼與迷惘感染了。結果是她不敢揭開自己的童年故事,讓自己的身體能和真相生活在一起。
在另外一個案例中,一個非常聰明的女人寫道,她不想對自己的父母做出一
概而論的評價,而是要把事情分開來看。因為無論她小時候被打還是被性侵,她還是與父母一起度過了一些美好時光。她的心理治療師肯定她應該去權衡美好與不好的時光,而且身為成年人必須了解不可能有完美的父母,所有父母都會犯錯。然而重點並不在此。重點是現在已然成年的這位女子必須發展出對那個小女孩的同理心,沒有人看見那個小女孩的苦痛,她被求取自身利益的父母利用了,多虧了她洋溢的才華,她可以完美地滿足父母的利益。如果她現在已經能去感覺那個小女孩的苦痛,並且去陪伴內在小孩,那麼她就不應讓美好的時光與不好的時光互相抵銷。這麼一來,她又會披上那個小女孩的角色,這個小女孩想去滿足父母的心願:愛他們、原諒他們、記住美好時光等。
這個孩子不斷地嘗試這麼做,希望能理解她遭遇到的那些來自於父母的自相矛盾的訊息及行為。但這種內在的「工作」只會更強化她的困惑。這個孩子不可能理解她的母親也身處在一個內心的防空洞裡,建築著對抗自己感覺的防禦工事,以至於沒有任何理解孩子需求的感受力。
問這些問題,並不是要一概而論地批判父母,而是為了要找出那個受苦、說不出話的孩子的觀點,以及放下在我看來是破壞性的依附關係。誠如我之前所說的,這種依附的組成是感激、同情、否認、渴望、粉飾,以及無數始終無法圓滿而且注定無法圓滿的期望。對曾忍受過的殘暴行徑表達出寬容的態度,並不會打開通往長大成人的道路。能打開那條路的是獲知自己的真相,以及滋長出對那個受虐兒的同理心。看清虐待如何阻礙了成年人的整個人生,以及摧毀了多少可能性,同時又有多少不幸被不經意地傳給了下一代。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第二部「心理治療中的傳統道德與身體的知識」,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181-184。)
5) 親子間的真正溝通:站在孩子這邊,看見童年真相。(已重新下標)
同樣讓心理治療師感到棘手的是治療過動兒童的症狀。如果這些孩子的情況
被視為與遺傳有關,或是應該加以矯正的壞習慣,這些孩子要怎麼融入家庭呢?
而所有真正的病因都將成為祕密?但如果我們準備好去看清這些情緒其實有現
實的基礎,反映了他們缺乏照料、遭受虐待,或尤其是缺乏情緒滋養(nährender
Kommunikation),我們眼中就不會再看到無意義地到處吵鬧的孩子,而是承受著痛苦的孩子,是不能知道受苦之因的孩子。如果我們能接受這些,就能幫助自己與他們。也許我們(和他們)便不會那麼害怕情緒、痛楚、恐懼與憤怒,而是理解我們的父母究竟對我們做過什麼。
多數心理治療師支持的(道德)義務,是無論如何都不對父母追究責任的態
度,導致了對疾病之因不自覺的漠視,同時也影響了治療疾病的機會。現代的大腦科學家在幾年前便已知道,出生的第一個月到三歲期間,如果與母親之間缺乏良好且可信賴的依附,腦中將會留下影響重大的痕跡,並導致嚴重的失調。或許早是讓這種知識在心理治療師的訓練中傳播開來的時候了,如此一來,他們接受的傳統教養所造成的傷害性影響,也許會稍微減弱。因為禁止我們過問父母行為的,常常就是我們自身的教養,也就是相信黑色教育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傳統道德、宗教規條,以及某些精神分析理論,都導致了連兒童心理治療師也對於指出父母的責任一事躊躇不前。他們害怕這麼做會造成父母的罪惡感,而如此一來這些父母可能會傷害孩子。
我深信情況會是相反的。一旦建立起治療的關係,說出真相是可以喚醒個案
的。當然,兒童心理治療師無法去改變「問題」兒童的父母,但如果他將必要的知識傳達給他們,那麼基本上就能協助改善父母與孩子的關係。舉例而言,如果告知父母真正溝通的情緒滋養意義,並且幫助他使用這方面的知識,就會為父母打開一扇通往全新體驗的大門。父母拒絕與孩子溝通,常常並非出於惡意,而是因為他們自己在小時候也沒有經歷過這種形式的情感關懷照顧,他們完全不知道這種東西存在。父母可以與孩子一同學習如何有意義地溝通,但前提是這些孩子獲得心理治療師全然的支持,而這位心理治療師自己已經擺脫了黑色教育,也就是完全站在孩子這邊。
有這樣的治療師提供知情見證者的支持,鼓勵過動(或承受著其他苦痛)的孩子去感覺他的不安,而非發洩他的不安,並且對父母表達他的感覺,而不是害怕感覺並與感覺分離。如此一來,父母會從孩子身上學到,人可以擁有感覺,而無須害怕感覺將導致惡果,感覺反而可以讓人得到依靠並且創造互信。
我知道有位母親很感謝她的孩子拯救她擺脫了她對父母的毀滅性依附。這位母親小時候曾遭到父母嚴重的虐待,她接受了許多年的心理治療,依然努力去看父母好的一面。她由於女兒的過動症以及具攻擊性的情緒爆發行為而深感痛苦,她的女兒自出生以來就不斷地接受醫生治療。這種狀態幾年下來都沒有改善。她帶著孩子去看醫生,給孩子吃不同的藥,定期造訪自己的心理治療師,但卻一再地為自己的父母辯護。在意識層面上,她從未認為自己是因為父母而受苦,而只意識到孩子讓她痛苦。
直到有一天她,她終於經由一位新的心理治療師而承認她三十年來對父母積壓在心中的怒火,因此勃然大怒。此時奇蹟發生了(雖然這根本不是奇蹟):在短短幾天之內,她的女兒開始用正常的方式玩耍,過動的病症都消失了,會提出疑問並且明確地回答。這位母親猶如從厚重迷霧裡走出來,像是她現在第一次看見她的孩子。而這樣一個不被利用來當成投射對象的孩子,便可以安靜地玩耍,不需要像發瘋似的跑來跑去。她不用再去完成拯救媽媽的無望任務,或至少是用她自己的「失調」來讓媽媽面對真相。
(本文擷取、整理自:愛麗絲.米勒著,林硯芬譯,《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秘密》,第三部「厭食症:對真正溝通的渴望」,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20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