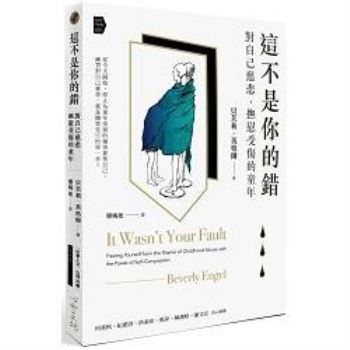羞恥感如何影響受虐者
如果你在童年時曾受虐待或被忽視,羞恥感會影響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自信心、自尊心、自我的身體形象,到你與他人的關係、經營親密關係的能力、成為好父母的能力;從工作表現到學習新事物或照顧自己。羞恥感是形形色色個人問題的根源,這些問題包括:
◆自我批判和自責。
◆自我忽視。
◆自我毀滅的行為(譬如吃得過量或過少而傷害自己的身體、酗酒、嗑藥、抽菸成癮、自殘或易遭意外)。
◆自我破壞的行為(挑起與所愛之人的爭執,或破壞自己的工作)。
◆完美主義(基於很怕被挑錯)。
◆深信好事落不到自己身上。
◆深信假使有人真的了解你,他們會討厭你或覺得你令人反感。
◆討好別人。
◆容易挑剔別人(把羞恥感加諸於他人身上)。
◆容易發怒(常常鬥毆,或開車時容易發怒)。
◆對社會宣洩(違規或違法)。
◆重複被害或加害的行為,讓虐待的行為持續下去。
受虐經驗基本上都會在受虐的孩子身上造成改變,這不只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創傷,更因為他們覺得失去了純真和尊嚴,並背負著羞恥感的沉重負荷。受到精神虐待、身體虐待和性虐待的孩子可能會被羞恥感壓垮,使得潛能的發展完全受阻。他的內心很可能一直停留在經歷受害過程(victimization)的年紀,終生不斷地一次又一次重演虐待情事。
不論遭受哪一種虐待,羞恥感都是核心問題,它深深牽動著受虐者和施虐者的行為。羞恥感會以幾種方式驅動著虐待的循環:
◆羞恥感會讓受害者不敢相信自己值得被愛、被善待和被尊重;結果之一是他們始終留在受虐的關係裡。
◆羞恥感會使得受害者相信自己受到無禮和輕蔑是應該的。
◆羞恥感會驅使人去羞辱、汙衊自己的伴侶或小孩。
◆虐待他人的人,通常是在藉此擺脫自己的羞恥感。
◆羞恥感很可能會導致情緒爆發,挑起會觸發虐待行為的憤怒。
童年受虐所導致的羞恥感常常會以下列一種或多種方式表現出來:
◆它會讓受害者用批判性的自我對話來羞辱自己,或者引發酗酒、嗑藥、破壞性的飲食行為,或其他傷害自己的形式。三分之二接受戒毒的人提到兒時曾受虐待或被忽視(Swan, 1998)。◆它會讓受害者發展出受害的行為模式(victim-like behavior),因此他們會預期並接受他人帶來的虐待行為。在受虐婦女庇護所中,高達百分之九十的婦女提及小時候曾受虐待或被忽視(美國健康與人道服務部,2013)。
◆它會讓受虐者變得容易施虐。曾經受虐待或被忽視的兒童,大約有百分之三十長大後會虐待自己的孩子(美國健康與人道服務部,2013)。
要去面對羞恥感在人生中所帶來的各種問題,是很令人怯步的。羞恥感要如何療癒,這問題也會把人壓得窒息。好消息是,你並不孤單,有成千上萬的人正面對著同樣的問題。更好的消息是,羞恥感是有方法可以治癒的。《這不是你的錯》會一步一步帶領你走完療癒羞恥感的旅程,讓你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不再被你是「不如人」的、不足的、受傷的、不值得或不可愛的等等想法所蒙蔽。
慈悲心和自我慈悲的療癒力
幾年前,我在工作上越發感到挫敗。我擔任心理治療師三十五年,以處理童年受虐的個案見長,始終努力在尋找有效的方法來幫助個案消除令人耗弱的羞恥感。我並不孤單,很多心理治療師和相關從業者長久以來深知,羞恥是受虐過的人最揮之不去的感受,個案在化解這種感受的過程中也格外艱辛。我本身有過對付這頑固羞恥感的經驗:經過多年的治療,我仍在努力對抗著我自己在兒時受虐經驗所引發的羞恥感。
我決心要找到一個方法來幫助童年受虐的人對治羞恥感,我越來越認為,羞恥感是受過創傷之後最嚴重的後果。經過五年的研究,我得出一個結論,慈悲心(compassion)就是對治羞恥感的藥方。羞恥感就像毒藥,個案若想得救,就需要另一種物質──解藥──來中和毒性。唯一能把羞恥感使人孤立、帶來羞辱、令人耗弱的毒性抵銷掉的,就是慈悲心。
我深知慈悲心對於個案們的療癒力量。我也熟讀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的著作,她深信童年曾受虐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她所謂的「知情見證者」(compassionate-witness)來確證他們的經驗,支持他們走過痛苦(Miller, 1994)。我親身體驗過擔任一名知情見證者能帶給個案什麼樣的療癒效果,也深深體驗過在一名同理的治療師的協助下,我如何脫胎換骨。近年來,很多研究者關注「慈悲心」這個主題。他們的論文裡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人的善意、支持、鼓勵和慈悲,對於我們的大腦、身體及整體的健全感有著巨大的影響。慈愛和善意甚至會影響人類基因的表現,尤其是在生命初期(Gilbert, 2009; Cozolino, 2007)。
隨著我的研究持續進行,我發覺儘管我更充分地了解到慈悲心的療癒力,但我尚未真正體認對於接受心理治療的病人,尤其是童年受虐過的人來說,自我慈悲(self-compassion)──在發覺自己不足,遭遇挫敗,或在平時感到痛苦的情況下,以慈悲心對待自己──的重要性。在2003年,克莉絲汀.聶夫(Kristin Neff)發表了兩篇論文的第一篇,對自我慈悲加以定義,並闡述如何測量(Neff, 2003a; Neff, 2003b);在此之前,自我慈悲從未被正式研究過。如今,以自我慈悲為主題的文章與論文已經超過兩百篇。
在這些研究文獻裡最一致的發現之一,是越能夠自我慈悲,接受心理治療的期間越短(Barnard and Curry,2011)。最近一項綜合二十篇研究的後設分析顯示,自我慈悲對於憂鬱、焦慮和壓力有著正面的作用(MacBeth and Gumley, 2012)。
自我慈悲似乎也可以緩和人們對於負面事件——尤其是創傷——的反應,提升復原力。吉伯特和普羅克特(Gilbert and Procter, 2006)認為,自我慈悲之所以能夠提供情緒的復原力是因為解除了面對威脅的防禦系統。研究也指出,受虐的個體若具有較高度對自我慈悲的能力,比較能夠應付令人沮喪的事件(Vettese等,2011)。
有證據顯示,自我慈悲的程度可用來診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輕重。針對經歷過意外或重症等創傷事件,表現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大學生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那些更能自我慈悲的人比缺乏自我慈悲的人所表現的症候群現象較少。特別的是,那些更能自我慈悲的人比較沒有逃避情緒的現象,也比較能夠自在地面對和創傷經驗有關的想法、感受和感知(Thompson and Waltz, 2008)。
最後,自我慈悲不僅是可以幫助童年受創者復原的關鍵因素,這項特質到頭來也是減緩羞恥感的一大關鍵。研究顯示,受創的人會經驗到重度的羞恥感和罪惡感(Jonsson and Segesten, 2004),這確認了我長年來治療童年受虐者的體會。 羞恥感也被認為是一系列心理問題和攻擊傾向的重大成因(Gilbert, 1997; Gilbert, 2003; Gilligan, 2003; Tangney and Dearing, 2002)。研究也發現,焦慮、羞恥和罪惡感的降低,以及表達悲傷、憤怒和親近感之意願的提升,都和較高度的自我慈悲能力有關(Germer and Neff, 2013)。
我也發現有一名臨床醫師運用了自我慈悲的能力,來幫助有嚴重羞恥感和自我批判的人,他是著有《慈悲心》(The Compassionate Mind)的保羅.吉伯特(Paul Gilbert)。一項針對吉伯特的「慈悲心訓練」(CMT,一種團體治療模式,對治羞恥感、罪惡感和自責格外有效)之效能所進行的研究發現,該訓練大大降低了憂鬱、自我攻擊、自卑感和羞恥感(Gilbert and Procter, 2006)。
此外,研究指出自我慈悲也是對付自我批判的一帖解藥,而自我批判是有嚴重羞恥感的人的一大特質(Gilbert and Miles, 2000)。自我慈悲會強力觸發催產素分泌,催產素這種荷爾蒙會提高信任、鎮靜、安全、寬容以及連結的感受。自我批判對人體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杏仁核是大腦最古老的部分,作用在於迅速偵測出環境裡的威脅。當人遇上威脅,就會產生迎戰或逃離的應急反應,也就是說,杏仁核會傳送訊號,使得血壓、腎上腺素、皮質醇上升,集結所需的力氣與精力來面對或避免威脅。雖然這個系統經過演化,目的是為了應付身體所受的攻擊,但也會因為情緒上的攻擊——不管是來自自身或他人——而被激發。久而久之,高水位的皮質醇會耗盡與體驗愉悅有關的神經傳導素,進而導致憂鬱(Gilbert, 2005)。
神經學上的證據也顯示,自我仁慈(self-kindness,這是自我慈悲的一大部分)和自我批判,就大腦功能的運作而言是完全相反的。新近的一項研究運用fMRI(功能性磁振造影)科技來檢視個體對挫敗的反應。受試者接受腦部掃描的同時,被告知某個假設性的狀況,譬如「連續接到三封求職被拒的信」,然後想像用自我仁慈或自我批判的方式回應這情況。自我批判與前額葉皮質區和大腦背側前扣帶迴的活動有關,這兩個部位是大腦處理錯誤和解決問題的部位。自我仁慈和肯定自己則與左顳葉和腦島活化有關,這兩個部位處理的是正面情緒和慈悲心(Longe等,2010)。聶夫(2011)說得好:「自我仁慈並非把自己看成有待解決的一個問題……而是把自己看成值得關懷的一個重要人物。」我格外感興趣的是神經學領域對慈悲心的新近研究,因為它關係到羞恥感——也就是說,我們如今知道了自覺不討人喜愛和羞恥感將如何阻塞神經迴路,以及這兩者在神經學上的一些相關性。最重要的是,由於大腦有生長新的神經元和突觸的能力,我們可以透過自我同理(self-empathy)和自我慈悲的新經驗,來積極修復與羞恥有關的舊記憶。
基於我的研究,我決定除了以慈悲心對待個案所受的苦之外,我還必須教導他們如何持續地自我慈悲,才能療癒他們所經受的層層疊疊的羞恥。
把自我慈悲當作一項療癒工具,是個相對新穎的概念。多年來治療師一直教導個案們如何呵護「內在小孩」,就很多方面來說,這是個很成功的治療策略。不過教導個案自我慈悲則更為深入。這方法幫助受害者更深刻地觸及童年的苦難。這讓他們和受虐的記憶聯繫,但是與之隔著一段距離,也就是說,並非真正地再次經驗受虐情事,而是回想起這段經歷,彷彿他們慈悲地見證著自己的經歷。這麼一來,他們可以對當時年幼的自己生出慈悲心,但毋須變成當時的自己。這方法既可以降低個體因記憶而再次受創的可能,並讓他們成為自己從小所渴望的慈愛守護者和庇護者。這方式提供了個案療傷止痛的一個方式,並學會以更慈愛和仁慈的方式對待今日的自己。
慈悲心治癒方案(the compassion cure program)
結合了我對慈悲心和自我慈悲的理解,和多年來治療童年受虐個案的點滴匯聚的體悟,我專為有受虐經驗的人打造出一套治療方案,擺脫羞恥感的折磨。我的「慈悲心治癒方案」(the compassion cure program)以關乎自我慈悲、慈悲心、羞恥感以及修復式正義的開創性科學研究為基礎,輔之以真實的案例(為保護個案隱私,內容經過改編)。這個專屬的歷程和練習,能夠幫助受害者減少或消除那沉甸甸地壓著他們、讓他們困在過去之中的羞恥感。藉由學會練習自我慈悲,你會摒除根植於羞恥感的信念,譬如自己是沒用的、無能的、糟糕的或不值得愛的。受虐的被害者應付這些不實但強大的信念的方式,通常是不加理會,或者自大或過度表現,藉此說服自己是有用的、有能力的,又或變成吹毛求疵的完美主義者。這些策略會耗上大量精力,但並沒有效果。相反的,積極地面對、認清、確證和理解羞恥感,才是克服它的方法。
別去否認羞恥感以及它所衍生的感受,而是要把它攤在陽光下。別為你的羞恥感到可恥,而是接納它。別老是從自身之外去尋求贊同與認可,而是學著從內心看重自己。我的慈悲心治癒方案是以基於自我慈悲的練習,將幫助你完成這些任務。
如果你在童年時曾受虐待或被忽視,羞恥感會影響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自信心、自尊心、自我的身體形象,到你與他人的關係、經營親密關係的能力、成為好父母的能力;從工作表現到學習新事物或照顧自己。羞恥感是形形色色個人問題的根源,這些問題包括:
◆自我批判和自責。
◆自我忽視。
◆自我毀滅的行為(譬如吃得過量或過少而傷害自己的身體、酗酒、嗑藥、抽菸成癮、自殘或易遭意外)。
◆自我破壞的行為(挑起與所愛之人的爭執,或破壞自己的工作)。
◆完美主義(基於很怕被挑錯)。
◆深信好事落不到自己身上。
◆深信假使有人真的了解你,他們會討厭你或覺得你令人反感。
◆討好別人。
◆容易挑剔別人(把羞恥感加諸於他人身上)。
◆容易發怒(常常鬥毆,或開車時容易發怒)。
◆對社會宣洩(違規或違法)。
◆重複被害或加害的行為,讓虐待的行為持續下去。
受虐經驗基本上都會在受虐的孩子身上造成改變,這不只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創傷,更因為他們覺得失去了純真和尊嚴,並背負著羞恥感的沉重負荷。受到精神虐待、身體虐待和性虐待的孩子可能會被羞恥感壓垮,使得潛能的發展完全受阻。他的內心很可能一直停留在經歷受害過程(victimization)的年紀,終生不斷地一次又一次重演虐待情事。
不論遭受哪一種虐待,羞恥感都是核心問題,它深深牽動著受虐者和施虐者的行為。羞恥感會以幾種方式驅動著虐待的循環:
◆羞恥感會讓受害者不敢相信自己值得被愛、被善待和被尊重;結果之一是他們始終留在受虐的關係裡。
◆羞恥感會使得受害者相信自己受到無禮和輕蔑是應該的。
◆羞恥感會驅使人去羞辱、汙衊自己的伴侶或小孩。
◆虐待他人的人,通常是在藉此擺脫自己的羞恥感。
◆羞恥感很可能會導致情緒爆發,挑起會觸發虐待行為的憤怒。
童年受虐所導致的羞恥感常常會以下列一種或多種方式表現出來:
◆它會讓受害者用批判性的自我對話來羞辱自己,或者引發酗酒、嗑藥、破壞性的飲食行為,或其他傷害自己的形式。三分之二接受戒毒的人提到兒時曾受虐待或被忽視(Swan, 1998)。◆它會讓受害者發展出受害的行為模式(victim-like behavior),因此他們會預期並接受他人帶來的虐待行為。在受虐婦女庇護所中,高達百分之九十的婦女提及小時候曾受虐待或被忽視(美國健康與人道服務部,2013)。
◆它會讓受虐者變得容易施虐。曾經受虐待或被忽視的兒童,大約有百分之三十長大後會虐待自己的孩子(美國健康與人道服務部,2013)。
要去面對羞恥感在人生中所帶來的各種問題,是很令人怯步的。羞恥感要如何療癒,這問題也會把人壓得窒息。好消息是,你並不孤單,有成千上萬的人正面對著同樣的問題。更好的消息是,羞恥感是有方法可以治癒的。《這不是你的錯》會一步一步帶領你走完療癒羞恥感的旅程,讓你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不再被你是「不如人」的、不足的、受傷的、不值得或不可愛的等等想法所蒙蔽。
慈悲心和自我慈悲的療癒力
幾年前,我在工作上越發感到挫敗。我擔任心理治療師三十五年,以處理童年受虐的個案見長,始終努力在尋找有效的方法來幫助個案消除令人耗弱的羞恥感。我並不孤單,很多心理治療師和相關從業者長久以來深知,羞恥是受虐過的人最揮之不去的感受,個案在化解這種感受的過程中也格外艱辛。我本身有過對付這頑固羞恥感的經驗:經過多年的治療,我仍在努力對抗著我自己在兒時受虐經驗所引發的羞恥感。
我決心要找到一個方法來幫助童年受虐的人對治羞恥感,我越來越認為,羞恥感是受過創傷之後最嚴重的後果。經過五年的研究,我得出一個結論,慈悲心(compassion)就是對治羞恥感的藥方。羞恥感就像毒藥,個案若想得救,就需要另一種物質──解藥──來中和毒性。唯一能把羞恥感使人孤立、帶來羞辱、令人耗弱的毒性抵銷掉的,就是慈悲心。
我深知慈悲心對於個案們的療癒力量。我也熟讀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的著作,她深信童年曾受虐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她所謂的「知情見證者」(compassionate-witness)來確證他們的經驗,支持他們走過痛苦(Miller, 1994)。我親身體驗過擔任一名知情見證者能帶給個案什麼樣的療癒效果,也深深體驗過在一名同理的治療師的協助下,我如何脫胎換骨。近年來,很多研究者關注「慈悲心」這個主題。他們的論文裡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人的善意、支持、鼓勵和慈悲,對於我們的大腦、身體及整體的健全感有著巨大的影響。慈愛和善意甚至會影響人類基因的表現,尤其是在生命初期(Gilbert, 2009; Cozolino, 2007)。
隨著我的研究持續進行,我發覺儘管我更充分地了解到慈悲心的療癒力,但我尚未真正體認對於接受心理治療的病人,尤其是童年受虐過的人來說,自我慈悲(self-compassion)──在發覺自己不足,遭遇挫敗,或在平時感到痛苦的情況下,以慈悲心對待自己──的重要性。在2003年,克莉絲汀.聶夫(Kristin Neff)發表了兩篇論文的第一篇,對自我慈悲加以定義,並闡述如何測量(Neff, 2003a; Neff, 2003b);在此之前,自我慈悲從未被正式研究過。如今,以自我慈悲為主題的文章與論文已經超過兩百篇。
在這些研究文獻裡最一致的發現之一,是越能夠自我慈悲,接受心理治療的期間越短(Barnard and Curry,2011)。最近一項綜合二十篇研究的後設分析顯示,自我慈悲對於憂鬱、焦慮和壓力有著正面的作用(MacBeth and Gumley, 2012)。
自我慈悲似乎也可以緩和人們對於負面事件——尤其是創傷——的反應,提升復原力。吉伯特和普羅克特(Gilbert and Procter, 2006)認為,自我慈悲之所以能夠提供情緒的復原力是因為解除了面對威脅的防禦系統。研究也指出,受虐的個體若具有較高度對自我慈悲的能力,比較能夠應付令人沮喪的事件(Vettese等,2011)。
有證據顯示,自我慈悲的程度可用來診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輕重。針對經歷過意外或重症等創傷事件,表現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大學生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那些更能自我慈悲的人比缺乏自我慈悲的人所表現的症候群現象較少。特別的是,那些更能自我慈悲的人比較沒有逃避情緒的現象,也比較能夠自在地面對和創傷經驗有關的想法、感受和感知(Thompson and Waltz, 2008)。
最後,自我慈悲不僅是可以幫助童年受創者復原的關鍵因素,這項特質到頭來也是減緩羞恥感的一大關鍵。研究顯示,受創的人會經驗到重度的羞恥感和罪惡感(Jonsson and Segesten, 2004),這確認了我長年來治療童年受虐者的體會。 羞恥感也被認為是一系列心理問題和攻擊傾向的重大成因(Gilbert, 1997; Gilbert, 2003; Gilligan, 2003; Tangney and Dearing, 2002)。研究也發現,焦慮、羞恥和罪惡感的降低,以及表達悲傷、憤怒和親近感之意願的提升,都和較高度的自我慈悲能力有關(Germer and Neff, 2013)。
我也發現有一名臨床醫師運用了自我慈悲的能力,來幫助有嚴重羞恥感和自我批判的人,他是著有《慈悲心》(The Compassionate Mind)的保羅.吉伯特(Paul Gilbert)。一項針對吉伯特的「慈悲心訓練」(CMT,一種團體治療模式,對治羞恥感、罪惡感和自責格外有效)之效能所進行的研究發現,該訓練大大降低了憂鬱、自我攻擊、自卑感和羞恥感(Gilbert and Procter, 2006)。
此外,研究指出自我慈悲也是對付自我批判的一帖解藥,而自我批判是有嚴重羞恥感的人的一大特質(Gilbert and Miles, 2000)。自我慈悲會強力觸發催產素分泌,催產素這種荷爾蒙會提高信任、鎮靜、安全、寬容以及連結的感受。自我批判對人體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杏仁核是大腦最古老的部分,作用在於迅速偵測出環境裡的威脅。當人遇上威脅,就會產生迎戰或逃離的應急反應,也就是說,杏仁核會傳送訊號,使得血壓、腎上腺素、皮質醇上升,集結所需的力氣與精力來面對或避免威脅。雖然這個系統經過演化,目的是為了應付身體所受的攻擊,但也會因為情緒上的攻擊——不管是來自自身或他人——而被激發。久而久之,高水位的皮質醇會耗盡與體驗愉悅有關的神經傳導素,進而導致憂鬱(Gilbert, 2005)。
神經學上的證據也顯示,自我仁慈(self-kindness,這是自我慈悲的一大部分)和自我批判,就大腦功能的運作而言是完全相反的。新近的一項研究運用fMRI(功能性磁振造影)科技來檢視個體對挫敗的反應。受試者接受腦部掃描的同時,被告知某個假設性的狀況,譬如「連續接到三封求職被拒的信」,然後想像用自我仁慈或自我批判的方式回應這情況。自我批判與前額葉皮質區和大腦背側前扣帶迴的活動有關,這兩個部位是大腦處理錯誤和解決問題的部位。自我仁慈和肯定自己則與左顳葉和腦島活化有關,這兩個部位處理的是正面情緒和慈悲心(Longe等,2010)。聶夫(2011)說得好:「自我仁慈並非把自己看成有待解決的一個問題……而是把自己看成值得關懷的一個重要人物。」我格外感興趣的是神經學領域對慈悲心的新近研究,因為它關係到羞恥感——也就是說,我們如今知道了自覺不討人喜愛和羞恥感將如何阻塞神經迴路,以及這兩者在神經學上的一些相關性。最重要的是,由於大腦有生長新的神經元和突觸的能力,我們可以透過自我同理(self-empathy)和自我慈悲的新經驗,來積極修復與羞恥有關的舊記憶。
基於我的研究,我決定除了以慈悲心對待個案所受的苦之外,我還必須教導他們如何持續地自我慈悲,才能療癒他們所經受的層層疊疊的羞恥。
把自我慈悲當作一項療癒工具,是個相對新穎的概念。多年來治療師一直教導個案們如何呵護「內在小孩」,就很多方面來說,這是個很成功的治療策略。不過教導個案自我慈悲則更為深入。這方法幫助受害者更深刻地觸及童年的苦難。這讓他們和受虐的記憶聯繫,但是與之隔著一段距離,也就是說,並非真正地再次經驗受虐情事,而是回想起這段經歷,彷彿他們慈悲地見證著自己的經歷。這麼一來,他們可以對當時年幼的自己生出慈悲心,但毋須變成當時的自己。這方法既可以降低個體因記憶而再次受創的可能,並讓他們成為自己從小所渴望的慈愛守護者和庇護者。這方式提供了個案療傷止痛的一個方式,並學會以更慈愛和仁慈的方式對待今日的自己。
慈悲心治癒方案(the compassion cure program)
結合了我對慈悲心和自我慈悲的理解,和多年來治療童年受虐個案的點滴匯聚的體悟,我專為有受虐經驗的人打造出一套治療方案,擺脫羞恥感的折磨。我的「慈悲心治癒方案」(the compassion cure program)以關乎自我慈悲、慈悲心、羞恥感以及修復式正義的開創性科學研究為基礎,輔之以真實的案例(為保護個案隱私,內容經過改編)。這個專屬的歷程和練習,能夠幫助受害者減少或消除那沉甸甸地壓著他們、讓他們困在過去之中的羞恥感。藉由學會練習自我慈悲,你會摒除根植於羞恥感的信念,譬如自己是沒用的、無能的、糟糕的或不值得愛的。受虐的被害者應付這些不實但強大的信念的方式,通常是不加理會,或者自大或過度表現,藉此說服自己是有用的、有能力的,又或變成吹毛求疵的完美主義者。這些策略會耗上大量精力,但並沒有效果。相反的,積極地面對、認清、確證和理解羞恥感,才是克服它的方法。
別去否認羞恥感以及它所衍生的感受,而是要把它攤在陽光下。別為你的羞恥感到可恥,而是接納它。別老是從自身之外去尋求贊同與認可,而是學著從內心看重自己。我的慈悲心治癒方案是以基於自我慈悲的練習,將幫助你完成這些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