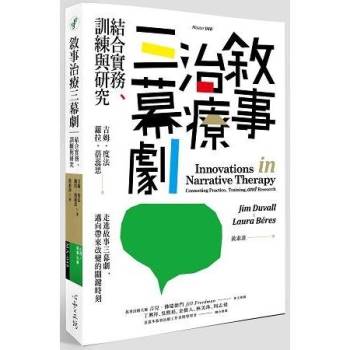2-1-1
發展故事情節
當事人可能會對自己或別人,以負面、概括化的自我認同的說法開始,例如,父母可能會宣稱九歲大的兒子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或是說自己是憂鬱症;了解當事人習慣以這種方式來說明問題,對治療師很有用,請務必記得。當當事人前來尋求治療時,描述問題、危機或議題,治療師認可當事人所經驗到的沮喪,經由解構式的傾聽和提問,以貼近經驗和非概括性的語氣,和當事人商討問題的定義(White,2007a)。這在治療會談剛開始的時候尤其重要,因為當自我認同被概括化,又被貼上某個標籤類別(例如ADHD、憂鬱症、邊緣型人格等等),就很難得到另類評價。概括的、全面性類別會讓治療師連結到抽象的概念中,而不是連結到特定的尋求協助的人身上。類別和標籤等概括化自我認同的做法,只會拉大與當事人的距離,和他們失聯,妨礙他們分辨出更有收穫的替代故事情節路徑的意願。所以,命名、外化和解構問題,有助於在問題和為問題所困的人之間,建立起一樣的關係。
當治療師面對概括化的自我認同描述,諸如「他有過動症」或是「我很憂鬱」,當事人已經開始描述問題重重的時空和事件,治療師帶著好奇、以解構法傾聽,進入當事人所說的問題故事,在這種方式下,當事人的故事受到慎重對待;同時,治療師注意傾聽的是還有什麼沒有說出來,而不是這當事人認為重要的事。
要注意,解構式傾聽和解構式提問是交叉出現的,後者針對問題的概括影響,邀請當事人再考慮和再評估先前的負向自我認同結論。隨著時間演進,當問題的概括影響一再受到質疑,就會為替代故事建立更多空間,因此變得更清晰可見。下面這段解構式傾聽和提問的範例,摘錄自與一個被診斷為憂鬱症患者的治療會談。
治療師:納森,今天我們最重要的討論重點是什麼?
納 森(從椅子向前傾,手肘放在膝蓋上,緊握雙手,向下看著地板):我會誠實以告,我從來沒有想過會跟你這樣的人見面,你知道,好像我有問題,需要找心理醫師,我其實不是會這樣做的人。
治療師:當然,我可以理解你從來沒有想過會來跟我這樣的人見面,所以,這對你是全新的經驗。是什麼讓你決定要來這個會談,進來跟我聊聊?納 森:嗯!這其實不是我的意思,我去看醫生,他告訴我我有憂鬱症,說我應該找你,治療我的憂鬱(他抬起頭,直接看著治療師),你可以嗎?你能治好我的憂鬱症嗎?
治療師:我還是有一點困惑,納森,有很多種不一樣的憂鬱症,每一個人的憂鬱都是不同的。讓我知道更多有關你的「憂鬱」和你的特殊情況(背景故事),將對我很有幫助;還有跟憂鬱無關的你也是,如此一來,當你說你有憂鬱症時,也許我能更了解你的意思。首先,你能多說一點你自己跟憂鬱無關的部分嗎?然後,我很好奇你是怎麼開始認為自己憂鬱?
納 森:我並不是一直這樣,我曾經有過很不錯的「正常」生活,我的妻子瑞蔻,我們婚姻生活一直很棒,很享受一起行動,我也有很好的朋友和活躍的社交生活,生活很順利。後來我的公司業務緊縮,我因此丟了工作。我在那家公司做了二十三年,一路做到副總裁,經過這麼多年,他們還是把我辭退了,實在不可思議!在那之後,我想我十分混亂和悲慘,大概是放棄嘗試了吧!婚姻因此也出了問題。不久之後,瑞蔻說她不能忍受我這個樣子,決定和我分開,她說她需要空間思考我們之間怎麼了,我得搬離開家去住在一個公寓的地下室。所以,最近這七個月以來,我丟了工作,沒了老婆,失去住家,我得了憂鬱症。
治療師:在過去的七個月中你經歷了許多重要的失落。你知道,納森,聽你描述這一連串的事件讓我想到:「納森有『憂鬱症』嗎?還是這是他過去這段時間裡,經歷這些事的合理反應?」聽起來像是一大堆教人不安的事情,失去工作,經歷了你跟瑞蔻在關係上的瓶頸,然後,搬離開家去住在公寓地下室。在發生了這麼多事情後,我很好奇,你如何處理你的生活和你自己?回顧過去七個月所發生的事情,你會如何想像自己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反應?
納 森(在椅子上坐直,看著地板):也許會多一點慈悲,我變得十分煩躁和易怒,很難相處,我以前是個很好相處的人,有很多好朋友,最近他們都很生我的氣。
治療師: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的煩躁和憤怒橫阻在你和其他人的關係之間,像是瑞蔻和你的朋友?
納 森:它像一個已經按下去的按鈕,就在我和瑞蔻之間、我和朋友之間。截至目前為止,治療師認可納森的感受,也對他生活中重大事件做出反應,治療師主動接納、肯定納森的感受,接著,治療師將模糊矛盾帶進納森的經驗中,暗示他也許他不是「憂鬱」,而是他經歷生活中重大和困惑的事件,那些反應都是合理的。某種意義上,這個對話將納森從單一個體的診斷「憂鬱」裡帶離開,轉換成從他的生活脈絡來判斷。最後,這個對話從一個全面的、疏離感受的憂鬱分類,因為外化、具體化而成為貼近感受的描述,像是困惑、煩躁和生氣。
將好奇和解構式傾聽的姿態,融入治療性對話的雙重傾聽(double listening),是麥克.懷特發展出來的,他這樣說:「這些傾聽的做法指稱的是『雙重傾聽』,為探索的可能性打開寬廣的領域。」(2003, p.30)雙重傾聽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的生活是雙重故事,當我們聆聽當事人述說經驗,他們的習慣會連結到其他的經驗,卻沒有在治療會談中詳盡說明,而是隱含其中,所以治療師要開放地聆聽當事人想說的蛛絲馬跡,並且邀請他們說些之前可能沒有說出來的部分。
治療師:之前你說你「大概是放棄嘗試了吧!」,因此變得有點混亂和悲慘,然後,煩躁和生氣開始擋在你和你的重要關係之間。我很好奇,納森,你當時放棄了什麼?這可能很重要,值得我們討論嗎?
納 森(點頭表示同意):丟了工作使我變得非常混亂,好像我一無是處,事實上,我不記得我生命中曾經這麼困惑、混亂和了無生氣過。我一直是個不錯的員工,卻莫名沒了工作,毫無邏輯可循,我覺得失控,假如我二十三年來都是個好員工,卻還會丟掉工作,那就好像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你知道,就像是再努力又有什麼用?我想我變得精疲力竭,被失業卡死在那裡,失業也讓我無法分辨什麼是身邊真正重要的。我跟瑞蔻的關係,我和朋友的關係,對我都很重要。對於所發生的這一切,我覺得非常悲傷。是啊!這些都是很重要很值得談的,我需要重回軌道。
治療師:所以,納森,是不是可以這麼說,你是那種很看重你跟別人關係的人嗎?
納 森: 喔!是的,我是,我是活在人群裡的人,我真的不是過去七個月的那種人。
因此,納森對這些強而有力生活經驗的反應的力道,也說明了那些隱含在他的述說之外,另一個關於他所持的強烈價值和他更偏好的自我認同。卡瑞、瓦瑟和盧賽爾(Carey, Walther, and Russell,2009)引用麥克.懷特不在場,但隱含的事物(absent, butimplicit)的概念(這是麥克.懷特從賈克.德希達的研究成果所發展而來),進一步延伸如下:
假如我們接受這個說法:當事人可能只能提供出特定的生活經驗描述,治療師仍能從中區辨出什麼「不是」他們的經驗,然後,以我們傾聽的角度,不只聽見什麼「是」問題,也聽見他們述說中「不在場,但隱含的事物」,也就是聽見什麼「不是」問題。
問問題,會使當事人強烈持有的價值觀更加明顯可見,他們提出來的價值觀是由關於生活的某些特定知識、信念所塑造,這些知識、信念鑲嵌在被說出來的故事裡,但是卻又隱藏在問題故事的陰影之下。
所以,治療師以假設性好奇的姿勢開始進行治療會談,在會談初期運用解構式的雙重傾聽,初期階段是故事被說出的時候,也促使治療會談向前推移。因為所有的故事並非完全平等,治療師要和當事人共同合作,決定哪個故事對當事人來說是最重要且值得述說的。
2-2-2
評估影響(⋯⋯因為發生了)
當自我認同的意義有所改變時,我們不得不評估問題和生活經驗的影響力,在這個階段,經由重新回顧和重新詮釋這些寓存於各種不同事件中的經驗,當事人受邀反思生活中的問題對他們造成的影響。
在治療過程中評估這個面向,為的是探索意義的相對性和多元性,經由搭建鷹架,治療師致力於在對話當中釐清意義。格根和凱(Gergen & Kaye, 1992)解釋道:
這裡牽涉的是:相對性意義的重新概念化、接受不確定性、多元意義的創生性、探索、理解到不必堅持一個不變的故事,或尋找一個明確的故事。(p.181)
這個反思、創生的會談成為重寫故事歷程的關鍵。治療師和來求助者關係的親近和分分秒秒的合作,在這個階段益加重要,在進行反思練習時,當事人持續與侷限他們的問題保持距離,同時越來越朝向增加處理生活能力的方向。
這個反思的行動讓當事人能夠從不同的觀點,評估他們與問題事件的關係,多元性觀點具有解放侷限信念的效果,它強調信念並不是不變的真理,而是可以適時改變的,「對於那些採納這個觀點的人而言,這個立場提供了靈活融入無限的、開放的生活意義的期盼。」(Gergen & Kaye, 1992,183)反思的練習
現在,當成練習範例,花一點時間體驗這個簡單的練習,在一張白紙上畫一個S,假想這個S 是你的生命地圖,在S 底端寫下「出生」,頂端寫下「現在」,接下來,試著做某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去做做看。從S 的底端開始,依時間順序列出你生命中四件最重要的事件,在每件事情上寫下一個句子或幾個字,或描述一下你從中學到什麼。
現在,反思這些事件,它們都具有相同重量嗎?還是某些事情佔了上風,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它們都是正面的、負面的、兩者兼具?你從哪些事件學習最多:正面的、負面的,或是兩者之間?
現在,再試試,除了這四件事情之外,再挑出一件你有非常強烈情緒的事情,這件事情如何影響你的信念和你看世界的方式?想一下下列的問題:
◎這些信念是來自這個事件的影響嗎?還影響到你現在的生活嗎?
◎假如你可以重新回顧和重新思考這個事件中的經驗,那些在當時可能被忽視或被貶抑到陰影中的經驗,除了當初的反應,你可以重新找到不同的經驗嗎?
◎你會想保有最初的詮釋、假設和信念,或是你可能重新回顧這個事件,重新詮釋它,把它們改變成為更適合你現在的生活?
◎事件本身和所賦予事件的意義是否有所不同,假如你是:
‧年輕二十歲或年長二十歲來看這件事?
‧從另一個文化來看這件事?
‧從不同性別看這件事?
◎當你回想這個事件,是否有一些遺忘的經驗重新出現在回憶中?假如是這樣,這些經驗是否提供另類意義,而造成不一樣的自我認同結果?
這些對經驗的反思歷程,能與問題逐漸產生距離,也因此使經驗相對化(Gergen & Kaye, 1992),而把人與問題的關係放在適當位置。這些轉化的對話邀請當事人去思考,如果他們抱持不同的假設,有可能採取哪些不同的行動,有哪些能力、承諾和喜好,會跟之前隱藏未見的經驗相關,而變得更加明顯,讓它們蠢蠢欲動?
治療師(反思提問):山姆,讓我問你另一個問題,假如你是那個先前你提到三十六歲的成年人,回顧你的人生,現在的你是十五歲,三十六歲的你會給十五歲的你怎樣的忠告,讓你的生活從「惹惱人」和「討人厭」解放出來?關於你和玲達的關係,你想你會給自己什麼忠告?山 姆: 哇!好問題,雖然是有點困難的問題。(凝視旁邊思考答案)嗯嗯,我想三十六歲的我會告訴我要學著更有耐心更專心,有點像空手道小子的老師跟他說要有耐心、要思考,當事情有點難搞的時候,他們就去釣魚,就不會跟我一樣總是一觸即發又心浮氣躁的。我想三十六歲的自己也會跟我說要對大姐好一點,她是對的,我一直都不夠成熟,我不希望人家覺得我不成熟,我不喜歡現在橫阻在我們之間的情況,我喜歡跟玲達一起做些事情,像以前一樣一起玩笑。
所有這些,是否意味著當事人經常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的信念和環繞周圍的世界,既然都是真的,所以無法改變?或是,他們能夠退一步,反思他們的經驗和生活中的事件,重新評估、重新詮釋、重新思考,變得更精密地符合現在的生活?誠如福克和戈德納(Fook & Gardner)所言:「在這種觀點下,反思取向企圖聚焦在整體經驗,而且涉及許多特點:認知元素、情感元素、從不同觀點的意義和詮釋。」(2007, p.25)反思取向檢視位居重要事件中的多元經驗,而不是強調事件的主流面向。
文化、信念、故事和自我認同,都是從詮釋事件裡的經驗形成的,我們所擁有的理解,或是我們賦予事件的意義,都會受到環繞周圍的文化脈絡所侷限;同樣的,事情越重要就越可能強烈地塑造我們的自我認同與周遭世界的信念,也就強化了我們將這些信念信以為真,或視為真理;然而,這些過去事件都可以重新回顧和重新詮釋,使其更加適合當前的生活。
當我們和當事人一起反思他們的經驗時,觀照我們如何運用自己和在治療會談細節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重要。福克和戈德納說:「我們負責解釋、選擇、優先考慮、有些看見有些沒看見,以特定方式運用知識,處理大量我們自己的、社會的、歷史情境的事情。」(2007, p.28)。當我們參與反思,透明度變成極有價值的運作原則,有助於讓別人了解我們觀點的來龍去脈與背景。我們不僅在行動中反思,而且是帶著反思行動,讓我們的觀點一目了然。
當我們探討治療和訓練的平行效果時,反思實務會在我們的訓練和研究計畫中整合到每一次治療會談中,學生治療者經常被鼓勵對他們的實務工作進行反思,強調透明度和持續的技巧發展。反思性對治療師和來求助者具有雙重的價值,提供一個反思的、實務基礎的歷程,治療師能夠藉此延伸他們的知識和技巧,拓展理論取向的界限(Bird, 2006)。對於來尋求協助的家庭成員,他們的理解和喜好會受到認可和重視,使他們能夠延伸其學習,並朝向比較喜歡的行動。
發展故事情節
當事人可能會對自己或別人,以負面、概括化的自我認同的說法開始,例如,父母可能會宣稱九歲大的兒子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或是說自己是憂鬱症;了解當事人習慣以這種方式來說明問題,對治療師很有用,請務必記得。當當事人前來尋求治療時,描述問題、危機或議題,治療師認可當事人所經驗到的沮喪,經由解構式的傾聽和提問,以貼近經驗和非概括性的語氣,和當事人商討問題的定義(White,2007a)。這在治療會談剛開始的時候尤其重要,因為當自我認同被概括化,又被貼上某個標籤類別(例如ADHD、憂鬱症、邊緣型人格等等),就很難得到另類評價。概括的、全面性類別會讓治療師連結到抽象的概念中,而不是連結到特定的尋求協助的人身上。類別和標籤等概括化自我認同的做法,只會拉大與當事人的距離,和他們失聯,妨礙他們分辨出更有收穫的替代故事情節路徑的意願。所以,命名、外化和解構問題,有助於在問題和為問題所困的人之間,建立起一樣的關係。
當治療師面對概括化的自我認同描述,諸如「他有過動症」或是「我很憂鬱」,當事人已經開始描述問題重重的時空和事件,治療師帶著好奇、以解構法傾聽,進入當事人所說的問題故事,在這種方式下,當事人的故事受到慎重對待;同時,治療師注意傾聽的是還有什麼沒有說出來,而不是這當事人認為重要的事。
要注意,解構式傾聽和解構式提問是交叉出現的,後者針對問題的概括影響,邀請當事人再考慮和再評估先前的負向自我認同結論。隨著時間演進,當問題的概括影響一再受到質疑,就會為替代故事建立更多空間,因此變得更清晰可見。下面這段解構式傾聽和提問的範例,摘錄自與一個被診斷為憂鬱症患者的治療會談。
治療師:納森,今天我們最重要的討論重點是什麼?
納 森(從椅子向前傾,手肘放在膝蓋上,緊握雙手,向下看著地板):我會誠實以告,我從來沒有想過會跟你這樣的人見面,你知道,好像我有問題,需要找心理醫師,我其實不是會這樣做的人。
治療師:當然,我可以理解你從來沒有想過會來跟我這樣的人見面,所以,這對你是全新的經驗。是什麼讓你決定要來這個會談,進來跟我聊聊?納 森:嗯!這其實不是我的意思,我去看醫生,他告訴我我有憂鬱症,說我應該找你,治療我的憂鬱(他抬起頭,直接看著治療師),你可以嗎?你能治好我的憂鬱症嗎?
治療師:我還是有一點困惑,納森,有很多種不一樣的憂鬱症,每一個人的憂鬱都是不同的。讓我知道更多有關你的「憂鬱」和你的特殊情況(背景故事),將對我很有幫助;還有跟憂鬱無關的你也是,如此一來,當你說你有憂鬱症時,也許我能更了解你的意思。首先,你能多說一點你自己跟憂鬱無關的部分嗎?然後,我很好奇你是怎麼開始認為自己憂鬱?
納 森:我並不是一直這樣,我曾經有過很不錯的「正常」生活,我的妻子瑞蔻,我們婚姻生活一直很棒,很享受一起行動,我也有很好的朋友和活躍的社交生活,生活很順利。後來我的公司業務緊縮,我因此丟了工作。我在那家公司做了二十三年,一路做到副總裁,經過這麼多年,他們還是把我辭退了,實在不可思議!在那之後,我想我十分混亂和悲慘,大概是放棄嘗試了吧!婚姻因此也出了問題。不久之後,瑞蔻說她不能忍受我這個樣子,決定和我分開,她說她需要空間思考我們之間怎麼了,我得搬離開家去住在一個公寓的地下室。所以,最近這七個月以來,我丟了工作,沒了老婆,失去住家,我得了憂鬱症。
治療師:在過去的七個月中你經歷了許多重要的失落。你知道,納森,聽你描述這一連串的事件讓我想到:「納森有『憂鬱症』嗎?還是這是他過去這段時間裡,經歷這些事的合理反應?」聽起來像是一大堆教人不安的事情,失去工作,經歷了你跟瑞蔻在關係上的瓶頸,然後,搬離開家去住在公寓地下室。在發生了這麼多事情後,我很好奇,你如何處理你的生活和你自己?回顧過去七個月所發生的事情,你會如何想像自己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反應?
納 森(在椅子上坐直,看著地板):也許會多一點慈悲,我變得十分煩躁和易怒,很難相處,我以前是個很好相處的人,有很多好朋友,最近他們都很生我的氣。
治療師: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的煩躁和憤怒橫阻在你和其他人的關係之間,像是瑞蔻和你的朋友?
納 森:它像一個已經按下去的按鈕,就在我和瑞蔻之間、我和朋友之間。截至目前為止,治療師認可納森的感受,也對他生活中重大事件做出反應,治療師主動接納、肯定納森的感受,接著,治療師將模糊矛盾帶進納森的經驗中,暗示他也許他不是「憂鬱」,而是他經歷生活中重大和困惑的事件,那些反應都是合理的。某種意義上,這個對話將納森從單一個體的診斷「憂鬱」裡帶離開,轉換成從他的生活脈絡來判斷。最後,這個對話從一個全面的、疏離感受的憂鬱分類,因為外化、具體化而成為貼近感受的描述,像是困惑、煩躁和生氣。
將好奇和解構式傾聽的姿態,融入治療性對話的雙重傾聽(double listening),是麥克.懷特發展出來的,他這樣說:「這些傾聽的做法指稱的是『雙重傾聽』,為探索的可能性打開寬廣的領域。」(2003, p.30)雙重傾聽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的生活是雙重故事,當我們聆聽當事人述說經驗,他們的習慣會連結到其他的經驗,卻沒有在治療會談中詳盡說明,而是隱含其中,所以治療師要開放地聆聽當事人想說的蛛絲馬跡,並且邀請他們說些之前可能沒有說出來的部分。
治療師:之前你說你「大概是放棄嘗試了吧!」,因此變得有點混亂和悲慘,然後,煩躁和生氣開始擋在你和你的重要關係之間。我很好奇,納森,你當時放棄了什麼?這可能很重要,值得我們討論嗎?
納 森(點頭表示同意):丟了工作使我變得非常混亂,好像我一無是處,事實上,我不記得我生命中曾經這麼困惑、混亂和了無生氣過。我一直是個不錯的員工,卻莫名沒了工作,毫無邏輯可循,我覺得失控,假如我二十三年來都是個好員工,卻還會丟掉工作,那就好像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你知道,就像是再努力又有什麼用?我想我變得精疲力竭,被失業卡死在那裡,失業也讓我無法分辨什麼是身邊真正重要的。我跟瑞蔻的關係,我和朋友的關係,對我都很重要。對於所發生的這一切,我覺得非常悲傷。是啊!這些都是很重要很值得談的,我需要重回軌道。
治療師:所以,納森,是不是可以這麼說,你是那種很看重你跟別人關係的人嗎?
納 森: 喔!是的,我是,我是活在人群裡的人,我真的不是過去七個月的那種人。
因此,納森對這些強而有力生活經驗的反應的力道,也說明了那些隱含在他的述說之外,另一個關於他所持的強烈價值和他更偏好的自我認同。卡瑞、瓦瑟和盧賽爾(Carey, Walther, and Russell,2009)引用麥克.懷特不在場,但隱含的事物(absent, butimplicit)的概念(這是麥克.懷特從賈克.德希達的研究成果所發展而來),進一步延伸如下:
假如我們接受這個說法:當事人可能只能提供出特定的生活經驗描述,治療師仍能從中區辨出什麼「不是」他們的經驗,然後,以我們傾聽的角度,不只聽見什麼「是」問題,也聽見他們述說中「不在場,但隱含的事物」,也就是聽見什麼「不是」問題。
問問題,會使當事人強烈持有的價值觀更加明顯可見,他們提出來的價值觀是由關於生活的某些特定知識、信念所塑造,這些知識、信念鑲嵌在被說出來的故事裡,但是卻又隱藏在問題故事的陰影之下。
所以,治療師以假設性好奇的姿勢開始進行治療會談,在會談初期運用解構式的雙重傾聽,初期階段是故事被說出的時候,也促使治療會談向前推移。因為所有的故事並非完全平等,治療師要和當事人共同合作,決定哪個故事對當事人來說是最重要且值得述說的。
2-2-2
評估影響(⋯⋯因為發生了)
當自我認同的意義有所改變時,我們不得不評估問題和生活經驗的影響力,在這個階段,經由重新回顧和重新詮釋這些寓存於各種不同事件中的經驗,當事人受邀反思生活中的問題對他們造成的影響。
在治療過程中評估這個面向,為的是探索意義的相對性和多元性,經由搭建鷹架,治療師致力於在對話當中釐清意義。格根和凱(Gergen & Kaye, 1992)解釋道:
這裡牽涉的是:相對性意義的重新概念化、接受不確定性、多元意義的創生性、探索、理解到不必堅持一個不變的故事,或尋找一個明確的故事。(p.181)
這個反思、創生的會談成為重寫故事歷程的關鍵。治療師和來求助者關係的親近和分分秒秒的合作,在這個階段益加重要,在進行反思練習時,當事人持續與侷限他們的問題保持距離,同時越來越朝向增加處理生活能力的方向。
這個反思的行動讓當事人能夠從不同的觀點,評估他們與問題事件的關係,多元性觀點具有解放侷限信念的效果,它強調信念並不是不變的真理,而是可以適時改變的,「對於那些採納這個觀點的人而言,這個立場提供了靈活融入無限的、開放的生活意義的期盼。」(Gergen & Kaye, 1992,183)反思的練習
現在,當成練習範例,花一點時間體驗這個簡單的練習,在一張白紙上畫一個S,假想這個S 是你的生命地圖,在S 底端寫下「出生」,頂端寫下「現在」,接下來,試著做某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去做做看。從S 的底端開始,依時間順序列出你生命中四件最重要的事件,在每件事情上寫下一個句子或幾個字,或描述一下你從中學到什麼。
現在,反思這些事件,它們都具有相同重量嗎?還是某些事情佔了上風,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它們都是正面的、負面的、兩者兼具?你從哪些事件學習最多:正面的、負面的,或是兩者之間?
現在,再試試,除了這四件事情之外,再挑出一件你有非常強烈情緒的事情,這件事情如何影響你的信念和你看世界的方式?想一下下列的問題:
◎這些信念是來自這個事件的影響嗎?還影響到你現在的生活嗎?
◎假如你可以重新回顧和重新思考這個事件中的經驗,那些在當時可能被忽視或被貶抑到陰影中的經驗,除了當初的反應,你可以重新找到不同的經驗嗎?
◎你會想保有最初的詮釋、假設和信念,或是你可能重新回顧這個事件,重新詮釋它,把它們改變成為更適合你現在的生活?
◎事件本身和所賦予事件的意義是否有所不同,假如你是:
‧年輕二十歲或年長二十歲來看這件事?
‧從另一個文化來看這件事?
‧從不同性別看這件事?
◎當你回想這個事件,是否有一些遺忘的經驗重新出現在回憶中?假如是這樣,這些經驗是否提供另類意義,而造成不一樣的自我認同結果?
這些對經驗的反思歷程,能與問題逐漸產生距離,也因此使經驗相對化(Gergen & Kaye, 1992),而把人與問題的關係放在適當位置。這些轉化的對話邀請當事人去思考,如果他們抱持不同的假設,有可能採取哪些不同的行動,有哪些能力、承諾和喜好,會跟之前隱藏未見的經驗相關,而變得更加明顯,讓它們蠢蠢欲動?
治療師(反思提問):山姆,讓我問你另一個問題,假如你是那個先前你提到三十六歲的成年人,回顧你的人生,現在的你是十五歲,三十六歲的你會給十五歲的你怎樣的忠告,讓你的生活從「惹惱人」和「討人厭」解放出來?關於你和玲達的關係,你想你會給自己什麼忠告?山 姆: 哇!好問題,雖然是有點困難的問題。(凝視旁邊思考答案)嗯嗯,我想三十六歲的我會告訴我要學著更有耐心更專心,有點像空手道小子的老師跟他說要有耐心、要思考,當事情有點難搞的時候,他們就去釣魚,就不會跟我一樣總是一觸即發又心浮氣躁的。我想三十六歲的自己也會跟我說要對大姐好一點,她是對的,我一直都不夠成熟,我不希望人家覺得我不成熟,我不喜歡現在橫阻在我們之間的情況,我喜歡跟玲達一起做些事情,像以前一樣一起玩笑。
所有這些,是否意味著當事人經常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的信念和環繞周圍的世界,既然都是真的,所以無法改變?或是,他們能夠退一步,反思他們的經驗和生活中的事件,重新評估、重新詮釋、重新思考,變得更精密地符合現在的生活?誠如福克和戈德納(Fook & Gardner)所言:「在這種觀點下,反思取向企圖聚焦在整體經驗,而且涉及許多特點:認知元素、情感元素、從不同觀點的意義和詮釋。」(2007, p.25)反思取向檢視位居重要事件中的多元經驗,而不是強調事件的主流面向。
文化、信念、故事和自我認同,都是從詮釋事件裡的經驗形成的,我們所擁有的理解,或是我們賦予事件的意義,都會受到環繞周圍的文化脈絡所侷限;同樣的,事情越重要就越可能強烈地塑造我們的自我認同與周遭世界的信念,也就強化了我們將這些信念信以為真,或視為真理;然而,這些過去事件都可以重新回顧和重新詮釋,使其更加適合當前的生活。
當我們和當事人一起反思他們的經驗時,觀照我們如何運用自己和在治療會談細節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重要。福克和戈德納說:「我們負責解釋、選擇、優先考慮、有些看見有些沒看見,以特定方式運用知識,處理大量我們自己的、社會的、歷史情境的事情。」(2007, p.28)。當我們參與反思,透明度變成極有價值的運作原則,有助於讓別人了解我們觀點的來龍去脈與背景。我們不僅在行動中反思,而且是帶著反思行動,讓我們的觀點一目了然。
當我們探討治療和訓練的平行效果時,反思實務會在我們的訓練和研究計畫中整合到每一次治療會談中,學生治療者經常被鼓勵對他們的實務工作進行反思,強調透明度和持續的技巧發展。反思性對治療師和來求助者具有雙重的價值,提供一個反思的、實務基礎的歷程,治療師能夠藉此延伸他們的知識和技巧,拓展理論取向的界限(Bird, 2006)。對於來尋求協助的家庭成員,他們的理解和喜好會受到認可和重視,使他們能夠延伸其學習,並朝向比較喜歡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