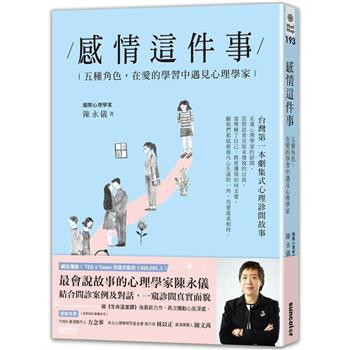信任
信任不是要來的,是要證明自己是可以被信賴的。
{星期一,上午十點}
今天問診的病人是王建昇,David Wang。在進到候診間見到這位病人之前,當然也按例通過電話。但我跟這位初診病患的電話對談,卻比平常簡短了許多。
「你好,我是在網路上找到你的。看過了你的簡介,覺得應該很合適。我只是想請教你三個問題。」他很有禮貌,講話清楚直接,不浪費時間。
「好的,請說。」聆聽,是心理師的基本功,當對方願意說的時候,一切都是我的線索。
「第一,網站上寫著你有收我這家公司的醫療保險,想跟你確認這點。第二,想請問你的治療學派、個人理念,以及常用的方式,第三,請問你會說國語嗎?謝謝你。」
我常想,不只是心理師,其實在許多的行業中,特別是服務業,聆聽的訓練都是很重要的。
這位王先生顯然做過功課,有很具體的需求,如果這時我很制式化地向他用我慣用的方式從頭介紹,可能會讓他覺得答非所問,抓不到他的重點。不過他的第二個問題,好像是隨堂抽考,讓我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要辨別跟解釋不同的心理學派,好在這次我只要介紹我所熟悉的認知行為療法就可以了。
想必我在電話中的回答都一一過了關,他希望約診,也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基本資料,我們就約了第一次的門診。
到了他約診的時間,我走出辦公室,進入候診間,我的目光在抬起頭看我的人當中很快地掃了一圈。一位年輕的華裔男子站了起來。
「David?」我問。他點點頭,跟著我進了辦公室。
他在長沙發上坐了下來,建昇個子不高,大概一百七十多公分,瘦瘦的,有雙深邃卻靈活的大眼睛。在紐約的初秋,他穿了一件淺色襯衫和卡其色的褲子。他外表給人整體的感覺是乾淨、整齊,態度上有點急切,表達能力很好,行為上顯得有些拘束。
建昇來自台灣,國中畢業後到美國唸書,大學從著名的長春藤名校完成了主修電機的學士學位。畢業後他很快地在一家知名公司找到工作,幾年後也升到了主管的位置。在台灣的父母,對他的成就感到非常地欣慰與驕傲,家族企業中的上上下下,也沒有人不知道這位優秀的少爺。
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建昇越來越覺得他的志向並不在此,反而對人、對心理、對哲學更感興趣。漸漸發現自己對這方面的嚮往,大過於只是興趣而已。於是組織能力、執行力與行動力都很強的他,就做了許多功課,最後毅然決然地辭去了原本高薪高位的工作,進入了另一所長春藤名校,攻讀臨床心理學的博士學位。
這位來自台灣的同學還真的不是普通的優秀……在美國,臨床心理學的博士班是非常難進的,錄取率比有些醫學院還難,平均約在百分之四上下。更別說是從電機那麼遠的領域跨過來,就是心理系一路唸上來的學生,要進臨床心理博士班也不是容易的事。五年後,他順利地拿到了博士學位,在完成實習後,又被知名大學錄取,成為助理教授,同時也在附近開業,開始看病人了。他是一位臨床心理師。
原來是同行?難怪,電話約診中所問的問題是如此聚焦。
相信,才能開啟對話
「我實在是沒辦法了!碰到了難題,靠我自己,解決不了。但是來找你,總覺得你要做什麼,我都一清二楚,下一步要怎麼做,我也想得到。會有什麼新東西、新想法、新解答嗎?」他眉頭深鎖,看來是真心地糾結……
「嗯,但你還是來了。而且這應該不是一時衝動的結果,因為你還花時間做了功課,把想法付諸行動地打了電話,約了時間,最後,人也來了。」
他的大眼睛轉啊轉地說:「我……該從何開始呢?」
「可以從現在在你腦袋裡的東西開始。」我感受到他的焦慮與無助。
「啊?我不用組織一下,介紹前因後果,提供一下背景因素?」他似乎有點驚訝。
「不需要吧,那樣不是會有點累?你需要負擔那麼重嗎?你來這裡,只要放輕鬆,把你心中的事情、想法、感受,想講的都可以講出來,其他的工作,是我要做的,不是嗎?」
他看起來還是不太放心。
本來靠著椅背的我,坐起來,上身向前傾,縮短了我們的距離,眼睛直視著他:「David,以心理師對心理師的立場,我想問你,你覺得在心理治療跟諮商的互動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想都不想地說:「信任,我通常都要求病人要信任我……」他停頓了一下,我知道他還沒說完,「但是信任不是要來的,或是可以給的,是要證明自己是可以被信賴的」,他振振有詞,說的都沒錯。
「在面對病人時,我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我受過正當嚴格的訓練,也累積了相當的經驗,是可以被病人信任的。」他繼續說著,是個很有自信的年輕人。
我一面聽,一面點著頭。
「相信你今天到這來,也是做過一番功課,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認為我的訓練跟經驗可以被你接受。那如果我說,我也相信自己,對我的專業能力、經歷,也很有信心……這有幫助嗎?可以換取你的信任嗎?」
我看得出,他很用力地在想。
我接著問:「你也聽過『leap of faith』這句話—信心的飛躍,你認為,為什麼要用飛躍來形容?腳踏實地走過去不就好了,要用飛的?」
他想了很久。
我耐心地等待,觀察他的面部表情。
「如果等到事實、證據,都收集齊全了,就不用信賴,用證實就可以了。那時候,就不用飛躍。但那也不叫faith了。」
我點點頭,「這樣講得通。所以……faith可能是在還不確定,甚至不知道的情況下,作一個選擇……」我還沒說完,David 就接下去說:「選擇相信?」
我揚了揚眉毛,歪著頭,做出了或許的表示。
面對這位優秀又自信的年輕人,想必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別人叫他做什麼,或者給他答案。
建昇,這位來自台灣的臨床心理師,想了想,突然鬆了一口氣,挺直的腰桿也鬆懈了下來,往後面的沙發背一靠,眼睛看著我說:「OK。」
這是一種信任。
也是一個我可以接受的開始。
Learning of Love
聆聽,是心理師的基本功,當對方願意說的時候,一切都是我的線索。
愛情,不需要道理
愛情猶如鑽石,它的價值,不會被外在因素所影響。
{星期一,上午十點}
「一直以來,我都以為我是個懂得用別人的角度看事情的人,很能體會別人的感受。我也算是個懂得如何溝通,讓別人可以理解我所要表達訊息的人。但是,在我碰到一生當中最愛的人時,我卻發現,雙方竟然如此地不能溝通,根本就是無解!」David長期以來的自我認知,好像受到了挑戰,對方是他愛的人,不對,是他最愛的人。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這位王心理師David,認識了靖君。一向理性的David告訴我,他第一次親身經歷到愛情是毫無道理可言的。靖君不僅長他十多歲,且為人妻,還育有一兒一女,是一位母親。她與David幾乎就是一見鍾情。
「我發現,愛情,雖然沒有道理,卻是universal的,是人的共性。在不同文化、環境、背景下的人,不論愛的對象是誰,經歷愛情的感受都是一樣的。愛情本身,它的本質是一樣的。」他好像深怕我會評論他對靖君的愛情,很努力地在辯解,在針對一個假想敵對他所做出的控訴,辯解。
「你看,古今中外,不論是文學、詩詞、歌曲,或是時事新聞,不乏各式各樣的愛情故事。同性的、異性的,已婚、未婚的,大家看好的,時代不允許的……但每一個故事,每一段愛情,當事人本身所經歷的感受,如果去掉這些外在因素的不同,其實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就像一顆鑽石,這愛的感受,不論放在誰的手上,是從誰的手中獻出,要送給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送—這鑽石本身是不變的,它的價值,也不會被這些外在因素所影響。」他滔滔不絕地繼續說。
David所深愛的靖君,年齡大他很多,且目前是已婚、有孩子的。因此,David是靖君婚姻中的第三者。他迫切地需要我了解,愛情是不受這些所影響的。人,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別人的眼光。來到心理治療室的診間,David也不例外。他擔心我會怎麼看他,這是可以理解的。
心理師的角色,是幫助病人了解自己
心理師也是人,當然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見。但是進入診間,必須要練習將自己的感受、理念,甚至道德觀,都放在門外,盡可能地持有開放、包容,不帶評論或價值觀地接受所面對的病人。這樣的切換,需要經驗以及有毅力的練習,不能假裝的。
人很敏感,對方是否誠心,是不是敷衍,有沒有偽裝,心中都是能感受到的。人與人互動時所顯露出的表情、肢體語言、聲調、語氣,那怕是很短暫或微小,都可能反映出內心真實的想法或感受。不過,包容歸包容,法規還是要遵循。
心理師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可以不用遵守保密原則:懷疑兒童被虐待,或認為病人極有可能傷害自己或他人,這時必須聯絡相關單位盡速處理。
這是法規與程序規定,但是就算遇到這種情況,除了要告知病人,並且遵循這些規定之外,我還是要保持不評斷、不批評他們。例如,我個人是如何看待自殺,或是虐待兒童的行為,這並不重要。
心理師的角色不是警察,也不是老師,而是幫助病人了解自己,克服心理相關的挑戰,達到想要的目標。當然,如果病人來找心理師的目的,是心理師不贊同或不接受的,心理師有權,也理當拒絕。例如,一個不認同同性親密伴侶的心理師,很難客觀地幫助病人釐清同性親密關係中的細節,或做同性伴侶的諮商,這時,通常就應該婉拒病人。有的時候,心理師的挑戰會來自於了解自己的能耐、偏見和底線。最怕的,是以為自己可以客觀,不帶偏見地為病人著想,以為自己可以接受病人的一切,卻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誤導了病人。
我想……首先,必須要降低David的不安,排除他對我是否能接受這些事實的疑慮。同時,我也需要迅速地評估自己是否願意,以及能夠做到接受這些外在條件,並且不讓它們影響我專注在David內心的痛苦與掙扎上。當下,我很快地初步評估後,認為我可以做到,所以應該能夠繼續。
「我了解你所說的感覺。愛情的感受是跨越任何的阻礙、本質不變的經歷。但聽起來,你很努力地想保護這段感情,深怕被別人所誤解了。別人的眼光,在你們的愛情中所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瞬間,David像是洩了氣的皮球,頭低了下去,彷彿是在跟自己說話:「其實,因為她現在已婚的狀態,我們沒有辦法像一般情侶一樣的交往,享受彼此的感情。只能在不影響目前生活的前提下,在不認識我們的人當中,或是私底下,才能在一起。唉,就算在不認識的人面前,我們的年齡差距也常讓別人……另眼相看。我實在不習慣這樣地被對待,好像要為我們的相愛感到抱歉,但同時卻也更讓我想要捍衛我們的關係,為我們爭取應有的權益。但是,我們面對的挑戰,還不只這些。」
David是在回台灣看家人的時候,有機會認識了靖君。兩人一開始也抗拒、掙扎了許久。就在David不知不覺之中,他回台灣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彼此通話的時間也不斷拉長,並且每次努力找機會見面時,就逐漸發現他們在生活中佔據彼此時間的比例持續升高,甚至到了好像已經不能沒有對方的地步了。
「我從來沒有這種感受過。以前看了會翻白眼的愛情情節,現在都是我的心聲!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我不是被沖昏頭,這是我想要的,她是我要的!」
我不禁笑了:「歡迎來到凡間。」
與病人的互動是很微妙的,非常動態,也是瞬息萬變的。一句開玩笑的話,對不同的人,或是對同一個人,但在不同時間點說出的反應都可能不一樣。我接著加了一句:「我想,我知道那種感受。」
愛的三角理論
愛情是什麼?心理學家斯騰伯格(Robert J.Sternberg)曾提出一個愛的三角理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如下頁圖),用一個三角形將愛分成了八種類型。這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分別代表著:激情(passion)、親密(intimacy)與承諾(commitment)。
「激情」就是性的渴望與需求,「親密」是心靈上的契合,「承諾」是對未來的預期有所保證。當一段感情中這三種都有,當然就是完整的愛(consummate love)。如果三種都沒有,就沒有愛(non-love)。
彼此只有心靈上的契合和親密(親近)感,是朋友間的喜歡。彼此只有激情,被歸類於迷戀(infatuation)。彼此只有承諾,則是空洞的愛(empty love)。如果有了親密和承諾,卻缺乏激情,斯騰伯格稱此為伴侶的愛(companionate love)。若激情加上承諾,卻沒有親密感的關係,例如,熱戀中彼此還不甚了解,卻突然決定閃電結婚的情侶/夫妻,被稱作愚昧的愛(fatuous love)。最後,若是同時擁有激情與親密,卻沒有承諾的愛,被稱之為浪漫的愛(romantic love),也就是愛情。
很明顯地,David戀愛了。但這段充滿激情與親密感的愛情,所帶給他的,不只是前所未有的好,卻也是未曾經歷過的苦,不然他今天不會坐在我的對面。他花了許多時間在捍衛自己的經歷與感受,也很在意別人的觀感,希望取得認同。我希望在讓他放心的同時,協助 David聚焦一下,慢慢回到驅使他尋求心理協助的誘因。
Learning of Love
愛情,所帶給你的,不只是前所未有的好,也可能是未曾經歷過的苦。
世俗框架
大環境的壓力,在不同人身上的影響力也可能不太一樣。
{星期一,上午十點}
「David,上週過的如何?」這好像是我慣用的開場白,但卻也是晤談的重要目的。畢竟每次會面時間只有短短的四十五分鐘,如何在暖身與過度寒暄之間取得平衡,也是一門功課。
「我真的很痛苦……」我感受得到他強烈的情緒,用直視他的眼光,以及我的表情和肢體語言,表達我在專心聆聽。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都相處得很融洽,非常的自然,像是天生就應該在一起。所有的默契、互動都很輕鬆,一點都不辛苦、不刻意。」我點頭,表示理解,同時準備好接下來他即將呈現出相應這一切不可思議的自然、無法想像的好,卻又讓他痛苦不堪的一面。
「問題出在我們以外的一切。」David用手撐住了頭,彷彿支撐不了他滿滿的煩惱。
靖君跟她先生其實已經貌合神離很久了。彼此各過各的生活,在平行沒有交集的婚姻之路上走了二十餘年。在這期間,身為典型的家庭主婦,該做的事靖君一樣也沒少做:準備一家人的三餐、顧孩子、認真持家之外,公婆處該打點的打點,需要幫忙的幫忙。本來她已經認命地接受這樣的生活,打算在小兒子唸大學後,再想想自己後半生要怎麼過。遇見David後的發展,是超乎她任何想像以外的經歷。
「我不懂,這樣的婚姻有什麼意義,有任何維持的必要嗎?」講到這裡,David激動了起來,但還是義正嚴詞、有條有理地表達他的想法。
「你們以外的問題,指的是靖君的婚姻?」我想確認一下他先前所表達的。
「主要是這空殼子婚姻,但還有很多延伸的相關議題,像周圍人的眼光跟期待,還有傳統、社會期許,這些世俗框架,把她束縛得動彈不得!」
把她束縛得動彈不得。這是David的看法,至於靖君是如何看待自己目前的狀態,我無從得知。但David似乎認為靖君是被目前的生活架構所侷限,因而無法活出自我。
David所謂的世俗框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社會的秩序與文化的傳承,都需要這個框架,更有許多人,因著這個框架才有安全感,才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該往那裡去。因此,靖君本身是否因為這個框架而感到動彈不得,還有待確認。
就生活與成長背景而言,David與靖君是很不同的。光是東、西方的差異,年齡的距離,通常就會把他們分為不同類型、不同族群的人。但是,他們的生命交集在相遇的那一個點上的時候,彼此所經歷的吸引力、愛與被愛,如David之前所說,是那麼地真實,那麼地寶貴,跟古今中外發生在任何情侶之間的愛情,沒有分別。
這段戀情,之後應該如何發展,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呢?我猜David一定已經想過了。我想定位出David的想法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這應該是造成他痛苦無助的主要因素。
「你可不可以為我描述一下,在你所想像中,在最理想的世界裡,你們的關係接下來應該是怎麼發展?五年,甚至十年後,你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基本上,David認為他跟靖君沒有理由不在一起。他的想法雖然單純,但也不是沒有道理。凡事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把情況用自己認可的方式呈現出來,有的時候是騙別人,有的時候也是騙自己……總之,自己都是有理的。我必須說,David的邏輯聽起來是通的。
靖君跟先生的婚姻形同虛設,沒有情感上的負擔。孩子也都大了,連小兒子也都要大學畢業了,已學著獨立,因此沒有養育或教養的問題。至於年齡……
「拜託喔!我都不想講這塊,這是什麼時代了?同性婚姻都有權利,尊重兩個獨立個體之間的愛與選擇,更何況,現在不是也流行所謂的姊弟戀?為了這個而分開,失去相愛相守的機會,不只是可惜,簡直是笑死人了!」David的回答,很符合我對他的了解與預期。
他接著說:「你問我對未來的預期,我認為她現在就應該跟家人攤牌。提不提我們的關係都無所謂。重點是要把這段沒有意義的婚姻,拿到檯面上來講清楚。這國王的新衣,應該被指出來。大家都有權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後,就離婚。不用等到你說的五年、十年、今年或明年,我們就應該可以在一起。託你的福,十年、十五年後,我們會繼續享受彼此的感情,過著比現在更滿足的生活。」託我的福……還真幽默,對一個小留學生來說,他的中文程度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好。
「David,我聽到你說的了:婚姻、孩子、年齡。這些是你所能想到,可能成為你們之間阻礙的因素。但你剛剛還有提到傳統跟社會期許,是什麼呢?」
別人的眼光。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大環境的壓力,在不同人身上的影響力也可能不太一樣。接下來,我想該聽聽靖君是怎麼說的,她的感受與想法又是什麼呢?如果他們的想法一致,甚至類似,今天David也不會坐在這裡,糾結著這些想不通、過不去的問題了。
差異,所擦出的火花
越不一樣的人,彼此的吸引力應該越高。
星期一,上午十點,地點:台灣,台北}
為了維繫與靖君的感情,David回台灣的次數越來越多。特別是在寒暑假,學校沒有課的時候,他幾乎都在台灣。家人很開心看到這樣的轉變,對他回台承接家業的可能,也表示樂觀。這週剛好我跟David同時都在台灣,所以他希望邀請靖君一起加入看診。
以心理師的觀點來說,我們有的時候會邀請病人身邊親近或相關的人來到診間,加入討論或治療。這時要注意的是,不要忘了我的病人才是主角,是主人。
自始至終,病人的福祉與安危是我最優先,也是最重要的考量。所有從一對一面談所延伸或轉換的方式,都是以對病人有益的角度為出發點。在這些前提的考量下,我同意David邀請靖君,趁我們三個人都在台灣的時候,加入David跟我的會談。
雖然已經聽David描述了許多,頭一次見到靖君,還是跟我的想像有些不一樣。她滿臉的笑容,讓人感到溫馨,並不如我所預期的拘謹。她的身形嬌小,與David瘦高的身材,有些差距。先不說相貌,兩人在裝扮上就明顯地有著東西方和年代上的差異:David從小在美國長大,穿著比較洋派、年輕。雖然已經在大學任教了,平常一件T恤、一條牛仔褲,配上球鞋的休閒打扮,很有可能讓人誤認他還是個大學生!相對地,靖君的穿著打扮顯得端莊、穩重。她穿戴得不浮誇,但當天所配戴的珍珠耳環、項鍊,背著的名牌包,給人的感覺就是一位很有品味的婦人。還沒開口,兩人身上所散發的氣息就很不同,年齡的差距也相當地明顯。但這些,顯然都沒有阻礙他們相戀、相愛。
戀愛的成因
在心理學的歷史上,不乏有研究上的嘗試,想要找出可以讓人戀愛的因素。在現實生活中,這是一個滿有商機的市場。從古至今,也不乏想要左右別人戀愛對象的企圖。但是到現在,我們仍舊無法預測,更別說去控制,誰會愛上誰了。不過,人是生物,生物的基本需求是要生存。有些人會說,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戀愛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繁殖後代。根據演化的理論,基因相同度高(近親)交配所產生的後代,存活率較低。相對來說,基因相同度低(血緣關係遠)交配所產生的後代,在各方面都會比較強健,存活率較高。
在一九九五年,有位瑞士的生物學家,使用了一種與免疫系統相關的基因集來做研究。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基因(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它的主要功能是幫助免疫系統辨別敵我,分辨哪些是自己的細胞,哪些是不屬於自己,需要攻擊的外來生物。此項研究對象包含了四十九位女性,以及四十四位男性。在研究一開始的時候,就收集了受試者 MHC 基因的分析資料。研究者為男性提供了T恤,以及無味的肥皂與刮鬍水,並且指導男性受試者在接下來的兩天當中,都要穿這件同樣的T恤,使用所提供的肥皂與刮鬍水,並且盡量保持「原味」,不要用古龍水或其他有味道的產品。兩天後,請男性受試者把T恤帶回實驗室。實驗者將這些有汗味的衣服放進了紙箱中,紙箱上方開有一個小孔。
之後,每一位女性受試者會拿到不同組合的箱子,並且要從箱子的小孔中聞箱子內的氣味。這些箱子裡包括與女性受試者本身 MHC 基因相差最遠的男性受試者穿過的T恤,還有與女性受試者本身 MHC 基因最相近的,以及一個沒有被穿過的新T恤做為控制組。在聞過不同的箱子後,女性受試者要回報自己比較喜歡哪個箱子的味道,願意跟那一個箱子的主人交往。
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女性受試者都選擇了 MHC 基因與自己最遠的味道,有些甚至說這味道讓她們想起了自己的男友(前任或現任都有)。
嗅覺系統是我們五個感官中唯一一個不需要經過視丘(thalamus)的處理,就可以直接將訊息傳達到前腦的感官。嗅覺所接收到的訊息可以直接與情緒和記憶產生連結,也是感官中最原始的一個。想必,這樣的獨特性在演化、生存、擇偶與繁殖的環節中,承擔著重要任務,讓它具有直覺反應,能以抄捷徑的方式迅速傳達訊息的功能。
根據這項研究,越不一樣的人,彼此的吸引力應該越高。
那……為什麼我對眼前這一對相戀的情侶,還是有很納悶的感覺,不是那麼自然而然可以接受呢?很慚愧地,他們之間的差異,不禁讓我想到這其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會不會是什麼騙局,有什麼目的?
別人未必要懂得我們,才能做出好的建議
坐下來後,靖君緩緩地說出她的感受與看法。除了外觀,他們的性格和人際互動模式也截然不同。David急切又強勢,靖君柔中帶剛;David主要是邏輯導向,靖君凡事憑感覺,不愛講「那些大衛喜歡說的大道理」。大衛,她是這麼稱呼他的,我覺得有點可愛。
「遇見大衛是在偶然的朋友聚會中。我沒有辦法解釋,第一眼就覺得他不一樣。我是個很傳統、很認命的人。婚姻中的無奈,讓我學習到平淡的珍貴。當你嘗過煎熬的日子,就會知道平淡不是婚姻中最糟糕的事……當你經過毫無盼望的深淵,就會知道沒有期待不是人生中最深切的悲哀。」
在她優雅、沉靜外表的背後,到底有著什麼樣的遭遇,隱藏了多少的悲哀?
「但是」,她繼續輕聲細語,用我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跟大衛在一起的熟悉感是前所未有的。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幾乎不用言語。這是我從未有過的感受。我的反應完全不受控制,無法自拔。這一切是多麼地離經叛道,有多少不堪入耳的名詞可以用來形容我,我的作為?這些,不用別人告訴我,我很清楚。但是我別無選擇,我沒有辦法控制。」靖君從我手中拿了我遞給她的面紙,卻擋不住不斷流出的眼淚。
靖君說,她了解大衛的「理性邏輯」、「大道理」,但覺得大衛基本上是個外國人,對傳統觀念不熟悉,也無法體會它的重要性。雖然靖君也坦承目前的婚姻只流於生活上的形式,丈夫因工作關係經常出差在外,有時候一個月當中也見不上幾次面。但是這形式,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除了這些大衛所謂的形式以外,她還有責任,對公婆、長輩以及孩子們的責任。要捨棄這些,對她而言是難以想像,也做不到的事。
「這……這簡直是不可理喻!」David急得快跳起來了。
「公婆的關係是因為婚姻才有,怎麼可以又回過來,用公婆為理由來維持這段婚姻?根本是circular argument(循環論證)。如果所謂的長輩,是自己的父母,那更沒道理了,他們難道不希望你快樂嗎?再來,孩子們都已經成年了,他們會需要你多久?他們不希望你快樂嗎?」
David的科學邏輯訓練、西方文化教育,又強烈地呈現出來。當下,我忽然有點擔心,不知道靖君對大衛所說的理解多少?
顯然他們之間類似的對話,似乎已經有過很多次了。
「我說了,你不了解傳統文化,你沒結過婚,更沒有孩子,這種感受你不懂,我也說不清楚。」
靖君輕描淡寫的兩句話,確實是將了大衛一軍啊!
這類型的論證,我其實很不贊同,因為它很不公平,也會像煞車一樣,讓對話中止:「你沒有經歷過……所以不會了解……」
當別人的想法或意見跟我們不一樣的時候,並不一定代表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的難處,或因為他們不能體會,才會強人所難。有沒有可能,別人是對的?他們不一定需要體會我們的感受,才能做出好的建議。
好比一位醫生,針對病人的疾患開藥,並且確定這個藥可以有效治療這個疾病,但這藥卻非常難吃,難以下嚥……病人可能會說:「你沒得過這病,不知道它為我帶來的痛苦,你也沒吃過這藥,不知道它有多難吃!」這兩個抱怨可能都是正確的:醫生沒經歷過這病痛,也沒吃過這種藥,但這卻不影響醫生提供了有價值的建議—這可以讓你藥到病除!做對的事,提供正確的建議,不一定容易,感覺也不一定好受。但如果把感受與對錯混為一談,不但會模糊焦點,更會阻礙交流。這樣的溝通不僅是效率低、沒有交集,更是難以達到共識。
他們是如此地不同,讓我不禁懷疑這段感情的真實性,懷疑這有沒有可能是個騙局?但是騙局是要有目的的,是誰要騙誰?David有什麼是靖君可能想要的?錢財、地位、美國公民?不對,他們的問題癥結,就是靖君不要這些!那靖君有什麼會是David想要騙的?錢財、地位、台灣身分證?最後一項David已經有了,前面兩項,一旦靖君如David所求地離了婚,她就會幾乎失去一切,更何況,David本身家庭很富裕,自己的工作穩定,也有不錯的社會經濟地位。這是騙局的可能性很低。我只能說,他們似乎愛得很深,卻各有堅持。
靖君那邊看來也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我的病人是David,我得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靖君加入我們這次晤談,有助於我直接了解與評估她的想法、訴求和感受,不用經過David的轉述,同時也讓我了解David面對的是什麼情況。
在目前的狀況下,靖君很清楚地表達,她無法如大衛所想、所要求地跟先生離婚,與大衛開始新的生活。在確認David所處的外在環境與各種限制後,他可能有哪些選擇?他想做、能做的又是什麼?這是我們接下來需要釐清的。
信任不是要來的,是要證明自己是可以被信賴的。
{星期一,上午十點}
今天問診的病人是王建昇,David Wang。在進到候診間見到這位病人之前,當然也按例通過電話。但我跟這位初診病患的電話對談,卻比平常簡短了許多。
「你好,我是在網路上找到你的。看過了你的簡介,覺得應該很合適。我只是想請教你三個問題。」他很有禮貌,講話清楚直接,不浪費時間。
「好的,請說。」聆聽,是心理師的基本功,當對方願意說的時候,一切都是我的線索。
「第一,網站上寫著你有收我這家公司的醫療保險,想跟你確認這點。第二,想請問你的治療學派、個人理念,以及常用的方式,第三,請問你會說國語嗎?謝謝你。」
我常想,不只是心理師,其實在許多的行業中,特別是服務業,聆聽的訓練都是很重要的。
這位王先生顯然做過功課,有很具體的需求,如果這時我很制式化地向他用我慣用的方式從頭介紹,可能會讓他覺得答非所問,抓不到他的重點。不過他的第二個問題,好像是隨堂抽考,讓我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要辨別跟解釋不同的心理學派,好在這次我只要介紹我所熟悉的認知行為療法就可以了。
想必我在電話中的回答都一一過了關,他希望約診,也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基本資料,我們就約了第一次的門診。
到了他約診的時間,我走出辦公室,進入候診間,我的目光在抬起頭看我的人當中很快地掃了一圈。一位年輕的華裔男子站了起來。
「David?」我問。他點點頭,跟著我進了辦公室。
他在長沙發上坐了下來,建昇個子不高,大概一百七十多公分,瘦瘦的,有雙深邃卻靈活的大眼睛。在紐約的初秋,他穿了一件淺色襯衫和卡其色的褲子。他外表給人整體的感覺是乾淨、整齊,態度上有點急切,表達能力很好,行為上顯得有些拘束。
建昇來自台灣,國中畢業後到美國唸書,大學從著名的長春藤名校完成了主修電機的學士學位。畢業後他很快地在一家知名公司找到工作,幾年後也升到了主管的位置。在台灣的父母,對他的成就感到非常地欣慰與驕傲,家族企業中的上上下下,也沒有人不知道這位優秀的少爺。
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建昇越來越覺得他的志向並不在此,反而對人、對心理、對哲學更感興趣。漸漸發現自己對這方面的嚮往,大過於只是興趣而已。於是組織能力、執行力與行動力都很強的他,就做了許多功課,最後毅然決然地辭去了原本高薪高位的工作,進入了另一所長春藤名校,攻讀臨床心理學的博士學位。
這位來自台灣的同學還真的不是普通的優秀……在美國,臨床心理學的博士班是非常難進的,錄取率比有些醫學院還難,平均約在百分之四上下。更別說是從電機那麼遠的領域跨過來,就是心理系一路唸上來的學生,要進臨床心理博士班也不是容易的事。五年後,他順利地拿到了博士學位,在完成實習後,又被知名大學錄取,成為助理教授,同時也在附近開業,開始看病人了。他是一位臨床心理師。
原來是同行?難怪,電話約診中所問的問題是如此聚焦。
相信,才能開啟對話
「我實在是沒辦法了!碰到了難題,靠我自己,解決不了。但是來找你,總覺得你要做什麼,我都一清二楚,下一步要怎麼做,我也想得到。會有什麼新東西、新想法、新解答嗎?」他眉頭深鎖,看來是真心地糾結……
「嗯,但你還是來了。而且這應該不是一時衝動的結果,因為你還花時間做了功課,把想法付諸行動地打了電話,約了時間,最後,人也來了。」
他的大眼睛轉啊轉地說:「我……該從何開始呢?」
「可以從現在在你腦袋裡的東西開始。」我感受到他的焦慮與無助。
「啊?我不用組織一下,介紹前因後果,提供一下背景因素?」他似乎有點驚訝。
「不需要吧,那樣不是會有點累?你需要負擔那麼重嗎?你來這裡,只要放輕鬆,把你心中的事情、想法、感受,想講的都可以講出來,其他的工作,是我要做的,不是嗎?」
他看起來還是不太放心。
本來靠著椅背的我,坐起來,上身向前傾,縮短了我們的距離,眼睛直視著他:「David,以心理師對心理師的立場,我想問你,你覺得在心理治療跟諮商的互動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想都不想地說:「信任,我通常都要求病人要信任我……」他停頓了一下,我知道他還沒說完,「但是信任不是要來的,或是可以給的,是要證明自己是可以被信賴的」,他振振有詞,說的都沒錯。
「在面對病人時,我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我受過正當嚴格的訓練,也累積了相當的經驗,是可以被病人信任的。」他繼續說著,是個很有自信的年輕人。
我一面聽,一面點著頭。
「相信你今天到這來,也是做過一番功課,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認為我的訓練跟經驗可以被你接受。那如果我說,我也相信自己,對我的專業能力、經歷,也很有信心……這有幫助嗎?可以換取你的信任嗎?」
我看得出,他很用力地在想。
我接著問:「你也聽過『leap of faith』這句話—信心的飛躍,你認為,為什麼要用飛躍來形容?腳踏實地走過去不就好了,要用飛的?」
他想了很久。
我耐心地等待,觀察他的面部表情。
「如果等到事實、證據,都收集齊全了,就不用信賴,用證實就可以了。那時候,就不用飛躍。但那也不叫faith了。」
我點點頭,「這樣講得通。所以……faith可能是在還不確定,甚至不知道的情況下,作一個選擇……」我還沒說完,David 就接下去說:「選擇相信?」
我揚了揚眉毛,歪著頭,做出了或許的表示。
面對這位優秀又自信的年輕人,想必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別人叫他做什麼,或者給他答案。
建昇,這位來自台灣的臨床心理師,想了想,突然鬆了一口氣,挺直的腰桿也鬆懈了下來,往後面的沙發背一靠,眼睛看著我說:「OK。」
這是一種信任。
也是一個我可以接受的開始。
Learning of Love
聆聽,是心理師的基本功,當對方願意說的時候,一切都是我的線索。
愛情,不需要道理
愛情猶如鑽石,它的價值,不會被外在因素所影響。
{星期一,上午十點}
「一直以來,我都以為我是個懂得用別人的角度看事情的人,很能體會別人的感受。我也算是個懂得如何溝通,讓別人可以理解我所要表達訊息的人。但是,在我碰到一生當中最愛的人時,我卻發現,雙方竟然如此地不能溝通,根本就是無解!」David長期以來的自我認知,好像受到了挑戰,對方是他愛的人,不對,是他最愛的人。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這位王心理師David,認識了靖君。一向理性的David告訴我,他第一次親身經歷到愛情是毫無道理可言的。靖君不僅長他十多歲,且為人妻,還育有一兒一女,是一位母親。她與David幾乎就是一見鍾情。
「我發現,愛情,雖然沒有道理,卻是universal的,是人的共性。在不同文化、環境、背景下的人,不論愛的對象是誰,經歷愛情的感受都是一樣的。愛情本身,它的本質是一樣的。」他好像深怕我會評論他對靖君的愛情,很努力地在辯解,在針對一個假想敵對他所做出的控訴,辯解。
「你看,古今中外,不論是文學、詩詞、歌曲,或是時事新聞,不乏各式各樣的愛情故事。同性的、異性的,已婚、未婚的,大家看好的,時代不允許的……但每一個故事,每一段愛情,當事人本身所經歷的感受,如果去掉這些外在因素的不同,其實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就像一顆鑽石,這愛的感受,不論放在誰的手上,是從誰的手中獻出,要送給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送—這鑽石本身是不變的,它的價值,也不會被這些外在因素所影響。」他滔滔不絕地繼續說。
David所深愛的靖君,年齡大他很多,且目前是已婚、有孩子的。因此,David是靖君婚姻中的第三者。他迫切地需要我了解,愛情是不受這些所影響的。人,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別人的眼光。來到心理治療室的診間,David也不例外。他擔心我會怎麼看他,這是可以理解的。
心理師的角色,是幫助病人了解自己
心理師也是人,當然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見。但是進入診間,必須要練習將自己的感受、理念,甚至道德觀,都放在門外,盡可能地持有開放、包容,不帶評論或價值觀地接受所面對的病人。這樣的切換,需要經驗以及有毅力的練習,不能假裝的。
人很敏感,對方是否誠心,是不是敷衍,有沒有偽裝,心中都是能感受到的。人與人互動時所顯露出的表情、肢體語言、聲調、語氣,那怕是很短暫或微小,都可能反映出內心真實的想法或感受。不過,包容歸包容,法規還是要遵循。
心理師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可以不用遵守保密原則:懷疑兒童被虐待,或認為病人極有可能傷害自己或他人,這時必須聯絡相關單位盡速處理。
這是法規與程序規定,但是就算遇到這種情況,除了要告知病人,並且遵循這些規定之外,我還是要保持不評斷、不批評他們。例如,我個人是如何看待自殺,或是虐待兒童的行為,這並不重要。
心理師的角色不是警察,也不是老師,而是幫助病人了解自己,克服心理相關的挑戰,達到想要的目標。當然,如果病人來找心理師的目的,是心理師不贊同或不接受的,心理師有權,也理當拒絕。例如,一個不認同同性親密伴侶的心理師,很難客觀地幫助病人釐清同性親密關係中的細節,或做同性伴侶的諮商,這時,通常就應該婉拒病人。有的時候,心理師的挑戰會來自於了解自己的能耐、偏見和底線。最怕的,是以為自己可以客觀,不帶偏見地為病人著想,以為自己可以接受病人的一切,卻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誤導了病人。
我想……首先,必須要降低David的不安,排除他對我是否能接受這些事實的疑慮。同時,我也需要迅速地評估自己是否願意,以及能夠做到接受這些外在條件,並且不讓它們影響我專注在David內心的痛苦與掙扎上。當下,我很快地初步評估後,認為我可以做到,所以應該能夠繼續。
「我了解你所說的感覺。愛情的感受是跨越任何的阻礙、本質不變的經歷。但聽起來,你很努力地想保護這段感情,深怕被別人所誤解了。別人的眼光,在你們的愛情中所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瞬間,David像是洩了氣的皮球,頭低了下去,彷彿是在跟自己說話:「其實,因為她現在已婚的狀態,我們沒有辦法像一般情侶一樣的交往,享受彼此的感情。只能在不影響目前生活的前提下,在不認識我們的人當中,或是私底下,才能在一起。唉,就算在不認識的人面前,我們的年齡差距也常讓別人……另眼相看。我實在不習慣這樣地被對待,好像要為我們的相愛感到抱歉,但同時卻也更讓我想要捍衛我們的關係,為我們爭取應有的權益。但是,我們面對的挑戰,還不只這些。」
David是在回台灣看家人的時候,有機會認識了靖君。兩人一開始也抗拒、掙扎了許久。就在David不知不覺之中,他回台灣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彼此通話的時間也不斷拉長,並且每次努力找機會見面時,就逐漸發現他們在生活中佔據彼此時間的比例持續升高,甚至到了好像已經不能沒有對方的地步了。
「我從來沒有這種感受過。以前看了會翻白眼的愛情情節,現在都是我的心聲!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我不是被沖昏頭,這是我想要的,她是我要的!」
我不禁笑了:「歡迎來到凡間。」
與病人的互動是很微妙的,非常動態,也是瞬息萬變的。一句開玩笑的話,對不同的人,或是對同一個人,但在不同時間點說出的反應都可能不一樣。我接著加了一句:「我想,我知道那種感受。」
愛的三角理論
愛情是什麼?心理學家斯騰伯格(Robert J.Sternberg)曾提出一個愛的三角理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如下頁圖),用一個三角形將愛分成了八種類型。這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分別代表著:激情(passion)、親密(intimacy)與承諾(commitment)。
「激情」就是性的渴望與需求,「親密」是心靈上的契合,「承諾」是對未來的預期有所保證。當一段感情中這三種都有,當然就是完整的愛(consummate love)。如果三種都沒有,就沒有愛(non-love)。
彼此只有心靈上的契合和親密(親近)感,是朋友間的喜歡。彼此只有激情,被歸類於迷戀(infatuation)。彼此只有承諾,則是空洞的愛(empty love)。如果有了親密和承諾,卻缺乏激情,斯騰伯格稱此為伴侶的愛(companionate love)。若激情加上承諾,卻沒有親密感的關係,例如,熱戀中彼此還不甚了解,卻突然決定閃電結婚的情侶/夫妻,被稱作愚昧的愛(fatuous love)。最後,若是同時擁有激情與親密,卻沒有承諾的愛,被稱之為浪漫的愛(romantic love),也就是愛情。
很明顯地,David戀愛了。但這段充滿激情與親密感的愛情,所帶給他的,不只是前所未有的好,卻也是未曾經歷過的苦,不然他今天不會坐在我的對面。他花了許多時間在捍衛自己的經歷與感受,也很在意別人的觀感,希望取得認同。我希望在讓他放心的同時,協助 David聚焦一下,慢慢回到驅使他尋求心理協助的誘因。
Learning of Love
愛情,所帶給你的,不只是前所未有的好,也可能是未曾經歷過的苦。
世俗框架
大環境的壓力,在不同人身上的影響力也可能不太一樣。
{星期一,上午十點}
「David,上週過的如何?」這好像是我慣用的開場白,但卻也是晤談的重要目的。畢竟每次會面時間只有短短的四十五分鐘,如何在暖身與過度寒暄之間取得平衡,也是一門功課。
「我真的很痛苦……」我感受得到他強烈的情緒,用直視他的眼光,以及我的表情和肢體語言,表達我在專心聆聽。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都相處得很融洽,非常的自然,像是天生就應該在一起。所有的默契、互動都很輕鬆,一點都不辛苦、不刻意。」我點頭,表示理解,同時準備好接下來他即將呈現出相應這一切不可思議的自然、無法想像的好,卻又讓他痛苦不堪的一面。
「問題出在我們以外的一切。」David用手撐住了頭,彷彿支撐不了他滿滿的煩惱。
靖君跟她先生其實已經貌合神離很久了。彼此各過各的生活,在平行沒有交集的婚姻之路上走了二十餘年。在這期間,身為典型的家庭主婦,該做的事靖君一樣也沒少做:準備一家人的三餐、顧孩子、認真持家之外,公婆處該打點的打點,需要幫忙的幫忙。本來她已經認命地接受這樣的生活,打算在小兒子唸大學後,再想想自己後半生要怎麼過。遇見David後的發展,是超乎她任何想像以外的經歷。
「我不懂,這樣的婚姻有什麼意義,有任何維持的必要嗎?」講到這裡,David激動了起來,但還是義正嚴詞、有條有理地表達他的想法。
「你們以外的問題,指的是靖君的婚姻?」我想確認一下他先前所表達的。
「主要是這空殼子婚姻,但還有很多延伸的相關議題,像周圍人的眼光跟期待,還有傳統、社會期許,這些世俗框架,把她束縛得動彈不得!」
把她束縛得動彈不得。這是David的看法,至於靖君是如何看待自己目前的狀態,我無從得知。但David似乎認為靖君是被目前的生活架構所侷限,因而無法活出自我。
David所謂的世俗框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社會的秩序與文化的傳承,都需要這個框架,更有許多人,因著這個框架才有安全感,才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該往那裡去。因此,靖君本身是否因為這個框架而感到動彈不得,還有待確認。
就生活與成長背景而言,David與靖君是很不同的。光是東、西方的差異,年齡的距離,通常就會把他們分為不同類型、不同族群的人。但是,他們的生命交集在相遇的那一個點上的時候,彼此所經歷的吸引力、愛與被愛,如David之前所說,是那麼地真實,那麼地寶貴,跟古今中外發生在任何情侶之間的愛情,沒有分別。
這段戀情,之後應該如何發展,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呢?我猜David一定已經想過了。我想定位出David的想法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這應該是造成他痛苦無助的主要因素。
「你可不可以為我描述一下,在你所想像中,在最理想的世界裡,你們的關係接下來應該是怎麼發展?五年,甚至十年後,你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基本上,David認為他跟靖君沒有理由不在一起。他的想法雖然單純,但也不是沒有道理。凡事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把情況用自己認可的方式呈現出來,有的時候是騙別人,有的時候也是騙自己……總之,自己都是有理的。我必須說,David的邏輯聽起來是通的。
靖君跟先生的婚姻形同虛設,沒有情感上的負擔。孩子也都大了,連小兒子也都要大學畢業了,已學著獨立,因此沒有養育或教養的問題。至於年齡……
「拜託喔!我都不想講這塊,這是什麼時代了?同性婚姻都有權利,尊重兩個獨立個體之間的愛與選擇,更何況,現在不是也流行所謂的姊弟戀?為了這個而分開,失去相愛相守的機會,不只是可惜,簡直是笑死人了!」David的回答,很符合我對他的了解與預期。
他接著說:「你問我對未來的預期,我認為她現在就應該跟家人攤牌。提不提我們的關係都無所謂。重點是要把這段沒有意義的婚姻,拿到檯面上來講清楚。這國王的新衣,應該被指出來。大家都有權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後,就離婚。不用等到你說的五年、十年、今年或明年,我們就應該可以在一起。託你的福,十年、十五年後,我們會繼續享受彼此的感情,過著比現在更滿足的生活。」託我的福……還真幽默,對一個小留學生來說,他的中文程度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好。
「David,我聽到你說的了:婚姻、孩子、年齡。這些是你所能想到,可能成為你們之間阻礙的因素。但你剛剛還有提到傳統跟社會期許,是什麼呢?」
別人的眼光。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大環境的壓力,在不同人身上的影響力也可能不太一樣。接下來,我想該聽聽靖君是怎麼說的,她的感受與想法又是什麼呢?如果他們的想法一致,甚至類似,今天David也不會坐在這裡,糾結著這些想不通、過不去的問題了。
差異,所擦出的火花
越不一樣的人,彼此的吸引力應該越高。
星期一,上午十點,地點:台灣,台北}
為了維繫與靖君的感情,David回台灣的次數越來越多。特別是在寒暑假,學校沒有課的時候,他幾乎都在台灣。家人很開心看到這樣的轉變,對他回台承接家業的可能,也表示樂觀。這週剛好我跟David同時都在台灣,所以他希望邀請靖君一起加入看診。
以心理師的觀點來說,我們有的時候會邀請病人身邊親近或相關的人來到診間,加入討論或治療。這時要注意的是,不要忘了我的病人才是主角,是主人。
自始至終,病人的福祉與安危是我最優先,也是最重要的考量。所有從一對一面談所延伸或轉換的方式,都是以對病人有益的角度為出發點。在這些前提的考量下,我同意David邀請靖君,趁我們三個人都在台灣的時候,加入David跟我的會談。
雖然已經聽David描述了許多,頭一次見到靖君,還是跟我的想像有些不一樣。她滿臉的笑容,讓人感到溫馨,並不如我所預期的拘謹。她的身形嬌小,與David瘦高的身材,有些差距。先不說相貌,兩人在裝扮上就明顯地有著東西方和年代上的差異:David從小在美國長大,穿著比較洋派、年輕。雖然已經在大學任教了,平常一件T恤、一條牛仔褲,配上球鞋的休閒打扮,很有可能讓人誤認他還是個大學生!相對地,靖君的穿著打扮顯得端莊、穩重。她穿戴得不浮誇,但當天所配戴的珍珠耳環、項鍊,背著的名牌包,給人的感覺就是一位很有品味的婦人。還沒開口,兩人身上所散發的氣息就很不同,年齡的差距也相當地明顯。但這些,顯然都沒有阻礙他們相戀、相愛。
戀愛的成因
在心理學的歷史上,不乏有研究上的嘗試,想要找出可以讓人戀愛的因素。在現實生活中,這是一個滿有商機的市場。從古至今,也不乏想要左右別人戀愛對象的企圖。但是到現在,我們仍舊無法預測,更別說去控制,誰會愛上誰了。不過,人是生物,生物的基本需求是要生存。有些人會說,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戀愛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繁殖後代。根據演化的理論,基因相同度高(近親)交配所產生的後代,存活率較低。相對來說,基因相同度低(血緣關係遠)交配所產生的後代,在各方面都會比較強健,存活率較高。
在一九九五年,有位瑞士的生物學家,使用了一種與免疫系統相關的基因集來做研究。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基因(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它的主要功能是幫助免疫系統辨別敵我,分辨哪些是自己的細胞,哪些是不屬於自己,需要攻擊的外來生物。此項研究對象包含了四十九位女性,以及四十四位男性。在研究一開始的時候,就收集了受試者 MHC 基因的分析資料。研究者為男性提供了T恤,以及無味的肥皂與刮鬍水,並且指導男性受試者在接下來的兩天當中,都要穿這件同樣的T恤,使用所提供的肥皂與刮鬍水,並且盡量保持「原味」,不要用古龍水或其他有味道的產品。兩天後,請男性受試者把T恤帶回實驗室。實驗者將這些有汗味的衣服放進了紙箱中,紙箱上方開有一個小孔。
之後,每一位女性受試者會拿到不同組合的箱子,並且要從箱子的小孔中聞箱子內的氣味。這些箱子裡包括與女性受試者本身 MHC 基因相差最遠的男性受試者穿過的T恤,還有與女性受試者本身 MHC 基因最相近的,以及一個沒有被穿過的新T恤做為控制組。在聞過不同的箱子後,女性受試者要回報自己比較喜歡哪個箱子的味道,願意跟那一個箱子的主人交往。
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女性受試者都選擇了 MHC 基因與自己最遠的味道,有些甚至說這味道讓她們想起了自己的男友(前任或現任都有)。
嗅覺系統是我們五個感官中唯一一個不需要經過視丘(thalamus)的處理,就可以直接將訊息傳達到前腦的感官。嗅覺所接收到的訊息可以直接與情緒和記憶產生連結,也是感官中最原始的一個。想必,這樣的獨特性在演化、生存、擇偶與繁殖的環節中,承擔著重要任務,讓它具有直覺反應,能以抄捷徑的方式迅速傳達訊息的功能。
根據這項研究,越不一樣的人,彼此的吸引力應該越高。
那……為什麼我對眼前這一對相戀的情侶,還是有很納悶的感覺,不是那麼自然而然可以接受呢?很慚愧地,他們之間的差異,不禁讓我想到這其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會不會是什麼騙局,有什麼目的?
別人未必要懂得我們,才能做出好的建議
坐下來後,靖君緩緩地說出她的感受與看法。除了外觀,他們的性格和人際互動模式也截然不同。David急切又強勢,靖君柔中帶剛;David主要是邏輯導向,靖君凡事憑感覺,不愛講「那些大衛喜歡說的大道理」。大衛,她是這麼稱呼他的,我覺得有點可愛。
「遇見大衛是在偶然的朋友聚會中。我沒有辦法解釋,第一眼就覺得他不一樣。我是個很傳統、很認命的人。婚姻中的無奈,讓我學習到平淡的珍貴。當你嘗過煎熬的日子,就會知道平淡不是婚姻中最糟糕的事……當你經過毫無盼望的深淵,就會知道沒有期待不是人生中最深切的悲哀。」
在她優雅、沉靜外表的背後,到底有著什麼樣的遭遇,隱藏了多少的悲哀?
「但是」,她繼續輕聲細語,用我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跟大衛在一起的熟悉感是前所未有的。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幾乎不用言語。這是我從未有過的感受。我的反應完全不受控制,無法自拔。這一切是多麼地離經叛道,有多少不堪入耳的名詞可以用來形容我,我的作為?這些,不用別人告訴我,我很清楚。但是我別無選擇,我沒有辦法控制。」靖君從我手中拿了我遞給她的面紙,卻擋不住不斷流出的眼淚。
靖君說,她了解大衛的「理性邏輯」、「大道理」,但覺得大衛基本上是個外國人,對傳統觀念不熟悉,也無法體會它的重要性。雖然靖君也坦承目前的婚姻只流於生活上的形式,丈夫因工作關係經常出差在外,有時候一個月當中也見不上幾次面。但是這形式,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除了這些大衛所謂的形式以外,她還有責任,對公婆、長輩以及孩子們的責任。要捨棄這些,對她而言是難以想像,也做不到的事。
「這……這簡直是不可理喻!」David急得快跳起來了。
「公婆的關係是因為婚姻才有,怎麼可以又回過來,用公婆為理由來維持這段婚姻?根本是circular argument(循環論證)。如果所謂的長輩,是自己的父母,那更沒道理了,他們難道不希望你快樂嗎?再來,孩子們都已經成年了,他們會需要你多久?他們不希望你快樂嗎?」
David的科學邏輯訓練、西方文化教育,又強烈地呈現出來。當下,我忽然有點擔心,不知道靖君對大衛所說的理解多少?
顯然他們之間類似的對話,似乎已經有過很多次了。
「我說了,你不了解傳統文化,你沒結過婚,更沒有孩子,這種感受你不懂,我也說不清楚。」
靖君輕描淡寫的兩句話,確實是將了大衛一軍啊!
這類型的論證,我其實很不贊同,因為它很不公平,也會像煞車一樣,讓對話中止:「你沒有經歷過……所以不會了解……」
當別人的想法或意見跟我們不一樣的時候,並不一定代表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的難處,或因為他們不能體會,才會強人所難。有沒有可能,別人是對的?他們不一定需要體會我們的感受,才能做出好的建議。
好比一位醫生,針對病人的疾患開藥,並且確定這個藥可以有效治療這個疾病,但這藥卻非常難吃,難以下嚥……病人可能會說:「你沒得過這病,不知道它為我帶來的痛苦,你也沒吃過這藥,不知道它有多難吃!」這兩個抱怨可能都是正確的:醫生沒經歷過這病痛,也沒吃過這種藥,但這卻不影響醫生提供了有價值的建議—這可以讓你藥到病除!做對的事,提供正確的建議,不一定容易,感覺也不一定好受。但如果把感受與對錯混為一談,不但會模糊焦點,更會阻礙交流。這樣的溝通不僅是效率低、沒有交集,更是難以達到共識。
他們是如此地不同,讓我不禁懷疑這段感情的真實性,懷疑這有沒有可能是個騙局?但是騙局是要有目的的,是誰要騙誰?David有什麼是靖君可能想要的?錢財、地位、美國公民?不對,他們的問題癥結,就是靖君不要這些!那靖君有什麼會是David想要騙的?錢財、地位、台灣身分證?最後一項David已經有了,前面兩項,一旦靖君如David所求地離了婚,她就會幾乎失去一切,更何況,David本身家庭很富裕,自己的工作穩定,也有不錯的社會經濟地位。這是騙局的可能性很低。我只能說,他們似乎愛得很深,卻各有堅持。
靖君那邊看來也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我的病人是David,我得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靖君加入我們這次晤談,有助於我直接了解與評估她的想法、訴求和感受,不用經過David的轉述,同時也讓我了解David面對的是什麼情況。
在目前的狀況下,靖君很清楚地表達,她無法如大衛所想、所要求地跟先生離婚,與大衛開始新的生活。在確認David所處的外在環境與各種限制後,他可能有哪些選擇?他想做、能做的又是什麼?這是我們接下來需要釐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