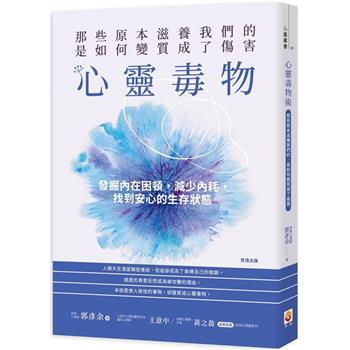付出努力後,都渴望能被看見、重視與鼓勵。
當渴望落空,付出與努力一再換來輕忽、無視、冷漠,甚至是苛責時,就會慢慢產生質變,成為毀天滅地的武器⋯⋯
如果不能及時踩住煞車,中斷惡性循環,這些原有的美好付出與努力,
最終都將可能成為吞噬自己與他人的地獄⋯⋯
從好脾氣變成充滿憤怒的地獄入口?
「溫良恭儉讓」生活運作模式的原型—沙林的故事前篇
「我是沙林,因為隨機傷人被捕。」
高中以前,我各項表現都名列前茅,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
同學眼中的我,是個開朗、搞笑、脾氣好的樂天派。也是班上的領導者、意見領袖。家人也以我為榮。
家人事業繁忙,因此我從小就自律,從不任性發脾氣,不讓他們擔心。
家人期待我繼承家業,希望我未來就讀相關科系,但我對家族事業一點興趣都沒有,完全不想繼承家業。想要靠自己的力量,開創自己的天地。
不過家人很堅持,我也不想讓他們失望,畢竟他們提供了我優渥的生長環境,工作也很辛苦。因此勉強選了家人期待的大學科系就讀。
進到大學後,因為對該科系所學內容完全沒有興趣,排名墊底,讀得非常辛苦。
看著同學們熱切地討論所學專業,對未來高談闊論,只有我感到迷惘。
我再也不是過去同學眼中開朗樂觀的領袖了,反而成了常常翹課、窩在宿舍睡覺、打電動的邊緣人。課堂上分組時,同學都很害怕跟我分到同組,因為我從不出席分組討論,大家都對我敬而遠之。
「沒差啦!無所謂!」我笑著對自己說。
當不及格的成績單寄到家裡,家人看著成績單不發一語。但我從他們眼裡看到了滿滿的失望。隔了一陣子,我因為太多科目不及格而被退學了。
退學後,家人拿了幾分大學考試報名資訊給我,讓我重考。
於是,我又考進了跟家業相關但完全不感興趣的科系。然後,再次成為班上的邊緣人。依然翹課、窩在宿舍睡覺、打電動。
除此之外,我也會寫些犯罪殺人小說並發表在網路上,排遣鬱悶的心情。
有天,我在社群網站看到高中好友們即將畢業的消息。他們非常開心大學即將畢業,對未來滿是憧憬與期待。
當天,我夢到高中時期的自己,那個受人歡迎、是眾人意見領袖的自己。可醒來後我看著鏡中的自己,長髮、滿臉鬍渣又邋遢不堪。
我對鏡中的人,感到好陌生。
腦中浮現了高中時期的自己,也讓我覺得好陌生。
我在想,究竟哪一個是真正的自己?還是其實我什麼都不是?
我的心中始終隱隱藏著一股不平、憤怒,此刻突然強烈地炸裂了開來。
為什麼別人可以過得那麼幸福?為什麼只有我一事無成?你們這些人有什麼了不起的?憑什麼看不起我?
於是我決定,將計畫著醞釀已久,讓眾人關注、且難以忘懷的大事,付諸實行。
從不生氣
從小乖巧又成績表現優異的沙林,鮮少表達出自己的情緒,他從不讓家人擔心,在同儕中更是圓融的領導者與開心果。別人眼中的沙林,就是個能力強、待人處事隨和、好相處,幾乎沒有缺點的人。
沙林也希望自己可以盡可能達成他人的期待,尤其是滿足父母的期待,畢竟父母辛苦工作,提供了自己優渥的生活品質。而且父母也是親族中最有名望的,大家都在看著將來要繼承家族事業的繼承者表現,所以他不能讓父母丟臉。沙林好強、要強的個性,也讓他從不展現自己脆弱的一面。
沙林也會有自己的情緒及困擾,特別是他內心想望與外界期待發生衝突的時候,他的應對方式就是否認、壓抑以及隱藏。他幾乎從不生氣,對任何人都是。理智上,他認為自己衣食無虞,在物質上要什麼有什麼,也不用擔心未來要做什麼,任何的情緒與抱怨都是無病呻吟,但情感上,他隱隱覺得自己活得很卑微,總是在討好別人,連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情緒都有困難。別人覺得他很優秀,也什麼都有,但他覺得自己很無能,無法真正的做自己。無能會使人瘋狂。
心理學家羅洛梅認為,無能與瘋狂〈mad〉兩者有著密切的關聯,他所定義的瘋狂主要有兩點:「其一是個人的憤怒已達暴力程度的感受;其二是傳統精神醫學對精神病的觀點。」
羅洛梅進一步解析,無能之所以可能會造成瘋狂,期間有經歷過五個權力層次的過程:
第一個層次是存在的權力。
存在的權力始於誕生,嬰兒會以哭泣和振臂等方式來展現自己的感受,並透過這些舉動向照顧者傳達訊息,這便是嬰兒展現與體認自己存在的權力。存在的權力先於善惡,非善也非惡,必須在生活中被體認與展現,否則會發展成精神病、神經症或暴力。新生兒如果無法得到旁人回應,發育便會遲滯,身心也會跟著萎靡。
第二個層次是自我肯定。
人類擁有自我覺察的能力所產生的自我意識,生活的關鍵除了生理需求被滿足之外,心理需求也不可或缺。我們窮其一生都在追尋自我價值,對人類來說,生命不僅是有存在的需要,更有肯定自己的需要。能夠擁有自尊活著是非常重要的。
家庭是人們獲得認同與自我肯定最初也是最重的的起源地,如果孩子能在家中獲得認同、被賦予價值,他們就能將注意力轉往發展其他事物,但如果無法從家中獲得認同與價值感,自我認同受到阻礙,追求自我肯定這件事就會成為他一生中的強迫性需要,將會無止盡地驅策著他。
第三個層次是自我堅持。
當自我肯定受到阻礙,我們會用較強烈的行為模式,來反抗這些阻礙自我肯定的力量,我們會建立出自己的界線,使他人不得不正視我們,以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與信念。
第四個層次是侵略性。
當自我堅持持續受到阻礙,越過他人界線,入侵他人權位或地盤,並將其中一部分占為己有的強烈反應形式便會發展出來,這便是侵略性。
第五個層次便是暴力。
當前述所有層次的努力都徒勞無功、其他可能的方式都無效,憤怒會逐步累積在心中,達到頂點時,暴力便會爆發,成為解除緊張和獲得價值的唯一方式。此時,環境刺激會跳過大腦,直接轉變成暴力攻擊的衝動,這是其他方式都被阻斷時,人們回應環境的方式。
沙林在個人發展自我過程中所必需的權力層次中不停受挫。為了要獲得家庭的認同,他按照父母的期待,就讀與家業相關的科系,並且要求自己將來要繼承家業,但這並非沙林對自己的認同,也非他的價值觀。沙林否認、壓抑自己的想法與感受,放棄內在渴望與自我堅持,既不會防衛自己也不會反擊。這些種種累積下來,最後終使他走向暴力一途。
暴力是無能的展現
沙林的處境就如同羅洛梅所說,面臨個人價值感的喪失時,內心感受到無能的喪失感:「我們今日身在比暴力更悲慘的處境中,就是太多人覺得自己沒有權力,也無法擁有權力,甚至連自我肯定也被否決,再也沒有任何事物值得他們去肯定,於是除了宣洩暴力之外,別無他途。」
沙林覺得自己沒有權力,也無法擁有權力,他從原本的表現優異,到後來被退學、成為群體中的邊緣人,原本表現不如他的同儕,正一個個超越他,且都將陸續要展開自己美好的未來,沙林卻什麼都沒有。他無法肯定自己、無法成為自己,而且再也找不到其他值得他去肯定的事物。沒有價值感的人是難以長久生存的,於是,對沙林來說,只剩下暴力宣洩的方式,能夠證明自己的價值。
羅洛梅認為,無能與冷漠是醞釀暴力的溫床,暴力行為多是出自那些想要建立自尊、保護自我形象或想要展現自己重要性的人所使用的方式,暴力不是出自於過剩的權能,而是來自於無能。如同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Arendt〉所說的:「暴力是無能的表現」。
精神分析師湯普生〈ClaraM.Thompson〉也提到:「侵略出自栽培和操控生命的天賦傾向,這似乎是所有生物的特徵,只有當生命力在發展中受到阻礙時,暴怒或憤恨等成分才會與之連結。」當人們的自我發展受到扼殺,也沒能找到任何可能保護自己、獲得尊嚴的方式,內在的各種負向能量就會堆疊成絕望,最後走向暴力。
無法成為自己的絕望
哲學家齊克果指出,最普遍的絕望乃是人陷入這樣的絕境:不能選擇、沒有成為自己的意願;而最深切的絕望乃是選擇「做不是自己的人」。另一方面,「決意成為真正的自己,確是絕望的相反」,而這種抉擇乃是人的最終極責任。
人的價值感來自於能夠自我認同、肯定,並成為真實的自己,當處在這種狀態時,人的內心是充滿能量與希望的。如同心理學家卡爾‧羅哲斯〈CralR.Rogers〉所提到的:「當人能夠不必死撐著虛偽的表面,或硬牆、大壩,人的感覺就會洶湧而起,掃光一切。而這種感覺早在他的內心中蓄勢待發了。同時,這個現象也可以說明,人的內心有一種逼人的需求,使人非去尋找而變成自己不可。」羅哲思認為,人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追求著且最想要達成的目標,就是變成他自己。
心理學家馬斯洛也說:「如果人的本質核心被否認或壓抑,就會生病,有時以明顯的方式,有時以隱微的方式⋯⋯這種內在核心非常纖細微妙,很容易被習性和文化壓力戰勝⋯⋯即使它受到否認,仍然一直潛藏不斷要求得到實現⋯⋯每一次與我們核心的疏遠,每一個違反我們本性的罪過,都會記錄在潛意識中,使我們鄙視自己。」
這種無法成為自己,不斷壓抑自己真實感受、討好別人、否定自己、感覺不到自我價值且日復一日的「永劫回歸」的生活,讓人無法承受。
「永劫回歸」這個概念出自於尼采。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sprachZarathustra〉一書中,描述一位透悟許多真理的老先知,提出「永劫回歸」的概念。查拉圖斯特拉提出一項挑戰,假使你會周而復始地重複過著一模一樣的人生,你會有什麼改變:「假使某天或某晚,惡魔趁你不備,偷偷潛入最深的孤寂裡對你說:『你從前至今的此生,將無止境地重複無數次,每一次均毫無變化,同樣的痛苦和喜悅,同樣的思維和嘆息,此生中每件極大極小的事,都將一再重演,以同樣的順序和因果,就連眼前的蜘蛛、林間的月光、此時此刻以及我的出現,也不例外。存在的沙漏將永無止盡地上下翻轉,你就如同那裡頭的一粒沙!』你難道不會崩潰,咬牙切齒地詛咒說這話的惡魔?還是你曾經歷過這驚人的一刻並回答祂:『祢是神,我不曾聽過比這更神聖的話?』如果這想法占據你的心,它將從此改變你,或者,將你擊垮。」
心理學家亞隆會使用「永劫回歸」這項永無止境反覆過同樣人生的思考實驗,來引導個案思索自己的一生,他認為,如果有人在這樣的思考實驗中,發現這過程很痛苦或不堪忍受,代表這個人的一生過得並不好。亞隆會引導個案進一步去思考如何改變人生,放眼未來:「你現在可以怎麼做,好讓你在一年或五年後回頭看時,不會因為累積了新的悔恨而感到同樣的沮喪?換句話說,你能找到一種不會累積悔恨的生活方式嗎?」
「永劫回歸」是亞隆用來引領個案創造熱愛人生的一種方式。但對沙林來說,這樣日復一日,重複過沒有價值感、沒有自己的「永劫回歸」生活,卻是擊垮他的絕望。
面對這種感覺不到自身價值、未來沒有任何成為自己的可能性累積而成的絕望,沙林選擇用極端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他放棄思考與尋找幫助自己脫離絕望、活出自己、不再累積悔恨的生活方式,反而以隨機的方式,暴力攻擊無辜的陌生人來宣洩自己的憤怒,並以此攫取眾人關注來得到價值感。
沙林的做法,再次讓自己和身邊的人陷入了絕望。
借鏡故事的思考練習
如果發現總是壓抑、否認或者害怕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情緒⋯⋯
*想一想,如果表達了自己真正的想法、情緒,會發生什麼事?你擔心可能會發生的最糟事情會是什麼?這些事情會對生活有什麼影響?你該如何因應?
*想一想,不斷壓抑、否認自己的想法、情緒,對自己與生活會帶來什麼影響?你會如何看待這樣的自己?這樣持續下去會發生什麼事?這些後續可能發生的事是自己想要的嗎?會對自己或身邊的人產生什麼影響?
*想一想,如果表達了真實的想法與情緒,身邊的人會如何重新認識你?他們可能會有什麼反應?你們的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
*想一想,如果一直壓抑、否認自己的想法、情緒,身邊的人會認識到怎樣的你?對你們關係的影響是什麼?
*想一想,「適度表達真實想法與情緒」以及「完全壓抑否認真實想法與情緒」的自己,會分別對生活帶來什麼不同的影響?如果你發現家人、身邊的親朋好友幾乎沒有表達過任何負面情緒或與他人不同的想法,總是很隨和、很好相處⋯⋯
*試著從對方角度,設想可能的想法與感受,並表達出來。*鼓勵對方說出己的想法、感受,讓對方有機會做真實的自己。
*觀察、瞭解對方可能的真實狀態,並表達理解、接納與欣賞。*理解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感受、情緒,不可能永遠平和、沒有衝突地與所有人相處,表達與展現這些不同,是人性的一環。
*接納親近的人展現自己獨特之處的方式,並試著用溝通、協調的方式,盡可能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可能共識。
*記得對方跟我們一樣,都是獨特的,都有自己的想法、感受與情緒,跟我們一樣是個人。不要強迫對方跟我們百分之百一樣,或完全接受我們的價值觀,即使對方是我們最親近的父母、家人,或者兒女,他們都是他們自己。
面對內心憤怒的思考練習
‧想一想,憤怒的背後是什麼?有什麼期待?有什麼不平?想要被理解什麼?
‧如果能用具體的言詞,表達出這些背後的期待、不平與希望被理解的想法,你會想對誰說些什麼?希望對方怎麼回應自己?
‧想一想,自己是個怎樣的人?你對自己有什麼評價?這些評價與事實相符嗎?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樣的遺憾或悔恨?‧從過去的遺憾或悔恨中,你體悟或學到了什麼?
‧從現在開始,你可以做些什麼,以讓將來不再累積新的遺憾或悔恨?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過什麼樣的生活?現在可以做什麼幫助自己往這些目標邁進?
面對被壓抑的內心憤怒—沙林的故事後篇
在下手隨機傷人的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我打開地獄之門,走了進去。
回頭看過去那個從不發脾氣、總是很乖、聽話的我,仿佛是另外一個人。或者說,那根本不是我,地獄之門一直在我心中,只是我忍耐著不去打開。
裡面有我一直渴求的反抗、破壞以及力量。
在計畫到實際動手的過程,我感受到無比戰慄的緊張感與能量感,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我所渴望的自己。我想經歷看看,那個不曾經歷的自己,然後,為自己劃上句點。
在被捕後,展開了長期的審判過程。在審判的過程裡,刺激的戰慄感消失了,無比的空虛隨之襲來。這不是我所期待的,我感覺自己比以前更加脆弱、無能。
期間,出現了兩個我在拉扯,一個是那個已經質變的我,覺得自己強大、無所不能的我;一個是更加脆弱不安的我,覺得自己無能、無價值的我。我不知道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我。
漫長的審判過程讓我逐步釐清,其實兩個都是我,就像硬幣一樣,是一體兩面。我想起自己在動手執行計畫時,那個被我認為脆弱無能的自己,拉住了自以為無所不能的我,殘存的理智,阻止了我針對受害者的致命部位進行攻擊。沒有任何一位受害者死亡,都是可恢復的傷勢。雖然如此,我依然對受害人、其家人以及整個社會造成了無可磨滅的傷害。
如果重來,我要為自己發聲,讓那個有能量的我能勇敢表達對未來的想法,爭取自己未來想做的事,讓我有機會成為我自己,也讓身邊的人認識真正的我,不再留遺憾,這樣我就不須要再用傷人的方式來尋找與證明自己。如果我能提早多想一點、想遠一點,就能預見這一切,避免這些發生。
我從傷人過程中短暫得到的價值感和力量感,事後看來,都不過是一種虛妄的幻覺,我為此深深懊悔。
可惜人生沒辦法重來一次,用這種慘痛的方式學習,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餘生,如果還有機會獲得自由,我想要彌補這個缺憾,也希望所有人能不重蹈覆轍我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