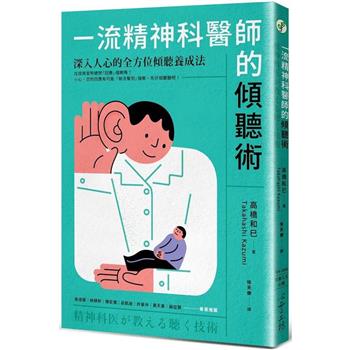前言
人,會隨語言成長。
特別是嬰兒,習得語言與心理發育之間有著密切關聯。
孩子從一歲起開始學會語言表達,最初只會說「媽媽」、「爸爸」這類一段式短語,逐漸地又學會說「媽媽,過來」這類兩段式短語,再過一段時間又會說「媽媽,我要果汁」等簡易的句型。隨著語言成長,不可否認地,他們的視野也在不斷擴大著。
在嬰兒階段,最明顯會發生的心理發育,會發生於所謂的「第一次叛逆期」。在該階段中,嬰兒會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新語言表達方式。
那就是「討厭,不要」。
這是對母親的反抗。原本對孩子而言,母親是他在這世界上最重要並且最信賴的存在。但孩子會反抗母親,該階段被稱為「第一次叛逆期」,也就是嬰兒出生以後第一次呈現出的自我表達。所謂的自我表達,就是要表達自己與別人的不同。
出生以來,孩子都是在被母親抱在懷裡,或是跟在母親後面。可是到了一定階段,母親叫他「好好刷牙」、「自己穿衣服」、「乖乖坐著吃飯」的時候,他們會反抗地回答「討厭,不要」,這是心理發展過程中一種極其重要的變化。
獲得新的語言表達,能拓展他們的自我。也就是至今為止都是在母親保護下成長的孩子,開始有自己的獨立的思維。經歷了「第一次叛逆期」,孩子又會開始順著母親的意,但是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是基於他們明白「拒絕是一種選擇」之上,自己所選擇的結果。他們的心胸已經變得更加寬廣了。
另一種情形是:還未能經歷「討厭,不要」這類心理語言表達、就經過了第一次叛逆期的孩子們,會變得怎麼樣呢?他們很難在社會上(尤其是與他人交往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想法。比如,在幼稚園就算自己的玩具被其他孩子搶走了,他們也不會說「這是我的,還給我」,因為他們不知道「討厭,不要」這樣的表達方式。
大多數的孩子都會經歷「第一次叛逆期」的發展過程。
之後,孩子們會獲得更多的詞彙,心胸也會更寬廣。可是接下來他們要面臨的就是人生的第二大階段:青春期(第二次叛逆期)。新語言是這個:
「別管我」。
這句話是在宣示「我不要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們在青春期開始以這種方式自我表達,就意味了精神上的獨立。這一點也奠定了學業有成後經濟獨立的基礎。青春期的內容取決於之前所培育的親子關係。有的孩子吃完飯後會安靜地離開餐桌前的父母,回到自己房間。有的孩子則會和父母產生激烈的爭吵(有的時候甚至引發家暴)。不管是哪種情況,他們想表達的都是「這是我的事,別管我」的精神獨立宣言。
長大成人之後,到了25歲左右,我們會靈活運用社會上所有的語言表達方式,心理上進入穩定狀態。
可是長大以後,我們時常也會找到「新語言」。和別人談話時,會突然被對方的話語所打動,發現「原來還可以有這種表達方式」,或是當我們聽朋友跟自己訴苦時,也會打從心裡覺得「真坦率,我要是也能這樣就好了」。這一點說明了,有時當我們不知道怎樣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情緒時,有人為自己代言說出心聲的感覺。
如果已經成年的我們,經歷過第一次叛逆期的「討厭,不要」和第二次叛逆期的「別管我」,那麼或許我們的人生還會再次迎來一次巨大的轉變。
其實,精神治療與心理諮商,就是一段探尋新的語言表達方式的過程。
也就是我們透過傾訴自己的方式,尋找到新的語言表達。
接受心理諮商的目的,就是在表達自己的痛苦心聲的過程中,能更明確地找到表達自我情緒感受的詞彙。至今為止,因為不知該如何自我表達而感到苦惱的人們,可以從中找到確切的表達方式。就在這瞬間,我們會突然覺悟到「原來這才是我想表達的」,並從中體會到自己的思路變得更加寬廣。
當我們發現了好幾種這類語言後,自然地這些語言就會在腦海中擴散開來、並就此落地生根。新的語言表達詞彙經過日積月累,其結果會改變統整我們一切語言的文法(syntax),最終我們的人生觀便因此改變。
在物理學上,有著被稱為「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一種概念。這是一種可以找到普遍性秩序的自然力量。這也就是說,各式各樣不同要素的互相作用下重新編整,最終自發性地建立秩序。舉個簡單的例子,就像雪的結晶一樣。在一定溫度下,大氣中的水蒸氣會自然形成美麗的六角形結晶。
另外根據研究,構成了遺傳基因的DNA,是由稱為核酸的基本組成要素,經過了幾億年不斷進行分子自我組織化的成果後,。才形成了如今的精密構造。當我們提到更具普遍性的秩序時,以DNA的角度來解釋,就是在這地球上更具有適應性、更具生存能力這一點。據說,大腦的神經細胞系統也是經由長期的自我組織化所建構而成的。
我認為,心理諮商過程中的探尋新語言與重新編整詞彙,就是一段自我組織化的過程。更進一步說,這種力量甚至可以達到將神經迴路重組化的效果。
在心理諮商過程中,我們如果能做到自由傾訴自我,就意味著「自我組織化」的啟動。這是從潛意識中還未被語言化的情感層面出發,再從發現語言、將語言組織化形成句子、最後達到改變人生價值觀的過程。在心理諮商過程中這段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接下來便依序來探討這個問題。
透過傾訴自我,人會改變,自我的價值觀會改變。
人透過傾訴自我,能夠找到多少新的語言與文字脈絡,決定了傾訴者人生轉變的速度與深度。
我們能否協助好傾訴方釋懷暢談,取決於身為傾聽方的「傾聽力」。
(本書會提供各種具體案例,這些案例都是作者模擬虛構的,請諒解。)
第一章 為什麼被人傾聽能讓心情舒暢──因為人之所以傾訴心聲,是為了得到支持
1.「傾聽的技巧」是指什麼?
得到了認同,才會感到如釋重負
在心理諮商/精神治療中,最有效的應該是讓個案藉由獲得傾聽而感到如釋重負。我相信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都體會過這種效果。
比如這樣的開頭「我告訴你,最近……」,之後開始聊一些不順心、不開心的事,比如「我被A(化名)這麼批評,你說過不過分?」等等。傾訴者抱怨完以後會覺得心理舒服很多,然後忘記這些事。
傾訴者之所以覺得心情舒暢,是因為他釋放了對A的不滿的同時,這樣的情緒也得到了認同。當然,我們不知道傾聽方是否贊同或反對A的想法,但至少由於傾聽方一直保持著沉默,才使傾訴方覺得自己的觀點得到了認同。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傾聽的效果。
不過對於靜靜傾聽方(諮商師)而言,心裡會積壓起一種不滿感。之所以產生這種不滿,是因為傾訴者對A的憤怒,無意中傳達給了傾聽方,尤其在傾聽方無法反應的時候,更加會有這種感受。
如果,傾訴方在抱怨完以後,向傾聽方問一句「你怎麼看?」,那麼傾聽方的不滿就會消失。傾訴方與傾聽方都會感到自在,對話也會順利地延續下去。
有種人善於「傾聽」,這種人往往是先靜靜傾聽,在傾聽的過程中適當地迎合對方說句「對啊」、「是有點過分」等等,這麼一來就不會產生不滿足的感受。
能做到不回話、靜靜傾聽才夠專業
傾訴方與傾聽方的關係是「訴說─傾聽」, 這一點是心理諮商中的基本關係。傾訴的效果,就算在日常生活當中,也和心理諮商的道理相通。
但是在傾聽的方式上,這兩者之間有所差異。最大的差異是在心理諮商的過程中,作為傾聽方的諮商師不能迎合或回應對方,只能聽不能說。
為什麼不能回應或迎合傾訴者呢?
結論是,這麼作會影響傾訴者自我組織的能力。(後續會解釋)
但是,光聽會使傾聽方(諮商師)心裡積壓起不滿感。尤其是在接受心理諮商的階段,一般提到的不會是什麼日常的瑣碎小事,而是更加沉重的問題。不斷傾聽著悲觀負面的話題內容,會讓諮商師容易對傾訴方(個案)產生類似於憤怒的複雜情緒。
在雙方面對面談話的過程中,傾聽方所感受到的憤怒情緒會無意中傳達給傾訴方。作為傾訴方剛開始還能自由自在地吐露心聲,但過一段時間會逐漸發現「自己沒能得到理解」,如此一來心理諮商便會陷入泥淖當中。心理諮商中「透過被人傾聽而如釋重負」的效果也會隨之消失。
所謂「傾聽的技術」,就是讓諮商師在不積壓不滿感的情況下、靜靜地傾聽到最後一刻的一門技術。以傾訴方的角度而言,這是們讓他們敞開心胸、暢所欲言、激發自我組織開始運作的一門技術。
我認為,我們可以說這是「善於傾聽」的極致技術。
2. 傾訴方之所以感到如釋重負,是因為傾聽方代表了全世界的認同
唯一的認同者
當我們傾訴煩惱時,如果自己的煩惱得到了認同,傾訴者的自責情感就會減緩;他們會感到「這樣的自己也不算壞」。這是當我們對人吐露心聲便感到如釋重負的最大原因。
相反地,如果我們不向任何人傾訴煩惱,只是一個人胡思亂想,大多會越想越痛苦。這麼一來我們便會不斷自責,認為只有自己是個沒用的人。這種情緒的背後,是基於自己被他人嫌棄、被排擠所產生的孤立感與恐懼感。
比如說,過去曾有這麼一個案例。這是在母子單親家庭裡長大的十九歲的女兒B。她努力用功,考上了理想的大學。進了大學以後,本打算好好享受一下大學生活,但她突然發現,周遭的同學都是生活富裕並且性格開朗的華麗女大學生,而自己卻一直煩惱於自己的個性內向、不愛表達自己、不善與人交往,性格也不夠開朗,她因此開始自責。
她曾經跟高中好友這麼描述過「因為我的家庭生長環境,使我的個性很內向。我恨自己的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
如果她的好友能帶著理解的口吻回答她「原來是這個原因啊,妳辛苦了」。那麼B就會得到安心輕鬆,然後會自我調整,產生「算了,還是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學生活吧」的想法。
可是,如果好友反過來勸她「母親一個人把你撫養長大非常辛苦,妳不應該恨她。事到如今妳更不該責怪父母」的話,B就無法釋下重負,煩惱反而會加深,她會因此變得更加自責、更加內向。
無論她的同學做出怎樣的反應,周圍的女大學生開朗、自己內向,這一點事實不會改變。可是,根據同學的反應,她的情緒會變得放鬆或是變得更內向。情緒得到放鬆,是因為她找到了能理解自己、認同自己的人。無論我們有多重大的不幸或是煩惱,只要是與他人之間有所連結,我們就會變得更堅強,煩惱也會變小。相反地,如果我們什麼事都一個人孤獨地承受,人會變脆弱,煩惱會越來越大。
B小姐的傾訴對象是她的好友,雖然只是位好友,但得到了好友的認同,她就彷彿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同。相反,雖然只是一位朋友,如果被這位朋友否定,她就會感到被全世界拋棄。對傾訴方來說,她擁有的這僅僅「一位」傾聽者,也就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傾聽者。身為傾聽者的責任十分重大。
有一句話很流行,叫「大家一起闖紅燈就不怕」。確實如果一個人違反規則會被責怪,大家一起違反規則就不擔心會被譴責。如果是一個人,違反了規則就會自我譴責,並被所有人責怪,但如果大家一起違反規則,就會覺得規則是規則,只要沒事就沒關係,反而是合理的判斷,或許還可以當成一種主張。總而言之,只要大家的心意一致,就會讓人覺得心情輕鬆。
這其實就和將自己的煩惱向他人傾訴是相同道理。
只要有一個人認同自己,我們就會覺得大家都認同自己。就算只有一個人,也會讓我們有得到全世界認可的安心感,因為這個世界上大多人的理解與認識彼此息息相關。就算在人生觀與政治信仰上有所差異,只要活在這世上,所有人便會藉著一種共通的基礎、理解、認識和彼此同意的事實,也就是「語言」做為橋樑來相互聯繫。確認了這種聯繫的存在後,我們就有被理解認可的安心感。
3. 認同並傾聽的難題所在
讓「傾訴方」如釋重負的三大要件
從現在開始,我把使人放鬆的聽話方式稱為「傾聽」。我曾說過,這種傾聽方式中包含了三大要件。第一是「認同並傾聽」、第二是「靜靜傾聽」、第三是「代表世界傾聽」。
我長年以來從事心理諮商商的教育工作,這項工作稱為心理諮商的職業指導。 我時常感受到「認同性的傾聽」難度有多高。一直聽對方說話,話中肯定會出現自己無法贊同的內容,因此會忍不住插嘴。在對話過程中,要求一個人光聽不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更不要說「代表世界傾聽」這種說法,說不定會被認為太過誇張。可是我們在希望自己的心聲獲得傾聽時,理所當然會選擇對象。就算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們也會選擇傾訴的對象,也就是能理解我們心情的對象。如果是針對一些更深刻的煩惱,會更會審慎選擇。那時,對傾訴者來說,傾聽者可以代表全世界。
關於「認同並傾聽」的難題所在,我想借用案例來加以說明。
有否認才有認同
要做到認同並傾聽,作為傾聽方首先必須理解認同與否認的兩個立場。
也就是,對於對方所傾訴的內容表示。
①「我懂,沒錯沒錯,我能認同這種情緒」的心態。
②「你說的這些事太荒唐,我不能認同」的否認心態。
比如,當個案說「活著很累,我很想死」的時候,作為專業人士的精神科醫生與心理諮商師,為了包容、認同對方,首先必須理解這兩種心態。
也就是:
①「沒錯,如果感覺那麼痛苦,是會產生想死的念頭。」
②「就算這樣也別想不開,我們想辦法解決問題嘛!」
這兩種心態,就是認同與否認的心態。
如果有人說「我想死」,諮商師最多就是回應一句「是嗎?」,或是輕輕點點頭。這裡面包含了 ①「我可以理解這種心情,確實會這樣」,也同時抱有②「我們應該解決問題,繼續活下去」的心情。這兩種認同與否認的心態。從個案的角度來看,如果能從諮商師的點頭回應中同時感受到這兩種情緒,會讓個案從中得到很強烈的安全感。
當一個人說出「想死」的時候,其實也是在表達「想活下去」的心情。我認為,如果不想活著,就不會產生想死的念頭。
如果個案想死的念頭不得到認可,被勸導說「別那麼想不開,努力向前看」的話,個案會感到被否認,情緒會因此更加低落,還應該會後悔地想著「唉,要是沒(對這個人)說這些話就好了」。
但要是我們換個說法,只認同對方想死的念頭,回應一句「這樣確實很痛苦,就算想死也無可奈何」,那麼個案也會感到被否認,似乎自己受到遺棄,只能一死了之,情緒也會更低落。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呢?我要再次強調:「想死」的情緒裡,也包含著「想活下去」的求生欲望。
針對在心理諮商中我們面對的最極端訴求「想死」,要真正做到「認同並傾聽」的難題何在,我想讀者們應該明白了吧。
我之所以舉了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就是為了證實,不管我們面對的是哪一種傾訴內容,作為諮商師,我們必須要先理解認同與否認的心態,才可能做到「傾聽」。如果做不到這點,我們會永遠擺盪於「局部理解」或「局部否定」的不穩定狀態中。諮商師心理不穩定的狀態,會在無意中傳達給個案。
無論我們聽到任何內容,都能保持著既認同又否認的兩面性,這需要很大的包容力。這可說是極其高難度的心理諮商技術。在培養諮商師的過程中,我作為老師,會選擇將這門技術只教授給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學生們。
那麼,我最先教授的是什麼呢?是「靜靜傾聽」。在做到「認同並傾聽」前,我首先教授學員的是「請無論如何絕不插話,只要靜靜傾聽」。為什麼從第二項開始教起呢,其中的道理我會在第二章裡敘述。
人,會隨語言成長。
特別是嬰兒,習得語言與心理發育之間有著密切關聯。
孩子從一歲起開始學會語言表達,最初只會說「媽媽」、「爸爸」這類一段式短語,逐漸地又學會說「媽媽,過來」這類兩段式短語,再過一段時間又會說「媽媽,我要果汁」等簡易的句型。隨著語言成長,不可否認地,他們的視野也在不斷擴大著。
在嬰兒階段,最明顯會發生的心理發育,會發生於所謂的「第一次叛逆期」。在該階段中,嬰兒會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新語言表達方式。
那就是「討厭,不要」。
這是對母親的反抗。原本對孩子而言,母親是他在這世界上最重要並且最信賴的存在。但孩子會反抗母親,該階段被稱為「第一次叛逆期」,也就是嬰兒出生以後第一次呈現出的自我表達。所謂的自我表達,就是要表達自己與別人的不同。
出生以來,孩子都是在被母親抱在懷裡,或是跟在母親後面。可是到了一定階段,母親叫他「好好刷牙」、「自己穿衣服」、「乖乖坐著吃飯」的時候,他們會反抗地回答「討厭,不要」,這是心理發展過程中一種極其重要的變化。
獲得新的語言表達,能拓展他們的自我。也就是至今為止都是在母親保護下成長的孩子,開始有自己的獨立的思維。經歷了「第一次叛逆期」,孩子又會開始順著母親的意,但是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是基於他們明白「拒絕是一種選擇」之上,自己所選擇的結果。他們的心胸已經變得更加寬廣了。
另一種情形是:還未能經歷「討厭,不要」這類心理語言表達、就經過了第一次叛逆期的孩子們,會變得怎麼樣呢?他們很難在社會上(尤其是與他人交往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想法。比如,在幼稚園就算自己的玩具被其他孩子搶走了,他們也不會說「這是我的,還給我」,因為他們不知道「討厭,不要」這樣的表達方式。
大多數的孩子都會經歷「第一次叛逆期」的發展過程。
之後,孩子們會獲得更多的詞彙,心胸也會更寬廣。可是接下來他們要面臨的就是人生的第二大階段:青春期(第二次叛逆期)。新語言是這個:
「別管我」。
這句話是在宣示「我不要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們在青春期開始以這種方式自我表達,就意味了精神上的獨立。這一點也奠定了學業有成後經濟獨立的基礎。青春期的內容取決於之前所培育的親子關係。有的孩子吃完飯後會安靜地離開餐桌前的父母,回到自己房間。有的孩子則會和父母產生激烈的爭吵(有的時候甚至引發家暴)。不管是哪種情況,他們想表達的都是「這是我的事,別管我」的精神獨立宣言。
長大成人之後,到了25歲左右,我們會靈活運用社會上所有的語言表達方式,心理上進入穩定狀態。
可是長大以後,我們時常也會找到「新語言」。和別人談話時,會突然被對方的話語所打動,發現「原來還可以有這種表達方式」,或是當我們聽朋友跟自己訴苦時,也會打從心裡覺得「真坦率,我要是也能這樣就好了」。這一點說明了,有時當我們不知道怎樣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情緒時,有人為自己代言說出心聲的感覺。
如果已經成年的我們,經歷過第一次叛逆期的「討厭,不要」和第二次叛逆期的「別管我」,那麼或許我們的人生還會再次迎來一次巨大的轉變。
其實,精神治療與心理諮商,就是一段探尋新的語言表達方式的過程。
也就是我們透過傾訴自己的方式,尋找到新的語言表達。
接受心理諮商的目的,就是在表達自己的痛苦心聲的過程中,能更明確地找到表達自我情緒感受的詞彙。至今為止,因為不知該如何自我表達而感到苦惱的人們,可以從中找到確切的表達方式。就在這瞬間,我們會突然覺悟到「原來這才是我想表達的」,並從中體會到自己的思路變得更加寬廣。
當我們發現了好幾種這類語言後,自然地這些語言就會在腦海中擴散開來、並就此落地生根。新的語言表達詞彙經過日積月累,其結果會改變統整我們一切語言的文法(syntax),最終我們的人生觀便因此改變。
在物理學上,有著被稱為「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一種概念。這是一種可以找到普遍性秩序的自然力量。這也就是說,各式各樣不同要素的互相作用下重新編整,最終自發性地建立秩序。舉個簡單的例子,就像雪的結晶一樣。在一定溫度下,大氣中的水蒸氣會自然形成美麗的六角形結晶。
另外根據研究,構成了遺傳基因的DNA,是由稱為核酸的基本組成要素,經過了幾億年不斷進行分子自我組織化的成果後,。才形成了如今的精密構造。當我們提到更具普遍性的秩序時,以DNA的角度來解釋,就是在這地球上更具有適應性、更具生存能力這一點。據說,大腦的神經細胞系統也是經由長期的自我組織化所建構而成的。
我認為,心理諮商過程中的探尋新語言與重新編整詞彙,就是一段自我組織化的過程。更進一步說,這種力量甚至可以達到將神經迴路重組化的效果。
在心理諮商過程中,我們如果能做到自由傾訴自我,就意味著「自我組織化」的啟動。這是從潛意識中還未被語言化的情感層面出發,再從發現語言、將語言組織化形成句子、最後達到改變人生價值觀的過程。在心理諮商過程中這段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接下來便依序來探討這個問題。
透過傾訴自我,人會改變,自我的價值觀會改變。
人透過傾訴自我,能夠找到多少新的語言與文字脈絡,決定了傾訴者人生轉變的速度與深度。
我們能否協助好傾訴方釋懷暢談,取決於身為傾聽方的「傾聽力」。
(本書會提供各種具體案例,這些案例都是作者模擬虛構的,請諒解。)
第一章 為什麼被人傾聽能讓心情舒暢──因為人之所以傾訴心聲,是為了得到支持
1.「傾聽的技巧」是指什麼?
得到了認同,才會感到如釋重負
在心理諮商/精神治療中,最有效的應該是讓個案藉由獲得傾聽而感到如釋重負。我相信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都體會過這種效果。
比如這樣的開頭「我告訴你,最近……」,之後開始聊一些不順心、不開心的事,比如「我被A(化名)這麼批評,你說過不過分?」等等。傾訴者抱怨完以後會覺得心理舒服很多,然後忘記這些事。
傾訴者之所以覺得心情舒暢,是因為他釋放了對A的不滿的同時,這樣的情緒也得到了認同。當然,我們不知道傾聽方是否贊同或反對A的想法,但至少由於傾聽方一直保持著沉默,才使傾訴方覺得自己的觀點得到了認同。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傾聽的效果。
不過對於靜靜傾聽方(諮商師)而言,心裡會積壓起一種不滿感。之所以產生這種不滿,是因為傾訴者對A的憤怒,無意中傳達給了傾聽方,尤其在傾聽方無法反應的時候,更加會有這種感受。
如果,傾訴方在抱怨完以後,向傾聽方問一句「你怎麼看?」,那麼傾聽方的不滿就會消失。傾訴方與傾聽方都會感到自在,對話也會順利地延續下去。
有種人善於「傾聽」,這種人往往是先靜靜傾聽,在傾聽的過程中適當地迎合對方說句「對啊」、「是有點過分」等等,這麼一來就不會產生不滿足的感受。
能做到不回話、靜靜傾聽才夠專業
傾訴方與傾聽方的關係是「訴說─傾聽」, 這一點是心理諮商中的基本關係。傾訴的效果,就算在日常生活當中,也和心理諮商的道理相通。
但是在傾聽的方式上,這兩者之間有所差異。最大的差異是在心理諮商的過程中,作為傾聽方的諮商師不能迎合或回應對方,只能聽不能說。
為什麼不能回應或迎合傾訴者呢?
結論是,這麼作會影響傾訴者自我組織的能力。(後續會解釋)
但是,光聽會使傾聽方(諮商師)心裡積壓起不滿感。尤其是在接受心理諮商的階段,一般提到的不會是什麼日常的瑣碎小事,而是更加沉重的問題。不斷傾聽著悲觀負面的話題內容,會讓諮商師容易對傾訴方(個案)產生類似於憤怒的複雜情緒。
在雙方面對面談話的過程中,傾聽方所感受到的憤怒情緒會無意中傳達給傾訴方。作為傾訴方剛開始還能自由自在地吐露心聲,但過一段時間會逐漸發現「自己沒能得到理解」,如此一來心理諮商便會陷入泥淖當中。心理諮商中「透過被人傾聽而如釋重負」的效果也會隨之消失。
所謂「傾聽的技術」,就是讓諮商師在不積壓不滿感的情況下、靜靜地傾聽到最後一刻的一門技術。以傾訴方的角度而言,這是們讓他們敞開心胸、暢所欲言、激發自我組織開始運作的一門技術。
我認為,我們可以說這是「善於傾聽」的極致技術。
2. 傾訴方之所以感到如釋重負,是因為傾聽方代表了全世界的認同
唯一的認同者
當我們傾訴煩惱時,如果自己的煩惱得到了認同,傾訴者的自責情感就會減緩;他們會感到「這樣的自己也不算壞」。這是當我們對人吐露心聲便感到如釋重負的最大原因。
相反地,如果我們不向任何人傾訴煩惱,只是一個人胡思亂想,大多會越想越痛苦。這麼一來我們便會不斷自責,認為只有自己是個沒用的人。這種情緒的背後,是基於自己被他人嫌棄、被排擠所產生的孤立感與恐懼感。
比如說,過去曾有這麼一個案例。這是在母子單親家庭裡長大的十九歲的女兒B。她努力用功,考上了理想的大學。進了大學以後,本打算好好享受一下大學生活,但她突然發現,周遭的同學都是生活富裕並且性格開朗的華麗女大學生,而自己卻一直煩惱於自己的個性內向、不愛表達自己、不善與人交往,性格也不夠開朗,她因此開始自責。
她曾經跟高中好友這麼描述過「因為我的家庭生長環境,使我的個性很內向。我恨自己的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
如果她的好友能帶著理解的口吻回答她「原來是這個原因啊,妳辛苦了」。那麼B就會得到安心輕鬆,然後會自我調整,產生「算了,還是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學生活吧」的想法。
可是,如果好友反過來勸她「母親一個人把你撫養長大非常辛苦,妳不應該恨她。事到如今妳更不該責怪父母」的話,B就無法釋下重負,煩惱反而會加深,她會因此變得更加自責、更加內向。
無論她的同學做出怎樣的反應,周圍的女大學生開朗、自己內向,這一點事實不會改變。可是,根據同學的反應,她的情緒會變得放鬆或是變得更內向。情緒得到放鬆,是因為她找到了能理解自己、認同自己的人。無論我們有多重大的不幸或是煩惱,只要是與他人之間有所連結,我們就會變得更堅強,煩惱也會變小。相反地,如果我們什麼事都一個人孤獨地承受,人會變脆弱,煩惱會越來越大。
B小姐的傾訴對象是她的好友,雖然只是位好友,但得到了好友的認同,她就彷彿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同。相反,雖然只是一位朋友,如果被這位朋友否定,她就會感到被全世界拋棄。對傾訴方來說,她擁有的這僅僅「一位」傾聽者,也就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傾聽者。身為傾聽者的責任十分重大。
有一句話很流行,叫「大家一起闖紅燈就不怕」。確實如果一個人違反規則會被責怪,大家一起違反規則就不擔心會被譴責。如果是一個人,違反了規則就會自我譴責,並被所有人責怪,但如果大家一起違反規則,就會覺得規則是規則,只要沒事就沒關係,反而是合理的判斷,或許還可以當成一種主張。總而言之,只要大家的心意一致,就會讓人覺得心情輕鬆。
這其實就和將自己的煩惱向他人傾訴是相同道理。
只要有一個人認同自己,我們就會覺得大家都認同自己。就算只有一個人,也會讓我們有得到全世界認可的安心感,因為這個世界上大多人的理解與認識彼此息息相關。就算在人生觀與政治信仰上有所差異,只要活在這世上,所有人便會藉著一種共通的基礎、理解、認識和彼此同意的事實,也就是「語言」做為橋樑來相互聯繫。確認了這種聯繫的存在後,我們就有被理解認可的安心感。
3. 認同並傾聽的難題所在
讓「傾訴方」如釋重負的三大要件
從現在開始,我把使人放鬆的聽話方式稱為「傾聽」。我曾說過,這種傾聽方式中包含了三大要件。第一是「認同並傾聽」、第二是「靜靜傾聽」、第三是「代表世界傾聽」。
我長年以來從事心理諮商商的教育工作,這項工作稱為心理諮商的職業指導。 我時常感受到「認同性的傾聽」難度有多高。一直聽對方說話,話中肯定會出現自己無法贊同的內容,因此會忍不住插嘴。在對話過程中,要求一個人光聽不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更不要說「代表世界傾聽」這種說法,說不定會被認為太過誇張。可是我們在希望自己的心聲獲得傾聽時,理所當然會選擇對象。就算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們也會選擇傾訴的對象,也就是能理解我們心情的對象。如果是針對一些更深刻的煩惱,會更會審慎選擇。那時,對傾訴者來說,傾聽者可以代表全世界。
關於「認同並傾聽」的難題所在,我想借用案例來加以說明。
有否認才有認同
要做到認同並傾聽,作為傾聽方首先必須理解認同與否認的兩個立場。
也就是,對於對方所傾訴的內容表示。
①「我懂,沒錯沒錯,我能認同這種情緒」的心態。
②「你說的這些事太荒唐,我不能認同」的否認心態。
比如,當個案說「活著很累,我很想死」的時候,作為專業人士的精神科醫生與心理諮商師,為了包容、認同對方,首先必須理解這兩種心態。
也就是:
①「沒錯,如果感覺那麼痛苦,是會產生想死的念頭。」
②「就算這樣也別想不開,我們想辦法解決問題嘛!」
這兩種心態,就是認同與否認的心態。
如果有人說「我想死」,諮商師最多就是回應一句「是嗎?」,或是輕輕點點頭。這裡面包含了 ①「我可以理解這種心情,確實會這樣」,也同時抱有②「我們應該解決問題,繼續活下去」的心情。這兩種認同與否認的心態。從個案的角度來看,如果能從諮商師的點頭回應中同時感受到這兩種情緒,會讓個案從中得到很強烈的安全感。
當一個人說出「想死」的時候,其實也是在表達「想活下去」的心情。我認為,如果不想活著,就不會產生想死的念頭。
如果個案想死的念頭不得到認可,被勸導說「別那麼想不開,努力向前看」的話,個案會感到被否認,情緒會因此更加低落,還應該會後悔地想著「唉,要是沒(對這個人)說這些話就好了」。
但要是我們換個說法,只認同對方想死的念頭,回應一句「這樣確實很痛苦,就算想死也無可奈何」,那麼個案也會感到被否認,似乎自己受到遺棄,只能一死了之,情緒也會更低落。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呢?我要再次強調:「想死」的情緒裡,也包含著「想活下去」的求生欲望。
針對在心理諮商中我們面對的最極端訴求「想死」,要真正做到「認同並傾聽」的難題何在,我想讀者們應該明白了吧。
我之所以舉了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就是為了證實,不管我們面對的是哪一種傾訴內容,作為諮商師,我們必須要先理解認同與否認的心態,才可能做到「傾聽」。如果做不到這點,我們會永遠擺盪於「局部理解」或「局部否定」的不穩定狀態中。諮商師心理不穩定的狀態,會在無意中傳達給個案。
無論我們聽到任何內容,都能保持著既認同又否認的兩面性,這需要很大的包容力。這可說是極其高難度的心理諮商技術。在培養諮商師的過程中,我作為老師,會選擇將這門技術只教授給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學生們。
那麼,我最先教授的是什麼呢?是「靜靜傾聽」。在做到「認同並傾聽」前,我首先教授學員的是「請無論如何絕不插話,只要靜靜傾聽」。為什麼從第二項開始教起呢,其中的道理我會在第二章裡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