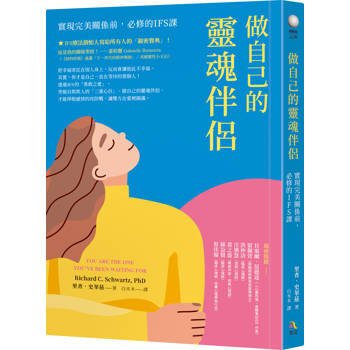〈序章 是什麼讓愛變得這麼難?〉
世上有許多伴侶都陷入如同柯特與瑪莉莎一樣的窘境。他們費力地想對抗各種婚姻關係專家和文化所暗示的惡魔,例如「溝通不良」和「缺乏同理心」。他們傷痕累累,心力交瘁,卻仍無法修復關係。他們在指責對方與自我反省間來回擺盪:怪對方無法讓家裡氣氛融洽,怪自己無法讓這段關係美滿,尤其是,伴侶關係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可是數一數二的。
有沒有可能,柯特和瑪莉莎真正該怪罪的是他們試過的那些解方呢?有沒有可能,就算他倆溝通的方式再怎麼完美,對彼此的妥協和同理再多,仍無法真正修復兩人之間的關係?婚姻專家告訴這些伴侶,「只要懂得體貼彼此,你們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伴侶雙方會先分別指出自己需要從對方身上獲得什麼,再由專家協助找出改變自己的方式,以滿足彼此的需求,這就是整個療程的目的。但有沒有可能,這種「體貼彼此需求」的方法本身就存在重大的破綻,才會讓兩人不管再怎麼努力,卻仍以失敗告終?
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不管雙方有多渴望與對方建立彼此扶持、互相敬重的親密連結,但他們身上或生活環境中(如果不加以改變的話),確實有些因素會使兩人難以建立這樣的關係。我會在本書中清楚說明這些因素,並提供一系列明確的做法來改善這些狀況。它將幫助伴侶們以我稱之為「勇敢之愛」(courageous love)的情感,來取代彼此在關係中既期待卻也害怕的控制、依賴、占有或疏離。
當關係中的兩人不再需要再為對方的心情負全責,卸下取悅對方的責任,並以勇敢之愛來珍視對方時,伴侶間許多長期存在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因為當兩人都懂得如何照顧好自己脆弱的部分時,就不會再強迫對方符合自己的期待,也不會再試圖操控對方的人生。
「勇敢之愛」包括了接納伴侶所有的「部分」,它讓我們不再需要把伴侶限縮在特定角色中,例如負責照顧的家長、負責拯救的救星、負責保護的守護者、負責給予讚美並賦予自信心的角色等。當對方嘗到獲得接納與自由的滋味,體會到它的美妙和非比尋常後,便能開始相信自己可以放下防備並敞開心胸。
也就是說,擁有照顧好自己情緒的能力,能使你得到想要的親密。因為一旦有了這種能力,無論伴侶對你親近或疏離,你都有勇氣能夠因應,不會為此過度反應。當你不再那麼害怕失去對方,也不再那麼怕被對方傷害時,便能全心擁抱伴侶的存在,並在對方的愛裡感受喜悅。
依你的情感經驗看來,以上這些說法是否都像天方夜譚?你是不是在想:「這些狀態聽起來很美好,但我要去哪裡才能找到夠成熟、有辦法這樣對我的人?」說不定,對方不在天涯,就在咫尺。只要你和伴侶都能將注意力「自轉」(U-turn, you-turn),開始以不同的方式認同自己的內在,就會發現「勇敢之愛」自然而然地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必須努力才能達到的狀態。你也會發現自己不再需要伴侶的照顧,因為光是從自己身上,就能獲得許多協助與支持。
我在本書所提倡的思維不太容易獲得西方文化的認同。西方文化傾向於專注要求伴侶取悅我們,要別人滿足自己的需求,卻不認為能從自己身上得到些什麼。我們總是想著手改造折騰自己的外在因素,卻不願意觸碰痛苦的內在根源。像這樣聚焦於外在──並要求他人來體貼自己的療癒方式──頂多只能為暴風雨(不論內在或外在的)帶來片刻寧靜而已,還會讓心中那片原本能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的沃土漸漸荒廢。事實上還有其他方法,不必捨近求遠,接下來我也會在本書中與你一起探索。不過在那之前,我們先來檢視一下「體貼對方需求」的這種方法究竟有什麼問題。
▍三重心計
接下來,我會仔細說明為什麼伴侶不可能隨時隨地都能成功取悅你,並長久滿足你的需求。舉例來說,假設你曾經歷只有拒絕和寂寞的日子,而伴侶的愛只能讓你暫時推開籠罩在頭上的烏雲。每當對方不在身邊,每當對方沒有心情取悅你時,你就會開始厭惡自己,覺得自己毫無存在價值。如果你之所以和對方在一起,是想靠他拯救自己的人生,那麼你總有一天會失望。
然而一旦那分愛不再甜如糖蜜──甚至只是偶爾沒那麼甜,就會讓我們害怕地開始著手進行「三重心計」。第一和第二重心計的目的,都是要讓伴侶變回那充滿愛的拯救者角色,第三重則是退而求其次,尋找其他辦法。
第一重心計是最常見的,就是直接強迫伴侶變回熱戀時的那個模樣。為了攻破對方堅固的心防,有時我們甚至連變鈍的鋸子、解剖刀、炸藥都會搬出來。我們懇求、命令、談條件、冷嘲熱諷,以羞辱、誘騙、隱瞞等各種方式逼對方就範,而對方通常會拒絕這種魯莽的掏心掏肺,因為他們可以感覺到,隱含在誘迫改變背後的批評和操縱企圖,從而豎起防衛之心。
第二重心計則是把同樣的手段用在自己身上。先是設法推測伴侶到底不滿意我們哪裡,再自以為是地設想對方想要的自己,並試圖把自身塑造成那個樣子(就算那個模樣和我們的本質毫無關連)。我們透過自我批評和自我羞辱割除部分本性,期盼能靠著取悅對方讓伴侶愛我們。然而這種改變並非出於自願,因此常會招致更強大的反效果。
當我們放棄從伴侶身上獲得渴望已久的愛時,第三重心計便開始了。到了這時候,我們不再向對方敞開心房,而是:一、尋找下一位伴侶,或是:二、為了繼續和同一個人在一起,所以每當感覺空虛與痛苦時,便麻痺自己或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上,甚至是:三、讓自己麻木到足以獨自生活。
這三重心計是不同層次的「放逐計畫」。一開始,我們先試著要求伴侶,要求對方把內在那些威脅到我們的部分趕走,接著就是把自以為對方不喜歡的(自己的)內在部分趕走,最後則是放逐心中與伴侶互相依戀的內在部分。若有人為了繼續和伴侶在一起,為了維繫彼此的關係,而放逐自己的內在部分,那麼兩人都得為此付出一些代價。
雖然這些前來尋求幫助的伴侶對彼此的埋怨可說五花八門,不過從兩人不良的互動模式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觀察到,伴侶間的問題不外乎這三重心計的排列組合。因為每個人心底都有個裝滿傷心與愧疚、痛苦與空虛的地下室,而且我們其實大多懂得如何處理這些感受,不需要麻痺自己或轉移注意力,直到我們終於能等到那個特別的人或特別的愛。
▍成為自己內在部分的主要照顧者
幸好,我們有辦法放下心中那些會讓自己對感情失望的傷痛和愧疚,而放下的第一步,是轉換心思關注的焦點。多數人會像黛比一樣,爭先恐後地迴避自己的內心世界,把心思放在外在的解決方案,例如設法找到那個注定要拯救我們的愛人,找錯了就換一個。在伴侶治療中,我試著讓伴侶雙方都進行「自轉」──把心思焦點轉向自己,請他們往自己的內心世界更靠近一些,不要因害怕而遠離。
當人們聆聽自己的內心深處時,就會發現日常生活中的背景噪音,是由許多不同的知覺、感受、幻想、想法、衝動所構成。若能專注於其中一種內在感受,並透過提問來了解,就會發現那種感受不過是一些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想法或情緒。人的內在是由許多不同的次人格(subpersonality)所組成,我稱之為「部分」;不同的部分共同組合成我們錯綜複雜的內在家庭。正因為一個人的內心同時存在著許多不同部分,所以才經常出現各種自相矛盾的難解需求。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就在詩作〈自我之歌〉中精闢地描述了這種狀態:「是我在自相矛盾嗎?很好,那我就自相矛盾吧。(我博大精深,我包羅萬象)」
不只惠特曼,我們每個人都是這麼包羅萬象,擁有多重面向。因此可以說,德爾菲神諭告誡我們的「認識自己」(know thyself),應該理解為「認識不同面向的自己」(know thyselves)。
我之所以會稱這個有點爭議性的次人格為「部分」,是因為我開始將這個理論運用在臨床上時,許多個案就是用這個詞彙來形容自己不同的人格面向。有的個案可能會說:「有部分的我想維持這段婚姻關係,也想對我太太忠誠;但有另一部分的我想要自由,想要一週七個晚上都和不同的女性歡愛。」也有人這樣表示:「我知道自己的事業還算成功,但有部分的我會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太太會發現真正的我有多愚蠢、多沒用。」
當我開始用這種方法來治療個案後,很驚訝地發現,只要我能在晤談時創造出一個令個案安心、感覺自己被接納的氛圍,他們就能很自然地與不同的內在部分對話。當個案進入專注於內在的神奇狀態時,他們可以和內在部分聊天,也能提問並了解內在部分為什麼會出現不合理的反應,為什麼會做出自我毀滅的事。聆聽內在部分的心聲後,那些原本看似不合理的事情,就會變得情有可原。因為內在部分會告訴個案,他們其實還卡在過去的某一段記憶裡,而對當時的他們來說,那些想法和行為不但合理,甚至是必要的手段。
你可以成為自己的治療師──你就是自己心中最脆弱部分尋尋覓覓的那個人。當你有能力療癒自己,你的伴侶也會從拯救你的責任中獲得釋放,更不必承受你求愛的三重心計,如此一來,你們才可能享有真正的親密。
〈第1章 親密關係的文化限制〉
要是一個人成長的家庭和所在的文化,能鼓勵他好好照顧自己內在被放逐的脆弱部分,那麼維繫親密關係不會是什麼大問題。然而不幸的是,知道這個祕密的人寥寥無幾;家人甚至很可能教你要反其道而行──覺得受傷、需要人陪、羞愧內疚、痛苦煎熬時,要把有這些感受的自己關起來,捨棄掉這些部分的自己。與此同時,我們的文化又以疲勞轟炸的方式告訴我們,在你終於找到「靈魂伴侶」之後,人生會變得多美好。
▍婚姻讓人們沒空談情說愛?
我們的文化之所以要人們在親密關係中尋找浪漫、追求解脫跟救贖,是為了說服大家進入獨特的婚姻制度。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說,「美式婚姻……是人類嘗試過最困難的婚配方式之一。」在過去,每對伴侶身邊都圍繞著親戚朋友或有相似價值觀的同儕,彼此互相照應。然而在當今社會中,一對伴侶多半就是一個獨立運作的單位,需要自給自足。兩人不只從原本各自的社群中被剝離,也往往因為工作上的要求過多,或是在遠離親屬網絡的情況下難以應付養育子女所需,使得雙方經常忙到沒時間與身邊的伴侶培養感情。
養育小孩的確是伴侶們可能會面臨的其中一項嚴峻考驗。幾乎所有研究都顯示,伴侶雙方對婚姻的滿意度會在第一個小孩出世後驟降,直到年紀最小的孩子離家後才會回升。再加上兩人都成長於這個重視外在容貌體態,卻忽視且恐懼內心真實渴望的社會,雙方終將與各自的自我斷了線。在這種近乎「不可能的任務」安排下,伴侶還得承接你傾注在他身上的期待──希望對方能討你開心;而且要是對方沒有這麼做,必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社會文化設想的愛情救贖
養育小孩的確是伴侶們可能會面臨的其中一項嚴峻考驗。幾乎所有研究都顯示,伴侶雙方對婚姻的滿意度會在第一個小孩出世後驟降,直到年紀最小的孩子離家後才會回升。再加上兩人都成長於這個重視外在容貌體態,卻忽視且恐懼內心真實渴望的社會,雙方終將與各自的自我斷了線。在這種近乎「不可能的任務」安排下,伴侶還得承接你傾注在他身上的期待──希望對方能討你開心;而且要是對方沒有這麼做,必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長大後就會離開自己的父母,我們的孩子也會在長大後離開我們;換句話說,只有伴侶會永遠陪在我們身邊。因此,如果目前這個外貌至上、過度工作、消費成癮、快速變動的文化無法在短期內改善,伴侶們確實需要找到能對彼此感到高度滿意的方法才行。這對有孩子的人來說尤其重要,除了能讓孩子免於面對雙親離異的痛苦,也不必覺得自己對父母的幸福有責任。
在成長的過程中,如果有人能教我們如何療癒自己的內在部分,我們對關係的滿意度就會提高,因為我們對伴侶的要求就會減少。在我們對伴侶的要求中,有太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部分,如果我們願意分擔一些照顧自己內在部分的責任,而不是把這些工作全數丟給伴侶,就能從伴侶身上獲得更多滿足。當伴侶不必安撫你的內在部分,不必平息你的怒火,也不必在他不願照你意思做的時候,面對你的不滿,他便能從這些巨大壓力中解脫,成為你期望的愛人、陪伴者和一起冒險的夥伴。一旦你自行治癒了心中被放逐的脆弱部分,放下通往你內心城堡的吊橋,就能讓伴侶有辦法更靠近你,與你共創美好的連結。
▍逃離黑暗之海
對大多數人來說,若沒有持續從親密伴侶身上獲得肯定,往往會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以下感受:覺得自己很失敗、沒有價值、空虛、寂寞、遭拒、不安、絕望、醜陋、無聊、恐懼……都是難以忍受的情緒,會讓我們不顧一切想避開。另一方面,被我們稱為「幸福」的場景,大多發生在我們不受這些情緒所苦的時候。然而有太多時候,我們在這片黑暗的情緒之海載浮載沉,另一半成了我們維繫生命的浮木,我們得緊抓著對方,才不會被傷痛與愧疚淹沒,不至於被恐懼滅頂—難怪每當我們認為伴侶有可能離開自己時,就會感到擔心受怕又嫉妒。若對方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再當那塊浮木,甚至把我們推入那片黑暗之海時,我們也理所當然地開始想「下一個應該會更好」,接著便是真的付諸行動。
這種隨時都可能滅頂的幸福,不僅非常不穩定,也很容易受到干擾。除了伴侶有一天可能因過勞而撐不下去,大浪來臨時(例如事業失敗或來自雙親的批評),無論伴侶再怎麼努力救我們,我們仍有可能被吞噬。
我們的文化提供了許多可供攀附的浮木:電視、社群媒體、購物、工作、抽菸、合法與不合法的藥物、酒精、色情、性服務、整形、飲食方法和運動健身、高油高脂的食物……各種常見又會令人上癮的東西。但前面提到的這些替代品也都很脆弱,無法真正取代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儘管這些能令人們分心的事物只能讓我們短暫浮出水面一下下,但至少能在一段關係漸漸沉進水底的時候麻痺我們感受到的失望,讓我們不至於放棄這段感情,也能在下一段親密關係出現之前,暫時無視心中的苦痛。這些替代品讓我們開始相信幸福很近,就像一雙新鞋、一次週末小旅行或一份新工作般唾手可得。
然而這些令人分心的事物最終成了惡性循環的一部分,使我們有如上癮般,不停尋求這種隨時可能滅頂的愉悅,而非能長久維繫的幸福。越是深陷其中,就更是與世隔絕──也與自己隔絕──仍浸泡在黑暗之海中的我們,也會變得更害怕那些會吞噬自己的海浪,因此更加迫切追求短暫的幸福。換個方式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自己明明被困在一個很深的洞穴裡,但社會送過來的救命工具竟是各式各樣的鏟子。一如歌手李歐納.孔(Leonard Cohen)所唱的那句:「你受困在苦難中,而歡愉就是把你封進苦難裡的東西。」
◎練習.試著看見內心
請花幾分鐘時間在心裡回答以下問題。你可以把答案寫在日記上,或是採用任何能一邊閱讀,一邊記下答案的方式。
‧你心裡有什麼感受和想法是自己害怕面對的呢?例如空虛的感覺?怕自己沒人愛?
‧你期待另一半透過什麼方式好讓那些感受和想法消失?
‧你會在什麼情況下,使用前面提到的方法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你又會選擇哪種方式?
‧你有把握自己能療癒心中那些「害怕面對某些感受和想法」的內在部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