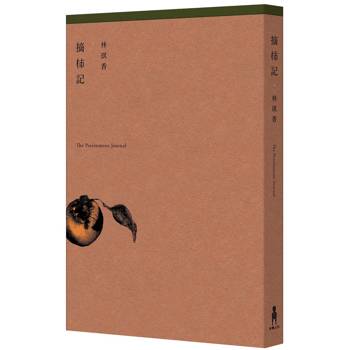序
寫這篇文章時,我正在前往曾木溫泉的路上。我們的車子老舊,車廂內瀰漫著淡淡的煤油氣味,引擎吵耳,暖氣系統不中用,呼呼吹出溫風卻吹不到後座來。後座沒設安全帶,沙發又特別滑,穿梭在迂迴的山路上時,我抱緊著身體,繃緊下半身的肌肉,與寒意對抗,與激烈抖動的車廂對抗,滿心期待著踏進溫泉水時自腳尖湧上的那陣麻痺。窗外灰濛的天飄下粉雪,而我手心裡殘留了緊握著雪球時的奇妙觸感—上車前,天空傾倒著雪,雪一顆顆的如同保麗龍,握一把,一捏,竟就成了堅實的雪球。對了,如此的雪,叫作「霰」。
這段車程,該會成為我日後關於冬季的美好回憶吧。混著氣味、聲音、風景、皮膚感觸、雀躍、腰痠背痛。
這幾年,尤其是疫情過後,我感到跟世間萬物的距離感有點含糊不清了。家人朋友在地理上分隔,然而卻常在雲端上相聚。獨自去餐廳,自助點了餐後,為我送餐來的是一台機器人,不自覺地低聲說了謝謝,它不作回應。某天翻看舊書,掉出了一張十多年前在柏林短居時的電影票,才想到不知何時,電影票已變成會因受熱而褪色的單薄感熱紙,甚至只是一個二維條碼。很多以往能用五感來感受的事情,都化為螢光幕上的訊號,方便得讓我忘記了自己的若有所失。
兒子在疫情期間走進我的生命,見他每天使勁撐開全身感官來認識世界,一片落葉,端詳、緊捏,在臉上擦,甚至塞進嘴裡饞,而我只懂欣賞其鮮紅與嫩黃,心想,他的世界定比我的精彩很多。
在日本生活的第十二個年頭,我完成了這本小書,關於我在日本遇到的場所、物件、飲食、人和自然。一些無法複製貼上的經歷、一些撤銷不了的耗損,都是我珍惜的事。書中文章大都寫於疫情之後,也有部分是早些年替媒體寫下的,修改了並補充遺漏。
書名《摘柿記》,源自我居住的社區的庭園裡,種了幾棵柿樹,每年秋季果實累累,明明清甜可口卻無人問津,而另一邊的栗子樹,時節剛到,果實便被搖下,內容給取走。
想來或許是柿子太平凡,才備受冷落吧。摘柿、嚐澀柿子、曬柿乾,都是我來日本後才經驗到的。以柿為喻,提醒自己記緊摘取尋常。
在此感謝成就這本書的每一個人。感謝設計師齋藤先生,在擁擠的日程裡割出時間來替這書作設計。謝謝我的伴侶金森正起,一人擔起了修葺老房的工作,讓我能把時間花在寫作上。謝謝我的兒子,我的小天使,我的安慰劑與光。
寫這篇文章時,我正在前往曾木溫泉的路上。我們的車子老舊,車廂內瀰漫著淡淡的煤油氣味,引擎吵耳,暖氣系統不中用,呼呼吹出溫風卻吹不到後座來。後座沒設安全帶,沙發又特別滑,穿梭在迂迴的山路上時,我抱緊著身體,繃緊下半身的肌肉,與寒意對抗,與激烈抖動的車廂對抗,滿心期待著踏進溫泉水時自腳尖湧上的那陣麻痺。窗外灰濛的天飄下粉雪,而我手心裡殘留了緊握著雪球時的奇妙觸感—上車前,天空傾倒著雪,雪一顆顆的如同保麗龍,握一把,一捏,竟就成了堅實的雪球。對了,如此的雪,叫作「霰」。
這段車程,該會成為我日後關於冬季的美好回憶吧。混著氣味、聲音、風景、皮膚感觸、雀躍、腰痠背痛。
這幾年,尤其是疫情過後,我感到跟世間萬物的距離感有點含糊不清了。家人朋友在地理上分隔,然而卻常在雲端上相聚。獨自去餐廳,自助點了餐後,為我送餐來的是一台機器人,不自覺地低聲說了謝謝,它不作回應。某天翻看舊書,掉出了一張十多年前在柏林短居時的電影票,才想到不知何時,電影票已變成會因受熱而褪色的單薄感熱紙,甚至只是一個二維條碼。很多以往能用五感來感受的事情,都化為螢光幕上的訊號,方便得讓我忘記了自己的若有所失。
兒子在疫情期間走進我的生命,見他每天使勁撐開全身感官來認識世界,一片落葉,端詳、緊捏,在臉上擦,甚至塞進嘴裡饞,而我只懂欣賞其鮮紅與嫩黃,心想,他的世界定比我的精彩很多。
在日本生活的第十二個年頭,我完成了這本小書,關於我在日本遇到的場所、物件、飲食、人和自然。一些無法複製貼上的經歷、一些撤銷不了的耗損,都是我珍惜的事。書中文章大都寫於疫情之後,也有部分是早些年替媒體寫下的,修改了並補充遺漏。
書名《摘柿記》,源自我居住的社區的庭園裡,種了幾棵柿樹,每年秋季果實累累,明明清甜可口卻無人問津,而另一邊的栗子樹,時節剛到,果實便被搖下,內容給取走。
想來或許是柿子太平凡,才備受冷落吧。摘柿、嚐澀柿子、曬柿乾,都是我來日本後才經驗到的。以柿為喻,提醒自己記緊摘取尋常。
在此感謝成就這本書的每一個人。感謝設計師齋藤先生,在擁擠的日程裡割出時間來替這書作設計。謝謝我的伴侶金森正起,一人擔起了修葺老房的工作,讓我能把時間花在寫作上。謝謝我的兒子,我的小天使,我的安慰劑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