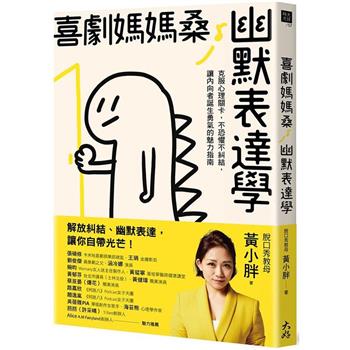◎女生可以展現力量嗎?關於女權
──「你有討厭的人嗎?」
面對著深陷自我糾結,不停地渴望別人愛我、不願意被人討厭的學生,我常會問出這句話:「你有討厭的人嗎?」
對方可能會遲疑許久才支支吾吾地說,「我有討厭的人。」那神情帶有罪惡感,她不願意承認自己會討厭別人,也不想面對自己的黑暗面。畢竟大多數女生從小被教導著端莊、優雅、與人為善⋯⋯等好女孩基本功。
而既然她親口承認了腹黑面,那我會接著問:「討厭誰?告訴我全名。」
我可以感覺到她心跳加速,有時腦袋快速運轉著「要講哪一個?」、有時連講出那個人的名字都有一定程度的厭惡感而不自知,有時卻帶著興奮,因為直接面對自己最深層的想法時,其實很豁然開朗。等待那些情緒一閃而過後,她衝口而出「XXX」,我期待的是她的舒暢感。那種感覺很像做了一場心靈SPA,一直浸泡在滾熱的水中,等到鼓起勇氣踩進透沁涼的冷水裡,全身刺麻地接受這種名為「討厭」的感覺。
我們會討厭別人,但我們連討厭的感覺都不知道。我們還會有一種標準詢問自己,這樣算是討厭嗎?嘿!女孩,你知道高潮的時候有沒有到,卻告訴自己要很討厭才算討厭──不是這樣的,一點點高潮也算高潮。
◆接受討厭別人的自己,讓勇氣誕生出來
我們先來接受情緒的合理性,每個人都可以討厭人,包括自己,當然也可以討厭別人,並且沒來由地討厭。有些人的存在本身就很刺眼,扎入你心裡的煩躁,想到他就覺得不舒適,甚至會有噁心感,這大大小小的情緒感受,都是討厭。
無端討厭別人,的確是一種不友善的行為。我們不用放大這種感受,時時刻刻想著那個討厭的存在,但我們可以接受會討厭別人的自己。這樣一來,當別人沒有理由的討厭你時,你反而比較能夠理解對方。關於「被討厭的勇氣」,或許我們先學著接受自己的卑劣黑暗面,才有機會讓勇氣誕生出來。
有些同學會顧左右而言他,說自己是討厭那件事、不是討厭那個人。這樣雖然聽起來比較圓融和善,但事實上也是把自己陷入於「只要自己行為改善,就會讓所有人都喜歡」的情境中。承認吧!有些人只是存在著就讓你感到刺眼煩躁。而你也有可能只是存在著,就讓某個人覺得不願接近。總有些學生,無法接受自己會被討厭,所以也無法討厭別人。他們時常會散發一種討好的氛圍,對方說什麼她都好,認為這叫隨和,實際上她把決定的權力交給對方,壓住她心底的埋怨與不認同,這種只要對方不討厭我就好的相處模式,其實讓人倍感壓力呢!
有趣的是,這種時不時討好別人的人,最常羨慕的對象就是「必取」(Bitch),對於自媒體那些勇敢說出「不喜歡我就閃開」的名人有著非比尋常的投射。我很好奇,是那些名人自帶光環才讓人心生嚮往?還是這些人內心太過沒有價值感,必須用討好來感受自己的存在?
◆找到自己的價值,就不怕別人討厭
四十歲的我,在人際關係上分合多次,發現那些坦率地承認某些物種就是跟我不合的人,反而好相處。畢竟我們已經生活在近代,人類文明已經多元到不需要符合每個人的價值觀就能活著。於是,社會教我的是,不用跟每個人做朋友。
我是在站立幫(注:由台灣喜劇之父張碩修成立的全台第一個喜劇團體)學會討厭的感受,那是我三十歲左右的事。在那之前,原生離異家庭導致我向外發展,在朋友群中常常是領導位置,外向、活潑、幽默、好相處是我的標籤,從來沒遇過交朋友這麼辛苦的局面。
可是,脫口秀不只是交朋友啊~我們要負擔的是各自段落的笑點,還要在團隊演出中合作。自編自導自演的演出中,牽扯的不只是隨和程度,還有更多來自個人的創作,也就是「個人價值觀」。
什麼東西好笑?這來自於個人的背景與觀點。當一群男生聚在一起時的幹話,集結成一齣現場喜劇,唯一的女生要隨和地飾演花瓶?還是要板起臉說「這根本就不好笑」?
這兩種情況我都嘗試了,甚至跟著台上的音樂節奏高喊:「前女友,婊子!」看著當事人變臉離開演出場地,經過我的身邊,有個抽離的我在捶打自己:「黃小胖!你是誰?」那一幕午夜夢迴時常常出現,我真的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
為了舞台機會,我願意討好,討好觀眾、夥伴,卻忘了討好我自己。第一年的演出,充滿自我懷疑。用二十八年確認夢想站上舞台的我,不喜歡這些製作背後的價值系統,我學會很多貶抑女性的名詞,出演更多被幻想的角色,我努力地變得更漂亮來迎合主流價值、表現隨和,直到當我反彈時招致「情緒化」的回應。不會吵架的我,在每次團練會議中表現冷漠、嚴肅、哭泣,都無法好好解釋自己身為女性的無奈與受傷。我覺得有些觀點很難笑,但他們笑瘋了啊!在笑點為上的世界中,要怎麼表現生氣才對?要怎麼樣表現生氣,才能是他們心中懂幽默的女性?
五、六年來的「鬧不合」,因為一個導火線,我離開站立幫。而後,經歷結婚、生子,再度回歸演出「十光機」,沒有太多的和解動作或剖心時刻,因為時間夠我們長大成熟。我們開始懂,爭吵都是在辯證自我,都是讓我們更成為「自己」。而成為自己的過程中,不能抗拒衝突,也不需要別人欣然接受蛻變的你。
◆有意識地面對討厭與憤怒,那是你勇氣的來源
當我選擇另覓表演舞台後,自製演出並專心耕耘女性幽默,不處於同一個競爭的環境中,我反而看到自己的價值。之前的我,覺得要有贏的把握才可以「現」;後來我明白了,展現力量也可以堅定,甚至帶有溫柔。
展現力量不代表打趴別人,女權的存在不是為了打趴男性,而是讓我們懂,我們可以爭取;當有不平等的形式藏在話語權背後,我們可以捍衛;當既得利益者不自覺地霸凌時,我們可以表達;當對方說「女生都好情緒化、好難搞、好恰北北」時,我們可以說:「對,我就是女生,怎麼樣!這位玻璃心的男生,你還好嗎?」
如果先天的養成教育讓女性更懂委曲求全,更懂和善待人,那我們需要有意識地面對自己的憤怒,那就是勇氣的來源。要夠生氣才找得到的力量,通常是有一個捍衛的原因才找得到,因為母性是女性內建的基因,當我們很想守護時,就會想挺身作戰。
我是從接受「自己會討厭別人」這件事之後,才開始慢慢接受「原來就是有觀眾會討厭我」,無關乎我的人品與價值,只因為我代表的思想很刺激他、我說出來的話對他來說很刺耳,或只因為我是黃小胖。
如果我不是個「咖」,我沒有擁有任何思想與存在感,那我也不會對任何人帶來影響。當我接受這股關於我的力量,我越發閃耀,那些關於討厭我的聲音就越小聲,越無害。請接受某些人只是存在著就會讓你很煩躁的感覺,懂得生氣、懂得勇氣之後,就疏離那個人一點吧!不用老是複習、咀嚼討厭的感受,當你選擇活得自在,也才能感謝那個讓你學會「討厭」的人,同時也接受自己會被別人討厭的事實。
(對了,對於那些討厭我的人,有時我會很阿Q的想,說不定是我的眼睛長得像他前女友,我的聲音像他的前妻,或是我的身材像他媽,所以我會被討厭吧。)
◎幽默感是綜合感受,不是招式拆解
為什麼同樣一個笑話,他講起來好好笑,你講起來卻不好笑?
我們來聊聊,脫口秀演員為何是「演員」。不只是為了冠上一個職業別,我想更多的是我們知道怎麼「詮釋」笑話。那代表的是我們的腦中完全理解這則笑話的邏輯,我們展現出這則笑話應該要有的情緒、肢體動作以及節奏。
想像成臨摹一幅畫,明明我完全照著大師的每個步驟,甚至努力地照著用色比例,卻還是畫不好。有可能是下筆的力道,也有可能是畫畫的順序,反正各種都差一點,結果就會全盤崩解。
◆如何培養個人魅力、觀點和幽默感?
在笑話之中,演員的情緒掌握、呼吸、帶領觀眾的意識,就是火候。
要說玄一點,也可以說是靈魂。尤其自編自導自演的站立喜劇就像原創畫作,當演員很懂這則笑話的靈魂時,不一定需要照著同樣的語氣節奏(同樣的畫畫順序)進行,但就是可以傳遞笑點。
一般人在重述一則笑話時,不會想到自己的長相、背景、說話語氣、情緒、呼吸、頓點,都會影響笑話的成功度;既然複製貼上的笑果有限,那我們需要了解的是技巧。我認為,站立喜劇演員有三大條件:個人魅力、觀點、幽默感。
在各種關於表達教育的演講教學以及培育脫口秀演員的歷程中,我深深感悟到對台灣人來說,「營造個人魅力」很難,「培養觀點」很辛苦,但「擁有幽默感」卻是相對簡單。
怎麼說?看看我們全台灣的小編就知道了!幽默高手藏在民間,只要不讓他們露臉,他們可以藏在插圖與鍵盤後,開啟幽默的炸彈開關。為何會這樣?網路調查,台灣人的先天智商頗高,這絕對有幽默感的優勢。另外,民主自由的風氣也帶給我們較為無拘、素放的態度。但為何我們檯面上的幽默高手不多呢?關鍵就回到「個人魅力」與「個人觀點」。
也就是說,當「個人」被放在公眾注視下,就很難發揮。我們很在意別人的看法、他人的視線壓力,那就像是個緊箍咒,限縮我們原有的魅力與觀點,無法順利表達。
如果,當我們已經逐漸成熟到不那麼在乎別人的看法,也已經開始營造「個人魅力」,那要怎麼培養個人觀點呢?
◆學會主觀思考,才能讓你被看見、被聽見
觀點其實是主觀的心情、態度、立場。想像一下,你是一名聽眾,坐在台下百般無聊,努力忍住想拿手機的欲望。講者滔滔不絕布達一般的資訊,此時的你是不是會不由自主地放空?但如果講者主觀一點,是不是會讓你更好奇一點資訊內容?
主觀感受是一種聽覺的箭,不自覺就會射入你的耳朵,不想聽都聽得到。
或許有些人會說,我超討厭主觀的人,我不想成為主觀不顧他人感受的人。在這邊先不提「主觀是好或壞」的議題,先提「成為一個講者,必須站在聽眾的立場,觀察自己怎麼樣才會聽得到講者的訊息」。
很遺憾的是,在社群媒體抓眼球的現代,觀眾喜歡「先」知道一個講者的觀點。他到底站在什麼立場說話?他的態度是什麼?然後被他的情緒所感染,導致不自覺打開耳朵、聽到心中,可能偶有不同的觀點,或甚至聽完覺得不喜歡,但「已經聽到了」。
完全客觀的科學數據,留下的是文字資料,而人類需要的其實是情感訊息。
在台灣,上台說話等於不帶情感,是一種人們根深蒂固對於「專業」的錯誤認知。卻沒發現,各行各業有不同的專業情緒:早餐店阿姨喊「帥哥美女」是他的熱情專業;嘻哈歌手點個頭就是打招呼了,是他的態度專業;批發市場的老闆,標準配備是急促與俐落,他們才不打招呼呢!
一般人或許認為自己的舞台沒有那麼多元,最好就像主播一樣沒有情緒,面帶微笑、單純播報內容就好。但主播訓練有素的口條、清晰的聲音品質、背後帶有豐富的影像變化,這些強大的技巧與元素,都在在幫助觀眾集中注意力。可是,我們只是想模仿主播那樣的平板情緒,卻沒有意識到,主播每日處理上百條新聞,每條新聞點都富含不同的情感,因此更需要抽離、客觀,才能有條不紊──而這,不是每個上台/表達/提案所需要的精神。
尤其極力掩飾緊張時,人們會將精神專注於「鎖定」情緒,於是變得更加木訥──當潛意識告訴自己,這種情況是「專業表現」時,其實你並沒有跟聽者產生連結。
請相信,富有觀點的說話不代表情緒化,而是這樣說話讓人類打開聽覺。觀點是一個溝通的起點,不是終點,總要有人先站在某一立場思考,另一方才能幫忙試想其他層面,溝通才能漸入佳境。
所以,觀點是必須先行切入,但又可以調整的;信念與價值觀,才是觀點說話背後難以改變的東西。但一般人說話,並不會把信念或價值觀掛在嘴邊,說出「做一個善良的人」會令人頭皮發麻,但說出「你這樣××的行為很討厭」卻是我們最常出現的「有觀點的話」。
浮誇的語氣、偏頗的立場,都是方便人們聽到訊息的方法,而且很容易讓人笑出來。「這種人就是××」、「男生就是××」、「女生都很××」,別說這種語法常見在脫口秀演員的語彙中,若你身邊有人也是這樣說話,只要他不是衝著你,通常人們都會被逗樂。
◆讓情緒替你說更多,產生更大動能
課堂中,我總是花很大的力氣去解釋「觀點才能讓聽眾聽到」,但還是無法說服學生學著主觀一點。畢竟,我們的文化一直教導我們主觀以及情緒化的壞處,卻沒教會我們「先主觀但不交惡且聆聽」這種彈性的人際交流。所以我總是退而求其次,讓同學學會「成為一個更能展現情緒的人」。
教學的過程中,同學們會說出「負面情緒」這四個字。好像某些情緒是不被接受認同的,好比悲傷、憤怒、埋怨、忌妒⋯⋯等,他們無法理解「上台除了展現專業以及愉悅之外,還應該有什麼情緒?」
此時我會用最專業、愉悅的口吻陳述:「海龜需要大家停止使用塑膠製品哦!」讓大家發現,這樣沒有幫助到海龜,也沒有幫助到聽眾了解這段話的用意。聯合國氣候峰會上,來自瑞典的女孩用激進的口氣說:「你們怎麼敢?」(How dare you?)憤恨不平、情緒激昂的演說,讓世界譁然且瘋傳。回想一下,會讓聽眾目不轉睛的演說是滿載焦慮、急促、憤怒跟悲傷情緒的,不管是環保、女權、難民⋯⋯等議題,都因為情緒而讓聽眾的腦袋開始運作。
若把情緒比喻成燃料,我認為所謂的負面情緒更能產生動能:生氣的時候更專注,更有活力;悲傷的時候更善感細膩,更能同理,也更容易化悲憤為力量。
我是透過觀察自己生氣的源頭,才找到天命的。我特別容易因為「女性、性平」這樣的關鍵字而牽動情緒,而環保、動保、政治⋯⋯等相關議題,我承認我是「被教育」、「被影響」才會關注。當發掘了自己的憤怒後,找到動力來源,等於找到燃料更持久的供應方式,就能持續為其發聲。
有個特別的點是,好好笑女孩劇團徵選脫口秀演員時,我會觀察對方「愛不愛抱怨」。如果她對很多事都看不順眼,那代表她會有很多素材來源、很多想講的話、很多想改變的事,在我心底,算是一個加分的性格項目。
等等,我必須先平反一下。不是所有在台上的演員都這麼難搞!教學上充滿「包容」的黃小胖,是知道怎麼讓人展現「抱怨天份」運用在舞台上,而不是鼓勵女孩成為一個只抱怨不思幽默的人。
對什麼事都有意見的人,很適合創作,不一定適合一起生活啦!生活上充滿情緒化的表達確實讓人心累,溝通拉扯也充滿煩躁。所以在我看來,倒不如把諸多不滿轉換成創作,當開始欣賞自己的抱怨後,也會淡化對親密關係的表達張力。
提醒一下,對世界各種情況覺得很理所當然的人,其實在創作上會很辛苦哦。
◆表演不是學喜怒哀樂,而是更深層細膩的情緒表達
回到最剛開始提到的,為什麼同樣一個笑話,他講起來好好笑,你講起來卻不好笑?我認為,諧星所傳遞情緒的細膩度,代表了他懂這個笑點的精髓。這不是嘴角上揚幾度、眼球轉向哪裡、語氣停頓幾秒的問題,幽默感需要你對世界的綜合感受。
這也是我認為表演課應該是人生必修課的原因。每一個人都應該理解並且擁抱情緒,透過學習,會認知自己的存在,進行深層的自我對話。坊間對於表演課的認知是學習喜、怒、哀、樂,對我來說,那是套用在國民教育底下的認知標準,把情緒拆解成四大方向,每一個分成十級分,代表方便打分數。但學過表演的人就知道,原來光是「喜」的層次就超越百種,沒有好壞標準,只有角色背景,也就是「你是誰?」、「你為什麼而喜?」、「你想將喜傳達給誰?」、「你想怎麼表現喜?」。
演技就是這樣難以言喻。
在學習感受的過程,有時會放大情緒而導致困擾,但接下來更重要的步驟,就是學習轉換思維,把所有不甘心的、不合理的、只有對立面的事物,用「抽離」的心態看待它。
什麼是抽離?想像自己是另一個攝影師正在看待眼前的事物,有沒有別種角度會令你發笑?或者身處不同的時空、背景、文化,會不會令你覺得這一切很荒謬?如果沒有面臨到攸關生死與創傷,是不是可以放寬一點點標準?如果不用那麼嚴肅地面對失敗或錯誤,或許就可以種下幽默的種子。
很多諧星都是以面癱聞名,臉上幾乎沒有表情地說出笑點,人稱冷面笑匠。這種諧星並不符合前面所分享的情緒高漲,有時會讓觀眾以為這才是喜劇的精髓。那麼他到底是很抽離還是很情緒化?
根據我的觀察,會想上台,將自己的思想放在檯面上的人,其實都具備勇氣、想改變世界、渴望被聽到的心。而不管他的外包裝偏向抽離或是情緒化,他一定對世界充滿情感,那麼你呢?
──「你有討厭的人嗎?」
面對著深陷自我糾結,不停地渴望別人愛我、不願意被人討厭的學生,我常會問出這句話:「你有討厭的人嗎?」
對方可能會遲疑許久才支支吾吾地說,「我有討厭的人。」那神情帶有罪惡感,她不願意承認自己會討厭別人,也不想面對自己的黑暗面。畢竟大多數女生從小被教導著端莊、優雅、與人為善⋯⋯等好女孩基本功。
而既然她親口承認了腹黑面,那我會接著問:「討厭誰?告訴我全名。」
我可以感覺到她心跳加速,有時腦袋快速運轉著「要講哪一個?」、有時連講出那個人的名字都有一定程度的厭惡感而不自知,有時卻帶著興奮,因為直接面對自己最深層的想法時,其實很豁然開朗。等待那些情緒一閃而過後,她衝口而出「XXX」,我期待的是她的舒暢感。那種感覺很像做了一場心靈SPA,一直浸泡在滾熱的水中,等到鼓起勇氣踩進透沁涼的冷水裡,全身刺麻地接受這種名為「討厭」的感覺。
我們會討厭別人,但我們連討厭的感覺都不知道。我們還會有一種標準詢問自己,這樣算是討厭嗎?嘿!女孩,你知道高潮的時候有沒有到,卻告訴自己要很討厭才算討厭──不是這樣的,一點點高潮也算高潮。
◆接受討厭別人的自己,讓勇氣誕生出來
我們先來接受情緒的合理性,每個人都可以討厭人,包括自己,當然也可以討厭別人,並且沒來由地討厭。有些人的存在本身就很刺眼,扎入你心裡的煩躁,想到他就覺得不舒適,甚至會有噁心感,這大大小小的情緒感受,都是討厭。
無端討厭別人,的確是一種不友善的行為。我們不用放大這種感受,時時刻刻想著那個討厭的存在,但我們可以接受會討厭別人的自己。這樣一來,當別人沒有理由的討厭你時,你反而比較能夠理解對方。關於「被討厭的勇氣」,或許我們先學著接受自己的卑劣黑暗面,才有機會讓勇氣誕生出來。
有些同學會顧左右而言他,說自己是討厭那件事、不是討厭那個人。這樣雖然聽起來比較圓融和善,但事實上也是把自己陷入於「只要自己行為改善,就會讓所有人都喜歡」的情境中。承認吧!有些人只是存在著就讓你感到刺眼煩躁。而你也有可能只是存在著,就讓某個人覺得不願接近。總有些學生,無法接受自己會被討厭,所以也無法討厭別人。他們時常會散發一種討好的氛圍,對方說什麼她都好,認為這叫隨和,實際上她把決定的權力交給對方,壓住她心底的埋怨與不認同,這種只要對方不討厭我就好的相處模式,其實讓人倍感壓力呢!
有趣的是,這種時不時討好別人的人,最常羨慕的對象就是「必取」(Bitch),對於自媒體那些勇敢說出「不喜歡我就閃開」的名人有著非比尋常的投射。我很好奇,是那些名人自帶光環才讓人心生嚮往?還是這些人內心太過沒有價值感,必須用討好來感受自己的存在?
◆找到自己的價值,就不怕別人討厭
四十歲的我,在人際關係上分合多次,發現那些坦率地承認某些物種就是跟我不合的人,反而好相處。畢竟我們已經生活在近代,人類文明已經多元到不需要符合每個人的價值觀就能活著。於是,社會教我的是,不用跟每個人做朋友。
我是在站立幫(注:由台灣喜劇之父張碩修成立的全台第一個喜劇團體)學會討厭的感受,那是我三十歲左右的事。在那之前,原生離異家庭導致我向外發展,在朋友群中常常是領導位置,外向、活潑、幽默、好相處是我的標籤,從來沒遇過交朋友這麼辛苦的局面。
可是,脫口秀不只是交朋友啊~我們要負擔的是各自段落的笑點,還要在團隊演出中合作。自編自導自演的演出中,牽扯的不只是隨和程度,還有更多來自個人的創作,也就是「個人價值觀」。
什麼東西好笑?這來自於個人的背景與觀點。當一群男生聚在一起時的幹話,集結成一齣現場喜劇,唯一的女生要隨和地飾演花瓶?還是要板起臉說「這根本就不好笑」?
這兩種情況我都嘗試了,甚至跟著台上的音樂節奏高喊:「前女友,婊子!」看著當事人變臉離開演出場地,經過我的身邊,有個抽離的我在捶打自己:「黃小胖!你是誰?」那一幕午夜夢迴時常常出現,我真的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
為了舞台機會,我願意討好,討好觀眾、夥伴,卻忘了討好我自己。第一年的演出,充滿自我懷疑。用二十八年確認夢想站上舞台的我,不喜歡這些製作背後的價值系統,我學會很多貶抑女性的名詞,出演更多被幻想的角色,我努力地變得更漂亮來迎合主流價值、表現隨和,直到當我反彈時招致「情緒化」的回應。不會吵架的我,在每次團練會議中表現冷漠、嚴肅、哭泣,都無法好好解釋自己身為女性的無奈與受傷。我覺得有些觀點很難笑,但他們笑瘋了啊!在笑點為上的世界中,要怎麼表現生氣才對?要怎麼樣表現生氣,才能是他們心中懂幽默的女性?
五、六年來的「鬧不合」,因為一個導火線,我離開站立幫。而後,經歷結婚、生子,再度回歸演出「十光機」,沒有太多的和解動作或剖心時刻,因為時間夠我們長大成熟。我們開始懂,爭吵都是在辯證自我,都是讓我們更成為「自己」。而成為自己的過程中,不能抗拒衝突,也不需要別人欣然接受蛻變的你。
◆有意識地面對討厭與憤怒,那是你勇氣的來源
當我選擇另覓表演舞台後,自製演出並專心耕耘女性幽默,不處於同一個競爭的環境中,我反而看到自己的價值。之前的我,覺得要有贏的把握才可以「現」;後來我明白了,展現力量也可以堅定,甚至帶有溫柔。
展現力量不代表打趴別人,女權的存在不是為了打趴男性,而是讓我們懂,我們可以爭取;當有不平等的形式藏在話語權背後,我們可以捍衛;當既得利益者不自覺地霸凌時,我們可以表達;當對方說「女生都好情緒化、好難搞、好恰北北」時,我們可以說:「對,我就是女生,怎麼樣!這位玻璃心的男生,你還好嗎?」
如果先天的養成教育讓女性更懂委曲求全,更懂和善待人,那我們需要有意識地面對自己的憤怒,那就是勇氣的來源。要夠生氣才找得到的力量,通常是有一個捍衛的原因才找得到,因為母性是女性內建的基因,當我們很想守護時,就會想挺身作戰。
我是從接受「自己會討厭別人」這件事之後,才開始慢慢接受「原來就是有觀眾會討厭我」,無關乎我的人品與價值,只因為我代表的思想很刺激他、我說出來的話對他來說很刺耳,或只因為我是黃小胖。
如果我不是個「咖」,我沒有擁有任何思想與存在感,那我也不會對任何人帶來影響。當我接受這股關於我的力量,我越發閃耀,那些關於討厭我的聲音就越小聲,越無害。請接受某些人只是存在著就會讓你很煩躁的感覺,懂得生氣、懂得勇氣之後,就疏離那個人一點吧!不用老是複習、咀嚼討厭的感受,當你選擇活得自在,也才能感謝那個讓你學會「討厭」的人,同時也接受自己會被別人討厭的事實。
(對了,對於那些討厭我的人,有時我會很阿Q的想,說不定是我的眼睛長得像他前女友,我的聲音像他的前妻,或是我的身材像他媽,所以我會被討厭吧。)
◎幽默感是綜合感受,不是招式拆解
為什麼同樣一個笑話,他講起來好好笑,你講起來卻不好笑?
我們來聊聊,脫口秀演員為何是「演員」。不只是為了冠上一個職業別,我想更多的是我們知道怎麼「詮釋」笑話。那代表的是我們的腦中完全理解這則笑話的邏輯,我們展現出這則笑話應該要有的情緒、肢體動作以及節奏。
想像成臨摹一幅畫,明明我完全照著大師的每個步驟,甚至努力地照著用色比例,卻還是畫不好。有可能是下筆的力道,也有可能是畫畫的順序,反正各種都差一點,結果就會全盤崩解。
◆如何培養個人魅力、觀點和幽默感?
在笑話之中,演員的情緒掌握、呼吸、帶領觀眾的意識,就是火候。
要說玄一點,也可以說是靈魂。尤其自編自導自演的站立喜劇就像原創畫作,當演員很懂這則笑話的靈魂時,不一定需要照著同樣的語氣節奏(同樣的畫畫順序)進行,但就是可以傳遞笑點。
一般人在重述一則笑話時,不會想到自己的長相、背景、說話語氣、情緒、呼吸、頓點,都會影響笑話的成功度;既然複製貼上的笑果有限,那我們需要了解的是技巧。我認為,站立喜劇演員有三大條件:個人魅力、觀點、幽默感。
在各種關於表達教育的演講教學以及培育脫口秀演員的歷程中,我深深感悟到對台灣人來說,「營造個人魅力」很難,「培養觀點」很辛苦,但「擁有幽默感」卻是相對簡單。
怎麼說?看看我們全台灣的小編就知道了!幽默高手藏在民間,只要不讓他們露臉,他們可以藏在插圖與鍵盤後,開啟幽默的炸彈開關。為何會這樣?網路調查,台灣人的先天智商頗高,這絕對有幽默感的優勢。另外,民主自由的風氣也帶給我們較為無拘、素放的態度。但為何我們檯面上的幽默高手不多呢?關鍵就回到「個人魅力」與「個人觀點」。
也就是說,當「個人」被放在公眾注視下,就很難發揮。我們很在意別人的看法、他人的視線壓力,那就像是個緊箍咒,限縮我們原有的魅力與觀點,無法順利表達。
如果,當我們已經逐漸成熟到不那麼在乎別人的看法,也已經開始營造「個人魅力」,那要怎麼培養個人觀點呢?
◆學會主觀思考,才能讓你被看見、被聽見
觀點其實是主觀的心情、態度、立場。想像一下,你是一名聽眾,坐在台下百般無聊,努力忍住想拿手機的欲望。講者滔滔不絕布達一般的資訊,此時的你是不是會不由自主地放空?但如果講者主觀一點,是不是會讓你更好奇一點資訊內容?
主觀感受是一種聽覺的箭,不自覺就會射入你的耳朵,不想聽都聽得到。
或許有些人會說,我超討厭主觀的人,我不想成為主觀不顧他人感受的人。在這邊先不提「主觀是好或壞」的議題,先提「成為一個講者,必須站在聽眾的立場,觀察自己怎麼樣才會聽得到講者的訊息」。
很遺憾的是,在社群媒體抓眼球的現代,觀眾喜歡「先」知道一個講者的觀點。他到底站在什麼立場說話?他的態度是什麼?然後被他的情緒所感染,導致不自覺打開耳朵、聽到心中,可能偶有不同的觀點,或甚至聽完覺得不喜歡,但「已經聽到了」。
完全客觀的科學數據,留下的是文字資料,而人類需要的其實是情感訊息。
在台灣,上台說話等於不帶情感,是一種人們根深蒂固對於「專業」的錯誤認知。卻沒發現,各行各業有不同的專業情緒:早餐店阿姨喊「帥哥美女」是他的熱情專業;嘻哈歌手點個頭就是打招呼了,是他的態度專業;批發市場的老闆,標準配備是急促與俐落,他們才不打招呼呢!
一般人或許認為自己的舞台沒有那麼多元,最好就像主播一樣沒有情緒,面帶微笑、單純播報內容就好。但主播訓練有素的口條、清晰的聲音品質、背後帶有豐富的影像變化,這些強大的技巧與元素,都在在幫助觀眾集中注意力。可是,我們只是想模仿主播那樣的平板情緒,卻沒有意識到,主播每日處理上百條新聞,每條新聞點都富含不同的情感,因此更需要抽離、客觀,才能有條不紊──而這,不是每個上台/表達/提案所需要的精神。
尤其極力掩飾緊張時,人們會將精神專注於「鎖定」情緒,於是變得更加木訥──當潛意識告訴自己,這種情況是「專業表現」時,其實你並沒有跟聽者產生連結。
請相信,富有觀點的說話不代表情緒化,而是這樣說話讓人類打開聽覺。觀點是一個溝通的起點,不是終點,總要有人先站在某一立場思考,另一方才能幫忙試想其他層面,溝通才能漸入佳境。
所以,觀點是必須先行切入,但又可以調整的;信念與價值觀,才是觀點說話背後難以改變的東西。但一般人說話,並不會把信念或價值觀掛在嘴邊,說出「做一個善良的人」會令人頭皮發麻,但說出「你這樣××的行為很討厭」卻是我們最常出現的「有觀點的話」。
浮誇的語氣、偏頗的立場,都是方便人們聽到訊息的方法,而且很容易讓人笑出來。「這種人就是××」、「男生就是××」、「女生都很××」,別說這種語法常見在脫口秀演員的語彙中,若你身邊有人也是這樣說話,只要他不是衝著你,通常人們都會被逗樂。
◆讓情緒替你說更多,產生更大動能
課堂中,我總是花很大的力氣去解釋「觀點才能讓聽眾聽到」,但還是無法說服學生學著主觀一點。畢竟,我們的文化一直教導我們主觀以及情緒化的壞處,卻沒教會我們「先主觀但不交惡且聆聽」這種彈性的人際交流。所以我總是退而求其次,讓同學學會「成為一個更能展現情緒的人」。
教學的過程中,同學們會說出「負面情緒」這四個字。好像某些情緒是不被接受認同的,好比悲傷、憤怒、埋怨、忌妒⋯⋯等,他們無法理解「上台除了展現專業以及愉悅之外,還應該有什麼情緒?」
此時我會用最專業、愉悅的口吻陳述:「海龜需要大家停止使用塑膠製品哦!」讓大家發現,這樣沒有幫助到海龜,也沒有幫助到聽眾了解這段話的用意。聯合國氣候峰會上,來自瑞典的女孩用激進的口氣說:「你們怎麼敢?」(How dare you?)憤恨不平、情緒激昂的演說,讓世界譁然且瘋傳。回想一下,會讓聽眾目不轉睛的演說是滿載焦慮、急促、憤怒跟悲傷情緒的,不管是環保、女權、難民⋯⋯等議題,都因為情緒而讓聽眾的腦袋開始運作。
若把情緒比喻成燃料,我認為所謂的負面情緒更能產生動能:生氣的時候更專注,更有活力;悲傷的時候更善感細膩,更能同理,也更容易化悲憤為力量。
我是透過觀察自己生氣的源頭,才找到天命的。我特別容易因為「女性、性平」這樣的關鍵字而牽動情緒,而環保、動保、政治⋯⋯等相關議題,我承認我是「被教育」、「被影響」才會關注。當發掘了自己的憤怒後,找到動力來源,等於找到燃料更持久的供應方式,就能持續為其發聲。
有個特別的點是,好好笑女孩劇團徵選脫口秀演員時,我會觀察對方「愛不愛抱怨」。如果她對很多事都看不順眼,那代表她會有很多素材來源、很多想講的話、很多想改變的事,在我心底,算是一個加分的性格項目。
等等,我必須先平反一下。不是所有在台上的演員都這麼難搞!教學上充滿「包容」的黃小胖,是知道怎麼讓人展現「抱怨天份」運用在舞台上,而不是鼓勵女孩成為一個只抱怨不思幽默的人。
對什麼事都有意見的人,很適合創作,不一定適合一起生活啦!生活上充滿情緒化的表達確實讓人心累,溝通拉扯也充滿煩躁。所以在我看來,倒不如把諸多不滿轉換成創作,當開始欣賞自己的抱怨後,也會淡化對親密關係的表達張力。
提醒一下,對世界各種情況覺得很理所當然的人,其實在創作上會很辛苦哦。
◆表演不是學喜怒哀樂,而是更深層細膩的情緒表達
回到最剛開始提到的,為什麼同樣一個笑話,他講起來好好笑,你講起來卻不好笑?我認為,諧星所傳遞情緒的細膩度,代表了他懂這個笑點的精髓。這不是嘴角上揚幾度、眼球轉向哪裡、語氣停頓幾秒的問題,幽默感需要你對世界的綜合感受。
這也是我認為表演課應該是人生必修課的原因。每一個人都應該理解並且擁抱情緒,透過學習,會認知自己的存在,進行深層的自我對話。坊間對於表演課的認知是學習喜、怒、哀、樂,對我來說,那是套用在國民教育底下的認知標準,把情緒拆解成四大方向,每一個分成十級分,代表方便打分數。但學過表演的人就知道,原來光是「喜」的層次就超越百種,沒有好壞標準,只有角色背景,也就是「你是誰?」、「你為什麼而喜?」、「你想將喜傳達給誰?」、「你想怎麼表現喜?」。
演技就是這樣難以言喻。
在學習感受的過程,有時會放大情緒而導致困擾,但接下來更重要的步驟,就是學習轉換思維,把所有不甘心的、不合理的、只有對立面的事物,用「抽離」的心態看待它。
什麼是抽離?想像自己是另一個攝影師正在看待眼前的事物,有沒有別種角度會令你發笑?或者身處不同的時空、背景、文化,會不會令你覺得這一切很荒謬?如果沒有面臨到攸關生死與創傷,是不是可以放寬一點點標準?如果不用那麼嚴肅地面對失敗或錯誤,或許就可以種下幽默的種子。
很多諧星都是以面癱聞名,臉上幾乎沒有表情地說出笑點,人稱冷面笑匠。這種諧星並不符合前面所分享的情緒高漲,有時會讓觀眾以為這才是喜劇的精髓。那麼他到底是很抽離還是很情緒化?
根據我的觀察,會想上台,將自己的思想放在檯面上的人,其實都具備勇氣、想改變世界、渴望被聽到的心。而不管他的外包裝偏向抽離或是情緒化,他一定對世界充滿情感,那麼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