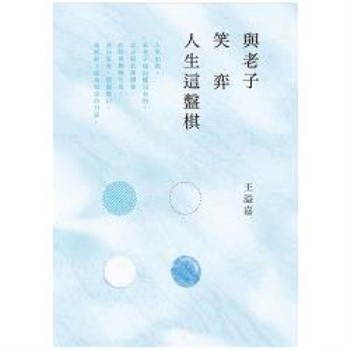【內文節選一】
道:自然與人生Vs物理與哲理
【原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翻譯】
可以用語言表述的「道」,就不是恆常的「道」。可以用名稱界定的「名」,就不是恆常的「名」。「無」,是天地的起始;「有」,是萬物的根源。所以,從「無」的角度,可以揣摩「道」的奧妙;從「有」的角度,可以觀察「道」的蹤跡。「無」和「有」的名稱雖然不同,來源卻相同;這種同一,就叫做玄祕。玄祕而又玄祕啊!是宇宙萬般奧妙的總門戶。
【弈後語】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老子的這個起手式真是玄妙無比。一個對人生感到好奇、喜歡思考、想要了解這個塵世及周遭萬事萬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人,必然會被他這段話所吸引(老子是誰眾說紛紜,下面就單以「老子」來統稱《道德經》的所有可能作者)。
宇宙萬物是如何產生與運作的呢?很多人把它推給一個造物主(上帝),而「道」則是老子所提供的答案。但他開宗明義就提醒我們,真正的「道」是不可言說,無法用語言文字做完整而精確的表達,因為語文不只有它的侷限性,更有它的歧義性,老子所說的「道」,還有接下來的「無」與「有」等都是「名」,它們真正的涵義是什麼,就一直眾說紛紜。但我想這並非老子在故弄玄虛,而是他一語道破了人類在認知與探究諸多問題時的困境。
有人指出,既然老子一開口就說「道可道,非常道」,那接下來為什麼還說得那麼多,不是在自打嘴巴嗎?我以為這正是一個偉大思想家應該有的風範――樂於思考、表達自己對諸多問題的看法,但同時又提醒自己和他人,自己的觀點絕非什麼「絕對真理」,既不周全完備,可能還有不少破綻、錯誤,歡迎找碴。這也是我們這些後生小輩在讀《道德經》時應該有的態度:即使老子說得再好,我們也不能盲目地全盤接受,而要自己用心去思考和推敲,當他露出破綻時,可能還需要好好戳他一下。宇宙萬物都是「有」,但這些「有」從何而來?我們一直往上推,即使把它們推給上帝,上帝又從何而來?老子認為宇宙萬物的最初根源是「無」,這裡所說的「無」可以是空無、無可名狀、不可思議的一種狀態;然後從「無」裡生出「有」,然後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見第四一局)。而「無」裡為什麼會生出「有」?答案就是「道」。這個說法看似玄妙,跟當今物理學界對宇宙起源的觀點倒是非常類似: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宇宙是由一個密度無限大、體積無限小、無可名狀、不可思議的「奇點」在大約兩百億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不斷擴張、衍生而成。而在此之前,什麼都沒有,連時間也不存在,也就是「無」。
老子所說的「道」、「無」與「有」,還讓人想起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說過的一段話:「所有的事物……都是由一種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所決定。上至星辰下至昆蟲,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不論是人類、蔬菜還是宇宙塵──我們都是隨著一種神祕的音樂起舞,然而這吹奏者卻遙不可測。」愛因斯坦所說的「吹奏者」,讓人想起基督教的「上帝」,但我以為它更接近老子所說的「道」,兩者有不少互通之處:
愛因斯坦認為宇宙萬象背後有一些共通的運作律則,也就是現在通稱的「物理」。「物理」包含兩個面向:一是「物」――星辰、昆蟲、人類、蔬菜等存在物;一是「理」――神祕的音樂、萬有引力、磁場、能量等律則。「物」就是老子所說的「有」,「理」就是「無」(無形的律則);從物質面,我們可以看到「道」的蹤跡(觀其徼);從律則面,我們可以認識「道」的奧妙(觀其妙)。物質(有)與律則(無)乃是「道」一體的兩面(同出而異名),但為什麼會有這些物質和律則?它們又如何形成?愛因斯坦覺得神祕難解、遙不可測,也就是老子所說的「玄」。但我並不想跟某些人一樣穿鑿附會,說老子是什麼「現代物理學或宇宙學的先知」。因為我認為老子畢竟只是個哲學家、思想家而非科學家、物理學家,他對宇宙起源與法則的描述是哲學式的,可能來自他的觀察與思考,它們之所以和發軔於西方的當代物理學有類似或雷同之處,也許就像皮亞傑(J.Piaget)所說:「知識的結構在反映心智的結構。」――不管古今中外,所有偉大的人類心智在思索同一個問題時,經常會得到同樣的結論。我們要知道,愛因斯坦就是老子的忠實讀者,知名的華人數學家陳省身說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時,曾到愛因斯坦家裡做客,就在愛氏書籍不多的書架上看到一本德文譯本的《道德經》,愛因斯坦跟老子應該是惺惺相惜。
但我還是必須說,老子的「道」跟愛因斯坦的「神祕音樂」仍然有所不同。基本上,愛因斯坦是個物理學家,他說的只侷限於自然界的物質、現象與律則,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天道」;但身為哲學家的老子卻想將「天道」擴及「人道」,也就是想藉他對自然現象、律則的觀察與思考鋪衍出一套用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這是否可以成立?在一個層面(天)出現的現象或律則,必然會重現或適用於另一個層面(人)嗎?就讓我們慢慢看下去吧!
【內文節選二】
以道為師:成就偉大的三不主義
【原文】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翻譯】
大道彌漫,像河水氾濫,無所不在,周流左右。萬物依賴它生長而不推辭,成就一切而不占有,養育萬物而不自以為主,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它是「小」;萬物都歸附於它,而它卻不加以主宰,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它是「大」。因為它從不自以為大,所以能成就它的偉大。
【弈後語】
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是個浪漫主義者,在政治方面,他堅持自由民主的理想,為理想而奮鬥,可歌可泣、無怨無悔;在愛情方面,則秉持「三不主義」原則,周旋於眾多異性間,多采多姿、無牽無掛。所謂「三不主義」,就是「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這個原則使他縱橫情場幾十年,雖然韻事不斷、艷福匪淺,但從來沒有惹禍上身,也沒有給對方增添麻煩,可以說是他獨特的「浪漫之道」。在這一局,老子也提出「道」的「三不主義」:不推辭、不占有、不作主。首先,他說「道」是無所不在的(泛兮),我們周遭的萬物,從日月星辰、山川木石到蟲魚花鳥,包括我們人類在內,身上都有道的蹤影。接下來指出「道」的三個特性:第一,「不推辭」:萬物都依賴「道」來生長,「道」對此從不推辭,更不拒絕。第二,「不占有」:「道」成就宇宙中的一切,但對這一切卻都不會據為己有。第三,「不作主」:「道」養育萬物,但卻不以主人自居;放任萬物自行發展,不會替它們作主。施明德的「三不主義」跟老子的「三不主義」頗為類似,因為都有「順其自然」之意。
從某個角度來看,「道」的「不作主」可以說是卑微(小)的,因為它聽憑萬物自作主張,好像自己沒有甚麼權力、甚至不負責任;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不作主」卻也是偉大的(大),因為萬物都依靠「道」,但「道」卻不會因此而想要主宰萬物,它尊重它們。「道」不僅可大可小,而且因為不自認為自己偉大,所以反而成就了它的偉大,這跟前面所說的「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一樣,都是在反映老子獨特的逆向辯證思維。
當然,老子的用意絕不只是要我們認識「道」的特性而已,更期待大家能成為得道之士與行道之人。這並非在強人所難,因為「道」無所不在,我們每個人都是「道」的載體,都可以在自己身上顯現「道」的特性――不推辭、不占有與不作主,也就是「三不主義」。
不管是當老闆或做員工、做父親或當兒子,對於自己應該做甚至忽然加到自己身上的工作都自在承擔,不推辭、不抱怨,這種「不推辭」就是「道」的表現。雖然做了很多事、得到各種收穫,但卻不居功、不據為己有,這種「不占有」也是在表現「道」。雖然子女、員工、學生等等有很多人都依靠你而得以成長、發展,但你如果能不以主宰自居,不要他們聽命於你,而讓他們依本性去自由發展,這種「不作主」就更是「道」的表現。
在為人處事方面,能奉行這「三不主義」,就是在行道,在「人道」中顯現「天道」。這樣的人當然不會自認為偉大,而這正是他讓人覺得偉大的地方。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施明德那聽起來有點吊兒郎當的「三不主義」,也許也可以我們一些新的啟發。【內文節選三】
理想世界:回到過去或邁向未來?
【原文】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翻譯】
國家小,人口少。即使有各種器具也不使用。人們愛惜生命而不遠行遷徙。雖有車船,卻沒有必要乘坐;雖有武器裝備,卻沒有地方部署。讓人們回復到結繩記事的狀態。
在這樣的國土裡,人民有甜美的飲食,美觀的服飾,安適的居所,歡樂的習俗。鄰國之間彼此可以看見,雞鳴狗叫聲也相互可以聽到,但人民從生到死,卻不相往來。
【弈後語】
在這一局,老子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國。但看起來,這個理想國似乎不是在未來,而是在過去;從務實的角度來看,不僅不可能實現,而且也不是很理想。
不可能實現,主要是因為人類的文明是不斷前進的,不太可能再走回頭路。要大家回復到結繩記事的狀態,不僅是在開時代倒車,而且是強人所難。當大家都在使用電燈時,偶而點點蠟燭,發發思古之幽情,為生活增加情趣,似乎也不錯;但若要大家把電燈都收起來,丟進倉庫裡,全部都改用過去的蠟燭,那怎麼可能?
不太理想,因為在比較之下,明明有更好的東西,卻要大家用較差的東西,自然會讓人失望。小國寡民,聽起來似乎不錯,但雞犬相聞,卻又要大家老死不相往來,生活不僅容易變得閉鎖、沉悶,也違反自然。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因為老子所處時代的政治昏暗、人欲橫流、社會動盪、大國不斷兼併小國、人民離散、生活痛苦,他的理想國主要是有感於此而提出的一個心靈避難所。除了有濃厚的復古意味外(儒家的理想國也是在過去,但西方則大異其趣,他們的理想世界通常是在未來),不重物質而強調精神生活的滿足更是重點,所謂「老死不相往來」並非有意閉鎖,而是精神生活若圓滿自足,就不會對外界有太大的興趣,也不必寄望於他人或外界為自己的人生提供意義。老子的理想國讓我想起位於喜馬拉雅山腳下的不丹小國:根據聯合國在二○○四年的全球人類發展報告,不丹在一九二個國家中位居一三四名,不只經濟與物質生活相對落後,也相當閉鎖,她直到一九七四年才開放外國人進入,一九九九年才有電視。但在二○○六年英國萊斯特大學公布的《全球快樂排行榜》中,不丹在一七八個國家卻名列第八,位居亞洲第一位,比日本高出八十名,比美國高出九名。為什麼不丹人會特別快樂?因為前國王旺楚克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施政方針是不像其他國家般追求「國民生產毛額」(GDP),他要的是「國民幸福指數」(GNH),重視社會和諧與人民精神生活的滿足,曾經創下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民感覺幸福的紀錄,還因此而被譽為人間最後的樂土。這似乎印證了老子的某些說法。
但諷刺的是,當愈來愈多的外國人因慕名而進入這塊人間最後的樂土,還有在二○○八年轉型成民主政體,加快現代化的腳步後,擁有電視、手機、電腦、汽車的人愈來愈多,但生活卻愈來愈不快樂,竊盜、搶劫等犯罪頻傳,酗酒、吸毒人數激增,到二○一一年,感覺幸福的不丹人已降為百分之四十一。這似乎也在支持老子的某些論點,追逐物欲只會讓人更感空虛。
不丹人為什麼會變得比較不幸福,牽涉到很多因素。幸福其實是一種很主觀的感受,過去不丹人覺得很幸福,有一個原因是他們缺乏比較,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人過著什麼生活,想當然爾地覺得自己很幸福;但在和外界接觸愈多、了解愈多後,相較之下,就會有愈多的人覺得自己其實不幸福。這也是為什麼有人會說「無知是一種幸福」的原因,老子在前面所說的「常使民無知無欲」是否也有這個意思?值得大家深思。但為了讓人保持這種「主觀的幸福感」,就必須過著與外界隔絕的生活、甚至禁止人民和外界接觸嗎?我以為這是鴕鳥心態,也沒有人有權這樣做。曾任美國經濟學會與美國科學促進會會長的伯丁教授,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跟老子的「小國寡民」有點類似:他認為未來的理想世界應該由大約五百個獨立的國家所組成,這些國家都像「島嶼」一樣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與認同,也有產生個別突變的能力,但並非老死不相往來,而是透過貿易、旅遊與國際組織而彼此有密切的接觸。但在接觸中,他們不是互相羨慕,而是彼此欣賞,對自己國家與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有相當的自信,也許可以擷取他人的一些優點來彌補自己的不足,但絕不會在比較中迷失自我。
也許這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世界吧?當然,它也不見得能實現。但對個人來說,認為美好人生應該是在有待開發的未來,而不是在無可挽回的過去,才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態度吧!
道:自然與人生Vs物理與哲理
【原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翻譯】
可以用語言表述的「道」,就不是恆常的「道」。可以用名稱界定的「名」,就不是恆常的「名」。「無」,是天地的起始;「有」,是萬物的根源。所以,從「無」的角度,可以揣摩「道」的奧妙;從「有」的角度,可以觀察「道」的蹤跡。「無」和「有」的名稱雖然不同,來源卻相同;這種同一,就叫做玄祕。玄祕而又玄祕啊!是宇宙萬般奧妙的總門戶。
【弈後語】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老子的這個起手式真是玄妙無比。一個對人生感到好奇、喜歡思考、想要了解這個塵世及周遭萬事萬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人,必然會被他這段話所吸引(老子是誰眾說紛紜,下面就單以「老子」來統稱《道德經》的所有可能作者)。
宇宙萬物是如何產生與運作的呢?很多人把它推給一個造物主(上帝),而「道」則是老子所提供的答案。但他開宗明義就提醒我們,真正的「道」是不可言說,無法用語言文字做完整而精確的表達,因為語文不只有它的侷限性,更有它的歧義性,老子所說的「道」,還有接下來的「無」與「有」等都是「名」,它們真正的涵義是什麼,就一直眾說紛紜。但我想這並非老子在故弄玄虛,而是他一語道破了人類在認知與探究諸多問題時的困境。
有人指出,既然老子一開口就說「道可道,非常道」,那接下來為什麼還說得那麼多,不是在自打嘴巴嗎?我以為這正是一個偉大思想家應該有的風範――樂於思考、表達自己對諸多問題的看法,但同時又提醒自己和他人,自己的觀點絕非什麼「絕對真理」,既不周全完備,可能還有不少破綻、錯誤,歡迎找碴。這也是我們這些後生小輩在讀《道德經》時應該有的態度:即使老子說得再好,我們也不能盲目地全盤接受,而要自己用心去思考和推敲,當他露出破綻時,可能還需要好好戳他一下。宇宙萬物都是「有」,但這些「有」從何而來?我們一直往上推,即使把它們推給上帝,上帝又從何而來?老子認為宇宙萬物的最初根源是「無」,這裡所說的「無」可以是空無、無可名狀、不可思議的一種狀態;然後從「無」裡生出「有」,然後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見第四一局)。而「無」裡為什麼會生出「有」?答案就是「道」。這個說法看似玄妙,跟當今物理學界對宇宙起源的觀點倒是非常類似: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宇宙是由一個密度無限大、體積無限小、無可名狀、不可思議的「奇點」在大約兩百億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不斷擴張、衍生而成。而在此之前,什麼都沒有,連時間也不存在,也就是「無」。
老子所說的「道」、「無」與「有」,還讓人想起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說過的一段話:「所有的事物……都是由一種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所決定。上至星辰下至昆蟲,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不論是人類、蔬菜還是宇宙塵──我們都是隨著一種神祕的音樂起舞,然而這吹奏者卻遙不可測。」愛因斯坦所說的「吹奏者」,讓人想起基督教的「上帝」,但我以為它更接近老子所說的「道」,兩者有不少互通之處:
愛因斯坦認為宇宙萬象背後有一些共通的運作律則,也就是現在通稱的「物理」。「物理」包含兩個面向:一是「物」――星辰、昆蟲、人類、蔬菜等存在物;一是「理」――神祕的音樂、萬有引力、磁場、能量等律則。「物」就是老子所說的「有」,「理」就是「無」(無形的律則);從物質面,我們可以看到「道」的蹤跡(觀其徼);從律則面,我們可以認識「道」的奧妙(觀其妙)。物質(有)與律則(無)乃是「道」一體的兩面(同出而異名),但為什麼會有這些物質和律則?它們又如何形成?愛因斯坦覺得神祕難解、遙不可測,也就是老子所說的「玄」。但我並不想跟某些人一樣穿鑿附會,說老子是什麼「現代物理學或宇宙學的先知」。因為我認為老子畢竟只是個哲學家、思想家而非科學家、物理學家,他對宇宙起源與法則的描述是哲學式的,可能來自他的觀察與思考,它們之所以和發軔於西方的當代物理學有類似或雷同之處,也許就像皮亞傑(J.Piaget)所說:「知識的結構在反映心智的結構。」――不管古今中外,所有偉大的人類心智在思索同一個問題時,經常會得到同樣的結論。我們要知道,愛因斯坦就是老子的忠實讀者,知名的華人數學家陳省身說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時,曾到愛因斯坦家裡做客,就在愛氏書籍不多的書架上看到一本德文譯本的《道德經》,愛因斯坦跟老子應該是惺惺相惜。
但我還是必須說,老子的「道」跟愛因斯坦的「神祕音樂」仍然有所不同。基本上,愛因斯坦是個物理學家,他說的只侷限於自然界的物質、現象與律則,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天道」;但身為哲學家的老子卻想將「天道」擴及「人道」,也就是想藉他對自然現象、律則的觀察與思考鋪衍出一套用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這是否可以成立?在一個層面(天)出現的現象或律則,必然會重現或適用於另一個層面(人)嗎?就讓我們慢慢看下去吧!
【內文節選二】
以道為師:成就偉大的三不主義
【原文】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翻譯】
大道彌漫,像河水氾濫,無所不在,周流左右。萬物依賴它生長而不推辭,成就一切而不占有,養育萬物而不自以為主,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它是「小」;萬物都歸附於它,而它卻不加以主宰,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它是「大」。因為它從不自以為大,所以能成就它的偉大。
【弈後語】
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是個浪漫主義者,在政治方面,他堅持自由民主的理想,為理想而奮鬥,可歌可泣、無怨無悔;在愛情方面,則秉持「三不主義」原則,周旋於眾多異性間,多采多姿、無牽無掛。所謂「三不主義」,就是「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這個原則使他縱橫情場幾十年,雖然韻事不斷、艷福匪淺,但從來沒有惹禍上身,也沒有給對方增添麻煩,可以說是他獨特的「浪漫之道」。在這一局,老子也提出「道」的「三不主義」:不推辭、不占有、不作主。首先,他說「道」是無所不在的(泛兮),我們周遭的萬物,從日月星辰、山川木石到蟲魚花鳥,包括我們人類在內,身上都有道的蹤影。接下來指出「道」的三個特性:第一,「不推辭」:萬物都依賴「道」來生長,「道」對此從不推辭,更不拒絕。第二,「不占有」:「道」成就宇宙中的一切,但對這一切卻都不會據為己有。第三,「不作主」:「道」養育萬物,但卻不以主人自居;放任萬物自行發展,不會替它們作主。施明德的「三不主義」跟老子的「三不主義」頗為類似,因為都有「順其自然」之意。
從某個角度來看,「道」的「不作主」可以說是卑微(小)的,因為它聽憑萬物自作主張,好像自己沒有甚麼權力、甚至不負責任;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不作主」卻也是偉大的(大),因為萬物都依靠「道」,但「道」卻不會因此而想要主宰萬物,它尊重它們。「道」不僅可大可小,而且因為不自認為自己偉大,所以反而成就了它的偉大,這跟前面所說的「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一樣,都是在反映老子獨特的逆向辯證思維。
當然,老子的用意絕不只是要我們認識「道」的特性而已,更期待大家能成為得道之士與行道之人。這並非在強人所難,因為「道」無所不在,我們每個人都是「道」的載體,都可以在自己身上顯現「道」的特性――不推辭、不占有與不作主,也就是「三不主義」。
不管是當老闆或做員工、做父親或當兒子,對於自己應該做甚至忽然加到自己身上的工作都自在承擔,不推辭、不抱怨,這種「不推辭」就是「道」的表現。雖然做了很多事、得到各種收穫,但卻不居功、不據為己有,這種「不占有」也是在表現「道」。雖然子女、員工、學生等等有很多人都依靠你而得以成長、發展,但你如果能不以主宰自居,不要他們聽命於你,而讓他們依本性去自由發展,這種「不作主」就更是「道」的表現。
在為人處事方面,能奉行這「三不主義」,就是在行道,在「人道」中顯現「天道」。這樣的人當然不會自認為偉大,而這正是他讓人覺得偉大的地方。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施明德那聽起來有點吊兒郎當的「三不主義」,也許也可以我們一些新的啟發。【內文節選三】
理想世界:回到過去或邁向未來?
【原文】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翻譯】
國家小,人口少。即使有各種器具也不使用。人們愛惜生命而不遠行遷徙。雖有車船,卻沒有必要乘坐;雖有武器裝備,卻沒有地方部署。讓人們回復到結繩記事的狀態。
在這樣的國土裡,人民有甜美的飲食,美觀的服飾,安適的居所,歡樂的習俗。鄰國之間彼此可以看見,雞鳴狗叫聲也相互可以聽到,但人民從生到死,卻不相往來。
【弈後語】
在這一局,老子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國。但看起來,這個理想國似乎不是在未來,而是在過去;從務實的角度來看,不僅不可能實現,而且也不是很理想。
不可能實現,主要是因為人類的文明是不斷前進的,不太可能再走回頭路。要大家回復到結繩記事的狀態,不僅是在開時代倒車,而且是強人所難。當大家都在使用電燈時,偶而點點蠟燭,發發思古之幽情,為生活增加情趣,似乎也不錯;但若要大家把電燈都收起來,丟進倉庫裡,全部都改用過去的蠟燭,那怎麼可能?
不太理想,因為在比較之下,明明有更好的東西,卻要大家用較差的東西,自然會讓人失望。小國寡民,聽起來似乎不錯,但雞犬相聞,卻又要大家老死不相往來,生活不僅容易變得閉鎖、沉悶,也違反自然。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因為老子所處時代的政治昏暗、人欲橫流、社會動盪、大國不斷兼併小國、人民離散、生活痛苦,他的理想國主要是有感於此而提出的一個心靈避難所。除了有濃厚的復古意味外(儒家的理想國也是在過去,但西方則大異其趣,他們的理想世界通常是在未來),不重物質而強調精神生活的滿足更是重點,所謂「老死不相往來」並非有意閉鎖,而是精神生活若圓滿自足,就不會對外界有太大的興趣,也不必寄望於他人或外界為自己的人生提供意義。老子的理想國讓我想起位於喜馬拉雅山腳下的不丹小國:根據聯合國在二○○四年的全球人類發展報告,不丹在一九二個國家中位居一三四名,不只經濟與物質生活相對落後,也相當閉鎖,她直到一九七四年才開放外國人進入,一九九九年才有電視。但在二○○六年英國萊斯特大學公布的《全球快樂排行榜》中,不丹在一七八個國家卻名列第八,位居亞洲第一位,比日本高出八十名,比美國高出九名。為什麼不丹人會特別快樂?因為前國王旺楚克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施政方針是不像其他國家般追求「國民生產毛額」(GDP),他要的是「國民幸福指數」(GNH),重視社會和諧與人民精神生活的滿足,曾經創下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民感覺幸福的紀錄,還因此而被譽為人間最後的樂土。這似乎印證了老子的某些說法。
但諷刺的是,當愈來愈多的外國人因慕名而進入這塊人間最後的樂土,還有在二○○八年轉型成民主政體,加快現代化的腳步後,擁有電視、手機、電腦、汽車的人愈來愈多,但生活卻愈來愈不快樂,竊盜、搶劫等犯罪頻傳,酗酒、吸毒人數激增,到二○一一年,感覺幸福的不丹人已降為百分之四十一。這似乎也在支持老子的某些論點,追逐物欲只會讓人更感空虛。
不丹人為什麼會變得比較不幸福,牽涉到很多因素。幸福其實是一種很主觀的感受,過去不丹人覺得很幸福,有一個原因是他們缺乏比較,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人過著什麼生活,想當然爾地覺得自己很幸福;但在和外界接觸愈多、了解愈多後,相較之下,就會有愈多的人覺得自己其實不幸福。這也是為什麼有人會說「無知是一種幸福」的原因,老子在前面所說的「常使民無知無欲」是否也有這個意思?值得大家深思。但為了讓人保持這種「主觀的幸福感」,就必須過著與外界隔絕的生活、甚至禁止人民和外界接觸嗎?我以為這是鴕鳥心態,也沒有人有權這樣做。曾任美國經濟學會與美國科學促進會會長的伯丁教授,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跟老子的「小國寡民」有點類似:他認為未來的理想世界應該由大約五百個獨立的國家所組成,這些國家都像「島嶼」一樣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與認同,也有產生個別突變的能力,但並非老死不相往來,而是透過貿易、旅遊與國際組織而彼此有密切的接觸。但在接觸中,他們不是互相羨慕,而是彼此欣賞,對自己國家與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有相當的自信,也許可以擷取他人的一些優點來彌補自己的不足,但絕不會在比較中迷失自我。
也許這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世界吧?當然,它也不見得能實現。但對個人來說,認為美好人生應該是在有待開發的未來,而不是在無可挽回的過去,才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