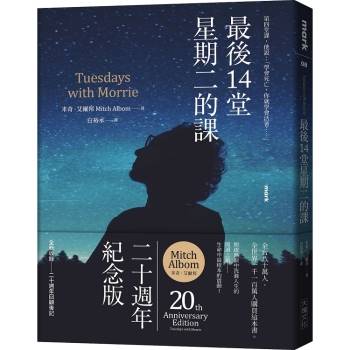有關老師,之一
一九九四年夏天,他被判了死刑。
但回頭看,墨瑞早在這之前就有不好的預感。
他不再跳舞的那一天,他就知道了。
我的老教授一直喜歡跳舞。
音樂並不重要,不管是搖滾、大樂團或藍調,他來者不拒。
他會閉上眼睛,臉上掛著幸福的微笑,開始有韻律的手舞足蹈起來。他的舞姿不是頂漂亮,不過他不擔心舞伴的問題,因為墨瑞都是一人獨舞。
他每周三晚上總會前往哈佛廣場的教堂,參加一項叫「自由舞蹈」的節目。會場有燈光效果及震耳欲聾的音箱,墨瑞走進會場,場中多半是年輕學生。
他穿著白色T恤及黑色的寬鬆運動長褲,脖子上掛著條毛巾。
不管放什麼音樂,他都是聞樂起舞,從吉魯巴到吉最米.漢崔克斯(Jimi Hendrix)的音樂,他都能跳。他扭啊扭、擺啊擺,兩手飛舞,彷彿是嗑了藥的指揮家,直舞到大汗淋漓,背脊濕透。
會場沒人知道他是位傑出的社會學教授,長年在大學教書,寫過多本廣受好評的著作,他們只當他是個老瘋癲。
有一次他帶了卷探戈錄音帶,要他們播放出來,然後他充當起指導,滿場遊走忙個不停,像個拉丁大情人。
等到樂聲結束,大家都鼓掌起來,而他還意猶未盡,面有得色。
但人生終有笙歌散盡的一天。
他六十幾歲開始有哮喘毛病,呼吸變得困難。一天他在查爾斯河邊走著走著,突然迎面颳來一陣刺骨寒風,頓時讓他喘不過氣來。
他被緊急送到醫院,注射腎上腺素治療。
又過了幾年,他開始行動不便。
有次在朋友的慶生宴上,他無緣無故就跌倒。又一天晚上,他從一家劇院台階上摔下去,把在場的人嚇壞了。
有人高喊:「讓開,不要圍著!」
這時他已經高齡七十,所以人們只是悄聲說「他老了」,扶著他重新站起身來。
不過墨瑞比一般人更了解自己,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這不只是人老了的現象。他一直感到倦怠,覺也睡不好,還夢到自己死去。他開始去看醫生,到處遍尋良醫。
醫生為他驗血,為他驗尿,還從肛門穿入直腸鏡檢查,但什麼毛病都找不到。
最後一位醫生為他做了肌肉組織切片生化檢驗,從墨瑞小腿背取了一小片檢體。
檢驗結果認為是神經傳導方面的問題,墨瑞於是又接受了一連串的檢驗。
有一項檢驗要他坐在一張特製的椅子上,對他施以電擊(有點像在坐電椅),記錄他的神經系統反應。
醫生看了檢驗結果後說:「我們要做進一步檢查。」
墨瑞問:「為什麼?是怎麼回事?」
「我們還不確定。你的時間比較慢。」
他的時間比較慢?這是什麼意思?
最後,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一個炎熱悶濕的日子,墨瑞和太太夏綠蒂前往一位神經學醫生的診所,醫生要他們先坐下來,才告訴他們壞消息:墨瑞得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簡稱ALS),又稱路格瑞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這是一種可怕無情的神經系統重症,沒有方法可以醫治。
墨瑞問:「我為什麼會得這種病?」
沒有人知道。
「病已經到末期了嗎?」
是的。
「那麼我快死了?」
醫生說,很遺憾,是的。
醫生和墨瑞及夏綠蒂坐著談了將近兩個小時,耐心回答他們各種問題。他們要離開時,醫生給了他們有關ALS的一些資料,幾本小冊子,彷彿他們是要開個銀行帳戶似的。
走出外面,陽光燦爛,眾人忙著自己的事,有個女人慌張跑到停車錶前投幣,另一個女人提著大包小包的採購雜貨。
夏綠蒂腦海中翻攪著千千萬萬個思緒:我們還剩多少時間?我們要怎麼面對?我們要怎麼負擔醫藥費?
在這同時,我的老師感到驚異不解:四周為何一切如常?世界不是應該停下來嗎?他們不曉得我發生了什麼事嗎?
然而世界沒有停下來,世界根本理也不理,而當墨瑞虛弱地拉開車門落座,他感覺彷彿陷入無底洞中。
他想著:這下怎麼辦?
我老師苦思答案的期間,病魔一天又一天、一星期接一星期的襲上身來。
一天早上,他從車庫倒車出來,結果幾乎使不出力氣來踩煞車。從此他再也不能開車。
他老是跌倒,因此買了根枴杖。從此他再也不能自由走動。
他照老習慣到YMCAA去游泳,但發現他再也無法自己換衣服。
他因此請了第一個家庭看護,名叫東尼的一個神學生,幫忙扶他進出游泳池,穿脫泳衣。在更衣室裡面,別人裝作沒在看他,但都還是看著。
從此他再也沒有隱私權。一九九四年秋,墨瑞來到丘陵起伏的布蘭迪斯校園,教他最後一門大學課程。他當然可以不教這門課,校方會諒解,何必在這麼多學生面前受這個苦?待在家裡吧,打理自己的事。
但墨瑞從沒想到要辭去教職。
墨瑞蹣跚走進教室,這是他棲身三十多年的家。
他拄著枴杖,花了一會兒工夫才走到椅子前面。
他好不容易坐了下來,把眼鏡從鼻梁上拿下來,望著那一張張瞪著他看的年輕面孔。
「朋友們,我想你們都是來上社會心理學的課。
這門課我教了二十年,而這是我第一次要說,上這堂課有個風險,因為我得了會致命的病。我可能無法教到學期結束。
「如果你們覺得不妥的話,可以放棄選修,我會了解。」
他露出微笑。
從此他再也沒有祕密可言。
ALS就像蠟燭一樣,它把你的神經熔化掉,剩下你的身體像一攤蠟。
這種病常從腿部開始發作,逐漸向上蔓延。你會無法控制大腿肌肉,所以你再也無法站立。
你會無法控制軀幹肌肉,所以你再也無法坐直。
到了最後你如果還活著,你要在喉嚨上穿孔,靠一根管子呼吸,而你的神智完全清醒,被禁閉在軟趴趴的臭皮囊中,也許還可以眨個眼皮或是嗒舌作響,就像科幻電影裡面的情節,整個人困陷在自己的肉體中。從得病到這個階段,只要短短五年時間。
墨瑞的醫生說,他大概還有兩年可活。
墨瑞自己知道剩不到兩年。
但我的老師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那天從診所出來,得知自己的性命危如累卵之後,就開始醞釀這個決定。他問自己:我是要日漸委靡不振,或是要善加利用剩下的時間?
他不願就此凋零萎謝,他不要為了自己離死不遠而羞於見人。
他要另闢蹊徑,以死亡作為他生命最後的計畫,他所剩歲月的重心所在。
既然人終不免一死,他可是很有價值的,不是嗎?他可以研究死亡,當它是一本活教材。研究我的緩慢步向死亡,觀察我身上發生的事,和我一道學習。
墨瑞要走過生與死之間的最後一道橋梁,並留下此行的記述。
秋季學期很快過去了。他所服的藥愈來愈多,醫療成為家常便飯。護士來家中幫墨瑞運動他日漸萎縮的腿部,讓肌肉有活動,把他的腿前後彎曲伸展,就像用幫浦打水一樣。按摩師每星期來一次,因為他一直覺得肌肉沈重僵硬不堪,按摩一下有助紓解。
他跟靜坐老師學習,閉上眼睛、專注凝神,直到整個世界只剩下呼吸,吸氣、呼氣,吸氣、呼氣。
一天他拄著枴杖,從家裡走上人行道,結果當街摔倒,從此枴杖換成手扶助行架。
他的身體日益衰弱,上廁所都變得太累,因此墨瑞開始使用便壺。他小便時必須用手撐著身體,所以得要別人拿著便壺才行。
多數人都會對此感到尷尬,特別是像墨瑞這麼年高德劭的人,但墨瑞並不像多數人。他一些同事好友來訪時,他會問:「聽著,我得要小便,你不介意幫忙吧?你這樣做沒問題嗎?」
他們通常都會樂於伸出援手,連他們自己也感到驚訝。
事實上呢,他的訪客愈來愈多,讓他應接不暇。他主持若干討論死亡的小組,大家一起探討死亡的真正意義,談著世人總是害怕死亡,卻不見得了解其意涵。
他對朋友說,他們若真的想幫他,就不應該同情他,而是多多來訪、多打電話,和他討論他們的問題,就和過去大家相處一樣,因為墨瑞一向是很好的聆聽者。
墨瑞雖然受到病魔折騰,他的聲音仍然有力而富於磁性,而他的腦中更有千萬個思緒躍動翻騰。他要證明,垂死的人並不一定是無用之人。
新的一年來了又去。
墨瑞雖然沒有跟別人講,但自己知道這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現在已經必須坐輪椅,他爭取著時間,要把自己心裡的話,講給他所愛的每個人聽。布蘭迪斯大學一個同事突然心臟病發去世,墨瑞參加了他的葬禮,回到家來很沮喪。
「多麼可惜啊,」他說:「這麼多人說了這麼多好聽的話,歐文自己卻聽不到。」
墨瑞不甘遭受同樣命運。
他到處打電話,跟人約時間。一個寒冷的星期天午後,他家中聚集了一小群朋友及家人,舉行一場「生之葬禮」。每個人都說了些話,對我的老教授致上敬意,有人哭,有人笑,還有位女士朗誦了一首詩:
我親愛深情的好友
你長生的心
在時間長流中添增年輪
溫柔的水杉……
墨瑞和他們一同哭笑。我們平時從不會對所愛的人講的衷心話語,墨瑞在這一天都傾心剖白。他的「生之葬禮」可說大獲成功。
只是墨瑞還沒死。
事實上,他生命中最不尋常的一段經歷,現在才要開始。有關學生
這個時候,我應該說明一下,在那個夏日午後,我擁抱了我親愛而睿智的老教授,並且答應要保持聯絡之後,發生了些什麼事。
我並沒有和他保持聯絡。
事實上,我和大學認識的大多數人都失去了聯絡,包括我那群喝酒的朋友,以及第一個和我同床共枕的女孩在內。
畢業後的幾年歷練,讓我變得世故老氣,完全不復當年我離開校園、前往紐約大都會,一心想以一己所學貢獻世人時的意氣風發。
我發現世人對我並不是很感興趣。
二十出頭的我到處飄泊,租房子找分類廣告,一心不解自己為什麼會四處碰壁。
我的夢想是成為著名的音樂家(我彈鋼琴),但我在昏暗空盪的酒吧混跡好幾年。
許多機會無疾而終,樂團分分合合,製作人似乎忙著發掘新星,但就是沒有想到我,我的夢想終而變了顏色。我生平頭一遭嘗到失敗的滋味。
在此同時,我也第一次和死亡交鋒。我最喜歡的一個舅舅,以四十四歲英年死於胰臟癌。當年他教我學音樂、教我開車、教我打美式足球,揶揄我和女孩子的交往。
他是我孩提時代學習的楷模,我心裡總想著:「我長大以後要像舅舅一樣。」他是個矮小但英俊的人,唇上留著濃密的髭鬚。他生命最後一年我都在他身邊,住在同棟公寓的樓下。
我看著他原本健壯的身體日益衰弱,接著變得浮腫。我看著他夜復一夜飽受病魔折磨,在飯桌上痛得整個人彎下去,兩手緊抱腹部,眼睛緊閉,嘴巴因痛苦而扭曲變形。「啊,上帝,」他痛苦呻吟著:「啊,耶穌!」我、舅媽,以及他們的兩個小兒子,只能無言兀立,默默洗著碗盤,眼睛望向別處。
這是我生命中最感無助的時刻。
五月的一個晚上,我舅舅和我坐在他公寓的陽台上,晚風習習,溫暖宜人。他眼睛望向夜空,強咬著牙跟我說,他看不到自己的孩子讀下個學年了,問我能不能幫忙照顧他們。
我求他不要講這種話,他只是悲傷地望著我。
幾個星期後他過世了。
喪禮過後,我的生命改變了。
我突然覺得時間變得很珍貴,就像流水去而不返,一刻也不容錯失。我不再去人沒坐滿的酒吧演奏音樂,也不再躲在房間寫那些沒人想聽的歌。我回學校念書,修了一個新聞碩士,人家給我的第一個工作我就接了,成為一個體育記者。
如今我不再追求自己成名,而是報導那些名運動員如何功成名就。
我為幾家報社做事,還為雜誌社寫稿,我沒命似的埋首工作,日以繼夜,全心投入。
我早上醒來刷牙,然後就坐到打字機前,身上穿的仍是前一晚入睡也沒換的衣服。
我舅舅在一家公司做事,他對日復一日重複沈悶的工作痛恨不已,我下定決心不要變得跟他一樣。
我到處尋求機會,從紐約跳槽到佛羅里達,最後終於在底特律定下來,成為《底特律自由報》(Detroit Free Press)的體育專欄作家。
底特律對運動的狂熱可說無休無止,擁有職業的美式足球隊、籃球隊、棒球隊及曲棍球隊,我正可以一展抱負。
短短幾年間,我不僅主持一個體育專欄,還寫書、上電台、固定出現在電視上,針對身價千萬的美式足球員及假仁假義的大學運動員養成計畫大發議論。
於今席捲全美的新聞媒體狂潮,我也有推波助瀾之功;我炙手可熱。
我開始置產,不再是無殼蝸牛。
我買了山坡上一幢房子,車子換了一輛又一輛。
我投資股票,有自己的投資組合。我像是用高速檔行駛,不管做什麼,我都是快馬加鞭,剋期完成。
我狂熱投入運動健身,開起車來風馳電掣。我賺錢多到自己數不完。
我遇到一個名叫潔寧的深色頭髮女孩,雖然我忙得不可開交、跟她聚少離多,她還是愛著我。我們交往七年後結了婚,而婚禮後一個禮拜,我就回到工作崗位。
我跟她說也跟自己說,我們有朝一日會生兒育女。這是她衷心深盼的事,但這一天遲遲未來。
我用成就來滿足自己,因為成功讓我覺得可以主宰事物,讓我可以榨取到最後一絲的快樂享受,直到我老病交加而死,就像我舅舅一樣,我認為自己終究也難逃這一關。
那麼墨瑞呢?我偶爾也會想到他,想到他教我的「做人本分」及「與人溝通」,但這總是顯得遙不可及,彷彿是下輩子的事。
這些年來,我只要一看到布蘭迪斯大學來的信件,就隨手一丟,以為又是校方來請求捐款了。
因此我並不知道墨瑞生病的事,而可以告訴我消息的人,早被我淡忘了;他們的電話號碼,大概深埋在閣樓不知哪個雜物箱裡面。
事情本可能一成不變這樣下去,要不是我一天深夜亂轉著電視頻道,有個節目突然讓我豎起了耳朵……
一九九四年夏天,他被判了死刑。
但回頭看,墨瑞早在這之前就有不好的預感。
他不再跳舞的那一天,他就知道了。
我的老教授一直喜歡跳舞。
音樂並不重要,不管是搖滾、大樂團或藍調,他來者不拒。
他會閉上眼睛,臉上掛著幸福的微笑,開始有韻律的手舞足蹈起來。他的舞姿不是頂漂亮,不過他不擔心舞伴的問題,因為墨瑞都是一人獨舞。
他每周三晚上總會前往哈佛廣場的教堂,參加一項叫「自由舞蹈」的節目。會場有燈光效果及震耳欲聾的音箱,墨瑞走進會場,場中多半是年輕學生。
他穿著白色T恤及黑色的寬鬆運動長褲,脖子上掛著條毛巾。
不管放什麼音樂,他都是聞樂起舞,從吉魯巴到吉最米.漢崔克斯(Jimi Hendrix)的音樂,他都能跳。他扭啊扭、擺啊擺,兩手飛舞,彷彿是嗑了藥的指揮家,直舞到大汗淋漓,背脊濕透。
會場沒人知道他是位傑出的社會學教授,長年在大學教書,寫過多本廣受好評的著作,他們只當他是個老瘋癲。
有一次他帶了卷探戈錄音帶,要他們播放出來,然後他充當起指導,滿場遊走忙個不停,像個拉丁大情人。
等到樂聲結束,大家都鼓掌起來,而他還意猶未盡,面有得色。
但人生終有笙歌散盡的一天。
他六十幾歲開始有哮喘毛病,呼吸變得困難。一天他在查爾斯河邊走著走著,突然迎面颳來一陣刺骨寒風,頓時讓他喘不過氣來。
他被緊急送到醫院,注射腎上腺素治療。
又過了幾年,他開始行動不便。
有次在朋友的慶生宴上,他無緣無故就跌倒。又一天晚上,他從一家劇院台階上摔下去,把在場的人嚇壞了。
有人高喊:「讓開,不要圍著!」
這時他已經高齡七十,所以人們只是悄聲說「他老了」,扶著他重新站起身來。
不過墨瑞比一般人更了解自己,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這不只是人老了的現象。他一直感到倦怠,覺也睡不好,還夢到自己死去。他開始去看醫生,到處遍尋良醫。
醫生為他驗血,為他驗尿,還從肛門穿入直腸鏡檢查,但什麼毛病都找不到。
最後一位醫生為他做了肌肉組織切片生化檢驗,從墨瑞小腿背取了一小片檢體。
檢驗結果認為是神經傳導方面的問題,墨瑞於是又接受了一連串的檢驗。
有一項檢驗要他坐在一張特製的椅子上,對他施以電擊(有點像在坐電椅),記錄他的神經系統反應。
醫生看了檢驗結果後說:「我們要做進一步檢查。」
墨瑞問:「為什麼?是怎麼回事?」
「我們還不確定。你的時間比較慢。」
他的時間比較慢?這是什麼意思?
最後,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一個炎熱悶濕的日子,墨瑞和太太夏綠蒂前往一位神經學醫生的診所,醫生要他們先坐下來,才告訴他們壞消息:墨瑞得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簡稱ALS),又稱路格瑞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這是一種可怕無情的神經系統重症,沒有方法可以醫治。
墨瑞問:「我為什麼會得這種病?」
沒有人知道。
「病已經到末期了嗎?」
是的。
「那麼我快死了?」
醫生說,很遺憾,是的。
醫生和墨瑞及夏綠蒂坐著談了將近兩個小時,耐心回答他們各種問題。他們要離開時,醫生給了他們有關ALS的一些資料,幾本小冊子,彷彿他們是要開個銀行帳戶似的。
走出外面,陽光燦爛,眾人忙著自己的事,有個女人慌張跑到停車錶前投幣,另一個女人提著大包小包的採購雜貨。
夏綠蒂腦海中翻攪著千千萬萬個思緒:我們還剩多少時間?我們要怎麼面對?我們要怎麼負擔醫藥費?
在這同時,我的老師感到驚異不解:四周為何一切如常?世界不是應該停下來嗎?他們不曉得我發生了什麼事嗎?
然而世界沒有停下來,世界根本理也不理,而當墨瑞虛弱地拉開車門落座,他感覺彷彿陷入無底洞中。
他想著:這下怎麼辦?
我老師苦思答案的期間,病魔一天又一天、一星期接一星期的襲上身來。
一天早上,他從車庫倒車出來,結果幾乎使不出力氣來踩煞車。從此他再也不能開車。
他老是跌倒,因此買了根枴杖。從此他再也不能自由走動。
他照老習慣到YMCAA去游泳,但發現他再也無法自己換衣服。
他因此請了第一個家庭看護,名叫東尼的一個神學生,幫忙扶他進出游泳池,穿脫泳衣。在更衣室裡面,別人裝作沒在看他,但都還是看著。
從此他再也沒有隱私權。一九九四年秋,墨瑞來到丘陵起伏的布蘭迪斯校園,教他最後一門大學課程。他當然可以不教這門課,校方會諒解,何必在這麼多學生面前受這個苦?待在家裡吧,打理自己的事。
但墨瑞從沒想到要辭去教職。
墨瑞蹣跚走進教室,這是他棲身三十多年的家。
他拄著枴杖,花了一會兒工夫才走到椅子前面。
他好不容易坐了下來,把眼鏡從鼻梁上拿下來,望著那一張張瞪著他看的年輕面孔。
「朋友們,我想你們都是來上社會心理學的課。
這門課我教了二十年,而這是我第一次要說,上這堂課有個風險,因為我得了會致命的病。我可能無法教到學期結束。
「如果你們覺得不妥的話,可以放棄選修,我會了解。」
他露出微笑。
從此他再也沒有祕密可言。
ALS就像蠟燭一樣,它把你的神經熔化掉,剩下你的身體像一攤蠟。
這種病常從腿部開始發作,逐漸向上蔓延。你會無法控制大腿肌肉,所以你再也無法站立。
你會無法控制軀幹肌肉,所以你再也無法坐直。
到了最後你如果還活著,你要在喉嚨上穿孔,靠一根管子呼吸,而你的神智完全清醒,被禁閉在軟趴趴的臭皮囊中,也許還可以眨個眼皮或是嗒舌作響,就像科幻電影裡面的情節,整個人困陷在自己的肉體中。從得病到這個階段,只要短短五年時間。
墨瑞的醫生說,他大概還有兩年可活。
墨瑞自己知道剩不到兩年。
但我的老師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那天從診所出來,得知自己的性命危如累卵之後,就開始醞釀這個決定。他問自己:我是要日漸委靡不振,或是要善加利用剩下的時間?
他不願就此凋零萎謝,他不要為了自己離死不遠而羞於見人。
他要另闢蹊徑,以死亡作為他生命最後的計畫,他所剩歲月的重心所在。
既然人終不免一死,他可是很有價值的,不是嗎?他可以研究死亡,當它是一本活教材。研究我的緩慢步向死亡,觀察我身上發生的事,和我一道學習。
墨瑞要走過生與死之間的最後一道橋梁,並留下此行的記述。
秋季學期很快過去了。他所服的藥愈來愈多,醫療成為家常便飯。護士來家中幫墨瑞運動他日漸萎縮的腿部,讓肌肉有活動,把他的腿前後彎曲伸展,就像用幫浦打水一樣。按摩師每星期來一次,因為他一直覺得肌肉沈重僵硬不堪,按摩一下有助紓解。
他跟靜坐老師學習,閉上眼睛、專注凝神,直到整個世界只剩下呼吸,吸氣、呼氣,吸氣、呼氣。
一天他拄著枴杖,從家裡走上人行道,結果當街摔倒,從此枴杖換成手扶助行架。
他的身體日益衰弱,上廁所都變得太累,因此墨瑞開始使用便壺。他小便時必須用手撐著身體,所以得要別人拿著便壺才行。
多數人都會對此感到尷尬,特別是像墨瑞這麼年高德劭的人,但墨瑞並不像多數人。他一些同事好友來訪時,他會問:「聽著,我得要小便,你不介意幫忙吧?你這樣做沒問題嗎?」
他們通常都會樂於伸出援手,連他們自己也感到驚訝。
事實上呢,他的訪客愈來愈多,讓他應接不暇。他主持若干討論死亡的小組,大家一起探討死亡的真正意義,談著世人總是害怕死亡,卻不見得了解其意涵。
他對朋友說,他們若真的想幫他,就不應該同情他,而是多多來訪、多打電話,和他討論他們的問題,就和過去大家相處一樣,因為墨瑞一向是很好的聆聽者。
墨瑞雖然受到病魔折騰,他的聲音仍然有力而富於磁性,而他的腦中更有千萬個思緒躍動翻騰。他要證明,垂死的人並不一定是無用之人。
新的一年來了又去。
墨瑞雖然沒有跟別人講,但自己知道這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現在已經必須坐輪椅,他爭取著時間,要把自己心裡的話,講給他所愛的每個人聽。布蘭迪斯大學一個同事突然心臟病發去世,墨瑞參加了他的葬禮,回到家來很沮喪。
「多麼可惜啊,」他說:「這麼多人說了這麼多好聽的話,歐文自己卻聽不到。」
墨瑞不甘遭受同樣命運。
他到處打電話,跟人約時間。一個寒冷的星期天午後,他家中聚集了一小群朋友及家人,舉行一場「生之葬禮」。每個人都說了些話,對我的老教授致上敬意,有人哭,有人笑,還有位女士朗誦了一首詩:
我親愛深情的好友
你長生的心
在時間長流中添增年輪
溫柔的水杉……
墨瑞和他們一同哭笑。我們平時從不會對所愛的人講的衷心話語,墨瑞在這一天都傾心剖白。他的「生之葬禮」可說大獲成功。
只是墨瑞還沒死。
事實上,他生命中最不尋常的一段經歷,現在才要開始。有關學生
這個時候,我應該說明一下,在那個夏日午後,我擁抱了我親愛而睿智的老教授,並且答應要保持聯絡之後,發生了些什麼事。
我並沒有和他保持聯絡。
事實上,我和大學認識的大多數人都失去了聯絡,包括我那群喝酒的朋友,以及第一個和我同床共枕的女孩在內。
畢業後的幾年歷練,讓我變得世故老氣,完全不復當年我離開校園、前往紐約大都會,一心想以一己所學貢獻世人時的意氣風發。
我發現世人對我並不是很感興趣。
二十出頭的我到處飄泊,租房子找分類廣告,一心不解自己為什麼會四處碰壁。
我的夢想是成為著名的音樂家(我彈鋼琴),但我在昏暗空盪的酒吧混跡好幾年。
許多機會無疾而終,樂團分分合合,製作人似乎忙著發掘新星,但就是沒有想到我,我的夢想終而變了顏色。我生平頭一遭嘗到失敗的滋味。
在此同時,我也第一次和死亡交鋒。我最喜歡的一個舅舅,以四十四歲英年死於胰臟癌。當年他教我學音樂、教我開車、教我打美式足球,揶揄我和女孩子的交往。
他是我孩提時代學習的楷模,我心裡總想著:「我長大以後要像舅舅一樣。」他是個矮小但英俊的人,唇上留著濃密的髭鬚。他生命最後一年我都在他身邊,住在同棟公寓的樓下。
我看著他原本健壯的身體日益衰弱,接著變得浮腫。我看著他夜復一夜飽受病魔折磨,在飯桌上痛得整個人彎下去,兩手緊抱腹部,眼睛緊閉,嘴巴因痛苦而扭曲變形。「啊,上帝,」他痛苦呻吟著:「啊,耶穌!」我、舅媽,以及他們的兩個小兒子,只能無言兀立,默默洗著碗盤,眼睛望向別處。
這是我生命中最感無助的時刻。
五月的一個晚上,我舅舅和我坐在他公寓的陽台上,晚風習習,溫暖宜人。他眼睛望向夜空,強咬著牙跟我說,他看不到自己的孩子讀下個學年了,問我能不能幫忙照顧他們。
我求他不要講這種話,他只是悲傷地望著我。
幾個星期後他過世了。
喪禮過後,我的生命改變了。
我突然覺得時間變得很珍貴,就像流水去而不返,一刻也不容錯失。我不再去人沒坐滿的酒吧演奏音樂,也不再躲在房間寫那些沒人想聽的歌。我回學校念書,修了一個新聞碩士,人家給我的第一個工作我就接了,成為一個體育記者。
如今我不再追求自己成名,而是報導那些名運動員如何功成名就。
我為幾家報社做事,還為雜誌社寫稿,我沒命似的埋首工作,日以繼夜,全心投入。
我早上醒來刷牙,然後就坐到打字機前,身上穿的仍是前一晚入睡也沒換的衣服。
我舅舅在一家公司做事,他對日復一日重複沈悶的工作痛恨不已,我下定決心不要變得跟他一樣。
我到處尋求機會,從紐約跳槽到佛羅里達,最後終於在底特律定下來,成為《底特律自由報》(Detroit Free Press)的體育專欄作家。
底特律對運動的狂熱可說無休無止,擁有職業的美式足球隊、籃球隊、棒球隊及曲棍球隊,我正可以一展抱負。
短短幾年間,我不僅主持一個體育專欄,還寫書、上電台、固定出現在電視上,針對身價千萬的美式足球員及假仁假義的大學運動員養成計畫大發議論。
於今席捲全美的新聞媒體狂潮,我也有推波助瀾之功;我炙手可熱。
我開始置產,不再是無殼蝸牛。
我買了山坡上一幢房子,車子換了一輛又一輛。
我投資股票,有自己的投資組合。我像是用高速檔行駛,不管做什麼,我都是快馬加鞭,剋期完成。
我狂熱投入運動健身,開起車來風馳電掣。我賺錢多到自己數不完。
我遇到一個名叫潔寧的深色頭髮女孩,雖然我忙得不可開交、跟她聚少離多,她還是愛著我。我們交往七年後結了婚,而婚禮後一個禮拜,我就回到工作崗位。
我跟她說也跟自己說,我們有朝一日會生兒育女。這是她衷心深盼的事,但這一天遲遲未來。
我用成就來滿足自己,因為成功讓我覺得可以主宰事物,讓我可以榨取到最後一絲的快樂享受,直到我老病交加而死,就像我舅舅一樣,我認為自己終究也難逃這一關。
那麼墨瑞呢?我偶爾也會想到他,想到他教我的「做人本分」及「與人溝通」,但這總是顯得遙不可及,彷彿是下輩子的事。
這些年來,我只要一看到布蘭迪斯大學來的信件,就隨手一丟,以為又是校方來請求捐款了。
因此我並不知道墨瑞生病的事,而可以告訴我消息的人,早被我淡忘了;他們的電話號碼,大概深埋在閣樓不知哪個雜物箱裡面。
事情本可能一成不變這樣下去,要不是我一天深夜亂轉著電視頻道,有個節目突然讓我豎起了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