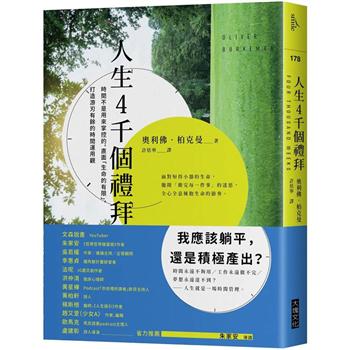前言
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人類的平均壽命短到離譜,少到嚇人,小器到不給面子。比一比你就懂我為什麼這麼說:第一個現代人類出現在至少二十萬年前的非洲平原,而科學家推測,生命未來將以某種形式再延續十五億年以上,直到日益增強的太陽熱度奪走最後一個有機體的性命。而你呢?假設你活到八十歲好了,那麼你大約有四千個星期可活。
當然,你可能很幸運,活到了九十歲,那麼你大約有四千七百個禮拜。你也可能和珍妮.卡爾芒(Jeanne Calment)一樣超級幸運。這位法國女性一九九七年過世時,據說享嵩壽一百二十二歲,成為有史以來最長壽的人士。卡爾芒記得自己見過梵谷,她主要的印象是這位十九世紀的繪畫大師酒氣沖天。此外,第一個成功複製的哺乳類動物桃莉羊在一九九六年誕生時,卡爾芒也得以成為見證人。生物學家預測,與卡爾芒相去不遠的壽命,很快就會成為常態。然而,即便高壽如卡爾芒,她依舊只在世間待了大約六千四百個星期。
以這樣的驚人對比來談壽命,就知道為什麼從古希臘哲人到今日的哲學家,向來把人生苦短視為人類存在的基本問題:上天讓我們的心智有辦法制定幾乎是無遠弗屆的遠大計畫,但實際上根本沒時間付諸行動。羅馬哲學家塞內卡(Seneca)在後世將標題定為《論生命之短暫》(On the Shortness of Life)的書信中,感慨道:「這段交到我們手中的時間匆匆流逝。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部分的人終於感到準備好要開始活的時候,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刻。」我第一次算出四千禮拜這個數字時,腦中一陣暈眩,但一回過神就開始騷擾朋友,要他們猜一般人可以活多久,而且不能做任何心算,要不假思索直接猜。有一位朋友的答案是六位數,而我感到有必要向她指出,即便是相當保守的六位數字,例如三十一萬個星期,大約已經等同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古蘇美人以來,所有人類文明存在的時間。當代哲學家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曾經寫道,幾乎以任何有意義的時間尺度來看,「我們所有人隨時會向生命道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廣義的時間管理,理應是每個人關切的重要事項,可以說人生其實就是一場時間管理。然而,如同時間管理更時髦的兄弟「生產力」,現代所謂「時間管理學」的定義十分狹隘,主要談如何日理萬機,擬定完美的晨間流程,或是在週日煮一堆東西,一次搞定一整個星期的晚餐。這些事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重要性,但不是人生的全部。這個世界處處充滿驚喜,卻很少有生產力大師認為,我們瘋狂地做一大堆事,最終的目的是體驗到更多人生的喜悅。這個世界似乎正在加速衝向災難,我們的文明生活已經進入瘋狂階段,疫情癱瘓了社會,地球這顆行星愈來愈炎熱,但如果你想找到一套時間管理系統協助你和同胞齊心協力,有效解決目前的事件或環境的命運,那就祝你好運了。你可能會以為,至少會有幾本講生產力的書,認真看待人生短暫的嚴肅事實,而不是假裝可以忽略這件事,但是你猜錯了。
因此,本書試圖找回平衡,看看我們能否發現或重拾某種思考時間的方式,好好解決自己面對的真實情境:我們擁有的四千禮拜的壽命短到令人髮指,但仍然充滿光明燦爛的可能性。
輸送帶人生
當然,從某方面來講,今日已經不需要有人提醒時間不夠用。我們的心思全放在爆滿的電子信箱與冗長的待辦事項,心懷罪惡感,老覺得應該再多完成一點事情。我們和愚公一樣努力移山,而且移的不只一座(你怎麼知道人們感到很忙?這種事就和你如何知道某個人吃素一樣:別擔心,他們會告訴你)。民調一再顯示,我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時間壓力;
然而在二〇一三年,荷蘭學術團隊所做的研究,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可能性:這類說我們很忙的民調,可能還低估了這場忙碌流行病的傳染規模,因為極度忙碌的人士過分焦頭爛額,沒空接受民調。隨著近日零工經濟成長,忙碌被重新定義成「複業」(hustle)—無止境的工作不再是必須忍耐再忍耐的重擔,而是令人振奮的生活方式選項,值得在社群媒體上炫耀一番。然而事實上,複業其實是極致的新瓶裝舊酒:壓力逼得我們把永遠在膨脹的活動量,塞進每天再怎麼努力也不會多出一分一秒的二十四小時。然而,哀號很忙只不過是開端。停下來想一想,就會發現其他五花八門的抱怨,其實也是在抱怨時間有限。我們每天都得抗拒網路上令人分心的事物,驚覺能維持專注力的時間大幅縮短,即便是從小就愛看書的我們,如今才讀了一段文字,就忍不住想伸手拿手機。這種現象令人憂心忡忡的根本原因在於,這代表我們未能善用原本就不多的光陰供應(如果晨間時光的供應是無限的,浪費一個早上滑臉書,就不會讓人那麼想掐死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你遇上的問題不是過分忙碌而是不夠充實,在無聊的工作裡日益倦怠,或是想就業也找不到工作。相較於人生苦短,工作不順遠遠更令人沮喪,因為你正在以不想要的方式,消耗自己有限的時間。這年頭最糟糕的發展,甚至也能間接以我們時間有限這個基本事實來解釋。舉例來說,在YouTube 影片的煽風點火下,出現了極度分裂的政黨支持者與激進的恐怖分子。起因是我們的時間與注意力相當有限,也因此很寶貴,社群媒體公司有動機使出渾身解數,不擇手段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那就是為什麼社群媒體要讓用戶觀看保證會群情激憤的內容,而不是無聊的正確事實。
此外,人類有一堆永不過時的煩惱,例如:挑選結婚對象、要不要生小孩、要追求哪一條職業道路。如果我們可以活個幾千年,那種事令人苦惱的程度就會大幅降低,因為時間很充裕,你可以花個數十年,把每一種可能性都嘗試看看。再者,我們的時間煩惱目錄,不能不加上一個令人警覺的現象:三十歲以上的人都熟悉那種感覺,年紀愈大,時間流逝的速度似乎就愈快,而且是穩定加速中。依據七、八十歲人士的說法,幾個月感覺簡直只有幾分鐘而已。很難想像比這更殘酷的命運安排:我們的四千個禮拜不只是持續減少,而是剩得愈少,時間消逝的速度感覺就愈快。如果說我們跟手中有限的時間,關係向來緊張,近日發生的事件更是帶我們來到關鍵時刻。新冠肺炎疫情在二〇二〇年讓我們面臨封城,日常事務被打斷。許多人談到時間完全被打亂,感到不知所措。日子不知怎麼地好像一下子飛逝,但也永遠過不完。時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讓每個人身處不同的世界:有工作、家中又有幼兒的人,時間根本不夠用;休無薪假或無業的人士則時間太多。此外,大家開始在不固定的時間工作,在家窩在發光筆電前,脫離白天與夜晚的循環,或是冒著生命危險,在醫院與快遞貨倉待命。感覺上,未來好像被按下了暫停鍵,許多人困在精神科醫師所說的「新型的永恆當下」,處在焦慮的混沌狀態,不停查看社群媒體,中間穿插一下Zoom 視訊與失眠,無法制定任何有意義的計畫,甚至無法明確描繪出下星期結束後的生活。
對許多人來講,一切的一切讓不善於管理有限的時間,變得特別令人沮喪。我們努力讓時間發揮最大效益,但除了沒成功不說,甚至一再雪上加霜。最近幾年,我們被活出百分之百全效生活的建議給淹沒,市面上的書籍鼓勵我們做到《極度生產力》(ExtremeProductivity,譯註:中譯本書名為《時間,愈用愈有價值》),《一週只需要工作四小時》(The4-Hour Workweek,中譯本書名為《一週工作4小時》),還要《更聰明、更快、更好》(Smarter Faster Better,中譯本書名為《為什麼這樣工作會快、準、好》)。五花八門的網站要我們化身為「生活駭客」,好讓完成日常事務的時間能少個幾秒鐘(「生活駭客」一詞本身就是古怪的建議,彷彿你的人生頂多稱得上某種老是出錯的裝置,需要加以調整,不再永遠處於未達最佳運轉狀態)。各式各樣的app 與穿戴式裝置,再加上Soylent 等代餐飲料,讓你不必浪費時間吃正餐,協助你工作時獲得最大的工作報酬,運動時獲得最大的運動報酬,就連睡覺都能發揮最大的益處。其他成千上萬種產品與服務,主要的賣點也是協助你達成被廣為稱讚的目標:從你的時間中擠出最大效益。問題不在於這些技巧與產品沒用。它們確實有用。你可以完成更多事,趕去開更多會,送孩子去更多課後活動,替你的雇主賺更多錢。然而矛盾的是,成功後,我們得到的只有感到更忙碌、更焦慮,某方面來講還更空虛。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T. Hall)談到現代世界的時間,感覺就像是永遠不會停下的輸送帶,我們一送出完成的工作,就會冒出新工作。所謂變得「更有生產力」,似乎只會加快輸送帶的運轉速度,動作不快點就完了:全面感到深沉的倦怠是今日的常態現象,特徵是無力完成基本的日常事務,年輕成人的受害程度尤其深。套用千禧社會評論家麥爾坎•哈里斯(Malcolm Harris)的話來講:「這個世代的人是被精密打造的工具。從還在媽媽肚子裡,就被塑造成一流的精實生產機器。」他們身上籠罩著無力的疲憊感。
時間有一個面向令人抓狂,但大部分的管理建議似乎都沒注意到這一點。時間有如不受控的幼兒:你愈想控制,要時間照你說的話去做,它就愈是從你手中逃脫。想一想所有意圖協助我們戰勝時間的科技:按照任何合理的邏輯來看,在一個有洗碗機、微波爐與噴射引擎的世界,我們省下了無數小時,理應感到時間變得更充裕、游刃有餘才對,但這不是任何人的實際感受。生活的步調變快,每個人愈來愈沒耐性。不曉得為什麼,在微波爐前等個兩分鐘,比用烤箱烤東西兩小時更煩人。花十秒鐘等網頁龜速下載,令人跳腳的程度,也超過花三天等待相同的內容以紙本形式寄達。
我們增加工作生產力的努力,很多也同樣弄巧成拙。幾年前,我因為被電子郵件淹沒,成功安裝一個叫「清空收件匣」(Inbox Zero)的系統,但很快就發現,我回信變得超有效率之後,只會冒出數量更龐大的電子郵件。暴增的郵件搞得我感到更忙碌,因此我買了時間管理大師大衛•艾倫(David Allen)的《搞定!》(Getting Things Done)一書。艾倫在書中提出的保證很吸引我:「就算你的待辦事項數量多到令人喘不過氣,你依舊可以頭腦清醒,生產力十足」,並維持「武術家所謂『心靜如水』的狀態」。然而,我未能體會艾倫更深層的暗示:你永遠會有太多事要處理。我著手試著完成不可能的工作量。事實上,我迅速完成待辦事項的能力還真的增強了,但結果是神奇地冒出來(這其實不是魔法,只是簡單的心理學外加資本主義。後文會再談到)。前人完全沒料到未來會是這種面貌。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九三〇年的「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那場演講提出著名的預言:由於富裕程度增加,科技進步,在一世紀內,再也沒人需要一星期工作十五小時以上。未來的挑戰將是如何充實我們所有新到手的空檔,卻不至於閒到發瘋。「自有人類以來,史上第一次,」凱因斯告訴聽眾:「人們將面對一個真正、永恆的問題:不再有迫切的經濟壓力之後,該如何利用這份自由。」然而,凱因斯預言失準,民眾賺到足夠的錢滿足需求後,只會找到新的需求,渴望新的生活方式;人們不曾趕上隔壁令人羨慕的鄰居,因為眼看即將追上時,又找到過得更好、想要模仿的新對象。於是乎,每個人汲汲營營,追名逐利,忙碌很快就成為身分地位的象徵。但這一聽就是荒謬透頂的事,因為幾乎在整個人類史上,有錢的重點,就是不必再被工作追著跑。此外,富人的忙碌會傳染,因為對於金字塔頂端的人,極度有效的賺錢方法,就是改善公司與產業的效率,削減成本。這對下層民眾來說,生活益發沒保障,被迫更努力地工作,但也僅能糊口而已。
(未完)
第1章 接受人生有限
我們真正碰上的問題,不在於人生在世、時間有限。真正的問題,或者我希望讓各位明白的是,我們無意間承襲了一套有問題的想法,壓力十足,感到必須按照那種講法來利用有限的時間,但幾乎只會讓事情雪上加霜。如果要瞭解我們是如何陷入今日的窘境,找出如何才能逃脫,與時間建立更理想的關係,我們必須倒轉時鐘,回到時鐘尚未問世的年代。
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人類的平均壽命短到離譜,少到嚇人,小器到不給面子。比一比你就懂我為什麼這麼說:第一個現代人類出現在至少二十萬年前的非洲平原,而科學家推測,生命未來將以某種形式再延續十五億年以上,直到日益增強的太陽熱度奪走最後一個有機體的性命。而你呢?假設你活到八十歲好了,那麼你大約有四千個星期可活。
當然,你可能很幸運,活到了九十歲,那麼你大約有四千七百個禮拜。你也可能和珍妮.卡爾芒(Jeanne Calment)一樣超級幸運。這位法國女性一九九七年過世時,據說享嵩壽一百二十二歲,成為有史以來最長壽的人士。卡爾芒記得自己見過梵谷,她主要的印象是這位十九世紀的繪畫大師酒氣沖天。此外,第一個成功複製的哺乳類動物桃莉羊在一九九六年誕生時,卡爾芒也得以成為見證人。生物學家預測,與卡爾芒相去不遠的壽命,很快就會成為常態。然而,即便高壽如卡爾芒,她依舊只在世間待了大約六千四百個星期。
以這樣的驚人對比來談壽命,就知道為什麼從古希臘哲人到今日的哲學家,向來把人生苦短視為人類存在的基本問題:上天讓我們的心智有辦法制定幾乎是無遠弗屆的遠大計畫,但實際上根本沒時間付諸行動。羅馬哲學家塞內卡(Seneca)在後世將標題定為《論生命之短暫》(On the Shortness of Life)的書信中,感慨道:「這段交到我們手中的時間匆匆流逝。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部分的人終於感到準備好要開始活的時候,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刻。」我第一次算出四千禮拜這個數字時,腦中一陣暈眩,但一回過神就開始騷擾朋友,要他們猜一般人可以活多久,而且不能做任何心算,要不假思索直接猜。有一位朋友的答案是六位數,而我感到有必要向她指出,即便是相當保守的六位數字,例如三十一萬個星期,大約已經等同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古蘇美人以來,所有人類文明存在的時間。當代哲學家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曾經寫道,幾乎以任何有意義的時間尺度來看,「我們所有人隨時會向生命道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廣義的時間管理,理應是每個人關切的重要事項,可以說人生其實就是一場時間管理。然而,如同時間管理更時髦的兄弟「生產力」,現代所謂「時間管理學」的定義十分狹隘,主要談如何日理萬機,擬定完美的晨間流程,或是在週日煮一堆東西,一次搞定一整個星期的晚餐。這些事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重要性,但不是人生的全部。這個世界處處充滿驚喜,卻很少有生產力大師認為,我們瘋狂地做一大堆事,最終的目的是體驗到更多人生的喜悅。這個世界似乎正在加速衝向災難,我們的文明生活已經進入瘋狂階段,疫情癱瘓了社會,地球這顆行星愈來愈炎熱,但如果你想找到一套時間管理系統協助你和同胞齊心協力,有效解決目前的事件或環境的命運,那就祝你好運了。你可能會以為,至少會有幾本講生產力的書,認真看待人生短暫的嚴肅事實,而不是假裝可以忽略這件事,但是你猜錯了。
因此,本書試圖找回平衡,看看我們能否發現或重拾某種思考時間的方式,好好解決自己面對的真實情境:我們擁有的四千禮拜的壽命短到令人髮指,但仍然充滿光明燦爛的可能性。
輸送帶人生
當然,從某方面來講,今日已經不需要有人提醒時間不夠用。我們的心思全放在爆滿的電子信箱與冗長的待辦事項,心懷罪惡感,老覺得應該再多完成一點事情。我們和愚公一樣努力移山,而且移的不只一座(你怎麼知道人們感到很忙?這種事就和你如何知道某個人吃素一樣:別擔心,他們會告訴你)。民調一再顯示,我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時間壓力;
然而在二〇一三年,荷蘭學術團隊所做的研究,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可能性:這類說我們很忙的民調,可能還低估了這場忙碌流行病的傳染規模,因為極度忙碌的人士過分焦頭爛額,沒空接受民調。隨著近日零工經濟成長,忙碌被重新定義成「複業」(hustle)—無止境的工作不再是必須忍耐再忍耐的重擔,而是令人振奮的生活方式選項,值得在社群媒體上炫耀一番。然而事實上,複業其實是極致的新瓶裝舊酒:壓力逼得我們把永遠在膨脹的活動量,塞進每天再怎麼努力也不會多出一分一秒的二十四小時。然而,哀號很忙只不過是開端。停下來想一想,就會發現其他五花八門的抱怨,其實也是在抱怨時間有限。我們每天都得抗拒網路上令人分心的事物,驚覺能維持專注力的時間大幅縮短,即便是從小就愛看書的我們,如今才讀了一段文字,就忍不住想伸手拿手機。這種現象令人憂心忡忡的根本原因在於,這代表我們未能善用原本就不多的光陰供應(如果晨間時光的供應是無限的,浪費一個早上滑臉書,就不會讓人那麼想掐死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你遇上的問題不是過分忙碌而是不夠充實,在無聊的工作裡日益倦怠,或是想就業也找不到工作。相較於人生苦短,工作不順遠遠更令人沮喪,因為你正在以不想要的方式,消耗自己有限的時間。這年頭最糟糕的發展,甚至也能間接以我們時間有限這個基本事實來解釋。舉例來說,在YouTube 影片的煽風點火下,出現了極度分裂的政黨支持者與激進的恐怖分子。起因是我們的時間與注意力相當有限,也因此很寶貴,社群媒體公司有動機使出渾身解數,不擇手段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那就是為什麼社群媒體要讓用戶觀看保證會群情激憤的內容,而不是無聊的正確事實。
此外,人類有一堆永不過時的煩惱,例如:挑選結婚對象、要不要生小孩、要追求哪一條職業道路。如果我們可以活個幾千年,那種事令人苦惱的程度就會大幅降低,因為時間很充裕,你可以花個數十年,把每一種可能性都嘗試看看。再者,我們的時間煩惱目錄,不能不加上一個令人警覺的現象:三十歲以上的人都熟悉那種感覺,年紀愈大,時間流逝的速度似乎就愈快,而且是穩定加速中。依據七、八十歲人士的說法,幾個月感覺簡直只有幾分鐘而已。很難想像比這更殘酷的命運安排:我們的四千個禮拜不只是持續減少,而是剩得愈少,時間消逝的速度感覺就愈快。如果說我們跟手中有限的時間,關係向來緊張,近日發生的事件更是帶我們來到關鍵時刻。新冠肺炎疫情在二〇二〇年讓我們面臨封城,日常事務被打斷。許多人談到時間完全被打亂,感到不知所措。日子不知怎麼地好像一下子飛逝,但也永遠過不完。時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讓每個人身處不同的世界:有工作、家中又有幼兒的人,時間根本不夠用;休無薪假或無業的人士則時間太多。此外,大家開始在不固定的時間工作,在家窩在發光筆電前,脫離白天與夜晚的循環,或是冒著生命危險,在醫院與快遞貨倉待命。感覺上,未來好像被按下了暫停鍵,許多人困在精神科醫師所說的「新型的永恆當下」,處在焦慮的混沌狀態,不停查看社群媒體,中間穿插一下Zoom 視訊與失眠,無法制定任何有意義的計畫,甚至無法明確描繪出下星期結束後的生活。
對許多人來講,一切的一切讓不善於管理有限的時間,變得特別令人沮喪。我們努力讓時間發揮最大效益,但除了沒成功不說,甚至一再雪上加霜。最近幾年,我們被活出百分之百全效生活的建議給淹沒,市面上的書籍鼓勵我們做到《極度生產力》(ExtremeProductivity,譯註:中譯本書名為《時間,愈用愈有價值》),《一週只需要工作四小時》(The4-Hour Workweek,中譯本書名為《一週工作4小時》),還要《更聰明、更快、更好》(Smarter Faster Better,中譯本書名為《為什麼這樣工作會快、準、好》)。五花八門的網站要我們化身為「生活駭客」,好讓完成日常事務的時間能少個幾秒鐘(「生活駭客」一詞本身就是古怪的建議,彷彿你的人生頂多稱得上某種老是出錯的裝置,需要加以調整,不再永遠處於未達最佳運轉狀態)。各式各樣的app 與穿戴式裝置,再加上Soylent 等代餐飲料,讓你不必浪費時間吃正餐,協助你工作時獲得最大的工作報酬,運動時獲得最大的運動報酬,就連睡覺都能發揮最大的益處。其他成千上萬種產品與服務,主要的賣點也是協助你達成被廣為稱讚的目標:從你的時間中擠出最大效益。問題不在於這些技巧與產品沒用。它們確實有用。你可以完成更多事,趕去開更多會,送孩子去更多課後活動,替你的雇主賺更多錢。然而矛盾的是,成功後,我們得到的只有感到更忙碌、更焦慮,某方面來講還更空虛。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T. Hall)談到現代世界的時間,感覺就像是永遠不會停下的輸送帶,我們一送出完成的工作,就會冒出新工作。所謂變得「更有生產力」,似乎只會加快輸送帶的運轉速度,動作不快點就完了:全面感到深沉的倦怠是今日的常態現象,特徵是無力完成基本的日常事務,年輕成人的受害程度尤其深。套用千禧社會評論家麥爾坎•哈里斯(Malcolm Harris)的話來講:「這個世代的人是被精密打造的工具。從還在媽媽肚子裡,就被塑造成一流的精實生產機器。」他們身上籠罩著無力的疲憊感。
時間有一個面向令人抓狂,但大部分的管理建議似乎都沒注意到這一點。時間有如不受控的幼兒:你愈想控制,要時間照你說的話去做,它就愈是從你手中逃脫。想一想所有意圖協助我們戰勝時間的科技:按照任何合理的邏輯來看,在一個有洗碗機、微波爐與噴射引擎的世界,我們省下了無數小時,理應感到時間變得更充裕、游刃有餘才對,但這不是任何人的實際感受。生活的步調變快,每個人愈來愈沒耐性。不曉得為什麼,在微波爐前等個兩分鐘,比用烤箱烤東西兩小時更煩人。花十秒鐘等網頁龜速下載,令人跳腳的程度,也超過花三天等待相同的內容以紙本形式寄達。
我們增加工作生產力的努力,很多也同樣弄巧成拙。幾年前,我因為被電子郵件淹沒,成功安裝一個叫「清空收件匣」(Inbox Zero)的系統,但很快就發現,我回信變得超有效率之後,只會冒出數量更龐大的電子郵件。暴增的郵件搞得我感到更忙碌,因此我買了時間管理大師大衛•艾倫(David Allen)的《搞定!》(Getting Things Done)一書。艾倫在書中提出的保證很吸引我:「就算你的待辦事項數量多到令人喘不過氣,你依舊可以頭腦清醒,生產力十足」,並維持「武術家所謂『心靜如水』的狀態」。然而,我未能體會艾倫更深層的暗示:你永遠會有太多事要處理。我著手試著完成不可能的工作量。事實上,我迅速完成待辦事項的能力還真的增強了,但結果是神奇地冒出來(這其實不是魔法,只是簡單的心理學外加資本主義。後文會再談到)。前人完全沒料到未來會是這種面貌。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九三〇年的「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那場演講提出著名的預言:由於富裕程度增加,科技進步,在一世紀內,再也沒人需要一星期工作十五小時以上。未來的挑戰將是如何充實我們所有新到手的空檔,卻不至於閒到發瘋。「自有人類以來,史上第一次,」凱因斯告訴聽眾:「人們將面對一個真正、永恆的問題:不再有迫切的經濟壓力之後,該如何利用這份自由。」然而,凱因斯預言失準,民眾賺到足夠的錢滿足需求後,只會找到新的需求,渴望新的生活方式;人們不曾趕上隔壁令人羨慕的鄰居,因為眼看即將追上時,又找到過得更好、想要模仿的新對象。於是乎,每個人汲汲營營,追名逐利,忙碌很快就成為身分地位的象徵。但這一聽就是荒謬透頂的事,因為幾乎在整個人類史上,有錢的重點,就是不必再被工作追著跑。此外,富人的忙碌會傳染,因為對於金字塔頂端的人,極度有效的賺錢方法,就是改善公司與產業的效率,削減成本。這對下層民眾來說,生活益發沒保障,被迫更努力地工作,但也僅能糊口而已。
(未完)
第1章 接受人生有限
我們真正碰上的問題,不在於人生在世、時間有限。真正的問題,或者我希望讓各位明白的是,我們無意間承襲了一套有問題的想法,壓力十足,感到必須按照那種講法來利用有限的時間,但幾乎只會讓事情雪上加霜。如果要瞭解我們是如何陷入今日的窘境,找出如何才能逃脫,與時間建立更理想的關係,我們必須倒轉時鐘,回到時鐘尚未問世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