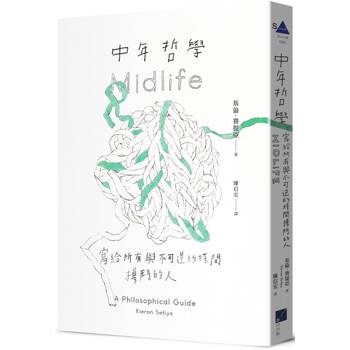第六章 活在當下
我站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公室裡,雙手抱胸,盯著電腦螢幕上的游標在「活在當下」這個標題下閃爍,內心猶豫不決。我真的想寫這一章嗎?
我當然想。我已經為這本書努力了幾個月,前面更構思了多年。我想把這本書寫完。但老實說,這個念頭讓我感到害怕。我不禁自問:「假設這本書完成了,文字經過修訂和編輯,校樣也送回來了:你會有巨大的喜悅與幸福感嗎?」結果,一股無可抑制的自我意識明確回答道:「不會!」我頂多會有一股矛盾的感受。我寫完這本書以後,將會因為自己完成了一件我認為值得做的事情而感到高興,但也必須向這個對我來說深具意義的計畫道別。這會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一個空洞。
如果經驗具有參考價值的話,那這個空洞不必太久就會被填滿。我會有其他計畫要忙:一堂必須教的課、一本必須讀的書、一篇必須寫的文章。我會繼續向前進。不過,這種前進就像是在跑步機上跑步一樣。人生是一連串的計畫,完成一件之後就拋在身後,數量慢慢增加。未來只會帶來更多我在過去已經歷過的那些成就和失敗。它與我已經過去的生活唯一的區別,只在於數量上的不同,只不過是活動的持續累積罷了。
工作只是其中之一,還有私人生活中的各種傳統里程碑:第一個吻、第一任女友、失去童貞、訂婚、結婚、生孩子、為孩子包尿布、養育他們直到高中畢業、進入大學,然後看他們展開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諧星史都華.李(Stewart Lee)所謂的「人生樂事真是有夠沒完沒了」。這些成就對我很重要,但每一項都是苦甜參半:滿懷渴望、努力追求,而終究在完成之後感到失落。這件事結束了,接下來呢?
一再重複與徒勞無功的感受,以及渴望滿足後的空虛:我不是唯一有這些感覺的人。也許你也有過類似的感覺,深陷於中年的各種追求中,一項接著一項,不停思索接下來要做些什麼。我們是中年危機的典型受害者,努力實現那些看似值得追求的目標,雖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內心卻常感焦躁不安,且難以滿足。
儘管我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與彌爾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但第二章提出的治療方法對我的痛苦卻毫無效果。問題不在於寫作一本書或者教授一堂課,就像彌爾的社會改革運動以減少人類苦難為目標那樣,都只具有改善性價值。無論哲學探究在解決問題或是滿足那些我們本來不需要、甚至沒有會更好的需求等方面有何作用,它的價值遠不止於此:哲學具有存在性價值。(至少我是這樣認為,儘管並非只有哲學具有存在性價值。)
我的問題並不在於錯失(第三章)或者出錯(第四章):它們是渴望未被滿足的兩種形式。我的挑戰也不在於遇到挫折,而是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這正是令人困惑的地方,即成功有時候看起來可能像是失敗。無論這種空虛感與面對死亡之間是否有深刻的連繫(對我來說,它們確實緊密相連),總之,在生命篇章中的這一連串成就,總是伴隨著某種空虛感,即使我能永恆或不朽也無法消除這種對人生的懷疑。無論追求一個接一個崇高目標有什麼錯,努力延續這種追求並不能治癒其中的問題。
我們正面臨的這場危機,比起先前遇到的任何危機都更加險惡。但不要絕望。接下來,我將想像自己是坐在心理治療師沙發上的病人,在一位固執哲學家的耐心引導下,試圖找出並詳細描述我的問題,而這個描述本身就是解決方案。原來,答案一直藏在我內心深處,而且是由叔本華放在那裡的。叔本華是西方哲學史上最惡名昭彰的悲觀主義者,也是對「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這種結果的嚴厲批評者。
【叔本華說對了什麼】
叔本華一七八八年出生於但澤(Danzig),今波蘭格但斯克(Gdansk)。他的父母一位是商人,一位是受歡迎的小說家。十五歲那年,叔本華勉強同意放棄自己的學術抱負,接手家族生意,以換取能跟隨父母展開一趟誘人的歐洲之旅。後來證明,這是一個極其荒謬的不幸決定。一八〇三年夏天,叔本華在倫敦目睹了處決,看到死囚臉上流露的恐懼和驚駭;他也參觀了法國的公共監獄,那裡的囚犯像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被展示出來。多年後,他將自己這些經歷比作佛陀初次接觸疾病、衰老、痛苦和死亡的覺悟經驗:他見識到人類生活的悲慘處境,從此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對於叔本華而言,作為聽話兒子的獎勵,是一場糟糕透頂的家庭假期。
事情並未好轉。他的父親在兩年後疑似自殺,從倉庫閣樓上跌入運河裡溺斃。叔本華信守了從商的承諾,忍受了兩年單調乏味的工作後,才又重拾學業,輾轉於哥達(Gotha)、哥廷根(Göttingen)、柏林和耶拿(Jena),最終在一八一三年取得博士學位。母親約翰娜(Johanna)嫌棄他的博士論文《論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On the Fourfol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晦澀難懂,是一本「為藥劑師而寫」的書,絕對不會有人買。母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從未緩和。一八一四年,叔本華搬到德勒斯登,從此再也沒有與母親見面。
叔本華就是在德勒斯登寫出他的傑作《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可嘆的是,這本書在當時並沒有被視為一部傑作。後來叔本華獲得柏林大學聘用,卻把自己的課安排在與黑格爾衝堂的時間,絲毫沒有考慮到黑格爾是當時最著名的哲學家。這樣的做法就好比把一部影集的首播安排在與超級盃轉播相同的時間。可想而知,沒人來聽他的課。叔本華帶著屈辱於一八二二年離開柏林。直到晚年,他才因為在一八五一年出版了《附錄與補遺》(Parerga and Paralipomena)這部散文與沉思集而獲得一些名聲。他在九年後去世,倒在自己公寓的沙發上,享年七十二歲。
如果我說叔本華對欲望/渴望(desire)抱持不信任態度,你可能覺得這不足為奇。但他的不信任態度卻是出奇強烈:問題不在於欲望經常得不到滿足,而是欲望會造成一種兩難的困境,即使得到滿足也無法化解。假設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東西,你的欲望終於實現了。這時你應該感到欣喜,但實際上你會感到茫然和沮喪。因為追求已經結束,你已然無事可做。人生需要方向,必須有尚未完成的欲望、目標和計畫。然而,這同樣也是死路,因為想要你沒有的東西即意味著受苦。如同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寫的:
然而,一切的意志源於需求與欠缺,因此帶來痛苦,所以〔動物〕由於其本質和起源而注定受苦。但另一方面,動物如果因為意志太容易獲得滿足,導致意志對象被剝奪,這時他們又會因為欠缺意志對象而感到一股可怕的空虛和煩悶。換句話說,動物的存有與存在會成為一項難以承受的重擔。因此,動物就像鐘擺一樣在痛苦與煩悶之間擺盪,而這兩者實際上就是動物的最終組成部分。
這就是叔本華認為的兩難困境。你的意志要麼有對象,要麼沒有:你要麼想要某些東西,要麼根本沒有這樣的欲望。你如果沒有欲望,你將變得漫無目標,生活變得空虛。這就是煩悶的深淵。反之,如果你有欲望,你欲望的對象必定是那些尚未實現的結果,而這些結果就是你追求的目標,占據了你生活中的各種活動。然而,渴望你沒有的東西本身會帶來痛苦。你為了逃避煩悶而找事情做,反而因此把自己打入痛苦的深淵。
難怪學生都不去聽叔本華的課:他和勵志演說家恰恰相反。他眼中的人生異常荒涼。確實沒有目標的人生相當空虛,甚至稱不上是人生。我們需要有事情做,而一旦完成一件事情,就需要再找別的事情來做。然而,追求目標並不全然是痛苦的,至少不必如此。像我現在想要寫完這本書,我對於將來它完成時抱有正面的期待,而對於現在它仍未完成抱有負面的感受:草稿還躺在電腦的硬碟裡。對於叔本華來說,這種負面感受帶來痛苦。但實際上,我們可以認為並沒有那麼糟。我對寫書這件事抱持的是一種有興趣的偏好,而非那種迫切、痛苦的欲望。把這種狀態稱為「受苦」,未免誇大了未滿足欲望所帶來的情感衝擊。很好,我們化解了叔本華的困境!
但話說回來,叔本華的看法確實有其道理。他對我們與欲望之間關係的悲觀負面描述,蘊含著洞見。我們可以這樣想:唯有追求目標才能為人生賦予意義,但對於目標的追求,不是以失敗告終(這樣自然不好),就是在成功後畫下句點。如果你關注的是成就,例如升遷、生兒育女、寫書、救人,完成這些計畫或許有其價值,但這也意味著這個計畫不再能引導你前進。當然,你會有其他目標,也可以設立新的目標。問題不在於目標可能耗竭,導致你陷入叔本華稱之為漫無目標的夢魘般煩悶中;問題在於你對價值的參與本質上是自我毀滅的。你與那些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活動之間的關係,是在努力完成它們後,從而將它們從你的生活中驅逐。你把時間投注於一一完成為人生賦予意義的各種活動。雖然你不可能完成所有活動,但這個事實帶來的慰藉僅是聊勝於無。而且,達成一項成就後所獲得的滿足,也只能維持一下子。因為你與構成人生意義的價值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內在對立的:你在追求與完成目標的過程中,你和這些價值產生互動,但你想要取得的結果卻會剝奪你繼續與這些價值互動的可能性。你對一個目標的追求,實際上是在耗竭你與某種美好事物的互動關係,就好像你交朋友的目的是為了和他道別。因此,即使叔本華對於欲望帶來痛苦的描述有些偏激,我們仍能從中學到一件事:欲望和目標之間存在一種結構性矛盾。
依循前面各章的做法,接下來我們同樣將借用一些新的術語或概念,來幫助我們探索心靈、促進成長。先從構成你生活的各項活動開始:找工作、交報告、下班開車回家、聽音樂、出門散步。借用語言學的術語,我們可以說有些活動是「終點性」(telic)的:它們以達到某個終點為目標,一旦完成,即結束並不再繼續(耗竭)。(「telic」一詞源自希臘文的「telos」,意為終點或目的,「teleology」〔目的論〕也是源自這個字根。)開車回家就是一種終點性的活動:當你到家時,這個活動就完成並耗竭了。結婚或寫書這類計畫也是如此,它們都是可以完成的。有些活動則是「無終點性」(atelic)的:這類活動不以達成某個終點為目標,也不會有真正完成的時刻。例如,除了從A點走到B點,你也可以無目的地散步。這就是一種無終點性的活動。聽音樂、和朋友或家人外出閒晃,或者思索中年問題,也都屬於這類活動。你可以選擇停止做這些事情,但它們無法被真正完成,因為它們沒有明確的終點,也不會有耗竭或結束的狀態。
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形上學》(Metaphysics)中也做了類似的區分。在亞里斯多德眼中,世界上有兩種「行為」(praxis)或行動。一些是「不完整的」(incomplete),例如學習或建造某物,因為「如果你正在學習,就意味著你還沒學會」。而有些行為則「自帶完整的屬性」,像是觀看、理解或思考。亞里斯多德稱第一種行動為「動性」行動(kinêsis):這種行動本質上是終點性的,目標在於本身的終結。如同哲學家寇斯曼(Aryeh Kosman)貼切指出的:「〔這種〕存在本身是自我顛覆的,因為它的整個目標與計畫就是自我毀滅。」
這就是埋首於計畫、執迷於完成工作的問題所在。如果你的意義來源主要依賴於終點性的活動,則無論這些活動帶有何種價值(終極價值、存在性價值,或是改善性價值),它們的成功都只能意味著結束。這就像你拚命地試圖抹去人生中的意義,只是因為世界上有太多意義,或是你不斷發現新的意義,才不至於完全耗竭。叔本華在這方面的看法確實有其道理:如果你過度聚焦於終點性的活動,你的努力最終會與自己作對。你追求目標的動機「來自於欠缺,來自於不足」,甚至可能來自於痛苦──因為你與這些目標之間還有一段距離,所以感到缺失。然而,一旦你達成了目標,你也就終結了一項曾賦予你人生意義的活動。
我的中年危機就是受到這種自毀引擎所驅動,而你的中年危機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如此。我用了四十年培養對終點性活動的愛好與才能,不斷追求成就和下一件大事,不斷追求個人生活與職業生涯上的成功,結果卻因此感到內心空虛。滿足總是屬於未來或過去。人不應該這樣過活。
社會歷史學家會問,奮鬥與成功的意識形態是如何隨著時間發展的,這種意識形態如何在不同歷史與地理環境中展現其地方性,以及它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社會學家韋伯於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劃時代著作)有哪些關連。而我們會問,這種意識形態跟中年有哪些關連。理論上,任何人都能察覺到存在於終點性活動中的空虛。像彌爾這樣的天才可能會提早遭遇危機,但往往是在中年,一般人對於終點性活動的依賴最有可能顯現出來,因為長期追求的目標要麼實現了,要麼無法實現。你已經得到多年來努力爭取的工作,找到了理想的伴侶,成就了你期盼的家庭──或者沒有。在此之前,你可能都沒有理由去反思抱負的耗竭,以及你的人生在多大程度上是圍繞這些抱負建構的。到了中年,一切突然變得清楚起來。你可能模糊地感受到靈魂的自毀傾向。歡迎來到我的世界。
你的危機如果很嚴重,你會看到人生的敘事破裂了:事情開始分崩離析。在瑞秋.庫斯克(Rachel Cusk)《輪廓》(Outline)這本不好懂的小說中,一位創造力豐沛的作家前往雅典教授暑期課程。由於她對自己的人生避而不談,卻因此吸引到別人對她傾吐人生故事。她的朋友帕尼歐提斯(Paniotis)講述了自己離婚的經過:
他現在意識到,進步原則一直在他的婚姻裡作用著,推促他購屋、累積財產、買車、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規劃更多的旅遊、結交更多的朋友,甚至就連生育子女也被視為人生這趟瘋狂旅程中不能不造訪的一個景點。而他現在看到,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一旦不再有東西可以添加或者改善,一旦不再有需要達成的目標或者必須通過的階段,這趟旅程似乎已經抵達了終點,於是他和妻子被一股巨大的徒勞感受所困擾,覺得自己彷彿患了什麼病,但實際上只是在一段太忙碌的人生之後隨之而來的靜止感而已,就像水手在海上航行太久之後再次踏上陸地的感受。但對於他們兩人而言,這種感覺卻意味著他們已不再相愛。
對於帕尼歐提斯而言,終點導向思維,也就是將意義投資於一個又一個計畫,最終導致了叔本華所說的煩悶深淵:在他與妻子的關係中,已經沒有事情可以做了,因此,像破解最後一個線索的尋寶遊戲一樣,這段婚姻也走到了盡頭。錯誤從一開始就存在,隱藏在從A點到B點的匆忙之中:愛情不是一個可以完成的計畫。
關係可能會失敗;愛有可能不完美;愛可能會消退。哲學改變不了這些事實。但如果你的挫折感來自於你對愛情抱持終點性態度,認為愛終有耗竭的一天,搞婚外情也不會對你有所幫助。問問自己:我是真的想和別人在一起,還是我只是渴望那種墜入愛河的刺激,或是想要重新體驗把人拐上床那種終點性的興奮感。我不是說你不會樂在其中;也許你會,但這同樣有耗盡的一天。外遇如同是一項計畫,它終究會結束,然後你將回到原點:也就是,再次站在欲望的終點上。想想引誘安娜.卡列尼娜的渥倫斯基伯爵(Count Vronsky):「他很快感覺到,他原本預期能得到如山般龐大的快樂,但他的欲望滿足後為他帶來的,卻只有那座山的一顆沙粒。欲望得到實現讓他明白,人們想像幸福在於欲望的滿足,這是一個世人一再重蹈的亙古錯誤。」
(下略)
我站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公室裡,雙手抱胸,盯著電腦螢幕上的游標在「活在當下」這個標題下閃爍,內心猶豫不決。我真的想寫這一章嗎?
我當然想。我已經為這本書努力了幾個月,前面更構思了多年。我想把這本書寫完。但老實說,這個念頭讓我感到害怕。我不禁自問:「假設這本書完成了,文字經過修訂和編輯,校樣也送回來了:你會有巨大的喜悅與幸福感嗎?」結果,一股無可抑制的自我意識明確回答道:「不會!」我頂多會有一股矛盾的感受。我寫完這本書以後,將會因為自己完成了一件我認為值得做的事情而感到高興,但也必須向這個對我來說深具意義的計畫道別。這會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一個空洞。
如果經驗具有參考價值的話,那這個空洞不必太久就會被填滿。我會有其他計畫要忙:一堂必須教的課、一本必須讀的書、一篇必須寫的文章。我會繼續向前進。不過,這種前進就像是在跑步機上跑步一樣。人生是一連串的計畫,完成一件之後就拋在身後,數量慢慢增加。未來只會帶來更多我在過去已經歷過的那些成就和失敗。它與我已經過去的生活唯一的區別,只在於數量上的不同,只不過是活動的持續累積罷了。
工作只是其中之一,還有私人生活中的各種傳統里程碑:第一個吻、第一任女友、失去童貞、訂婚、結婚、生孩子、為孩子包尿布、養育他們直到高中畢業、進入大學,然後看他們展開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諧星史都華.李(Stewart Lee)所謂的「人生樂事真是有夠沒完沒了」。這些成就對我很重要,但每一項都是苦甜參半:滿懷渴望、努力追求,而終究在完成之後感到失落。這件事結束了,接下來呢?
一再重複與徒勞無功的感受,以及渴望滿足後的空虛:我不是唯一有這些感覺的人。也許你也有過類似的感覺,深陷於中年的各種追求中,一項接著一項,不停思索接下來要做些什麼。我們是中年危機的典型受害者,努力實現那些看似值得追求的目標,雖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內心卻常感焦躁不安,且難以滿足。
儘管我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與彌爾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但第二章提出的治療方法對我的痛苦卻毫無效果。問題不在於寫作一本書或者教授一堂課,就像彌爾的社會改革運動以減少人類苦難為目標那樣,都只具有改善性價值。無論哲學探究在解決問題或是滿足那些我們本來不需要、甚至沒有會更好的需求等方面有何作用,它的價值遠不止於此:哲學具有存在性價值。(至少我是這樣認為,儘管並非只有哲學具有存在性價值。)
我的問題並不在於錯失(第三章)或者出錯(第四章):它們是渴望未被滿足的兩種形式。我的挑戰也不在於遇到挫折,而是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這正是令人困惑的地方,即成功有時候看起來可能像是失敗。無論這種空虛感與面對死亡之間是否有深刻的連繫(對我來說,它們確實緊密相連),總之,在生命篇章中的這一連串成就,總是伴隨著某種空虛感,即使我能永恆或不朽也無法消除這種對人生的懷疑。無論追求一個接一個崇高目標有什麼錯,努力延續這種追求並不能治癒其中的問題。
我們正面臨的這場危機,比起先前遇到的任何危機都更加險惡。但不要絕望。接下來,我將想像自己是坐在心理治療師沙發上的病人,在一位固執哲學家的耐心引導下,試圖找出並詳細描述我的問題,而這個描述本身就是解決方案。原來,答案一直藏在我內心深處,而且是由叔本華放在那裡的。叔本華是西方哲學史上最惡名昭彰的悲觀主義者,也是對「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這種結果的嚴厲批評者。
【叔本華說對了什麼】
叔本華一七八八年出生於但澤(Danzig),今波蘭格但斯克(Gdansk)。他的父母一位是商人,一位是受歡迎的小說家。十五歲那年,叔本華勉強同意放棄自己的學術抱負,接手家族生意,以換取能跟隨父母展開一趟誘人的歐洲之旅。後來證明,這是一個極其荒謬的不幸決定。一八〇三年夏天,叔本華在倫敦目睹了處決,看到死囚臉上流露的恐懼和驚駭;他也參觀了法國的公共監獄,那裡的囚犯像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被展示出來。多年後,他將自己這些經歷比作佛陀初次接觸疾病、衰老、痛苦和死亡的覺悟經驗:他見識到人類生活的悲慘處境,從此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對於叔本華而言,作為聽話兒子的獎勵,是一場糟糕透頂的家庭假期。
事情並未好轉。他的父親在兩年後疑似自殺,從倉庫閣樓上跌入運河裡溺斃。叔本華信守了從商的承諾,忍受了兩年單調乏味的工作後,才又重拾學業,輾轉於哥達(Gotha)、哥廷根(Göttingen)、柏林和耶拿(Jena),最終在一八一三年取得博士學位。母親約翰娜(Johanna)嫌棄他的博士論文《論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On the Fourfol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晦澀難懂,是一本「為藥劑師而寫」的書,絕對不會有人買。母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從未緩和。一八一四年,叔本華搬到德勒斯登,從此再也沒有與母親見面。
叔本華就是在德勒斯登寫出他的傑作《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可嘆的是,這本書在當時並沒有被視為一部傑作。後來叔本華獲得柏林大學聘用,卻把自己的課安排在與黑格爾衝堂的時間,絲毫沒有考慮到黑格爾是當時最著名的哲學家。這樣的做法就好比把一部影集的首播安排在與超級盃轉播相同的時間。可想而知,沒人來聽他的課。叔本華帶著屈辱於一八二二年離開柏林。直到晚年,他才因為在一八五一年出版了《附錄與補遺》(Parerga and Paralipomena)這部散文與沉思集而獲得一些名聲。他在九年後去世,倒在自己公寓的沙發上,享年七十二歲。
如果我說叔本華對欲望/渴望(desire)抱持不信任態度,你可能覺得這不足為奇。但他的不信任態度卻是出奇強烈:問題不在於欲望經常得不到滿足,而是欲望會造成一種兩難的困境,即使得到滿足也無法化解。假設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東西,你的欲望終於實現了。這時你應該感到欣喜,但實際上你會感到茫然和沮喪。因為追求已經結束,你已然無事可做。人生需要方向,必須有尚未完成的欲望、目標和計畫。然而,這同樣也是死路,因為想要你沒有的東西即意味著受苦。如同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寫的:
然而,一切的意志源於需求與欠缺,因此帶來痛苦,所以〔動物〕由於其本質和起源而注定受苦。但另一方面,動物如果因為意志太容易獲得滿足,導致意志對象被剝奪,這時他們又會因為欠缺意志對象而感到一股可怕的空虛和煩悶。換句話說,動物的存有與存在會成為一項難以承受的重擔。因此,動物就像鐘擺一樣在痛苦與煩悶之間擺盪,而這兩者實際上就是動物的最終組成部分。
這就是叔本華認為的兩難困境。你的意志要麼有對象,要麼沒有:你要麼想要某些東西,要麼根本沒有這樣的欲望。你如果沒有欲望,你將變得漫無目標,生活變得空虛。這就是煩悶的深淵。反之,如果你有欲望,你欲望的對象必定是那些尚未實現的結果,而這些結果就是你追求的目標,占據了你生活中的各種活動。然而,渴望你沒有的東西本身會帶來痛苦。你為了逃避煩悶而找事情做,反而因此把自己打入痛苦的深淵。
難怪學生都不去聽叔本華的課:他和勵志演說家恰恰相反。他眼中的人生異常荒涼。確實沒有目標的人生相當空虛,甚至稱不上是人生。我們需要有事情做,而一旦完成一件事情,就需要再找別的事情來做。然而,追求目標並不全然是痛苦的,至少不必如此。像我現在想要寫完這本書,我對於將來它完成時抱有正面的期待,而對於現在它仍未完成抱有負面的感受:草稿還躺在電腦的硬碟裡。對於叔本華來說,這種負面感受帶來痛苦。但實際上,我們可以認為並沒有那麼糟。我對寫書這件事抱持的是一種有興趣的偏好,而非那種迫切、痛苦的欲望。把這種狀態稱為「受苦」,未免誇大了未滿足欲望所帶來的情感衝擊。很好,我們化解了叔本華的困境!
但話說回來,叔本華的看法確實有其道理。他對我們與欲望之間關係的悲觀負面描述,蘊含著洞見。我們可以這樣想:唯有追求目標才能為人生賦予意義,但對於目標的追求,不是以失敗告終(這樣自然不好),就是在成功後畫下句點。如果你關注的是成就,例如升遷、生兒育女、寫書、救人,完成這些計畫或許有其價值,但這也意味著這個計畫不再能引導你前進。當然,你會有其他目標,也可以設立新的目標。問題不在於目標可能耗竭,導致你陷入叔本華稱之為漫無目標的夢魘般煩悶中;問題在於你對價值的參與本質上是自我毀滅的。你與那些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活動之間的關係,是在努力完成它們後,從而將它們從你的生活中驅逐。你把時間投注於一一完成為人生賦予意義的各種活動。雖然你不可能完成所有活動,但這個事實帶來的慰藉僅是聊勝於無。而且,達成一項成就後所獲得的滿足,也只能維持一下子。因為你與構成人生意義的價值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內在對立的:你在追求與完成目標的過程中,你和這些價值產生互動,但你想要取得的結果卻會剝奪你繼續與這些價值互動的可能性。你對一個目標的追求,實際上是在耗竭你與某種美好事物的互動關係,就好像你交朋友的目的是為了和他道別。因此,即使叔本華對於欲望帶來痛苦的描述有些偏激,我們仍能從中學到一件事:欲望和目標之間存在一種結構性矛盾。
依循前面各章的做法,接下來我們同樣將借用一些新的術語或概念,來幫助我們探索心靈、促進成長。先從構成你生活的各項活動開始:找工作、交報告、下班開車回家、聽音樂、出門散步。借用語言學的術語,我們可以說有些活動是「終點性」(telic)的:它們以達到某個終點為目標,一旦完成,即結束並不再繼續(耗竭)。(「telic」一詞源自希臘文的「telos」,意為終點或目的,「teleology」〔目的論〕也是源自這個字根。)開車回家就是一種終點性的活動:當你到家時,這個活動就完成並耗竭了。結婚或寫書這類計畫也是如此,它們都是可以完成的。有些活動則是「無終點性」(atelic)的:這類活動不以達成某個終點為目標,也不會有真正完成的時刻。例如,除了從A點走到B點,你也可以無目的地散步。這就是一種無終點性的活動。聽音樂、和朋友或家人外出閒晃,或者思索中年問題,也都屬於這類活動。你可以選擇停止做這些事情,但它們無法被真正完成,因為它們沒有明確的終點,也不會有耗竭或結束的狀態。
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形上學》(Metaphysics)中也做了類似的區分。在亞里斯多德眼中,世界上有兩種「行為」(praxis)或行動。一些是「不完整的」(incomplete),例如學習或建造某物,因為「如果你正在學習,就意味著你還沒學會」。而有些行為則「自帶完整的屬性」,像是觀看、理解或思考。亞里斯多德稱第一種行動為「動性」行動(kinêsis):這種行動本質上是終點性的,目標在於本身的終結。如同哲學家寇斯曼(Aryeh Kosman)貼切指出的:「〔這種〕存在本身是自我顛覆的,因為它的整個目標與計畫就是自我毀滅。」
這就是埋首於計畫、執迷於完成工作的問題所在。如果你的意義來源主要依賴於終點性的活動,則無論這些活動帶有何種價值(終極價值、存在性價值,或是改善性價值),它們的成功都只能意味著結束。這就像你拚命地試圖抹去人生中的意義,只是因為世界上有太多意義,或是你不斷發現新的意義,才不至於完全耗竭。叔本華在這方面的看法確實有其道理:如果你過度聚焦於終點性的活動,你的努力最終會與自己作對。你追求目標的動機「來自於欠缺,來自於不足」,甚至可能來自於痛苦──因為你與這些目標之間還有一段距離,所以感到缺失。然而,一旦你達成了目標,你也就終結了一項曾賦予你人生意義的活動。
我的中年危機就是受到這種自毀引擎所驅動,而你的中年危機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如此。我用了四十年培養對終點性活動的愛好與才能,不斷追求成就和下一件大事,不斷追求個人生活與職業生涯上的成功,結果卻因此感到內心空虛。滿足總是屬於未來或過去。人不應該這樣過活。
社會歷史學家會問,奮鬥與成功的意識形態是如何隨著時間發展的,這種意識形態如何在不同歷史與地理環境中展現其地方性,以及它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社會學家韋伯於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劃時代著作)有哪些關連。而我們會問,這種意識形態跟中年有哪些關連。理論上,任何人都能察覺到存在於終點性活動中的空虛。像彌爾這樣的天才可能會提早遭遇危機,但往往是在中年,一般人對於終點性活動的依賴最有可能顯現出來,因為長期追求的目標要麼實現了,要麼無法實現。你已經得到多年來努力爭取的工作,找到了理想的伴侶,成就了你期盼的家庭──或者沒有。在此之前,你可能都沒有理由去反思抱負的耗竭,以及你的人生在多大程度上是圍繞這些抱負建構的。到了中年,一切突然變得清楚起來。你可能模糊地感受到靈魂的自毀傾向。歡迎來到我的世界。
你的危機如果很嚴重,你會看到人生的敘事破裂了:事情開始分崩離析。在瑞秋.庫斯克(Rachel Cusk)《輪廓》(Outline)這本不好懂的小說中,一位創造力豐沛的作家前往雅典教授暑期課程。由於她對自己的人生避而不談,卻因此吸引到別人對她傾吐人生故事。她的朋友帕尼歐提斯(Paniotis)講述了自己離婚的經過:
他現在意識到,進步原則一直在他的婚姻裡作用著,推促他購屋、累積財產、買車、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規劃更多的旅遊、結交更多的朋友,甚至就連生育子女也被視為人生這趟瘋狂旅程中不能不造訪的一個景點。而他現在看到,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一旦不再有東西可以添加或者改善,一旦不再有需要達成的目標或者必須通過的階段,這趟旅程似乎已經抵達了終點,於是他和妻子被一股巨大的徒勞感受所困擾,覺得自己彷彿患了什麼病,但實際上只是在一段太忙碌的人生之後隨之而來的靜止感而已,就像水手在海上航行太久之後再次踏上陸地的感受。但對於他們兩人而言,這種感覺卻意味著他們已不再相愛。
對於帕尼歐提斯而言,終點導向思維,也就是將意義投資於一個又一個計畫,最終導致了叔本華所說的煩悶深淵:在他與妻子的關係中,已經沒有事情可以做了,因此,像破解最後一個線索的尋寶遊戲一樣,這段婚姻也走到了盡頭。錯誤從一開始就存在,隱藏在從A點到B點的匆忙之中:愛情不是一個可以完成的計畫。
關係可能會失敗;愛有可能不完美;愛可能會消退。哲學改變不了這些事實。但如果你的挫折感來自於你對愛情抱持終點性態度,認為愛終有耗竭的一天,搞婚外情也不會對你有所幫助。問問自己:我是真的想和別人在一起,還是我只是渴望那種墜入愛河的刺激,或是想要重新體驗把人拐上床那種終點性的興奮感。我不是說你不會樂在其中;也許你會,但這同樣有耗盡的一天。外遇如同是一項計畫,它終究會結束,然後你將回到原點:也就是,再次站在欲望的終點上。想想引誘安娜.卡列尼娜的渥倫斯基伯爵(Count Vronsky):「他很快感覺到,他原本預期能得到如山般龐大的快樂,但他的欲望滿足後為他帶來的,卻只有那座山的一顆沙粒。欲望得到實現讓他明白,人們想像幸福在於欲望的滿足,這是一個世人一再重蹈的亙古錯誤。」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