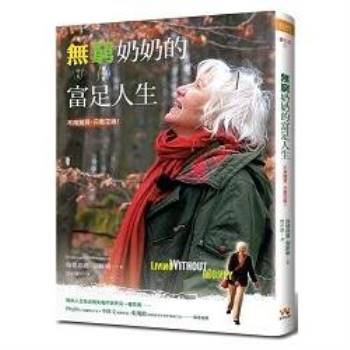承諾
我兩歲生日收到的禮物是一座娃娃屋,當年我一定欣喜若狂,因為我一邊大笑一邊拍著手在房間裡跳來跑去,雀躍的身影如今依舊歷歷在目。兩個哥哥、母親和保母艾拉也感染了我這個小小孩的喜悅,在一旁跟著開心。當時我們住在梅梅爾(Memel),父親在那兒有座咖啡烘焙廠―應該說曾經擁有過。
但我和我的小小玩具王國只共度了短短幾個月的幸福時光。一九四四年夏天,家裡隱隱浮動著一股不安,一開始我怎麼也想不透。先是放在閣樓地板上的心愛娃娃屋消失不見,接著屋子裡所有家具全蓋上了布,母親和祖母也整理行囊,準備出門。他們只帶上必要的行李,不斷彼此打氣,保證我們很快會回家。馬車備妥,等候出發。平常星期日時,我們偶爾駕著馬車出遊,度過快樂的時光。不過,這次的氣氛截然不同,母親淚流滿面,兩個哥哥也異常安靜。迥異於平日的是,街上擠滿了驅馬駕車的人潮。我們的馬車匯入隊伍裡,跟著往前走。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心裡十分害怕,哭了起來。母親無暇照應我,心思全放在我的小妹身上,當時她病入膏肓,不過仍從醫院接了回來。不到三歲的我又冷又餓,一心只想回家,想回去找我的絨毛玩偶,躺在溫暖的被窩裡。終於,母親注意到了我的絕望,輕聲對我說:「噓,小寶貝,情況會好轉的。」但是我覺得事情不會好轉,明天不會變好,過了一天也一樣。後來我們在某地低價賣掉馬車,改搭火車繼續前進。火車班班超載,車廂裡冷颼颼的,搭乘起來極不舒服。旅程勞累辛苦,而且不乏危險。火車只要一靠站,母親就迅速抓起一把大鍋子,到鐵軌兩旁的農舍乞討食物給我們四個孩子和祖母。母親每次飛奔出去,對我們就像是酷刑,不知道她能否及時趕回來。有一次母親果真還沒出現,火車就開動了,嚇得我們使盡吃奶的力氣放聲尖叫。至今我仍不清楚是我們絕望的叫聲停下了火車,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有好幾次,火車上的乘客全得盡速下車,躲到最近的樹底下尋求保護。下一秒,天空中即忽見戰鬥機密布,並且擊發砲彈轟炸火車,連人也不放過。我們的恐懼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攻擊行動逐漸膨脹,心裡明白有幾個同行的乘客倒臥在鐵軌旁,已經死去。有時候火車一停就是好幾個小時,無窮無盡,誰也不知道能否開動,又會在何時繼續前行。我們橫越了幾千公里,從東普魯士到南德,接著又往北走一段路,直到抵達阿勒爾河(Aller)畔的費爾登(Verden),旅程才算告一段落。當地的家庭聚集在火車站迎接我們,我這才明白原來我們是難民,而他們不管願意與否,都必須接納我們。許多人毫不掩飾自己的情緒,明顯表露出排拒的態度,因為要和因戰爭而流落至此的身無分文陌生人分享自己的一切,而感到憤恨不平。不過,幸好我們運氣很好,收容我們的農夫是個好人,他和妻子非常疼愛我們這些孩子,復活節時,我們還找了藏起來的彩蛋,而且好幾個星期都享用豐盛的食物,從未挨餓受凍。母親和祖母幫忙農夫做家事,這是在和睦氣氛中進行的交換與分享,施與受。在如此安樂的環境中,我幾乎忘了過去幾個月的痛苦。
但是戰爭仍未結束,媽媽終日掛心其他親戚,一得知他們後來到了石勒蘇益格―荷爾絲泰因邦(Schleswig-Holstein),說什麼也要到那兒去。善良的農夫力勸我們留下,但只是白費力氣。我們再次踏上旅程,最後雖然找到親戚,卻經歷了截然不同的施與受。有個農夫家庭滿心不樂意收容我們,嫌我們帶來麻煩。我們一家大小只能擠在一間小斗室,感覺自己像是多餘的累贅,而且生活窮困貧乏。待在這裡,我們又一次忍飢挨餓。戰爭後來終於結束,但我們永遠失去了以前那個家,再也回不去了。我們和其他逃難出來的人一樣,必須在新的環境中設法安頓自己,於是我們到田野中撿拾剩下的麥穗,也撿拾馬鈴薯,全家人還經常拿著籃子和水桶到森林裡採集莓果。
收容我們的農夫家庭不願意和我們分享食物,煮飯時,滿屋飄著飯菜香,擠在斗室裡的我們只能口水直流,可惜光是聞香也不能填飽肚子。母親後來在一處莊園找到了農務工作,才換來一點奶油和牛奶。除此之外,她還教附近幾個農家女兒彈鋼琴,酬勞是馬鈴薯、麵包、蛋和麵粉等寶貴的食物。有一天,父親從戰場上歸來,到北德來找我們,著手建立自己的家,我們才總算慢慢過起所謂的「正常」生活。只不過,過去幾年的經歷並非船過水無痕,仍舊對我造成了影響,我成了一個愛幻想的安靜小女孩。上小學後,我埋頭學習認字,認得了字後,眼前彷彿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的第一本書是本質地粗糙的厚重童話故事集,我時常帶著這個寶貝窩到我在樹籬中一手搭蓋出來的樹洞裡,和故事中的王子與公主待在屬於我們的小天地,全心全意沉浸在一個比現實生活公正與美好的世界。我在樹洞裡汲取力量,培養出自己對於生命可能樣貌的最初觀念,或者應該說,我認為生命應有的樣貌。我對於故事中邪惡必敗、愛贏得勝利的結局深為傾心。是的,我希望擁有這樣的世界。
然而我卻被迫經歷人射殺人、強取豪奪、衣食無虞者不願施捨一口食物給挨餓者的境況。為什麼我就得留下心愛的玩具,搭著寒冷的火車好幾個月跋涉千里,挨餓受凍,穿越屍橫遍地的地區?為什麼只因為我是難民小孩,就活該被罵成無賴?只因為我沒有真正的鞋子可穿,勉強湊合著木頭做成的鞋,就得受盡嘲笑?誰能明白這一切?還有,在這樣的世界裡,我失去了什麼?我至今依然認為童話有其象徵意義。我知道每個人都能貢獻一己之力,把地球變得更美好,更適合居住。當年在那個寂寞的童話樹洞裡,我想必早已預料到這一點。到現在,我眼前仍舊浮現那個哀傷的難民小女孩對自己許下的宏大承諾:「我要付出一切,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戰爭,人人活得有尊嚴。」
打開了一扇門
我的兒子轉學到文理高中後適應困難,出現焦慮與不安。儘管我再怎麼安慰他,「你不需要覺得害怕。」「我會陪著你。」也始終沒有效果。我不由得憂心忡忡。
進修教師培訓課程時,我認識了幾位心理系學生,向他們討教這個問題。他們請我帶著兒子到他們在漢堡的機構,進行遊戲治療。在治療過程中,孩子透過遊戲獲得他人的支持與理解,父母則和另一個人對話討論,試圖釐清孩子出現精神障礙的可能成因以及治療方式。由於整個過程也屬於心理系學生的進修課程,所以我們無需付費。我同意待在鑲著單向玻璃的房間裡進行討論,也就是說,教授和他的學生可以在單向玻璃的另一邊,全程追蹤與討論這件「施維姆案」。由於我看不見另一邊的他們,所以很容易忘記自己正被人觀察著。我和兒子連續好幾週到漢堡進行治療,而這個經驗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十七歲兒子雖然出現許多治療的可能,但是總體而言,當年的專業心理治療尚未發展成熟。在我們學校老師當中,我是第一個接觸這類事情的人。我兒子經過十次諮商逐漸找回重心後,我的世界卻第一次崩解了。
我哭了。我每個星期三下午去見談話對象羅伯特,講沒幾句話,眼淚就潰不成堤,一發不可收拾。然而那是解脫的淚水,所以每次諮商結束,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總是一身輕鬆,感覺淚水鬆脫了內在的阻礙,蓄滿新的能量。我學習將意識放在呼吸上,專注於一呼一吸之間,控制調息,就像調整自己的想法一樣。我從未想過自己對自己竟擁有如此的力量。
我之所以淚流滿面,與心中潛在的受害者角色有關,與始終伴著我(且壓迫我)的無助感有關。我逐漸明白自己並不只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始作俑者。我必須擺脫別人是壞人的想法,看清自己也是助紂為虐的幫凶。以前我當然察覺到我能保護自己,而且我的舉止粗野不雅時所產生的罪惡感也是其來有自,但是在治療前,我始終沒看出有機會能處理心中的罪惡感。
如今我大學時期學習的心理學理論終於派上用場,與現實接軌。諮商過程中驚喜不斷,到最後我明白了一件事:只要準備好,人人都可以改變自己。我想起心理學課堂上曾經教過的有名案例:兩個男嬰出生後沒多久,無意中被調換了,一個出身有教養的高貴家庭,另一個則來自賊窩。但是小男嬰長大後,竟發展出不適合各自成長環境的行為模式。由於現象異常,後來才發現抱錯了小孩。由此得出的明顯結論是:行為模式是先天遺傳,而非後天養成的,教育無法戰勝天性,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就是會打洞。
但是,果真如此嗎?這個問題長年困擾著我。現在,我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了答案:人人都有機會創造自己的生命,而非聽任命運擺布。我因為這個認知而變得更加堅強,最後決定永遠放棄教職。和羅伯特諮商一年後,我才認清目前的學校環境無法實現我的理想。身為老師,我的首要義務是教導學生格物致知,我希望促使社會發生正面變化的真正目標,卻不屬於我的責任範圍。不過即使如此,我仍舊在教育界堅持了十五年,現在我興高采烈放棄了教職。激勵人心的創意
有天早晨,廣播報導了加拿大一座村莊的交換中心。當地一家幾乎養活全村人的工廠由於經營不善而破產,居民為了求生存,共同成立了一個交換中心,運作的模式聽起來非常簡單,而且顯然運作有效:每個人將自己的特殊才能存放在一個想像中的「罐子」裡,大家可以各自取用。根據「人人都擁有他人不會的才能」的中心思想,這裡提供了各式各樣的選項,有木工、園藝、砌牆、按摩、剪髮、烘焙、烹調食物、照顧小孩、修車等等,全都集中放進「罐子」裡。大家把自己能夠提供的服務登記在公共集會中心,但不同的是,這裡並不使用金錢支付報酬,而是將各自履行服務後所得的「債權」扣除掉各自的「債務」。
報導中舉了一個例子,清楚說明運作原則:有個人花了五個小時幫鄰居修車,將花費的時間登記下來,日後他若想翻修房子,就可找懂得貼壁紙或是裝地毯的人來幫忙,屆時他的「債權」就會縮減。原來那位鄰居因為修車而增加的「債務」,就靠幫其他村民帶小孩抵銷。
聽到這個方法,我腦筋頓時開了竅。除了不需要支出金錢即可解決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情之外,因應困難而生的模式忽然之間也變成實實在在的互助形式。加拿大當地居民以前時間都耗在單調的工廠勞動,現在則是貢獻在與其他村民的互動上。我十分亢奮,心想這真是一舉兩得。尋覓已久的解答就在眼前,這是一個實際與貧窮和孤立打交道的機會。
我口沫橫飛告訴朋友這個加拿大的嘗試,他們和我一樣喜歡這個不需要花錢就能解決困難的想法。不過,也有其他朋友反對,認為這點子要在人人彼此認識的小村莊才有辦法實踐,在大城市的可行性不高。或許他們說得有理,但是我並未因為此種懷疑態度,就打消成立交換中心的念頭。此外,我也知道引起大眾注意我的計畫是首要之務,於是我寫了一篇新聞稿,內容大致如下:「我們的社會在許多領域都嚴重失衡。例如仔細觀察勞動市場就會發現,為數不少的人負擔過重,筋疲力盡;另一方面,又有眾多失業者希望生活有點意義而痛苦煩惱。這兩種人都同樣不幸福,前者時間全花在工作上,沒有氣力進行其他活動,所以孤單寂寞;後者卻感覺自己沒有價值、沒有用處,沒人需要自己,顯得退縮畏怯。有個補救的方法是:時間多的人,將時間分享給沒有時間者,這對兩方都有助益。我利用業餘時間成立一個交換中心,彼此分享與交換才智、服務和有用之物,無需支付任何費用。透過這種方式,人人都可負擔,也能消弭貧富差異,達到社會互助的新形式。由於施與受的行為在現代受到了干擾與妨礙,因此我將這個中心命名為『施與受中心』。」
我拿著文章踏遍多特蒙的報社,引起廣泛的興趣,隔天我的計畫就刊登在各家報紙上,還附上了我的照片。
我在思索執行計畫的過程中,想起了在各城市行之有年的共乘中心,它的原則也是一樣的:不會開車或是不想開車的人,花最少的錢搭乘別人的車子,而駕駛人一來可以節省油錢,二來有人作伴聊天。而車子消耗同樣的汽油,不是只將一個人帶到目的地,而是兩個、三個,甚至四個,因此具有經濟效益又環保。共乘中心交易活絡,有些駕駛人純粹只是想找樂子,另些人則是想要有人分攤油錢。
總之,共乘中心和我的理念一樣,分享、互動、有效利用資源。共乘中心通行全德國,我想像「施與受中心」也能擴張到同樣規模。不過我不打算從中獲利,只希望拋磚引玉,推動此事順利進展,然後就退出,繼續尋找新的任務。但是事與願違。
「施與受中心」啟用
我的文章見諸報章後,許多有興趣的人紛紛上門報名。我為每個人建立專屬的索引卡片,特意避掉職業、年齡之類的個人訊息。我們不希望將人主觀分類,而是人人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與需求,來決定要提供的內容與希望收到的服務。但說的比做的還要簡單。第一批電話來自家庭主婦,她們把孩子拉拔大之後,多出了許多時間。不過她們對於付出的興趣大於接受,大部分希望照顧病人、關心別人,就像她們一輩子習以為常的模式。我建議她們也應該思考接受方面的事,不過她們都嫌麻煩。「接受」這種事情不存在她們的觀念中。但是我不輕易妥協,這些無所事事主婦的奉獻對我來說並不重要,要緊的是真正的交換,一種均衡的「施與受」關係。
於是我和這些有意願的主婦便圍繞著「志工」概念、對於不算職業也無法支薪的家務的不公平評價、婦女在職場中的艱困角色等等話題打轉,最後她們才勉勉強強在「接受」欄位填入選項,大部分不外乎手工或是園藝方面的工作。
由於我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說服主婦接受他人的服務,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其實我也預料到一般人會避免過度接受與索取,相較之下寧可付出。多年來,這始終是主要的問題,因為教會教導人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換句淺顯一點的話說,「接受」或者「索取」,意思有點接近偷竊或者搶奪,而顯然沒人願意與此扯上關係。
但是,我認為平等善用施與受這兩種觀念才是上策,唯有如此,交換的活動才能夠成立。因此,即使面臨種種使人挫折的問題,我仍舊保持著初心:想要加入的人,必須決定要付出以及其後接受的內容。這兩種需求全都登記在索引卡片上,一開始由我自己幫不同的客戶配對,但不久即發現這是項吃力不討好的任務。
由於尚未有人真正需要幫助,於是我先把生活經歷類似的人聚在一起。例如有兩位退休的婦女不約而同在電話中告訴我,自從先生過世後,她們覺得孤單寂寞,生活非常空虛,其中一位渴望能在週末時逛逛城市,但是不想獨自一人。幾天後,另一位也表達出類似的需求,於是我把對方的電話號碼各自給了兩位退休婦人,並請她們一旦互動成功後,務必通知我。兩個星期過去,我沒有接到她們任何消息,最後我打電話給其中一位,結果竟聽了火冒三丈的「顧客」一頓訓。原來她們在電話中就先吵了起來,對方一昧只想要教導她。她氣憤地說看來自己最好現在就退出這項計畫,「施與受中心」不是她要的。雖然我可以說服這位老太太留下來,但是她的反應確實讓我好好思索了一番。此種將素未謀面的人湊在一起的方式顯然不可行,有必要盡快讓「交換者」彼此認識。兩個月後,終於有了機會。我費了很大的勁在附近找到一棟等著整修的建築,隨時可供我們聚會使用,無需支付租金,只要我們幫忙收拾善後、分擔工作就行了。而這只要「施與受中心」十個人很快就能搞定。
交換中心成立之初,我固定在星期一下午六點到八點、星期四上午十點到十二點,以及星期五下午三點到五點接聽電話,後來又加上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二晚上八點到十點交換者的定期聚會。聚會後,才發現七十位會員之間的意見非常分歧。
再見了,我的家當
搬家對我而言是家常便飯,所以十分清楚有多辛苦、多麻煩。以前搬家時,我已逐步精簡自己的家當,數百本書早就送到別人手裡,目前只剩下幾本。我習慣把看完的書立刻送給別人。至於衣服,每買一件新衣,我就會送出一件舊的。因此我擁有的東西真的不多,但仍舊得好好思考怎麼處理其餘家當,尤其一想到客廳裡的大沙發,我即頭痛不已。我盯著大沙發陷入沉思,就在此時,門外樓梯間傳來腳步聲。隔壁的年輕人剛下班回家,我趕緊攔下他,問他想不想要沙發。他欣喜若狂,開心地把那個龐然大物拖到他屋裡,而我又少了一個煩惱。
我把床送給樓下的年輕女子,五斗櫃給隔壁另一位鄰居,餐桌和椅子流浪到一個朋友家裡,新地毯則轉讓給另一個朋友。如果我找不到有人需要幫忙看家,也有個女子把她多數時候總是空著的房子提供給我過渡期使用,所以我把貴重的青年風格(Jugendstil)書桌送給她,也算某種形式的預付租金。
我大概將十組人哄出我未來的前住所。他們來看看有沒有自己用得上的物品,然後總會瞪大眼睛問道:真的不需要付錢給我嗎?我把要淘汰的舊冰箱先推到走廊上,不到一天,就被一個收舊貨的藝術家發現,我滿心歡喜將冰箱送給他。我最後幾箱書給幾位大學生換來了喜悅。檯燈、畫、盆栽、唱片、CD、玻璃杯和其他奢侈品,也很快換了主人。能把東西送給真正需要的人,讓我打從心底感到開心。最後只剩下幾乎還是全新的衣櫃。有個朋友建議我把衣櫃放在她家,以防我未來也許還想擁有時,可以再搬走。我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留下了衣櫃,因為我可以把一些不想丟掉或送走的東西保存在裡面,例如私人證件、幾篇文章、兩本相簿,還有幾樣過冬的物品。正當我還在思索如何搬運這件笨重的家具時,電話忽然響了,有個熟人問要不要載我一程?我興高采烈接受她的驚喜提議。我最後一件家當就這樣慎重地搬了過去。
從此之後多年,這座衣櫃變得非常重要,它多少代表了家鄉或者自己的歸宿。每次我去看它時,也和借我放櫃子的朋友見見面,有時候我會留下來過夜,總是覺得賓至如歸。其實我也想放棄這最後一件家當,但是至今無法成功。那感覺就像長跑一樣:剛開始跑時游刃有餘,最後幾公尺卻難以克服。我很清楚自己根本不需要這個衣櫃了,但真要我處理掉,心裡卻還是會抗拒。
送掉其他東西,對我倒是輕而易舉,每清理一件物品,我心裡便歡呼道:又鏟掉一座山了!就連退掉房子時,預期應該出現的悲傷也不見蹤影,相較之下,我反而感到更富有了,因為我贏得了一座寶山:自由。以前我只在外出旅行時,才能感受得到自由。
我兩歲生日收到的禮物是一座娃娃屋,當年我一定欣喜若狂,因為我一邊大笑一邊拍著手在房間裡跳來跑去,雀躍的身影如今依舊歷歷在目。兩個哥哥、母親和保母艾拉也感染了我這個小小孩的喜悅,在一旁跟著開心。當時我們住在梅梅爾(Memel),父親在那兒有座咖啡烘焙廠―應該說曾經擁有過。
但我和我的小小玩具王國只共度了短短幾個月的幸福時光。一九四四年夏天,家裡隱隱浮動著一股不安,一開始我怎麼也想不透。先是放在閣樓地板上的心愛娃娃屋消失不見,接著屋子裡所有家具全蓋上了布,母親和祖母也整理行囊,準備出門。他們只帶上必要的行李,不斷彼此打氣,保證我們很快會回家。馬車備妥,等候出發。平常星期日時,我們偶爾駕著馬車出遊,度過快樂的時光。不過,這次的氣氛截然不同,母親淚流滿面,兩個哥哥也異常安靜。迥異於平日的是,街上擠滿了驅馬駕車的人潮。我們的馬車匯入隊伍裡,跟著往前走。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心裡十分害怕,哭了起來。母親無暇照應我,心思全放在我的小妹身上,當時她病入膏肓,不過仍從醫院接了回來。不到三歲的我又冷又餓,一心只想回家,想回去找我的絨毛玩偶,躺在溫暖的被窩裡。終於,母親注意到了我的絕望,輕聲對我說:「噓,小寶貝,情況會好轉的。」但是我覺得事情不會好轉,明天不會變好,過了一天也一樣。後來我們在某地低價賣掉馬車,改搭火車繼續前進。火車班班超載,車廂裡冷颼颼的,搭乘起來極不舒服。旅程勞累辛苦,而且不乏危險。火車只要一靠站,母親就迅速抓起一把大鍋子,到鐵軌兩旁的農舍乞討食物給我們四個孩子和祖母。母親每次飛奔出去,對我們就像是酷刑,不知道她能否及時趕回來。有一次母親果真還沒出現,火車就開動了,嚇得我們使盡吃奶的力氣放聲尖叫。至今我仍不清楚是我們絕望的叫聲停下了火車,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有好幾次,火車上的乘客全得盡速下車,躲到最近的樹底下尋求保護。下一秒,天空中即忽見戰鬥機密布,並且擊發砲彈轟炸火車,連人也不放過。我們的恐懼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攻擊行動逐漸膨脹,心裡明白有幾個同行的乘客倒臥在鐵軌旁,已經死去。有時候火車一停就是好幾個小時,無窮無盡,誰也不知道能否開動,又會在何時繼續前行。我們橫越了幾千公里,從東普魯士到南德,接著又往北走一段路,直到抵達阿勒爾河(Aller)畔的費爾登(Verden),旅程才算告一段落。當地的家庭聚集在火車站迎接我們,我這才明白原來我們是難民,而他們不管願意與否,都必須接納我們。許多人毫不掩飾自己的情緒,明顯表露出排拒的態度,因為要和因戰爭而流落至此的身無分文陌生人分享自己的一切,而感到憤恨不平。不過,幸好我們運氣很好,收容我們的農夫是個好人,他和妻子非常疼愛我們這些孩子,復活節時,我們還找了藏起來的彩蛋,而且好幾個星期都享用豐盛的食物,從未挨餓受凍。母親和祖母幫忙農夫做家事,這是在和睦氣氛中進行的交換與分享,施與受。在如此安樂的環境中,我幾乎忘了過去幾個月的痛苦。
但是戰爭仍未結束,媽媽終日掛心其他親戚,一得知他們後來到了石勒蘇益格―荷爾絲泰因邦(Schleswig-Holstein),說什麼也要到那兒去。善良的農夫力勸我們留下,但只是白費力氣。我們再次踏上旅程,最後雖然找到親戚,卻經歷了截然不同的施與受。有個農夫家庭滿心不樂意收容我們,嫌我們帶來麻煩。我們一家大小只能擠在一間小斗室,感覺自己像是多餘的累贅,而且生活窮困貧乏。待在這裡,我們又一次忍飢挨餓。戰爭後來終於結束,但我們永遠失去了以前那個家,再也回不去了。我們和其他逃難出來的人一樣,必須在新的環境中設法安頓自己,於是我們到田野中撿拾剩下的麥穗,也撿拾馬鈴薯,全家人還經常拿著籃子和水桶到森林裡採集莓果。
收容我們的農夫家庭不願意和我們分享食物,煮飯時,滿屋飄著飯菜香,擠在斗室裡的我們只能口水直流,可惜光是聞香也不能填飽肚子。母親後來在一處莊園找到了農務工作,才換來一點奶油和牛奶。除此之外,她還教附近幾個農家女兒彈鋼琴,酬勞是馬鈴薯、麵包、蛋和麵粉等寶貴的食物。有一天,父親從戰場上歸來,到北德來找我們,著手建立自己的家,我們才總算慢慢過起所謂的「正常」生活。只不過,過去幾年的經歷並非船過水無痕,仍舊對我造成了影響,我成了一個愛幻想的安靜小女孩。上小學後,我埋頭學習認字,認得了字後,眼前彷彿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的第一本書是本質地粗糙的厚重童話故事集,我時常帶著這個寶貝窩到我在樹籬中一手搭蓋出來的樹洞裡,和故事中的王子與公主待在屬於我們的小天地,全心全意沉浸在一個比現實生活公正與美好的世界。我在樹洞裡汲取力量,培養出自己對於生命可能樣貌的最初觀念,或者應該說,我認為生命應有的樣貌。我對於故事中邪惡必敗、愛贏得勝利的結局深為傾心。是的,我希望擁有這樣的世界。
然而我卻被迫經歷人射殺人、強取豪奪、衣食無虞者不願施捨一口食物給挨餓者的境況。為什麼我就得留下心愛的玩具,搭著寒冷的火車好幾個月跋涉千里,挨餓受凍,穿越屍橫遍地的地區?為什麼只因為我是難民小孩,就活該被罵成無賴?只因為我沒有真正的鞋子可穿,勉強湊合著木頭做成的鞋,就得受盡嘲笑?誰能明白這一切?還有,在這樣的世界裡,我失去了什麼?我至今依然認為童話有其象徵意義。我知道每個人都能貢獻一己之力,把地球變得更美好,更適合居住。當年在那個寂寞的童話樹洞裡,我想必早已預料到這一點。到現在,我眼前仍舊浮現那個哀傷的難民小女孩對自己許下的宏大承諾:「我要付出一切,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戰爭,人人活得有尊嚴。」
打開了一扇門
我的兒子轉學到文理高中後適應困難,出現焦慮與不安。儘管我再怎麼安慰他,「你不需要覺得害怕。」「我會陪著你。」也始終沒有效果。我不由得憂心忡忡。
進修教師培訓課程時,我認識了幾位心理系學生,向他們討教這個問題。他們請我帶著兒子到他們在漢堡的機構,進行遊戲治療。在治療過程中,孩子透過遊戲獲得他人的支持與理解,父母則和另一個人對話討論,試圖釐清孩子出現精神障礙的可能成因以及治療方式。由於整個過程也屬於心理系學生的進修課程,所以我們無需付費。我同意待在鑲著單向玻璃的房間裡進行討論,也就是說,教授和他的學生可以在單向玻璃的另一邊,全程追蹤與討論這件「施維姆案」。由於我看不見另一邊的他們,所以很容易忘記自己正被人觀察著。我和兒子連續好幾週到漢堡進行治療,而這個經驗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十七歲兒子雖然出現許多治療的可能,但是總體而言,當年的專業心理治療尚未發展成熟。在我們學校老師當中,我是第一個接觸這類事情的人。我兒子經過十次諮商逐漸找回重心後,我的世界卻第一次崩解了。
我哭了。我每個星期三下午去見談話對象羅伯特,講沒幾句話,眼淚就潰不成堤,一發不可收拾。然而那是解脫的淚水,所以每次諮商結束,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總是一身輕鬆,感覺淚水鬆脫了內在的阻礙,蓄滿新的能量。我學習將意識放在呼吸上,專注於一呼一吸之間,控制調息,就像調整自己的想法一樣。我從未想過自己對自己竟擁有如此的力量。
我之所以淚流滿面,與心中潛在的受害者角色有關,與始終伴著我(且壓迫我)的無助感有關。我逐漸明白自己並不只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始作俑者。我必須擺脫別人是壞人的想法,看清自己也是助紂為虐的幫凶。以前我當然察覺到我能保護自己,而且我的舉止粗野不雅時所產生的罪惡感也是其來有自,但是在治療前,我始終沒看出有機會能處理心中的罪惡感。
如今我大學時期學習的心理學理論終於派上用場,與現實接軌。諮商過程中驚喜不斷,到最後我明白了一件事:只要準備好,人人都可以改變自己。我想起心理學課堂上曾經教過的有名案例:兩個男嬰出生後沒多久,無意中被調換了,一個出身有教養的高貴家庭,另一個則來自賊窩。但是小男嬰長大後,竟發展出不適合各自成長環境的行為模式。由於現象異常,後來才發現抱錯了小孩。由此得出的明顯結論是:行為模式是先天遺傳,而非後天養成的,教育無法戰勝天性,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就是會打洞。
但是,果真如此嗎?這個問題長年困擾著我。現在,我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了答案:人人都有機會創造自己的生命,而非聽任命運擺布。我因為這個認知而變得更加堅強,最後決定永遠放棄教職。和羅伯特諮商一年後,我才認清目前的學校環境無法實現我的理想。身為老師,我的首要義務是教導學生格物致知,我希望促使社會發生正面變化的真正目標,卻不屬於我的責任範圍。不過即使如此,我仍舊在教育界堅持了十五年,現在我興高采烈放棄了教職。激勵人心的創意
有天早晨,廣播報導了加拿大一座村莊的交換中心。當地一家幾乎養活全村人的工廠由於經營不善而破產,居民為了求生存,共同成立了一個交換中心,運作的模式聽起來非常簡單,而且顯然運作有效:每個人將自己的特殊才能存放在一個想像中的「罐子」裡,大家可以各自取用。根據「人人都擁有他人不會的才能」的中心思想,這裡提供了各式各樣的選項,有木工、園藝、砌牆、按摩、剪髮、烘焙、烹調食物、照顧小孩、修車等等,全都集中放進「罐子」裡。大家把自己能夠提供的服務登記在公共集會中心,但不同的是,這裡並不使用金錢支付報酬,而是將各自履行服務後所得的「債權」扣除掉各自的「債務」。
報導中舉了一個例子,清楚說明運作原則:有個人花了五個小時幫鄰居修車,將花費的時間登記下來,日後他若想翻修房子,就可找懂得貼壁紙或是裝地毯的人來幫忙,屆時他的「債權」就會縮減。原來那位鄰居因為修車而增加的「債務」,就靠幫其他村民帶小孩抵銷。
聽到這個方法,我腦筋頓時開了竅。除了不需要支出金錢即可解決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情之外,因應困難而生的模式忽然之間也變成實實在在的互助形式。加拿大當地居民以前時間都耗在單調的工廠勞動,現在則是貢獻在與其他村民的互動上。我十分亢奮,心想這真是一舉兩得。尋覓已久的解答就在眼前,這是一個實際與貧窮和孤立打交道的機會。
我口沫橫飛告訴朋友這個加拿大的嘗試,他們和我一樣喜歡這個不需要花錢就能解決困難的想法。不過,也有其他朋友反對,認為這點子要在人人彼此認識的小村莊才有辦法實踐,在大城市的可行性不高。或許他們說得有理,但是我並未因為此種懷疑態度,就打消成立交換中心的念頭。此外,我也知道引起大眾注意我的計畫是首要之務,於是我寫了一篇新聞稿,內容大致如下:「我們的社會在許多領域都嚴重失衡。例如仔細觀察勞動市場就會發現,為數不少的人負擔過重,筋疲力盡;另一方面,又有眾多失業者希望生活有點意義而痛苦煩惱。這兩種人都同樣不幸福,前者時間全花在工作上,沒有氣力進行其他活動,所以孤單寂寞;後者卻感覺自己沒有價值、沒有用處,沒人需要自己,顯得退縮畏怯。有個補救的方法是:時間多的人,將時間分享給沒有時間者,這對兩方都有助益。我利用業餘時間成立一個交換中心,彼此分享與交換才智、服務和有用之物,無需支付任何費用。透過這種方式,人人都可負擔,也能消弭貧富差異,達到社會互助的新形式。由於施與受的行為在現代受到了干擾與妨礙,因此我將這個中心命名為『施與受中心』。」
我拿著文章踏遍多特蒙的報社,引起廣泛的興趣,隔天我的計畫就刊登在各家報紙上,還附上了我的照片。
我在思索執行計畫的過程中,想起了在各城市行之有年的共乘中心,它的原則也是一樣的:不會開車或是不想開車的人,花最少的錢搭乘別人的車子,而駕駛人一來可以節省油錢,二來有人作伴聊天。而車子消耗同樣的汽油,不是只將一個人帶到目的地,而是兩個、三個,甚至四個,因此具有經濟效益又環保。共乘中心交易活絡,有些駕駛人純粹只是想找樂子,另些人則是想要有人分攤油錢。
總之,共乘中心和我的理念一樣,分享、互動、有效利用資源。共乘中心通行全德國,我想像「施與受中心」也能擴張到同樣規模。不過我不打算從中獲利,只希望拋磚引玉,推動此事順利進展,然後就退出,繼續尋找新的任務。但是事與願違。
「施與受中心」啟用
我的文章見諸報章後,許多有興趣的人紛紛上門報名。我為每個人建立專屬的索引卡片,特意避掉職業、年齡之類的個人訊息。我們不希望將人主觀分類,而是人人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與需求,來決定要提供的內容與希望收到的服務。但說的比做的還要簡單。第一批電話來自家庭主婦,她們把孩子拉拔大之後,多出了許多時間。不過她們對於付出的興趣大於接受,大部分希望照顧病人、關心別人,就像她們一輩子習以為常的模式。我建議她們也應該思考接受方面的事,不過她們都嫌麻煩。「接受」這種事情不存在她們的觀念中。但是我不輕易妥協,這些無所事事主婦的奉獻對我來說並不重要,要緊的是真正的交換,一種均衡的「施與受」關係。
於是我和這些有意願的主婦便圍繞著「志工」概念、對於不算職業也無法支薪的家務的不公平評價、婦女在職場中的艱困角色等等話題打轉,最後她們才勉勉強強在「接受」欄位填入選項,大部分不外乎手工或是園藝方面的工作。
由於我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說服主婦接受他人的服務,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其實我也預料到一般人會避免過度接受與索取,相較之下寧可付出。多年來,這始終是主要的問題,因為教會教導人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換句淺顯一點的話說,「接受」或者「索取」,意思有點接近偷竊或者搶奪,而顯然沒人願意與此扯上關係。
但是,我認為平等善用施與受這兩種觀念才是上策,唯有如此,交換的活動才能夠成立。因此,即使面臨種種使人挫折的問題,我仍舊保持著初心:想要加入的人,必須決定要付出以及其後接受的內容。這兩種需求全都登記在索引卡片上,一開始由我自己幫不同的客戶配對,但不久即發現這是項吃力不討好的任務。
由於尚未有人真正需要幫助,於是我先把生活經歷類似的人聚在一起。例如有兩位退休的婦女不約而同在電話中告訴我,自從先生過世後,她們覺得孤單寂寞,生活非常空虛,其中一位渴望能在週末時逛逛城市,但是不想獨自一人。幾天後,另一位也表達出類似的需求,於是我把對方的電話號碼各自給了兩位退休婦人,並請她們一旦互動成功後,務必通知我。兩個星期過去,我沒有接到她們任何消息,最後我打電話給其中一位,結果竟聽了火冒三丈的「顧客」一頓訓。原來她們在電話中就先吵了起來,對方一昧只想要教導她。她氣憤地說看來自己最好現在就退出這項計畫,「施與受中心」不是她要的。雖然我可以說服這位老太太留下來,但是她的反應確實讓我好好思索了一番。此種將素未謀面的人湊在一起的方式顯然不可行,有必要盡快讓「交換者」彼此認識。兩個月後,終於有了機會。我費了很大的勁在附近找到一棟等著整修的建築,隨時可供我們聚會使用,無需支付租金,只要我們幫忙收拾善後、分擔工作就行了。而這只要「施與受中心」十個人很快就能搞定。
交換中心成立之初,我固定在星期一下午六點到八點、星期四上午十點到十二點,以及星期五下午三點到五點接聽電話,後來又加上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二晚上八點到十點交換者的定期聚會。聚會後,才發現七十位會員之間的意見非常分歧。
再見了,我的家當
搬家對我而言是家常便飯,所以十分清楚有多辛苦、多麻煩。以前搬家時,我已逐步精簡自己的家當,數百本書早就送到別人手裡,目前只剩下幾本。我習慣把看完的書立刻送給別人。至於衣服,每買一件新衣,我就會送出一件舊的。因此我擁有的東西真的不多,但仍舊得好好思考怎麼處理其餘家當,尤其一想到客廳裡的大沙發,我即頭痛不已。我盯著大沙發陷入沉思,就在此時,門外樓梯間傳來腳步聲。隔壁的年輕人剛下班回家,我趕緊攔下他,問他想不想要沙發。他欣喜若狂,開心地把那個龐然大物拖到他屋裡,而我又少了一個煩惱。
我把床送給樓下的年輕女子,五斗櫃給隔壁另一位鄰居,餐桌和椅子流浪到一個朋友家裡,新地毯則轉讓給另一個朋友。如果我找不到有人需要幫忙看家,也有個女子把她多數時候總是空著的房子提供給我過渡期使用,所以我把貴重的青年風格(Jugendstil)書桌送給她,也算某種形式的預付租金。
我大概將十組人哄出我未來的前住所。他們來看看有沒有自己用得上的物品,然後總會瞪大眼睛問道:真的不需要付錢給我嗎?我把要淘汰的舊冰箱先推到走廊上,不到一天,就被一個收舊貨的藝術家發現,我滿心歡喜將冰箱送給他。我最後幾箱書給幾位大學生換來了喜悅。檯燈、畫、盆栽、唱片、CD、玻璃杯和其他奢侈品,也很快換了主人。能把東西送給真正需要的人,讓我打從心底感到開心。最後只剩下幾乎還是全新的衣櫃。有個朋友建議我把衣櫃放在她家,以防我未來也許還想擁有時,可以再搬走。我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留下了衣櫃,因為我可以把一些不想丟掉或送走的東西保存在裡面,例如私人證件、幾篇文章、兩本相簿,還有幾樣過冬的物品。正當我還在思索如何搬運這件笨重的家具時,電話忽然響了,有個熟人問要不要載我一程?我興高采烈接受她的驚喜提議。我最後一件家當就這樣慎重地搬了過去。
從此之後多年,這座衣櫃變得非常重要,它多少代表了家鄉或者自己的歸宿。每次我去看它時,也和借我放櫃子的朋友見見面,有時候我會留下來過夜,總是覺得賓至如歸。其實我也想放棄這最後一件家當,但是至今無法成功。那感覺就像長跑一樣:剛開始跑時游刃有餘,最後幾公尺卻難以克服。我很清楚自己根本不需要這個衣櫃了,但真要我處理掉,心裡卻還是會抗拒。
送掉其他東西,對我倒是輕而易舉,每清理一件物品,我心裡便歡呼道:又鏟掉一座山了!就連退掉房子時,預期應該出現的悲傷也不見蹤影,相較之下,我反而感到更富有了,因為我贏得了一座寶山:自由。以前我只在外出旅行時,才能感受得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