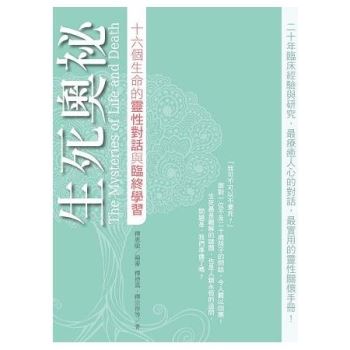3. 請問,要如何原諒?
真正的原諒,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然而,它也是維持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要素。
─ M.史考特.派克
他,非常激動,跪在床上,朝著巡房的醫療團隊一直拜,邊哭邊說:
「你救救我,救救我!我這輩子都沒做壞事,為什麼讓我得到這種病……」
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七十多歲的阿輝伯,有些戲劇化,但更多的卻是不忍!
※無法結合的愛,悲劇的開始
大家都聽到阿輝伯的求救,病房主任安撫說,「沒關係,沒關係,咱們慢慢來!」「我們病房有心理師、師父可以協助你,有什麼事跟師父說。」
我觀察眼前的景象,阿輝伯長得溫文儒雅,高高瘦瘦的!太太則長得圓圓壯壯的,就坐在病床旁,一腳放在椅子上,一腳踩地,不停的抖腳,冷眼旁觀眼前發生的一切,甚至斜視看著阿輝伯,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
走近一步,我發現病床底下有一片黃色黏稠的汙漬,異味撲鼻而來……是尿漬!
好一幅奇特的畫面!難道阿輝伯想上洗手間,阿輝嫂置之不理?臨床上,如果夫妻感情不和,往往會請別人照顧;可是,阿輝嫂卻一直守在旁邊,並未離開。
這對老夫妻究竟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慢慢接觸後,阿輝伯與阿輝嫂都特別喜歡與我單獨聊天。一個總是談昔日的美好戀情及豐功偉業;一個老是在抱怨罵人。我只是聆聽著,不做任何反駁或評論,試著拼湊兩人的生命歷程與交集處。
阿輝嫂談的都是阿輝伯,但不稱呼名字,而是叫「那個沒良心的」、「壞心的」、「膨肚短命」(台語,罵人的話),如何拋棄她和孩子,什麼難聽的話都能說出口,甚至咬牙切齒,最後總是悲從中來……
阿輝伯卻從來不談阿輝嫂,記憶中似乎沒有這個人的存在,他非常思念著與他無緣的日本女子,以及自己的風光事業,沉浸在昔日的美好回憶,一派紳士模樣……
阿輝伯與阿輝嫂彷彿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人,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而這一切要追溯到五十年前,牽涉三代的複雜情感。
阿輝嫂是養女,沒有地位,也未受教育;阿輝伯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外遇,外遇的對象就是阿輝嫂的養母。
阿輝伯是獨子,受良好教育,母親辛苦的把他養大,阿輝伯不負母親所望,和日本人合作養鰻魚,又有養雞廠,和許多大飯店往來,事業做得很成功。
阿輝伯和一位日本女孩交往並同居了六年,兩人非常相愛;可是,阿輝伯的母親得知日本女孩無法生育後,非常著急,心想沒有後代怎麼向祖先交代?
於是,阿輝伯的母親強烈反對兩人交往,極力拆散;阿輝伯非常愛這個日本女孩,不願意分開。最後,無計可施,母親只好跪求阿輝伯,「你不能娶她!」然後,把阿輝嫂硬塞給他,求他娶阿輝嫂。
孝順的阿輝伯只能答應母親了!日本女孩傷心的離開台灣,返回日本。
阿輝嫂從小就知道阿輝伯這個人,也十分仰慕阿輝伯,有機會嫁給他,求之不得,連作夢都會笑,滿是待嫁女兒心。
※沉默的抗議,不回家的人
結婚那一天,不明就裡的阿輝嫂高高興興當新娘子,渾然不知新郎的心情,更不知命運即將逆轉。新婚第二天開始,阿輝伯家裡一刻也待不住,天天在外過夜,對這樁沒有愛的婚姻投下強烈而沉默的抗議。
從此,阿輝伯一個女人換過一個女人,總在尋覓那位日本女孩的影子,卻怎麼也填不滿內心的空虛,心裡非常苦悶。
特別的是,阿輝伯難得回家,但只要回家一趟,隔年阿輝嫂便生下一個孩子,共生下五個孩子;不過,阿輝伯在外面的子女卻有六個,比家裡還多。
阿輝嫂記得有一次,阿輝伯難得回家,那天正好是民國四十八年的八七水災,水都淹過厝尾頂(屋頂),她身上背著孩子,手上又抱著孩子,根本忙不過來;離譜的是,她眼睜睜的看著阿輝伯匆忙跑出家門,想去照顧外面的孩子。
說到這裡,阿輝嫂氣到不行,一直罵,「沒良心啦!事業做那麼大,都不拿錢回家,都養外面的……」
我心想,如果沒拿錢回家,阿輝嫂又如何養大五個孩子呢?還有,總是流連在外的阿輝伯,最後又怎麼願意回歸家庭呢?
阿輝伯雖然在外有六個孩子,可是都沒往來,每一任外遇對象都帶著孩子離開;後來,阿輝伯被日本朋友騙了,公司倒閉,晚年落得又病又窮的窘境,被最後一個同居對象趕出來,流落街頭……
阿輝伯無處可去,只能打電話給元配阿輝嫂的女兒,女兒便帶他回家。回家後,阿輝伯一直覺得不舒服,檢查發現有一顆十多公分的腫瘤,已是癌末,無法治療了!
那麼,誰來照顧阿輝伯?自然就是阿輝嫂了!
身為元配的委屈,阿輝嫂甘願嗎?
※情未了,該如何原諒?
對阿輝嫂而言,失去半世紀的青春歲月,卻累積一身的怨,原諒談何容易!
縱使想原諒,也不知該如何原諒,錯綜複雜的情感非外人能懂吧?
於是,這樣的場景常常上演──
有一次,阿輝伯告訴我,他的牙齒掉光了,想做假牙。
阿輝嫂立刻說,「哼!人都要死了,做什麼假牙!」
還有每當阿輝伯來不及而尿在床上時,阿輝嫂就念,「我才不要管他,那是報應啦!」、「死好,報應啦,死好啦!」
又有一次,阿輝伯說身體發癢、一直抓癢時,女兒便拿藥膏幫阿輝伯擦藥,並對阿輝嫂說,「媽,您有空的時候,爸若很癢,幫他擦擦藥膏啦!」
阿輝嫂回答,「我才沒那麼衰小(台語,倒楣),我才不要摸他身體!」
甚至有時阿輝嫂要我不要理阿輝伯,「師父,不要理他,你都不知道他年輕時有多壞;所以,現在才會這樣啦,這是報應,大家都不要理他……」
阿輝嫂從年輕罵到老,孩子們從小聽到大,都聽得很厭煩了,乾脆回嘴,「如果他那麼壞,妳為何還要一直跟他生孩子……」
或許我是一個還不錯的聽眾,在我面前,阿輝嫂總是盡情的罵阿輝伯!有時重複罵,有時又會添加一些內容。當然,我不會讓阿輝伯知道。因為阿輝伯在我面前,表現出來的都是美好的一面,非常愛面子;我也不會讓阿輝嫂知道,阿輝伯究竟跟我說些什麼?
阿輝嫂一看到阿輝伯就是罵,沒有平靜的日子,阿輝伯其實不知道該如何和阿輝嫂說話。
阿輝伯真的那麼不好嗎?我試著瞭解其中的因緣。
「我年輕時的那個女朋友,身材很好,頭髮長長的,長得有夠漂亮,也很有氣質……」談起日本女友,阿輝伯眼眶含淚,都五十年了還忘不了。
「在日本,我黑白兩道都有朋友;他們說要來看我,都還沒來!還有,我要把錢要回來……」
阿輝伯的心事大概只能對我說吧!我細細聽著,他也特別喜歡跟我聊;逢例假日時,還一天數次的向護理站問我何時來?醫院有表演時,也要我坐在身旁,一起吃蛋糕、水果,待我比親生孩子還好。所以,每天早上,我常常泡一壺茶,和阿輝伯喝茶、聊過往。
其實,我一直等待著……終於有事情發生了!
有一天,阿輝嫂說她去問神明,並告訴我,「師父,我去萬應公那兒『搏杯』,萬應公說,他這一劫能過……」還說,「我聽人家說,喝茶會解藥效;師父,我看以後不要再泡茶給他喝了!」
原來,阿輝嫂還是很愛阿輝伯啊!
何況阿輝嫂天天來照顧阿輝伯,未請看護,不離不棄……一有動靜,馬上起來。阿輝伯心裡其實也清楚他對不起阿輝嫂,只是從小眼中的阿輝嫂像傭人般,比她優秀的優越感還在;所以,阿輝嫂罵人時,他也不吭聲。
※有愛就有希望,釋放恩怨情緒
有愛就有希望,加上兩人又非常信任我;於是,我有了下一波的照顧計畫,安排他們兩人第一次約會,希望他們能當面把內心話說出來,吵一架也好。
那一天傍晚五、六點,我推著阿輝伯的輪椅,並半推半拉著阿輝嫂,來到空中花園。就定位後,阿輝嫂插腰、眼睛斜視,一副心不甘情不願的模樣。
我先發言,「阿輝伯,根據這段期間的觀察,我覺得阿輝嫂很愛你,把你照顧得很好哦!」
這是故意說給阿輝嫂聽的,估計她一定會反駁,果不其然,阿輝嫂說話了,「哼!我衰小,誰在愛他?」
阿輝伯不說話,我問阿輝嫂為什麼倒楣?
「師父啊,你都不知道,那個人多沒良心,賺錢都不拿回家……」
我轉頭對阿輝伯說,「阿輝伯啊,我看你人很好也很有責任感,應該不像阿輝嫂說的那樣吧?不是那種人!」
「是啊,把我講成那樣,我沒那樣啦!」阿輝伯否認。
阿輝嫂一聽,氣得破口大罵,手指著阿輝伯,邊哭邊說,「你還敢說不是,從結婚到現在……你外面的女人一個換過一個,賺錢從來沒拿回來過……你還敢說……你讓你的孩子沒一個像樣的,你害孩子從小沒有父親……」
似乎講到真正痛處了,阿輝伯回神過來,「妳……妳,妳說什麼?」
「什麼是我讓妳的孩子沒父親?當初又是誰害我沒父親?如果不是妳養母搶走我父親,我小時候會過得那麼辛苦嗎?是妳害我沒父親,妳現在卻說我害妳那些孩子沒父親?」
阿輝伯發怒了,「那天要不是我媽媽跪著求我娶妳,我才不會娶妳呢!」「如果不是我媽媽跪著叫我娶妳,讓我和心愛的女朋友分開,今天我的人生也不會那麼落魄……」
這些話,阿輝伯隱忍了五十年,終於脫口而出;阿輝嫂一直以來總是懷疑的原因,今天也得到證實了。
阿輝嫂情緒非常激動,「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和我結婚,五十年來就是要報復,你一直在報復我……」她哭得肝腸寸斷。
積壓五十年的恩怨,兩人終於發洩出來,淚流不止……
※放下過去,道歉與原諒
不論阿輝嫂或阿輝伯,五十年來兩人都過得太辛苦了!
我安撫阿輝嫂,請她先坐下來,「師父知道妳五十年來的苦,沒有一個女人可以像妳這樣,還願意來照顧阿輝伯……」
我對阿輝伯說,「師父知道你對日本女友很專情,一直無法忘記,一直想找一個可以取代的人,卻找不到;可是,你又不想回家,實在很空虛。這也造成大家都誤會你很花心,風流又不負責任!師父相信你心裡也不願意這樣,你其實很痛苦,都沒人瞭解你的心情……對不對?」
聽到這裡,阿輝伯又哭了,一直點頭說「對」!阿輝伯五十年來心裡的無助、渴求、絕望終於有人理解了。
接著,我話題一轉,「但是,阿輝伯,我們說一句實在話,你人生走到這個階段,什麼人陪在你身邊把屎把尿的,你日本女朋友不可能回來,外面那些女人也不理你了,最後是誰跟在你身邊呢?」
「阿輝嫂每天從早到晚跟前跟後,你心裡難道都不懂嗎?今天如果她不關心你,根本不用理你。說真的,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這個樣子的。人家對你不離不棄,這樣守著你,是不是要跟人家說一聲……阿輝嫂對你真的很好啦!」我沒有直接要他道歉,只強調阿輝嫂對他好。
這時,阿輝伯說話了,「唉,師父,你不知道啦,一步錯,步步錯……」又說,「我不敢要求她百分之百原諒我啦,如果能原諒我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有一點點諒解,我就很滿足了!」
我轉向阿輝嫂說,「妳有聽到嗎?」
「我如果沒有原諒他,今天會在這裡嗎?」阿輝嫂回答。
我想,兩人的心結應該化解了,兩人也累了,便帶他們回病房。不過,他們之間似乎有些微妙的變化,兩人竟然有些靦腆,不好意思。阿輝嫂不再兇巴巴的,從沒見她這樣害羞過。
※接納過去,愛重來
離開後,那天晚上我沒睡好,心中掛念著昨天兩人情緒高漲,又正值冬天,阿輝伯的身體是否承受得住?
一大早,天未亮,我就到醫院,趕快去病房探視。病房燈未開,阿輝伯還在睡覺,阿輝嫂則坐在椅子上打盹,我想就近觀察阿輝伯的病情是否有變化?
我躡手躡腳的走近,房間太暗了,一不小心,扯掉了氧氣管,管子脫落,原本一片安靜的病房,突然發出很大的噴氣聲響「嘁……」
當下,只見阿輝嫂動作迅速的從椅子上跳下來,「輝仔,輝仔,你有沒有怎樣,你有沒有怎樣……」把阿輝伯從頭到腳摸一遍,一直問,「有沒有怎樣?」
「沒啦,沒有怎樣,我還沒死啦!」阿輝伯幽默的說。
這時,我把燈打開,只見阿輝嫂滿臉通紅!
阿輝伯看見我便說,「師父,我跟你說哦,我要去做假牙了!」
昨天回到病房後,一定發生了什麼事,一切都轉變了?
說著說著,阿輝伯的女兒提著早餐進來,她說,「師父,昨天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爸媽怎麼那麼高興,我爸還跟我說:哦,把心裡話說出來,整個人很快活!」女兒一時還搞不清楚爸媽怎麼一下子變得那麼祥和,甚至可用恩愛形容!
經過那次的約會後,阿輝伯得到更好的照顧。阿輝嫂不再冷言冷語,只要阿輝伯需要,她就會幫忙,連床下地板都乾乾淨淨的,不再有黏稠汙漬及怪味道。
在和阿輝伯喝茶聊天的過程中,阿輝伯會主動問我,「師父,你們佛教都在講什麼?」不再有第一次見面那樣的言語出現了,他已慢慢接受自己的病情,接受我的宗教,並慢慢瞭解佛教的一些道理,及阿彌陀佛的意思,慢慢知道他以後該去的國度。
事實上,我也不斷肯定他的人生,因為從來沒人瞭解過他,況且最後家庭也包容他、接納他;所以,他覺得滿足了,對人生也滿意了。
由於病情控制得不錯,阿輝伯出院了。
遺憾的是,在我還沒來得及去他家裡探視,沒多久,阿輝伯就往生了。
※悠悠人生,歲月靜好
阿輝伯往生後,阿輝嫂回來找我,告訴我回家後那段時間的情況。
阿輝伯回家後,很平靜,想到師父時就開始念佛,他總說,「以後我要去師父佛祖的家!」阿輝嫂就跟著一起念佛、用功。
不過,阿輝伯曾感性的對阿輝嫂說,「這輩子很抱歉,下輩子再還妳。」
阿輝嫂問說,「你下輩子要還我?」
聽到這樣的問話,阿輝伯立刻改口說,「不是啦,不是啦,下輩子不要再來這裡(人間)啦,我要去師父佛祖的家。」
「如果這樣,你就要念佛哦!」阿輝嫂鼓勵他。
阿輝伯其實對我的感情比阿彌陀佛還深,我對他說,「千萬不要跟著師父,要去阿彌陀佛那兒!」所以,阿輝伯就說,「要去師父他佛祖的家。」
往生前幾天,阿輝伯交代,「我一輩子都是有頭有臉的人,我死的時候,要幫我穿上那套西裝,帶上我那一只勞力士手錶;西裝的袖子要弄好,不要擋到手錶。我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師父他佛祖的家報到。」
我想像著阿輝嫂陪伴阿輝伯念佛的情景,兩人終能攜手走過人生,歲月靜好……
【靈性照顧point】
關係和解──原諒別人,也原諒自己
人與人之間,因緣聚合,產生了關係,不論是親情、愛情、友情……當關係出現裂痕,如果沒有在當下或日後適時化解、療癒,終將形成未知的風暴,可能在生命的最後造成干擾。
從靈性照顧的觀點來說,臨終前,就如《心經》所說:「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不論是對生的依戀而怕死,或對得而失去的不捨,或對關係的愛恨糾葛而放不下……都是一種罣礙;若要沒有罣礙,就要回頭看看自己的人生,如讓你過不去的關係,趁還能溝通時儘快處理。
關係和解,包括與他人的和解,以及常被忽略的──與自己和解。
與他人的關係和解,要評估彼此之間有沒有和解的因子存在,是否有連結的共通點;也要考量靈性照顧者或執行的人,和兩人是否建立起信任感了,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準備?因為要把陳年糾葛的心結打開,往往如同揭瘡疤一般,會有陣痛,需要時間走過。
例如,案例中的阿輝伯與阿輝嫂,因為對宗教師有足夠的信任,加上阿輝伯心存虧欠,阿輝嫂還有愛;不然,夫妻兩人無從和解,更不必談要放下半世紀的恩怨情仇。
在過程中,雙方可能會各說各話,或數落對方的不是,或抱怨,或憤恨不平,容易負面看待對方。靈性照顧者的原則是,不評判、不批判,同理他們的苦,同理他們的感受,接納他們,扮演溝通橋梁的角色,要評估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會傷害對方的話就到照顧者為止,但有利雙方和諧的則要適時傳達,讓他們都能看到對方的優點,並可進一步適時提點,讓他們主動察覺,「哦,我這樣子好像也有不對的地方!」
在臨床上,我們發現佛教徒容易忽視關係的和解,為什麼?因為有的人認為,一切皆空,不應該計較,現在都什麼時候了,還想這個做什麼,不要執著,要超越;所以,直接念佛祝福對方就好了,然後要放下,要歡喜、要感恩哦!
問題是,心結未解,要放下談何容易?無法放下,該如何歡喜、感恩呢?
有一個很典型的案例,一位男性病人住進安寧病房,太太和女兒是虔誠的佛教徒,都希望他念佛。然而,病人說,「妳們自己去妳們的極樂世界吧!不要叫我念佛,不要跟我講那一套,我不想聽。」因為太太和女兒都覺得病人沒有善根,總是要求他念佛、學佛;可是,病人根本無法接受母女倆的方式,彼此的距離就愈來愈遠。即使病人已經臨終快要往生,太太和女兒仍然覺得都是因為病人沒善根。
學佛不是用來檢視別人或要求別人的,而是要修正自己的行為,檢視自己是否學習到佛的精神,心中是否有真正的愛與慈悲。
我們也碰過這樣的案例,有一位病人的女兒出家,病人很不諒解,十年來都不跟女兒講話;即使病人住進安寧病房,出家的女兒去探視,病人還是很生氣。女兒非常挫折、無助。
後來,一位宗教師對病人說,「阿伯,您知道念佛是什麼意思嗎?念佛就是放輕鬆!」阿伯驚訝的回答,「哦,原來念佛就是要放輕鬆,這樣我要念,我可以念!」
因為病人發現,念佛和他的身心有關,對他當下有幫助,而不是一念佛就要他去極樂世界。就這樣,宗教師當溝通橋梁,病人和出家的女兒距離開始慢慢拉近,出家的女兒很感謝宗教師,不然他十年的佛法修習,得不到臨終父親的不原諒,會是一生的遺憾。
這關鍵在於,有些人學佛,似乎另闢一條蹊徑,存在於現實之外,無法運用在生活周遭的人事,甚至出現一種莫名的優越感,柔軟心不見了;於是,和家人愈離愈遠。
關係的和解,最困難的其實是與自己和解。
我們看到很多病人往往認為自己不夠好,或沒有價值,甚至沒有用,不論別人怎麼肯定他,就是無法肯定自己;或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無法原諒自己,卻還是渴望愛……總和自己的內在產生衝突與矛盾。
有一位病人,生了四個兒子,年輕就守寡,還要照顧癱瘓的婆婆;更糟的是,一個兒子車禍往生,一個智能不足,一個罹患小兒麻痺,最正常的兒子結婚後,生下一個腦性麻痹的孩子。病人最後則罹患癌症。
她認為,「像我這麼歹命的人,死了一定會去陰曹地府受苦!我不甘願,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親朋鄰里則說,她家可能祖墳有問題,或可能被人詛咒,或祖先得罪人了。
在生命回顧時,我們問,「在當時的背景之下,妳沒有尋求或申請社會福利補助?」她說,「既然把孩子生下來,再怎麼艱苦,也要把孩子撫養長大,每個孩子都是我心頭上的一塊肉,我都不能放棄,也不能推卸責任!」
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母親啊!有多少人可以這麼堅強走過來?我們肯定她,「妳怎麼有辦法一個人扛起這麼大的擔子,真是不簡單……令人讚歎啊!所以,陰曹地府大概去不成了……」
第一次聽到有人肯定她、讚歎她,何況是出家法師說她好,彷彿佛菩薩加持,一切都被原諒、被寬恕了。最後病人無罣礙的離開了。
在關係和解中,生命回顧可說是最好的方式,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歷史的蛛絲馬跡,找到可以肯定的切入點,因為病人本身看不到。而與自己和解,首先要打開心門;如果自己不想走出幽暗的過去,任誰也無法可施。
臨終其實是一個很適合的場域,提供了我們以比較開闊的格局理解生命的機會,順著身體的變化,感知生命的無常,體悟生命的真理。如果接受了,就平安;不接受,就不平安。這時候,靈性照顧者也比較容易隨著這樣的自然趨勢,導引病人看見自己的生命脈絡,看見關係背後的信息,得以修補關係,原諒別人,也原諒自己。
真正的原諒,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然而,它也是維持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要素。
─ M.史考特.派克
他,非常激動,跪在床上,朝著巡房的醫療團隊一直拜,邊哭邊說:
「你救救我,救救我!我這輩子都沒做壞事,為什麼讓我得到這種病……」
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七十多歲的阿輝伯,有些戲劇化,但更多的卻是不忍!
※無法結合的愛,悲劇的開始
大家都聽到阿輝伯的求救,病房主任安撫說,「沒關係,沒關係,咱們慢慢來!」「我們病房有心理師、師父可以協助你,有什麼事跟師父說。」
我觀察眼前的景象,阿輝伯長得溫文儒雅,高高瘦瘦的!太太則長得圓圓壯壯的,就坐在病床旁,一腳放在椅子上,一腳踩地,不停的抖腳,冷眼旁觀眼前發生的一切,甚至斜視看著阿輝伯,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
走近一步,我發現病床底下有一片黃色黏稠的汙漬,異味撲鼻而來……是尿漬!
好一幅奇特的畫面!難道阿輝伯想上洗手間,阿輝嫂置之不理?臨床上,如果夫妻感情不和,往往會請別人照顧;可是,阿輝嫂卻一直守在旁邊,並未離開。
這對老夫妻究竟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慢慢接觸後,阿輝伯與阿輝嫂都特別喜歡與我單獨聊天。一個總是談昔日的美好戀情及豐功偉業;一個老是在抱怨罵人。我只是聆聽著,不做任何反駁或評論,試著拼湊兩人的生命歷程與交集處。
阿輝嫂談的都是阿輝伯,但不稱呼名字,而是叫「那個沒良心的」、「壞心的」、「膨肚短命」(台語,罵人的話),如何拋棄她和孩子,什麼難聽的話都能說出口,甚至咬牙切齒,最後總是悲從中來……
阿輝伯卻從來不談阿輝嫂,記憶中似乎沒有這個人的存在,他非常思念著與他無緣的日本女子,以及自己的風光事業,沉浸在昔日的美好回憶,一派紳士模樣……
阿輝伯與阿輝嫂彷彿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人,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而這一切要追溯到五十年前,牽涉三代的複雜情感。
阿輝嫂是養女,沒有地位,也未受教育;阿輝伯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外遇,外遇的對象就是阿輝嫂的養母。
阿輝伯是獨子,受良好教育,母親辛苦的把他養大,阿輝伯不負母親所望,和日本人合作養鰻魚,又有養雞廠,和許多大飯店往來,事業做得很成功。
阿輝伯和一位日本女孩交往並同居了六年,兩人非常相愛;可是,阿輝伯的母親得知日本女孩無法生育後,非常著急,心想沒有後代怎麼向祖先交代?
於是,阿輝伯的母親強烈反對兩人交往,極力拆散;阿輝伯非常愛這個日本女孩,不願意分開。最後,無計可施,母親只好跪求阿輝伯,「你不能娶她!」然後,把阿輝嫂硬塞給他,求他娶阿輝嫂。
孝順的阿輝伯只能答應母親了!日本女孩傷心的離開台灣,返回日本。
阿輝嫂從小就知道阿輝伯這個人,也十分仰慕阿輝伯,有機會嫁給他,求之不得,連作夢都會笑,滿是待嫁女兒心。
※沉默的抗議,不回家的人
結婚那一天,不明就裡的阿輝嫂高高興興當新娘子,渾然不知新郎的心情,更不知命運即將逆轉。新婚第二天開始,阿輝伯家裡一刻也待不住,天天在外過夜,對這樁沒有愛的婚姻投下強烈而沉默的抗議。
從此,阿輝伯一個女人換過一個女人,總在尋覓那位日本女孩的影子,卻怎麼也填不滿內心的空虛,心裡非常苦悶。
特別的是,阿輝伯難得回家,但只要回家一趟,隔年阿輝嫂便生下一個孩子,共生下五個孩子;不過,阿輝伯在外面的子女卻有六個,比家裡還多。
阿輝嫂記得有一次,阿輝伯難得回家,那天正好是民國四十八年的八七水災,水都淹過厝尾頂(屋頂),她身上背著孩子,手上又抱著孩子,根本忙不過來;離譜的是,她眼睜睜的看著阿輝伯匆忙跑出家門,想去照顧外面的孩子。
說到這裡,阿輝嫂氣到不行,一直罵,「沒良心啦!事業做那麼大,都不拿錢回家,都養外面的……」
我心想,如果沒拿錢回家,阿輝嫂又如何養大五個孩子呢?還有,總是流連在外的阿輝伯,最後又怎麼願意回歸家庭呢?
阿輝伯雖然在外有六個孩子,可是都沒往來,每一任外遇對象都帶著孩子離開;後來,阿輝伯被日本朋友騙了,公司倒閉,晚年落得又病又窮的窘境,被最後一個同居對象趕出來,流落街頭……
阿輝伯無處可去,只能打電話給元配阿輝嫂的女兒,女兒便帶他回家。回家後,阿輝伯一直覺得不舒服,檢查發現有一顆十多公分的腫瘤,已是癌末,無法治療了!
那麼,誰來照顧阿輝伯?自然就是阿輝嫂了!
身為元配的委屈,阿輝嫂甘願嗎?
※情未了,該如何原諒?
對阿輝嫂而言,失去半世紀的青春歲月,卻累積一身的怨,原諒談何容易!
縱使想原諒,也不知該如何原諒,錯綜複雜的情感非外人能懂吧?
於是,這樣的場景常常上演──
有一次,阿輝伯告訴我,他的牙齒掉光了,想做假牙。
阿輝嫂立刻說,「哼!人都要死了,做什麼假牙!」
還有每當阿輝伯來不及而尿在床上時,阿輝嫂就念,「我才不要管他,那是報應啦!」、「死好,報應啦,死好啦!」
又有一次,阿輝伯說身體發癢、一直抓癢時,女兒便拿藥膏幫阿輝伯擦藥,並對阿輝嫂說,「媽,您有空的時候,爸若很癢,幫他擦擦藥膏啦!」
阿輝嫂回答,「我才沒那麼衰小(台語,倒楣),我才不要摸他身體!」
甚至有時阿輝嫂要我不要理阿輝伯,「師父,不要理他,你都不知道他年輕時有多壞;所以,現在才會這樣啦,這是報應,大家都不要理他……」
阿輝嫂從年輕罵到老,孩子們從小聽到大,都聽得很厭煩了,乾脆回嘴,「如果他那麼壞,妳為何還要一直跟他生孩子……」
或許我是一個還不錯的聽眾,在我面前,阿輝嫂總是盡情的罵阿輝伯!有時重複罵,有時又會添加一些內容。當然,我不會讓阿輝伯知道。因為阿輝伯在我面前,表現出來的都是美好的一面,非常愛面子;我也不會讓阿輝嫂知道,阿輝伯究竟跟我說些什麼?
阿輝嫂一看到阿輝伯就是罵,沒有平靜的日子,阿輝伯其實不知道該如何和阿輝嫂說話。
阿輝伯真的那麼不好嗎?我試著瞭解其中的因緣。
「我年輕時的那個女朋友,身材很好,頭髮長長的,長得有夠漂亮,也很有氣質……」談起日本女友,阿輝伯眼眶含淚,都五十年了還忘不了。
「在日本,我黑白兩道都有朋友;他們說要來看我,都還沒來!還有,我要把錢要回來……」
阿輝伯的心事大概只能對我說吧!我細細聽著,他也特別喜歡跟我聊;逢例假日時,還一天數次的向護理站問我何時來?醫院有表演時,也要我坐在身旁,一起吃蛋糕、水果,待我比親生孩子還好。所以,每天早上,我常常泡一壺茶,和阿輝伯喝茶、聊過往。
其實,我一直等待著……終於有事情發生了!
有一天,阿輝嫂說她去問神明,並告訴我,「師父,我去萬應公那兒『搏杯』,萬應公說,他這一劫能過……」還說,「我聽人家說,喝茶會解藥效;師父,我看以後不要再泡茶給他喝了!」
原來,阿輝嫂還是很愛阿輝伯啊!
何況阿輝嫂天天來照顧阿輝伯,未請看護,不離不棄……一有動靜,馬上起來。阿輝伯心裡其實也清楚他對不起阿輝嫂,只是從小眼中的阿輝嫂像傭人般,比她優秀的優越感還在;所以,阿輝嫂罵人時,他也不吭聲。
※有愛就有希望,釋放恩怨情緒
有愛就有希望,加上兩人又非常信任我;於是,我有了下一波的照顧計畫,安排他們兩人第一次約會,希望他們能當面把內心話說出來,吵一架也好。
那一天傍晚五、六點,我推著阿輝伯的輪椅,並半推半拉著阿輝嫂,來到空中花園。就定位後,阿輝嫂插腰、眼睛斜視,一副心不甘情不願的模樣。
我先發言,「阿輝伯,根據這段期間的觀察,我覺得阿輝嫂很愛你,把你照顧得很好哦!」
這是故意說給阿輝嫂聽的,估計她一定會反駁,果不其然,阿輝嫂說話了,「哼!我衰小,誰在愛他?」
阿輝伯不說話,我問阿輝嫂為什麼倒楣?
「師父啊,你都不知道,那個人多沒良心,賺錢都不拿回家……」
我轉頭對阿輝伯說,「阿輝伯啊,我看你人很好也很有責任感,應該不像阿輝嫂說的那樣吧?不是那種人!」
「是啊,把我講成那樣,我沒那樣啦!」阿輝伯否認。
阿輝嫂一聽,氣得破口大罵,手指著阿輝伯,邊哭邊說,「你還敢說不是,從結婚到現在……你外面的女人一個換過一個,賺錢從來沒拿回來過……你還敢說……你讓你的孩子沒一個像樣的,你害孩子從小沒有父親……」
似乎講到真正痛處了,阿輝伯回神過來,「妳……妳,妳說什麼?」
「什麼是我讓妳的孩子沒父親?當初又是誰害我沒父親?如果不是妳養母搶走我父親,我小時候會過得那麼辛苦嗎?是妳害我沒父親,妳現在卻說我害妳那些孩子沒父親?」
阿輝伯發怒了,「那天要不是我媽媽跪著求我娶妳,我才不會娶妳呢!」「如果不是我媽媽跪著叫我娶妳,讓我和心愛的女朋友分開,今天我的人生也不會那麼落魄……」
這些話,阿輝伯隱忍了五十年,終於脫口而出;阿輝嫂一直以來總是懷疑的原因,今天也得到證實了。
阿輝嫂情緒非常激動,「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和我結婚,五十年來就是要報復,你一直在報復我……」她哭得肝腸寸斷。
積壓五十年的恩怨,兩人終於發洩出來,淚流不止……
※放下過去,道歉與原諒
不論阿輝嫂或阿輝伯,五十年來兩人都過得太辛苦了!
我安撫阿輝嫂,請她先坐下來,「師父知道妳五十年來的苦,沒有一個女人可以像妳這樣,還願意來照顧阿輝伯……」
我對阿輝伯說,「師父知道你對日本女友很專情,一直無法忘記,一直想找一個可以取代的人,卻找不到;可是,你又不想回家,實在很空虛。這也造成大家都誤會你很花心,風流又不負責任!師父相信你心裡也不願意這樣,你其實很痛苦,都沒人瞭解你的心情……對不對?」
聽到這裡,阿輝伯又哭了,一直點頭說「對」!阿輝伯五十年來心裡的無助、渴求、絕望終於有人理解了。
接著,我話題一轉,「但是,阿輝伯,我們說一句實在話,你人生走到這個階段,什麼人陪在你身邊把屎把尿的,你日本女朋友不可能回來,外面那些女人也不理你了,最後是誰跟在你身邊呢?」
「阿輝嫂每天從早到晚跟前跟後,你心裡難道都不懂嗎?今天如果她不關心你,根本不用理你。說真的,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這個樣子的。人家對你不離不棄,這樣守著你,是不是要跟人家說一聲……阿輝嫂對你真的很好啦!」我沒有直接要他道歉,只強調阿輝嫂對他好。
這時,阿輝伯說話了,「唉,師父,你不知道啦,一步錯,步步錯……」又說,「我不敢要求她百分之百原諒我啦,如果能原諒我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有一點點諒解,我就很滿足了!」
我轉向阿輝嫂說,「妳有聽到嗎?」
「我如果沒有原諒他,今天會在這裡嗎?」阿輝嫂回答。
我想,兩人的心結應該化解了,兩人也累了,便帶他們回病房。不過,他們之間似乎有些微妙的變化,兩人竟然有些靦腆,不好意思。阿輝嫂不再兇巴巴的,從沒見她這樣害羞過。
※接納過去,愛重來
離開後,那天晚上我沒睡好,心中掛念著昨天兩人情緒高漲,又正值冬天,阿輝伯的身體是否承受得住?
一大早,天未亮,我就到醫院,趕快去病房探視。病房燈未開,阿輝伯還在睡覺,阿輝嫂則坐在椅子上打盹,我想就近觀察阿輝伯的病情是否有變化?
我躡手躡腳的走近,房間太暗了,一不小心,扯掉了氧氣管,管子脫落,原本一片安靜的病房,突然發出很大的噴氣聲響「嘁……」
當下,只見阿輝嫂動作迅速的從椅子上跳下來,「輝仔,輝仔,你有沒有怎樣,你有沒有怎樣……」把阿輝伯從頭到腳摸一遍,一直問,「有沒有怎樣?」
「沒啦,沒有怎樣,我還沒死啦!」阿輝伯幽默的說。
這時,我把燈打開,只見阿輝嫂滿臉通紅!
阿輝伯看見我便說,「師父,我跟你說哦,我要去做假牙了!」
昨天回到病房後,一定發生了什麼事,一切都轉變了?
說著說著,阿輝伯的女兒提著早餐進來,她說,「師父,昨天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爸媽怎麼那麼高興,我爸還跟我說:哦,把心裡話說出來,整個人很快活!」女兒一時還搞不清楚爸媽怎麼一下子變得那麼祥和,甚至可用恩愛形容!
經過那次的約會後,阿輝伯得到更好的照顧。阿輝嫂不再冷言冷語,只要阿輝伯需要,她就會幫忙,連床下地板都乾乾淨淨的,不再有黏稠汙漬及怪味道。
在和阿輝伯喝茶聊天的過程中,阿輝伯會主動問我,「師父,你們佛教都在講什麼?」不再有第一次見面那樣的言語出現了,他已慢慢接受自己的病情,接受我的宗教,並慢慢瞭解佛教的一些道理,及阿彌陀佛的意思,慢慢知道他以後該去的國度。
事實上,我也不斷肯定他的人生,因為從來沒人瞭解過他,況且最後家庭也包容他、接納他;所以,他覺得滿足了,對人生也滿意了。
由於病情控制得不錯,阿輝伯出院了。
遺憾的是,在我還沒來得及去他家裡探視,沒多久,阿輝伯就往生了。
※悠悠人生,歲月靜好
阿輝伯往生後,阿輝嫂回來找我,告訴我回家後那段時間的情況。
阿輝伯回家後,很平靜,想到師父時就開始念佛,他總說,「以後我要去師父佛祖的家!」阿輝嫂就跟著一起念佛、用功。
不過,阿輝伯曾感性的對阿輝嫂說,「這輩子很抱歉,下輩子再還妳。」
阿輝嫂問說,「你下輩子要還我?」
聽到這樣的問話,阿輝伯立刻改口說,「不是啦,不是啦,下輩子不要再來這裡(人間)啦,我要去師父佛祖的家。」
「如果這樣,你就要念佛哦!」阿輝嫂鼓勵他。
阿輝伯其實對我的感情比阿彌陀佛還深,我對他說,「千萬不要跟著師父,要去阿彌陀佛那兒!」所以,阿輝伯就說,「要去師父他佛祖的家。」
往生前幾天,阿輝伯交代,「我一輩子都是有頭有臉的人,我死的時候,要幫我穿上那套西裝,帶上我那一只勞力士手錶;西裝的袖子要弄好,不要擋到手錶。我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師父他佛祖的家報到。」
我想像著阿輝嫂陪伴阿輝伯念佛的情景,兩人終能攜手走過人生,歲月靜好……
【靈性照顧point】
關係和解──原諒別人,也原諒自己
人與人之間,因緣聚合,產生了關係,不論是親情、愛情、友情……當關係出現裂痕,如果沒有在當下或日後適時化解、療癒,終將形成未知的風暴,可能在生命的最後造成干擾。
從靈性照顧的觀點來說,臨終前,就如《心經》所說:「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不論是對生的依戀而怕死,或對得而失去的不捨,或對關係的愛恨糾葛而放不下……都是一種罣礙;若要沒有罣礙,就要回頭看看自己的人生,如讓你過不去的關係,趁還能溝通時儘快處理。
關係和解,包括與他人的和解,以及常被忽略的──與自己和解。
與他人的關係和解,要評估彼此之間有沒有和解的因子存在,是否有連結的共通點;也要考量靈性照顧者或執行的人,和兩人是否建立起信任感了,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準備?因為要把陳年糾葛的心結打開,往往如同揭瘡疤一般,會有陣痛,需要時間走過。
例如,案例中的阿輝伯與阿輝嫂,因為對宗教師有足夠的信任,加上阿輝伯心存虧欠,阿輝嫂還有愛;不然,夫妻兩人無從和解,更不必談要放下半世紀的恩怨情仇。
在過程中,雙方可能會各說各話,或數落對方的不是,或抱怨,或憤恨不平,容易負面看待對方。靈性照顧者的原則是,不評判、不批判,同理他們的苦,同理他們的感受,接納他們,扮演溝通橋梁的角色,要評估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會傷害對方的話就到照顧者為止,但有利雙方和諧的則要適時傳達,讓他們都能看到對方的優點,並可進一步適時提點,讓他們主動察覺,「哦,我這樣子好像也有不對的地方!」
在臨床上,我們發現佛教徒容易忽視關係的和解,為什麼?因為有的人認為,一切皆空,不應該計較,現在都什麼時候了,還想這個做什麼,不要執著,要超越;所以,直接念佛祝福對方就好了,然後要放下,要歡喜、要感恩哦!
問題是,心結未解,要放下談何容易?無法放下,該如何歡喜、感恩呢?
有一個很典型的案例,一位男性病人住進安寧病房,太太和女兒是虔誠的佛教徒,都希望他念佛。然而,病人說,「妳們自己去妳們的極樂世界吧!不要叫我念佛,不要跟我講那一套,我不想聽。」因為太太和女兒都覺得病人沒有善根,總是要求他念佛、學佛;可是,病人根本無法接受母女倆的方式,彼此的距離就愈來愈遠。即使病人已經臨終快要往生,太太和女兒仍然覺得都是因為病人沒善根。
學佛不是用來檢視別人或要求別人的,而是要修正自己的行為,檢視自己是否學習到佛的精神,心中是否有真正的愛與慈悲。
我們也碰過這樣的案例,有一位病人的女兒出家,病人很不諒解,十年來都不跟女兒講話;即使病人住進安寧病房,出家的女兒去探視,病人還是很生氣。女兒非常挫折、無助。
後來,一位宗教師對病人說,「阿伯,您知道念佛是什麼意思嗎?念佛就是放輕鬆!」阿伯驚訝的回答,「哦,原來念佛就是要放輕鬆,這樣我要念,我可以念!」
因為病人發現,念佛和他的身心有關,對他當下有幫助,而不是一念佛就要他去極樂世界。就這樣,宗教師當溝通橋梁,病人和出家的女兒距離開始慢慢拉近,出家的女兒很感謝宗教師,不然他十年的佛法修習,得不到臨終父親的不原諒,會是一生的遺憾。
這關鍵在於,有些人學佛,似乎另闢一條蹊徑,存在於現實之外,無法運用在生活周遭的人事,甚至出現一種莫名的優越感,柔軟心不見了;於是,和家人愈離愈遠。
關係的和解,最困難的其實是與自己和解。
我們看到很多病人往往認為自己不夠好,或沒有價值,甚至沒有用,不論別人怎麼肯定他,就是無法肯定自己;或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無法原諒自己,卻還是渴望愛……總和自己的內在產生衝突與矛盾。
有一位病人,生了四個兒子,年輕就守寡,還要照顧癱瘓的婆婆;更糟的是,一個兒子車禍往生,一個智能不足,一個罹患小兒麻痺,最正常的兒子結婚後,生下一個腦性麻痹的孩子。病人最後則罹患癌症。
她認為,「像我這麼歹命的人,死了一定會去陰曹地府受苦!我不甘願,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親朋鄰里則說,她家可能祖墳有問題,或可能被人詛咒,或祖先得罪人了。
在生命回顧時,我們問,「在當時的背景之下,妳沒有尋求或申請社會福利補助?」她說,「既然把孩子生下來,再怎麼艱苦,也要把孩子撫養長大,每個孩子都是我心頭上的一塊肉,我都不能放棄,也不能推卸責任!」
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母親啊!有多少人可以這麼堅強走過來?我們肯定她,「妳怎麼有辦法一個人扛起這麼大的擔子,真是不簡單……令人讚歎啊!所以,陰曹地府大概去不成了……」
第一次聽到有人肯定她、讚歎她,何況是出家法師說她好,彷彿佛菩薩加持,一切都被原諒、被寬恕了。最後病人無罣礙的離開了。
在關係和解中,生命回顧可說是最好的方式,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歷史的蛛絲馬跡,找到可以肯定的切入點,因為病人本身看不到。而與自己和解,首先要打開心門;如果自己不想走出幽暗的過去,任誰也無法可施。
臨終其實是一個很適合的場域,提供了我們以比較開闊的格局理解生命的機會,順著身體的變化,感知生命的無常,體悟生命的真理。如果接受了,就平安;不接受,就不平安。這時候,靈性照顧者也比較容易隨著這樣的自然趨勢,導引病人看見自己的生命脈絡,看見關係背後的信息,得以修補關係,原諒別人,也原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