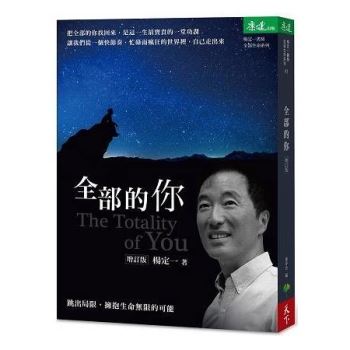*不是活在過去,就是活在未來
人生,是從念頭的幻覺建立的,而這些念頭不是停留在過去,就是投射在未來。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從不斷的要求、追求所產生的。其實,早期的人和動物沒有多大差別,吃飽了,解渴了,就可以休息,好好消化。過一天,是一天。生活也只是滿足身體的需要,適應周邊環境的變化。透過文明化,人開始發展記憶,開始累積。不光把過去的經驗累積、存檔,還進一步可以隨時調回來,跟生活上種種狀況作個比較,得到學習。學習中,再進一步規劃,以防範未然,或爭取更好的機會。
進一步講,人越發達,越會停留在過去或未來,透過思考﹝腦的動作﹞,我們從動物求生的動力,轉成腦海中的求生動力。不光是回想、分析腦海中的記憶,還投射出各式各樣的可能性。人類文明化的過程,正可以用腦的思考來衡量。
正是透過這個過程,我們每一個人都把瞬間當作通往目的地的手段。也就是說,透過過去的經驗,來達到一個更理想的未來。大家都在忙碌當中,哪有時間停在現在,正是因為現在不順心,我們才寧願待到未來!
有趣的是,我們的身體因為有一個機械和生理的架構,在很多層面還停留在動物的階段。生理的需要,即使到了現代,還是要吃飽、喝足、休息,跟幾萬年前一樣。不幸的是,因為我們活在腦的境界,透過腦打造了一個虛擬實境。讓身體分不清這一切是腦袋裡的,還是外頭的現實,分不清表相與真相。
於是,腦裡面的壓力自然轉化成身體上所面臨的壓力。因為神經系統真的以為隨時有危機,所以我們時時都「不在」。雖然跟身邊的人在交流,但心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很少停留在「這裡!現在!」,反而追求的都是「別地!未來!」。
甚至,我們會把「這裡!現在!」當作一個通往「彼地—彼時」的橋梁、樓梯。
要通往更好的未來,更好的地點,更好的生活狀況。進一步說,回到這個世界,我們都以為「別的那裡—別的瞬間」會比「這裡!現在!」更好。讀到這些話,不需要質疑。只要好好觀察每個人一生的經過,就能檢驗這些話正不正確。我們一生出來,自然就進入一個學習階段。從牙牙學語起,什麼事能做、不能做,什麼話能說、不能說,每一句話,甚至每個思考,就已經受到家庭的制約,反映了父母的教養方式、情感交流、人際互動……種種的生命價值觀念。父母的期待、對我們的規劃,我們自然就接受了。就像種子落入了心靈,生命的藍圖── 未來怎麼成人、做什麼工作、人生規劃── 就已經定型了。透過這些規劃,我們自然被灌輸了:要未雨綢繆,要為未來規劃、打算、計較。
等到入學,又進入了另一套更完整的規劃體系。透過小學、中學的基本學習,乃至於大學、研究所的進階教育,為個人的人生規劃作一個培養、鍛鍊和籌備。因為未來會比過去更有成就,或者反過來說,要透過過去跟現在更多的努力,未來才會有成就。所以,我們每個人就認真學習,累積知識,強化分別。同時,我們也把教育體系的獎勵和懲罰納入心靈。進一步透過這完整的系統,將自己的能力作一個區隔和突顯,很早就自然建立了成功和失敗的觀念。
進入就業的市場,繼續接受環境的要求和期待,也進一步接收到別人對我們的判斷。我們盡力做個好員工,好同事,希望對人生的規劃目標可以更上一層樓。為了達成未來的規劃,一切短期的需求都可以犧牲。我們把人生濃縮成一個學習和準備的過程,為了佔領更好的未來。對大部份人來說,未來的表現,佔掉了大部份的人生精力。
有了對象,我們不光對自己,還對對象自然有期待。希望透過比較親密的關係,可以找到更完整的我、更圓滿的一切。因為,每一個人都帶著自己的設定一路到現在,對自己其實不滿意。自然期待透過伴侶,可以完成我們失落的「另一半」。
進一步,有了家庭,我們就自然落入父母的角色。不光要求另一半盡責,對孩子未來的要求更不用多說。從小到大,種種細節都要掌握。為了孩子「好」,我們做父母的,一切犧牲都值得。為了一個希望、一份前途、一個願景,我們就跟孩子一起,一路走下去。在這條人生大道上,重複當年父母走過的老路。年紀更大了,身體機能開始衰退,開始有各式各樣的疾病。我們不光回想過去,還可能更把希望寄託在未來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期待他們生活狀況更好,將自己年輕時未完成的心願,交給他們來執行。不知不覺,家庭、社會、民族的設定變得愈來愈牢不可破。更嚴重的,我們不光是活在一個「人在,心不在」的人生裡。無形中,還把每一個念頭﹝過去的經驗、未來的投射﹞當作固態的實相。
從無色無相,把每一個念頭轉成有色有相的念相,讓它好像是個活生生的實體。
*療癒萎縮體
面對萎縮體,也就是面對過去種種的制約──包括個人,以及人類集體。
可以看到自己的萎縮體,甚至可以看清、看透它,也就是把它消解、療癒最好的辦法。
萎縮體,跟念頭體是分不開的,而念頭體則跟有形有色的外在世界分不開。要看清萎縮體,也就是看穿念頭體、看穿有色有形的世界,把我們的內在世界,也就是我們無色無形的意識找回來。只要我們把生命的源頭找回來,任何念頭體和萎縮體自然就消失了。
站在物理的角度,其實很容易理解── 任何固態的東西,我們去分析它,只要維度低於分子的尺寸,自然會發現,「沒有」是遠遠超過「有」的。進一步講,任何有色有形的東西,包括念頭,都包含著「空」。
我們抬起頭來看著天空,就知道這原理從最小到最大都是正確的。雖然抬頭看是滿天星星,但仔細觀察,星和星之間,都是由空所組合的。
進一步說,有限的體,不管是山水、椅子、花草、貓、狗、人……都含著無垠的浩瀚,而這個無垠的浩瀚遠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色相形狀。
瞧,這裡有一個悖論!── 我們不斷地用有限、分門別類的語言,來表達不可分別的無限大和無限小的宇宙,而兩邊的世界根本接軌不上。但是,我希望透過這本書,證實倒不是如此。其實,這些由腦造出的悖論,是很容易解答的。
每一個人都體驗過,也是意識醒覺的一部份。所以從某一個層面來說,醒覺就是把自己找回來。把最單純、最原初的那個意識找回來。
只要看到這些原理,甚至可以觀察到這一反應發生的流程,就已經可以把人生的困擾解開一半了。所以古人會強調──看清,就是解脫。一樣的意思。會讓我們發現,我們一生都被自己的頭腦跟情緒綁住,從來沒有離開過它們的範圍。借古人的解釋,再進一步講。解脫,就是從腦落到心。也就是從念頭轉到心的智慧,而心的智慧不是靠念頭或語言可以描述出來的。它其實是更大的聰明,我們稱之為智慧。我記得,我在《真原醫》也花相當多的篇幅來說明心的智慧是遠遠超過腦,是任何腦的境界所無法比擬的。
當然,我在這裡所提到的「心」,指稱的是一個超越思考而無思無想、無限大的狀態。它是還沒有念頭前,就已經存在。
怎麼回到心?怎麼落在心?是我們在這本書想進一步說明、分享的。反過來,全部的你,也可以說是──把腦和心或是一切都找回來,都跟生命整合起來。
*建立身分
身分,是一切「不快樂」的來源。
我們人一生出來,就已經離不開社會、家庭所帶來的制約和約束﹝conditioning﹞。光是從父母給我們的名字,就被這張文字標籤鎖定了一個身分,建立了一個後天的「自己」。
我們很早,甚至還是嬰兒的時候,就學到分別和區隔,學到了孩子是和父母不同的角色。父母會給我們帶來安全、生命的自主與滿足。做孩子的我們,就可以期待得到飲食、飽暖,得到保護。
有了兄弟姊妹,我們又理解了,原來手足的身分和我這個人的身分不同。而且,在父母的眼中,他們的身分和我個人的身分又有許多地方不同。透過玩耍,我們自然會認出某個玩具是「我」的,還會跟別人的比較。透過玩具的大小、顏色、功能、好不好玩,我們就學會了建立自己獨立的身分,和兄弟姊妹、鄰居的孩子區隔開來。也透過比較,自然也會跟父母要求比較「好」、比較「好玩」的玩具,在一群小孩子中,確立自己的身分。無形當中,把這個玩具當成很重要的一部份,把這個身分當作自己。再懂事點,自然就會分辨出什麼是父母期待的表現、態度,為了滿足父母的期望,自然就鎖定一些行為來展現。透過這些種種互動的分別,我們很小就認識了自己在這個世界的身分,和在家庭中的角色。
上學後,我們的身分認同就更鞏固、更堅實了。我們變成了一個班裡的一個同學,一個要表現得比別人好的學生。我們學會了要努力用功,在老師和其他同學面前要表現出可以得到認可、讚許的一個樣子。這種身分,是最受大家歡迎的。那時候,我們也已經懂了,懂得了快樂和不快樂。很自然的,我們發現在家裡,有些行為會受到周邊人的歡迎或排斥。受到歡迎,會強化我們的身分,會讓我們更趨向那個樣子。反過來,也有許多互動讓別人不滿,甚至排斥。這些都會讓我們覺得不愉快,一樣會強化了個人對自己、對別人的負面認同。
等到我們進入青少年期,其他人的身分已經愈來愈堅固,而「我」這個人也只是社會林林總總身分的一部份。這個身分的定位,和「我」未來在社會要扮演的角色也分不開。「我」未來想要扮演的社會角色,已經被自己指定的身分綁住了,也就是反映「我」對我自己的認同。
這個認同,是在個人的特質和環境互動中逐漸定型的。如果我剛好擅長體育,在別人眼中是運動明星,我也會想往體育競爭去發展,覺得自己應該可以成為好球員或是優秀的運動員。假如我個性內向,寧願安靜讀書,逐漸也就成為大家眼中學習好的孩子,自認為日後就應該成為學者。倘若我外貌或身材出色,得到了同輩的關注,我也就更注重打扮和外表的修飾,好繼續得到外界的肯定和特殊待遇。甚至,如果我個頭比較瘦小,玩耍總是爭不贏,或許我會變得退縮,避開需要跟人競爭的情況。
從特質,經過與外界的互動,一個人在無意間得到了鼓勵或否定,而指派給自己一個未來的角色和身分。所以,很多年輕人會想當醫生、護理師、老師、家長、企業家、歌手、明星、學者、工程師、技師……都離不開他自己所指定的身分,也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認同。
很有意思的是,華人對身分特別重視。也許這就是儒家思想的影響,認為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要有他的角色,他的身分。但是,這個角色和身分似乎已經合而為一。這一來,每一個人都離不開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而個人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又自然變成身分很重要的一部份。我們很常見到──人與人之間的稱呼,都要掛上一個身分來鑑別。而且這個身分多半離不開角色,例如:王教授、李老闆、邱董事長、林副總、盧總、張指揮官、陳工程師、楊老師、王同學、李小姐、林哥哥、陳小妹……也可以說,從這個稱謂,已經定出了這個人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有趣的是,別人這麼叫,自己也很理所當然,自己都被別人口中的身分和角色給迷住了。好像不這麼稱呼,就看不到這個人。然而,人被這麼稱呼習慣了,如果沒聽到,還會渾身不對勁。人家叫我楊老師、李老師,我就是老師的身分,那麼,就要有個當老師的樣子。更有趣的是,換了一個角色,還要讓周邊的人跟著調整稱謂,來確立這個新角色。有時候,這麼確立還不夠,還要昭告天下。
反過來,我們對別人也是一樣。用一個稱謂「框住」對他的看法,而這個看法其實是過去以來種種印象的積累。最可憐的是,每一個人對別人一點都不客觀,都是從過去的制約來投射出這個人的角色,並限制了我們對這個人的期待。在
東方社會,這個情況特別明顯,人就是會對有身分的人另眼看待。
接下來,我要繼續談的是,為什麼一切的不快樂,全都和身分的認定有關。
7透過「我」看生命
我,一點都不客觀。我,從來沒有客觀過。有了我,就不可能是客觀的。
雖然前面有提過,我這裡想再強調一次── 生命本來是很好過、很單純的。一個瞬間,再接著下一個瞬間。從一個瞬間,再轉到下一個瞬間。然而,透過「我」,我們會把一個很簡單的生命狀況擴大,讓自己完全過不去。
透過這樣強勢的「我」來看這世界,會發現樣樣都不客觀。「我」像個過濾網,會扭曲一切──一切我們所體會、所看到、所經驗的。把這一切,帶到一個幻覺的層面來分析。然而,這幻覺正是「我」製造出來的。
最有意思的是,這個「我」對樣樣都有看法,不斷地在分析、判斷、抱怨。沒有一樣東西會被「我」放過。「我」都有意見。我們前面也提過,這意見通常不是正念的意見。它會勾結我們的萎縮體,把事態鬧大。把一個瞬間變成一齣戲。
透過種種過去累積的印象,再投射出最壞的可能性。
比如說,我們跟另一半約好,結果對方沒有準時出現。我們在那裡乾等,可能心裡忍不住開始抱怨「這個人從來不會準時,一點時間觀念都沒有。」再多等幾分鐘,心裡就開始猜測「他是不是有了別人,一點都不重視我,我還是跟他分手好了。」再十五分鐘「我該不該打電話,算了,他又不是小孩,成天要我管?」再十五分鐘「不對,他是不是出車禍了?」這一連串的念頭,都偏向負面的念頭。
我們人,就是有這種把小事變成大事的本事。每個人都一樣。反過來,假如我們客觀地看每一個生命的狀況,都會發現──再怎麼困難,它本身是很單純的。
那個瞬間過去了,就沒有了。再怎麼痛,再怎麼悲哀,也就是在那個瞬間發生。接下來,就消失。放不過,是我們自己的念頭透過過去的記憶,把很多相關不相關的狀況擰在一起,作很多層面的連結。
並透過這樣的連結,不斷地投射到未來──要怎麼去規劃、該怎麼防範未然。
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生命跟「我」和「我的身分」綁在一起。還認為──沒有「我」就沒有生命。
通常,我們在說「生命」或「人生」的時候,指稱的也不過是生命的狀況、生命的表相、生命的故事內容。然而,這些種種的生命狀況,正是透過「我」或念頭的探討,而變成了「我的生命狀況」。正是透過「我」的過濾,這些狀況變得完全跟生命分不開來。
我們每一個人無形當中都把「我」和「我的生命狀況」混淆了,變成同一件事。通常在講「我」的時候,其實在含糊地指稱「我的狀況」或「我的故事」。而「我」一生的故事,跟任何人的故事都不一樣。「我的故事比你的更精彩」、「我的委屈沒有人可以理解」、「我是怎麼樣犧牲奉獻」、「我失去了家庭,現在又失去了朋友」、「我這輩子做到這個位置」、「沒有人的家庭像我家這樣悲慘」、「我受的傷多深」、「我經過了數不清的悲痛」……這些故事明明都只是「我的故事」,卻不知不覺變成了我,定義了我,都成為定義「我」的生命的很重要的一部份。讓我們不斷地把生命的現象,當成了真正的生命來看。
進一步說,生命本來是包括一個更大的架構。在這個架構下,生命的種種狀況才會發生。也就是說,生命包括兩種意識。一個就是我們局限而有條件的意識。它,確實跟我們的人生故事是分不開的,也就是前頭提過的人生的前景,不斷透過因果而成形。它也是透過相對、比較的邏輯,也就是我們腦的分析邏輯而建立的。但是,除了這一部份,我們還有一個遠遠更大的意識,也就是我們提過的生命的背景。它是個一體意識,就是個輕鬆的知覺,不受任何條件約束。
\它是永恆、絕對的存在,跟人生的故事不相關。而且本身就不需要作任何分別。但是從這個背景,又允許任何前景、任何人生故事的演出。
同時存在這兩個意識,也就是把全部的生命找回來。然而,因為任何形相,包括念頭跟「我」的吸引力太強大了。所以,我們被「我」給困住了,而把更大的無限大的意識忘記了。就好像「我」蓋住了無限大的意識。這也是一生不快樂的主要原因。
找回來另外一個更大的意識,自然就會發現──我們本來早就是完整、圓滿,一點一滴都加不上去的。但是,因為有了「我」,而且還是這麼強烈的「我」,而把這世界扭曲了。
1超越和奇點
人生的超越,也只是找到絕對和相對的交會點。
我在《靜坐》跟讀者分享了很多靜坐的方法,這些方法不是採用專注﹝止、定﹞就是覺察﹝觀﹞。
此外,我還提到了「奇點」﹝singularity﹞和「超越」﹝transcendence﹞的觀念。奇點是個物理的名稱,表達任何東西﹝例如說「注意力」﹞濃縮到一個點上,不斷地縮小、不斷地集中,直到一個極限的地步,自然就跳出了時空。這麼說,超過奇點,任何東西已經不受人間所帶來的時空管制。這是人類從古到今所追求的修行境界。
意識的超越,就是解脫,跳出人間。也就是回到我們人的本性、佛性,或是天國。也就是回到永恆、無限大的一體之境。這種成就,有史以來,體悟到的人可說寥寥無幾。
每一部經典都在談這個題目。但可以這麼說,因為採用局限的語言文字,想表達無限大的潛能,這些經典留下的最多不過是一些路標,指向那不可用任何路標描述的境地。只是想用語言,帶著大家跨出用語言所能形容的理解;期望能用語言,去跨越腦所可以掌握的理解。
我們聽到這兒,自然會覺得這種理解是追求不到,做不來的。我們自然會用腦袋裡的邏輯去延伸這些路標,把它造回我們人間所可以體會的理解。這本身就會帶來矛盾,因為延伸不了。延伸不了的原因,是我們先被這延伸的語言限制了。
我想進一步解釋這一點。
出乎意料的是,這些理解本來就存在我們身邊,根本不需要去追求解釋。因為每一句話、每一個念頭、每一個動作……這些有形有色都含著無形無色。
這個重點本身就帶給我們一把鑰匙,可以打開意識的門戶。我們前面談過,假如沒有無形無色存在於有形有色之中,那麼,有形有色本身就不可能存在。進一步講,是從無色無形延伸出來有色有形,而透過無色無形才讓我們體會到有色有形。假如我們生命不是永恆的,絕對體會不到什麼叫作無常。是從「不動」、「寧靜」,才可以體會到種種的「動」,包括聲音。是從最根本的狀態──喜樂、愛、光明,我們才能體會到種種痛苦、萎縮和黑暗。
倘若不是如此,我們再怎麼努力,不可能體會到種種的有色有形。不可能體會到「動」。不可能體會到種種無常、痛苦、萎縮、黑暗和悲傷。也沒有什麼人間或「我的身分」好談的。這個道理雖然是再明白不過了,卻和我們一般人的想法是顛倒的。
問題是──怎麼把這永恆、寧靜、不動的無形無色找回來?
不光把這無形無色找回來,重點是──怎樣隨時活在無形無色跟有形有色的交會點,讓我們隨時採用兩個意識來面對生命。而且,這個交會點,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之內。
無形無色的知覺,是我們生命絕對的部份,跟任何人生條件都不相關。不可能生,也不可能死。
人類還沒出現,它已經存在了。我們前頭稱之為人生的背景、因地。進一步講,跟「我」不相關。
相對的,有形有色的意識,是局限的,離不開我們人生種種的條件變化。它也有生,它也有死。
它也只是反映了腦分別解釋的邏輯,而用這個邏輯來解釋人間。就這樣,這個局限的意識,誤導了我們每一個人,讓我們一直以為這就是全部的生命。根本想不到,這只是生命一個很小、很局限的部份。
卻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裡面打轉,從來沒有跳出來過。
從這個局限的意識裡面,我們又產生一個「我」。這個「我」、這個局限的意識是透過形相而延伸出來的,把我們的注意力完全綁住,才造出人生種種的悲歡離合。我們所看到、體驗到的世界,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局限意識的境界。
進一步說,把全部的人生找回來,也只是輕輕鬆鬆地把這個「我」的境界放下來。看穿這個局限意識所帶來的一切形相,並讓最源頭、從來沒有離開過的意識存在。讓這個最源頭的知覺輕輕鬆鬆存在,也就夠了。
只要把這個相對、局限的意識放下來,我們什麼都不用做。絕對、無限的意識自然會爆發出來。
人生,是從念頭的幻覺建立的,而這些念頭不是停留在過去,就是投射在未來。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從不斷的要求、追求所產生的。其實,早期的人和動物沒有多大差別,吃飽了,解渴了,就可以休息,好好消化。過一天,是一天。生活也只是滿足身體的需要,適應周邊環境的變化。透過文明化,人開始發展記憶,開始累積。不光把過去的經驗累積、存檔,還進一步可以隨時調回來,跟生活上種種狀況作個比較,得到學習。學習中,再進一步規劃,以防範未然,或爭取更好的機會。
進一步講,人越發達,越會停留在過去或未來,透過思考﹝腦的動作﹞,我們從動物求生的動力,轉成腦海中的求生動力。不光是回想、分析腦海中的記憶,還投射出各式各樣的可能性。人類文明化的過程,正可以用腦的思考來衡量。
正是透過這個過程,我們每一個人都把瞬間當作通往目的地的手段。也就是說,透過過去的經驗,來達到一個更理想的未來。大家都在忙碌當中,哪有時間停在現在,正是因為現在不順心,我們才寧願待到未來!
有趣的是,我們的身體因為有一個機械和生理的架構,在很多層面還停留在動物的階段。生理的需要,即使到了現代,還是要吃飽、喝足、休息,跟幾萬年前一樣。不幸的是,因為我們活在腦的境界,透過腦打造了一個虛擬實境。讓身體分不清這一切是腦袋裡的,還是外頭的現實,分不清表相與真相。
於是,腦裡面的壓力自然轉化成身體上所面臨的壓力。因為神經系統真的以為隨時有危機,所以我們時時都「不在」。雖然跟身邊的人在交流,但心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很少停留在「這裡!現在!」,反而追求的都是「別地!未來!」。
甚至,我們會把「這裡!現在!」當作一個通往「彼地—彼時」的橋梁、樓梯。
要通往更好的未來,更好的地點,更好的生活狀況。進一步說,回到這個世界,我們都以為「別的那裡—別的瞬間」會比「這裡!現在!」更好。讀到這些話,不需要質疑。只要好好觀察每個人一生的經過,就能檢驗這些話正不正確。我們一生出來,自然就進入一個學習階段。從牙牙學語起,什麼事能做、不能做,什麼話能說、不能說,每一句話,甚至每個思考,就已經受到家庭的制約,反映了父母的教養方式、情感交流、人際互動……種種的生命價值觀念。父母的期待、對我們的規劃,我們自然就接受了。就像種子落入了心靈,生命的藍圖── 未來怎麼成人、做什麼工作、人生規劃── 就已經定型了。透過這些規劃,我們自然被灌輸了:要未雨綢繆,要為未來規劃、打算、計較。
等到入學,又進入了另一套更完整的規劃體系。透過小學、中學的基本學習,乃至於大學、研究所的進階教育,為個人的人生規劃作一個培養、鍛鍊和籌備。因為未來會比過去更有成就,或者反過來說,要透過過去跟現在更多的努力,未來才會有成就。所以,我們每個人就認真學習,累積知識,強化分別。同時,我們也把教育體系的獎勵和懲罰納入心靈。進一步透過這完整的系統,將自己的能力作一個區隔和突顯,很早就自然建立了成功和失敗的觀念。
進入就業的市場,繼續接受環境的要求和期待,也進一步接收到別人對我們的判斷。我們盡力做個好員工,好同事,希望對人生的規劃目標可以更上一層樓。為了達成未來的規劃,一切短期的需求都可以犧牲。我們把人生濃縮成一個學習和準備的過程,為了佔領更好的未來。對大部份人來說,未來的表現,佔掉了大部份的人生精力。
有了對象,我們不光對自己,還對對象自然有期待。希望透過比較親密的關係,可以找到更完整的我、更圓滿的一切。因為,每一個人都帶著自己的設定一路到現在,對自己其實不滿意。自然期待透過伴侶,可以完成我們失落的「另一半」。
進一步,有了家庭,我們就自然落入父母的角色。不光要求另一半盡責,對孩子未來的要求更不用多說。從小到大,種種細節都要掌握。為了孩子「好」,我們做父母的,一切犧牲都值得。為了一個希望、一份前途、一個願景,我們就跟孩子一起,一路走下去。在這條人生大道上,重複當年父母走過的老路。年紀更大了,身體機能開始衰退,開始有各式各樣的疾病。我們不光回想過去,還可能更把希望寄託在未來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期待他們生活狀況更好,將自己年輕時未完成的心願,交給他們來執行。不知不覺,家庭、社會、民族的設定變得愈來愈牢不可破。更嚴重的,我們不光是活在一個「人在,心不在」的人生裡。無形中,還把每一個念頭﹝過去的經驗、未來的投射﹞當作固態的實相。
從無色無相,把每一個念頭轉成有色有相的念相,讓它好像是個活生生的實體。
*療癒萎縮體
面對萎縮體,也就是面對過去種種的制約──包括個人,以及人類集體。
可以看到自己的萎縮體,甚至可以看清、看透它,也就是把它消解、療癒最好的辦法。
萎縮體,跟念頭體是分不開的,而念頭體則跟有形有色的外在世界分不開。要看清萎縮體,也就是看穿念頭體、看穿有色有形的世界,把我們的內在世界,也就是我們無色無形的意識找回來。只要我們把生命的源頭找回來,任何念頭體和萎縮體自然就消失了。
站在物理的角度,其實很容易理解── 任何固態的東西,我們去分析它,只要維度低於分子的尺寸,自然會發現,「沒有」是遠遠超過「有」的。進一步講,任何有色有形的東西,包括念頭,都包含著「空」。
我們抬起頭來看著天空,就知道這原理從最小到最大都是正確的。雖然抬頭看是滿天星星,但仔細觀察,星和星之間,都是由空所組合的。
進一步說,有限的體,不管是山水、椅子、花草、貓、狗、人……都含著無垠的浩瀚,而這個無垠的浩瀚遠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色相形狀。
瞧,這裡有一個悖論!── 我們不斷地用有限、分門別類的語言,來表達不可分別的無限大和無限小的宇宙,而兩邊的世界根本接軌不上。但是,我希望透過這本書,證實倒不是如此。其實,這些由腦造出的悖論,是很容易解答的。
每一個人都體驗過,也是意識醒覺的一部份。所以從某一個層面來說,醒覺就是把自己找回來。把最單純、最原初的那個意識找回來。
只要看到這些原理,甚至可以觀察到這一反應發生的流程,就已經可以把人生的困擾解開一半了。所以古人會強調──看清,就是解脫。一樣的意思。會讓我們發現,我們一生都被自己的頭腦跟情緒綁住,從來沒有離開過它們的範圍。借古人的解釋,再進一步講。解脫,就是從腦落到心。也就是從念頭轉到心的智慧,而心的智慧不是靠念頭或語言可以描述出來的。它其實是更大的聰明,我們稱之為智慧。我記得,我在《真原醫》也花相當多的篇幅來說明心的智慧是遠遠超過腦,是任何腦的境界所無法比擬的。
當然,我在這裡所提到的「心」,指稱的是一個超越思考而無思無想、無限大的狀態。它是還沒有念頭前,就已經存在。
怎麼回到心?怎麼落在心?是我們在這本書想進一步說明、分享的。反過來,全部的你,也可以說是──把腦和心或是一切都找回來,都跟生命整合起來。
*建立身分
身分,是一切「不快樂」的來源。
我們人一生出來,就已經離不開社會、家庭所帶來的制約和約束﹝conditioning﹞。光是從父母給我們的名字,就被這張文字標籤鎖定了一個身分,建立了一個後天的「自己」。
我們很早,甚至還是嬰兒的時候,就學到分別和區隔,學到了孩子是和父母不同的角色。父母會給我們帶來安全、生命的自主與滿足。做孩子的我們,就可以期待得到飲食、飽暖,得到保護。
有了兄弟姊妹,我們又理解了,原來手足的身分和我這個人的身分不同。而且,在父母的眼中,他們的身分和我個人的身分又有許多地方不同。透過玩耍,我們自然會認出某個玩具是「我」的,還會跟別人的比較。透過玩具的大小、顏色、功能、好不好玩,我們就學會了建立自己獨立的身分,和兄弟姊妹、鄰居的孩子區隔開來。也透過比較,自然也會跟父母要求比較「好」、比較「好玩」的玩具,在一群小孩子中,確立自己的身分。無形當中,把這個玩具當成很重要的一部份,把這個身分當作自己。再懂事點,自然就會分辨出什麼是父母期待的表現、態度,為了滿足父母的期望,自然就鎖定一些行為來展現。透過這些種種互動的分別,我們很小就認識了自己在這個世界的身分,和在家庭中的角色。
上學後,我們的身分認同就更鞏固、更堅實了。我們變成了一個班裡的一個同學,一個要表現得比別人好的學生。我們學會了要努力用功,在老師和其他同學面前要表現出可以得到認可、讚許的一個樣子。這種身分,是最受大家歡迎的。那時候,我們也已經懂了,懂得了快樂和不快樂。很自然的,我們發現在家裡,有些行為會受到周邊人的歡迎或排斥。受到歡迎,會強化我們的身分,會讓我們更趨向那個樣子。反過來,也有許多互動讓別人不滿,甚至排斥。這些都會讓我們覺得不愉快,一樣會強化了個人對自己、對別人的負面認同。
等到我們進入青少年期,其他人的身分已經愈來愈堅固,而「我」這個人也只是社會林林總總身分的一部份。這個身分的定位,和「我」未來在社會要扮演的角色也分不開。「我」未來想要扮演的社會角色,已經被自己指定的身分綁住了,也就是反映「我」對我自己的認同。
這個認同,是在個人的特質和環境互動中逐漸定型的。如果我剛好擅長體育,在別人眼中是運動明星,我也會想往體育競爭去發展,覺得自己應該可以成為好球員或是優秀的運動員。假如我個性內向,寧願安靜讀書,逐漸也就成為大家眼中學習好的孩子,自認為日後就應該成為學者。倘若我外貌或身材出色,得到了同輩的關注,我也就更注重打扮和外表的修飾,好繼續得到外界的肯定和特殊待遇。甚至,如果我個頭比較瘦小,玩耍總是爭不贏,或許我會變得退縮,避開需要跟人競爭的情況。
從特質,經過與外界的互動,一個人在無意間得到了鼓勵或否定,而指派給自己一個未來的角色和身分。所以,很多年輕人會想當醫生、護理師、老師、家長、企業家、歌手、明星、學者、工程師、技師……都離不開他自己所指定的身分,也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認同。
很有意思的是,華人對身分特別重視。也許這就是儒家思想的影響,認為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要有他的角色,他的身分。但是,這個角色和身分似乎已經合而為一。這一來,每一個人都離不開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而個人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又自然變成身分很重要的一部份。我們很常見到──人與人之間的稱呼,都要掛上一個身分來鑑別。而且這個身分多半離不開角色,例如:王教授、李老闆、邱董事長、林副總、盧總、張指揮官、陳工程師、楊老師、王同學、李小姐、林哥哥、陳小妹……也可以說,從這個稱謂,已經定出了這個人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有趣的是,別人這麼叫,自己也很理所當然,自己都被別人口中的身分和角色給迷住了。好像不這麼稱呼,就看不到這個人。然而,人被這麼稱呼習慣了,如果沒聽到,還會渾身不對勁。人家叫我楊老師、李老師,我就是老師的身分,那麼,就要有個當老師的樣子。更有趣的是,換了一個角色,還要讓周邊的人跟著調整稱謂,來確立這個新角色。有時候,這麼確立還不夠,還要昭告天下。
反過來,我們對別人也是一樣。用一個稱謂「框住」對他的看法,而這個看法其實是過去以來種種印象的積累。最可憐的是,每一個人對別人一點都不客觀,都是從過去的制約來投射出這個人的角色,並限制了我們對這個人的期待。在
東方社會,這個情況特別明顯,人就是會對有身分的人另眼看待。
接下來,我要繼續談的是,為什麼一切的不快樂,全都和身分的認定有關。
7透過「我」看生命
我,一點都不客觀。我,從來沒有客觀過。有了我,就不可能是客觀的。
雖然前面有提過,我這裡想再強調一次── 生命本來是很好過、很單純的。一個瞬間,再接著下一個瞬間。從一個瞬間,再轉到下一個瞬間。然而,透過「我」,我們會把一個很簡單的生命狀況擴大,讓自己完全過不去。
透過這樣強勢的「我」來看這世界,會發現樣樣都不客觀。「我」像個過濾網,會扭曲一切──一切我們所體會、所看到、所經驗的。把這一切,帶到一個幻覺的層面來分析。然而,這幻覺正是「我」製造出來的。
最有意思的是,這個「我」對樣樣都有看法,不斷地在分析、判斷、抱怨。沒有一樣東西會被「我」放過。「我」都有意見。我們前面也提過,這意見通常不是正念的意見。它會勾結我們的萎縮體,把事態鬧大。把一個瞬間變成一齣戲。
透過種種過去累積的印象,再投射出最壞的可能性。
比如說,我們跟另一半約好,結果對方沒有準時出現。我們在那裡乾等,可能心裡忍不住開始抱怨「這個人從來不會準時,一點時間觀念都沒有。」再多等幾分鐘,心裡就開始猜測「他是不是有了別人,一點都不重視我,我還是跟他分手好了。」再十五分鐘「我該不該打電話,算了,他又不是小孩,成天要我管?」再十五分鐘「不對,他是不是出車禍了?」這一連串的念頭,都偏向負面的念頭。
我們人,就是有這種把小事變成大事的本事。每個人都一樣。反過來,假如我們客觀地看每一個生命的狀況,都會發現──再怎麼困難,它本身是很單純的。
那個瞬間過去了,就沒有了。再怎麼痛,再怎麼悲哀,也就是在那個瞬間發生。接下來,就消失。放不過,是我們自己的念頭透過過去的記憶,把很多相關不相關的狀況擰在一起,作很多層面的連結。
並透過這樣的連結,不斷地投射到未來──要怎麼去規劃、該怎麼防範未然。
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生命跟「我」和「我的身分」綁在一起。還認為──沒有「我」就沒有生命。
通常,我們在說「生命」或「人生」的時候,指稱的也不過是生命的狀況、生命的表相、生命的故事內容。然而,這些種種的生命狀況,正是透過「我」或念頭的探討,而變成了「我的生命狀況」。正是透過「我」的過濾,這些狀況變得完全跟生命分不開來。
我們每一個人無形當中都把「我」和「我的生命狀況」混淆了,變成同一件事。通常在講「我」的時候,其實在含糊地指稱「我的狀況」或「我的故事」。而「我」一生的故事,跟任何人的故事都不一樣。「我的故事比你的更精彩」、「我的委屈沒有人可以理解」、「我是怎麼樣犧牲奉獻」、「我失去了家庭,現在又失去了朋友」、「我這輩子做到這個位置」、「沒有人的家庭像我家這樣悲慘」、「我受的傷多深」、「我經過了數不清的悲痛」……這些故事明明都只是「我的故事」,卻不知不覺變成了我,定義了我,都成為定義「我」的生命的很重要的一部份。讓我們不斷地把生命的現象,當成了真正的生命來看。
進一步說,生命本來是包括一個更大的架構。在這個架構下,生命的種種狀況才會發生。也就是說,生命包括兩種意識。一個就是我們局限而有條件的意識。它,確實跟我們的人生故事是分不開的,也就是前頭提過的人生的前景,不斷透過因果而成形。它也是透過相對、比較的邏輯,也就是我們腦的分析邏輯而建立的。但是,除了這一部份,我們還有一個遠遠更大的意識,也就是我們提過的生命的背景。它是個一體意識,就是個輕鬆的知覺,不受任何條件約束。
\它是永恆、絕對的存在,跟人生的故事不相關。而且本身就不需要作任何分別。但是從這個背景,又允許任何前景、任何人生故事的演出。
同時存在這兩個意識,也就是把全部的生命找回來。然而,因為任何形相,包括念頭跟「我」的吸引力太強大了。所以,我們被「我」給困住了,而把更大的無限大的意識忘記了。就好像「我」蓋住了無限大的意識。這也是一生不快樂的主要原因。
找回來另外一個更大的意識,自然就會發現──我們本來早就是完整、圓滿,一點一滴都加不上去的。但是,因為有了「我」,而且還是這麼強烈的「我」,而把這世界扭曲了。
1超越和奇點
人生的超越,也只是找到絕對和相對的交會點。
我在《靜坐》跟讀者分享了很多靜坐的方法,這些方法不是採用專注﹝止、定﹞就是覺察﹝觀﹞。
此外,我還提到了「奇點」﹝singularity﹞和「超越」﹝transcendence﹞的觀念。奇點是個物理的名稱,表達任何東西﹝例如說「注意力」﹞濃縮到一個點上,不斷地縮小、不斷地集中,直到一個極限的地步,自然就跳出了時空。這麼說,超過奇點,任何東西已經不受人間所帶來的時空管制。這是人類從古到今所追求的修行境界。
意識的超越,就是解脫,跳出人間。也就是回到我們人的本性、佛性,或是天國。也就是回到永恆、無限大的一體之境。這種成就,有史以來,體悟到的人可說寥寥無幾。
每一部經典都在談這個題目。但可以這麼說,因為採用局限的語言文字,想表達無限大的潛能,這些經典留下的最多不過是一些路標,指向那不可用任何路標描述的境地。只是想用語言,帶著大家跨出用語言所能形容的理解;期望能用語言,去跨越腦所可以掌握的理解。
我們聽到這兒,自然會覺得這種理解是追求不到,做不來的。我們自然會用腦袋裡的邏輯去延伸這些路標,把它造回我們人間所可以體會的理解。這本身就會帶來矛盾,因為延伸不了。延伸不了的原因,是我們先被這延伸的語言限制了。
我想進一步解釋這一點。
出乎意料的是,這些理解本來就存在我們身邊,根本不需要去追求解釋。因為每一句話、每一個念頭、每一個動作……這些有形有色都含著無形無色。
這個重點本身就帶給我們一把鑰匙,可以打開意識的門戶。我們前面談過,假如沒有無形無色存在於有形有色之中,那麼,有形有色本身就不可能存在。進一步講,是從無色無形延伸出來有色有形,而透過無色無形才讓我們體會到有色有形。假如我們生命不是永恆的,絕對體會不到什麼叫作無常。是從「不動」、「寧靜」,才可以體會到種種的「動」,包括聲音。是從最根本的狀態──喜樂、愛、光明,我們才能體會到種種痛苦、萎縮和黑暗。
倘若不是如此,我們再怎麼努力,不可能體會到種種的有色有形。不可能體會到「動」。不可能體會到種種無常、痛苦、萎縮、黑暗和悲傷。也沒有什麼人間或「我的身分」好談的。這個道理雖然是再明白不過了,卻和我們一般人的想法是顛倒的。
問題是──怎麼把這永恆、寧靜、不動的無形無色找回來?
不光把這無形無色找回來,重點是──怎樣隨時活在無形無色跟有形有色的交會點,讓我們隨時採用兩個意識來面對生命。而且,這個交會點,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之內。
無形無色的知覺,是我們生命絕對的部份,跟任何人生條件都不相關。不可能生,也不可能死。
人類還沒出現,它已經存在了。我們前頭稱之為人生的背景、因地。進一步講,跟「我」不相關。
相對的,有形有色的意識,是局限的,離不開我們人生種種的條件變化。它也有生,它也有死。
它也只是反映了腦分別解釋的邏輯,而用這個邏輯來解釋人間。就這樣,這個局限的意識,誤導了我們每一個人,讓我們一直以為這就是全部的生命。根本想不到,這只是生命一個很小、很局限的部份。
卻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裡面打轉,從來沒有跳出來過。
從這個局限的意識裡面,我們又產生一個「我」。這個「我」、這個局限的意識是透過形相而延伸出來的,把我們的注意力完全綁住,才造出人生種種的悲歡離合。我們所看到、體驗到的世界,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局限意識的境界。
進一步說,把全部的人生找回來,也只是輕輕鬆鬆地把這個「我」的境界放下來。看穿這個局限意識所帶來的一切形相,並讓最源頭、從來沒有離開過的意識存在。讓這個最源頭的知覺輕輕鬆鬆存在,也就夠了。
只要把這個相對、局限的意識放下來,我們什麼都不用做。絕對、無限的意識自然會爆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