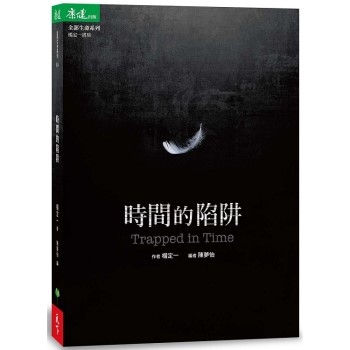第三章 時間帶來的重擔
The Burden of Time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只要談到時間,都有兩個直接的反應。首先,把它當作一個節律器,就像為生活定下節奏和步調,才可以衡量每一個規劃,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追求,每一個結果。但同時,它也帶給我們一種壓迫感,讓現代人總是感覺時間不夠用。
在這個不夠用的情況下,我們自然會想要一心多用──同一個時間,能處理愈多事愈好。透過快速的技術發展,我們可以同時停留在幾個知識的平台。不光有手機隨時可以通訊,還有電腦,同時還可以說話、寫字、和其他的運作。
不要說兩千年前的人,即使是五十年前的人,來到我們這個世界,也會嚇壞的。會認為每一個人的神經都過度激動,不只同時做好幾件事,而且步調快到想像不到,不要說跟不跟得上了。
我也發現,這個時間的重擔所波及的年齡層愈來愈下降。尤其華人,總是要充份利用時間,追求高效率,強調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麼要求自己還不夠,還要把這種追求延伸到下一代。一個孩子,只要懂事、進入小學,總是感覺跟不上,來不及。
讓我最同情的是,小孩子不光是睡不夠,在學校的時間長,功課多,家長的要求又加倍。就好像一上學,就要承擔週邊種種的期望和壓力。如果這個孩子自我要求又高,那麼時間的負擔更是沉重。
所以,我們過去看到是有了一定的年紀才有憂鬱症,例如事業受到打擊,或女士在產後、更年期的變化。然而,現在就連憂鬱症的發生年齡也不斷下降。幾歲的孩子就有憂鬱的症狀,甚至有自殺的念頭。我才會說憂鬱症是二十一世紀最嚴重的慢性病,而時間的重擔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要談時間的重擔,最多也就是「跟不上」。我們每個人都跟不上。一個人在跟不上的狀況下,自然會產生一個兩難。也就是說,在時間的壓迫下,我們認為隨時要有一個決策的備案,用來節省時間、解決時間帶來的壓力。這是我們每個人隨時在面對的。可惜,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步調自然會加快,而讓我們停不下來。就連休息的時候,還可能想要選擇快速的動,例如不光是看電視,還要對話快,鏡頭不斷的變化,或有暴力的刺激。晚上參加活動,要有大聲的音樂和熱鬧。這些娛樂的選擇,反映了我們個人對生活要求的快步調。
這樣子,別說休息時,慢不下來。就連睡覺的時候都停不下來,難怪那麼多人有失眠的問題。
我過去做為一個醫師、科學家,自然喜歡從機制或問題的根源著手。比如說,我當年研究免疫,就想知道殺手細胞和T細胞怎麼殺腫瘤。當時很年輕,很快把這個主題告一個段落,而且跟別人的切入點都不同。
現在,要切入時間這個主題,說時間是我們人類最寶貴的工具,也是我們最大的殺手,我認為這一點都不過份。我在這本書,希望可以再進一步打開──時間,其實跟我們人類的演化有密切的關係。這種觀點,或許你會認為是理所當然,因為歷史本來就是時間演變的記錄。但我要講的是,人類因為有時間的觀念,才有以後的發展。只是因為時間的觀念過度強化,自然擺盪到一個不均衡的狀態。
講了這些,即使把它解開,最多只是把症狀做個說明。我真正感興趣的,正如我過去所扮的角色,是希望找到一個徹底解答的方法。
第十九章 當下,不是過去和未來的對稱
Now is on a Different Scale Compared to Past and Future
回到當下,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嚴格講,它不是一個練習。
前面也提過,當下,其實不是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一個東西。讓我用這張圖來說明這個觀念──如果用翹翹板的兩端,各自代表過去和未來,那麼,當下並不是過去和未來的對等,而是完全落在不同的軌道。我在這裡,用一個螺旋來表達。
我之所以有勇氣,在這個時候出來談這些觀念,因為我認為──任何練習,無論是瑜伽、靜坐或所有傳統的練習,都還只是一個暫停(time out)的觀念,是一種專一、和其他狀態互斥的隔離狀態(exclusive state)。透過練習,即使有了這種狀態,早晚還是要回到人間。只有「全部生命系列」帶出來的臣服和參,不是一種暫停的隔離,而是進入非時間的永恆。讓非時間的永恆,和時間隨時交疊,同時存在。透過臣服與參,一個人不知不覺,隨時可以接受絕對與相對。甚至,可以輕輕鬆鬆滑回另一個軌道。我現在才會出來,甚至還帶出「反復工程」的觀念。
就是因為當下和時間的觀念是在兩個軌道,我們從任何瞬間,其實「回不到」當下。任何瞬間本來都有「絕對」,所以,「回到」當下,不是透過任何動力,而是剛好相反──最多把時間的觀念挪開,當下和非時間的永恆,自然就在眼前。
所以,談當下帶著我們走,最多也只是把非時間的永恆當作我們主要的意識層面,讓祂帶著我們走。心流,自然就流出來了。我們可以完成想不到的工作,儘管完成或不完成任何工作,也不重要。「全部生命系列」的寫作就是最好的實例。從我的角度,沒有刻意去「寫」任何一本書。最多只是把時間的觀念挪開,讓當下浮出來,想轉達什麼,也就自然出來了。
有意思的是,對我而言,沒有「誰」 在寫,寫起來也不費力,甚至連規劃也沒有。事後,看每一個作品,好像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的步調、邏輯就像是剛剛好。相信你讀這些作品時,也自然從非時間永恆的意識層面,延伸出一個理解。儘管這些話,對頭腦會不斷產生矛盾或悖論。但是,從心的層面,你知道這些話離不開真實。也因為如此,會不斷回來尋、回來找。
我在《神聖的你》、《不合理的快樂》也談過,人類過去的突破,都是透過心流帶出來的。無論哪個領域的突破,都是從心流出來的。
那麼,什麼是心流?
心流是非時間的狀態,是「在」,是沒有念頭。是把相對,完全交給絕對。或是反過來說,是絕對,帶著心,流出來種種的創意──創出一個作品,或一個突破。
當然,站在心的層面,沒有「誰」在做──嚴格講,也沒有人可以宣稱這是他的作品。假如誰還認為自己是一個作品的創作者,這樣的作品不會有長期的價值,更不用談永久的價值。
所以,非時間,其實並不抽象。每個文化也都有類似的表達──什麼叫做心,什麼叫做穩重、紮實。在所謂的「現代化」之前,社會的步調很慢。一個人如果步調快,像是情緒上反應快,例如急躁,或是動作很快,會被認為不紮實。坦白講,用我們現代人的步調活在古代,一定會被認為不夠穩重。甚至會被認為內心有很大的障礙,神經衰弱,或有什麼重大的疾病。從古人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的步調相當不正常,就好像每個人都放逐了自己,拋棄了自己。
古代社會的人,比較可以隨時體會到非時間的觀念,而自然停留在這個狀態,因為這是最舒暢、輕鬆、不費力的狀態。現代人凡事都用腦筋去想,反而是一個費力的過程。我過去在很多場合談到,如果父母希望孩子成為天才(對我,每個孩子本來就是天才),那麼,父母自己要懂得什麼是非時間,隨時帶他進入非時間的狀態。
換一個方式來說,修行,其實是從「動」到非時間的「不動」。透過臣服與參,最多是提醒我們自己,有個「不動」──非時間的永恆。
一個人假如懂了這一點,他其實不用參,也不用臣服,本來就隨時停留在這裡,臣服在這裡。
練習:肯定一切
我希望這本書不光帶來一個理論的架構,還可以讓非時間的永恆徹底落到我們心中,成為意識、潛意識的主要的部份。非時間的永恆,本來就是我們的本質,只是我們忘記了,才要用許多練習來提醒。提醒什麼?提醒──我們本來就有的。
我在過去的作品,尤其《我是誰》也已經帶出各式各樣的練習,當作一個提醒。無論臣服、參、I Am 的靜坐或其他方法,最多也只是帶來一個反復,讓我們踩一個剎車,提醒自己本來就知道、本來就在的狀態。
真實只有一個,我能做的,最多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在這本書的第19章到第36章,我會在每一章結尾安排一個練習,看你能不能一整天都進行。一開始,可能不熟練。沒有關係,對自己要有耐心。讓自己一再重複,慢慢熟悉。
這些練習,會不斷回到同樣的重點。即使我只稱這些練習為提醒,但是,不要小看這些提醒。就是因為生活中可以隨時進行,可以說比透過任何靜坐得到的隔離狀態更實用。隨時活出這些提醒,我們也就自然把人生當作最好的道場,無論醒著、睡覺,都可以不斷地展開──我們本來就有的狀態,最根本的狀態。這一章的練習,足以彙總這本書的重點。要進入這個練習,你要先體會以下幾點:
非時間,不是時間的相反。當下,也不是過去和未來的對稱。透過時間,要找到非時間,是不可能的。再進一步說,其實沒有一個東西可以稱作當下。假如有個東西叫作當下,每一個人早就活在當下。
非時間或當下,本身是一個絕對的觀念,不是在相對的時間領域可以找到的。雖然如此,只有透過每一個瞬間,我們才可以找到相對和絕對的交會。但是,這個交會點,倒不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瞬間。因為,每個人只要想起瞬間,其實已經過去了。所以,這個交會點,不是透過體驗、想或任何觀念可以描述。
這個交會點,最多只是來表達──時間和非時間,在每一個瞬間,都同時存在。而這個交會的點,不在瞬間,而是在我們的頭腦,或意識。我們的意識,落在哪一點──是相對,或是絕對──也就自然到了那一點。
講得更透明一些,假如我們隨時把自己的身分落在人間,我們每一個瞬間也跟著離不開這個世界。但是,只要我們把自己的身分從這個世界挪開,隨時知道「我」跟絕對分不開。我們每一個瞬間,也就跟著活起來,進入一個非時間的狀態。也就是那麼簡單。
還有另一個重點,隨時要提醒自己:
我們所看到、可以體會、可以想到的一切,全部都是果,倒沒有一個東西叫做因。就是有一個因,也不是我們可以體會到的。所以,去找因,永遠找不到。
只要我們肯定這個世界是真實,甚至認為自己所看到、所想、所體會、可以用語言描述的,樣樣都是絕對不變的存有,那麼,對我們而言,因-果當然存在。而且,樣樣離不開因-果。
因為我們可見的世界是因-果組合的,我常常說,最難懂的是,週邊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物,最終都是同一種東西的組合。而且,這個組合的源頭,也是因-果化出來的。在這樣的框架下,我們這一生可以活出來的,沒有一項不是因-果。人間的一切是註定,也沒有什麼東西叫做自由。
接下來的練習,最多只是透過我們每一個細胞,每一個領悟,每一個反應去知道、肯定、體會前面這些話。
面對任何事情,再好,再不好,都可以徹底去接受。接受的是──宇宙絕對不可能犯錯,一切都安排的剛剛好。面對任何災難,還是剛剛好。剛剛好,透過它們,我來到這裡現在,可以肯定一切都剛剛好。
即使我可以自由選擇,我最多也只會選擇每個瞬間所帶來的考驗和一切。而我充滿著自信,知道沒有一件事情我會希望轉變,也沒有任何想得、想追求的。
我充份知道,沒有一樣可以「做」的,能夠影響我本來就有的絕對。我本來就是絕對的存在。絕對本來就是我。只是因為忘記了,還需要做這些提醒。
一天, 重複幾次。就連剛睡醒,或要睡了,也不斷地做前面的提醒。
一開始,你可以把這幾句話讀出聲音來,幫助自己進入這個狀態。熟練了,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這些觀念帶出來,活進去。
一天下來,你可能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有時候不免會質疑這些話的正確性。這時候,這個練習特別重要──也就是接受眼前的不安、恐懼、質疑、憤怒、失落、反彈、追求。一樣的,也不斷接受自己還有許多問題──還有一個相對和絕對分別的觀念,還認為醒覺不可能那麼容易,還認為有一個練習可以讓自己醒覺。
不斷接受眼前的狀態,一個人自然就進入臣服。如果還有非時間和當下的觀念,也就承認自己還有這個狀態。
這些提醒和練習,雖然在其他的作品也談過。但我相信,走到現在,你的體會和它的力道,會跟以前完全不同。
把這個練習落到生活每一個角落,一個人自然體會到,一切人間的經過都是註定。雖然是註定,只要選擇接受一切,也就自然發現,在生命更深的層面,倒沒有什麼叫做註定或不註定。
透過肯定、接受每一個瞬間,我們自然跟生命的絕對接上頭。輕鬆而不費力,把我們意識的中心或注意力移到──絕對的層面。
The Burden of Time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只要談到時間,都有兩個直接的反應。首先,把它當作一個節律器,就像為生活定下節奏和步調,才可以衡量每一個規劃,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追求,每一個結果。但同時,它也帶給我們一種壓迫感,讓現代人總是感覺時間不夠用。
在這個不夠用的情況下,我們自然會想要一心多用──同一個時間,能處理愈多事愈好。透過快速的技術發展,我們可以同時停留在幾個知識的平台。不光有手機隨時可以通訊,還有電腦,同時還可以說話、寫字、和其他的運作。
不要說兩千年前的人,即使是五十年前的人,來到我們這個世界,也會嚇壞的。會認為每一個人的神經都過度激動,不只同時做好幾件事,而且步調快到想像不到,不要說跟不跟得上了。
我也發現,這個時間的重擔所波及的年齡層愈來愈下降。尤其華人,總是要充份利用時間,追求高效率,強調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麼要求自己還不夠,還要把這種追求延伸到下一代。一個孩子,只要懂事、進入小學,總是感覺跟不上,來不及。
讓我最同情的是,小孩子不光是睡不夠,在學校的時間長,功課多,家長的要求又加倍。就好像一上學,就要承擔週邊種種的期望和壓力。如果這個孩子自我要求又高,那麼時間的負擔更是沉重。
所以,我們過去看到是有了一定的年紀才有憂鬱症,例如事業受到打擊,或女士在產後、更年期的變化。然而,現在就連憂鬱症的發生年齡也不斷下降。幾歲的孩子就有憂鬱的症狀,甚至有自殺的念頭。我才會說憂鬱症是二十一世紀最嚴重的慢性病,而時間的重擔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要談時間的重擔,最多也就是「跟不上」。我們每個人都跟不上。一個人在跟不上的狀況下,自然會產生一個兩難。也就是說,在時間的壓迫下,我們認為隨時要有一個決策的備案,用來節省時間、解決時間帶來的壓力。這是我們每個人隨時在面對的。可惜,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步調自然會加快,而讓我們停不下來。就連休息的時候,還可能想要選擇快速的動,例如不光是看電視,還要對話快,鏡頭不斷的變化,或有暴力的刺激。晚上參加活動,要有大聲的音樂和熱鬧。這些娛樂的選擇,反映了我們個人對生活要求的快步調。
這樣子,別說休息時,慢不下來。就連睡覺的時候都停不下來,難怪那麼多人有失眠的問題。
我過去做為一個醫師、科學家,自然喜歡從機制或問題的根源著手。比如說,我當年研究免疫,就想知道殺手細胞和T細胞怎麼殺腫瘤。當時很年輕,很快把這個主題告一個段落,而且跟別人的切入點都不同。
現在,要切入時間這個主題,說時間是我們人類最寶貴的工具,也是我們最大的殺手,我認為這一點都不過份。我在這本書,希望可以再進一步打開──時間,其實跟我們人類的演化有密切的關係。這種觀點,或許你會認為是理所當然,因為歷史本來就是時間演變的記錄。但我要講的是,人類因為有時間的觀念,才有以後的發展。只是因為時間的觀念過度強化,自然擺盪到一個不均衡的狀態。
講了這些,即使把它解開,最多只是把症狀做個說明。我真正感興趣的,正如我過去所扮的角色,是希望找到一個徹底解答的方法。
第十九章 當下,不是過去和未來的對稱
Now is on a Different Scale Compared to Past and Future
回到當下,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嚴格講,它不是一個練習。
前面也提過,當下,其實不是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一個東西。讓我用這張圖來說明這個觀念──如果用翹翹板的兩端,各自代表過去和未來,那麼,當下並不是過去和未來的對等,而是完全落在不同的軌道。我在這裡,用一個螺旋來表達。
我之所以有勇氣,在這個時候出來談這些觀念,因為我認為──任何練習,無論是瑜伽、靜坐或所有傳統的練習,都還只是一個暫停(time out)的觀念,是一種專一、和其他狀態互斥的隔離狀態(exclusive state)。透過練習,即使有了這種狀態,早晚還是要回到人間。只有「全部生命系列」帶出來的臣服和參,不是一種暫停的隔離,而是進入非時間的永恆。讓非時間的永恆,和時間隨時交疊,同時存在。透過臣服與參,一個人不知不覺,隨時可以接受絕對與相對。甚至,可以輕輕鬆鬆滑回另一個軌道。我現在才會出來,甚至還帶出「反復工程」的觀念。
就是因為當下和時間的觀念是在兩個軌道,我們從任何瞬間,其實「回不到」當下。任何瞬間本來都有「絕對」,所以,「回到」當下,不是透過任何動力,而是剛好相反──最多把時間的觀念挪開,當下和非時間的永恆,自然就在眼前。
所以,談當下帶著我們走,最多也只是把非時間的永恆當作我們主要的意識層面,讓祂帶著我們走。心流,自然就流出來了。我們可以完成想不到的工作,儘管完成或不完成任何工作,也不重要。「全部生命系列」的寫作就是最好的實例。從我的角度,沒有刻意去「寫」任何一本書。最多只是把時間的觀念挪開,讓當下浮出來,想轉達什麼,也就自然出來了。
有意思的是,對我而言,沒有「誰」 在寫,寫起來也不費力,甚至連規劃也沒有。事後,看每一個作品,好像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的步調、邏輯就像是剛剛好。相信你讀這些作品時,也自然從非時間永恆的意識層面,延伸出一個理解。儘管這些話,對頭腦會不斷產生矛盾或悖論。但是,從心的層面,你知道這些話離不開真實。也因為如此,會不斷回來尋、回來找。
我在《神聖的你》、《不合理的快樂》也談過,人類過去的突破,都是透過心流帶出來的。無論哪個領域的突破,都是從心流出來的。
那麼,什麼是心流?
心流是非時間的狀態,是「在」,是沒有念頭。是把相對,完全交給絕對。或是反過來說,是絕對,帶著心,流出來種種的創意──創出一個作品,或一個突破。
當然,站在心的層面,沒有「誰」在做──嚴格講,也沒有人可以宣稱這是他的作品。假如誰還認為自己是一個作品的創作者,這樣的作品不會有長期的價值,更不用談永久的價值。
所以,非時間,其實並不抽象。每個文化也都有類似的表達──什麼叫做心,什麼叫做穩重、紮實。在所謂的「現代化」之前,社會的步調很慢。一個人如果步調快,像是情緒上反應快,例如急躁,或是動作很快,會被認為不紮實。坦白講,用我們現代人的步調活在古代,一定會被認為不夠穩重。甚至會被認為內心有很大的障礙,神經衰弱,或有什麼重大的疾病。從古人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的步調相當不正常,就好像每個人都放逐了自己,拋棄了自己。
古代社會的人,比較可以隨時體會到非時間的觀念,而自然停留在這個狀態,因為這是最舒暢、輕鬆、不費力的狀態。現代人凡事都用腦筋去想,反而是一個費力的過程。我過去在很多場合談到,如果父母希望孩子成為天才(對我,每個孩子本來就是天才),那麼,父母自己要懂得什麼是非時間,隨時帶他進入非時間的狀態。
換一個方式來說,修行,其實是從「動」到非時間的「不動」。透過臣服與參,最多是提醒我們自己,有個「不動」──非時間的永恆。
一個人假如懂了這一點,他其實不用參,也不用臣服,本來就隨時停留在這裡,臣服在這裡。
練習:肯定一切
我希望這本書不光帶來一個理論的架構,還可以讓非時間的永恆徹底落到我們心中,成為意識、潛意識的主要的部份。非時間的永恆,本來就是我們的本質,只是我們忘記了,才要用許多練習來提醒。提醒什麼?提醒──我們本來就有的。
我在過去的作品,尤其《我是誰》也已經帶出各式各樣的練習,當作一個提醒。無論臣服、參、I Am 的靜坐或其他方法,最多也只是帶來一個反復,讓我們踩一個剎車,提醒自己本來就知道、本來就在的狀態。
真實只有一個,我能做的,最多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在這本書的第19章到第36章,我會在每一章結尾安排一個練習,看你能不能一整天都進行。一開始,可能不熟練。沒有關係,對自己要有耐心。讓自己一再重複,慢慢熟悉。
這些練習,會不斷回到同樣的重點。即使我只稱這些練習為提醒,但是,不要小看這些提醒。就是因為生活中可以隨時進行,可以說比透過任何靜坐得到的隔離狀態更實用。隨時活出這些提醒,我們也就自然把人生當作最好的道場,無論醒著、睡覺,都可以不斷地展開──我們本來就有的狀態,最根本的狀態。這一章的練習,足以彙總這本書的重點。要進入這個練習,你要先體會以下幾點:
非時間,不是時間的相反。當下,也不是過去和未來的對稱。透過時間,要找到非時間,是不可能的。再進一步說,其實沒有一個東西可以稱作當下。假如有個東西叫作當下,每一個人早就活在當下。
非時間或當下,本身是一個絕對的觀念,不是在相對的時間領域可以找到的。雖然如此,只有透過每一個瞬間,我們才可以找到相對和絕對的交會。但是,這個交會點,倒不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瞬間。因為,每個人只要想起瞬間,其實已經過去了。所以,這個交會點,不是透過體驗、想或任何觀念可以描述。
這個交會點,最多只是來表達──時間和非時間,在每一個瞬間,都同時存在。而這個交會的點,不在瞬間,而是在我們的頭腦,或意識。我們的意識,落在哪一點──是相對,或是絕對──也就自然到了那一點。
講得更透明一些,假如我們隨時把自己的身分落在人間,我們每一個瞬間也跟著離不開這個世界。但是,只要我們把自己的身分從這個世界挪開,隨時知道「我」跟絕對分不開。我們每一個瞬間,也就跟著活起來,進入一個非時間的狀態。也就是那麼簡單。
還有另一個重點,隨時要提醒自己:
我們所看到、可以體會、可以想到的一切,全部都是果,倒沒有一個東西叫做因。就是有一個因,也不是我們可以體會到的。所以,去找因,永遠找不到。
只要我們肯定這個世界是真實,甚至認為自己所看到、所想、所體會、可以用語言描述的,樣樣都是絕對不變的存有,那麼,對我們而言,因-果當然存在。而且,樣樣離不開因-果。
因為我們可見的世界是因-果組合的,我常常說,最難懂的是,週邊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物,最終都是同一種東西的組合。而且,這個組合的源頭,也是因-果化出來的。在這樣的框架下,我們這一生可以活出來的,沒有一項不是因-果。人間的一切是註定,也沒有什麼東西叫做自由。
接下來的練習,最多只是透過我們每一個細胞,每一個領悟,每一個反應去知道、肯定、體會前面這些話。
面對任何事情,再好,再不好,都可以徹底去接受。接受的是──宇宙絕對不可能犯錯,一切都安排的剛剛好。面對任何災難,還是剛剛好。剛剛好,透過它們,我來到這裡現在,可以肯定一切都剛剛好。
即使我可以自由選擇,我最多也只會選擇每個瞬間所帶來的考驗和一切。而我充滿著自信,知道沒有一件事情我會希望轉變,也沒有任何想得、想追求的。
我充份知道,沒有一樣可以「做」的,能夠影響我本來就有的絕對。我本來就是絕對的存在。絕對本來就是我。只是因為忘記了,還需要做這些提醒。
一天, 重複幾次。就連剛睡醒,或要睡了,也不斷地做前面的提醒。
一開始,你可以把這幾句話讀出聲音來,幫助自己進入這個狀態。熟練了,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這些觀念帶出來,活進去。
一天下來,你可能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有時候不免會質疑這些話的正確性。這時候,這個練習特別重要──也就是接受眼前的不安、恐懼、質疑、憤怒、失落、反彈、追求。一樣的,也不斷接受自己還有許多問題──還有一個相對和絕對分別的觀念,還認為醒覺不可能那麼容易,還認為有一個練習可以讓自己醒覺。
不斷接受眼前的狀態,一個人自然就進入臣服。如果還有非時間和當下的觀念,也就承認自己還有這個狀態。
這些提醒和練習,雖然在其他的作品也談過。但我相信,走到現在,你的體會和它的力道,會跟以前完全不同。
把這個練習落到生活每一個角落,一個人自然體會到,一切人間的經過都是註定。雖然是註定,只要選擇接受一切,也就自然發現,在生命更深的層面,倒沒有什麼叫做註定或不註定。
透過肯定、接受每一個瞬間,我們自然跟生命的絕對接上頭。輕鬆而不費力,把我們意識的中心或注意力移到──絕對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