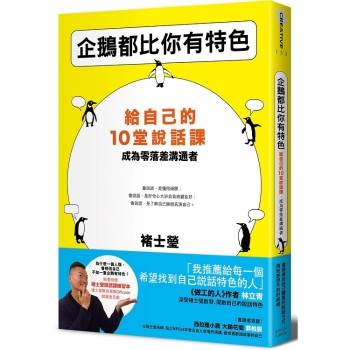第五課
學會說話,傳遞想法零落差
上台演講如何教我說話
誰說演講一定要用PPT?
最近有一位編輯朋友,提到她邀請台灣優秀的「工人作家」林立青,臨時錄一支一分鐘的宣傳短片時,他幾乎沒有花時間想,就開始錄,結果一次OK,時間也剛剛好。這位編輯非常驚訝,說他簡直帥到掉渣!
「我真沒想到,他是個這麼會說話的人!」
我聽了以後,想到一段小小的往事。
那是在林立青的第一本書《做工的人》剛剛出版的一個月後左右,短時間爆紅,開始演講邀約不斷。之前幾乎沒有站在台上演講經驗的他,在喝春酒的時候剛好坐在我的旁邊,非常謙虛地問我:
「演講應該怎麼準備……」
結果話還沒講完,我就打斷他說:「演講要好聽,只有一個重點:就是絕對不要用PPT。」
我在後來很久以後才知道,他原本要問我的問題完整句是:「演講應該怎麼準備PPT?」(笑)
他事後在臉書上回憶這段對話時這麼說:
「你用PPT只會讓自己偷懶,並且只會讓人覺得你照本宣科,一開始可能覺得很好用,但是你會養成依賴性,聽講者也會依賴,結果就是PPT成了主角,全場目光的焦點,連你都忘了自己才是主角。
如果從頭到尾都不用PPT,你就更可以專注地觀察聽眾的反應,和他們真正想要聽的故事,並且對你這個人的眼神,有很強烈的印象,而眼神才是演講者的最大武器,所以不用PPT的講者才是好講者。
不用擔心會忘記要講的內容,因為你真正想說的話,肯定不會忘掉,至於那些可以忘掉的話,就是多餘的。
還不知道他們要聽什麼嗎?那就鼓勵他們提問,自己仔細傾聽,比如有人問到工人受傷,哪需要簡報,當場往自己身上比就好啦!」
林立青說我當時回答他的方式,幾乎就是一場演講,一面說、一面幫他夾菜,整個過程都會有頓點,或是索性站起來用手腳比劃,讓他一直記得我當時的魅力和口條。從此以後,林立青說他所有的演講、座談,或者是討論分享,都完全沒有用PPT簡報。後來他發展出了一套非常適合自己的演講術:
要看曬傷嗎?我脫衣給你看。
要看濕疣嗎?你還可以摸我脖子。
要看工地平常穿衣嗎?我就一直都穿平常的衣服給你看。
想知道褲子為什麼要有很多口袋嗎?我當場掏鑰匙工具給你看。
想看腰包裡面有什麼嗎?我馬上解下來給你看看。
有了褚士瑩大哥傳授「現場神功」,我就再也不用費心一張一張的貼上照片還硬擠文字搭配說明了。
這還有一個好處,邀約的主辦單位根本不用費心搞一堆什麼電腦延長線、轉接線或是阿薩布魯的USB隨身碟,還怕你插進去時按到格式化或是檔案版本不對……最重要的是因為從一開始就學了褚士瑩大哥無簡報模式,所以也從來沒人批評過我的簡報做得不好看,這算另類的藏拙……
我很開心能夠看到一個如此有趣的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找到在台上演講時,表現自己最真實、最有溫度那一面的方法—這是無論再多精美的簡報,也無法取代的。
實際上,作為一個「前輩」,唯一能夠教給林立青的,也是長久以來,幫助我自己作為一個害羞的人,能夠順利在台上侃侃而談的方法。
這一套方法,讓我雖然每年只回台灣四次,每次停留兩個星期,但在這加起來六十天中,除了原本專業的NGO工作以外,仍然能夠以一天最多兩場,一年平均一百場演講的頻率,保持跟台灣社會各種面向的接觸。因為演講的關係,我面對面的對象從國內的公務人員,到來自國際的青年外交官;地點也從祖孫三代扶老攜幼的宮廟圖書館,到日本新興宗教的臥佛殿;內容從企業福委會為工程師宅男安排的職涯講座,到非營利組織裡專門為社工師舉辦的哲學思考訓練;聽眾也從上市公司的大企業老闆,到離島的原住民小學生。
因為題目不同,聽眾對象不同,客觀環境不同,社會氛圍不同,我自己的生命經驗不斷向前,因此對我來說每一場演講, 都是截然不同的有趣經驗。
多年以來,每年一百場,幾乎從來沒有兩場內容一模一樣的,並非我是一個口若懸河的演講家—因為我不是,而是我從來沒有把演講當成一件「工作」。
我只是教會了那個害羞的自己,走上講台,充分敞開自己,享受每一次獨一無二的經驗—無論作為聽眾,還是講者。
我不只在台上演講,我也喜歡在台下當聽眾。
我從來不覺得聽演講浪費時間。聽到一場好的演講,就像去芬威球場看一場紅襪隊對洋基隊的精采球賽。萬一聽到一場不好的演講,也會提醒我演講的時候,容易犯的錯誤,像一面鏡子,作為自己改進的借鏡。
演講的說話方法,不只幫助演講,也會大大幫助每一天日常生活的表達,讓自己的想法可以「零落差」地傳遞到聽者的耳朵。
一開始說就引起注意
身為一個以短篇小說創作開始,步上作家這條艱辛道路的作者,我從很早就意識到一個寫小說重要的原則:開頭第一句超重要!
因為讀者生活中有這麼多值得分心的選擇,不一定要看小說,就算看小說,書架上也有無數的選擇,如何讓一個讀者決定萬中選一,讀我寫的小說呢?除了第一句就引起濃厚的興趣之外,別無他法。
然而小說的開頭方式好像很多,其實歸納起來只有兩種:要不是因為「未知」引起濃濃的好奇心,像是去看球賽不知道紅襪隊跟洋基隊誰會贏,就是因為「已知」帶來的期待,像是去聽瑪丹娜的演唱會一定想要聽到的壓軸曲。
演講其實也一樣,演講者要針對聽眾的特質,決定他們是屬於好奇的「未知」型,還是期待的「已知」型。
為了要知道今天的聽眾屬於哪一種,我在演講一開始的時候,一定會先問聽眾一個問題。
如果聽眾看起來是青年、中生代,我會問:「我們曾經見過面的請舉手。」
如果聽眾的年齡差距很大,我會改問:「知道我是誰的請舉手。」
如果聽眾都很年輕,或是在學的學生,我則會問:「小時候在國語、國文課本上讀過我課文的請舉手。」
無論哪一個問法,如果舉手的人很多,那麼一定是屬於期待的「已知」型,我要抱著跟老朋友說話的口氣來進行這場演講。這麼問的好處是,我也因此可以很快地拉近那些沒有舉手的新朋友的距離,他們應該很驚訝看到身邊竟然有那麼多人舉手,所以也會從原先的「好奇」,轉為「期待」。
畢竟一般來說,人對於陌生的事物比較保持戒心、懷疑,但對於有點熟悉的事物,就會比較放鬆、信任。我想要一開始就創造那種放心、信任的氣氛。
如果我看一眼聽眾,這些人應該都是陌生人,那麼我就不會問這些問題。也有可能誤判,問了問題發現沒有人舉手,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用另種一方式取而代之,我會創造共同的經驗,像是對大家說剛剛來的路上好塞車啊!大家辛苦了!或是先說一下剛剛搭同一部電梯到演講會場時,我聽到大家在聊的話題。總之找到共同的經驗,就可以先拉近距離。
然後再立刻拉開距離。我會介紹我的工作,是一個在緬甸內戰的山區,教當地叛軍、武裝部隊,如何跟政府和平談判的NGO工作者。因為從來沒有人聽說過這樣的工作,也不知道這份工作在做什麼,所以會立刻讓本來不認識我的人,因此產生「好奇」。
開始的地基打得好,只要中間沒有出大錯,演講從一開始就能一錘定音。
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演講時使用PPT簡報,當然會有它的作用,比如說關鍵字是一個陌生的專有名詞,或是演講的內容是天文學的新發現,這種時候,語言能夠勾勒出來的「音風景」可能不夠具體,難以想像,就需要簡報的輔助。除此之外,我並不建議演講者大量使用PPT。
演講如果一開始,就把PPT簡報放在投影布幕上,演講就變成了一個準備充分的「表演」,有一定的招數跟套路,觀眾什麼時候該笑,什麼時候應該表現出驚奇,都在這份設計之中。
而且只要PPT張數越多,設計越精美,被「設計」的感受就會越強。
老實說,誰都不喜歡被設計,這樣感覺起來好蠢!
身為演講者,無論演講的內容是什麼,是失智症家屬的照顧,還是義大利的私房景點,我都必須確定,這是我非常深度了解的領域,而不是網路上查來的內容,或是主辦單位交給我的資料。而「我真的知道我在講什麼」最好的證據,就是能夠不需要PPT簡報,也能夠用說話表達,快速勾勒出一個清楚的藍圖,讓每個人都能夠在腦海裡看見那一幅圖畫。
「如果我對內容真的不熟悉,那怎麼辦呢?」
當有人這樣問我時,我就會非常誠實地告訴他:「那麼這就不是你應該要講的題目。」
只要這是一個你懂得很多的題目,你自然而然會顯得有自信,就算口才很糟糕,聽的人也會看到你的熱情,而真誠與熱情,能遮掩百分之九十九表達上的缺陷。
一期一會
我同時也是個謹守著「一期一會」哲學的人。
所謂的一期一會,就是把人與人的相逢,每一次都當作是第一次,也把每一次當作是最後一次。沒有什麼叫做「今天感冒,狀況不好,非常抱歉,我平常不是這樣子的」這種事,因為這一次,極有可能就是我們這輩子唯一一次的見面。無論今天的狀態多麼特殊,前一晚失眠,花粉過敏,剛剛來的路上被警察開罰單心情不好,或是牙齒痛到不行……無論任何原因,沒有辦法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別忘了很可能根本不會有下次,所以這次我們給對方的印象,將是他這輩子對於我這個人全部的印象了。
我在當配音員的時候,特別害怕感冒。但工作就是工作,所以就算一面咳嗽,聲音充滿了鼻音,喉嚨沙啞,還是要硬著頭皮把百貨公司週年慶的廣告完成。
讓人驚訝的是,除了我自己跟錄音師之外,無論客戶還是聽到廣播的路人,似乎沒人發現我感冒超嚴重—他們之所以不介意,搞不好是因為誤以為我的聲音本來就這麼沙啞富磁性。
「他們誤會我了嗎?」或許。
「我需要解釋嗎?」大可不必。
不必要解釋的原因有三個:第一,這樣也沒什麼不好。他們誤以為我的聲音就是這樣,但也不盡然是錯的,因為即使喉嚨沙啞的聲音,也確實是我的聲音,只不過並非我心目中認為自己最好的聲音罷了。說不定比起我自己認為好聽的聲音,有人更喜歡這樣的聲音?
第二,我的解釋,極有可能是多餘的。如果這個人,這輩子不會再遇到我第二次,他真的有需要知道我的聲音,跟平常不一樣嗎?
第三,我可能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人們不是為了我的聲音來聽演講的,而是為了內容。因為我不是歌劇界的美聲天王天后,聽眾一定不是為了來聽我的聲音,所以我如果應該向他們抱歉的話,是為我的內容不夠好道歉,而不應該是我的聲音不夠好。
想清楚了以後,抱著這樣「一期一會」的覺悟,場地可能不夠好,麥克風有問題,我的狀態不佳,準備不充分(有不止一次,我到了現場,才發現題目跟我知道的不一樣!)但我都得下一個決定:「無論如何,現在就是我們唯一的時間,而這裡就是我們唯一會相聚的地方,就是這樣了。現在,我該如何透過說話表現自己?」
然後,一切就變得清楚、簡單多了。
知道聽眾為什麼會來
你知道這個人為什麼會來聽你說話嗎?
收高昂費用的演講、收低廉費用的演講、收費但票價可以當場折抵消費的演講、不收費但收訂金的演講,還有不收費但是要預約的演講,以及完全不收費也不用預約的演講,每一種吸引來的聽眾型態都非常不同,期待也不同。
就像明明同是大提琴家,用同一把琴演奏同樣的曲目,付了很高的價格在人數有限的藝文沙龍裡聽,跟正好路過聽到一個街頭藝人在路邊拉琴,我們的態度跟期待就會完全不同,一個可能是「什麼!原來馬友友也不過如此!」而另一個則是「今天能讓我聽到,真的太幸運了!」
演講也是一樣,如果不知道聽眾的期待跟態度,演講者也一定不可能對聽眾說該說的話。
演講還有一種非常常見的聽眾,是「不得不」參加的。
公司舉辦的,以後還想混的員工不敢不參加。
被男女朋友拉來參加,其實一點都沒興趣。
學校規定當作上課,不但要參加,而且要點名,寫心得報告。
缺少服務學習時數、公務人員講習時數、教師進修時數,因此只是來簽到、簽退。
或者是保險公司、直銷公司拿「聽演講」來當作吸引潛在客戶的銷售工具。
也有可能因為送餐盒,會後憑入場票根還有誘人的摸彩。
演講者如果假裝台下的人,都應該興致勃勃來聽演講,很難不失望,因為這些人會滑手機、聊天、睡覺,不時進進出出,用各種積極的抵抗來破壞整體的氣氛。
所以我必須從一開始,就得到這類聽眾的注意。
最好的方式,就是我知道他們的存在,並且同理他們的處境。
「雖然我是因為自己真的想來,所以今天才會出現在這裡,但我知道其實很多人是不得不來的。」
如果我判斷這樣的人數比例高的時候,會在一開始就請他們從自己的經驗裡面來搜尋。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一本你原本不可能會從書架上選來看的書,或一部你不會去戲院看的電影,可是因為你很信任的人推薦,半信半疑之下看了,結果出乎意外,覺得很喜歡?」
我希望透過這個貼近生活的經驗,讓這些不想來,但無論什麼原因,已經坐在台下的人知道,今天可能就是另一次這樣誤打誤撞的美好經驗。
「希望從現在開始兩個小時,當我們要結束時,你會同樣有那種『啊!還好我有來!』的感受!」我笑著拍自己的胸脯,「至於能不能做到,這任務就交給我吧!」
用每個聽眾都聽得懂的語言,表現出對於他們處境的同理之後,我把成敗的責任攬到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像很多學校的老師,總是自我感覺太過良好,認為學生不認真聽或聽不懂,一定是學生的問題,而不是自己講得不好。
知道別人聽到的是什麼
無論老師或是上司,時常以比較高的姿態,讓我們不得不安靜聽他們說話,但是他們卻往往沉浸在自己做的PPT簡報,或想要急於表達的觀念,對聽眾的想法不感好奇,所以不在乎聽的人聽到了什麼,或聽到以後內心怎麼想。
即使在很專心的時候,我們只看過一遍的文章段落,都不見得能夠立刻了解,需要慢下來,回頭反覆咀嚼,更何況是在充滿讓人分心因素的演講場合,台上的人只匆匆帶過的話語呢?
因此我會提醒自己,說的時候,把自己當作聽的人,「把複雜的話變簡單」「簡短」,並且「對於對方聽到什麼,抱持真心的好奇」。
1‧複雜→簡單
什麼是「把複雜的話變簡單」?媽媽往往會幫我們把一整顆蘋果削成剛好一口一片,容易拿取、容易入口的小塊,在英語裡叫做「bite size」,意思就是「剛好一口的分量」。並不是一整顆蘋果不能夠直接拿起來啃,而是如果沒有人削成剛好一口的分量,很多時候我們就會因為懶得吃而放棄,或吃得很狼狽,而減少去吃的慾望—即使那個東西本身是美味的。
所以我會限制自己說話的內容,保持簡單,一次只提一個理念,確保我說的每一句,都是「剛好一口的分量」。
與其太貪心,覺得自己想說的每個觀念都好重要,造成消化不良,還不如確定一次一口,能夠徹底欣賞那一口的美味,仔細咀嚼,心滿意足地吞下去。
「簡單」很重要,我們想要傳達的想法和理念,都應該盡量保持簡單,可以清楚看得出原形。所以吃蘋果的時候,就知道自己確實在吃蘋果,而不是用荔枝果汁浸泡過後、再蘸抹茶鹽的蘋果。雖然那些元素分開來都有可能是好東西,而且是創意的組合,甚至對我們自己來說超級美味,但這麼複雜的組合,只有自己清楚,因為是自己想出來的。然而別人幾乎不可能記住艱澀又困難的「泡過荔枝水、蘸了京都抹茶鹽的完美蘋果片」,讓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簡單的概念,或簡單幾句話就能闡述清楚的一小片好吃的蘋果。
2‧長篇大論→簡短
不只「簡單」,還要「簡短」。知名的TED演說,規定一場演講需在十八分鐘內完畢,就是因為過長的時間,聽眾的注意力會分散。
因此,認為自己口才不好的人,保持簡單的演說長度,有很大的好處。不只在台上,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如此。
在職場上,不管是和老闆簡報工作內容、向客戶提案、銷售產品或為顧客提供服務,還是在會議中發言、向內部同事分享經驗、做教育訓練等等,這些場合的說話內容,都不會、也不該是兩個鐘頭的演說,而是區區幾分鐘的短講。
即使我在做兩、三個小時的演說時,也常常故意細分成「十點」主題,讓每一個十分鐘都是一場單獨的小演講。不但完整性高,而且顧慮到演講的時候,隨時有人突然放空,睡著突然醒來,去上洗手間、喝水;有人塞車晚到,有人必須早走去接孩子。這樣一來,就算錯過其中一些單元,但是因為每個小單元很簡短、很獨立,發現自己隨時都可以接得上,效果就會更好。
3‧不是炫耀知識而是激發好奇
至於為什麼要「對於對方聽到什麼,抱持真心的好奇」,是因為我們說話的時候,有一個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往往把精力花在我們自己想說的事情上,而不是別人真正想要知道的事情。
從小到大在課堂上,一定有很多這樣的經驗:老師在台上,獨自決定學生需要聽到什麼,而且一直趕進度,卻忘了問學生聽到了什麼。結果我們就在老師的好意之下,痛苦地接受了很多我們並不想學的事,或是一知半解、甚至錯誤的知識。
但當有一天,換成我們自己站在台上說話的時候,卻時常忘了那種痛苦的感覺,把精神花在準備簡報PPT,像個認真的好老師那樣,專注在自己要講什麼,而沒有從坐在台下的人的角度來想:如果我是聽眾,我會想聽到什麼?
別忘了給聽眾一個「我為什麼應該關心這件事」的理由。
要將一個理念帶給台下聽眾,需要讓聽眾的腦袋願意接納我,最好的方法是把我想說的事,跟他的生活經驗產生連結,激起觀眾的好奇心。
「泡過荔枝水、蘸了京都抹茶鹽的完美蘋果片」,就是可以激發台灣人好奇心的描述。大多數台灣人,尤其在南部,都曾在夜市吃過當場調味的芭樂,先在濃縮的金桔果汁中稍微浸泡醃漬,再撒甘草梅粉。所以我描述的經驗雖然是全新的,但很容易轉換,而且立刻燃起內在的「美食魂」,想要知道「泡過荔枝水、蘸了京都抹茶鹽的完美蘋果片」究竟是什麼味道的慾望,想要回家以後趕快嘗試看看,化為行動,而且知道該怎麼做。
我相信一個好的講者,不是重新去建構一個宇宙,而是透過說話,點出別人的世界觀裡的一處知識斷裂點,讓他們感受到橋接知識的必要。
畢竟演講不是為了要炫耀講者豐富的知識,而是要把知識傳達給台下的人,所以盡量用比喻或抽換成夠簡單、但觀念相近的例子來解釋,讓聽眾感同身受,產生情感上的連結,才能幫觀眾連接那個知識的斷裂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知道怎麼當一個好老師」。
學會說話,傳遞想法零落差
上台演講如何教我說話
誰說演講一定要用PPT?
最近有一位編輯朋友,提到她邀請台灣優秀的「工人作家」林立青,臨時錄一支一分鐘的宣傳短片時,他幾乎沒有花時間想,就開始錄,結果一次OK,時間也剛剛好。這位編輯非常驚訝,說他簡直帥到掉渣!
「我真沒想到,他是個這麼會說話的人!」
我聽了以後,想到一段小小的往事。
那是在林立青的第一本書《做工的人》剛剛出版的一個月後左右,短時間爆紅,開始演講邀約不斷。之前幾乎沒有站在台上演講經驗的他,在喝春酒的時候剛好坐在我的旁邊,非常謙虛地問我:
「演講應該怎麼準備……」
結果話還沒講完,我就打斷他說:「演講要好聽,只有一個重點:就是絕對不要用PPT。」
我在後來很久以後才知道,他原本要問我的問題完整句是:「演講應該怎麼準備PPT?」(笑)
他事後在臉書上回憶這段對話時這麼說:
「你用PPT只會讓自己偷懶,並且只會讓人覺得你照本宣科,一開始可能覺得很好用,但是你會養成依賴性,聽講者也會依賴,結果就是PPT成了主角,全場目光的焦點,連你都忘了自己才是主角。
如果從頭到尾都不用PPT,你就更可以專注地觀察聽眾的反應,和他們真正想要聽的故事,並且對你這個人的眼神,有很強烈的印象,而眼神才是演講者的最大武器,所以不用PPT的講者才是好講者。
不用擔心會忘記要講的內容,因為你真正想說的話,肯定不會忘掉,至於那些可以忘掉的話,就是多餘的。
還不知道他們要聽什麼嗎?那就鼓勵他們提問,自己仔細傾聽,比如有人問到工人受傷,哪需要簡報,當場往自己身上比就好啦!」
林立青說我當時回答他的方式,幾乎就是一場演講,一面說、一面幫他夾菜,整個過程都會有頓點,或是索性站起來用手腳比劃,讓他一直記得我當時的魅力和口條。從此以後,林立青說他所有的演講、座談,或者是討論分享,都完全沒有用PPT簡報。後來他發展出了一套非常適合自己的演講術:
要看曬傷嗎?我脫衣給你看。
要看濕疣嗎?你還可以摸我脖子。
要看工地平常穿衣嗎?我就一直都穿平常的衣服給你看。
想知道褲子為什麼要有很多口袋嗎?我當場掏鑰匙工具給你看。
想看腰包裡面有什麼嗎?我馬上解下來給你看看。
有了褚士瑩大哥傳授「現場神功」,我就再也不用費心一張一張的貼上照片還硬擠文字搭配說明了。
這還有一個好處,邀約的主辦單位根本不用費心搞一堆什麼電腦延長線、轉接線或是阿薩布魯的USB隨身碟,還怕你插進去時按到格式化或是檔案版本不對……最重要的是因為從一開始就學了褚士瑩大哥無簡報模式,所以也從來沒人批評過我的簡報做得不好看,這算另類的藏拙……
我很開心能夠看到一個如此有趣的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找到在台上演講時,表現自己最真實、最有溫度那一面的方法—這是無論再多精美的簡報,也無法取代的。
實際上,作為一個「前輩」,唯一能夠教給林立青的,也是長久以來,幫助我自己作為一個害羞的人,能夠順利在台上侃侃而談的方法。
這一套方法,讓我雖然每年只回台灣四次,每次停留兩個星期,但在這加起來六十天中,除了原本專業的NGO工作以外,仍然能夠以一天最多兩場,一年平均一百場演講的頻率,保持跟台灣社會各種面向的接觸。因為演講的關係,我面對面的對象從國內的公務人員,到來自國際的青年外交官;地點也從祖孫三代扶老攜幼的宮廟圖書館,到日本新興宗教的臥佛殿;內容從企業福委會為工程師宅男安排的職涯講座,到非營利組織裡專門為社工師舉辦的哲學思考訓練;聽眾也從上市公司的大企業老闆,到離島的原住民小學生。
因為題目不同,聽眾對象不同,客觀環境不同,社會氛圍不同,我自己的生命經驗不斷向前,因此對我來說每一場演講, 都是截然不同的有趣經驗。
多年以來,每年一百場,幾乎從來沒有兩場內容一模一樣的,並非我是一個口若懸河的演講家—因為我不是,而是我從來沒有把演講當成一件「工作」。
我只是教會了那個害羞的自己,走上講台,充分敞開自己,享受每一次獨一無二的經驗—無論作為聽眾,還是講者。
我不只在台上演講,我也喜歡在台下當聽眾。
我從來不覺得聽演講浪費時間。聽到一場好的演講,就像去芬威球場看一場紅襪隊對洋基隊的精采球賽。萬一聽到一場不好的演講,也會提醒我演講的時候,容易犯的錯誤,像一面鏡子,作為自己改進的借鏡。
演講的說話方法,不只幫助演講,也會大大幫助每一天日常生活的表達,讓自己的想法可以「零落差」地傳遞到聽者的耳朵。
一開始說就引起注意
身為一個以短篇小說創作開始,步上作家這條艱辛道路的作者,我從很早就意識到一個寫小說重要的原則:開頭第一句超重要!
因為讀者生活中有這麼多值得分心的選擇,不一定要看小說,就算看小說,書架上也有無數的選擇,如何讓一個讀者決定萬中選一,讀我寫的小說呢?除了第一句就引起濃厚的興趣之外,別無他法。
然而小說的開頭方式好像很多,其實歸納起來只有兩種:要不是因為「未知」引起濃濃的好奇心,像是去看球賽不知道紅襪隊跟洋基隊誰會贏,就是因為「已知」帶來的期待,像是去聽瑪丹娜的演唱會一定想要聽到的壓軸曲。
演講其實也一樣,演講者要針對聽眾的特質,決定他們是屬於好奇的「未知」型,還是期待的「已知」型。
為了要知道今天的聽眾屬於哪一種,我在演講一開始的時候,一定會先問聽眾一個問題。
如果聽眾看起來是青年、中生代,我會問:「我們曾經見過面的請舉手。」
如果聽眾的年齡差距很大,我會改問:「知道我是誰的請舉手。」
如果聽眾都很年輕,或是在學的學生,我則會問:「小時候在國語、國文課本上讀過我課文的請舉手。」
無論哪一個問法,如果舉手的人很多,那麼一定是屬於期待的「已知」型,我要抱著跟老朋友說話的口氣來進行這場演講。這麼問的好處是,我也因此可以很快地拉近那些沒有舉手的新朋友的距離,他們應該很驚訝看到身邊竟然有那麼多人舉手,所以也會從原先的「好奇」,轉為「期待」。
畢竟一般來說,人對於陌生的事物比較保持戒心、懷疑,但對於有點熟悉的事物,就會比較放鬆、信任。我想要一開始就創造那種放心、信任的氣氛。
如果我看一眼聽眾,這些人應該都是陌生人,那麼我就不會問這些問題。也有可能誤判,問了問題發現沒有人舉手,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用另種一方式取而代之,我會創造共同的經驗,像是對大家說剛剛來的路上好塞車啊!大家辛苦了!或是先說一下剛剛搭同一部電梯到演講會場時,我聽到大家在聊的話題。總之找到共同的經驗,就可以先拉近距離。
然後再立刻拉開距離。我會介紹我的工作,是一個在緬甸內戰的山區,教當地叛軍、武裝部隊,如何跟政府和平談判的NGO工作者。因為從來沒有人聽說過這樣的工作,也不知道這份工作在做什麼,所以會立刻讓本來不認識我的人,因此產生「好奇」。
開始的地基打得好,只要中間沒有出大錯,演講從一開始就能一錘定音。
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演講時使用PPT簡報,當然會有它的作用,比如說關鍵字是一個陌生的專有名詞,或是演講的內容是天文學的新發現,這種時候,語言能夠勾勒出來的「音風景」可能不夠具體,難以想像,就需要簡報的輔助。除此之外,我並不建議演講者大量使用PPT。
演講如果一開始,就把PPT簡報放在投影布幕上,演講就變成了一個準備充分的「表演」,有一定的招數跟套路,觀眾什麼時候該笑,什麼時候應該表現出驚奇,都在這份設計之中。
而且只要PPT張數越多,設計越精美,被「設計」的感受就會越強。
老實說,誰都不喜歡被設計,這樣感覺起來好蠢!
身為演講者,無論演講的內容是什麼,是失智症家屬的照顧,還是義大利的私房景點,我都必須確定,這是我非常深度了解的領域,而不是網路上查來的內容,或是主辦單位交給我的資料。而「我真的知道我在講什麼」最好的證據,就是能夠不需要PPT簡報,也能夠用說話表達,快速勾勒出一個清楚的藍圖,讓每個人都能夠在腦海裡看見那一幅圖畫。
「如果我對內容真的不熟悉,那怎麼辦呢?」
當有人這樣問我時,我就會非常誠實地告訴他:「那麼這就不是你應該要講的題目。」
只要這是一個你懂得很多的題目,你自然而然會顯得有自信,就算口才很糟糕,聽的人也會看到你的熱情,而真誠與熱情,能遮掩百分之九十九表達上的缺陷。
一期一會
我同時也是個謹守著「一期一會」哲學的人。
所謂的一期一會,就是把人與人的相逢,每一次都當作是第一次,也把每一次當作是最後一次。沒有什麼叫做「今天感冒,狀況不好,非常抱歉,我平常不是這樣子的」這種事,因為這一次,極有可能就是我們這輩子唯一一次的見面。無論今天的狀態多麼特殊,前一晚失眠,花粉過敏,剛剛來的路上被警察開罰單心情不好,或是牙齒痛到不行……無論任何原因,沒有辦法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別忘了很可能根本不會有下次,所以這次我們給對方的印象,將是他這輩子對於我這個人全部的印象了。
我在當配音員的時候,特別害怕感冒。但工作就是工作,所以就算一面咳嗽,聲音充滿了鼻音,喉嚨沙啞,還是要硬著頭皮把百貨公司週年慶的廣告完成。
讓人驚訝的是,除了我自己跟錄音師之外,無論客戶還是聽到廣播的路人,似乎沒人發現我感冒超嚴重—他們之所以不介意,搞不好是因為誤以為我的聲音本來就這麼沙啞富磁性。
「他們誤會我了嗎?」或許。
「我需要解釋嗎?」大可不必。
不必要解釋的原因有三個:第一,這樣也沒什麼不好。他們誤以為我的聲音就是這樣,但也不盡然是錯的,因為即使喉嚨沙啞的聲音,也確實是我的聲音,只不過並非我心目中認為自己最好的聲音罷了。說不定比起我自己認為好聽的聲音,有人更喜歡這樣的聲音?
第二,我的解釋,極有可能是多餘的。如果這個人,這輩子不會再遇到我第二次,他真的有需要知道我的聲音,跟平常不一樣嗎?
第三,我可能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人們不是為了我的聲音來聽演講的,而是為了內容。因為我不是歌劇界的美聲天王天后,聽眾一定不是為了來聽我的聲音,所以我如果應該向他們抱歉的話,是為我的內容不夠好道歉,而不應該是我的聲音不夠好。
想清楚了以後,抱著這樣「一期一會」的覺悟,場地可能不夠好,麥克風有問題,我的狀態不佳,準備不充分(有不止一次,我到了現場,才發現題目跟我知道的不一樣!)但我都得下一個決定:「無論如何,現在就是我們唯一的時間,而這裡就是我們唯一會相聚的地方,就是這樣了。現在,我該如何透過說話表現自己?」
然後,一切就變得清楚、簡單多了。
知道聽眾為什麼會來
你知道這個人為什麼會來聽你說話嗎?
收高昂費用的演講、收低廉費用的演講、收費但票價可以當場折抵消費的演講、不收費但收訂金的演講,還有不收費但是要預約的演講,以及完全不收費也不用預約的演講,每一種吸引來的聽眾型態都非常不同,期待也不同。
就像明明同是大提琴家,用同一把琴演奏同樣的曲目,付了很高的價格在人數有限的藝文沙龍裡聽,跟正好路過聽到一個街頭藝人在路邊拉琴,我們的態度跟期待就會完全不同,一個可能是「什麼!原來馬友友也不過如此!」而另一個則是「今天能讓我聽到,真的太幸運了!」
演講也是一樣,如果不知道聽眾的期待跟態度,演講者也一定不可能對聽眾說該說的話。
演講還有一種非常常見的聽眾,是「不得不」參加的。
公司舉辦的,以後還想混的員工不敢不參加。
被男女朋友拉來參加,其實一點都沒興趣。
學校規定當作上課,不但要參加,而且要點名,寫心得報告。
缺少服務學習時數、公務人員講習時數、教師進修時數,因此只是來簽到、簽退。
或者是保險公司、直銷公司拿「聽演講」來當作吸引潛在客戶的銷售工具。
也有可能因為送餐盒,會後憑入場票根還有誘人的摸彩。
演講者如果假裝台下的人,都應該興致勃勃來聽演講,很難不失望,因為這些人會滑手機、聊天、睡覺,不時進進出出,用各種積極的抵抗來破壞整體的氣氛。
所以我必須從一開始,就得到這類聽眾的注意。
最好的方式,就是我知道他們的存在,並且同理他們的處境。
「雖然我是因為自己真的想來,所以今天才會出現在這裡,但我知道其實很多人是不得不來的。」
如果我判斷這樣的人數比例高的時候,會在一開始就請他們從自己的經驗裡面來搜尋。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一本你原本不可能會從書架上選來看的書,或一部你不會去戲院看的電影,可是因為你很信任的人推薦,半信半疑之下看了,結果出乎意外,覺得很喜歡?」
我希望透過這個貼近生活的經驗,讓這些不想來,但無論什麼原因,已經坐在台下的人知道,今天可能就是另一次這樣誤打誤撞的美好經驗。
「希望從現在開始兩個小時,當我們要結束時,你會同樣有那種『啊!還好我有來!』的感受!」我笑著拍自己的胸脯,「至於能不能做到,這任務就交給我吧!」
用每個聽眾都聽得懂的語言,表現出對於他們處境的同理之後,我把成敗的責任攬到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像很多學校的老師,總是自我感覺太過良好,認為學生不認真聽或聽不懂,一定是學生的問題,而不是自己講得不好。
知道別人聽到的是什麼
無論老師或是上司,時常以比較高的姿態,讓我們不得不安靜聽他們說話,但是他們卻往往沉浸在自己做的PPT簡報,或想要急於表達的觀念,對聽眾的想法不感好奇,所以不在乎聽的人聽到了什麼,或聽到以後內心怎麼想。
即使在很專心的時候,我們只看過一遍的文章段落,都不見得能夠立刻了解,需要慢下來,回頭反覆咀嚼,更何況是在充滿讓人分心因素的演講場合,台上的人只匆匆帶過的話語呢?
因此我會提醒自己,說的時候,把自己當作聽的人,「把複雜的話變簡單」「簡短」,並且「對於對方聽到什麼,抱持真心的好奇」。
1‧複雜→簡單
什麼是「把複雜的話變簡單」?媽媽往往會幫我們把一整顆蘋果削成剛好一口一片,容易拿取、容易入口的小塊,在英語裡叫做「bite size」,意思就是「剛好一口的分量」。並不是一整顆蘋果不能夠直接拿起來啃,而是如果沒有人削成剛好一口的分量,很多時候我們就會因為懶得吃而放棄,或吃得很狼狽,而減少去吃的慾望—即使那個東西本身是美味的。
所以我會限制自己說話的內容,保持簡單,一次只提一個理念,確保我說的每一句,都是「剛好一口的分量」。
與其太貪心,覺得自己想說的每個觀念都好重要,造成消化不良,還不如確定一次一口,能夠徹底欣賞那一口的美味,仔細咀嚼,心滿意足地吞下去。
「簡單」很重要,我們想要傳達的想法和理念,都應該盡量保持簡單,可以清楚看得出原形。所以吃蘋果的時候,就知道自己確實在吃蘋果,而不是用荔枝果汁浸泡過後、再蘸抹茶鹽的蘋果。雖然那些元素分開來都有可能是好東西,而且是創意的組合,甚至對我們自己來說超級美味,但這麼複雜的組合,只有自己清楚,因為是自己想出來的。然而別人幾乎不可能記住艱澀又困難的「泡過荔枝水、蘸了京都抹茶鹽的完美蘋果片」,讓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簡單的概念,或簡單幾句話就能闡述清楚的一小片好吃的蘋果。
2‧長篇大論→簡短
不只「簡單」,還要「簡短」。知名的TED演說,規定一場演講需在十八分鐘內完畢,就是因為過長的時間,聽眾的注意力會分散。
因此,認為自己口才不好的人,保持簡單的演說長度,有很大的好處。不只在台上,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如此。
在職場上,不管是和老闆簡報工作內容、向客戶提案、銷售產品或為顧客提供服務,還是在會議中發言、向內部同事分享經驗、做教育訓練等等,這些場合的說話內容,都不會、也不該是兩個鐘頭的演說,而是區區幾分鐘的短講。
即使我在做兩、三個小時的演說時,也常常故意細分成「十點」主題,讓每一個十分鐘都是一場單獨的小演講。不但完整性高,而且顧慮到演講的時候,隨時有人突然放空,睡著突然醒來,去上洗手間、喝水;有人塞車晚到,有人必須早走去接孩子。這樣一來,就算錯過其中一些單元,但是因為每個小單元很簡短、很獨立,發現自己隨時都可以接得上,效果就會更好。
3‧不是炫耀知識而是激發好奇
至於為什麼要「對於對方聽到什麼,抱持真心的好奇」,是因為我們說話的時候,有一個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往往把精力花在我們自己想說的事情上,而不是別人真正想要知道的事情。
從小到大在課堂上,一定有很多這樣的經驗:老師在台上,獨自決定學生需要聽到什麼,而且一直趕進度,卻忘了問學生聽到了什麼。結果我們就在老師的好意之下,痛苦地接受了很多我們並不想學的事,或是一知半解、甚至錯誤的知識。
但當有一天,換成我們自己站在台上說話的時候,卻時常忘了那種痛苦的感覺,把精神花在準備簡報PPT,像個認真的好老師那樣,專注在自己要講什麼,而沒有從坐在台下的人的角度來想:如果我是聽眾,我會想聽到什麼?
別忘了給聽眾一個「我為什麼應該關心這件事」的理由。
要將一個理念帶給台下聽眾,需要讓聽眾的腦袋願意接納我,最好的方法是把我想說的事,跟他的生活經驗產生連結,激起觀眾的好奇心。
「泡過荔枝水、蘸了京都抹茶鹽的完美蘋果片」,就是可以激發台灣人好奇心的描述。大多數台灣人,尤其在南部,都曾在夜市吃過當場調味的芭樂,先在濃縮的金桔果汁中稍微浸泡醃漬,再撒甘草梅粉。所以我描述的經驗雖然是全新的,但很容易轉換,而且立刻燃起內在的「美食魂」,想要知道「泡過荔枝水、蘸了京都抹茶鹽的完美蘋果片」究竟是什麼味道的慾望,想要回家以後趕快嘗試看看,化為行動,而且知道該怎麼做。
我相信一個好的講者,不是重新去建構一個宇宙,而是透過說話,點出別人的世界觀裡的一處知識斷裂點,讓他們感受到橋接知識的必要。
畢竟演講不是為了要炫耀講者豐富的知識,而是要把知識傳達給台下的人,所以盡量用比喻或抽換成夠簡單、但觀念相近的例子來解釋,讓聽眾感同身受,產生情感上的連結,才能幫觀眾連接那個知識的斷裂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知道怎麼當一個好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