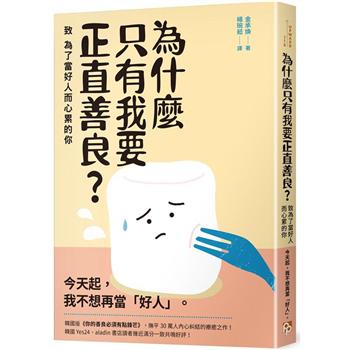要多麼張牙舞爪地對待彼此?
我當時只是需要關心
「我不會再見爸爸了,這樣比邊恨死他邊過活還好不是嗎?」
尚未擺脫稚氣的二十出頭青年尚旭說出了這句讓人倍感衝擊的話語,看起來像是平靜無波地度過了青少年時期且過著平凡生活的他,卻懷著對父親以及其他家人的憤怒。尚旭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積極活潑的性格,但卻出乎意料地連一個好朋友都沒有,既不能將心裡話坦誠相告,也不懂得如何與他人建立深厚聯繫, 雖然心裡很辛苦,但卻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尚旭很勉強地向我吐露了他的家庭故事。
尚旭的妹妹在小時候因為意外的關係而成了殘障人士,自從那之後父母就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照顧女兒這件事上,在尚旭有需要的時候,父母連一次都沒有守護在尚旭的身邊過,連小學的入學典禮都因為妹妹的關係,是尚旭自己一個人獨自參加的,尚旭為了想得到父母的關心而偷了朋友的錢,儘管當時是抱持著想要受到父母關注的心情而這麼做的,但尚旭得到的卻是「連你也要這麼讓人操心的話是要我怎麼辦才好!」的訓斥以及父親嚴厲的體罰。
父親的體罰並不是尚旭想要的「關愛」,尚旭因為太過埋怨和討厭獨占了父母的妹妹,在忍無可忍之下緊緊掐住了妹妹的脖子,最後被看到這一幕的父親打個半死。尚旭的心願是趕快賺錢然後離開父親,更準確來說,是想要擺脫這個令他感到厭煩的家庭。從未被家人好好接納過的尚旭,與世界也築起一道厚實的牆。
離開家人的話,就能夠從心靈的痛苦中解脫嗎?
我問尚旭:
「離開家人的話就能從父親那裡解脫嗎?」
「能!這是當然的啊。」
聽到這個充滿確信的答案讓我感到很心痛,古云「去者日以疏」,意味著眼不見,心境上也會逐漸疏離,尚旭的情況也能適用嗎?如果真的能如此的話那該有多好呢?
從家人那裡受到的傷害會在我們的靈魂深處留下疤痕,並不會因為沒看見就輕易消失,就算因為害怕、因為討厭而迴避,還是會執拗地留下影響,我們的生活、思考方式、人際關係等,所有的面向都會受到影響。我們的自尊感會因為傷痛而逐漸降低,而降低的自尊感又會讓我們無法走向世界,如此一來這種惡性循環就會持續下去。如果因為家人而受到傷害,請不要迴避,應該要面對它,即使痛苦也要正面迎擊才行。
特別像尚旭是位男性,父親的角色顯得更為重要,精神醫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在《阿德勒的理解人性》一書中提到,「在家庭生活中,父親這個角色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母親,儘管在人生初期,子女與父親的關係不比母親來得親密,但父親的影響力會在之後才顯現出其重要性」。
我認為對尚旭來說,比起離開父親身邊,更重要的是讓他的心從父親那裡獲得解脫,所以我建議尚旭和父親進行「溝通」,雖然尚旭一開始很激動,但在經過勸說之後還是答應了。
第一次的溝通是發送文字訊息,他傳送了「爸爸,祝您用餐愉快。兒子尚旭敬上。」,結果,沒有回覆。就這樣一週發送兩次短信,在經過一個月之後終於有了第一個回覆。 「好。」就沒了。
尚旭對爸爸會回信感到非常新奇和高興。他進一步升級了訊息內容,發送了「爸爸,謝謝您這段時間來的養育之恩。」沒有回覆。尚旭對於父親毫無反應而感到沮喪,我鼓勵他,並勸說他要持續發送文字訊息。
在持續發送訊息的過程之中,尚旭的生日也快到了,尚旭說:「做為生日紀念,我想打工給父母零用錢。」,就算父親毫無反應還是持續發送訊息,而且還想要在自己生日時向父母表達感謝之意,看到這樣的尚旭我也積極地為他加油打氣。
終於,尚旭的生日到了,但是沒有半個家人記得尚旭的生日,尚旭感到心灰意冷,還說要把為了送給父母而準備的零用錢自己花掉。我勸他說:「就當作是為了一直以來努力準備的你自己,還是按照原本的計畫送給父母怎麼樣?」
尚旭向父親行了大禮,把零用錢連同信紙一起遞了出去,父親沒特別說什麼,默默地接過手後就往陽臺走了出去。尚旭因為還是想聽父親說些什麼,所以也跟著往陽臺走去,卻發現父親正把信封握在手裡哭泣著。尚旭是第一次看到父親的眼淚,他也因此一點一點慢慢地打開了原本對父親緊閉的心門。
如果家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家庭成員都會受到衝擊和傷害,當困難的程度越大、越深,成員各自受到的衝擊就越難以平復。連自己的心都很難自制了,更不可能有擁抱他人傷口的力量,因此演變成了「雖然想得到安慰,卻沒有人能給予安慰」這樣令人惋惜的狀況,結果家庭成員開始互相傷害,不再有關愛、體諒與鼓勵,反而開始用如同鋒利武器般的言語互相攻擊。
尚旭的家庭應該也是同樣的情況。女兒在某天突然變成了殘疾人士,父親無法在照顧女兒的同時又一邊環顧四周,將全心全意都投注在讓女兒健康過日子上,甚至連應該要回過頭來關照身在其中受傷的自己、伴侶和兒子這件事都沒辦法想。雖然父親和母親都很希望尚旭能夠體諒父母的立場,但對尚旭來說,這只是在單方面強迫他體諒而已,假如父母能先吐露內心的傷痛,先試著靠近尚旭受傷的心靈,那會如何呢?或許尚旭的家人就能找到團結彼此內心、一起幸福生活的方法也不一定。
尚旭說那之後他和父親單獨去吃五花肉配燒酒,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做,父親當時說他本人也是被爺爺打大的,所以下定決心絕對不會打自己的小孩,但他卻沒能做到,也對此感到很抱歉。尚旭對我說:「我之前真的很想收到父親的道歉,但聽了父親的話之後,卻讓我的心情變得更複雜了。」
現在,尚旭如他所希望的從父母身邊經濟獨立了,而且比任何人都還要努力地生活著,尚旭說:「本來以為獨立的話就會變幸福,但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不過跟以前比起來,現在看到父親的臉時,心境上顯得更舒坦了,而且現在也不討厭妹妹了。」
人們總會認為「因為是家人,所以這是理所當然的」。像是「都會被諒解的吧」、「就算不說也會知道的吧」、「就算沒有取得原諒也沒關係吧」,因為是家人,因為立場相同,因為了解所有的狀況,所以認為他們當然能夠體諒,但是怎麼可以這樣呢?話要說出來才能被理解,把心掏出來才能舒展開來。
如果尚旭的父母一開始就能坦率地和尚旭交流心裡話、能夠撫慰尚旭的心靈,那該有多好呢?不過真的很幸好尚旭和他父親最終能慢慢地靠近彼此,想必父親在五花肉餐館肯定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才能說出口。我們真正需要鼓起勇氣的時機並不是搭乘令人戰慄的遊樂設施或是玩高空彈跳的時候,而是今天,今天就真摯地向家人坦露自己的心意,不要修飾,只要如實地說出口就行。
「不如自己一個人還更好」
秀智說她要和男朋友分手,因為男朋友做出了和她非常討厭的父親相似的舉動。秀智是看著喝醉酒的父親毆打母親的場景長大的,所以她下定決心「我絕對不要和像爸爸一樣的男人交往!」,沒想到卻在男朋友的身上看到了父親的影子。男朋友喝醉酒的話就會惹事生非,說隔壁桌的人在看他、鄙視他,喊著「有錢了不起啊!」,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別人表現出兇狠的樣子。
「我認為和那種男朋友分手是對的,但如果妳不先認可妳父親的話,下一次很可能又會遇上一模一樣的人。」我這麼說道。秀智聽到這番話後非常生氣,竟然要她認可那個光是想像都覺得很可怕的父親?站在秀智的立場來看是完全無法理解的。
這不是叫妳無條件接納妳父親的意思,而是要妳好好療癒並理解那段期間以來因為父親而十分疲憊的自己,這才是我所謂的「認可」,並不是要妳就這樣寬恕他,是希望妳能從心裡那個名為「父親」的包袱之中獲得解脫。
秀智因為遇到和父親很像的男朋友而煎熬著,但她選擇開始療癒、理解、擁抱過去那個因為父親而受傷的自己,她說當她真心誠意地輕拍自己的心之後,父親的模樣也開始慢慢地顯現出來。
父親在小時候被爺爺和奶奶拋棄了,他深受憂鬱症所苦,儘管如此父親還是為了家人努力、認真地生活,過去這段日子以來腦中都只有浮現父親不好的模樣,但現在會覺得父親也很可憐,變得能以更立體的角度看待父親。
秀智最終和男朋友分手了,其實她男朋友那些扭曲的言語和行為同樣起因於在父親那邊受過傷,男朋友也有著和秀智一樣的傷口,秀智就是被他那副和自己相似的面貌所吸引的。秀智在療癒和擁抱自己的同時,漸漸地擺脫了內心的包袱,也稍微能夠理解父親及分手的男友了。
義大利帕爾馬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賈科莫‧里佐拉蒂教授表示我們的大腦裡有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所以我們會做出反映別人行為的舉動,也就是我們具有讀懂別人想法和情緒的本能,這不單純只是「知道」,而是能夠「共感」,光是看到別人的肢體動作或聽到別人說話,就會感覺像是本人親自做出的舉動一樣,或許就是因為這樣嗎?我們和在人生過程中最常見到的人──父母變得越來越像,我們和父母變得越來越相像,也和與父母相似的人交往。
「我因為太討厭爸爸了,所以找了個和他完全相反的人交往。」就算是說出這種話的人,說到底還是把父母當作基準來尋找與其相反的對象交往,因此就「受到父母影響」這方面來看還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不管是喜歡也好,討厭也罷,還是都會被父母影響的。
接下來是大學生慧妍的諮詢信件。
我一個禮拜大概會哭三次,我也不太清楚我為什麼會哭,我的父母正在分居中,家庭環境也不太好,讀高中時也經常會有想死的念頭冒出來。但上了大學後出現了很好很好的人,我本來以為這種事是絕對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原本以為我不會感受到這種感情,不會有這樣的經歷,但我卻擁有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日子。可是,不久前我和男朋友分手了,因為我實在太累了,所以最後選擇放下他。儘管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人,但我卻感到很寂寞,我希望的事情他做不到,他想要的我也給不了。他和我不一樣,他是在富裕的家庭出生的,我的受害者心態似乎太過強烈了,以後好像也很難再跟其他人交往了。
「你們有對彼此說過自己想要什麼嗎?」當我這麼問時,慧妍的答案是沒有。雖然受害者心態是因為對方而感受到的,但會有這種想法的原因卻是來自於父母與家庭環境,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和父母見面,藉此來釋放自身的痛苦經驗和孤寂感。當然,這個過程會很辛苦,也可能辛苦到讓人不想經歷這種過程,但若不釋放的話,受害者心態只會變得更加強烈,就算與其他人交往,關係也可能會再次被這種受害者心態毀壞殆盡。
賽馬場的馬只會被要求看著前方奔跑,眼睛旁邊會被遮擋起來,受害者心態就如同這個遮蔽物。有遮蔽物的話,看待世界的視野及待人處事的視野必然會變狹窄,這樣就只會跟進到遮蔽物裡的人當朋友,必須要和父母見面,釋放該釋放的、整理該整理的,如此一來遮蔽物的角度才會逐漸變得寬廣,和已經走過的日子相比之下,未來要走下去的日子更重要,所以應該要努力找出自己的受害者心態是從何而來並加以解決才行,這麼做並非是為了誰,而是為了自己。
成勳是個三十多歲的上班族,認為人際關係很困難的他,一直記得小時候在餐廳裡跑來跑去的時候被爸爸拉到廁所裡打耳光的事情,這個傷痛讓他對婚姻產生了否定態度。我給了成勳一些建議,要他在三週後的結業式之前向父親提起當時的事情。兩週後,成勳說他和父親兩人單獨去喝酒了,也跟父親提到當時那件事留下的傷口至今都還存在著。「我真的做過這種事嗎?」父親這麼回道,他說自己想不起來了,還說自己當時的舉動是錯誤的,他對此感到很後悔。「明明像這樣敞開心扉說出來就好了,真搞不懂我之前為什麼一直做不到。」成勳後悔不已,對於婚姻的否定態度緩和了一些,心境上也變得稍微舒坦了一點。
我們有時候會因為對象是家人就隨意對待,所以因為家人而受到的傷害就會更深刻、更難以抹除,進而留下了傷痕。並非沒有從家人身上得到關愛就沒有愛人的資格,必須要先愛自己才行,如果你現在覺得很累,那就應該意識到這件事實並且正視它。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研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醫學博士貝塞爾‧范德科爾克(Bessel van der Kolk)曾說過,「想要克服心理陰影的話,就要在承受傷痛帶來的感受與情緒的同時,學會如何意識到自身其實已經知道的事實。」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學會認知自己對於家人帶來的傷痛所產生的感受與情緒,並且鼓起勇氣表現出來才行。
因為家人是家人,所以雖然近在咫尺卻感覺離得很遠,
是種雖然親密,卻又很疏離的關係。
因為是家人,期待越大,傷口也會隨之擴大發疼,
家人好像就是這樣的存在。
你知道父母最喜歡的歌曲嗎?
父母會知道我們最喜歡的歌曲嗎?
我當時只是需要關心
「我不會再見爸爸了,這樣比邊恨死他邊過活還好不是嗎?」
尚未擺脫稚氣的二十出頭青年尚旭說出了這句讓人倍感衝擊的話語,看起來像是平靜無波地度過了青少年時期且過著平凡生活的他,卻懷著對父親以及其他家人的憤怒。尚旭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積極活潑的性格,但卻出乎意料地連一個好朋友都沒有,既不能將心裡話坦誠相告,也不懂得如何與他人建立深厚聯繫, 雖然心裡很辛苦,但卻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尚旭很勉強地向我吐露了他的家庭故事。
尚旭的妹妹在小時候因為意外的關係而成了殘障人士,自從那之後父母就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照顧女兒這件事上,在尚旭有需要的時候,父母連一次都沒有守護在尚旭的身邊過,連小學的入學典禮都因為妹妹的關係,是尚旭自己一個人獨自參加的,尚旭為了想得到父母的關心而偷了朋友的錢,儘管當時是抱持著想要受到父母關注的心情而這麼做的,但尚旭得到的卻是「連你也要這麼讓人操心的話是要我怎麼辦才好!」的訓斥以及父親嚴厲的體罰。
父親的體罰並不是尚旭想要的「關愛」,尚旭因為太過埋怨和討厭獨占了父母的妹妹,在忍無可忍之下緊緊掐住了妹妹的脖子,最後被看到這一幕的父親打個半死。尚旭的心願是趕快賺錢然後離開父親,更準確來說,是想要擺脫這個令他感到厭煩的家庭。從未被家人好好接納過的尚旭,與世界也築起一道厚實的牆。
離開家人的話,就能夠從心靈的痛苦中解脫嗎?
我問尚旭:
「離開家人的話就能從父親那裡解脫嗎?」
「能!這是當然的啊。」
聽到這個充滿確信的答案讓我感到很心痛,古云「去者日以疏」,意味著眼不見,心境上也會逐漸疏離,尚旭的情況也能適用嗎?如果真的能如此的話那該有多好呢?
從家人那裡受到的傷害會在我們的靈魂深處留下疤痕,並不會因為沒看見就輕易消失,就算因為害怕、因為討厭而迴避,還是會執拗地留下影響,我們的生活、思考方式、人際關係等,所有的面向都會受到影響。我們的自尊感會因為傷痛而逐漸降低,而降低的自尊感又會讓我們無法走向世界,如此一來這種惡性循環就會持續下去。如果因為家人而受到傷害,請不要迴避,應該要面對它,即使痛苦也要正面迎擊才行。
特別像尚旭是位男性,父親的角色顯得更為重要,精神醫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在《阿德勒的理解人性》一書中提到,「在家庭生活中,父親這個角色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母親,儘管在人生初期,子女與父親的關係不比母親來得親密,但父親的影響力會在之後才顯現出其重要性」。
我認為對尚旭來說,比起離開父親身邊,更重要的是讓他的心從父親那裡獲得解脫,所以我建議尚旭和父親進行「溝通」,雖然尚旭一開始很激動,但在經過勸說之後還是答應了。
第一次的溝通是發送文字訊息,他傳送了「爸爸,祝您用餐愉快。兒子尚旭敬上。」,結果,沒有回覆。就這樣一週發送兩次短信,在經過一個月之後終於有了第一個回覆。 「好。」就沒了。
尚旭對爸爸會回信感到非常新奇和高興。他進一步升級了訊息內容,發送了「爸爸,謝謝您這段時間來的養育之恩。」沒有回覆。尚旭對於父親毫無反應而感到沮喪,我鼓勵他,並勸說他要持續發送文字訊息。
在持續發送訊息的過程之中,尚旭的生日也快到了,尚旭說:「做為生日紀念,我想打工給父母零用錢。」,就算父親毫無反應還是持續發送訊息,而且還想要在自己生日時向父母表達感謝之意,看到這樣的尚旭我也積極地為他加油打氣。
終於,尚旭的生日到了,但是沒有半個家人記得尚旭的生日,尚旭感到心灰意冷,還說要把為了送給父母而準備的零用錢自己花掉。我勸他說:「就當作是為了一直以來努力準備的你自己,還是按照原本的計畫送給父母怎麼樣?」
尚旭向父親行了大禮,把零用錢連同信紙一起遞了出去,父親沒特別說什麼,默默地接過手後就往陽臺走了出去。尚旭因為還是想聽父親說些什麼,所以也跟著往陽臺走去,卻發現父親正把信封握在手裡哭泣著。尚旭是第一次看到父親的眼淚,他也因此一點一點慢慢地打開了原本對父親緊閉的心門。
如果家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家庭成員都會受到衝擊和傷害,當困難的程度越大、越深,成員各自受到的衝擊就越難以平復。連自己的心都很難自制了,更不可能有擁抱他人傷口的力量,因此演變成了「雖然想得到安慰,卻沒有人能給予安慰」這樣令人惋惜的狀況,結果家庭成員開始互相傷害,不再有關愛、體諒與鼓勵,反而開始用如同鋒利武器般的言語互相攻擊。
尚旭的家庭應該也是同樣的情況。女兒在某天突然變成了殘疾人士,父親無法在照顧女兒的同時又一邊環顧四周,將全心全意都投注在讓女兒健康過日子上,甚至連應該要回過頭來關照身在其中受傷的自己、伴侶和兒子這件事都沒辦法想。雖然父親和母親都很希望尚旭能夠體諒父母的立場,但對尚旭來說,這只是在單方面強迫他體諒而已,假如父母能先吐露內心的傷痛,先試著靠近尚旭受傷的心靈,那會如何呢?或許尚旭的家人就能找到團結彼此內心、一起幸福生活的方法也不一定。
尚旭說那之後他和父親單獨去吃五花肉配燒酒,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做,父親當時說他本人也是被爺爺打大的,所以下定決心絕對不會打自己的小孩,但他卻沒能做到,也對此感到很抱歉。尚旭對我說:「我之前真的很想收到父親的道歉,但聽了父親的話之後,卻讓我的心情變得更複雜了。」
現在,尚旭如他所希望的從父母身邊經濟獨立了,而且比任何人都還要努力地生活著,尚旭說:「本來以為獨立的話就會變幸福,但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不過跟以前比起來,現在看到父親的臉時,心境上顯得更舒坦了,而且現在也不討厭妹妹了。」
人們總會認為「因為是家人,所以這是理所當然的」。像是「都會被諒解的吧」、「就算不說也會知道的吧」、「就算沒有取得原諒也沒關係吧」,因為是家人,因為立場相同,因為了解所有的狀況,所以認為他們當然能夠體諒,但是怎麼可以這樣呢?話要說出來才能被理解,把心掏出來才能舒展開來。
如果尚旭的父母一開始就能坦率地和尚旭交流心裡話、能夠撫慰尚旭的心靈,那該有多好呢?不過真的很幸好尚旭和他父親最終能慢慢地靠近彼此,想必父親在五花肉餐館肯定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才能說出口。我們真正需要鼓起勇氣的時機並不是搭乘令人戰慄的遊樂設施或是玩高空彈跳的時候,而是今天,今天就真摯地向家人坦露自己的心意,不要修飾,只要如實地說出口就行。
「不如自己一個人還更好」
秀智說她要和男朋友分手,因為男朋友做出了和她非常討厭的父親相似的舉動。秀智是看著喝醉酒的父親毆打母親的場景長大的,所以她下定決心「我絕對不要和像爸爸一樣的男人交往!」,沒想到卻在男朋友的身上看到了父親的影子。男朋友喝醉酒的話就會惹事生非,說隔壁桌的人在看他、鄙視他,喊著「有錢了不起啊!」,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別人表現出兇狠的樣子。
「我認為和那種男朋友分手是對的,但如果妳不先認可妳父親的話,下一次很可能又會遇上一模一樣的人。」我這麼說道。秀智聽到這番話後非常生氣,竟然要她認可那個光是想像都覺得很可怕的父親?站在秀智的立場來看是完全無法理解的。
這不是叫妳無條件接納妳父親的意思,而是要妳好好療癒並理解那段期間以來因為父親而十分疲憊的自己,這才是我所謂的「認可」,並不是要妳就這樣寬恕他,是希望妳能從心裡那個名為「父親」的包袱之中獲得解脫。
秀智因為遇到和父親很像的男朋友而煎熬著,但她選擇開始療癒、理解、擁抱過去那個因為父親而受傷的自己,她說當她真心誠意地輕拍自己的心之後,父親的模樣也開始慢慢地顯現出來。
父親在小時候被爺爺和奶奶拋棄了,他深受憂鬱症所苦,儘管如此父親還是為了家人努力、認真地生活,過去這段日子以來腦中都只有浮現父親不好的模樣,但現在會覺得父親也很可憐,變得能以更立體的角度看待父親。
秀智最終和男朋友分手了,其實她男朋友那些扭曲的言語和行為同樣起因於在父親那邊受過傷,男朋友也有著和秀智一樣的傷口,秀智就是被他那副和自己相似的面貌所吸引的。秀智在療癒和擁抱自己的同時,漸漸地擺脫了內心的包袱,也稍微能夠理解父親及分手的男友了。
義大利帕爾馬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賈科莫‧里佐拉蒂教授表示我們的大腦裡有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所以我們會做出反映別人行為的舉動,也就是我們具有讀懂別人想法和情緒的本能,這不單純只是「知道」,而是能夠「共感」,光是看到別人的肢體動作或聽到別人說話,就會感覺像是本人親自做出的舉動一樣,或許就是因為這樣嗎?我們和在人生過程中最常見到的人──父母變得越來越像,我們和父母變得越來越相像,也和與父母相似的人交往。
「我因為太討厭爸爸了,所以找了個和他完全相反的人交往。」就算是說出這種話的人,說到底還是把父母當作基準來尋找與其相反的對象交往,因此就「受到父母影響」這方面來看還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不管是喜歡也好,討厭也罷,還是都會被父母影響的。
接下來是大學生慧妍的諮詢信件。
我一個禮拜大概會哭三次,我也不太清楚我為什麼會哭,我的父母正在分居中,家庭環境也不太好,讀高中時也經常會有想死的念頭冒出來。但上了大學後出現了很好很好的人,我本來以為這種事是絕對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原本以為我不會感受到這種感情,不會有這樣的經歷,但我卻擁有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日子。可是,不久前我和男朋友分手了,因為我實在太累了,所以最後選擇放下他。儘管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人,但我卻感到很寂寞,我希望的事情他做不到,他想要的我也給不了。他和我不一樣,他是在富裕的家庭出生的,我的受害者心態似乎太過強烈了,以後好像也很難再跟其他人交往了。
「你們有對彼此說過自己想要什麼嗎?」當我這麼問時,慧妍的答案是沒有。雖然受害者心態是因為對方而感受到的,但會有這種想法的原因卻是來自於父母與家庭環境,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和父母見面,藉此來釋放自身的痛苦經驗和孤寂感。當然,這個過程會很辛苦,也可能辛苦到讓人不想經歷這種過程,但若不釋放的話,受害者心態只會變得更加強烈,就算與其他人交往,關係也可能會再次被這種受害者心態毀壞殆盡。
賽馬場的馬只會被要求看著前方奔跑,眼睛旁邊會被遮擋起來,受害者心態就如同這個遮蔽物。有遮蔽物的話,看待世界的視野及待人處事的視野必然會變狹窄,這樣就只會跟進到遮蔽物裡的人當朋友,必須要和父母見面,釋放該釋放的、整理該整理的,如此一來遮蔽物的角度才會逐漸變得寬廣,和已經走過的日子相比之下,未來要走下去的日子更重要,所以應該要努力找出自己的受害者心態是從何而來並加以解決才行,這麼做並非是為了誰,而是為了自己。
成勳是個三十多歲的上班族,認為人際關係很困難的他,一直記得小時候在餐廳裡跑來跑去的時候被爸爸拉到廁所裡打耳光的事情,這個傷痛讓他對婚姻產生了否定態度。我給了成勳一些建議,要他在三週後的結業式之前向父親提起當時的事情。兩週後,成勳說他和父親兩人單獨去喝酒了,也跟父親提到當時那件事留下的傷口至今都還存在著。「我真的做過這種事嗎?」父親這麼回道,他說自己想不起來了,還說自己當時的舉動是錯誤的,他對此感到很後悔。「明明像這樣敞開心扉說出來就好了,真搞不懂我之前為什麼一直做不到。」成勳後悔不已,對於婚姻的否定態度緩和了一些,心境上也變得稍微舒坦了一點。
我們有時候會因為對象是家人就隨意對待,所以因為家人而受到的傷害就會更深刻、更難以抹除,進而留下了傷痕。並非沒有從家人身上得到關愛就沒有愛人的資格,必須要先愛自己才行,如果你現在覺得很累,那就應該意識到這件事實並且正視它。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研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醫學博士貝塞爾‧范德科爾克(Bessel van der Kolk)曾說過,「想要克服心理陰影的話,就要在承受傷痛帶來的感受與情緒的同時,學會如何意識到自身其實已經知道的事實。」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學會認知自己對於家人帶來的傷痛所產生的感受與情緒,並且鼓起勇氣表現出來才行。
因為家人是家人,所以雖然近在咫尺卻感覺離得很遠,
是種雖然親密,卻又很疏離的關係。
因為是家人,期待越大,傷口也會隨之擴大發疼,
家人好像就是這樣的存在。
你知道父母最喜歡的歌曲嗎?
父母會知道我們最喜歡的歌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