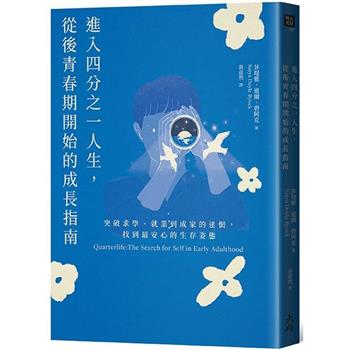Chapter 1. 比這更好的:尋找平庸人生裡的意義(節錄)
你知道有更好的東西,只是還不明白它在哪裡。
我對這階段的人生開始感興趣,是在大學即將畢業的時候。我不由得注意到班上幾乎每個人都不確定自己的未來,除了少數找好工作或準備念法學院的人顯得平靜而快樂以外,這情景就像哥吉拉(Godzilla)突然來到岸邊。有些人開始恐慌,朝各個方向飛奔,尋找生存的計畫,任何計畫都行。有些人完全聽天由命,彷彿認定自己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有些人則仍然瘋狂地盡情玩樂,好像繼續過著大學生活就會讓巨大的威脅消失。
在此之前,我們念書、寫報告與考試。我們運動、抗議與聚會,一起在自助餐廳吃午餐,沒下雨的時候躺在廣闊的草坪上。我們幾乎時時刻刻都很忙碌,但是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完成學業以順利畢業。每門課都有修業截止日期和考試,一學期接著一學期,直到考完最後一輪期末考,迎來家人到訪的畢業那天。一切發生得非常迅速。忽然間,我們就來到這裡:結束將近二十年的學校生活,對以後要做什麼卻沒有明確的方向。我們花費許多心力在如何考取大學,以及該上哪所學校的推銷宣傳上,但如今我們不再是客戶,只是一群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被扔出學術的安樂窩。沒有任何指示,有的只是:「去,去吧!我們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你們了。」
我覺得我並不比高中時更清楚自己的人生要做什麼。每當我表達自己對存在的主張時,大多數時候都無人理會。「這就是事實」,而我以後會「明白的」。我發現自己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相當喜愛的浪漫喜劇《情到深處》的最後幾幕。當我還是個患相思病的青少年時,我會一遍又一遍地重播男主角洛伊德.杜伯勒(Lloyd Dobler)將手提音響舉在頭上,有如羅密歐在追求茱麗葉的那一幕。(當然,我也反覆聽他播放的那首由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唱的〈在你眼中〉。)但在我快要畢業的時候,那部電影的另一幕開始悄悄潛入我的意識。洛伊德的「茱麗葉」──女主角黛安娜.寇特(Diane Court),身為畢業生代表的她,對著一大群畢業同學和拿著嗡嗡作響的攝影機的家長致上告別辭。最後她說:「我擁有世界上所有的希望和抱負,可是當我想到未來……說實話……我真的……很害怕。」簡單地說,那就是我的寫照。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抱負,而且不可否認地,害怕得要命。
畢業三年後,我在波特蘭市中心一家軟體新創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在大學畢業到從事這份工作之間,我曾試著投入人道主義和社會正義相關的工作。我申請了無數個非營利的職務,也到國外當了兩次志工,先是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的監獄,然後是在斯里蘭卡遭到海嘯摧殘的海岸邊。為了支付帳單,我還做過各種各樣的兼職和初階工作。在「社會創業」及「社交媒體」發展初期,我曾試著創立一家公司,讓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有機會幫助國內外的群體。(我因此涉足了新創公司與科技業。)這份專案經理的工作,是我畢業以來第一份待遇優渥的全職工作,我很慶幸自己突然有了儲蓄帳戶,但是我並不快樂。除了經濟上可以存活外,我一點都不了解自己做這些事的「意義」,也不覺得自己過著命中注定「屬於我」的生活。我有一份「好工作」,對此我心懷感激,但我協助開發的科技產品對人們絲毫沒有吸引力,似乎是從校友會的關係網誕生,而不是擁有真正的願景或需求。大多數的日子裡,我從二十六層樓高處望著窗外的夏日天空,但願自己是在平地上騎自行車。我曾試圖打造自己覺得有意義、同時又對世界有所影響的生活,但我失敗了。這不是我預想的未來,也不可能是我在學校多年來一直努力的目的。
當時我花了很多時間寫日記,記下我長期迷失方向的感覺。我曾寫到,所有的野生動物似乎在本能中都內建了某種形式的導航系統,比方說公狼離開狼群到世界闖蕩時,總有方向感和目的;或者不管距離多遠,大象都能找到水;海龜在大海中能找到灣流,知道何時何地該在沙灘上產卵;帝王斑蝶則懂得沿同一條路線,遷徙數千英里。但是人類單飛時,卻完全仰仗計畫、目標、策略與運氣來找到人生方向,我們的本能發生了什麼故障?儘管我的邏輯足以應付學校和社會上的事情,然而要有目的地規劃自己的人生時,對我來說卻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論我寫下或是說出多少,我仍然難以理解什麼是正確的決定,也難以聽見自己的身體和感受向我透露著什麼。我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地方遊蕩,但我經常覺得自己更像是一隻可憐的老虎,困在籠子裡來回踱步──而且有點「過於」被動──並不是一個狂野自由的人。
某一晚下班後,我在夏末的暑氣中飛快地騎自行車回家,氣喘吁吁、疲憊不堪地走進和室友合租的白色小屋。這星期非常難熬。我的辦公室裁員,我身邊最優秀的同事們,包括多位我管理的人突然都失業了。同時,所有最令人討厭的人都留了下來,像是掠奪成性的執行長和他弟弟,他的無能彷彿惡臭那般地散發出來。我知道自己不想繼續待在那個環境,因為我對自己協助開發的產品毫無信心,現在圍繞在身邊的又都是我不敬重的人。按照他人對我這年齡層的期待,我應該對人生充滿嚮往才對,然而我卻一天天失去原始的動力,對自己曾經盼望的生活失去信心。當我開始向室友講述我的一天,以及我的上司如何試圖說服我不要離職時,我忽然間搖搖晃晃地啜泣起來,癱倒在地板上。我已經到了極限。我不知道我對自己的人生做了什麼,儘管有人給過建議,我還是忍不住去想這件事。我對相互矛盾的信念和迫在眉睫必須做的決定感到厭惡:我該辭去這份愚蠢的科技業工作,等待認股選擇權下來,然後回去做多份兼職的工作嗎?還是該抓住升遷的機會並獲取經驗?或者休個假就好,得讓自己在痛苦中成長?
這之中沒有一個選項,能讓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最終目標。我知道自己對生兒育女不感興趣,結婚的念頭似乎還很遙遠,那麼我的目標只是累積財富、在公司裡步步高陞嗎?無論我望向何處,看到的都是死胡同。我的心無法平靜下來,我找不到自己的核心。我感到自己被徹底壓垮、精疲力盡,同時覺得自己空洞的擔憂無聊透頂。我所做的任何事,對這危機不斷的世界都不會造成什麼影響;我所做的一切,都沒能帶給我明確的喜悅或目的感。我倒在木地板上哭泣,感覺自己瘋了、卡住了。身為二十多歲的大學畢業生,我照理說應該蓬勃發展,所以我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儘管我在各方面都懵懵懂懂,但我開始看到周遭人們痛苦的模樣或姿態。從我的室友到朋友、約會對象、以前的同學與同事,我周圍的人都和我年紀相仿,他們都有類似的掙扎。有些同齡人的日子比我更艱難,有人因為複雜的診斷反覆進出醫院,有人甚至受到防止自殺的監控。不過還有很多其他人,看起來比我感覺的還要沉穩。他們似乎不會因為擔憂存在問題,而讓自己的生活基礎經常瀕臨破壞的邊緣。他們好像不會煩惱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即便他們似乎也不完全確定自己在做什麼。我們很少有人上過如何處理獨立生活中無數事情的課程,像是求職、安排開支、繳稅、約會、性交、設定界線、烹飪與清掃,然而我們卻被認定應該能夠應付這一切。在許多情況下,周遭的人都告訴我們不會有事。心理健康危機、憂鬱、焦慮似乎是種祕而不宣的事,但另一方面,假定我們這一代很淺薄的笑話卻日益增加。
我向來覺得那些笑話很古怪。幾乎每個世代都有重大的社會危機要解決,這有助於塑造這群人的世界觀。我們這一代的情況並無不同。我們邁入成年時正好是九一一事件餘波後,重返無休止的海外戰爭時期。氣候變遷日漸籠罩我們的未來,宛如有史以來構思過最恐怖的災難片。而當我們試圖追求美國夢的時候,還有大規模的經濟危機要處理。同時,對於發生在學校、食品雜貨店、音樂會、電影院與購物中心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我們被迫感到習以為常。
感覺好像沒人在照應我們。充斥著種族主義政策和私利的司法體系,監禁了無數和我同齡或比我年輕的人,也讓需要實際支持和方向指引的年輕公民淪為罪犯;而本來應當有導師和社會救助的地方,卻只有警察和法庭。我的許多同輩人都在工作中苦苦掙扎,所得的薪水絕不可能維持富足生活;有些人甚至貧困潦倒或無家可歸。我們有很多人背負著沉重的就學貸款和高築的信用卡債,部分原因出於社會中有專以我們這年齡層為目標的掠奪性做法。還有很多人經歷過創傷和虐待,卻沒得到適當的心理或身體照護,因而不斷進出毒品和酒精勒戒中心。太多人死於服藥過量,成為因企業貪婪而加劇的全國性流行病的受害者,這問題在未來幾年只會越來越氾濫。我們大多數人就算有保險也沒有可靠的健康保險。此外,如果有任何人因為痛苦、焦慮、憂鬱去找醫生或心理治療師求助,通常看診時間都很簡短,得到的只有迅速的診斷和處方藥。他們很少詢問,我們為什麼有這些情緒,更別說提供如何處理這些情緒的寶貴指引了。
當我在租屋處骯髒的地板上痛苦哭泣時,我知道,我缺乏方向的狀況一定有解決辦法。我也知道,在我和許多同輩感受到的困惑、神經質的痛苦背後,一定有更重要的意義。我無法相信,我們注定要面對擁擠不堪的監獄、無家可歸、槍枝暴力、一系列的精神障礙、慢性疼痛,或者無限循環地進出治療中心。倘若我這年齡層的人普遍都在受苦,那麼一定有更大的因素在影響整件事,不能單獨責怪我們每一個人。
我辭掉了那份工作,感覺很棒。我很確信那不是我的歸屬,雖然我還不知道自己應該在哪裡,但我不知怎麼地就是知道。如同社會心理學家肯尼斯.肯尼斯頓(Kenneth Keniston)多年前所寫的,一個人「可能會覺得他們有權擁有『比這更好的東西』,卻無法定義那『東西』是什麼」。我知道有更好的東西,只是還不明白那是什麼或者在哪裡。
Chapter 3. 兩種四分之一:追求穩定型與追求意義型(節錄)
對穩定及意義的渴望,經常令人無所適從。
就像人類在相似年紀開始有爬和走的衝動,我們也差不多在同樣時間渴望冒險、想過自己的生活。四分之一人生,是傳統上人們離開原生家庭,開始設法獨立過活的時期。無論最初是為了工作、為人父母、結婚或者求學,每個人都努力融入這個世界並展開新生活。
然而,四分之一人生的旅程不僅是尋找伴侶和事業,更是追尋自我。終極目標是找尋完整的體驗──不再感到人生表裡不一。探尋,是為了不再令人困擾地渴望別的東西、更多的東西。年輕人經常想要更多的安全感、平安以及社會的穩定,同時又想要冒險的感覺、經驗和個人的意義。我們需要堅固的結構來維持穩定,也需要賦予生活溫暖與目的的神祕感、親密關係,甚至是不確定性的元素。關於這點,站在四分之一人生心理學的角度,我的看法是:對穩定及意義的渴望,經常令人無所適從。
二十世紀中期,隨著中年危機的觀念盛行、引人注目,大規模的震盪開始擾亂成年期的預期目標。中年人突然追求起難以確切解釋的「更多」,人數多到足以在社會各界引起共鳴。中年危機可以定義為心理轉變的時刻,在這段時期,成年人不得不適應「空巢期」,還有許多婚姻破裂及個人危機,例如父母過世,引發了有關存在與心靈方面的疑問。全體社會不再認為,中老年人可以因為存活、安全感及家庭就感到滿足。很多中產階級的中年人意識到一個事實,即他們的人生欠缺了一些東西,他們還需要別的東西。
這場中年流行病引發的地震在成年期造成了缺口,之後發展心理學將這個缺口具體化。成年期的前半段成為「追求穩定」的階段,人們著重於達到經濟與個人安全,以及繁衍後代的目標。成年期的後半段,也就是中老年後,成為「追求意義」的階段,是透過有創造力的工作、人際關係,及探索內心世界來發覺自我的時期。這是簡單地拆解成年人的目標,從直覺來看十分合理:先創造穩定再追尋意義;在思考過多有關存在、心靈或死亡的問題前,先在生活中扎根。
然而事實上,像這樣清楚劃分成年期的發展目標,是相當少見且不切實際的。這個典型只反映了某一特定族群的生命歷程,對許多覺得被物質安全感及異性戀本位目標局限住期望的人而言,這種陳述即使在全盛時期也不是事實。更確切地說,無數我們珍藏在歷史、文學、神話中的青年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就是因為不符合這個過度簡化的陳述。人們不會那麼輕易地找到穩定性,否則他們就會感到空虛,並且被自己找到的東西悶到窒息。儘管如此,這個成年人目標的成規──在四分之一人生先追求穩定的平穩發展,到中年再追求意義──長期以來一直主宰著我們對成年期的理解。如同其他許多長期存在的文化信念,這樣的成規需要重新思考。
到目前為止,青年透過心理症狀、危機、創作和行動主義,抗議對成年期的狹隘描述。這些描述的定義,都是根據資本主義對成就與表現的期望,以及異性戀本位的父權社會令人窒息的性別角色,還有白人至上主義所造成的經濟與社會的弊病。約莫上個世紀開始,或許是起因於各種背景的青年強烈表達不滿,嚴格的性別角色持續鬆動,勞動法改變了,高等教育變得更容易獲得,節育措施提高了第一次懷孕的平均年齡,對成年期預設的價值觀也受到進一步的審查。按順序排列的發展目標──先求穩定,再求意義──這樣的概念遭到了質疑。事實是,追求穩定和意義一直都是四分之一人生的一部分,不是只有穩定而已。
現今,雖然有許多青年覺得失去了過往分段發展與明確性別角色的護欄,但同時也感到獲得解脫;他們慶幸比以往自由,卻又對「這觀點」感到不知所措和困惑。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退回到過去及所謂「傳統」的家庭角色。以前的目標令人不滿,但新的目標還沒有明確定義。
歸根結柢,四分之一人生階段是要塑造一個人的獨立性及生活方式,並分別、具體地闡明穩定和意義是什麼模樣。在四分之一人生階段茁壯成長,並不需要「正常」、「優秀」或「成功」。那些陳述存留得越久,強迫人們過著不符合他們本性或價值觀的生活,心理健康統計的流行疾病就會困擾年輕人越久。我們越明白追求穩定和追求意義都是恰當且健康的傾向,成年期就越不會只關注著「贏家」和「輸家」,或「優秀」和「低劣」。
受到追求意義發生在中年時期的假設所影響,大多數發展心理學都毫無保留地將四分之一人生的焦點放在追求穩定的目標上,因此我們只看到一半的故事。事實上,一直以來處於四分之一人生的青年都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傾向於先追求穩定,因此能相對自在地面對這樣的焦點;另一種則傾向於一開始先追求意義,這種人就會覺得自己與社會對這階段的人生期望格格不入。
處於四分之一人生的青年範圍廣泛,而我簡單地將這兩類人稱為「追求穩定型」與「追求意義型」。了解這兩類的青年,是理解四分之一人生心理學的第一步。一旦青年清楚自己處在追求意義型與追求穩定型之間的位置,他就會感到更有動力去處理四分之一人生需要的一切,不會因為混淆不清的說法、過時的期望,以及可能與他們所需完全相反的人生建議而不知所措。
他們之所以能辦到,經常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在外在世界設法維生或茁壯的方法。他們找到了自己的穩定,而且可以和他們的意義結合起來。事實上,追求意義型的人需要努力讓自己找到平衡,尋求一種穩定、正常的合群,卻又不會失去人生意義感的生活方式,即便一開始這麼做的時候會感到厭惡。在下一章,我將透過兩個我治療的追求意義型案主葛蕾絲和丹尼的故事,更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