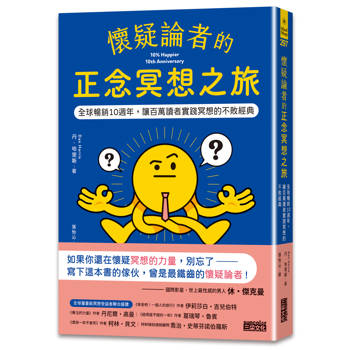深入險地,只挖大條新聞
二○○一年十月,我第一次來到巴基斯坦,在此之前我從未踏上第三世界國家,除非你把我一九八○年代參加青少年營隊的墨西哥提華納(Tijuana)之旅也算在內。
接到國際新聞部來電隔天,我就搭上飛機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完全不知等在眼前會是什麼景況。我來到了一個英國朋友口中的「正統『星際大戰 』場景」。行李提領處擠滿了睡眼惺忪的旅客、神色木然的警察,還有身穿棕色油膩連身工作服的行李工人。
我是大廳中唯一的西方人,通關處的另一頭有個本地司機等著我,手上舉著我的名牌。外頭是早晨霧濛濛的空氣,溫暖且散發著一絲輪胎燒焦的氣味。高速公路上滿是龐大鮮豔的貨櫃車,司機不時按喇叭,發出微小不成調的聲音。我後來搞懂了,這裡的人按喇叭不全是為了要其他用路人讓開,只是想提醒別人他的存在,就像一道聲波。
我從未感到離家如此遙遠。
接著我們抵達旅館──出乎意料,居然是高檔的萬豪酒店(Marriott),而且還比一般的美國萬豪連鎖酒店更大、更氣派。我放下行李,直接上樓前往總統套房,ABC的新聞團隊在此進駐。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多同事,他們大多是倫敦分部的成員,待過波士尼亞跟盧安達,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樣。這樣危險貧困的國家與採訪環境,似乎根本不會造成他們任何認知失調。身穿制服的旅館服務生每天為我們送來兩次點心:保鮮膜包覆的盤子裡盛著餅乾與綜合堅果。我的同事鮑布.伍卓夫(Bob Woodruff)悶悶不樂的踱步進來,打電話給客房服務點了炒蛋。
然而,情勢不久後就變得棘手起來。要不了幾天,我就聽說阿富汗主政者塔利班 (Taliban)送來邀請,請我們前往坎大哈(Kandahar)的總部,算是隨軍採訪。乍看之下,這是絕對愚蠢的點子--深入敵營,還送上門作客──因此在新聞小組間激起熱烈辯論。我們特地召開了盛大的會議,仔細推敲了一番。我聽了正反兩方的意見,但其實結論早已預設了:我絕對不可能錯過這條大新聞。
我打電話給母親,想在她看到新聞前先告知我的去向,但無法接上她工作的醫院。於是我退而求其次,打電話告訴父親,他一向是比較情緒化的那位。我才講出計畫,父親便哭了,話筒兩頭一度靜默,只除了父親勉力調整呼吸的聲音。眼前的興奮退去,代之而起是深深的悔意,一直到此刻,我才從這趟旅程對我的意義中醒來,看到這件事可能對家人造成多大衝擊。父親很快便恢復常態,並使出他招牌的自貶式幽默:「你有猶太血統,只不過不是從你媽那裡來的。」
那晚我分外自責,而且坦白講,我害怕到無法成眠。隔天,我與幾個記者搭著巴士,前往未知的命運。那條將南阿富汗對分的主要幹道光禿禿的,車程漫長而顛簸,我們骨頭都快散了,總算在半夜抵達阿富汗的坎大哈外圍,停在一棟政府集合大樓前。美國空軍摧毀了此地的電力供應,因此整個城市漆黑一片。我們快速爬上某個大樓屋頂,架設衛星訊號並發送新聞,遠在紐約主播臺的彼德.詹寧斯詢問我這趟旅程的經過。彼德和我通話完畢後,趁著準備播新聞的空檔,特地打電話給我父母幫我報平安。
接下來超現實的三天讓人頭昏腦脹。我們被滿面虯髯、全副武裝的男子護送,繞行整個市區,我們多半只能參觀他們願意呈現的區域,做為宣傳目的,像是美國軍機炸毀的大樓,據稱有不少無辜平民喪命。但我印象最深的,卻是這些塔利班戰士私下的行事作風。
高層指揮官總是不停吹噓、宣導政令,但這些小兵十分不同,作風隨和,愛交朋友。他們其實只是孩子,還教我們說當地的髒話(顯然「驢子」在普什圖語 中帶有嚴重的侮辱意味)。還有一回,其中一個小兵悄聲對我說:「帶我去美國。」
我在報導中添加不少這類花絮,收到總部電郵表示讚許,這份量足以讓剛起步的新進記者輕飄飄而顧盼自得。彼德稱我是「我們派往阿富汗的人」。我的組員是兩個英國人,他們花上好幾個小時取笑我,說我以後回去會變成一個「超級爛人」。他們倆會假裝我回到紐約,跟朋友去酒吧的場景,模仿我每次打斷別人談話的開場白:「是是是……嘿我有跟你說過我在阿富汗的事嗎?」
這趟旅程讓我首次嘗到某種滋味,我會說,這就是新聞採訪的海洛因:純粹而病態的興奮刺激。你去到一個原本不該去的地方,不但全身而退,還能因此上電視。我上癮了。
當然,我回到紐約之後可沒有多少時間洋洋得意。迎接我的是一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負評報導,藝評人卡琳.詹姆斯(Caryn James)將我的採訪與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BBC)的並陳,讓我相形見絀,還稱我的版本「溫情而恍惚」。這對我的認知可謂沉重打擊。我感到有苦難言,絕不同意她的說法,但很多同事不這麼認為。她的評論坐實了我根本太嫩、不適任,讓我在公司馬上從英雄變成驢子。
幾星期後,國際新聞部決定再給我一次機會,這次要我去賓拉登 (Osama bin Laden)的托拉波拉(Tora Bora)洞穴基地,當時正遭到接受美方資助的阿富汗本地軍閥攻擊。我在搭計程車前往機場的途中接到彼德來電,他告訴我,大家一致認為我第一回合搞砸了,這次我真的得證明自己的能力。我整趟飛行途中,都像嬰兒般縮在椅子裡。
托拉波拉沒有萬豪酒店。抵達之後,我們來到一片冰雪覆蓋的罌粟花田,付錢給鴉片農場主人後,借宿在他田中幾間搖晃的土屋裡。門外拴著一頭臭烘烘的大公牛,每天我們回來吃晚飯時,院子裡跑跳的雞就又少了一隻。
我在這次任務中成功為自己平反。為我扭轉劣勢的部分原因來自某個場景,有錄影為證:那時我正站在山邊,對著鏡頭講話,錄製新聞帶的轉場,話才說到一半,一道聲響呼嘯越過我腦門上方。我從來沒有聽過近距離槍響,因此約一秒過後我才醒悟發生了什麼事,並趕緊趴倒在地。這可一點都不溫情也不恍惚了,我老闆挺欣賞的。
不過,這事還是有兩處地方挺糗的。第一,仔細看過影帶會發現,鏡頭後方的阿富汗人沒有一個找掩護的,他們根本不為所動;其次,我聽到子彈破空心裡的第一反應是:拜託要錄到啊!
這次是個全新的體驗。如果我不是有任務在身,那聲槍響肯定會嚇得我尿溼褲子。在我過去的生活經驗裡,全然找不出稱得上英勇的事蹟,我沒服過兵役,也沒參加過激烈的運動賽事如美式足球。我之前唯一碰過的危險,是在曼哈頓一處十字路口,沒仔細看路而被計程車撞上。
然而,當你站在鏡頭前做新聞採訪時,卻可能以為自己刀槍不入,像是你與世界之間隔著一道緩衝;如果散步時用耳機聽iPod會帶你遠離現實,那麼新聞採訪便是這種超現實的加乘版本。以戰事新聞來說,我亟欲參與重大新聞事件的渴望,完全掩埋了我對焦慮的本能反射作用。
捲入風暴,內心毫無波瀾
托拉波拉地區的軍事行動失敗了,據說賓拉登沿著小徑逃入巴基斯坦,但對我來說卻是重生的契機。重新得到上司的信任之後,接下來三年我不停往返紐約與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以及伊拉克等地。我像是伍迪.艾倫電影《變色龍》(Zelig)的主角西力(Zelig),以世界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為背景,從中謀得個人利益。
這些採訪任務迫使我一再親身經歷最為怪異可怖的場景。在以色列,一處海濱旅館遭到自殺式炸彈攻擊後,我看著一陣海風掀起了散落的床單,露出一排人腿。在伊拉克,我跟一群海軍陸戰隊員低頭看著一具倒在路邊的腫脹屍體,不約而同發現,那男屍臉上的不是槍孔,而是一個個用電鑽鑽出來的洞。在約旦河西岸,我站在一位父親身旁,看著挖土機剷起一具具屍體,倒入一處醫院停車場臨時挖好的大坑。那男子長聲慘嚎,尖銳淒厲,眼睜睜看著兒子屍體滾入坑裡。
儘管在那父親的哭聲前,我再也無法克制的走出攝影機鏡頭之外,喉頭堵得緊緊的,但我對戰場慘劇的反應,或者更準確的說,我對慘劇的毫無反應讓我吃驚。就我來看,我並不那麼難過。我說服自己,這份工作要求我保持心理上的距離,就像影集《外科醫生》(M * A* S* H)裡的醫生在手術檯上開病人的玩笑。我認為記者的抽離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標,如此才能更精準傳達出急迫的訊息。要是每次看到悲慘可怖的事件都要崩潰一次,那我如何做好這份工作?
回到家鄉,有人會問我,這些海外經驗是否「改變」了我。我的直覺反應是:沒有。那句老話「隨遇而安」,似乎挺貼切的。我還是一樣的我,只是在歷史上拿到了所謂前排的戲票。我父母擔心我目睹的一切會造成心理創傷,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受傷。正好相反,我喜歡當戰地記者。其實,我愛得很,隨身保鏢、裝甲車,讓人載著到處走,感覺像是元首級人物。我還喜歡防彈背心,讓我的小骨架在電視上有放大效果。
在戰區裡,一切規則都懸而不用,不必看交通號誌、速限,也不管社交禮儀。這種遊走在社會規範邊緣的活力,就像是大城市碰到大斷電或大風雪。而且,風險當然有另一番浪漫感受。我們常故意扭曲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沒什麼比中了彈卻安然無恙更讓人興奮的了。」
我喜歡的還不光是這層興奮,而是真心相信我們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親眼見證美國軍事力量的最前端。我有達成目的的使命感,這正是個值得冒險的目標。就為了追求快感與實踐原則這兩個因素,我放任自己捲入ABC惡名昭彰的內部競爭,只求留在權力核心。
外人可能會認為我們大部分時間用在與友臺記者一較高下,實際上,我們絕大部分精力用在與自己人競爭。為了卡好採訪前線位置,我開始留意到自己較勁的對象,例如剛從地方新聞調來的另一位年輕記者大衛.賴特(David Wright),他聰明又有衝勁,這點讓我有些不爽。
過去的我,曾樂於在資深記者爭奪大新聞時作壁上觀,但現在的我已更有自信競爭。爭奪新聞的方式主要是透過大肆遊說,例如不停打電話和寫電子郵件給分配採訪任務的主播和主管。內部角力儘管在許多方面促進了組織體質的健康與活力,但同時也十分緊繃,我不得不花上不成比例的時間來跟同事比較。例如,有一陣子賴特在阿富汗衝鋒陷陣,我卻被綁在紐約動彈不得,那時的新聞我一點都看不下去。
在戰場上一面採訪,一面還得跟後方爭取播出,實在夠變態的,但在我看來,這就是表演慾的本質。身為記者的絕大特權,就是能目睹世界級的大事,與事件要角互動,身歷其境,體驗其中原汁原味;儘管如此,另一個絕對的詛咒,也就是我在九一一事件學到的:記者看這些事件的部分角度,絕少不了自我利益的糾葛。我去得成嗎?我表現好嗎?這種心理極少在知名記者傳記中揭露,起碼我讀過的都沒有,但這層內心戲絕對是真的。
彼德就曾與同輩主播如泰德.柯佩爾(Ted Koppel)上演精采角力。前總裁魯尼.阿雷吉(Roone Arledge)在新聞部門建構起了一套明星制度,揉和封建分封領地的競爭本質,相互爭奪珍稀的有限資源,例如重大專訪跟優秀的特派記者等。巴格達淪陷後,賴特和我都爭著第一個搶進伊拉克,彼德甚至打電話來取笑我誇張的手段,但語帶讚許。
在這樣一個容忍大家把怒氣做為手段的環境,我有時會放任脾氣失控,這是我在二十出頭時就有的毛病。那時我還是個波士頓的年輕主播,有次我在進廣告後把文件往空中一丟,抗議某個技術問題。沒多久便被老闆叫進辦公室警告:「大家都不喜歡你。」那次會議讓我的心臟頓時提到喉頭,迫使我調整自己的行事作風。然而始終有改進空間;身為特派記者,我偶爾會與同事口角,甚至有幾次在國外採訪時發生愚蠢至極的衝突。有次我在巴基斯坦,置身於一場擁擠憤怒的街頭示威,居然毫不明智地與一名示威者對罵,只因為他說九一一事件的背後黑手其實是以色列。
我不得不收斂壞脾氣的狀況之一,當然就是面對彼德.詹寧斯的時候。
不憂鬱的憂鬱症
二○○三年七月的某個悶熱日子,我在曼哈頓上西區的公寓前下了計程車,彼時我剛結束為期五個月的伊拉克採訪,自美國全面入侵該地到叛亂開始前幾個月,我都一直待在那裡。從沙漠回來的感覺很奇特,這裡四處是落葉喬木,而我也不再需要任何隨從。門房一臉驚訝的看著我,我猜他們正在腦中努力搜尋我的名字。
我在十四樓的走廊卸下行李,打開「家」門,兩年來我沒回來過幾次。這地方看起來十分可悲,布置得像大學宿舍、到處堆著未開封的郵件。我離開如此之久,連錄放影機都已經有新機型上市了,而我還是用著巨大的箱形電視,接著老式的卡匣錄影帶播放器。我的海外採訪任務還沒結束,但高層決定,現在該讓我把重心轉移到國內新聞,像是負責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並開始上主播臺播報新聞。
這段時間裡,我的個人生活有如荒原。我除了工作外的人際網絡本就少有聯繫,在海外採訪那段時間裡,更是大都失去聯絡了。那時我三十出頭,身邊朋友都已成雙成對或定了下來。與我同年紀的人大都成家立業,養育下一代了;反觀我自己,才剛結束一段轟轟烈烈但短暫的戀情,對象是我在伊拉克認識的西班牙記者。但我全心放在工作,穩定的情感關係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我回國沒多久便生了一種怪病,症狀有如流感,不時感到疲倦且全身疼痛,一直發冷,每次起床都十分艱難。我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一向疑神疑鬼,但這次不一樣,這情況持續了幾個月,期間我打了好幾通電話問爸媽,每次和他們傾吐一長串症狀記錄。我也接受不少檢驗,包括熱帶疾病、萊姆症,還有HIV病毒 ,我們也討論到了慢性疲勞症候群。
當檢驗報告出爐,都是陰性反應,於是我把矛頭轉向另一個原因:我的公寓瓦斯漏氣。我花了一大筆錢請人檢測整間屋子,所以有好幾個晚上都得跑去大學好友蕾吉娜(Regina)家睡地板。她是法學院畢業,自己開了一間引介法務人材的獵人頭公司。借宿那幾晚,她的迷你杜賓狗總是把飼料粒叼到我枕畔,在我耳邊喀喀大嚼。後來檢測結果顯示,瓦斯沒漏。我對蕾吉娜笑說,要是不趕快找到原因,我可能得承認自己腦筋短路了。
最後我終於崩潰,跑去看了心理醫師,他只花了五分鐘便作出診斷:憂鬱症。我位於紐約上東區的舒適辦公室中,定定告訴這位衣著休閒的和善醫生: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憂鬱啊。醫師解釋,患有憂鬱症而毫無感覺是完全可能的。當你愈試圖與自己的情緒全然切割,這些情緒往往會轉而影響你的生理狀況。
這話讓我茅塞頓開。我始終認為自己非常理性自覺,我的腦子像是個終年運轉的機器,不停安排、計劃與評估,但似乎遺漏了某些關鍵。那位醫師告訴我幾個理論,他說,我在海外目睹的事件太過駭人,可能超過我意識的處理能力;也可能是我潛意識裡對戰場的渴望激起我的腎上腺素--我基本上是患了新聞採訪海洛因戒斷症。也或許是這兩者的結合。醫師建議我服用抗憂鬱藥。
但不幸的是,我早就開始自行用藥了。
二○○一年十月,我第一次來到巴基斯坦,在此之前我從未踏上第三世界國家,除非你把我一九八○年代參加青少年營隊的墨西哥提華納(Tijuana)之旅也算在內。
接到國際新聞部來電隔天,我就搭上飛機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完全不知等在眼前會是什麼景況。我來到了一個英國朋友口中的「正統『星際大戰 』場景」。行李提領處擠滿了睡眼惺忪的旅客、神色木然的警察,還有身穿棕色油膩連身工作服的行李工人。
我是大廳中唯一的西方人,通關處的另一頭有個本地司機等著我,手上舉著我的名牌。外頭是早晨霧濛濛的空氣,溫暖且散發著一絲輪胎燒焦的氣味。高速公路上滿是龐大鮮豔的貨櫃車,司機不時按喇叭,發出微小不成調的聲音。我後來搞懂了,這裡的人按喇叭不全是為了要其他用路人讓開,只是想提醒別人他的存在,就像一道聲波。
我從未感到離家如此遙遠。
接著我們抵達旅館──出乎意料,居然是高檔的萬豪酒店(Marriott),而且還比一般的美國萬豪連鎖酒店更大、更氣派。我放下行李,直接上樓前往總統套房,ABC的新聞團隊在此進駐。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多同事,他們大多是倫敦分部的成員,待過波士尼亞跟盧安達,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樣。這樣危險貧困的國家與採訪環境,似乎根本不會造成他們任何認知失調。身穿制服的旅館服務生每天為我們送來兩次點心:保鮮膜包覆的盤子裡盛著餅乾與綜合堅果。我的同事鮑布.伍卓夫(Bob Woodruff)悶悶不樂的踱步進來,打電話給客房服務點了炒蛋。
然而,情勢不久後就變得棘手起來。要不了幾天,我就聽說阿富汗主政者塔利班 (Taliban)送來邀請,請我們前往坎大哈(Kandahar)的總部,算是隨軍採訪。乍看之下,這是絕對愚蠢的點子--深入敵營,還送上門作客──因此在新聞小組間激起熱烈辯論。我們特地召開了盛大的會議,仔細推敲了一番。我聽了正反兩方的意見,但其實結論早已預設了:我絕對不可能錯過這條大新聞。
我打電話給母親,想在她看到新聞前先告知我的去向,但無法接上她工作的醫院。於是我退而求其次,打電話告訴父親,他一向是比較情緒化的那位。我才講出計畫,父親便哭了,話筒兩頭一度靜默,只除了父親勉力調整呼吸的聲音。眼前的興奮退去,代之而起是深深的悔意,一直到此刻,我才從這趟旅程對我的意義中醒來,看到這件事可能對家人造成多大衝擊。父親很快便恢復常態,並使出他招牌的自貶式幽默:「你有猶太血統,只不過不是從你媽那裡來的。」
那晚我分外自責,而且坦白講,我害怕到無法成眠。隔天,我與幾個記者搭著巴士,前往未知的命運。那條將南阿富汗對分的主要幹道光禿禿的,車程漫長而顛簸,我們骨頭都快散了,總算在半夜抵達阿富汗的坎大哈外圍,停在一棟政府集合大樓前。美國空軍摧毀了此地的電力供應,因此整個城市漆黑一片。我們快速爬上某個大樓屋頂,架設衛星訊號並發送新聞,遠在紐約主播臺的彼德.詹寧斯詢問我這趟旅程的經過。彼德和我通話完畢後,趁著準備播新聞的空檔,特地打電話給我父母幫我報平安。
接下來超現實的三天讓人頭昏腦脹。我們被滿面虯髯、全副武裝的男子護送,繞行整個市區,我們多半只能參觀他們願意呈現的區域,做為宣傳目的,像是美國軍機炸毀的大樓,據稱有不少無辜平民喪命。但我印象最深的,卻是這些塔利班戰士私下的行事作風。
高層指揮官總是不停吹噓、宣導政令,但這些小兵十分不同,作風隨和,愛交朋友。他們其實只是孩子,還教我們說當地的髒話(顯然「驢子」在普什圖語 中帶有嚴重的侮辱意味)。還有一回,其中一個小兵悄聲對我說:「帶我去美國。」
我在報導中添加不少這類花絮,收到總部電郵表示讚許,這份量足以讓剛起步的新進記者輕飄飄而顧盼自得。彼德稱我是「我們派往阿富汗的人」。我的組員是兩個英國人,他們花上好幾個小時取笑我,說我以後回去會變成一個「超級爛人」。他們倆會假裝我回到紐約,跟朋友去酒吧的場景,模仿我每次打斷別人談話的開場白:「是是是……嘿我有跟你說過我在阿富汗的事嗎?」
這趟旅程讓我首次嘗到某種滋味,我會說,這就是新聞採訪的海洛因:純粹而病態的興奮刺激。你去到一個原本不該去的地方,不但全身而退,還能因此上電視。我上癮了。
當然,我回到紐約之後可沒有多少時間洋洋得意。迎接我的是一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負評報導,藝評人卡琳.詹姆斯(Caryn James)將我的採訪與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BBC)的並陳,讓我相形見絀,還稱我的版本「溫情而恍惚」。這對我的認知可謂沉重打擊。我感到有苦難言,絕不同意她的說法,但很多同事不這麼認為。她的評論坐實了我根本太嫩、不適任,讓我在公司馬上從英雄變成驢子。
幾星期後,國際新聞部決定再給我一次機會,這次要我去賓拉登 (Osama bin Laden)的托拉波拉(Tora Bora)洞穴基地,當時正遭到接受美方資助的阿富汗本地軍閥攻擊。我在搭計程車前往機場的途中接到彼德來電,他告訴我,大家一致認為我第一回合搞砸了,這次我真的得證明自己的能力。我整趟飛行途中,都像嬰兒般縮在椅子裡。
托拉波拉沒有萬豪酒店。抵達之後,我們來到一片冰雪覆蓋的罌粟花田,付錢給鴉片農場主人後,借宿在他田中幾間搖晃的土屋裡。門外拴著一頭臭烘烘的大公牛,每天我們回來吃晚飯時,院子裡跑跳的雞就又少了一隻。
我在這次任務中成功為自己平反。為我扭轉劣勢的部分原因來自某個場景,有錄影為證:那時我正站在山邊,對著鏡頭講話,錄製新聞帶的轉場,話才說到一半,一道聲響呼嘯越過我腦門上方。我從來沒有聽過近距離槍響,因此約一秒過後我才醒悟發生了什麼事,並趕緊趴倒在地。這可一點都不溫情也不恍惚了,我老闆挺欣賞的。
不過,這事還是有兩處地方挺糗的。第一,仔細看過影帶會發現,鏡頭後方的阿富汗人沒有一個找掩護的,他們根本不為所動;其次,我聽到子彈破空心裡的第一反應是:拜託要錄到啊!
這次是個全新的體驗。如果我不是有任務在身,那聲槍響肯定會嚇得我尿溼褲子。在我過去的生活經驗裡,全然找不出稱得上英勇的事蹟,我沒服過兵役,也沒參加過激烈的運動賽事如美式足球。我之前唯一碰過的危險,是在曼哈頓一處十字路口,沒仔細看路而被計程車撞上。
然而,當你站在鏡頭前做新聞採訪時,卻可能以為自己刀槍不入,像是你與世界之間隔著一道緩衝;如果散步時用耳機聽iPod會帶你遠離現實,那麼新聞採訪便是這種超現實的加乘版本。以戰事新聞來說,我亟欲參與重大新聞事件的渴望,完全掩埋了我對焦慮的本能反射作用。
捲入風暴,內心毫無波瀾
托拉波拉地區的軍事行動失敗了,據說賓拉登沿著小徑逃入巴基斯坦,但對我來說卻是重生的契機。重新得到上司的信任之後,接下來三年我不停往返紐約與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以及伊拉克等地。我像是伍迪.艾倫電影《變色龍》(Zelig)的主角西力(Zelig),以世界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為背景,從中謀得個人利益。
這些採訪任務迫使我一再親身經歷最為怪異可怖的場景。在以色列,一處海濱旅館遭到自殺式炸彈攻擊後,我看著一陣海風掀起了散落的床單,露出一排人腿。在伊拉克,我跟一群海軍陸戰隊員低頭看著一具倒在路邊的腫脹屍體,不約而同發現,那男屍臉上的不是槍孔,而是一個個用電鑽鑽出來的洞。在約旦河西岸,我站在一位父親身旁,看著挖土機剷起一具具屍體,倒入一處醫院停車場臨時挖好的大坑。那男子長聲慘嚎,尖銳淒厲,眼睜睜看著兒子屍體滾入坑裡。
儘管在那父親的哭聲前,我再也無法克制的走出攝影機鏡頭之外,喉頭堵得緊緊的,但我對戰場慘劇的反應,或者更準確的說,我對慘劇的毫無反應讓我吃驚。就我來看,我並不那麼難過。我說服自己,這份工作要求我保持心理上的距離,就像影集《外科醫生》(M * A* S* H)裡的醫生在手術檯上開病人的玩笑。我認為記者的抽離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標,如此才能更精準傳達出急迫的訊息。要是每次看到悲慘可怖的事件都要崩潰一次,那我如何做好這份工作?
回到家鄉,有人會問我,這些海外經驗是否「改變」了我。我的直覺反應是:沒有。那句老話「隨遇而安」,似乎挺貼切的。我還是一樣的我,只是在歷史上拿到了所謂前排的戲票。我父母擔心我目睹的一切會造成心理創傷,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受傷。正好相反,我喜歡當戰地記者。其實,我愛得很,隨身保鏢、裝甲車,讓人載著到處走,感覺像是元首級人物。我還喜歡防彈背心,讓我的小骨架在電視上有放大效果。
在戰區裡,一切規則都懸而不用,不必看交通號誌、速限,也不管社交禮儀。這種遊走在社會規範邊緣的活力,就像是大城市碰到大斷電或大風雪。而且,風險當然有另一番浪漫感受。我們常故意扭曲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沒什麼比中了彈卻安然無恙更讓人興奮的了。」
我喜歡的還不光是這層興奮,而是真心相信我們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親眼見證美國軍事力量的最前端。我有達成目的的使命感,這正是個值得冒險的目標。就為了追求快感與實踐原則這兩個因素,我放任自己捲入ABC惡名昭彰的內部競爭,只求留在權力核心。
外人可能會認為我們大部分時間用在與友臺記者一較高下,實際上,我們絕大部分精力用在與自己人競爭。為了卡好採訪前線位置,我開始留意到自己較勁的對象,例如剛從地方新聞調來的另一位年輕記者大衛.賴特(David Wright),他聰明又有衝勁,這點讓我有些不爽。
過去的我,曾樂於在資深記者爭奪大新聞時作壁上觀,但現在的我已更有自信競爭。爭奪新聞的方式主要是透過大肆遊說,例如不停打電話和寫電子郵件給分配採訪任務的主播和主管。內部角力儘管在許多方面促進了組織體質的健康與活力,但同時也十分緊繃,我不得不花上不成比例的時間來跟同事比較。例如,有一陣子賴特在阿富汗衝鋒陷陣,我卻被綁在紐約動彈不得,那時的新聞我一點都看不下去。
在戰場上一面採訪,一面還得跟後方爭取播出,實在夠變態的,但在我看來,這就是表演慾的本質。身為記者的絕大特權,就是能目睹世界級的大事,與事件要角互動,身歷其境,體驗其中原汁原味;儘管如此,另一個絕對的詛咒,也就是我在九一一事件學到的:記者看這些事件的部分角度,絕少不了自我利益的糾葛。我去得成嗎?我表現好嗎?這種心理極少在知名記者傳記中揭露,起碼我讀過的都沒有,但這層內心戲絕對是真的。
彼德就曾與同輩主播如泰德.柯佩爾(Ted Koppel)上演精采角力。前總裁魯尼.阿雷吉(Roone Arledge)在新聞部門建構起了一套明星制度,揉和封建分封領地的競爭本質,相互爭奪珍稀的有限資源,例如重大專訪跟優秀的特派記者等。巴格達淪陷後,賴特和我都爭著第一個搶進伊拉克,彼德甚至打電話來取笑我誇張的手段,但語帶讚許。
在這樣一個容忍大家把怒氣做為手段的環境,我有時會放任脾氣失控,這是我在二十出頭時就有的毛病。那時我還是個波士頓的年輕主播,有次我在進廣告後把文件往空中一丟,抗議某個技術問題。沒多久便被老闆叫進辦公室警告:「大家都不喜歡你。」那次會議讓我的心臟頓時提到喉頭,迫使我調整自己的行事作風。然而始終有改進空間;身為特派記者,我偶爾會與同事口角,甚至有幾次在國外採訪時發生愚蠢至極的衝突。有次我在巴基斯坦,置身於一場擁擠憤怒的街頭示威,居然毫不明智地與一名示威者對罵,只因為他說九一一事件的背後黑手其實是以色列。
我不得不收斂壞脾氣的狀況之一,當然就是面對彼德.詹寧斯的時候。
不憂鬱的憂鬱症
二○○三年七月的某個悶熱日子,我在曼哈頓上西區的公寓前下了計程車,彼時我剛結束為期五個月的伊拉克採訪,自美國全面入侵該地到叛亂開始前幾個月,我都一直待在那裡。從沙漠回來的感覺很奇特,這裡四處是落葉喬木,而我也不再需要任何隨從。門房一臉驚訝的看著我,我猜他們正在腦中努力搜尋我的名字。
我在十四樓的走廊卸下行李,打開「家」門,兩年來我沒回來過幾次。這地方看起來十分可悲,布置得像大學宿舍、到處堆著未開封的郵件。我離開如此之久,連錄放影機都已經有新機型上市了,而我還是用著巨大的箱形電視,接著老式的卡匣錄影帶播放器。我的海外採訪任務還沒結束,但高層決定,現在該讓我把重心轉移到國內新聞,像是負責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並開始上主播臺播報新聞。
這段時間裡,我的個人生活有如荒原。我除了工作外的人際網絡本就少有聯繫,在海外採訪那段時間裡,更是大都失去聯絡了。那時我三十出頭,身邊朋友都已成雙成對或定了下來。與我同年紀的人大都成家立業,養育下一代了;反觀我自己,才剛結束一段轟轟烈烈但短暫的戀情,對象是我在伊拉克認識的西班牙記者。但我全心放在工作,穩定的情感關係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我回國沒多久便生了一種怪病,症狀有如流感,不時感到疲倦且全身疼痛,一直發冷,每次起床都十分艱難。我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一向疑神疑鬼,但這次不一樣,這情況持續了幾個月,期間我打了好幾通電話問爸媽,每次和他們傾吐一長串症狀記錄。我也接受不少檢驗,包括熱帶疾病、萊姆症,還有HIV病毒 ,我們也討論到了慢性疲勞症候群。
當檢驗報告出爐,都是陰性反應,於是我把矛頭轉向另一個原因:我的公寓瓦斯漏氣。我花了一大筆錢請人檢測整間屋子,所以有好幾個晚上都得跑去大學好友蕾吉娜(Regina)家睡地板。她是法學院畢業,自己開了一間引介法務人材的獵人頭公司。借宿那幾晚,她的迷你杜賓狗總是把飼料粒叼到我枕畔,在我耳邊喀喀大嚼。後來檢測結果顯示,瓦斯沒漏。我對蕾吉娜笑說,要是不趕快找到原因,我可能得承認自己腦筋短路了。
最後我終於崩潰,跑去看了心理醫師,他只花了五分鐘便作出診斷:憂鬱症。我位於紐約上東區的舒適辦公室中,定定告訴這位衣著休閒的和善醫生: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憂鬱啊。醫師解釋,患有憂鬱症而毫無感覺是完全可能的。當你愈試圖與自己的情緒全然切割,這些情緒往往會轉而影響你的生理狀況。
這話讓我茅塞頓開。我始終認為自己非常理性自覺,我的腦子像是個終年運轉的機器,不停安排、計劃與評估,但似乎遺漏了某些關鍵。那位醫師告訴我幾個理論,他說,我在海外目睹的事件太過駭人,可能超過我意識的處理能力;也可能是我潛意識裡對戰場的渴望激起我的腎上腺素--我基本上是患了新聞採訪海洛因戒斷症。也或許是這兩者的結合。醫師建議我服用抗憂鬱藥。
但不幸的是,我早就開始自行用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