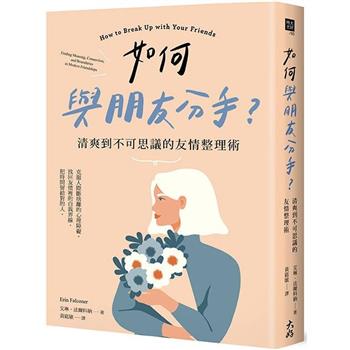Chapter 05:朋友越多,能付出的心力越少(節錄)
當我與女性朋友或同事交談時,我總是感到驚訝,她們每週都有六個「朋友聚會」,像是週日有產前派對、週四下班後會去小酌兩杯、週一相約做美甲,她們總是忙著購買禮物或預留活動時間。坦白說,光是聽她們說這些事,就覺得累了。這意味著我是一個糟糕的朋友嗎?為什麼我不想去做這些事呢?
在我開始為這本書做初步研究時,我突然明白了什麼。在《如何完成苦差事》一書中我寫道,我們把「忙碌」視為現代的炫耀方式,而實際上它是一種時髦的掩飾,是出於恐懼的過度安排(換句話說,即使是一秒鐘,我們也不想獨處)。同樣地,現代人也誤認為交友廣闊就能證明我們有價值。擁有許多「朋友」讓我們覺得自己很受歡迎,好讓我們能夠逃避自己,並幫助我們閃躲真正的關係所需要的親密感。這樣真的不太好。
這個領悟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動力之一,當友誼沒達到我們所知的應有價值時,就該採取行動了。你只能容納幾個人做你真正的朋友,想要更多也辦不到。有價值的友誼需要付出時間、功夫、努力和精力,而要對幾十位朋友都這樣付出,那是不可能的,這是簡單的數學。遺憾的是,社群媒體已經把這種友誼數學從基本算術推向了代數。
在個人的人際關係之外,我們開始擁護極簡主義。我們運用了令人怦然心動的整理技巧(謝啦,近藤麻理惠),並試圖在喧囂的世界過著專注的人生(卡爾,你的意思我們懂)。奇怪的是,這種極簡主義的概念並沒有被應用到生活中最重要的層面:我們的人際關係。少即是多,這是真的,我們的友誼也不例外。我們只需要在做到極簡的方法上,再建立一些規則架構即可。
文化評論家瑪麗亞.波波娃(Maria Popova)說:「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朋友』一詞已經完全淡化,幾乎毫無意義。你只要想想看,數一下在臉書上追蹤你,以及被列為『朋友』的人數。」平均每個人在臉書上有三百多名好友,哎呀!但老實說,其中很多都是夏令營朋友、已經五年沒見面的表兄弟姊妹,以及上上上個工作的同事。我們把幾乎不認識的人稱為「朋友」,我們把所有的同事稱為「朋友」,我們把相互欣賞誤以為是友誼,我們為了個人利益,誇耀和自己見過面的名人是「朋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對人友善是好事,這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也使我們變得更好。但我同意波波娃的觀點,我們正在淡化這個詞的含義。美國文學家愛默生對友誼的價值寫了很多文章,對此他也有強烈的感受:「我討厭人們濫用友誼之名,來指涉時髦與俗氣的人際結合。」
愛默生認為友誼有嚴格的定義,他說友誼是:
適合在所有的關係和生離死別的經歷中,提供幫助和安慰;適合寧靜的日子,適合高雅的才情,適合鄉間的漫步,但也適合崎嶇的道路和粗糙的飲食、船難、貧窮和迫害⋯⋯我們要為彼此的日常需要和人生職責賦予尊嚴,並用勇氣、智慧與和諧為友誼增添光彩。這種友誼永遠不該陷入某種尋常和妥協的情況中,而應該保持警覺和創意,並為原本索然無味的差事,增添韻律和理性。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但我不想和表妹的美髮師一起經歷船難,因為她只不過是我在表妹婚禮上認識的人。
用相同的稱謂來稱呼點頭之交和摯友,這麼做是在損害我們對友誼的感覺。我們還把自己置於棘手的境地,不曉得該對所有的「朋友」投入多少時間、情感和精力。如果我們回到亞里斯多德的建議,即最高形式的友誼是美德的一種,那會怎麼樣?亞里斯多德對友誼的描述包含了成長,其目的是幫助你不斷進步。
那麼,我們要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呢?友誼已經被社群媒體收編了,我們知道這些人脈是友善的,但不是由真正的朋友所組成。我建議對這些不同類型的關係用更準確的方式來描述,藉由確實地辨別出「職場朋友」、「學校朋友」和「寵物公園朋友」,我們就能把「朋友」的標籤留給那些與我們真正有交情的人。
如果我們希望透過改善友誼來改善我們的生活,那麼不妨去檢視你實際上能投入多少心力在幾位朋友身上。我們知道友誼需要用心,否則它們就會變質。所以,朋友的實際數量可以是多少呢?
牛津大學演化生物學家羅賓.鄧巴曾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從研究黑猩猩開始做起,看看牠們的大腦大小與社會群體大小之間的關係。接著,他從狩獵和採集生活為主的部落再到軍隊單位,檢視了各種人類社會,來了解人類大腦的大小與社交圈之間的關係。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對朋友的認知極限約為一百五十人,那是你的朋友圈;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一旦超出這個數字,在認知上你根本無從掌握。你認為是好朋友的人數自然還會更少,只有五十人。更上一層則是你有祕密或問題時會求助的人,大約有十五人。而最頂層的人,是你最親密的朋友,大約是五個人。
社群媒體讓我們能與更多人聯繫,這是我們原本不會或做不到的。對於住在遠方的家族成員或兒時朋友,要掌握他們的最新進展,運用社群媒體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你可以在朋友的小嬰兒照片上「按讚」;你可以在她抱怨先生的文章下面留一個含淚大笑的表情符號;你可以寄送生日祝福給你小學二年級的老師,但數位聯繫在某些方面無法模仿與朋友面對面相處的情況。你們會失去一起活動的即時體驗,因為即時體驗有時候是發生在不經意察覺的情況下,例如:你正在與朋友喝咖啡,她察覺到你發現她正在打量服務生,於是你們都笑翻了;或是,當她為失去親人而哭泣時,你也會流淚。另一點你無法用筆記型電腦取代的,是肢體感受的經驗。朋友會擁抱我們,碰一下我們的肩膀來強調一件事,或拍拍我們的背,這些都是在傳達感情,並觸發了大量的腦內啡。人類學家認為,靈長類動物在互相梳理毛髮時,腦內啡會激增,讓牠們對群體產生歸屬感,這會提高牠們的生存機會。由於我們知道孤獨的危險,人類的進化讓我們在親近自己關心的人會感覺很好,這是有道理的。疫情隔離期間,最苦澀的部分之一,不就是看到朋友用手勢示意的遠距「擁抱」嗎?也許社群媒體最大的壞處,就是營造出其他人比我們有更多的朋友,或是其他人與朋友相處得比我們更愉快。
Chapter 09:如何與朋友分手(節錄)
這是一條困難的路。當你體認到某人在你的生活中不再適合時,你仍然要去思考,一開始他們為什麼會出現在你身邊。摩爾和這個人有很多的冒險經歷和美好時光,她覺得要跟這位朋友分手很困難,這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著,『我能不能保有這些回憶,但我的生活中不要再出現你嗎?這要怎麼辦呢?我是否必須把一切都扔掉?我們去邁阿密、去牙買加旅行,所有那些歡樂時光——我是不是要把它們扔掉?』然後我意識到,不用,這些記憶仍然是美好的,那是我生命中的一段美好時光。」
有毒朋友並非每次都很難相處,否則他們也不會出現在你的生活中了,特別是如果惡質的人有一些自我覺察,她會用魅力或讚美來彌補她的惡毒行為。莎夏.唐有一位大學朋友,就遊走於惡劣和慷慨之間。「她以前會走在我前面,對我說非常不好的話,但事後她又會送我禮物,或為我做午餐,然後送到我工作的地方。這種情形是有毒的,我發現自己利用這段友誼來換取好東西,比如,我是大學生,我沒有錢,而你送了我衣服和東西。」莎夏.唐用一封電子郵件結束了這段關係,說出自己無法接受她的一些行為。「我記得她回信求我,說別這樣、別這樣、別這樣。我還記得,後來我沒有回信,而我感到非常自由。」
有時你被一個朋友甩了,但後來發覺雙方其實都有想結束的念頭。伊莉絲.羅南二十歲出頭時,被一位朋友甩了,但她一直不知道原因。「回想起來,我們有一種奇怪的依賴關係,我的作用幾乎像是她的男朋友,例如我會修理東西,我會把事情搞定。她沒有任何解釋就把我甩了,這實在太傷人了,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傷到她,所以我一直無法釋懷。」羅南試圖向這位朋友要求解釋,但從未收到,儘管她們的社交圈重疊,而且偶爾還會看到對方。「回想起來,我很高興,因為她其實在耗損我的心力。」
在人生中,有時你必須做正確的事,而這真的很難,與朋友分手就是其中之一,但你選擇的觀點可以徹底改變你的恐懼或憂慮。從前,如果人們的婚姻沒有維持五十年以上,我們就會認定婚姻失敗,如今隨著觀念不斷演進,情況不再如此。相同的道理,與朋友分手也是一樣的。如果一段友誼結束了,你把它視為失敗或浪費時間,你就沒有抓到重點,還會對你們雙方造成很大的傷害。請開始把關係結束視為已經走到盡頭,而不是徹底的失敗。當你明知這段友誼沒有作用也無法修復,卻選擇繼續維持,這才是唯一的失敗。因為如果你選擇結束,反而能保留與那個人在一起的所有美好時光,並從這個友情分手的經驗中記取教訓與重點。
當我與女性朋友或同事交談時,我總是感到驚訝,她們每週都有六個「朋友聚會」,像是週日有產前派對、週四下班後會去小酌兩杯、週一相約做美甲,她們總是忙著購買禮物或預留活動時間。坦白說,光是聽她們說這些事,就覺得累了。這意味著我是一個糟糕的朋友嗎?為什麼我不想去做這些事呢?
在我開始為這本書做初步研究時,我突然明白了什麼。在《如何完成苦差事》一書中我寫道,我們把「忙碌」視為現代的炫耀方式,而實際上它是一種時髦的掩飾,是出於恐懼的過度安排(換句話說,即使是一秒鐘,我們也不想獨處)。同樣地,現代人也誤認為交友廣闊就能證明我們有價值。擁有許多「朋友」讓我們覺得自己很受歡迎,好讓我們能夠逃避自己,並幫助我們閃躲真正的關係所需要的親密感。這樣真的不太好。
這個領悟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動力之一,當友誼沒達到我們所知的應有價值時,就該採取行動了。你只能容納幾個人做你真正的朋友,想要更多也辦不到。有價值的友誼需要付出時間、功夫、努力和精力,而要對幾十位朋友都這樣付出,那是不可能的,這是簡單的數學。遺憾的是,社群媒體已經把這種友誼數學從基本算術推向了代數。
在個人的人際關係之外,我們開始擁護極簡主義。我們運用了令人怦然心動的整理技巧(謝啦,近藤麻理惠),並試圖在喧囂的世界過著專注的人生(卡爾,你的意思我們懂)。奇怪的是,這種極簡主義的概念並沒有被應用到生活中最重要的層面:我們的人際關係。少即是多,這是真的,我們的友誼也不例外。我們只需要在做到極簡的方法上,再建立一些規則架構即可。
文化評論家瑪麗亞.波波娃(Maria Popova)說:「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朋友』一詞已經完全淡化,幾乎毫無意義。你只要想想看,數一下在臉書上追蹤你,以及被列為『朋友』的人數。」平均每個人在臉書上有三百多名好友,哎呀!但老實說,其中很多都是夏令營朋友、已經五年沒見面的表兄弟姊妹,以及上上上個工作的同事。我們把幾乎不認識的人稱為「朋友」,我們把所有的同事稱為「朋友」,我們把相互欣賞誤以為是友誼,我們為了個人利益,誇耀和自己見過面的名人是「朋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對人友善是好事,這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也使我們變得更好。但我同意波波娃的觀點,我們正在淡化這個詞的含義。美國文學家愛默生對友誼的價值寫了很多文章,對此他也有強烈的感受:「我討厭人們濫用友誼之名,來指涉時髦與俗氣的人際結合。」
愛默生認為友誼有嚴格的定義,他說友誼是:
適合在所有的關係和生離死別的經歷中,提供幫助和安慰;適合寧靜的日子,適合高雅的才情,適合鄉間的漫步,但也適合崎嶇的道路和粗糙的飲食、船難、貧窮和迫害⋯⋯我們要為彼此的日常需要和人生職責賦予尊嚴,並用勇氣、智慧與和諧為友誼增添光彩。這種友誼永遠不該陷入某種尋常和妥協的情況中,而應該保持警覺和創意,並為原本索然無味的差事,增添韻律和理性。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但我不想和表妹的美髮師一起經歷船難,因為她只不過是我在表妹婚禮上認識的人。
用相同的稱謂來稱呼點頭之交和摯友,這麼做是在損害我們對友誼的感覺。我們還把自己置於棘手的境地,不曉得該對所有的「朋友」投入多少時間、情感和精力。如果我們回到亞里斯多德的建議,即最高形式的友誼是美德的一種,那會怎麼樣?亞里斯多德對友誼的描述包含了成長,其目的是幫助你不斷進步。
那麼,我們要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呢?友誼已經被社群媒體收編了,我們知道這些人脈是友善的,但不是由真正的朋友所組成。我建議對這些不同類型的關係用更準確的方式來描述,藉由確實地辨別出「職場朋友」、「學校朋友」和「寵物公園朋友」,我們就能把「朋友」的標籤留給那些與我們真正有交情的人。
如果我們希望透過改善友誼來改善我們的生活,那麼不妨去檢視你實際上能投入多少心力在幾位朋友身上。我們知道友誼需要用心,否則它們就會變質。所以,朋友的實際數量可以是多少呢?
牛津大學演化生物學家羅賓.鄧巴曾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從研究黑猩猩開始做起,看看牠們的大腦大小與社會群體大小之間的關係。接著,他從狩獵和採集生活為主的部落再到軍隊單位,檢視了各種人類社會,來了解人類大腦的大小與社交圈之間的關係。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對朋友的認知極限約為一百五十人,那是你的朋友圈;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一旦超出這個數字,在認知上你根本無從掌握。你認為是好朋友的人數自然還會更少,只有五十人。更上一層則是你有祕密或問題時會求助的人,大約有十五人。而最頂層的人,是你最親密的朋友,大約是五個人。
社群媒體讓我們能與更多人聯繫,這是我們原本不會或做不到的。對於住在遠方的家族成員或兒時朋友,要掌握他們的最新進展,運用社群媒體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你可以在朋友的小嬰兒照片上「按讚」;你可以在她抱怨先生的文章下面留一個含淚大笑的表情符號;你可以寄送生日祝福給你小學二年級的老師,但數位聯繫在某些方面無法模仿與朋友面對面相處的情況。你們會失去一起活動的即時體驗,因為即時體驗有時候是發生在不經意察覺的情況下,例如:你正在與朋友喝咖啡,她察覺到你發現她正在打量服務生,於是你們都笑翻了;或是,當她為失去親人而哭泣時,你也會流淚。另一點你無法用筆記型電腦取代的,是肢體感受的經驗。朋友會擁抱我們,碰一下我們的肩膀來強調一件事,或拍拍我們的背,這些都是在傳達感情,並觸發了大量的腦內啡。人類學家認為,靈長類動物在互相梳理毛髮時,腦內啡會激增,讓牠們對群體產生歸屬感,這會提高牠們的生存機會。由於我們知道孤獨的危險,人類的進化讓我們在親近自己關心的人會感覺很好,這是有道理的。疫情隔離期間,最苦澀的部分之一,不就是看到朋友用手勢示意的遠距「擁抱」嗎?也許社群媒體最大的壞處,就是營造出其他人比我們有更多的朋友,或是其他人與朋友相處得比我們更愉快。
Chapter 09:如何與朋友分手(節錄)
這是一條困難的路。當你體認到某人在你的生活中不再適合時,你仍然要去思考,一開始他們為什麼會出現在你身邊。摩爾和這個人有很多的冒險經歷和美好時光,她覺得要跟這位朋友分手很困難,這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著,『我能不能保有這些回憶,但我的生活中不要再出現你嗎?這要怎麼辦呢?我是否必須把一切都扔掉?我們去邁阿密、去牙買加旅行,所有那些歡樂時光——我是不是要把它們扔掉?』然後我意識到,不用,這些記憶仍然是美好的,那是我生命中的一段美好時光。」
有毒朋友並非每次都很難相處,否則他們也不會出現在你的生活中了,特別是如果惡質的人有一些自我覺察,她會用魅力或讚美來彌補她的惡毒行為。莎夏.唐有一位大學朋友,就遊走於惡劣和慷慨之間。「她以前會走在我前面,對我說非常不好的話,但事後她又會送我禮物,或為我做午餐,然後送到我工作的地方。這種情形是有毒的,我發現自己利用這段友誼來換取好東西,比如,我是大學生,我沒有錢,而你送了我衣服和東西。」莎夏.唐用一封電子郵件結束了這段關係,說出自己無法接受她的一些行為。「我記得她回信求我,說別這樣、別這樣、別這樣。我還記得,後來我沒有回信,而我感到非常自由。」
有時你被一個朋友甩了,但後來發覺雙方其實都有想結束的念頭。伊莉絲.羅南二十歲出頭時,被一位朋友甩了,但她一直不知道原因。「回想起來,我們有一種奇怪的依賴關係,我的作用幾乎像是她的男朋友,例如我會修理東西,我會把事情搞定。她沒有任何解釋就把我甩了,這實在太傷人了,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傷到她,所以我一直無法釋懷。」羅南試圖向這位朋友要求解釋,但從未收到,儘管她們的社交圈重疊,而且偶爾還會看到對方。「回想起來,我很高興,因為她其實在耗損我的心力。」
在人生中,有時你必須做正確的事,而這真的很難,與朋友分手就是其中之一,但你選擇的觀點可以徹底改變你的恐懼或憂慮。從前,如果人們的婚姻沒有維持五十年以上,我們就會認定婚姻失敗,如今隨著觀念不斷演進,情況不再如此。相同的道理,與朋友分手也是一樣的。如果一段友誼結束了,你把它視為失敗或浪費時間,你就沒有抓到重點,還會對你們雙方造成很大的傷害。請開始把關係結束視為已經走到盡頭,而不是徹底的失敗。當你明知這段友誼沒有作用也無法修復,卻選擇繼續維持,這才是唯一的失敗。因為如果你選擇結束,反而能保留與那個人在一起的所有美好時光,並從這個友情分手的經驗中記取教訓與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