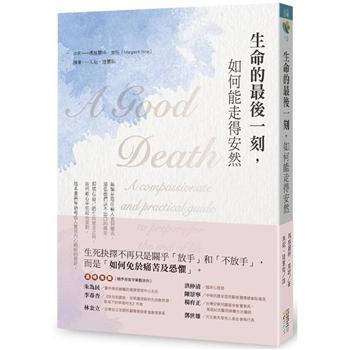在過去,想達到所謂「善終」,只能期盼命運別對自己和至愛的親人太嚴苛,但在醫療與藥物發展日新月異、安寧療護也逐漸為大眾認知與接受的今日,藉由症狀治療、止痛藥物、心理輔導,再加上親近家人的陪伴,無痛無憾、保有尊嚴的離世,已是一個可能達成的目標。
陪在臨終者身旁
有明確的證據顯示,在步向生命終點時若有人陪在身旁,臨終者會感到安心,恐懼也能平復。而能夠陪著你所愛的人走到生命終點,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經驗,將會讓你學到更多關於生命的一切。
美國安寧療護護理師喬伊・烏菲瑪認為,臨終者最害怕的兩件事,是疼痛與被遺棄。現代醫學與藥物雖能幫臨終者緩解身體的症狀與疼痛,但無論能把多少位專業醫護召集過來,病人從臨終到過世,陪在床畔最重要的人還是親近的家屬。
「如果一個人過世時沒有疼痛、被家人圍繞,而且那些家人是看著他們的至愛以符合其心願的方式過世,這樣就別無所求了。」安寧療護專科醫生麥可・巴巴托表示。
當親近的人即將過世,家屬需要具備點想像力。臨終者需要什麼東西、想聽些什麼話、想見到誰?有什麼能幫助他們安心離世?家屬和密友會比專業醫護更瞭解病人較偏好身旁擺放哪些物品。你可以為臨終者營造一個祥和並能給予慰藉的環境。例如收集臨終者想聽的音樂並放給他們聽,周遭放置他們偏愛的盆栽種類,在牆上掛他們喜愛的裝飾、照片或圖畫。
當你坐在臨終者床畔陪伴時,以下是你能做的一些簡單事項。這些建議沒有一項需要特殊技巧,也不會妨礙專業者的照護工作,對臨終者也不會造成危害。
*跟病人說話、唸他們最喜愛的文章或書籍、唱歌給他們聽。聽覺是臨終者最後喪失的一項感官知覺。
*其餘時間不妨就安靜坐著。這是把「別只是坐著,做點什麼」的想法,翻轉成「什麼都別做,只要坐著就好」的時候。
*傾聽。臨終者也許會說些似乎毫無意義的話,不過他們有可能是藉由隱喻來表達。臨終者會把夢境及現實、當下和過去混在一起。他們也許會看到過世已久的朋友或親戚,並跟對方說話。當他們這麼做,不妨傾聽並支持他們。不妨跟在場的其他人交談。無須輕聲細語,而是用正常的音量跟家人說話。即使臨終者可能沒辦法理解你們在說什麼,但他們會認出你們的聲音,這樣就會感到自己並不孤單。臨終者會樂於聽見家人與親友在周遭,就如他們在神智清醒但病得太重、而無法參與談話時一樣。
你也可以主動為臨終者舒緩不適:
*滋潤他們的口腔和嘴唇。在過世之前,臨終者不會口渴或有食慾,因為隨著身體功能開始停止運作,他們不再需要吃喝。不過他們可能會因口腔乾燥而感到不舒服。這種情況在臨終者身上很常見,這是由於在生命最後階段沒有喝水,口腔內會形成黏稠的唾液。不妨使用沾水的棉棒清潔他們的口腔,濕潤舌頭底下及口腔側壁,使口腔清爽。可以每十五分鐘做一次。或許你也可為他們塗點清新薄荷味的口腔舒緩凝膠。這麼做不僅是為了讓臨終者較舒適,也能讓你感到安慰,因為這容許你跟臨終者有身體上的接觸。
*梳理他們的頭髮,尤其如果他們神智清醒時也喜歡這樣的話。
*如果病人在臨終照護之家或醫院,騰出空間讓護理師可以至少每四小時替臨終者翻身一次,以避免壓瘡形成,一直到他們陷入昏迷。對於已經無法清楚說明疼痛來源的病人來說,壓瘡會增加不必要的疼痛,而且可能被誤認為躁動。若你是在家中看護臨終者,需確保至少每四小時將他們稍微抬起來翻身一次。
替臨終者舒緩不適,或許能讓你的家人覺得你提供了實質的照護,並且之後也會有助你克服喪親之痛。
至親過世後需面對什麼事?
我詢問我母親入住的安養院工作人員,我和我的姐妹們能否替她洗身和做入殮準備。我們沒有受過相關的正式訓練,也有點怕會遇到什麼意外狀況,所以由我的弟媳瑪麗——她是一位受過訓練的專業護士——來帶領我們,並示範怎麼做。那是一段平靜的時光;當我們清洗媽媽的頭髮和身體的同時,不知怎麼的,我感到很寬慰,彷彿我們正在給予她某種撫慰與安寧、一劑解除她生前經歷的疼痛與折磨的解藥,雖然我們無力挽回她的性命。
無論臨終者是在醫院還是照護之家過世,家屬都有權陪伴那個剛過世的人。通常護理師會來為大體做入殮準備,同時遵守必要的任何宗教習俗,而醫院工作人員會負責準備死亡證明。如果臨終者是在家中過世,沒有任何醫療專業者在場,那麼你可能須先確定,親屬當中,是否有人會希望在大體移出家裡之前看看他,做最後的道別?家人可先拉直過世者的身體,然後在他的後頸與下巴底下各放一條捲起來的毛巾,這樣過世者的嘴巴便會保持閉合,否則就會一直開著。接著打電話給在病人臨終期間負責診治的執業醫生,由他來開死亡證明。
為過世者做準備的這些工作,是直到最近的約一百年間,家屬才交由外人代勞。但目前出現一個跨國運動,提倡並教導人們為自己的過世親人洗身、做入殮準備、及籌劃葬儀。今日,有更多人開始重新學習照料過世者的古老技巧,你也能夠做到。
即使不是由你清洗大體,但你也可在場,並參與大體入殮的一些準備工作。但須留意的是,你需要在親人過世之前,及早跟禮儀公司安排好,因為家屬對於到場參與的態度,以及禮儀公司容許他們參與到什麼程度,都有不同。
可以確定的是,有過這個經驗的很多人,都發現它是一種非常療癒的心靈體驗。
如果你決定不照常規,例如想親自為大體做入殮準備,務必事先告知醫院或安養院,這樣他們才不會自動開始進行他們認定你會遵循的一套不同流程。此外,最好先確定你計畫要做的事是合法的。事先準備好正確的文件,例如准許你運送大體的許可等,將有助讓已經很艱難的悲傷時刻變得稍微輕鬆些,尤其若你打算做的是非常規的事,例如開自己的車運送大體等。
家屬還須辦理過世者的死亡登記。在新南威爾斯省,死亡通知必須在土葬或火葬後七天內,交給負責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記的戶籍登記官;這通常是禮儀師負責的工作之一。澳洲別的省份或是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要求。
家屬還須處理的另一件事是辦理遺囑認證。這項工作通常交由律師處理,但由你親自處理,不僅可省下一筆錢,而且根據曾親自處理的過來人所言,這是一種有助增強自信的經驗。不過,如果遺產包括多項複雜的資產,例如房地產、股票和投資,那麼最好還是交由經驗老道的遺產繼承律師來辦。應對悲傷
出生、死亡、愛,都是人生最重要的經歷,也是我們的喜悅與痛苦的源頭。愛與悲交織。有人說,你沒先去愛,就無法感受到悲傷。因此,也許我們愈愛某個人,當他們過世,我們也會愈悲傷。
對於處於悲傷的人,正式的心理諮商,以及親朋好友的傾聽與陪伴,有極大幫助。當處於悲傷最嚴重的階段,尤其是突然遇到、或短時間內接連遇到幾名親友過世,可能會讓人很難相信人生將有否極泰來的一天。即使在遭受喪親之痛打擊後,悲傷很難馬上開始漸漸減輕,但拒絕讓喪慟界定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生是會跟過去不同,但你將會好轉。
關於悲傷的新理論(或者是老生常談?)告訴我們,痛失至親是讓一個人成長的契機。在我弟弟朱利安意外過世後,我個人的悲傷歷程,讓我陷入非常陰暗的境地——哀痛、沮喪、無法工作,並開始質疑自己的婚姻,因為我惱怒我的丈夫在面對我悲傷時的處理方式,家人之間的關係也出現根本上的轉變。當中沒有一項會讓我希望或要求再體驗一次。但透過個人的傷痛,我被迫去學習、摒棄舊觀念、改變自己的思維,因而讓我能夠找到新的方式,去重新過日子。我找諮商師輔導,學習正念。我閱讀書籍,並認識一些我從前不會去來往的人。我以一種想不到的方式成長了。
我體認到自己的生命被一分為二:朱利安過世前,與朱利安過世後。在前半段的人生中,每當見到一個老人走在路上,我看到的是凋零、衰老與枯朽。但這些日子以來,每當我見到老年人,我都會自問,他們曾勇敢地承受了多少次喪慟。我好奇他們參加過多少朋友和親兄弟姐妹的葬禮。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令人敬佩的堅強與力量。我看到的是戰士。他們學會了放手,以及從放手中繼續過自己的日子。他們明白什麼叫孑然一身。
以下是為悲傷的人提供支持的幾個簡單關懷:
*如果對方看似沒有「比較平復」,毋須過於擔憂;別覺得你應該催他們加快速度。
*如果你很擔心他們儘管已經心情低落了非常之久,卻還是無法放下,就該懷疑他們的悲傷是否已轉變成憂鬱症。不妨留意他們是否拒絕讓你設法替他們換個環境。
*陪伴他們。當輪到自己時
說來矛盾,為了簡單瀟灑的走,為了在合理範圍內能盡量多由我們自己掌控的離世,我們就必須超前部署。為善終預做規劃,就跟好的財務規劃一樣,能為自己和家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也能在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之際減少許多憂慮和牽掛,讓自己較可依本身希望的方式,安然的離世。
最切身相關的是預立醫療指示。當你過於衰弱或失能,無法跟醫護人員妥善溝通時,你早已寫好的預立醫療指示,便是一個很好的依據,讓醫護人員得以照你的意願做或不做某些醫療處置。但在填寫預立醫療指示時,有幾點必須仔細考量:
*若我因某一疾病病危而接受急救,那麼當我因其他疾病或重傷命危,也會同意急救嗎?
*該如何為自己安排最適合善終的環境?我是否想在醫院加護病房過世?還是希望在家裡過世,有家人陪伴在側?或是在安寧療護病房,或在安養院?
*我的經濟狀況是否負擔得起,還有我的選項是否會因財務問題而受限?
*如果我可能快要過世,如何能讓我安適的離去?
*對於為延長性命所做的治療,例如動心臟手術,以及能讓我較舒服並減輕疼痛、但無法醫治疾病的治療,我是否瞭解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另外,最好預先規劃遺囑內容,然後定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更新。你也需指定授權人以及替代決策人,以便在你失能或其他因素無法親自討論時,授權人可代替你處理財務,而替代決策人可代你跟醫護專業者討論協商,及做醫療處置等方面的決定。
為善終預做規劃,能替自己和家人少些牽掛與煩惱,也能在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之際減少憂慮不安,讓自己較可依本身希望的方式,安然的離世。
陪在臨終者身旁
有明確的證據顯示,在步向生命終點時若有人陪在身旁,臨終者會感到安心,恐懼也能平復。而能夠陪著你所愛的人走到生命終點,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經驗,將會讓你學到更多關於生命的一切。
美國安寧療護護理師喬伊・烏菲瑪認為,臨終者最害怕的兩件事,是疼痛與被遺棄。現代醫學與藥物雖能幫臨終者緩解身體的症狀與疼痛,但無論能把多少位專業醫護召集過來,病人從臨終到過世,陪在床畔最重要的人還是親近的家屬。
「如果一個人過世時沒有疼痛、被家人圍繞,而且那些家人是看著他們的至愛以符合其心願的方式過世,這樣就別無所求了。」安寧療護專科醫生麥可・巴巴托表示。
當親近的人即將過世,家屬需要具備點想像力。臨終者需要什麼東西、想聽些什麼話、想見到誰?有什麼能幫助他們安心離世?家屬和密友會比專業醫護更瞭解病人較偏好身旁擺放哪些物品。你可以為臨終者營造一個祥和並能給予慰藉的環境。例如收集臨終者想聽的音樂並放給他們聽,周遭放置他們偏愛的盆栽種類,在牆上掛他們喜愛的裝飾、照片或圖畫。
當你坐在臨終者床畔陪伴時,以下是你能做的一些簡單事項。這些建議沒有一項需要特殊技巧,也不會妨礙專業者的照護工作,對臨終者也不會造成危害。
*跟病人說話、唸他們最喜愛的文章或書籍、唱歌給他們聽。聽覺是臨終者最後喪失的一項感官知覺。
*其餘時間不妨就安靜坐著。這是把「別只是坐著,做點什麼」的想法,翻轉成「什麼都別做,只要坐著就好」的時候。
*傾聽。臨終者也許會說些似乎毫無意義的話,不過他們有可能是藉由隱喻來表達。臨終者會把夢境及現實、當下和過去混在一起。他們也許會看到過世已久的朋友或親戚,並跟對方說話。當他們這麼做,不妨傾聽並支持他們。不妨跟在場的其他人交談。無須輕聲細語,而是用正常的音量跟家人說話。即使臨終者可能沒辦法理解你們在說什麼,但他們會認出你們的聲音,這樣就會感到自己並不孤單。臨終者會樂於聽見家人與親友在周遭,就如他們在神智清醒但病得太重、而無法參與談話時一樣。
你也可以主動為臨終者舒緩不適:
*滋潤他們的口腔和嘴唇。在過世之前,臨終者不會口渴或有食慾,因為隨著身體功能開始停止運作,他們不再需要吃喝。不過他們可能會因口腔乾燥而感到不舒服。這種情況在臨終者身上很常見,這是由於在生命最後階段沒有喝水,口腔內會形成黏稠的唾液。不妨使用沾水的棉棒清潔他們的口腔,濕潤舌頭底下及口腔側壁,使口腔清爽。可以每十五分鐘做一次。或許你也可為他們塗點清新薄荷味的口腔舒緩凝膠。這麼做不僅是為了讓臨終者較舒適,也能讓你感到安慰,因為這容許你跟臨終者有身體上的接觸。
*梳理他們的頭髮,尤其如果他們神智清醒時也喜歡這樣的話。
*如果病人在臨終照護之家或醫院,騰出空間讓護理師可以至少每四小時替臨終者翻身一次,以避免壓瘡形成,一直到他們陷入昏迷。對於已經無法清楚說明疼痛來源的病人來說,壓瘡會增加不必要的疼痛,而且可能被誤認為躁動。若你是在家中看護臨終者,需確保至少每四小時將他們稍微抬起來翻身一次。
替臨終者舒緩不適,或許能讓你的家人覺得你提供了實質的照護,並且之後也會有助你克服喪親之痛。
至親過世後需面對什麼事?
我詢問我母親入住的安養院工作人員,我和我的姐妹們能否替她洗身和做入殮準備。我們沒有受過相關的正式訓練,也有點怕會遇到什麼意外狀況,所以由我的弟媳瑪麗——她是一位受過訓練的專業護士——來帶領我們,並示範怎麼做。那是一段平靜的時光;當我們清洗媽媽的頭髮和身體的同時,不知怎麼的,我感到很寬慰,彷彿我們正在給予她某種撫慰與安寧、一劑解除她生前經歷的疼痛與折磨的解藥,雖然我們無力挽回她的性命。
無論臨終者是在醫院還是照護之家過世,家屬都有權陪伴那個剛過世的人。通常護理師會來為大體做入殮準備,同時遵守必要的任何宗教習俗,而醫院工作人員會負責準備死亡證明。如果臨終者是在家中過世,沒有任何醫療專業者在場,那麼你可能須先確定,親屬當中,是否有人會希望在大體移出家裡之前看看他,做最後的道別?家人可先拉直過世者的身體,然後在他的後頸與下巴底下各放一條捲起來的毛巾,這樣過世者的嘴巴便會保持閉合,否則就會一直開著。接著打電話給在病人臨終期間負責診治的執業醫生,由他來開死亡證明。
為過世者做準備的這些工作,是直到最近的約一百年間,家屬才交由外人代勞。但目前出現一個跨國運動,提倡並教導人們為自己的過世親人洗身、做入殮準備、及籌劃葬儀。今日,有更多人開始重新學習照料過世者的古老技巧,你也能夠做到。
即使不是由你清洗大體,但你也可在場,並參與大體入殮的一些準備工作。但須留意的是,你需要在親人過世之前,及早跟禮儀公司安排好,因為家屬對於到場參與的態度,以及禮儀公司容許他們參與到什麼程度,都有不同。
可以確定的是,有過這個經驗的很多人,都發現它是一種非常療癒的心靈體驗。
如果你決定不照常規,例如想親自為大體做入殮準備,務必事先告知醫院或安養院,這樣他們才不會自動開始進行他們認定你會遵循的一套不同流程。此外,最好先確定你計畫要做的事是合法的。事先準備好正確的文件,例如准許你運送大體的許可等,將有助讓已經很艱難的悲傷時刻變得稍微輕鬆些,尤其若你打算做的是非常規的事,例如開自己的車運送大體等。
家屬還須辦理過世者的死亡登記。在新南威爾斯省,死亡通知必須在土葬或火葬後七天內,交給負責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記的戶籍登記官;這通常是禮儀師負責的工作之一。澳洲別的省份或是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要求。
家屬還須處理的另一件事是辦理遺囑認證。這項工作通常交由律師處理,但由你親自處理,不僅可省下一筆錢,而且根據曾親自處理的過來人所言,這是一種有助增強自信的經驗。不過,如果遺產包括多項複雜的資產,例如房地產、股票和投資,那麼最好還是交由經驗老道的遺產繼承律師來辦。應對悲傷
出生、死亡、愛,都是人生最重要的經歷,也是我們的喜悅與痛苦的源頭。愛與悲交織。有人說,你沒先去愛,就無法感受到悲傷。因此,也許我們愈愛某個人,當他們過世,我們也會愈悲傷。
對於處於悲傷的人,正式的心理諮商,以及親朋好友的傾聽與陪伴,有極大幫助。當處於悲傷最嚴重的階段,尤其是突然遇到、或短時間內接連遇到幾名親友過世,可能會讓人很難相信人生將有否極泰來的一天。即使在遭受喪親之痛打擊後,悲傷很難馬上開始漸漸減輕,但拒絕讓喪慟界定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生是會跟過去不同,但你將會好轉。
關於悲傷的新理論(或者是老生常談?)告訴我們,痛失至親是讓一個人成長的契機。在我弟弟朱利安意外過世後,我個人的悲傷歷程,讓我陷入非常陰暗的境地——哀痛、沮喪、無法工作,並開始質疑自己的婚姻,因為我惱怒我的丈夫在面對我悲傷時的處理方式,家人之間的關係也出現根本上的轉變。當中沒有一項會讓我希望或要求再體驗一次。但透過個人的傷痛,我被迫去學習、摒棄舊觀念、改變自己的思維,因而讓我能夠找到新的方式,去重新過日子。我找諮商師輔導,學習正念。我閱讀書籍,並認識一些我從前不會去來往的人。我以一種想不到的方式成長了。
我體認到自己的生命被一分為二:朱利安過世前,與朱利安過世後。在前半段的人生中,每當見到一個老人走在路上,我看到的是凋零、衰老與枯朽。但這些日子以來,每當我見到老年人,我都會自問,他們曾勇敢地承受了多少次喪慟。我好奇他們參加過多少朋友和親兄弟姐妹的葬禮。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令人敬佩的堅強與力量。我看到的是戰士。他們學會了放手,以及從放手中繼續過自己的日子。他們明白什麼叫孑然一身。
以下是為悲傷的人提供支持的幾個簡單關懷:
*如果對方看似沒有「比較平復」,毋須過於擔憂;別覺得你應該催他們加快速度。
*如果你很擔心他們儘管已經心情低落了非常之久,卻還是無法放下,就該懷疑他們的悲傷是否已轉變成憂鬱症。不妨留意他們是否拒絕讓你設法替他們換個環境。
*陪伴他們。當輪到自己時
說來矛盾,為了簡單瀟灑的走,為了在合理範圍內能盡量多由我們自己掌控的離世,我們就必須超前部署。為善終預做規劃,就跟好的財務規劃一樣,能為自己和家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也能在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之際減少許多憂慮和牽掛,讓自己較可依本身希望的方式,安然的離世。
最切身相關的是預立醫療指示。當你過於衰弱或失能,無法跟醫護人員妥善溝通時,你早已寫好的預立醫療指示,便是一個很好的依據,讓醫護人員得以照你的意願做或不做某些醫療處置。但在填寫預立醫療指示時,有幾點必須仔細考量:
*若我因某一疾病病危而接受急救,那麼當我因其他疾病或重傷命危,也會同意急救嗎?
*該如何為自己安排最適合善終的環境?我是否想在醫院加護病房過世?還是希望在家裡過世,有家人陪伴在側?或是在安寧療護病房,或在安養院?
*我的經濟狀況是否負擔得起,還有我的選項是否會因財務問題而受限?
*如果我可能快要過世,如何能讓我安適的離去?
*對於為延長性命所做的治療,例如動心臟手術,以及能讓我較舒服並減輕疼痛、但無法醫治疾病的治療,我是否瞭解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另外,最好預先規劃遺囑內容,然後定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更新。你也需指定授權人以及替代決策人,以便在你失能或其他因素無法親自討論時,授權人可代替你處理財務,而替代決策人可代你跟醫護專業者討論協商,及做醫療處置等方面的決定。
為善終預做規劃,能替自己和家人少些牽掛與煩惱,也能在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之際減少憂慮不安,讓自己較可依本身希望的方式,安然的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