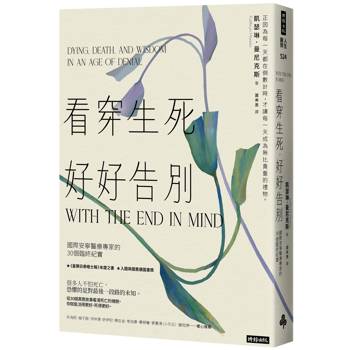序言/該是談論死亡的時候了
已經花了大半輩子陪伴臨終者,卻還想用更多時間來講述他們的故事,似乎有些奇怪;甚至還寄望讀者會選擇透過書頁來關懷臨終的陌生人,更加顯得狂妄。然而,這正是我下筆時的期望。
在我的行醫生涯裡,我一直都清楚地意識到,每當我們遇到重大變故時,我們都懷揣著自己的想法與期望。無論是生、死、愛、失去或轉變,每個人都是透過早已知悉的觀點來架構自己的體驗。問題在於,關於生、愛及喪慟(bereavement)均有廣泛討論,死亡本身卻逐漸變成一種禁忌。由於不知道自己將面對什麼,人們轉而從替代體驗中尋找線索:電視、電影、小說、社群媒體與新聞。這些誇大卻又過度簡化的臨終與死亡版本,取代了以往的普遍體驗:觀察生活圈裡的死亡、目睹足夠多的死亡以致能辨認其模式、知曉在活力消退的限制下也能過好生活,甚至對死亡過程產生熟悉感。
這般的過往智慧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消失無蹤。更好的醫療照護(如抗生素、腎透析與早期化療)、更好的營養、免疫接種及其他發展,已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疾病體驗,這些進步帶來治癒的希望,或者至少延後死亡,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然而,這也造成行為模式的改變,病入膏肓之人被送進醫院治療,而不是在家中等待死去。平均壽命增加,許多生命得到增強與延長。
然而,這些令人欣喜的醫療進步,僅能在一定程度內拯救我們;一旦超過能讓我們活得「還可以」的界線,便進入了徒勞無功的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科技變成一種新的臨終儀式,象徵著對死亡的否認,凌駕於對死亡的接受與體驗。但死亡率仍是百分之百,生命最後時日的模式與我們死去的方式,也沒有改變。不同的是,我們喪失了以往對整個過程的熟悉感,不再擁有從前那一套幫助我們應對死亡的詞彙及禮儀?那時人們還承認死亡是必然之事。如今我們不再是死在親切熟悉的房間裡,被所愛之人環繞,而是死在救護車上、急診室與加護病房裡,生命維持儀器隔開了我們與所愛之人。
本書講述的皆為真實事件,每一例均真實發生在過去四十年內某段時間的某個人身上。為了保護個人隱私,他們的名字均已更改,他們的工作、甚至性別或種族也已抽換。由於這些是故事,而不是病史,有時會將數人的經歷交織在一個人的敘述中,以描繪臨終旅程的各個層面。書中的許多情況或許會似曾相識,因為即便我們別過頭,死亡仍是無可避免的,這些故事將與許多人自身的經歷相似。
由於我的整個生涯大多從事緩和療護(palliative care)工作,大多數的故事難免與那些會接觸到緩和療護專家的人有關。這一般意味著他們身上棘手的生理症狀已獲得治療,且通常控制得當,情緒症狀亦得到妥善處理。緩和療護並不僅僅關乎死亡:人們在生病的任何階段,無論診斷結果為何,只要是有所需求時,都應該要能獲得良好的症狀管理。這正是緩和醫學專業的廣泛職責所在。然而,我們接觸的患者大多數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我們因而能了解到,當人們知道自己即將死亡的時候是如何生活。這部分的體驗正是我試圖透過本書故事所要傳達的:臨終之人仍在努力好好過生活,和我們其他人並無二致。
總的來說,我將我的眼睛與耳朵、我的病床邊視角、我參與的對話,以及我對事情的看法提供給讀者。若有什麼足以作為我們的借鑑,那是故事裡的主角們所給予的饋贈。若有錯誤,則由我全責負擔。
該是談論死亡的時候了。這就是我推動這場重要對話的方式。
已經花了大半輩子陪伴臨終者,卻還想用更多時間來講述他們的故事,似乎有些奇怪;甚至還寄望讀者會選擇透過書頁來關懷臨終的陌生人,更加顯得狂妄。然而,這正是我下筆時的期望。
在我的行醫生涯裡,我一直都清楚地意識到,每當我們遇到重大變故時,我們都懷揣著自己的想法與期望。無論是生、死、愛、失去或轉變,每個人都是透過早已知悉的觀點來架構自己的體驗。問題在於,關於生、愛及喪慟(bereavement)均有廣泛討論,死亡本身卻逐漸變成一種禁忌。由於不知道自己將面對什麼,人們轉而從替代體驗中尋找線索:電視、電影、小說、社群媒體與新聞。這些誇大卻又過度簡化的臨終與死亡版本,取代了以往的普遍體驗:觀察生活圈裡的死亡、目睹足夠多的死亡以致能辨認其模式、知曉在活力消退的限制下也能過好生活,甚至對死亡過程產生熟悉感。
這般的過往智慧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消失無蹤。更好的醫療照護(如抗生素、腎透析與早期化療)、更好的營養、免疫接種及其他發展,已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疾病體驗,這些進步帶來治癒的希望,或者至少延後死亡,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然而,這也造成行為模式的改變,病入膏肓之人被送進醫院治療,而不是在家中等待死去。平均壽命增加,許多生命得到增強與延長。
然而,這些令人欣喜的醫療進步,僅能在一定程度內拯救我們;一旦超過能讓我們活得「還可以」的界線,便進入了徒勞無功的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科技變成一種新的臨終儀式,象徵著對死亡的否認,凌駕於對死亡的接受與體驗。但死亡率仍是百分之百,生命最後時日的模式與我們死去的方式,也沒有改變。不同的是,我們喪失了以往對整個過程的熟悉感,不再擁有從前那一套幫助我們應對死亡的詞彙及禮儀?那時人們還承認死亡是必然之事。如今我們不再是死在親切熟悉的房間裡,被所愛之人環繞,而是死在救護車上、急診室與加護病房裡,生命維持儀器隔開了我們與所愛之人。
本書講述的皆為真實事件,每一例均真實發生在過去四十年內某段時間的某個人身上。為了保護個人隱私,他們的名字均已更改,他們的工作、甚至性別或種族也已抽換。由於這些是故事,而不是病史,有時會將數人的經歷交織在一個人的敘述中,以描繪臨終旅程的各個層面。書中的許多情況或許會似曾相識,因為即便我們別過頭,死亡仍是無可避免的,這些故事將與許多人自身的經歷相似。
由於我的整個生涯大多從事緩和療護(palliative care)工作,大多數的故事難免與那些會接觸到緩和療護專家的人有關。這一般意味著他們身上棘手的生理症狀已獲得治療,且通常控制得當,情緒症狀亦得到妥善處理。緩和療護並不僅僅關乎死亡:人們在生病的任何階段,無論診斷結果為何,只要是有所需求時,都應該要能獲得良好的症狀管理。這正是緩和醫學專業的廣泛職責所在。然而,我們接觸的患者大多數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我們因而能了解到,當人們知道自己即將死亡的時候是如何生活。這部分的體驗正是我試圖透過本書故事所要傳達的:臨終之人仍在努力好好過生活,和我們其他人並無二致。
總的來說,我將我的眼睛與耳朵、我的病床邊視角、我參與的對話,以及我對事情的看法提供給讀者。若有什麼足以作為我們的借鑑,那是故事裡的主角們所給予的饋贈。若有錯誤,則由我全責負擔。
該是談論死亡的時候了。這就是我推動這場重要對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