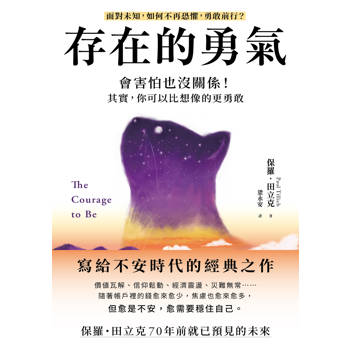內文選摘(節錄)
第二章 存有、非存有與焦慮
1一種焦慮的存有論
非存有的意義
勇氣是一種具有「不理會」性質的自我肯定:它不理會那些阻止一己進行自我肯定的東西。不同於斯多噶主義和新斯多噶主義的勇氣學說,「生命哲學」嚴肅且肯定的看待與勇氣相對立的部分。因為,如果「存有」被詮釋為生命、過程或生成(becoming)的話,那麼「非存有」在存有論的地位就和「存有」一樣基本。承認這個事實,並不代表要做出「存有」優於「非存有」的判斷,而是要求在存有論的基礎上思考「非存有」。在談到勇氣做為解釋「存有自身」的一把鑰匙時,我們可以說,當這把鑰匙打開存有的門時,也就同時找到了存有、對存有的否定和兩者的統一。
勇氣通常被形容為心靈克服恐懼的力量。恐懼(fear)的意義看似一目了然、不值得探究。但在過去二十年間,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編按:一個心理學流派,探討潛意識與無意識的深層心理結構,精神分析是其中一環)和存在主義哲學的合作帶來了對恐懼和焦慮(anxiety)的嚴格區分,也為這兩個概念帶來更精確的定義。目前的社會學分析指出,焦慮是一個重要的群體現象;文學和藝術無論在內容還是風格上,都把焦慮做為一個重要主題。這樣的影響至少喚醒了知識階層對他們自己焦慮的注意,而且讓焦慮的觀念和象徵滲透到大眾的意識中。今天,把我們的時代稱為﹁焦慮時代﹂幾乎成了老生常談。無論是美國或歐洲都是如此。
然而,勇氣的存有論必然包含焦慮的存有論,因為兩者是彼此相依的。我們可以相信,在勇氣存有論的燭照下,可以窺見焦慮的某些根本方面。關於焦慮的第一個斷言是:焦慮是一個存在者意識到自己有可能不存在的狀態。用更簡短的話來說就是:焦慮乃是對非存有的實有性知覺。這句話中的「實有性」,意指導致焦慮的不是有關非存有的抽象知識,而是知覺到非存有乃是一個人存有的一部分。產生焦慮的,不是一種對萬物短暫的了悟,也不是對他人之死的體驗,而是這些事件觸發我們對自己不得不死的這一潛在意識。焦慮是有限性的,被體驗為人自己的有限性。這是人之為人的自然焦慮,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所有生物的自然焦慮。那是對非存有的焦慮,也就是對人的有限性的意識。
恐懼與焦慮的相生
焦慮和恐懼有著相同的存有論根源,但實際上又不是相同的東西。這本是眾所周知的道理,但兩者的相同性一直被過度強調,以致如果我們提出不同的說法(包含應消除其誇大其詞的部分),兩者有別的事實就會被抹殺。恐懼與焦慮的不同處,正如許多著作者所同意,在於恐懼有一個具體的對象,該對象可以被面對、被分析、被攻擊和被忍受。
人可以對這個對象採取行動,並在採取行動的過程中參與到它其中︵即便這個參與是用鬥爭的方式︶。以這種方式,人就可以將恐懼的對象納入他的自我肯定中。勇氣能夠迎戰每一個恐懼的對象,這是因為那是一種人可以參與其中的對象。勇氣可以把具體對象所產生的恐懼納入自身,因為無論這對象是何等可怕,它都與人有一個交接面,透過這個交接面,它參與到我們之中,而我們也參與到它之中。大可以說,只要有恐懼的「對象」存在,那麼在參與的意義上,愛就可以征服它。
但焦慮卻不是這樣,因為焦慮並無確定的對象。或者用一句弔詭的話來說,焦慮的對象就是對每一個對象的否定。因此,想要參與它、與之鬥爭或愛它都是不可能的。處於焦慮中的人(只要其焦慮是一種純粹的焦慮),其他人是愛莫能助的。這種焦慮中的無可奈何,在人和動物身上都可以觀察得到,表現為失去方向感、反應不當和缺乏「意向性」(intentionality),也就是存有無法與有意義的知識內容或意志發生關聯。會出現這種讓人錯愕的狀況,是因為沒有一個可供主體(焦慮狀態的主體)聚焦的對象。唯一的對象是威脅本身而不是威脅的泉源,因為威脅的泉源是「空無」(nothingness)。
我們可能會問:這個威脅的「空無」是否是一種未知的、未確定的實際威脅?當一個已知的恐懼對象出現的那一時刻,焦慮不就終止了嗎?這樣一來,焦慮就是對未知之物的恐懼。但這種解釋是不充分的,因為有許多未知事物的領域(它們對每個主體各不相同)都不會引起主體焦慮。只有某種特殊種類的未知事物才會讓人產生焦慮,那是就其本性來說是不可能被認知的未知事物,因為它是「非存有」。
恐懼和焦慮有別,但又不可分割,它們互相涵蓋對方。恐懼的痛是焦慮,焦慮則努力追求成為恐懼。恐懼總是害怕某個物事,例如:害怕痛苦、害怕被別人或某群體排拒、害怕失去某物或某人、害怕死亡的來臨。然而,在參與到由這些東西所帶來的威脅時,讓主體害怕的不是它們本身的否定性,而是對這些否定性可能包含的東西的焦慮。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對死亡的恐懼(勝於其他任何例子)。就其做為一種「恐懼」而言,恐懼的對象是親自參與事件,如因預期自己會因疾病或意外致死,從而遭受劇痛和失去一切;就其做為一種「焦慮」而言,焦慮的對象是對「死後」情況的絕對未知,是「非存在」(這種非存在,即使可以被我們當下經驗的種種意象所充滿,依舊是非存在)。
讓哈姆雷特產生「存在還是不存在」(To be, or not to be.)獨白的夢境之所以可怕,並不是因為它們的外顯內容,而是因為它們對於空無(用宗教術語來說就是「永恆死亡」)的威脅所具有的象徵力量。但丁所創造的地獄象徵之所以令人產生焦慮,並不是因為這些象徵的具體形象,而是因為它們表現了在罪疚(guilt)的焦慮中所體驗到的「空無」的力量。《地獄篇》中所描寫的每一種情況,都是建立在參與和愛的基礎上的勇氣可以應付的。然而,它們其實是不可應付,因為它們並不是真實的情景,只是一些象徵:象徵著無對象(objectless) 和非存有。
對死亡的恐懼,決定了在每一種恐懼中的焦慮成分。焦慮如果沒有被對某一對象的恐懼所修改,那就是一種純粹焦慮,也是對終極非存有的焦慮。換句話說,焦慮就是無法應付特殊處境的威脅所產生的痛苦感覺。但更仔細的分析顯示,在對任何特殊處境的焦慮中,都隱含著人類處境的焦慮。這是人對潛在不能保持一己存有的焦慮,這種焦慮蟄伏在每一種恐懼中,並成為恐懼所包含的可怕成分。因此,在「純粹的焦慮」攫住心靈的那一刻,先前引起恐懼的對象就不再是明確的對象了。這些對象會顯現為它們以往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所是的東西:也就是人的基本焦慮的徵候。做為這樣的對象,甚至連最勇敢的攻擊也對之無能為力。
這種情形迫使焦慮的主體去確立恐懼的對象。焦慮力求變成恐懼,因為恐懼可以用勇氣應付。對於一個有限的存在物來說,是不可能忍受純粹的焦慮超過一剎那的時間。那些經驗過這種時刻的人(例如有過「靈魂暗夜」的神祕主義者、因魔鬼的攻擊而備感絕望的路德,或經驗「大厭惡」〔great disgust〕時的尼采—查拉圖斯特拉),都曾談到過這種焦慮難以想像的恐怖。人們一般會透過把焦慮轉化為對某事物的恐懼(不管任何事物),來迴避這種恐怖。
正如喀爾文所說,人類的心靈不只是不斷製造偶像的工廠,還是不斷製造恐懼的工廠。前者的目的是逃避上帝,後者的目的是逃避焦慮。這兩者逃避之間是緊密相關的,因為直面真正的上帝,也就意味著直面非存有的絕對威脅。這個「純粹的絕對」(引用路德的說法)會產生「純粹的焦慮」,因為它是對每一種有限的自我肯定的滅絕,而且也不是恐懼或勇氣的一個可能對象(參見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把焦慮轉化為恐懼的努力,最終是徒勞的。基本的焦慮(有限存在物對於非存有威脅的焦慮)是不可能被消滅的。這種焦慮屬於生命本身。
第二章 存有、非存有與焦慮
1一種焦慮的存有論
非存有的意義
勇氣是一種具有「不理會」性質的自我肯定:它不理會那些阻止一己進行自我肯定的東西。不同於斯多噶主義和新斯多噶主義的勇氣學說,「生命哲學」嚴肅且肯定的看待與勇氣相對立的部分。因為,如果「存有」被詮釋為生命、過程或生成(becoming)的話,那麼「非存有」在存有論的地位就和「存有」一樣基本。承認這個事實,並不代表要做出「存有」優於「非存有」的判斷,而是要求在存有論的基礎上思考「非存有」。在談到勇氣做為解釋「存有自身」的一把鑰匙時,我們可以說,當這把鑰匙打開存有的門時,也就同時找到了存有、對存有的否定和兩者的統一。
勇氣通常被形容為心靈克服恐懼的力量。恐懼(fear)的意義看似一目了然、不值得探究。但在過去二十年間,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編按:一個心理學流派,探討潛意識與無意識的深層心理結構,精神分析是其中一環)和存在主義哲學的合作帶來了對恐懼和焦慮(anxiety)的嚴格區分,也為這兩個概念帶來更精確的定義。目前的社會學分析指出,焦慮是一個重要的群體現象;文學和藝術無論在內容還是風格上,都把焦慮做為一個重要主題。這樣的影響至少喚醒了知識階層對他們自己焦慮的注意,而且讓焦慮的觀念和象徵滲透到大眾的意識中。今天,把我們的時代稱為﹁焦慮時代﹂幾乎成了老生常談。無論是美國或歐洲都是如此。
然而,勇氣的存有論必然包含焦慮的存有論,因為兩者是彼此相依的。我們可以相信,在勇氣存有論的燭照下,可以窺見焦慮的某些根本方面。關於焦慮的第一個斷言是:焦慮是一個存在者意識到自己有可能不存在的狀態。用更簡短的話來說就是:焦慮乃是對非存有的實有性知覺。這句話中的「實有性」,意指導致焦慮的不是有關非存有的抽象知識,而是知覺到非存有乃是一個人存有的一部分。產生焦慮的,不是一種對萬物短暫的了悟,也不是對他人之死的體驗,而是這些事件觸發我們對自己不得不死的這一潛在意識。焦慮是有限性的,被體驗為人自己的有限性。這是人之為人的自然焦慮,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所有生物的自然焦慮。那是對非存有的焦慮,也就是對人的有限性的意識。
恐懼與焦慮的相生
焦慮和恐懼有著相同的存有論根源,但實際上又不是相同的東西。這本是眾所周知的道理,但兩者的相同性一直被過度強調,以致如果我們提出不同的說法(包含應消除其誇大其詞的部分),兩者有別的事實就會被抹殺。恐懼與焦慮的不同處,正如許多著作者所同意,在於恐懼有一個具體的對象,該對象可以被面對、被分析、被攻擊和被忍受。
人可以對這個對象採取行動,並在採取行動的過程中參與到它其中︵即便這個參與是用鬥爭的方式︶。以這種方式,人就可以將恐懼的對象納入他的自我肯定中。勇氣能夠迎戰每一個恐懼的對象,這是因為那是一種人可以參與其中的對象。勇氣可以把具體對象所產生的恐懼納入自身,因為無論這對象是何等可怕,它都與人有一個交接面,透過這個交接面,它參與到我們之中,而我們也參與到它之中。大可以說,只要有恐懼的「對象」存在,那麼在參與的意義上,愛就可以征服它。
但焦慮卻不是這樣,因為焦慮並無確定的對象。或者用一句弔詭的話來說,焦慮的對象就是對每一個對象的否定。因此,想要參與它、與之鬥爭或愛它都是不可能的。處於焦慮中的人(只要其焦慮是一種純粹的焦慮),其他人是愛莫能助的。這種焦慮中的無可奈何,在人和動物身上都可以觀察得到,表現為失去方向感、反應不當和缺乏「意向性」(intentionality),也就是存有無法與有意義的知識內容或意志發生關聯。會出現這種讓人錯愕的狀況,是因為沒有一個可供主體(焦慮狀態的主體)聚焦的對象。唯一的對象是威脅本身而不是威脅的泉源,因為威脅的泉源是「空無」(nothingness)。
我們可能會問:這個威脅的「空無」是否是一種未知的、未確定的實際威脅?當一個已知的恐懼對象出現的那一時刻,焦慮不就終止了嗎?這樣一來,焦慮就是對未知之物的恐懼。但這種解釋是不充分的,因為有許多未知事物的領域(它們對每個主體各不相同)都不會引起主體焦慮。只有某種特殊種類的未知事物才會讓人產生焦慮,那是就其本性來說是不可能被認知的未知事物,因為它是「非存有」。
恐懼和焦慮有別,但又不可分割,它們互相涵蓋對方。恐懼的痛是焦慮,焦慮則努力追求成為恐懼。恐懼總是害怕某個物事,例如:害怕痛苦、害怕被別人或某群體排拒、害怕失去某物或某人、害怕死亡的來臨。然而,在參與到由這些東西所帶來的威脅時,讓主體害怕的不是它們本身的否定性,而是對這些否定性可能包含的東西的焦慮。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對死亡的恐懼(勝於其他任何例子)。就其做為一種「恐懼」而言,恐懼的對象是親自參與事件,如因預期自己會因疾病或意外致死,從而遭受劇痛和失去一切;就其做為一種「焦慮」而言,焦慮的對象是對「死後」情況的絕對未知,是「非存在」(這種非存在,即使可以被我們當下經驗的種種意象所充滿,依舊是非存在)。
讓哈姆雷特產生「存在還是不存在」(To be, or not to be.)獨白的夢境之所以可怕,並不是因為它們的外顯內容,而是因為它們對於空無(用宗教術語來說就是「永恆死亡」)的威脅所具有的象徵力量。但丁所創造的地獄象徵之所以令人產生焦慮,並不是因為這些象徵的具體形象,而是因為它們表現了在罪疚(guilt)的焦慮中所體驗到的「空無」的力量。《地獄篇》中所描寫的每一種情況,都是建立在參與和愛的基礎上的勇氣可以應付的。然而,它們其實是不可應付,因為它們並不是真實的情景,只是一些象徵:象徵著無對象(objectless) 和非存有。
對死亡的恐懼,決定了在每一種恐懼中的焦慮成分。焦慮如果沒有被對某一對象的恐懼所修改,那就是一種純粹焦慮,也是對終極非存有的焦慮。換句話說,焦慮就是無法應付特殊處境的威脅所產生的痛苦感覺。但更仔細的分析顯示,在對任何特殊處境的焦慮中,都隱含著人類處境的焦慮。這是人對潛在不能保持一己存有的焦慮,這種焦慮蟄伏在每一種恐懼中,並成為恐懼所包含的可怕成分。因此,在「純粹的焦慮」攫住心靈的那一刻,先前引起恐懼的對象就不再是明確的對象了。這些對象會顯現為它們以往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所是的東西:也就是人的基本焦慮的徵候。做為這樣的對象,甚至連最勇敢的攻擊也對之無能為力。
這種情形迫使焦慮的主體去確立恐懼的對象。焦慮力求變成恐懼,因為恐懼可以用勇氣應付。對於一個有限的存在物來說,是不可能忍受純粹的焦慮超過一剎那的時間。那些經驗過這種時刻的人(例如有過「靈魂暗夜」的神祕主義者、因魔鬼的攻擊而備感絕望的路德,或經驗「大厭惡」〔great disgust〕時的尼采—查拉圖斯特拉),都曾談到過這種焦慮難以想像的恐怖。人們一般會透過把焦慮轉化為對某事物的恐懼(不管任何事物),來迴避這種恐怖。
正如喀爾文所說,人類的心靈不只是不斷製造偶像的工廠,還是不斷製造恐懼的工廠。前者的目的是逃避上帝,後者的目的是逃避焦慮。這兩者逃避之間是緊密相關的,因為直面真正的上帝,也就意味著直面非存有的絕對威脅。這個「純粹的絕對」(引用路德的說法)會產生「純粹的焦慮」,因為它是對每一種有限的自我肯定的滅絕,而且也不是恐懼或勇氣的一個可能對象(參見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把焦慮轉化為恐懼的努力,最終是徒勞的。基本的焦慮(有限存在物對於非存有威脅的焦慮)是不可能被消滅的。這種焦慮屬於生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