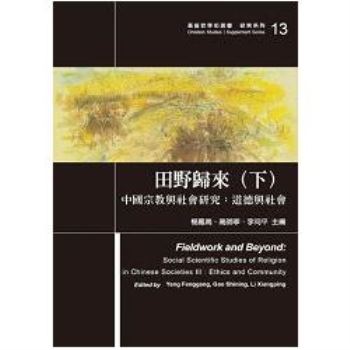有信仰的資本
─溫州民營企業主慈善捐贈行為研究
周怡、胡安寧
摘要:本文借助韋伯的雙利益驅動模型及其「扳道夫」假設,通過對溫州民營企業主問卷調查,分析其慈善捐贈行為的內在驅力及其差異。基本的研究發現包括:(1)企業主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均能對捐贈行為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2)不同信仰在捐贈方向、形式和結果上存在明顯差異,差異凸顯了不同信仰的選擇與不同利益之間的親和性;(3)企業黨組織作為外在於企業主權力的制度環境,能夠通過影響企業主理念利益的作用程度,進而影響慈善捐贈,但這種影響受到限制。
關鍵字:信仰、民營企業主、慈善捐贈
在馬克思的言說中「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Marx,1995/ 1887:829)。這類將資本等同於「沾滿鮮血的金錢」(Lagemann,1989:23)的表述在善與惡的道德評判上屬於極端的 「惡」,強調的是資本擁有者(富人)對非擁有者(窮人)的剝削或侵佔。相反,本文關注的「有信仰的資本」則與慈善捐贈行為相關聯(Bradley, 1987; Brooks, 2006),在行善意義上敘述資本所有者——民營企業主——對社會公益慈善的參與和投入,著重探討資本擁有者(富人)對非擁有者(窮人)的捐贈或給予及這種捐助行為背後的利益邏輯。具體來說,本文關注溫州民營企業主的捐贈行為,主要的研究問題為:企業主的信仰與其捐贈行為是否關聯,如何關聯?
一、理論綜述及研究框架
(一)有關捐贈行為的三因素界說
慈善捐贈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顯然與捐贈人的物質利益讓渡攸關。那麼,人們緣何能夠慷慨做出利益讓渡的捐贈行為,既有文獻集中於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和宗教因素的解釋。1.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的分析主要側重在國家政策、意識形態動員和政治信仰三個方面。就政府政策而言,一些研究發現,政府既可以通過再分配政策調節不平等, 進而影響捐贈行動(Curti,1958; Garnett, 1956; Lin, 2004); 也可以通過實行慈善抵稅政策激勵民間做公益捐贈( Labovitz,1974; Latcham, 1950)。就意識形態動員而言,海內外學者共同看到,中國社會無論在應急性災難事件中,還是在日常的濟貧捐贈中,意識形態宣傳的集體動員都發揮積極而強勢的召喚作用(Perry, 2007;Siu, 1990)。國家作為意識形態的引領者能夠借助媒體、教育等管道,將「企業社會責任」(Joyner and Payne, 2002)、「個人奉獻精神」(Cao, 2007)、「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官方修辭灌輸於民、內化於民,由此推動慈善捐贈(Wuthnow and Hunter ,1984)。其中,黨員身份作為一種政治信仰(公方彬,2012;Yang,2012)、政治忠誠(Szelenyi, 1982;Walder,2000)與慈善捐贈行動密切相關(Bradley,1987)。不僅黨員較普通群眾更積極投入捐贈,而且捐贈與否、如何捐贈也是衡量政治表現的標準之一。有研究發現政治信仰與慈善捐贈呈正相關關係(比如Layman, 2001; Pipes and Ebaugh, 2002),因為黨組織能夠通過內部話語和組織活動,提升黨員具備高於普通民眾的「大公無私」的社會責任,積極為社會做貢獻。
2.經濟因素
該因素分析側重在捐贈行為的經濟理性方面,將企業家的慈善捐助看作是期待回報的投資。一種觀點認為,做慈善捐贈只是企業的一種行銷策略,通過慈善捐贈能夠獲得更多的物質資源,改善企業經濟(Brooks,2006;Navarro, 1988)。另一種觀點看到,企業通過慈善捐贈,實現貨幣資本向符號資本的轉化,以支票換得無形的道德聲譽地位(Acs and Phillips, 2002; Bourdieu, 1984\ 1979; Ma and Parish, 2006; Wilson,2000)。當企業達到一定規模後,多數企業家會通過慈善捐贈,將有形的貨幣資本轉化為關係的社會資本、轉化為體現企業精神的文化資本、或轉化為標示企業地位聲望的象徵資本(Brooks, 2006)。還有一種觀點注意到,捐贈行為與企業屬性的相關性(Amato and Amato,2007; Brown, Helland and Smith, 2006)。即企業所有制形式、企業資產、盈利水準、企業規模、員工數量等企業屬性將直接影響企業主的捐贈。民營企業相對於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來說,在捐贈行為上更為慷慨(Seifert, Morris and Bartkus, 2003; 盧漢龍,2002 )。3.宗教因素
宗教因素分析的主要觀點包括:(1)宗教是企業慈善捐助的決定因素之一,它通過形成企業內部獨特的企業文化而使企業作出投身慈善的決策(Brown, Helland and Smith,2006)。有研究看到,宗教是法律和政策之外,另一個有助於規範企業社會責任的力量(Stabile, 2004)。在個體層面上,宗教信仰、宗教教義和宗教活動將與人為善的理念內化於個體,促發個體做公益性慈善捐贈(Bhatnagar, 1970; Coleman, 2003; Iannaccone, 1997; Loseke, 1997; McCulloch, 1988; Naar,1981; Wilson, 2003; Wuthnow, 1990)。(2)宗教組織是慈善捐贈的直接場所,是宗教關懷社會的重要管道(Bishop, 1912; Luidens and Nemeth,1994; Miyazaki, 2000; Prevey,1899)。比如,古代中國民間最早的慈善機構是佛教的「六疾館」;運作最成功的佛教慈善機構是唐代的「悲田養病坊」(黃為軍,2013)。(3)不同的宗教教義對慈善的看法存在差異(Brekke,1998; Cohen,2005; Müller, 1885; Tamari, 1997)。有如,宗教教義中的「愛」,有基督教的「普愛、博愛」、佛教的「慈悲喜舍」和儒教的「仁愛」 之別,不同「愛」所釋義的捐贈內涵不同。教義在感化人心靈世界的同時,也鼓勵信徒將信仰化為實踐,將「財富」、「愛」與「奉獻」結為一體(Bellah, 1958; Loseke, 1997)。有研究表明,信仰者虔誠度越高,教義對行動的約束越明顯,捐贈的激勵作用亦更直接(Lin, 2004)。
(二)理念與利益:韋伯的雙驅動模型及扳道夫假設
上述三種對捐贈行為所作的因素分析未脫出行動者行動的物質和精神面向,亦緊緊圍繞利益。什麼是利益?慈善捐贈作為一種與讓渡物質利益相聯繫的經濟行為,不應當被簡單理解為一種有條件交換行為,而是嵌套在社會結構(Granovetter, 1985)、網織於文化結構(Alexander,2003)中的。本文擬用韋伯(Marx Weber)的「扳道夫」(switchmen)假設去拓展利益的內涵。韋伯將利益分為兩類:一是物質利益(material interests),指物質層面上與經濟理性相聯繫的諸如收入、財富、權力等有形資源;另一是理念利益(ideal interests), 指精神層面上與行動者行動相聯繫的觀念利益,即存在於人頭腦中的理想型世界觀,如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信仰。在討論行動者行動時韋伯主張:「直接支配人行動的是物質利益和理念利益,而不是『理念』,但由『理念』創造的『世界意象』卻像扳道夫一樣決定著由物質利益驅力所推動的行動方向」(Weber,1978:280; Swidler,1986:273-286)。相對馬克思的物質決定論來講,韋伯的扳道夫命題顯然具有以下特點:(1)強調了人在行動前或行動過程中頭腦裡已經形成的對物所作的價值判斷;提出的是人行動過程中的物質-精神利益的雙驅動模型,即如果追求物質利益的驅力如同推動火車的動力,那麼理念利益有如扳道夫將主導該動力的方向。(2)借理念利益的提出,突出了制度環境對理念利益的影響。相對於理念泛指人類社會各種束之高閣的意識形態、思想和價值觀而言,理念利益則指特定制度環境下,某些理念經由行動者將其與實際行動相聯繫時,表現出的價值觀、動機和行為特徵;即理念利益是與行動者、行動者的行動以及行動者所處的特定制度環境緊密扣連的。因而,物質利益與理念利益所產生的驅動結果其實潛存於制度的脈絡中。(3)在將理念和理念利益歸為廣義的「理念」,將物質利益歸為「利益」之後,韋伯關聯理念與利益的重要概念是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Reinhard Bendix認為,韋伯用選擇性親和概念表達了理念的兩個面向:一是精神理念是由個人所選擇的,與選擇相關;二是這種選擇乃是用來符合其物質利益的,即理念扮演著強加並賦予物質利益正當性的角色(Bendix,1977:47),「使經濟謀利的觀念具有一種正面被接受的基礎」(張維安,1995:120)。當然,韋伯用「選擇性親和」去統轄理念與利益的關聯時,並沒有否定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緊張或分離。相反,他在跨文化的有關資本主義起源的比較分析裡,讓我們看到的理念與利益之間的關聯,是一種隨歷史情境和機緣而發生的緊張、分離和親近等各種關係。如,相對西方新教倫理的理念同資本主義商業利益保持選擇性親和(Weber,1958)而言,東方儒家道教倫理的理念卻與經商利益持有緊張關係(Weber, 1951)。(三)「三因素」、「雙利益」下的理論模型
用韋伯的雙利益驅動去統轄前述的三因素分析便形成本文最初的理論雛形。具體來說,我們把捐贈行為的驅動利益歸為「物質利益」和「理念利益」兩類;然後將政治、經濟和宗教三因素分別歸入雙利益驅動模式。由於經濟因素一般作為物質世界的重要指標,我們將其歸為物質利益;宗教因素因其所具有的精神超驗而被歸為理念利益;政治因素被一分為二,其中因政府政策制度及地位身份壓力等引發的慈善捐贈被列為物質利益,而由黨員身份、意識形態話語內化而成的指導行動的價值觀念屬於政治信仰,被列入理念利益(見圖1a)。
可是,循「有信仰的資本」之題意,並結合研究物件的實際,我們需要對理論雛形圖1a作進一步聚焦式的修正。
就研究題意看,慈善捐贈本身屬於物質利益的讓渡,能夠做出利益讓渡行為的支援點在捐贈者的精神理念。因此,本文側重理念利益對民營企業主捐贈行為的影響,而將物質利益的影響作為控制變數;也擬在選擇性親和的測量中分析物質利益的影響。即我們重點討論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對捐贈行為的影響,然後比較不同信仰與物質利益之間的關聯。
就表徵物質利益的經濟因素而言,我們不可否認在經濟利益、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之間(Weber,1978: 926-939),商人(民營企業主)總是以經濟利益的富足為第一考慮,並會以此為基礎朝向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方向轉移。但是在中國傳統儒家倫理長期奠定的制度環境中,「私為萬惡之源」、「重農輕商抑商」等理念根深蒂固(張維安,1995)。這種社會價值觀對商人社會地位所作的負面評價,會加速推動他們往社會地位、政治權力方向的轉移,如市場轉型期許多商業資本被用來買官,或用來修建祠堂等,以獲取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捐贈行為中不乏這樣的利益考慮,這類考慮背後的支援點是現實制度安排環境中依存的傳統文化理念。因此,本文用「企業是否建有黨組織」這一既表徵政治權力又不失地位追求的指標,去測度經濟因素或物質利益對民營企業主捐贈行為的影響。就研究物件溫州民營企業看,兩個重要的背景事實與本文密切相關:(1)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溫州一直以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為世人矚目。不少研究注意到,從家庭作坊起步的溫州民企在其組織結構上,一直存在受制度環境影響的政治特徵(曹正漢,2005;史晉川等,2004;Dickson,2003,2008;Tsai,2007): 企業初創期所有制形式上的「紅帽子」(掛靠經營)、企業壯大期行政結構上的「紅頂」(非公黨建)和「紅色CEO」招聘,以及民營企業主入黨,進入人大、政協參政議政等。「截止2010年底,溫州非公企業已建黨組織3,672個,非公企業黨員32,464人,入黨積極分子12,195人。溫州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在全國地級市中名列前茅」(管廷蓮,2011:10)。這一事實對本文的啟示在,我們需要在理念利益中考慮企業主的政治信仰,也需要考慮非公黨建作為一種外在於企業主個體的政治制度環境,能否制約或推動企業主的捐贈。(2)地處浙江省東南沿岸的溫州,是古東甌國的谷地,其悠久的歷史傳遞了豐富的宗教信仰文化(楊昭,1999;焦淑軍,2010)。Watchman Nee宣導的「地方教會」(local church)運動深深影響過溫州的基督教文化。目前大約有70-110萬的基督教徒,超過1,200座教堂,每百萬人口平均擁有10.15個教堂(洪朝暉、曾樂,2012),已成為中國擁有基督教徒比例最高的城市(Weller and Sun,2010;Cao,2007)。此外,自東晉修建崇安寺(後改稱開元寺)開始,佛教進入溫州。天寶年間,禪宗道場在龍興寺的設立,使溫州成為當時江浙一帶的禪學中心。改革開放後隨佛寺的重建,佛教成為溫州地區擁有最多信眾的信仰。與此同時,受到吳越文化的薰陶,民間信仰在溫州亦一直十分興盛(楊昭,1999),主要體現在祖先崇拜、村村建祠堂,以及對眾多民間「神」的祭祀活動中。總之,溫州彙集了佛教、基督教和民間信仰的諸多神祗,是國內宗教信仰比例最高的城市。這一背景事實讓本文不能繞過宗教信仰而妄談企業主的慈善捐贈。
藉上述討論,本文力圖在研究進路上作如下考慮:首先,根據韋伯的雙利益驅動模型,預設捐贈行為必定會受多方物質利益的驅動,但限於篇幅及研究主題,我們將物質利益因素作為控制變數,重點考察理念利益是否對企業主的捐贈行為產生影響。具體來說,分別探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以及兩種信仰體系對企業主慈善捐贈的影響。
其次,根據韋伯雙驅動模型的扳道夫假設,通過比較分析捐贈管道、捐贈匿名性以及捐贈獎勵等代表性資料,力求證明不同理念或不同信仰將賦予企業主不同的捐贈「方向」,也以此驗證理念與利益間存在選擇性親和之關係。
第三,在探究如圖1b所示的制度環境對企業主捐贈行為的影響時,本文將分析企業黨組織是否可能通過對企業主理念利益的作用進而影響捐贈。
─溫州民營企業主慈善捐贈行為研究
周怡、胡安寧
摘要:本文借助韋伯的雙利益驅動模型及其「扳道夫」假設,通過對溫州民營企業主問卷調查,分析其慈善捐贈行為的內在驅力及其差異。基本的研究發現包括:(1)企業主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均能對捐贈行為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2)不同信仰在捐贈方向、形式和結果上存在明顯差異,差異凸顯了不同信仰的選擇與不同利益之間的親和性;(3)企業黨組織作為外在於企業主權力的制度環境,能夠通過影響企業主理念利益的作用程度,進而影響慈善捐贈,但這種影響受到限制。
關鍵字:信仰、民營企業主、慈善捐贈
在馬克思的言說中「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Marx,1995/ 1887:829)。這類將資本等同於「沾滿鮮血的金錢」(Lagemann,1989:23)的表述在善與惡的道德評判上屬於極端的 「惡」,強調的是資本擁有者(富人)對非擁有者(窮人)的剝削或侵佔。相反,本文關注的「有信仰的資本」則與慈善捐贈行為相關聯(Bradley, 1987; Brooks, 2006),在行善意義上敘述資本所有者——民營企業主——對社會公益慈善的參與和投入,著重探討資本擁有者(富人)對非擁有者(窮人)的捐贈或給予及這種捐助行為背後的利益邏輯。具體來說,本文關注溫州民營企業主的捐贈行為,主要的研究問題為:企業主的信仰與其捐贈行為是否關聯,如何關聯?
一、理論綜述及研究框架
(一)有關捐贈行為的三因素界說
慈善捐贈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顯然與捐贈人的物質利益讓渡攸關。那麼,人們緣何能夠慷慨做出利益讓渡的捐贈行為,既有文獻集中於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和宗教因素的解釋。1.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的分析主要側重在國家政策、意識形態動員和政治信仰三個方面。就政府政策而言,一些研究發現,政府既可以通過再分配政策調節不平等, 進而影響捐贈行動(Curti,1958; Garnett, 1956; Lin, 2004); 也可以通過實行慈善抵稅政策激勵民間做公益捐贈( Labovitz,1974; Latcham, 1950)。就意識形態動員而言,海內外學者共同看到,中國社會無論在應急性災難事件中,還是在日常的濟貧捐贈中,意識形態宣傳的集體動員都發揮積極而強勢的召喚作用(Perry, 2007;Siu, 1990)。國家作為意識形態的引領者能夠借助媒體、教育等管道,將「企業社會責任」(Joyner and Payne, 2002)、「個人奉獻精神」(Cao, 2007)、「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官方修辭灌輸於民、內化於民,由此推動慈善捐贈(Wuthnow and Hunter ,1984)。其中,黨員身份作為一種政治信仰(公方彬,2012;Yang,2012)、政治忠誠(Szelenyi, 1982;Walder,2000)與慈善捐贈行動密切相關(Bradley,1987)。不僅黨員較普通群眾更積極投入捐贈,而且捐贈與否、如何捐贈也是衡量政治表現的標準之一。有研究發現政治信仰與慈善捐贈呈正相關關係(比如Layman, 2001; Pipes and Ebaugh, 2002),因為黨組織能夠通過內部話語和組織活動,提升黨員具備高於普通民眾的「大公無私」的社會責任,積極為社會做貢獻。
2.經濟因素
該因素分析側重在捐贈行為的經濟理性方面,將企業家的慈善捐助看作是期待回報的投資。一種觀點認為,做慈善捐贈只是企業的一種行銷策略,通過慈善捐贈能夠獲得更多的物質資源,改善企業經濟(Brooks,2006;Navarro, 1988)。另一種觀點看到,企業通過慈善捐贈,實現貨幣資本向符號資本的轉化,以支票換得無形的道德聲譽地位(Acs and Phillips, 2002; Bourdieu, 1984\ 1979; Ma and Parish, 2006; Wilson,2000)。當企業達到一定規模後,多數企業家會通過慈善捐贈,將有形的貨幣資本轉化為關係的社會資本、轉化為體現企業精神的文化資本、或轉化為標示企業地位聲望的象徵資本(Brooks, 2006)。還有一種觀點注意到,捐贈行為與企業屬性的相關性(Amato and Amato,2007; Brown, Helland and Smith, 2006)。即企業所有制形式、企業資產、盈利水準、企業規模、員工數量等企業屬性將直接影響企業主的捐贈。民營企業相對於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來說,在捐贈行為上更為慷慨(Seifert, Morris and Bartkus, 2003; 盧漢龍,2002 )。3.宗教因素
宗教因素分析的主要觀點包括:(1)宗教是企業慈善捐助的決定因素之一,它通過形成企業內部獨特的企業文化而使企業作出投身慈善的決策(Brown, Helland and Smith,2006)。有研究看到,宗教是法律和政策之外,另一個有助於規範企業社會責任的力量(Stabile, 2004)。在個體層面上,宗教信仰、宗教教義和宗教活動將與人為善的理念內化於個體,促發個體做公益性慈善捐贈(Bhatnagar, 1970; Coleman, 2003; Iannaccone, 1997; Loseke, 1997; McCulloch, 1988; Naar,1981; Wilson, 2003; Wuthnow, 1990)。(2)宗教組織是慈善捐贈的直接場所,是宗教關懷社會的重要管道(Bishop, 1912; Luidens and Nemeth,1994; Miyazaki, 2000; Prevey,1899)。比如,古代中國民間最早的慈善機構是佛教的「六疾館」;運作最成功的佛教慈善機構是唐代的「悲田養病坊」(黃為軍,2013)。(3)不同的宗教教義對慈善的看法存在差異(Brekke,1998; Cohen,2005; Müller, 1885; Tamari, 1997)。有如,宗教教義中的「愛」,有基督教的「普愛、博愛」、佛教的「慈悲喜舍」和儒教的「仁愛」 之別,不同「愛」所釋義的捐贈內涵不同。教義在感化人心靈世界的同時,也鼓勵信徒將信仰化為實踐,將「財富」、「愛」與「奉獻」結為一體(Bellah, 1958; Loseke, 1997)。有研究表明,信仰者虔誠度越高,教義對行動的約束越明顯,捐贈的激勵作用亦更直接(Lin, 2004)。
(二)理念與利益:韋伯的雙驅動模型及扳道夫假設
上述三種對捐贈行為所作的因素分析未脫出行動者行動的物質和精神面向,亦緊緊圍繞利益。什麼是利益?慈善捐贈作為一種與讓渡物質利益相聯繫的經濟行為,不應當被簡單理解為一種有條件交換行為,而是嵌套在社會結構(Granovetter, 1985)、網織於文化結構(Alexander,2003)中的。本文擬用韋伯(Marx Weber)的「扳道夫」(switchmen)假設去拓展利益的內涵。韋伯將利益分為兩類:一是物質利益(material interests),指物質層面上與經濟理性相聯繫的諸如收入、財富、權力等有形資源;另一是理念利益(ideal interests), 指精神層面上與行動者行動相聯繫的觀念利益,即存在於人頭腦中的理想型世界觀,如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信仰。在討論行動者行動時韋伯主張:「直接支配人行動的是物質利益和理念利益,而不是『理念』,但由『理念』創造的『世界意象』卻像扳道夫一樣決定著由物質利益驅力所推動的行動方向」(Weber,1978:280; Swidler,1986:273-286)。相對馬克思的物質決定論來講,韋伯的扳道夫命題顯然具有以下特點:(1)強調了人在行動前或行動過程中頭腦裡已經形成的對物所作的價值判斷;提出的是人行動過程中的物質-精神利益的雙驅動模型,即如果追求物質利益的驅力如同推動火車的動力,那麼理念利益有如扳道夫將主導該動力的方向。(2)借理念利益的提出,突出了制度環境對理念利益的影響。相對於理念泛指人類社會各種束之高閣的意識形態、思想和價值觀而言,理念利益則指特定制度環境下,某些理念經由行動者將其與實際行動相聯繫時,表現出的價值觀、動機和行為特徵;即理念利益是與行動者、行動者的行動以及行動者所處的特定制度環境緊密扣連的。因而,物質利益與理念利益所產生的驅動結果其實潛存於制度的脈絡中。(3)在將理念和理念利益歸為廣義的「理念」,將物質利益歸為「利益」之後,韋伯關聯理念與利益的重要概念是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Reinhard Bendix認為,韋伯用選擇性親和概念表達了理念的兩個面向:一是精神理念是由個人所選擇的,與選擇相關;二是這種選擇乃是用來符合其物質利益的,即理念扮演著強加並賦予物質利益正當性的角色(Bendix,1977:47),「使經濟謀利的觀念具有一種正面被接受的基礎」(張維安,1995:120)。當然,韋伯用「選擇性親和」去統轄理念與利益的關聯時,並沒有否定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緊張或分離。相反,他在跨文化的有關資本主義起源的比較分析裡,讓我們看到的理念與利益之間的關聯,是一種隨歷史情境和機緣而發生的緊張、分離和親近等各種關係。如,相對西方新教倫理的理念同資本主義商業利益保持選擇性親和(Weber,1958)而言,東方儒家道教倫理的理念卻與經商利益持有緊張關係(Weber, 1951)。(三)「三因素」、「雙利益」下的理論模型
用韋伯的雙利益驅動去統轄前述的三因素分析便形成本文最初的理論雛形。具體來說,我們把捐贈行為的驅動利益歸為「物質利益」和「理念利益」兩類;然後將政治、經濟和宗教三因素分別歸入雙利益驅動模式。由於經濟因素一般作為物質世界的重要指標,我們將其歸為物質利益;宗教因素因其所具有的精神超驗而被歸為理念利益;政治因素被一分為二,其中因政府政策制度及地位身份壓力等引發的慈善捐贈被列為物質利益,而由黨員身份、意識形態話語內化而成的指導行動的價值觀念屬於政治信仰,被列入理念利益(見圖1a)。
可是,循「有信仰的資本」之題意,並結合研究物件的實際,我們需要對理論雛形圖1a作進一步聚焦式的修正。
就研究題意看,慈善捐贈本身屬於物質利益的讓渡,能夠做出利益讓渡行為的支援點在捐贈者的精神理念。因此,本文側重理念利益對民營企業主捐贈行為的影響,而將物質利益的影響作為控制變數;也擬在選擇性親和的測量中分析物質利益的影響。即我們重點討論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對捐贈行為的影響,然後比較不同信仰與物質利益之間的關聯。
就表徵物質利益的經濟因素而言,我們不可否認在經濟利益、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之間(Weber,1978: 926-939),商人(民營企業主)總是以經濟利益的富足為第一考慮,並會以此為基礎朝向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方向轉移。但是在中國傳統儒家倫理長期奠定的制度環境中,「私為萬惡之源」、「重農輕商抑商」等理念根深蒂固(張維安,1995)。這種社會價值觀對商人社會地位所作的負面評價,會加速推動他們往社會地位、政治權力方向的轉移,如市場轉型期許多商業資本被用來買官,或用來修建祠堂等,以獲取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捐贈行為中不乏這樣的利益考慮,這類考慮背後的支援點是現實制度安排環境中依存的傳統文化理念。因此,本文用「企業是否建有黨組織」這一既表徵政治權力又不失地位追求的指標,去測度經濟因素或物質利益對民營企業主捐贈行為的影響。就研究物件溫州民營企業看,兩個重要的背景事實與本文密切相關:(1)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溫州一直以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為世人矚目。不少研究注意到,從家庭作坊起步的溫州民企在其組織結構上,一直存在受制度環境影響的政治特徵(曹正漢,2005;史晉川等,2004;Dickson,2003,2008;Tsai,2007): 企業初創期所有制形式上的「紅帽子」(掛靠經營)、企業壯大期行政結構上的「紅頂」(非公黨建)和「紅色CEO」招聘,以及民營企業主入黨,進入人大、政協參政議政等。「截止2010年底,溫州非公企業已建黨組織3,672個,非公企業黨員32,464人,入黨積極分子12,195人。溫州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在全國地級市中名列前茅」(管廷蓮,2011:10)。這一事實對本文的啟示在,我們需要在理念利益中考慮企業主的政治信仰,也需要考慮非公黨建作為一種外在於企業主個體的政治制度環境,能否制約或推動企業主的捐贈。(2)地處浙江省東南沿岸的溫州,是古東甌國的谷地,其悠久的歷史傳遞了豐富的宗教信仰文化(楊昭,1999;焦淑軍,2010)。Watchman Nee宣導的「地方教會」(local church)運動深深影響過溫州的基督教文化。目前大約有70-110萬的基督教徒,超過1,200座教堂,每百萬人口平均擁有10.15個教堂(洪朝暉、曾樂,2012),已成為中國擁有基督教徒比例最高的城市(Weller and Sun,2010;Cao,2007)。此外,自東晉修建崇安寺(後改稱開元寺)開始,佛教進入溫州。天寶年間,禪宗道場在龍興寺的設立,使溫州成為當時江浙一帶的禪學中心。改革開放後隨佛寺的重建,佛教成為溫州地區擁有最多信眾的信仰。與此同時,受到吳越文化的薰陶,民間信仰在溫州亦一直十分興盛(楊昭,1999),主要體現在祖先崇拜、村村建祠堂,以及對眾多民間「神」的祭祀活動中。總之,溫州彙集了佛教、基督教和民間信仰的諸多神祗,是國內宗教信仰比例最高的城市。這一背景事實讓本文不能繞過宗教信仰而妄談企業主的慈善捐贈。
藉上述討論,本文力圖在研究進路上作如下考慮:首先,根據韋伯的雙利益驅動模型,預設捐贈行為必定會受多方物質利益的驅動,但限於篇幅及研究主題,我們將物質利益因素作為控制變數,重點考察理念利益是否對企業主的捐贈行為產生影響。具體來說,分別探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以及兩種信仰體系對企業主慈善捐贈的影響。
其次,根據韋伯雙驅動模型的扳道夫假設,通過比較分析捐贈管道、捐贈匿名性以及捐贈獎勵等代表性資料,力求證明不同理念或不同信仰將賦予企業主不同的捐贈「方向」,也以此驗證理念與利益間存在選擇性親和之關係。
第三,在探究如圖1b所示的制度環境對企業主捐贈行為的影響時,本文將分析企業黨組織是否可能通過對企業主理念利益的作用進而影響捐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