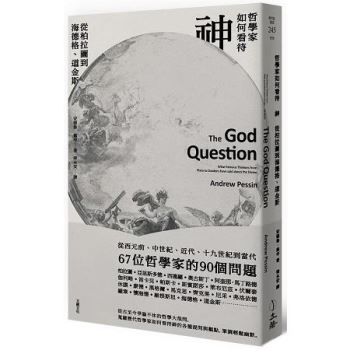第 V 部 當代哲學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哲學和宗教同途同歸
但都是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
有個人到雜貨店要買水果。店員給了他蘋果和梨子,然後又給他桃子、草莓和葡萄,但他統統不要。他只要買水果:店員給他的都是某種水果,不是水果本身。但在某個意義下,水果又不外只是這些蘋果、梨子和桃子。
海德格舉出這個例子是要說明黑格爾的「普遍性」(generality)觀念,然而,這例子本身也包含了海德格的上帝概念的種子。
讓我們先看看一個歷史悠久的對比:「雅典」與「耶路撒冷」的對比,換言之是西方哲學(源出古希臘人)和西方宗教(源出古以色列人)的對比。兩千多年來,它們常常發生衝突,三大一神教國度的哲學家莫不使出渾身解數捍衛那些和本教教義相左的哲學命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有人改為致力於調和兩者,常用方法是論證宗教當局並不完全明白本教教義,主張只有哲學家方能正確詮釋它們。也有些人否定哲學和宗教有調解的可能性,持的理由是哲學有賴理性、概念和語言,反觀宗教卻是最終奠基於某些不可言說和非理性的體驗。
但這兩種態度都假定了宗教和哲學有著根本分歧。
海德格可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共通性要遠大於很多人所了解。因為,如果說哲學關心的一直是存有論(研究存在或存有的學問),而宗教關心的一直是神學(研究上帝的學問),那麼,它們從事的其實是同一種探求:不妨稱之為存有神學(onto-theology)。因為兩者都是致力於說明個體、有限和不永的存有物(beings)是如何由普遍、無限和永恆的「存有」(Being)導致,或說明前者是如何可透過後者得到解釋。
兩者都走了一條錯誤道路。
柏拉圖把這個無限「存有」稱為「善之理型」(Form of Good)(譯註:這裡的善不是在道德意義下,意義大概是「美好」。),有時又稱之為「善自身」。由於把它理解為永恆不變,他主張它是普遍性最高的理型,所有理型都分受了它的一部分,亦即所有個體事物都不同程度上包含著善。亞里斯多德則強調這個「存有」是個「不動的推動者」:它永恆處於自我沉思狀態,是所有個體存有物發生變化和運動的「誘因」。到了中世紀,阿維森納、阿奎那和邁蒙尼德等思想家吸收了這種思想,發展出「第一因」的觀念。但信奉多神教的希臘人和中世紀一神論者的基本思路並無不同:所有個別存有物有都被認為是源於或本性根植於某種不變的普遍「存有」(或說「上帝」)。
他們犯了一個大錯:把「存有」當成只是存有物的其中一類,當成只是一類較高級的存有物。這樣,「存有」就被放在了存有物的同一個籃子裡,就像你買完蘋果和梨子後還可以買到一種叫「水果本身」的水果。但就像「水果」不外就是個別的蘋果、梨子和桃子等等,不外只是透過它們而顯現,所以不受限制和普遍的「存有」並不是另一種存有物。它不同於存有物,但只能透過存有物顯現。「存有」只是個別存有物的存有。
這樣的「存有」既不是固定,也不是永恆或不變。存有物究竟是什麼,說到底是由我們決定,而我們會怎樣決定,又取決於我們所處的歷史脈絡和思想脈絡。換言之,這個世界會因著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它和與之互動而有所不同,所以,「存有」(或說上帝)說到底不過是讓任何個體事物可以成為其之所是的時間脈絡或過程。
莎拉.科克利(Sarah Coakley, b. 1951)
女上帝
宗教哲學一直暗含著男性觀點和偏見
顯然易見的是,西方的宗教和宗教哲學一直由男性主導。但較不顯而易見的是,這現象會導致重大差異。哲學被認為是由理性管轄,而理性又被認為是放諸四海皆準,不帶有偏見和立場中立。所以,是男是女運用理性應該沒有分別:理性本身自會引導當事人得出不偏不倚的結論。所以,哲學是一直由男性主導的事實理應不會構成哲學差異。
但莎拉.科克利不這樣認為。她主張,如果我們認真對待對近幾十年發展出來的女性主義哲學,就會知道哲學由男性主導的事實有可能對宗教哲學影響深遠。
以「自我」的概念為例。哲學家談到「自我」,總是把重點放在個體的絕對自主,放在他們自由決定行動的能力。這強調衍生自對「惡的難題」的傳統回應:上帝容許個人行惡,是因為這是容許人類擁有自由意志的必然代價,而自由意志是一種更高的善。但女性主義哲學家注意到一些關於「自主的自我」這個概念的不有趣事實:它不只不是歷史中立或性別中立,不只不是純然理性思考的結果,反而是可以直接追溯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提倡的自律願景,反映的是一個只適合男性和只有男性搆得著的理想。因為當時只有男性是「獨立」和「自主」,可以自己賺錢維持生活,是有機會受教育因此可以作出真正自主的抉擇。反觀女性則是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和其他方面統統依賴男性。
「自由的個人」的典範因此是男性。
上帝的觀念也反映著同一偏見。從古希臘哲學家開始,神就被構想成為永恆不變,擁有無邊權力和絕對自主:這是前述男性理想的放大版本。另外哲學家幾千年來歸給上帝的屬性(能力、智慧、不動、道德純淨)全是傳統的理想男性屬性,反觀軟弱、無知、前後不一和罪性都是對女性的傳統刻板印象。
所以明顯的是,我們必須否定宗教哲學的思考方式一直是「普遍」和「中性」——不然「超越」和「無性別」的上帝又怎會事實上竟是男性!
同樣明顯的是:如果上帝歸根究柢是被構想為男性性別,那男性性別也必然會被構想為神性。
隨著女性哲學主義慢慢打入宗教哲學的領域,我們有理由預期強調的重點會有所轉換,並出現一些新的觀念和論證。我們也許會看見宗教哲學家不再那麼強調個人自主,不再那麼強調「自我」支配和控制環境的一面,改為強調「自我」的概念涉及相互依賴,強調「自我」離不開他人和環境。另外,我們也許還可望看見男性化的上帝概念(自主、全能、支配一切、超越時間和歷史但又控制時間和歷史)開始發生改變,轉向一種較女性化的上帝觀:這個上帝哺育萬物而有愛心,內在於世界,與我們的關係不是主從關係而是朋友關係。
我們也許不應該堅持上帝只能是個女人,但至少有權希望宗教哲學家自覺其所謂得自中性、普遍和「理性」反省的觀點,其實是一種男性觀點和男性偏見。
丹尼特(Daniel Dennett, b. 1942)
汝必須靠汝之雙腿站立(譯註:這是仿基督宗教「十誡」的語氣。)
道德的根基歸根究柢只能是我們自己
從本書最開頭,我們便看見道德和上帝之間關係緊密。柏拉圖認為,世界上的任何善都必然是衍生自這世界之外,哪怕道德和神明的確切關係並不容易掌握了解。後來的十幾二十個世紀消磨了大量精力去調和人類自由意志(也因此是道德責任)和上帝的全能之間的扞格,以及調和世界的苦難罪惡與上帝的全善的扞格。到了十八世紀,康德又發展出一種「道德論證」來證明上帝存在—時至今日仍然有人(例如麥羅德)沿著相同思路立論。那麼,歸根究柢來說,上帝真是道德的根基,道德的內容真是衍生自宗教, 宗教信仰真是可以指引道德行為嗎?很多人都認為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但丹尼特主張,我們應該問的是別的問題。
其中之一是:宗教信仰有讓我們變得道德嗎?有些人認為,信仰上帝是讓我們按道德行為的最好誘因或唯一誘因,因為它應許行善的人死後會永遠在天國享福,行惡的人死後會永遠在地獄受罰。但沒有證據顯示,非信徒的道德水平不如信徒。監獄裡信上帝的囚犯比例和整個社會大致差不多。無神論者當然會犯罪,甚至是犯下滔天大罪,但很多虔誠的一神論者一樣會這樣,而且有時還是為了自己的信仰而犯下大罪。有些宗教信徒固然會出於自己的信仰而傾向於行善,但很多沒有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一樣是傾向於行善。
更重要的是,道德行為有需要宗教動機的想法讓上帝的概念變得非常幼稚,也讓我們自貶身價:那樣的上帝更像是鼓勵我們不成熟而不是鼓勵我們做個有道德擔當的人。這樣一個上帝就像聖誕老人的放大版:行善吧,行善你就會獲得獎賞,不然你就會受到懲罰。我們也許會樂見我們的頑皮兒女因為想要得到一件玩具而守規矩,但我們對自己應該會有更高要求。我們會行善,只應該因為那是當做的事,不管那有沒有帶來即時或長遠利益。
道德的內容又是如何?我們全都渴望複雜的道德問題能有簡單答案,而看來沒有什麼比十誡還要簡單:做這個,不要做那個。更一般地說,我們都渴望按照權威的指示行事,不用自己傷腦筋。事實上,我們在日常生活很多方面都是聽從權威指示:我們讓醫生告訴我們該吃什麼藥,讓汽車技師告訴我們冒煙的引擎出了什麼毛病。但重要的是,我們是經過衡量之後才接受這些權威的指示:例如我判斷他是我信得過的人、他是專家,或他會以我的利益為念等等。但盲目接受權威又是另一回事:那就好比隨便聽一個阿貓阿狗的意見便決定自己要不要接受某種複雜的醫療程序。
有些人認為,毫不置疑地接受自己宗教的道德教導在道德上更值得嘉許。但把一種道德教導看成是不容討論或辯論而直接接受就是一種盲目接受。你也許真的相信那些道德守則是上帝口授,相信上帝全善和無所不知,相信你對上帝的愛足以讓你無須知道上帝是基於什麼理由規定那些道德守則。但我們一樣可以尊重你的真誠而不尊重你的信仰。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我們是被容許尊重任何上帝規定的道德守則:在用理性全盤檢討過這套守則之後,在對所有可得的證據進行過評估之後。沒有任何樂於接受盲目敬拜的上帝是值得敬拜的。
換言之,道德必須靠自己雙腿站立。我們也是一樣——我們的道德動機歸根究柢必須是發自內心,不管給它們套上宗教外衣有多麼方便。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b. 1941)
終極的波音七四七
當代的設計論證事實上會導致相反結論
二十世紀天文學家霍伊爾(Fred Hoyle)說過,認為隨機過程可以造就出最簡單的細胞,就好比認為一場刮過垃圾場的龍捲風可以組裝出一架波音七四七。此語可以表達出當代「設計論證」的精髓。我們已經看到過,當代的「設計論證」分為兩大形式:一種是奠基於物理學,一種是奠基於生物學,即奠基於器官和細胞的「不可化約複雜性」。兩者的中心思想都是,如果一個井然有序的系統怎麼看都不像是由自然過程引起,那我們就必須推論說它是它出自一個有智慧的設計者。道金斯同意這種設計論證非常強而有力——只不過,它的作用是證明上帝不存在。
先從生物學說起。一神論者主張,生物領域有不少例子帶有明顯的設計痕跡。所提到的例子包括一種稱為「維納斯花籃」的海綿、一種被稱為「荷蘭人煙斗」的植物和參天紅杉樹,它們被認為極不可能是演化而成。「不可化約複雜性」的更標準例子是眼睛和翅膀。試問半隻眼睛或半片翅膀用處何在?如果沒有用,那麼,這兩種器官就極不可能是由連續、隨機的過程導致,因為每一個干涉步驟都沒有比它的前身有更多生存優勢。
但這種想法有一個根本錯誤。當你只望向這段旅程的起點和終點(即只望向太古時代的原始分子和現今的複雜生命體),一定會認為它們極不可思議。但如果你把整個過程拆分為無數小段落,再用天擇的力量引導,它們就不會再顯得那麼不可能。事實上,「半隻眼或半片翅膀」不只可能帶給它們的擁有者生存優勢,還確實會帶給:自然世界充滿擁有不同程度眼睛和翅膀的生物。事實上,生物學從未找到過「不可化約複雜性」的真正例子,就連貝希拿來舉例的鞭毛也不算:它們不是真的不可化約。再看看物理學。一神論者認定,物理法則看來被調節得恰到好處,因為否則已知的生命體(包括我們在內)就不可能存在。這一類調節不只極為匪夷所思,也是演化論解釋不了(因為演化只適用於生物領域),所以物理法則必然是出自一位有智慧的設計者。
問題是,有別的解釋可以解釋得了這種現象。有些物理學家相信,物理學不可能是別的樣子:它的特性與其說是經過「微調」而成為現在的樣子,不如說必然只能如此。另一些物理學家則基於量子力學而相信,我們的宇宙只是無數基本特性各異的宇宙的其中之一。這些宇宙中會有一個包含我們宇宙的特性不足為奇,因為如果宇宙的總數是一百兆,又如果每十億個宇宙只有一個擁有與我們宇宙相同的特性,那有此特性的宇宙仍多達十億個。還有些科學家相信,我們的宇宙只是一長串前後相續的宇宙的其中之一,它們每一個都是生於大爆炸和毀於大塌陷,而繼起的每一個宇宙大概都有著不同物理特性。如果這種事發生得夠多次,那會產生一個擁有現在特性的宇宙便不會太難思議。
我們是還不知道這些理論哪個正確,但既然有別的可能解釋,就代表我們宇宙的不同尋常特性(就像生物世界不同尋常的複雜性那樣)不需要訴諸一位有智慧的設計者來解釋。
事實上還剛好相反。
我們一開始是因為要解釋極端匪夷所思的事情而訴諸一位有智慧的設計者。但這個設計者其實什麼都解釋不了。因為光是被告以「有誰創造了它」,我們還是不了解事情是怎樣發生。更重要的是,我們解釋匪夷所思的事情時,不應該訴諸更匪夷所思的事情,但試問,又有什麼比說是一個超越時空和看不見的存有創造了整個浩瀚宇宙更匪夷所思?當我們能夠真正體會這個世界的特徵有多麼「不可能」存在,就會同時體會到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稍稍解釋得了這些特徵的話,便只有不談設計者的演化論和當代物理學。
那表示,一神論者提出的設計證據恰恰會指向相反結論:沒有設計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