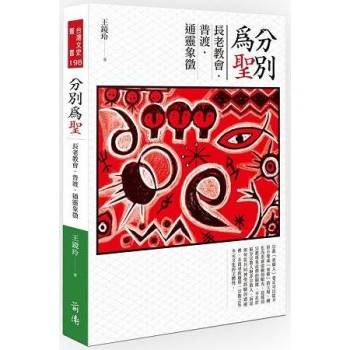【第一章】
非日常生活的
宗教現象
「去宗教」的人文教育
瞭解一個人的存在處境,應知道這一切的對應關係,都是經驗性的,而非只是概念。宗教人相信有一個絕對的真實,被視為「神聖」,超越了人的世界,又是人所安頓的世界。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發現只有在西方現代社會,「非宗教人」才發展得如此徹底。伊利亞德的觀點對應到台灣的現況,我們可以發現不一樣的多元性。不少台灣知識菁英對於超自然的態度是多元的,或者游離的。逢年過節回到故鄉祖厝拜祖先,在學術場合宣稱「無神論者」;聽到某些宗教研究者提到自身的宗教體驗時感到驚訝,甚至略帶歧視,似乎認為對方從科學理性改宗「退回」到反動保守的非理性陣營。這樣的心態反映了當代知識菁英面對自身文化傳統,以及學術訓練的價值觀或意識型態之間,還存在著複雜的磨和與轉化張力。
台灣人文科學研究者去研究非自己宗教信仰的宗教現象,把自身的信仰藏在理論背後,彷彿自己不屬於任何文化共同體的隱形人,以便宣稱自己是理論上的「客觀中立」。弔詭地是,明明是做以台灣為主的宗教研究,但總是要把宗教現象披掛一件又一件強勢文化的名牌理論,或者以「全球化」、「後現代」的理論拼裝大雜燴,或者宣稱活在「無君父」、「無家國」的理論普遍性之下,讓讀者忘了被壓在這些理論金鐘罩底下,貌似獨步天下的理性個人之內,難以脫離、卻被遺忘、難以說出口的「文化母體」。自身的階級、族群、宗教信仰、甚至年齡世代的立場,經常被選擇性地隱藏。我們這些研究者接受強勢文化理論的訓練,但強勢理論的傳承也正是我們要回過來透過自身所研究、所生活的文化母體,找出會通與轉化的契機所在。大部分的學者們使用國家的經費補助,沿用父姓,接收家族財產,母語表達能力早已退化、甚至無法以母語交談。討論學術時,總要夾雜幾句或整串強勢外語(尤其是英語),偶而加幾句母語(尤其是台語)來找尋認同或製造笑料。這個難以說出的文化母體就是作為人存在處境的「自我」,由屬於自身的族群、世代、性別、階級⋯等等,共同體的利害得失所匯聚而成的主體。這個主體必須面對那些想以「民粹」、以「國族主義」的標籤來矮化與歧視的存在處境,這個主體必須面對仍以英文霸權為主的理論叢林,來冒充「客觀性」而不想面對文化主體的被殖民自卑心態。
「宗教人」在台灣這樣多元宗教的社會裡,從來就不屬於單一宗教絕對真實的文化現況。反一神信仰的西方當代思潮的無神論者,曾經把完全剔除「神聖」視為人奪回主體的勝利,但在台灣社會對宗教的態度卻不是如此。台灣社會在日本統治時期,一方面以現代化來剔除台灣固有的宗教傳統,另一方面引進日本人的宗教,並對十九世紀末日治時期進入台灣的基督宗教,保持合作與控制的態度。
日本透過學校教育弱化台灣人對於傳統宗教的認同,引進現代科學與西方知識的世界觀,讓傳統信仰以超自然聖界來解釋自然與生命安危的世界觀被「除魅」。台灣傳統宗教信仰慣俗的世界觀,受到大環境的日治時期宗教政策的打壓,以及當時受現代西方知識訓練的台灣菁英,例如「台灣文化協會」的抨擊。一九四九年之後,從中國流亡到台灣的國民政府,曾以外來統治者的心態,繼續歧視在地的傳統宗教信仰。
社會學學者瞿海源曾提出台灣現代教育是以「世俗人文主義」為根本精神,不鼓勵宗教,並以破除傳統「迷信」,以政教分離之名,卻對宗教帶有敵意。研究台灣民間信仰的學者焦大衛(David Jordan)也指出台灣公立學校教育的反宗教、反傳統精神(anti-traditionalist)立場。但這兩位學者並沒有進一步指出,打壓台灣在地宗教傳統背後,並不像西方社會擺脫傳統基督宗教控制的政權爭奪戰。當代人文教育把透過神話與宗教儀式,所表達對未知世界的恐懼與敬畏,轉換成現代科學理性。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在戒嚴時期雖然控制台灣的宗教,但是宗教並沒有因為學校教育的打壓與歧視而衰微。受影響的是受更高教育者、擁有更多文化資本者投入傳統宗教的人口急遽下降,以致於傳統宗教面對新舊社會結構變遷時,在資本主義和工業社會傳承宗教人文精神的人才斷層。再加上學校教育與政府所制訂的西式週六日勞動休假的作息,讓以農曆為主的傳統民間信仰與慣俗節慶受到嚴重的打擊,以致於能夠參加宗教活動的信徒,往往是無須固定勞動時間的老年人、婦女,以及非固定上班時間的勞動者,青少年的參與者則往往演變成以脫離學校教育者為主。
台灣民間信仰也一直到解嚴(一九八七年)之後,政治管制的威權不再,民間信仰活動因為信者眾多,迅速回復生機。不過,因為官方長期受到美日殖民勢力的影響,以及被國民黨外省統治集團與反傳統宗教的知識菁英掌控之故,讓人口雖居底層多數、以母語為主的民間宗教文化體系──例如詩詞、視覺藝術(彩繪、雕刻、刺繡)、曲藝(北管、南管、武館)、劇場(布袋戲、歌仔戲、傀儡戲、講古),多年來遭受打壓,變成相對弱勢。這些傳統藝術喪失長久累積的文化資本,導致無法在學校正規教育下,傳承民間文化所蘊含的歷史記憶、宇宙觀和信仰慣習等知識體系,迄今仍艱辛地找尋傳承給下一輪世代的契機。這些式微的傳統民間文化象徵體系,不再是被重視的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經驗,而是被知識菁英邊緣化、歧視,卻又是大家必須參與,去面對生死、面對現實考驗的「非日常」宗教現象。非日常生活的宗教經驗――「通靈」現象
「通靈」體驗範圍廣泛, 從古老希臘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的神話祭儀、基督宗教《新約聖經・使徒行傳》裡的聖靈充滿、《山海經・大荒西經》裡通天的巫群,到現代新興宗教的靈性復興運動、基督宗教的靈恩運動、以及台灣當代的靈乩風潮等等,在本書中是指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與自身所感應的神聖力量之間的互動。面對宗教現象相當核心的通靈體驗,如何詮釋就構成不同研究派門的特色。我選擇用「通靈」的漢字,而不使用「神秘主義」/「密(冥)契主義」(mysticism)、或「薩滿信仰」(Shamanism)等等字詞,這些翻譯的字詞背後,都有其原先宗教傳統的特殊性,和台灣民間通靈現象之間有關連但不等同。「通」具有宗教人「去感通⋯」、傳達、通曉、以及雙向往來交換之意,不同於從「神聖」界的角度,去詮釋如何透過人、事、時、地、物來展現的「顯聖」。
研究諾斯替宗教(gnostic religion)的代表學者約納斯(Hans Jonas)曾指出,在諾斯替宗教的「靈知」(gnosis),包含對於超自然、「神」的知識,這樣的知識不只是理性的思辨,還包含參與拯救的奧秘、包含信者對於「神聖」體系承擔任務的實踐面。本書所探討的普渡儀式/海邊普化儀式、以及通靈宗教體驗,也將站在這樣的宗教知識的視野上,一方面關注於宗教人如何體現神聖對象及其所包含的信仰象徵體系;另一方面也關注宗教人的通靈體驗,如何救度宗教人自身、以及反映所處身的社會現實。不同的族群、階級、性別、世代,多少強弱勢文化體系的衝突鬥爭,在時空演變過程裡,不斷改寫聖界的系譜與版圖,而聖界也一再展現其多樣性與相對性,來對照人將自我中心絕對化的霸權。台灣漢人宗教的神靈世界不斷融合拼裝歷代以來儒、釋、道、巫的權力階序(hierarchy)的神譜,再加入宇宙生成的氣化論,以及自從一九八○年代後引進的各種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風潮的新靈性類別,構成多元並蓄的顯聖生發場域。宗教社會學家丁仁傑稱自一九八○年代之後在台灣蓬勃發展的靈性運動為「集體性起乩活動」,並認為這項運動跨越了特定宗教組織教派,形成特殊修行體系。消除個人負面因果、與個人所屬靈脈連結,進而獲得現世的圓滿與終極救贖。雖然被視為集體性起乩,但是通靈經驗當中的個人特殊性,例如性別、階級與世代差異,仍然是值得關注的焦點,這是我希望從社會學家的集體現象分析之外,去探索更多宗教人自身在通靈展演中,對待神靈與超自然力量之間自我表現的面貌。
「通靈」在本書是指主體感通到與自身更內在或更超越的「能量場」,可因其所感通的內容,而稱為「能量體」,可以以人格意志的「他者」能量場現身,或是以非人格的「他界」能量形式現身。並因為感應到這樣的能量場,而導致宗教人在面對生命困境、挑戰或考驗時,具有承擔的意志力,企圖活出有別於原先的生存狀態。透過肉體的感官知覺與行動表現,以及個體與其所處身的共同體(家庭、族群、信仰團體⋯等等)之間的認同關係,來作為「通靈」的外顯現象。
「通靈」一方面是指通靈者感應自身所擁有的、或可接收到的至大無外的「大宇宙」、「天」、「地」、「自然」、「神靈」的意識、意志或能量,以及與萬物有靈的靈力相通。另一方面「通靈」可以至小無內,從日常生活最根本的一呼一吸,從感官體驗、身體器官、經絡穴位裡氣的流通循環,去感受自身微觀小宇宙到浩瀚大宇宙的氣動/靈動的生剋、通順或阻礙。通靈現象可以是來自傳統單一宗教所表現的理念與儀式行為,例如和祖源(祖靈)之間「靈」(魂)秩序的調和與否;也可以是以漢人宇宙觀吸納其他跨宗教靈性象徵的拼裝混體,兼具在地宗教信仰和物質文化相結合,例如本書的長老教會的基督教式「趕鬼」現象、以及海邊普化儀式現象。「靈」的價值定位的尊卑高低、善惡好壞,並非超越文化象徵體系之外的玄學,反而是當我們更深入不同的特定文化象徵體系(階級、族群、性別、世代)意識型態時,發掘到人性如何透過文化象徵的時代與地域特性,展現出壓迫與解放的辯證關係。
現今學者的研究上,不管是鄭志明所提出的「多重至上神觀」、呂理政所提「多重宇宙認知」、還是渡邊欣雄用的諸神「聯合國」,通靈者所供奉與感通的對象,隨著台灣移民社會的生存需求,因應不同時期被清帝國、日本、國民政府的政治力控制,不斷混裝民間佛教、道教、外來宗教信仰、原住民在地信仰,加上原先以家族共同體為主的拜祖先與慣俗禁忌,以及各新興的通靈團體的諸聖界,不斷增加擴編、跨越原先漢人傳統宗教史的聖界範圍。
通靈者的聖界包含神佛的世界、祖源的世界、以及其他的靈界(或者被命名為有情眾生、孤魂野鬼、冤親債主、非人類的動物靈等等)。在多神信仰系譜裡,按照儀式現場的目的而有不同聖界的臨在。就以母神為主的通靈儀式現象來看,不管是本書第四章以觀音菩薩和九天玄女為主的通靈者到海邊進行的普化儀式,還是本書第五章以母娘為主的信仰者,到花蓮勝安宮進香會靈的通靈展演,通靈者對聖界分工的系譜,除了過去一般民間舊慣習俗裡的玉皇上帝神權階序體系、佛教、道教神譜的聖界之外,連結更多個人感應為主的「通靈」神話版本。除了聖界「多元」的集體特質之外,還包括人與「靈」關係的「個別化」。過去被以男性宗教祭司(道士、法師、童乩)所主導、以制度性的儀式來祭拜聖界的信仰文化,在通靈信仰強調個體和聖界感通的模式較為普遍之後,「個體化」的人與聖界關係,以及母性的靈力表現,逐漸成為通靈現象趨勢,而不只是依賴單一宮廟宗教祭司來傳授神意。通靈者各自發展和所親近的聖界相感通,遊走不同地域的宮壇與通靈團體之間。聖界不再只是高高在上、需要中介來傳達旨意,而是可以像親子/女關係、師徒一般,成為通靈者修行的無形靈師團隊。
諾伊曼(Erich Neumann)指出在心理學上,個體所感受到這種動力是強迫性的,正如伊利亞德所言的,神聖顯現自身,讓宗教人感應到這樣的動能。「靈」不只是他界,而是透過「我」的主體去感應,「靈」包含外在性與內在性。首先就外在性而言,對於顯聖形式與靈力運作的象徵系統,充分表現了當今社會中,物質世界雖已深受現代西化文明所影響,但是神靈世界仍以華人帝王權力階層的運作模式,藉由和現實世界的距離感,來凸顯人對於古老、崇高、難以測度的「外在性」的敬畏與崇拜。對於這些聖界崇高的敬畏,以古代帝制官將權力的象徵,透過民間戲曲的劇場展演,來獲得其他信徒在宗教象徵體系上的理解與認同,例如「接旨令」、「領令旗」、「賜寶劍」、「領金印」、「安營」⋯等等。這樣的「時間差」──回到古代、回到古老神話根源,讓通靈者在角色扮演上,跳脫現實世界的身分。
其次就「靈」的內在性而言,透過喚起對被壓抑、被遺忘的內在自我的探索,讓個人得以挖掘更深的自我潛意識,得以重新面對眼前難以承擔的身心考驗。這裡牽涉到的是這些通靈者信仰上對於「累世」、「輪迴」信念的想像,以及「靈」在「累世」輪迴中,所承擔的任務完成與否、在「因果」報應束縛下和其他「靈源」/「冤親債主」之間如何解冤釋結⋯等等個人神話的版本。透過透過內在自我的覺知,在儀式象徵性的交換中,以外顯的身體律動,來合理化通靈角色與個人現實命運的關連。這些透過外在性與內在性的聖界感應與想像的雙重性,一方面將聖界賦予最高人間權力象徵,回過來讓通靈者藉帝王式權力階序的聖界所肯定、以及被賦予使命與任務。個人不再只是面對現實權威或支配者匍伏下拜、卑微低下的「小老百姓」、被社會和大眾媒體邊緣化、甚至歧視的低薪或無業的弱者,而是神話世界裡成為神明任務的執行者。長時間拿刀切滷味、油膩殘漬依舊的手掌,在靈動時變換成蓮花指、劍指、化掌為拳、彷彿神明舞蹈的肢體開展。另一方面,這雙重的外在性與內在性,也透過通靈展演和轉世神話劇的角色扮演,通靈者意識到累世輪迴中曾經生為帝王將相、曾經梟雄亂賊,來對照與補償此生坎坷崎嶇的缺憾。被聖界肯定的滿足感,以及得知現在苦難來自過去因果報應的「公平性」,加上儀式象徵交換──供品的祭拜、符令、「開文」與金紙的燒化等,來企圖化解苦難來源的威脅,讓無力改變現狀的個人,找到暫時的寄託。
非日常生活的
宗教現象
「去宗教」的人文教育
瞭解一個人的存在處境,應知道這一切的對應關係,都是經驗性的,而非只是概念。宗教人相信有一個絕對的真實,被視為「神聖」,超越了人的世界,又是人所安頓的世界。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發現只有在西方現代社會,「非宗教人」才發展得如此徹底。伊利亞德的觀點對應到台灣的現況,我們可以發現不一樣的多元性。不少台灣知識菁英對於超自然的態度是多元的,或者游離的。逢年過節回到故鄉祖厝拜祖先,在學術場合宣稱「無神論者」;聽到某些宗教研究者提到自身的宗教體驗時感到驚訝,甚至略帶歧視,似乎認為對方從科學理性改宗「退回」到反動保守的非理性陣營。這樣的心態反映了當代知識菁英面對自身文化傳統,以及學術訓練的價值觀或意識型態之間,還存在著複雜的磨和與轉化張力。
台灣人文科學研究者去研究非自己宗教信仰的宗教現象,把自身的信仰藏在理論背後,彷彿自己不屬於任何文化共同體的隱形人,以便宣稱自己是理論上的「客觀中立」。弔詭地是,明明是做以台灣為主的宗教研究,但總是要把宗教現象披掛一件又一件強勢文化的名牌理論,或者以「全球化」、「後現代」的理論拼裝大雜燴,或者宣稱活在「無君父」、「無家國」的理論普遍性之下,讓讀者忘了被壓在這些理論金鐘罩底下,貌似獨步天下的理性個人之內,難以脫離、卻被遺忘、難以說出口的「文化母體」。自身的階級、族群、宗教信仰、甚至年齡世代的立場,經常被選擇性地隱藏。我們這些研究者接受強勢文化理論的訓練,但強勢理論的傳承也正是我們要回過來透過自身所研究、所生活的文化母體,找出會通與轉化的契機所在。大部分的學者們使用國家的經費補助,沿用父姓,接收家族財產,母語表達能力早已退化、甚至無法以母語交談。討論學術時,總要夾雜幾句或整串強勢外語(尤其是英語),偶而加幾句母語(尤其是台語)來找尋認同或製造笑料。這個難以說出的文化母體就是作為人存在處境的「自我」,由屬於自身的族群、世代、性別、階級⋯等等,共同體的利害得失所匯聚而成的主體。這個主體必須面對那些想以「民粹」、以「國族主義」的標籤來矮化與歧視的存在處境,這個主體必須面對仍以英文霸權為主的理論叢林,來冒充「客觀性」而不想面對文化主體的被殖民自卑心態。
「宗教人」在台灣這樣多元宗教的社會裡,從來就不屬於單一宗教絕對真實的文化現況。反一神信仰的西方當代思潮的無神論者,曾經把完全剔除「神聖」視為人奪回主體的勝利,但在台灣社會對宗教的態度卻不是如此。台灣社會在日本統治時期,一方面以現代化來剔除台灣固有的宗教傳統,另一方面引進日本人的宗教,並對十九世紀末日治時期進入台灣的基督宗教,保持合作與控制的態度。
日本透過學校教育弱化台灣人對於傳統宗教的認同,引進現代科學與西方知識的世界觀,讓傳統信仰以超自然聖界來解釋自然與生命安危的世界觀被「除魅」。台灣傳統宗教信仰慣俗的世界觀,受到大環境的日治時期宗教政策的打壓,以及當時受現代西方知識訓練的台灣菁英,例如「台灣文化協會」的抨擊。一九四九年之後,從中國流亡到台灣的國民政府,曾以外來統治者的心態,繼續歧視在地的傳統宗教信仰。
社會學學者瞿海源曾提出台灣現代教育是以「世俗人文主義」為根本精神,不鼓勵宗教,並以破除傳統「迷信」,以政教分離之名,卻對宗教帶有敵意。研究台灣民間信仰的學者焦大衛(David Jordan)也指出台灣公立學校教育的反宗教、反傳統精神(anti-traditionalist)立場。但這兩位學者並沒有進一步指出,打壓台灣在地宗教傳統背後,並不像西方社會擺脫傳統基督宗教控制的政權爭奪戰。當代人文教育把透過神話與宗教儀式,所表達對未知世界的恐懼與敬畏,轉換成現代科學理性。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在戒嚴時期雖然控制台灣的宗教,但是宗教並沒有因為學校教育的打壓與歧視而衰微。受影響的是受更高教育者、擁有更多文化資本者投入傳統宗教的人口急遽下降,以致於傳統宗教面對新舊社會結構變遷時,在資本主義和工業社會傳承宗教人文精神的人才斷層。再加上學校教育與政府所制訂的西式週六日勞動休假的作息,讓以農曆為主的傳統民間信仰與慣俗節慶受到嚴重的打擊,以致於能夠參加宗教活動的信徒,往往是無須固定勞動時間的老年人、婦女,以及非固定上班時間的勞動者,青少年的參與者則往往演變成以脫離學校教育者為主。
台灣民間信仰也一直到解嚴(一九八七年)之後,政治管制的威權不再,民間信仰活動因為信者眾多,迅速回復生機。不過,因為官方長期受到美日殖民勢力的影響,以及被國民黨外省統治集團與反傳統宗教的知識菁英掌控之故,讓人口雖居底層多數、以母語為主的民間宗教文化體系──例如詩詞、視覺藝術(彩繪、雕刻、刺繡)、曲藝(北管、南管、武館)、劇場(布袋戲、歌仔戲、傀儡戲、講古),多年來遭受打壓,變成相對弱勢。這些傳統藝術喪失長久累積的文化資本,導致無法在學校正規教育下,傳承民間文化所蘊含的歷史記憶、宇宙觀和信仰慣習等知識體系,迄今仍艱辛地找尋傳承給下一輪世代的契機。這些式微的傳統民間文化象徵體系,不再是被重視的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經驗,而是被知識菁英邊緣化、歧視,卻又是大家必須參與,去面對生死、面對現實考驗的「非日常」宗教現象。非日常生活的宗教經驗――「通靈」現象
「通靈」體驗範圍廣泛, 從古老希臘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的神話祭儀、基督宗教《新約聖經・使徒行傳》裡的聖靈充滿、《山海經・大荒西經》裡通天的巫群,到現代新興宗教的靈性復興運動、基督宗教的靈恩運動、以及台灣當代的靈乩風潮等等,在本書中是指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與自身所感應的神聖力量之間的互動。面對宗教現象相當核心的通靈體驗,如何詮釋就構成不同研究派門的特色。我選擇用「通靈」的漢字,而不使用「神秘主義」/「密(冥)契主義」(mysticism)、或「薩滿信仰」(Shamanism)等等字詞,這些翻譯的字詞背後,都有其原先宗教傳統的特殊性,和台灣民間通靈現象之間有關連但不等同。「通」具有宗教人「去感通⋯」、傳達、通曉、以及雙向往來交換之意,不同於從「神聖」界的角度,去詮釋如何透過人、事、時、地、物來展現的「顯聖」。
研究諾斯替宗教(gnostic religion)的代表學者約納斯(Hans Jonas)曾指出,在諾斯替宗教的「靈知」(gnosis),包含對於超自然、「神」的知識,這樣的知識不只是理性的思辨,還包含參與拯救的奧秘、包含信者對於「神聖」體系承擔任務的實踐面。本書所探討的普渡儀式/海邊普化儀式、以及通靈宗教體驗,也將站在這樣的宗教知識的視野上,一方面關注於宗教人如何體現神聖對象及其所包含的信仰象徵體系;另一方面也關注宗教人的通靈體驗,如何救度宗教人自身、以及反映所處身的社會現實。不同的族群、階級、性別、世代,多少強弱勢文化體系的衝突鬥爭,在時空演變過程裡,不斷改寫聖界的系譜與版圖,而聖界也一再展現其多樣性與相對性,來對照人將自我中心絕對化的霸權。台灣漢人宗教的神靈世界不斷融合拼裝歷代以來儒、釋、道、巫的權力階序(hierarchy)的神譜,再加入宇宙生成的氣化論,以及自從一九八○年代後引進的各種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風潮的新靈性類別,構成多元並蓄的顯聖生發場域。宗教社會學家丁仁傑稱自一九八○年代之後在台灣蓬勃發展的靈性運動為「集體性起乩活動」,並認為這項運動跨越了特定宗教組織教派,形成特殊修行體系。消除個人負面因果、與個人所屬靈脈連結,進而獲得現世的圓滿與終極救贖。雖然被視為集體性起乩,但是通靈經驗當中的個人特殊性,例如性別、階級與世代差異,仍然是值得關注的焦點,這是我希望從社會學家的集體現象分析之外,去探索更多宗教人自身在通靈展演中,對待神靈與超自然力量之間自我表現的面貌。
「通靈」在本書是指主體感通到與自身更內在或更超越的「能量場」,可因其所感通的內容,而稱為「能量體」,可以以人格意志的「他者」能量場現身,或是以非人格的「他界」能量形式現身。並因為感應到這樣的能量場,而導致宗教人在面對生命困境、挑戰或考驗時,具有承擔的意志力,企圖活出有別於原先的生存狀態。透過肉體的感官知覺與行動表現,以及個體與其所處身的共同體(家庭、族群、信仰團體⋯等等)之間的認同關係,來作為「通靈」的外顯現象。
「通靈」一方面是指通靈者感應自身所擁有的、或可接收到的至大無外的「大宇宙」、「天」、「地」、「自然」、「神靈」的意識、意志或能量,以及與萬物有靈的靈力相通。另一方面「通靈」可以至小無內,從日常生活最根本的一呼一吸,從感官體驗、身體器官、經絡穴位裡氣的流通循環,去感受自身微觀小宇宙到浩瀚大宇宙的氣動/靈動的生剋、通順或阻礙。通靈現象可以是來自傳統單一宗教所表現的理念與儀式行為,例如和祖源(祖靈)之間「靈」(魂)秩序的調和與否;也可以是以漢人宇宙觀吸納其他跨宗教靈性象徵的拼裝混體,兼具在地宗教信仰和物質文化相結合,例如本書的長老教會的基督教式「趕鬼」現象、以及海邊普化儀式現象。「靈」的價值定位的尊卑高低、善惡好壞,並非超越文化象徵體系之外的玄學,反而是當我們更深入不同的特定文化象徵體系(階級、族群、性別、世代)意識型態時,發掘到人性如何透過文化象徵的時代與地域特性,展現出壓迫與解放的辯證關係。
現今學者的研究上,不管是鄭志明所提出的「多重至上神觀」、呂理政所提「多重宇宙認知」、還是渡邊欣雄用的諸神「聯合國」,通靈者所供奉與感通的對象,隨著台灣移民社會的生存需求,因應不同時期被清帝國、日本、國民政府的政治力控制,不斷混裝民間佛教、道教、外來宗教信仰、原住民在地信仰,加上原先以家族共同體為主的拜祖先與慣俗禁忌,以及各新興的通靈團體的諸聖界,不斷增加擴編、跨越原先漢人傳統宗教史的聖界範圍。
通靈者的聖界包含神佛的世界、祖源的世界、以及其他的靈界(或者被命名為有情眾生、孤魂野鬼、冤親債主、非人類的動物靈等等)。在多神信仰系譜裡,按照儀式現場的目的而有不同聖界的臨在。就以母神為主的通靈儀式現象來看,不管是本書第四章以觀音菩薩和九天玄女為主的通靈者到海邊進行的普化儀式,還是本書第五章以母娘為主的信仰者,到花蓮勝安宮進香會靈的通靈展演,通靈者對聖界分工的系譜,除了過去一般民間舊慣習俗裡的玉皇上帝神權階序體系、佛教、道教神譜的聖界之外,連結更多個人感應為主的「通靈」神話版本。除了聖界「多元」的集體特質之外,還包括人與「靈」關係的「個別化」。過去被以男性宗教祭司(道士、法師、童乩)所主導、以制度性的儀式來祭拜聖界的信仰文化,在通靈信仰強調個體和聖界感通的模式較為普遍之後,「個體化」的人與聖界關係,以及母性的靈力表現,逐漸成為通靈現象趨勢,而不只是依賴單一宮廟宗教祭司來傳授神意。通靈者各自發展和所親近的聖界相感通,遊走不同地域的宮壇與通靈團體之間。聖界不再只是高高在上、需要中介來傳達旨意,而是可以像親子/女關係、師徒一般,成為通靈者修行的無形靈師團隊。
諾伊曼(Erich Neumann)指出在心理學上,個體所感受到這種動力是強迫性的,正如伊利亞德所言的,神聖顯現自身,讓宗教人感應到這樣的動能。「靈」不只是他界,而是透過「我」的主體去感應,「靈」包含外在性與內在性。首先就外在性而言,對於顯聖形式與靈力運作的象徵系統,充分表現了當今社會中,物質世界雖已深受現代西化文明所影響,但是神靈世界仍以華人帝王權力階層的運作模式,藉由和現實世界的距離感,來凸顯人對於古老、崇高、難以測度的「外在性」的敬畏與崇拜。對於這些聖界崇高的敬畏,以古代帝制官將權力的象徵,透過民間戲曲的劇場展演,來獲得其他信徒在宗教象徵體系上的理解與認同,例如「接旨令」、「領令旗」、「賜寶劍」、「領金印」、「安營」⋯等等。這樣的「時間差」──回到古代、回到古老神話根源,讓通靈者在角色扮演上,跳脫現實世界的身分。
其次就「靈」的內在性而言,透過喚起對被壓抑、被遺忘的內在自我的探索,讓個人得以挖掘更深的自我潛意識,得以重新面對眼前難以承擔的身心考驗。這裡牽涉到的是這些通靈者信仰上對於「累世」、「輪迴」信念的想像,以及「靈」在「累世」輪迴中,所承擔的任務完成與否、在「因果」報應束縛下和其他「靈源」/「冤親債主」之間如何解冤釋結⋯等等個人神話的版本。透過透過內在自我的覺知,在儀式象徵性的交換中,以外顯的身體律動,來合理化通靈角色與個人現實命運的關連。這些透過外在性與內在性的聖界感應與想像的雙重性,一方面將聖界賦予最高人間權力象徵,回過來讓通靈者藉帝王式權力階序的聖界所肯定、以及被賦予使命與任務。個人不再只是面對現實權威或支配者匍伏下拜、卑微低下的「小老百姓」、被社會和大眾媒體邊緣化、甚至歧視的低薪或無業的弱者,而是神話世界裡成為神明任務的執行者。長時間拿刀切滷味、油膩殘漬依舊的手掌,在靈動時變換成蓮花指、劍指、化掌為拳、彷彿神明舞蹈的肢體開展。另一方面,這雙重的外在性與內在性,也透過通靈展演和轉世神話劇的角色扮演,通靈者意識到累世輪迴中曾經生為帝王將相、曾經梟雄亂賊,來對照與補償此生坎坷崎嶇的缺憾。被聖界肯定的滿足感,以及得知現在苦難來自過去因果報應的「公平性」,加上儀式象徵交換──供品的祭拜、符令、「開文」與金紙的燒化等,來企圖化解苦難來源的威脅,讓無力改變現狀的個人,找到暫時的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