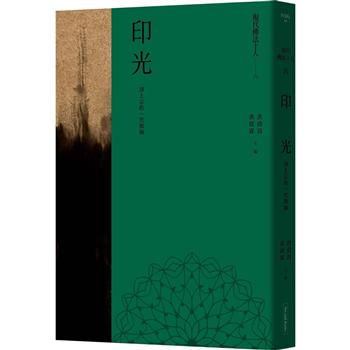以身證教化僧俗——印光大師
孤高梗介,萬眾信仰,常將死字掛心頭,淨土宗的一代祖師
印光出生於一八六一年,陝西合陽陳村人,俗家姓趙,名紹伊,字子任,出家名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是近代著名的淨土宗高僧,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
他一出生即患有眼疾,常處於黑暗不能視,後才病癒。年幼聰慧,隨兄長熟讀儒書,自以孔孟之道為任,受韓愈、歐陽修等大儒闢佛思想影響,當時也跟著批判佛教。至十五歲後,因病所困數年,省思闢佛言論,並讀佛經,始悟前非,於是回心向佛。
二十一歲時,逃家至終南山五台蓮華洞寺,禮道純和尚為師,並請剃度出家。長兄追至,要他回家辭別父母再出家,於是便歸家,但就被禁足,經八十餘天後,利用長兄不在,拿著僧服再次逃家。
逃家的印光後來安單於湖北蓮華寺,任知客僧,並行苦役,擔任劈柴燒柴的柴頭、挑水燒水的水頭,也代理庫房整理管理之庫頭。有一天,在幫忙整理攤曬經書時,看到《龍舒淨土文》殘本,方知有念佛往生淨土法門,是「一法圓賅萬行,普攝群機」,這對他日後宏揚淨土法門,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次年,到陝西興安雙溪寺印海定律師處受具足戒。在戒期中眼疾復發,於是一心念佛日夜不輟,幸蒙佛加持,戒期圓滿後,眼疾又癒,從此更加堅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甚至認為念佛可治眾病。因此之故,往後印光大師無論自行、化他,都以淨土法門為依歸。受戒後,回終南山太乙峰潛修,以專心念佛讀經為業,愈覺念佛法門更契群生之心。
一九〇九年,太虛就讀祇洹精舍,半年後精舍停辦,因而轉至普陀山法雨小學任教,期間曾親近印光,與之詩文酬唱,深得印光讚許。然十餘年後印光對太虛推動「整頓僧伽制度」不以為然,但也不礙兩人之情誼。
印光一生勤儉節用,悲濟群生,信眾供養資糧,悉皆代為廣種福田,或用於流通經籍,或用以救濟飢貧。其先後在上海、蘇州創辦弘社,二十餘年來所印佛書有百餘種,數量約不下四、五百萬冊、百萬餘幀的佛像,因此受法益者眾多。
六十二歲時,江蘇省提出寺廟興學的政策,引起佛界嘩然。大師為保教護寺,不遺餘力地奔走呼籲,方得扭轉危機。
一九三八年,七十七歲時,印光大師移錫靈巖山寺安居。由於年事已高,上山方滿三年便示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凌晨,從床坐起而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自言:「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享壽八十,僧臘六十。火化荼毘後得五彩舍利無數,令見聞者生起無比的信心。
重要著述及傳人
關於印光的著作,大致包含兩大類,一是印光大師親選的作品,一是弟子為其摘錄、編輯之言說,或圓寂後撰述的追悼文字。現已收編成七冊本的《印光大師全集》。
現今留存《印光大師全集》,其中前三冊是印光親撰作品,即第一冊《印光大師文鈔》(增廣正編),第二冊《印光大師文鈔續編》(第二編),第三冊《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外集)。
印光生前重刊或主持修訂的典籍,出版流通影響甚大,如《淨土五經》、《安士全書》、《淨土十要》、及四大名山志之修訂,雖非其著作,但可見保留文化與應俗教化之用心。
印光一生未為人剃度出家,也未有名定的弟子傳人,但在其道德行證的教化下,諸多大德皆師法之。弘一大師曾說:「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嘗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列。」又指示弟子:「現今修持,求其機理雙契,利鈍咸宜。易行捷證者,是在淨土法門。可閱《印光法師文鈔》及《嘉言錄》,尤其是嘉言分類易閱,開端之處如覺難領會,不妨從中間較淺顯處先閱。」可見弘一對印光大師之尊崇。
近代居士之中,以高鶴年、范古農、李炳南等受其影響最深,李炳南創辦台中蓮社,弘揚淨土法門,深受信眾崇敬,對光復後的臺灣佛教有巨大的影響,其弘揚淨土的思想方法,即承襲和發揚印光思想與精神而成的。
對佛教的貢獻——用身證度化僧俗
中國近代高僧之中,印光專弘淨土,被稱為淨宗土第十三代祖。而他在整個大時代中,可說是十分特別的典範,為人景仰。
首先,印光始終韜光養晦,不喜攀緣結交,不求名聞利養,惟有精勤念佛,專注用心,以期證得念佛三昧,如是精進不放逸,為眾信士崇敬。開示常以「但將一個死字,貼到額頭上,掛到眉毛上」之言,自警策勵專志念佛之心。
綜觀其一生專志念佛法門,亦深入經教,又能融入通俗來教化,其講述淨土念佛之理,深入淺出,易懂易行,故在社會上有廣大信徒隨其教行,弘揚淨土,而其著作皆是必讀必研之典籍。
其臨教難時,衛教心切,擇善固執,絕不讓人;遇天災時,捨一切信眾所供資用,救急布施。雖不同於太虛對內部僧伽作改革之言之行,甚至還認為整理僧伽制度是無用的新花樣,但這並非代表他不知道傳統佛教內部的問題,只是認為與其外塑不如內行以立標杆,例如他對大醒法師說;「你就是罵死了他們,他們仍舊不能把叢林改好,罵之無益,枉造口業。」可見其所期望且願行的是透過身證來度化僧俗、導正風氣,是保守派與革新派皆尊崇的大師。
印光大師從眾人無上的崇仰中抽離出來,以一個人的心性生命,以最純粹的心、最純粹的行,感動天下人,來啟發人心悟境。
他一心念佛、一心修證,或許有人認為,這是很個化的,和時代革新沒有什麼聯結。但是我們卻發現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印光愈是專精自己的修行,對時代的影響便愈大;他愈在山中純粹的念行,所展現的風貌,愈引發外在世界的震盪與崇仰。印光成為一個心性革新的力量來源,變成萬眾所依止的力量。在這個浮動的世間,他成為一股清流,不斷清除時代的浮渣,讓生命的覺性延續而行。
印光大師一心念佛、一心修證,讓人的心歸於究極的純粹,看來是單一的意念清淨之法,在現代卻有著特別的意義。現代人的所知障特別重,往往以自己人生的片段,附會解釋修行教法。特別是在這個混亂的時代,一心一意專志的修行者,更能夠幫助人們袪除煩惱,更能成就廣大的菩薩妙行,讓眾生獲得生命的大喜樂。
而淨土法門,對即將到來的太空世紀,人類即將面臨的外星世界,對宇宙的未知,有了新的意義。《阿彌陀經》中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距離地球如此遙遠的他方淨土,卻在一心皈命念佛中,產生了新的聯結,或許印光大師的一心念佛,竟為這個時代開創出一條嶄新的宇宙之路。
_____________
為在家弟子略說
三歸五戒十善義
悲哉眾生!從無始來,輪迴六道,流轉四生,無救無歸,無依無託,若失父之孤子,猶喪家之窮人。總由煩惱惡業,感斯生死苦果,盲無慧目,不能自出。大覺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間,為其說法,令度三歸,為翻邪歸正之本;令持五戒,為斷惡修善之緣,令行十善,為清淨身口意三業之根。從茲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三業既淨,然後可以遵修道品,令其背塵合覺,轉凡成聖。斷貪瞋癡煩惱之根本,成戒定慧菩提之大道。故為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三十七助道品等無量法門。又欲令速出生死,頓成佛道,故為說念佛求生淨土法門;使其不費多力,即生成辦。噫!世尊之恩,可謂極矣。雖父母不足譬,天地不足喻矣。不慧受恩實深,報恩無由。
今汝等謬聽人言,不遠數千里來,欲以我為師。然我自揣無德,再四推卻,汝等猶不應允。今不得已,將如來出世說法度生之意,略與汝等言之。並將三歸、五戒、十善,及淨土法門,略釋其義,使汝等有所取法,有所遵守。其四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等,非汝等智力所知,故略而不書。汝等若能依教奉行,是以佛為師,何況不慧!若不依教奉行,則尚負不慧之恩,何況佛恩!
三歸者(歸,亦作皈。皈字從白從反,取其反染成淨之義。)
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僧。
歸者,歸投;依者,依託。如人墮海,忽有船來,即便趣向,是歸投義;上船安坐,是依託義。生死為海,三寶為船,眾生歸依,即登彼岸。既歸依佛,以佛為師;從今日起,乃至命終,不得歸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既歸依法,以法為師;從今日起,乃至命終,不得歸依外道典籍(法即佛經,及修行種種法門,典籍即經書也)。既昄依僧,以僧為師;從於今日至命終時,不得皈依外道徒眾。
五戒者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好生惡死,物我同感。我既愛生,物豈願死?由是思之,生可殺乎?一切眾生輪迴六道,隨善惡業升降超沈。我與彼等,於多劫中互為父母,互為子女,當思拯拔,何忍殺乎?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於未來世皆當成佛。我若墜落,尚望拔濟。又既造殺業,必墮惡道,酬償宿債,展轉互殺,無有了期。由是思之,何敢殺乎?然殺生之由,起於食肉。若知如上所說因緣,自不敢食肉矣。又愚人謂肉為美,不知本是精血所成。內盛屎尿,外雜糞穢。腥臊臭穢,美從何來?常作不淨觀,食之當發嘔矣。又生謂人及禽獸,蛆蟲魚蝦,蚊蝱蚤蝨,凡有命者皆是。不可謂大者不可殺,小者可殺也。佛經廣說戒殺放生功德利益,俗人不能得讀。當觀安士先生「萬善先資」,可念知其梗概矣。
不偷盜者,即是見得思義,不與不取也。此事知廉恥者便能不犯。然細論之,非大聖大賢者所難免。何也?以公濟私,剋人益己,以勢取財,用計謀物,忌人富貴,願人貧賤,陽取為善之名,遇諸善事,心不認真;如設義學,不擇嚴師,誤人子弟;施醫藥,不辨真假,誤人性命;凡見急難,漠不速救,緩慢浮游,或致誤事;但取塞責了事,糜費他人錢財,於自心中不關緊要。如斯之類,皆名偷盜。以汝等身居善堂,故摘其利弊而略言之。
不邪淫者,俗人男女居室,生男育女,上關風化,下關祭祀,夫婦行淫,非其所禁。但當相敬如賓,為承宗祀,不可以為快樂,徇私忘身。雖是己妻,貪樂亦犯,但其罪輕微。若非己妻,苟合交通,即名邪淫,其罪極重。行邪淫者,是以人身行畜生事,報終命盡,先墮地獄餓鬼,後生畜生道中,千萬億劫不能出離。一切眾生從淫欲生,所以此戒難持易犯,縱是賢達,或時失足,何況愚人?若立志修持,須先明利害及對治方法,則如見毒蛇,如遇怨賊,恐畏怖懼,欲心自息矣。對治方法,廣載佛經,俗人無緣觀覽。當看安士先生「欲海回狂」,可以知其梗概矣(利,謂不犯之利。害,謂犯之禍害)。
不妄語者,言而有信,不虛妄發也。若見言不見,不見言見,以虛為實,以有為無等,凡是心口不相應,欲欺哄於人者皆是。又若自未斷惑,謂為斷惑;自未得道,謂為得道;名大妄語,其罪極重,命終之後,決定直墮阿鼻地獄,永無出期。今之修行而不知佛法教理者,比比皆是。當痛戒之,切要切要!以上四事,不論出家在家,受戒不受戒,犯之皆有罪過。以體性是惡故也。然不受戒人,一層罪過;受戒之人,兩層罪過。於作惡事罪上,又加一犯戒罪故。若持而不犯,功德無量無邊。切須勉之。
不飲酒者,酒能迷亂人心,壞智慧種。飲之令人顛倒昏狂,妄作非為,故佛制而斷之。凡修行者皆不許飲。並及葱韭薤(音械,小蒜也。)蒜五種葷菜,氣味臭穢,體不清潔,熟食發淫,生噉增恚,凡修行人皆不許食。然此小事,未受戒者,飲之食之,皆無罪過;受戒飲食,一層罪過。即是犯佛戒罪。佛已禁制,汝又去犯,故有罪也(五葷菜,西域有五,此方但四)。
十善者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綺語,六不兩舌,七不惡口,八不慳貪,九不瞋恚,十不邪見。
此中前三名身業,中四名口業,後三名意業。業者,事也。若持而不犯,則為十善;若犯而不持,則為十惡。十惡分上中下,感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身;十善分上中下,感天、人、阿修羅三善道身。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決定無疑,絲毫不錯也。殺盜淫妄,已於五戒中說。
綺語者,謂無益浮詞,華妙綺麗,談說淫欲,導人邪念等。兩舌者,謂向彼說此,向此說彼,挑唆是非,鬭構兩頭等。惡口者,謂言語麤惡,如刀如劍,發人隱惡,不避忌諱。又傷人父母,名大惡口;將來當受畜生果報。既受佛戒,切莫犯此。
慳貪者,自己之財不肯施人,名之為慳;他人之財但欲歸我,名之為貪。瞋恚者,恨怒也。見人有得,愁憂憤怒;見人有失,悅樂慶快。及逞勢逞氣,欺侮人物等。邪見者,不信為善得福,作惡得罪,言無因果,無有後世,輕侮聖言,毀佛經教等。
然此十善,總該一切,若能遵行,無惡不斷,無善不修。恐汝等不能體察,今略舉其一二。當孝順父母,無違無逆,委曲宛轉,勸令入道,斷葷吃素,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了脫生死。父母若信,善莫大焉。如決不依從,亦勿強逼,以失孝道。但於佛前,代父母懺悔罪過,斯可矣。於兄弟則盡友;於夫婦則盡敬;於子女則極方教訓,使其為良為善,切勿任意嬌慣,致成匪類;於鄰里鄉黨,當和睦忍讓,為說善惡因果,使其改過遷善;於朋友則盡信;於僕使當慈愛;於公事則盡心竭力,同於私事。凡見親識,遇父言慈,遇子言孝。若做生意,當以本求利,不可以假貨哄騙於人。若以此風化其一鄉一邑,便能消禍亂於未萌,致刑罰於無用。可謂在野盡忠,居家為政矣。
孤高梗介,萬眾信仰,常將死字掛心頭,淨土宗的一代祖師
印光出生於一八六一年,陝西合陽陳村人,俗家姓趙,名紹伊,字子任,出家名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是近代著名的淨土宗高僧,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
他一出生即患有眼疾,常處於黑暗不能視,後才病癒。年幼聰慧,隨兄長熟讀儒書,自以孔孟之道為任,受韓愈、歐陽修等大儒闢佛思想影響,當時也跟著批判佛教。至十五歲後,因病所困數年,省思闢佛言論,並讀佛經,始悟前非,於是回心向佛。
二十一歲時,逃家至終南山五台蓮華洞寺,禮道純和尚為師,並請剃度出家。長兄追至,要他回家辭別父母再出家,於是便歸家,但就被禁足,經八十餘天後,利用長兄不在,拿著僧服再次逃家。
逃家的印光後來安單於湖北蓮華寺,任知客僧,並行苦役,擔任劈柴燒柴的柴頭、挑水燒水的水頭,也代理庫房整理管理之庫頭。有一天,在幫忙整理攤曬經書時,看到《龍舒淨土文》殘本,方知有念佛往生淨土法門,是「一法圓賅萬行,普攝群機」,這對他日後宏揚淨土法門,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次年,到陝西興安雙溪寺印海定律師處受具足戒。在戒期中眼疾復發,於是一心念佛日夜不輟,幸蒙佛加持,戒期圓滿後,眼疾又癒,從此更加堅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甚至認為念佛可治眾病。因此之故,往後印光大師無論自行、化他,都以淨土法門為依歸。受戒後,回終南山太乙峰潛修,以專心念佛讀經為業,愈覺念佛法門更契群生之心。
一九〇九年,太虛就讀祇洹精舍,半年後精舍停辦,因而轉至普陀山法雨小學任教,期間曾親近印光,與之詩文酬唱,深得印光讚許。然十餘年後印光對太虛推動「整頓僧伽制度」不以為然,但也不礙兩人之情誼。
印光一生勤儉節用,悲濟群生,信眾供養資糧,悉皆代為廣種福田,或用於流通經籍,或用以救濟飢貧。其先後在上海、蘇州創辦弘社,二十餘年來所印佛書有百餘種,數量約不下四、五百萬冊、百萬餘幀的佛像,因此受法益者眾多。
六十二歲時,江蘇省提出寺廟興學的政策,引起佛界嘩然。大師為保教護寺,不遺餘力地奔走呼籲,方得扭轉危機。
一九三八年,七十七歲時,印光大師移錫靈巖山寺安居。由於年事已高,上山方滿三年便示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凌晨,從床坐起而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自言:「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享壽八十,僧臘六十。火化荼毘後得五彩舍利無數,令見聞者生起無比的信心。
重要著述及傳人
關於印光的著作,大致包含兩大類,一是印光大師親選的作品,一是弟子為其摘錄、編輯之言說,或圓寂後撰述的追悼文字。現已收編成七冊本的《印光大師全集》。
現今留存《印光大師全集》,其中前三冊是印光親撰作品,即第一冊《印光大師文鈔》(增廣正編),第二冊《印光大師文鈔續編》(第二編),第三冊《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外集)。
印光生前重刊或主持修訂的典籍,出版流通影響甚大,如《淨土五經》、《安士全書》、《淨土十要》、及四大名山志之修訂,雖非其著作,但可見保留文化與應俗教化之用心。
印光一生未為人剃度出家,也未有名定的弟子傳人,但在其道德行證的教化下,諸多大德皆師法之。弘一大師曾說:「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嘗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列。」又指示弟子:「現今修持,求其機理雙契,利鈍咸宜。易行捷證者,是在淨土法門。可閱《印光法師文鈔》及《嘉言錄》,尤其是嘉言分類易閱,開端之處如覺難領會,不妨從中間較淺顯處先閱。」可見弘一對印光大師之尊崇。
近代居士之中,以高鶴年、范古農、李炳南等受其影響最深,李炳南創辦台中蓮社,弘揚淨土法門,深受信眾崇敬,對光復後的臺灣佛教有巨大的影響,其弘揚淨土的思想方法,即承襲和發揚印光思想與精神而成的。
對佛教的貢獻——用身證度化僧俗
中國近代高僧之中,印光專弘淨土,被稱為淨宗土第十三代祖。而他在整個大時代中,可說是十分特別的典範,為人景仰。
首先,印光始終韜光養晦,不喜攀緣結交,不求名聞利養,惟有精勤念佛,專注用心,以期證得念佛三昧,如是精進不放逸,為眾信士崇敬。開示常以「但將一個死字,貼到額頭上,掛到眉毛上」之言,自警策勵專志念佛之心。
綜觀其一生專志念佛法門,亦深入經教,又能融入通俗來教化,其講述淨土念佛之理,深入淺出,易懂易行,故在社會上有廣大信徒隨其教行,弘揚淨土,而其著作皆是必讀必研之典籍。
其臨教難時,衛教心切,擇善固執,絕不讓人;遇天災時,捨一切信眾所供資用,救急布施。雖不同於太虛對內部僧伽作改革之言之行,甚至還認為整理僧伽制度是無用的新花樣,但這並非代表他不知道傳統佛教內部的問題,只是認為與其外塑不如內行以立標杆,例如他對大醒法師說;「你就是罵死了他們,他們仍舊不能把叢林改好,罵之無益,枉造口業。」可見其所期望且願行的是透過身證來度化僧俗、導正風氣,是保守派與革新派皆尊崇的大師。
印光大師從眾人無上的崇仰中抽離出來,以一個人的心性生命,以最純粹的心、最純粹的行,感動天下人,來啟發人心悟境。
他一心念佛、一心修證,或許有人認為,這是很個化的,和時代革新沒有什麼聯結。但是我們卻發現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印光愈是專精自己的修行,對時代的影響便愈大;他愈在山中純粹的念行,所展現的風貌,愈引發外在世界的震盪與崇仰。印光成為一個心性革新的力量來源,變成萬眾所依止的力量。在這個浮動的世間,他成為一股清流,不斷清除時代的浮渣,讓生命的覺性延續而行。
印光大師一心念佛、一心修證,讓人的心歸於究極的純粹,看來是單一的意念清淨之法,在現代卻有著特別的意義。現代人的所知障特別重,往往以自己人生的片段,附會解釋修行教法。特別是在這個混亂的時代,一心一意專志的修行者,更能夠幫助人們袪除煩惱,更能成就廣大的菩薩妙行,讓眾生獲得生命的大喜樂。
而淨土法門,對即將到來的太空世紀,人類即將面臨的外星世界,對宇宙的未知,有了新的意義。《阿彌陀經》中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距離地球如此遙遠的他方淨土,卻在一心皈命念佛中,產生了新的聯結,或許印光大師的一心念佛,竟為這個時代開創出一條嶄新的宇宙之路。
_____________
為在家弟子略說
三歸五戒十善義
悲哉眾生!從無始來,輪迴六道,流轉四生,無救無歸,無依無託,若失父之孤子,猶喪家之窮人。總由煩惱惡業,感斯生死苦果,盲無慧目,不能自出。大覺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間,為其說法,令度三歸,為翻邪歸正之本;令持五戒,為斷惡修善之緣,令行十善,為清淨身口意三業之根。從茲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三業既淨,然後可以遵修道品,令其背塵合覺,轉凡成聖。斷貪瞋癡煩惱之根本,成戒定慧菩提之大道。故為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三十七助道品等無量法門。又欲令速出生死,頓成佛道,故為說念佛求生淨土法門;使其不費多力,即生成辦。噫!世尊之恩,可謂極矣。雖父母不足譬,天地不足喻矣。不慧受恩實深,報恩無由。
今汝等謬聽人言,不遠數千里來,欲以我為師。然我自揣無德,再四推卻,汝等猶不應允。今不得已,將如來出世說法度生之意,略與汝等言之。並將三歸、五戒、十善,及淨土法門,略釋其義,使汝等有所取法,有所遵守。其四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等,非汝等智力所知,故略而不書。汝等若能依教奉行,是以佛為師,何況不慧!若不依教奉行,則尚負不慧之恩,何況佛恩!
三歸者(歸,亦作皈。皈字從白從反,取其反染成淨之義。)
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僧。
歸者,歸投;依者,依託。如人墮海,忽有船來,即便趣向,是歸投義;上船安坐,是依託義。生死為海,三寶為船,眾生歸依,即登彼岸。既歸依佛,以佛為師;從今日起,乃至命終,不得歸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既歸依法,以法為師;從今日起,乃至命終,不得歸依外道典籍(法即佛經,及修行種種法門,典籍即經書也)。既昄依僧,以僧為師;從於今日至命終時,不得皈依外道徒眾。
五戒者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好生惡死,物我同感。我既愛生,物豈願死?由是思之,生可殺乎?一切眾生輪迴六道,隨善惡業升降超沈。我與彼等,於多劫中互為父母,互為子女,當思拯拔,何忍殺乎?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於未來世皆當成佛。我若墜落,尚望拔濟。又既造殺業,必墮惡道,酬償宿債,展轉互殺,無有了期。由是思之,何敢殺乎?然殺生之由,起於食肉。若知如上所說因緣,自不敢食肉矣。又愚人謂肉為美,不知本是精血所成。內盛屎尿,外雜糞穢。腥臊臭穢,美從何來?常作不淨觀,食之當發嘔矣。又生謂人及禽獸,蛆蟲魚蝦,蚊蝱蚤蝨,凡有命者皆是。不可謂大者不可殺,小者可殺也。佛經廣說戒殺放生功德利益,俗人不能得讀。當觀安士先生「萬善先資」,可念知其梗概矣。
不偷盜者,即是見得思義,不與不取也。此事知廉恥者便能不犯。然細論之,非大聖大賢者所難免。何也?以公濟私,剋人益己,以勢取財,用計謀物,忌人富貴,願人貧賤,陽取為善之名,遇諸善事,心不認真;如設義學,不擇嚴師,誤人子弟;施醫藥,不辨真假,誤人性命;凡見急難,漠不速救,緩慢浮游,或致誤事;但取塞責了事,糜費他人錢財,於自心中不關緊要。如斯之類,皆名偷盜。以汝等身居善堂,故摘其利弊而略言之。
不邪淫者,俗人男女居室,生男育女,上關風化,下關祭祀,夫婦行淫,非其所禁。但當相敬如賓,為承宗祀,不可以為快樂,徇私忘身。雖是己妻,貪樂亦犯,但其罪輕微。若非己妻,苟合交通,即名邪淫,其罪極重。行邪淫者,是以人身行畜生事,報終命盡,先墮地獄餓鬼,後生畜生道中,千萬億劫不能出離。一切眾生從淫欲生,所以此戒難持易犯,縱是賢達,或時失足,何況愚人?若立志修持,須先明利害及對治方法,則如見毒蛇,如遇怨賊,恐畏怖懼,欲心自息矣。對治方法,廣載佛經,俗人無緣觀覽。當看安士先生「欲海回狂」,可以知其梗概矣(利,謂不犯之利。害,謂犯之禍害)。
不妄語者,言而有信,不虛妄發也。若見言不見,不見言見,以虛為實,以有為無等,凡是心口不相應,欲欺哄於人者皆是。又若自未斷惑,謂為斷惑;自未得道,謂為得道;名大妄語,其罪極重,命終之後,決定直墮阿鼻地獄,永無出期。今之修行而不知佛法教理者,比比皆是。當痛戒之,切要切要!以上四事,不論出家在家,受戒不受戒,犯之皆有罪過。以體性是惡故也。然不受戒人,一層罪過;受戒之人,兩層罪過。於作惡事罪上,又加一犯戒罪故。若持而不犯,功德無量無邊。切須勉之。
不飲酒者,酒能迷亂人心,壞智慧種。飲之令人顛倒昏狂,妄作非為,故佛制而斷之。凡修行者皆不許飲。並及葱韭薤(音械,小蒜也。)蒜五種葷菜,氣味臭穢,體不清潔,熟食發淫,生噉增恚,凡修行人皆不許食。然此小事,未受戒者,飲之食之,皆無罪過;受戒飲食,一層罪過。即是犯佛戒罪。佛已禁制,汝又去犯,故有罪也(五葷菜,西域有五,此方但四)。
十善者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綺語,六不兩舌,七不惡口,八不慳貪,九不瞋恚,十不邪見。
此中前三名身業,中四名口業,後三名意業。業者,事也。若持而不犯,則為十善;若犯而不持,則為十惡。十惡分上中下,感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身;十善分上中下,感天、人、阿修羅三善道身。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決定無疑,絲毫不錯也。殺盜淫妄,已於五戒中說。
綺語者,謂無益浮詞,華妙綺麗,談說淫欲,導人邪念等。兩舌者,謂向彼說此,向此說彼,挑唆是非,鬭構兩頭等。惡口者,謂言語麤惡,如刀如劍,發人隱惡,不避忌諱。又傷人父母,名大惡口;將來當受畜生果報。既受佛戒,切莫犯此。
慳貪者,自己之財不肯施人,名之為慳;他人之財但欲歸我,名之為貪。瞋恚者,恨怒也。見人有得,愁憂憤怒;見人有失,悅樂慶快。及逞勢逞氣,欺侮人物等。邪見者,不信為善得福,作惡得罪,言無因果,無有後世,輕侮聖言,毀佛經教等。
然此十善,總該一切,若能遵行,無惡不斷,無善不修。恐汝等不能體察,今略舉其一二。當孝順父母,無違無逆,委曲宛轉,勸令入道,斷葷吃素,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了脫生死。父母若信,善莫大焉。如決不依從,亦勿強逼,以失孝道。但於佛前,代父母懺悔罪過,斯可矣。於兄弟則盡友;於夫婦則盡敬;於子女則極方教訓,使其為良為善,切勿任意嬌慣,致成匪類;於鄰里鄉黨,當和睦忍讓,為說善惡因果,使其改過遷善;於朋友則盡信;於僕使當慈愛;於公事則盡心竭力,同於私事。凡見親識,遇父言慈,遇子言孝。若做生意,當以本求利,不可以假貨哄騙於人。若以此風化其一鄉一邑,便能消禍亂於未萌,致刑罰於無用。可謂在野盡忠,居家為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