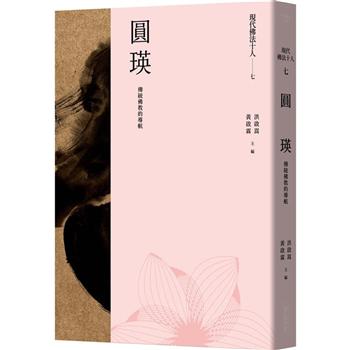獨步楞嚴承時勢──圓瑛法師
宗教兼通、保寺護教,勞苦功高傳統佛教的一代領袖
圓瑛大師生於一八七八年,福建省古田縣人。俗家姓吳,出家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
圓瑛的出生,相傳是父母求禱觀音,得夢觀音送子而來。但由於父母早逝,五歲多時就由叔父照顧,自幼聰穎,受私塾教育;年齡漸長,感身世孤零,人生如幻,十八歲時欲出家為僧,然而叔父勸阻不許。
十九歲時大病一場,於生病中發願,若獲痊癒,決志出家修行。後果然病癒,於是至福州鼓山拜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剃度出家。隔年至湧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並學習經教律儀,之後到福州大雪峰寺隨達公和尚修苦行,當飯頭菜頭。後發心行腳,廣參名宿,依常州天寧寺冶開老和尚參究禪宗心法,又至寧波天童寺依八指頭陀敬安禪師習禪定,一心參究;期間也隨道階、諦閑、祖印、慧明諸師學習天台教觀,在天童寺前後六年,因穎悟好學,使他在佛學和修持上,打下深厚的基礎。
在天童寺從敬安習禪期間,當時十八歲的太虛也到天童寺參學,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受道階器重,視為法器。圓瑛與太虛二人也在天童寺結下法緣,成為莫逆之交,並結盟為兄弟,圓瑛法師是年二十九歲。
一九〇八年,圓瑛回閩南泉州湧泉寺開座講經,因宗說兼通善巧,辯才無礙,深受與會緇素崇敬,至此聲譽逐漸傳揚於閩南、江南一帶。次年,圓瑛住持寧波接待寺,為中興古剎而除舊新建,並於寺中創設「佛教講習所」,培養弘法僧才。
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政策更新,影響佛門寺產,隔年,八指頭陀敬安法師聯合十七省僧侶代表於上海成立「中國佛教總會」以護佛寺,圓瑛法師就被選為總會參譯長。
因應廟產興學、寺廟管理條例等對佛教不利的社會氛圍,章太炎呼籲寺院自辦教育,一方面讓廟產興學無可著力,一方面也同時提升僧人素質,於是圓瑛在一九一七年當選寧波佛教會會長後,在江浙一帶講經說法,創辦兩所「僧民學校」與「寧波佛教孤兒院」,作為入學者義務教育與收容孤兒實施工讀教育,這樣的作為受到各省佛教會的傚仿。
一九一四年任中華佛教總會參議長。曾講經於福建、浙江、北京、天津和臺灣等地,遠及南洋。歷任寧波天童寺、福州雪峰寺、鼓山湧泉寺、上海圓明講堂、南洋檳城極樂寺等多寺住持。
一九二〇年,圓瑛至北京講經,正值華北五省鬧旱災,他參與發起組織佛教賑災會,災民得以安頓,得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頒贈《大藏經》一部,安置於寧波的接待禪寺。
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廟產興學政策再度被提起,官學兩界借「寺廟管理條例」政策,欲沒收寺產以充實教育經費,佛教為了自保,在圓瑛、太虛、諦閑等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等諸居士的組織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法師任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於是政府將政策修訂為「監督寺廟條例」,寺產危機方得渡過。
圓瑛主持中國佛教會的期間,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鼓勵寺院開設慈幼院、醫院、工廠等分擔社會責任。然而一九三一年「寺產興學」風波再起,圓瑛法師再度出面奔走,全國佛教團體一致支持呼應,風波才得以平息。
是年長江水災為患,數省受災,圓瑛籌募賑災款項。秋天,日本藉口入侵東三省,即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圓瑛通告全國佛教團體啟建護國道場,憂心於國事。隔年冬天,圓瑛住持之寧波天童寺大火,古剎蒙難,於是親自募捐,重建三年才完成,等住持天童寺滿六年,堅辭方丈職務。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圓瑛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於上海八一三戰事時,出入戰場運送傷兵難民,在上海圓明講堂設立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之後上海淪陷,救護隊轉到南京、漢口等繼續工作。而在救護工作經費出現問題時,又赴東南亞馬來半島募集醫藥費,亦拜會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華僑居士,組織募款機構以助抗日。
一九三九年秋天,圓瑛與弟子明陽回到上海圓明講堂,不久即遭人檢舉為抗日分子,為重慶政府在東南亞募抗日經費,因此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師徒兩人先關憲兵隊,後押送南京日軍憲兵司令部恐嚇刑訊,圓瑛不為屈服,經上海各界人士多方營救,日軍不得已才釋放他,但仍透過日本僧侶作說客,誘迫互相「合作」,亦被他拒絕。
圓瑛回上海後,仍駐錫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心撰著,共寫了《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阿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又至天津、北平、無錫、南京等地應請講經。
一九四五年春天,為補弘法人才之不足,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選取海內外青年學僧三十二人,自任院長,並親自主講《楞嚴經》,編寫講義。
一九五二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次年代表上海巿參加北京籌備中國佛教協會,在陳質如、趙樸初、周叔迦等的推選下成為第一任會長,後南返至寧波天童寺養病,未久即圓寂,享壽七十六歲。
主要著述與傳人
圓瑛博覽三藏,禪淨雙修,教觀兼通,一生弘講過許多經論,無門戶之見,主張各宗平等,性相通融。他曾說:「余生平本無門戶之見,初學禪宗,後則兼修淨土,深知禪淨同功;先學天台,後學賢首,乃知台賢一致;始學性宗,繼學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對密教,亦極信仰,固知顯教是佛所說,密教亦佛所說。」顯示他對佛法宗派的平等態度。
其中,圓瑛對《楞嚴經》的修證與講解尤其有獨到之處,被視為是近代僧眾大德中解說《楞嚴經》的第一人,其深入禪淨教觀等宗派教法,打破了一宗一派的局限。
其他主要講授的經典有:《佛說八大人覺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仁王護國經》、《佛說盂蘭盆經》、《圓覺經》、《大乘起信論》等。
圓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如《大乘起信論講義》、《首楞嚴經講義》、《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種,由門人弟子明暘法師編輯成《圓瑛法彙》印行流通於世。
其弟子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明暘法師、慈航法師、白聖長老、趙樸初居士。明暘從其剃度出家,隨侍圓瑛身邊直至其圓寂,所以圓瑛一生著述即是由明暘編輯成《圓瑛法彙》而出版。
其中慈航法師與白聖法師則來到臺灣。慈航為保護大陸來台學僧不遺餘力,安頓青年僧度過紛亂的時期。白聖在臺灣傳三壇大戒,領導整合「中國佛教會」,追根溯源,改變臺灣佛教的民間特質與日本佛教影響,紹繼漢傳佛教於臺灣。由此可見,圓瑛法脈下的四位弟子分別對大陸與臺灣佛教留下深遠影響。
護教衛國之典範
圓瑛兼通禪教,尤精《楞嚴》,被譽為「楞嚴獨步」。先後曾七度獲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並榮膺寧波天童寺、七塔寺等十大名剎方丈。晚年在上海創建圓明講堂,並辦有「楞嚴專宗學院」,培育僧材,桃李遍布海內外,在傳統派佛教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民國初年佛教改革的大風潮,諸多高僧大德都已意識到佛教非改革不可,也都努力作為。雖然因為緣起差異而有著截然不同的行事風格,卻是共同為著傳續佛法燈明而捨身護教。
圓瑛一生為教為國,盡心盡力,在行事風格上,不同於太虛在傳統經教學習外還有祇洹精舍的新式教育薰習、主張銳進改革;圓瑛為諦閑、印光等佛教界傳統派長老所器重,他代表著傳統派與改革派之間,緩和革新的中流砥柱。在一個全然創新的年代,他所扮演的角色,起了承先啟後的滑潤作用,也讓整個如高速列車奔馳的時代不會失控,在轉速與扭力上獲得平衡,得以順利開創未來的新局勢。
佛教與人生
諸位!今天講題是佛教與人生,先講佛教,然後再講人生。佛教即是佛之教法,佛是何許人,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宇宙人生真理,乃至徹底覺悟一心本源之理體。在過去二千九百六十五年時,降生於中印度迦維衛國,為皇太子,具偉大之人格,犧牲王位尊榮,發心入山修道,打破一切環境,解除人生痛苦;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佛,名為釋迦牟尼佛。
釋迦二字,釋能仁,牟尼二字,譯寂默。當佛出家時,觀見世間老病死苦,遂生感觸,欲求一解決老病死苦之方法,而為人類解除人生之痛苦。此種發心,即是孫總理所說三種仁,謂佛教為救世之仁,佛能之,故曰能仁。佛既出家之後,在雪山苦行六年,寂靜宴然,參究人生真理,安坐不動,靜極光通,因定發慧,默契無言大道,故曰寂默。又佛字覺義,覺則為佛,不覺即是眾生,不覺就是迷,佛與眾生,乃在一心迷悟之分。眾生雖迷,佛性本具,故佛成道時,說大地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猶如古鏡本具光明,祇因塵垢障蔽,不能發現;人人若肯擦磨心鏡,個個都可作佛,而釋迦是已成之佛。教者,我佛教化眾生之學說,綜四十九年,所說不出為戒定慧三種無漏學說。所謂攝心為戒,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此戒定慧三種,即是改造人生的方法。其宗旨純粹,義理淵博,能指迷啟悟,有益人生,故得成為佛教。
現在佛教講畢,接講人生。人生不出因果二字,由因果中間,含有善惡、苦樂、身心、生死八字,而因果實為人生之主要,善惡苦樂身心生死隨之轉變。人生無非依因感果,無因必不成果,譬如世間無有種子,那得結實,必先種其因,然後收其果,人生之定理,亦復如是。任從那種學說,不能推翻因果,若撥無因果,即是外道論議,世間邪說,違背正理。
按佛教以惑業為因,苦報為果,惑即迷惑,如貪瞋癡等心,業即依貪等所造之業,如殺盜淫等,此惑業二者為因,依業因必定招感苦果。試舉一例,若有一人,存貪財之迷惑心,不了愛財須當取之有道,必定依著貪財之第六意識而指揮眼根,去看那裡有財,再指揮身根,去竊取或搶劫,此即依惑造業,因也。若被人發覺,報告官府,被捕治罪,而受苦報,果也。此即人生不出因果之明證。
上約苦因苦果,而論人生,若善因善果,可以類推。更有進者,此約現世因果論,尚有隔世因果,不可不知,試問我們現前身心,即是人生果報,畢竟因從何來?若謂從父精母血,結合所成,此即不明人生之來源。要知我此身心之苦果,乃從前世惑業之苦因,所受之報,由夙生自己業緣,與父緣母緣三緣結合,而得受生,非僅父母精血而已。若是執精血所成,世間許多無子之人,豈無精血耶?以此推究自明。更復當知人生苦樂窮通壽夭得失,並非有那個可以主宰,完全由自己業因使然;「楞嚴經」云:「循業發現」是也。若明此理,對人生之境遇,可以隨緣而安,對人生行為,自能謹慎,集中一種心力,造成一種殊勝業力,招感將來殊勝之人生樂果,自是可能之事完矣。倘有疏忽之處,惟希見諒!
佛法之精神
今日承蒙諸君過愛,開會歡迎,圓瑛自愧德薄才庸,實不敢當。惟是大家有緣一堂聚會,很是一種良好機會,可作為一番佛教之討論。
夫佛教應行討論之點,不一而足,今天不妨把佛教是消極不是消極,是厭世不是厭世,這問題先來解決;這個問題解決之後,即能解釋世人種種之誤會。因世人多以佛教為消極,為厭世,不生信仰,故印度為佛教之祖國,流傳二千餘年,現在幾乎無有佛教。即東流中國,千有餘載,而今猶未普及,究其原因,不出三種:一、佛教經書義理深奧,未易領解,由難解故,人多不看,所以不知佛教之精華與佛教之利益。二、佛教徒輩不事宣傳,即有一二窮經明理之士,亦多蘊匵而藏,不行法施,所以餒人少聞佛法,聞既不聞,信仰何自而生?三、法門廣大,龍蛇混雜,凡聖交參,賢善之士,遁跡山林,韜光匿采,人多不見,不肖之流,偏在社會,出頭露角,人多輕慢,因不信僧界,併不信佛教。有此三種原因,故佛教不得昌明於世界。現因物質文明之失敗,哲學進步之趨勢,人心漸漸趨向於佛教,其間更有許多仍以佛教為消極,為厭世,而觀望不前者。圓瑛少安儒業,冠入空門,研究教典,垂三十年,深信佛教,實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是救世的,不是厭世。敢大聲疾呼,而告於我僑胞;試分三部討論:
一、就佛教本身而論:釋迦降生中印度,為淨飯王太子,因觀老病死苦,大生感觸,人生斯世,而有如是三事,無論何人,皆不能免,即發勝心,欲求一種方法解脫眾苦。如是可見最初發心即是為眾,不是為己。至十九歲出家,捨皇宮樂,棄輪王位,難捨能捨;學比丘法,修頭陀行,難行能行;著敝垢衣,行平等乞,循方乞食,難忍能忍。乃至坐菩提樹下,發廣大誓,謂:「不成佛道,不起此座。」此皆大精進,大勇猛,其中具四宏誓願:誓度無邊之眾生,誓斷無盡之煩惱,誓學無量之法門,誓成無上之佛道。此種宏願,完全是積極的,救世的,不可以其出家,遂謂為消極厭世。譬如世界學者要學一種學術,研究多年,放棄諸事,對其放棄方面觀之,近似消極,對其研究之方面觀之,正是積極,其目的,在犧牲個人,利益群眾,待學成之後,將其所學術,貢獻世界,利樂眾生;佛亦如是,豈可謂為消極厭世者乎?
二、就佛之字義而論:梵語「佛陀」,華譯「覺者」,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一切諸法,無所不知,無所不識。對宇宙人生二者論之,覺悟茫茫世間,芸芸眾生,無非業感。世界,乃眾生同業所感,共同依止,同得受用。眾生,即個人別業所感,苦樂果報,各別不同。細分之,同業之中,亦有別業,別業之中,亦有同業,一一皆由迷惑妄心所造,依惑造業,依業受報。世界之與眾生,皆屬果報,世界為依報,眾生依止,眾生為正報,正受苦樂。逆推之,果報由於業方,業力由於妄惑,妄惑不出眾生之心,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如是,則可證明世界皆是眾生業力造成,譬如世人,欲造一座房屋,亦皆由其心力,欲造幾層,便成幾層;則以小例大,心造世界,決定無疑。
試問:而今世界,是何世界?是不是人慾橫流之世界,是不是修羅爭鬥之世界,此種世界,皆由眾生貪瞋癡慢嫉妒種種惡心造成,這種惡現象,人心日積月漓,世道愈趨愈下,我愛群愛國之同胞,無一不抱救世之思想。亦有一般人,欲以鎗砲為救世具,思藉武力創造和平,此乃夢想顛倒,以殺伐因,求和平果,斷不能的。現欲救世,如炙病者,須得其穴,在愚見看來,有欲挽回世道,必定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宏揚佛教,此非圓瑛身為佛教徒,偏於佞佛也。因我佛自己覺悟,一切世界,都由心造,眾生以清淨心,造成清淨世界,以惡濁心,造成惡濁世界,故自覺之後,而行覺他,說法四十九年,說出種種法藥,救治眾生惡濁之心病。
今但舉「無我觀」之法藥,對治眾生「我執」之心病,先覺此身,乃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和合而有,離卻四大,無我可得,千萬不可認作實我,而起貪瞋癡慢嫉妒等心。世界上人,個個能修「無我觀」,能將這個「我執」打得破,則貪等諸惡濁心,自然息滅,惡濁心滅,清淨心生,不難轉惡濁世界而成清淨世界。佛欲喚醒世界眾生,共嘗法藥,祛除心病,經歷五時,循循善誘,自覺覺他,歷久不倦,豈可謂非積極者乎?
三、就佛之宗旨而論:佛以慈悲為本,慈者 ,與一切眾生之樂;悲者,拔一切眾生之苦。眾生未出輪迴,備受諸苦煎迫,如來因興無緣大悲(無緣者,無所不緣),運同體大悲,為說諸法,普令離苦得樂。而如來慈悲,視大地眾生,皆如一子,冤親平等,一視同仁,不生分別。如是看來,則如來慈悲,更有過於父母,父母慈悲,止於現世,如來度生,若眾生此世不受教,不得度,來世仍欲度之,必令離苦得樂方慰其心。又世之父母,若生多子,則心有分別,愛有厚薄,而如來則盡大地眾生,皆如一子,無不普教,不獨法施救護,倘若應以身命布施,而得救護者,亦欣然布施,而救護之,又不獨對同類之人如是,乃至異類之眾生,無不如是。
佛教有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菩薩救度眾生,常向異類中行(即變畜生等),試舉釋迦過去行菩薩道,有一世憐憫畜生,恆遭殘殺食噉之苦,有欲救護,乃變作鹿王,管五百鹿眾,彼時提婆達多(佛之堂弟)亦作鹿王,亦管五百鹿眾。一日,國王起兵圍獵,將那座大山重重圍繞,時釋迦鹿王,念眾生命頃刻,即思救護,乃語鄰群鹿王言:「汝我當為眾生,而作救護,同策喚王請願,求其解圍,自後,汝我每日輪流進貢一鹿,與王食之。」商量已訖,即詣王所,以作人言,謂:「小鹿今日為眾請願,求王解圍,王若行獵,食必不及,一二日其肉必腐,其味必變,不如不獵,小鹿願每日進貢一鹿,與王充饍,恆得食鮮,永不斷絕。」王見鹿知請願,又能作人語,心大奇之,乃許。後二群鹿,每日輪派一鹿進貢。一日,鄰郡鹿王派一母鹿進貢,而母鹿腹孕小鹿,三日可生,乃與王求請先派他鹿,待其字生,乃往進貢,王不許。而母鹿知釋迦鹿王有道,乃往求之,具訴其情。釋迦鹿王意想若派他鹿代死,心必不甘,誰願先死,若不允其請,則辜負所求,即以自身代往就死。即到王所,王問:何以自來?乃將其事一一告白於王,王聞之,大生慚愧,何以人而不如獸乎?即說偈曰:「汝是鹿頭人,我是人頭鹿,我從今日後,不食眾生肉。」遣鹿還山,王自此持齋,禁止全國,不許畋獵,由其捨一己之身命,救護無量眾生之身命,消弭無量眾生之殺業,佛教救護眾生,乃至捨頭目腦髓而不吝惜,豈可謂非積極救世者乎?
總上而論,佛教既是積極救世的,則與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係。凡抱愛群愛國思想家,皆當極方提倡,極力研究,極力宣傳,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殺機於無形,化戰器為無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個個皆存慈悲之心,則世界全無苦境,盡成樂觀,豈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圓瑛欲學佛教慈悲之道,所以前在寧波倡辦佛教孤兒院,迄今九週紀念。前歲,又同本教轉道和尚,及其師弟轉物三人,發願重興泉州開元寺,創辦開元慈兒院,教養兼施,定額一百二十名,已歷一載。自愧不能與一切人生之樂,拔一切眾生之苦,對此少數至窮苦而無告之孤兒,應盡佛子之天職,與以教養之樂,拔其飢寒之苦。此次來南洋也是代孤兒請願,籌集基金,今日迺蒙諸君開會歡迎,慚愧交併,不善言詞,統希指教!
宗教兼通、保寺護教,勞苦功高傳統佛教的一代領袖
圓瑛大師生於一八七八年,福建省古田縣人。俗家姓吳,出家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
圓瑛的出生,相傳是父母求禱觀音,得夢觀音送子而來。但由於父母早逝,五歲多時就由叔父照顧,自幼聰穎,受私塾教育;年齡漸長,感身世孤零,人生如幻,十八歲時欲出家為僧,然而叔父勸阻不許。
十九歲時大病一場,於生病中發願,若獲痊癒,決志出家修行。後果然病癒,於是至福州鼓山拜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剃度出家。隔年至湧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並學習經教律儀,之後到福州大雪峰寺隨達公和尚修苦行,當飯頭菜頭。後發心行腳,廣參名宿,依常州天寧寺冶開老和尚參究禪宗心法,又至寧波天童寺依八指頭陀敬安禪師習禪定,一心參究;期間也隨道階、諦閑、祖印、慧明諸師學習天台教觀,在天童寺前後六年,因穎悟好學,使他在佛學和修持上,打下深厚的基礎。
在天童寺從敬安習禪期間,當時十八歲的太虛也到天童寺參學,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受道階器重,視為法器。圓瑛與太虛二人也在天童寺結下法緣,成為莫逆之交,並結盟為兄弟,圓瑛法師是年二十九歲。
一九〇八年,圓瑛回閩南泉州湧泉寺開座講經,因宗說兼通善巧,辯才無礙,深受與會緇素崇敬,至此聲譽逐漸傳揚於閩南、江南一帶。次年,圓瑛住持寧波接待寺,為中興古剎而除舊新建,並於寺中創設「佛教講習所」,培養弘法僧才。
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政策更新,影響佛門寺產,隔年,八指頭陀敬安法師聯合十七省僧侶代表於上海成立「中國佛教總會」以護佛寺,圓瑛法師就被選為總會參譯長。
因應廟產興學、寺廟管理條例等對佛教不利的社會氛圍,章太炎呼籲寺院自辦教育,一方面讓廟產興學無可著力,一方面也同時提升僧人素質,於是圓瑛在一九一七年當選寧波佛教會會長後,在江浙一帶講經說法,創辦兩所「僧民學校」與「寧波佛教孤兒院」,作為入學者義務教育與收容孤兒實施工讀教育,這樣的作為受到各省佛教會的傚仿。
一九一四年任中華佛教總會參議長。曾講經於福建、浙江、北京、天津和臺灣等地,遠及南洋。歷任寧波天童寺、福州雪峰寺、鼓山湧泉寺、上海圓明講堂、南洋檳城極樂寺等多寺住持。
一九二〇年,圓瑛至北京講經,正值華北五省鬧旱災,他參與發起組織佛教賑災會,災民得以安頓,得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頒贈《大藏經》一部,安置於寧波的接待禪寺。
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廟產興學政策再度被提起,官學兩界借「寺廟管理條例」政策,欲沒收寺產以充實教育經費,佛教為了自保,在圓瑛、太虛、諦閑等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等諸居士的組織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法師任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於是政府將政策修訂為「監督寺廟條例」,寺產危機方得渡過。
圓瑛主持中國佛教會的期間,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鼓勵寺院開設慈幼院、醫院、工廠等分擔社會責任。然而一九三一年「寺產興學」風波再起,圓瑛法師再度出面奔走,全國佛教團體一致支持呼應,風波才得以平息。
是年長江水災為患,數省受災,圓瑛籌募賑災款項。秋天,日本藉口入侵東三省,即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圓瑛通告全國佛教團體啟建護國道場,憂心於國事。隔年冬天,圓瑛住持之寧波天童寺大火,古剎蒙難,於是親自募捐,重建三年才完成,等住持天童寺滿六年,堅辭方丈職務。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圓瑛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於上海八一三戰事時,出入戰場運送傷兵難民,在上海圓明講堂設立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之後上海淪陷,救護隊轉到南京、漢口等繼續工作。而在救護工作經費出現問題時,又赴東南亞馬來半島募集醫藥費,亦拜會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華僑居士,組織募款機構以助抗日。
一九三九年秋天,圓瑛與弟子明陽回到上海圓明講堂,不久即遭人檢舉為抗日分子,為重慶政府在東南亞募抗日經費,因此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師徒兩人先關憲兵隊,後押送南京日軍憲兵司令部恐嚇刑訊,圓瑛不為屈服,經上海各界人士多方營救,日軍不得已才釋放他,但仍透過日本僧侶作說客,誘迫互相「合作」,亦被他拒絕。
圓瑛回上海後,仍駐錫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心撰著,共寫了《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阿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又至天津、北平、無錫、南京等地應請講經。
一九四五年春天,為補弘法人才之不足,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選取海內外青年學僧三十二人,自任院長,並親自主講《楞嚴經》,編寫講義。
一九五二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次年代表上海巿參加北京籌備中國佛教協會,在陳質如、趙樸初、周叔迦等的推選下成為第一任會長,後南返至寧波天童寺養病,未久即圓寂,享壽七十六歲。
主要著述與傳人
圓瑛博覽三藏,禪淨雙修,教觀兼通,一生弘講過許多經論,無門戶之見,主張各宗平等,性相通融。他曾說:「余生平本無門戶之見,初學禪宗,後則兼修淨土,深知禪淨同功;先學天台,後學賢首,乃知台賢一致;始學性宗,繼學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對密教,亦極信仰,固知顯教是佛所說,密教亦佛所說。」顯示他對佛法宗派的平等態度。
其中,圓瑛對《楞嚴經》的修證與講解尤其有獨到之處,被視為是近代僧眾大德中解說《楞嚴經》的第一人,其深入禪淨教觀等宗派教法,打破了一宗一派的局限。
其他主要講授的經典有:《佛說八大人覺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仁王護國經》、《佛說盂蘭盆經》、《圓覺經》、《大乘起信論》等。
圓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如《大乘起信論講義》、《首楞嚴經講義》、《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種,由門人弟子明暘法師編輯成《圓瑛法彙》印行流通於世。
其弟子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明暘法師、慈航法師、白聖長老、趙樸初居士。明暘從其剃度出家,隨侍圓瑛身邊直至其圓寂,所以圓瑛一生著述即是由明暘編輯成《圓瑛法彙》而出版。
其中慈航法師與白聖法師則來到臺灣。慈航為保護大陸來台學僧不遺餘力,安頓青年僧度過紛亂的時期。白聖在臺灣傳三壇大戒,領導整合「中國佛教會」,追根溯源,改變臺灣佛教的民間特質與日本佛教影響,紹繼漢傳佛教於臺灣。由此可見,圓瑛法脈下的四位弟子分別對大陸與臺灣佛教留下深遠影響。
護教衛國之典範
圓瑛兼通禪教,尤精《楞嚴》,被譽為「楞嚴獨步」。先後曾七度獲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並榮膺寧波天童寺、七塔寺等十大名剎方丈。晚年在上海創建圓明講堂,並辦有「楞嚴專宗學院」,培育僧材,桃李遍布海內外,在傳統派佛教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民國初年佛教改革的大風潮,諸多高僧大德都已意識到佛教非改革不可,也都努力作為。雖然因為緣起差異而有著截然不同的行事風格,卻是共同為著傳續佛法燈明而捨身護教。
圓瑛一生為教為國,盡心盡力,在行事風格上,不同於太虛在傳統經教學習外還有祇洹精舍的新式教育薰習、主張銳進改革;圓瑛為諦閑、印光等佛教界傳統派長老所器重,他代表著傳統派與改革派之間,緩和革新的中流砥柱。在一個全然創新的年代,他所扮演的角色,起了承先啟後的滑潤作用,也讓整個如高速列車奔馳的時代不會失控,在轉速與扭力上獲得平衡,得以順利開創未來的新局勢。
佛教與人生
諸位!今天講題是佛教與人生,先講佛教,然後再講人生。佛教即是佛之教法,佛是何許人,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宇宙人生真理,乃至徹底覺悟一心本源之理體。在過去二千九百六十五年時,降生於中印度迦維衛國,為皇太子,具偉大之人格,犧牲王位尊榮,發心入山修道,打破一切環境,解除人生痛苦;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佛,名為釋迦牟尼佛。
釋迦二字,釋能仁,牟尼二字,譯寂默。當佛出家時,觀見世間老病死苦,遂生感觸,欲求一解決老病死苦之方法,而為人類解除人生之痛苦。此種發心,即是孫總理所說三種仁,謂佛教為救世之仁,佛能之,故曰能仁。佛既出家之後,在雪山苦行六年,寂靜宴然,參究人生真理,安坐不動,靜極光通,因定發慧,默契無言大道,故曰寂默。又佛字覺義,覺則為佛,不覺即是眾生,不覺就是迷,佛與眾生,乃在一心迷悟之分。眾生雖迷,佛性本具,故佛成道時,說大地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猶如古鏡本具光明,祇因塵垢障蔽,不能發現;人人若肯擦磨心鏡,個個都可作佛,而釋迦是已成之佛。教者,我佛教化眾生之學說,綜四十九年,所說不出為戒定慧三種無漏學說。所謂攝心為戒,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此戒定慧三種,即是改造人生的方法。其宗旨純粹,義理淵博,能指迷啟悟,有益人生,故得成為佛教。
現在佛教講畢,接講人生。人生不出因果二字,由因果中間,含有善惡、苦樂、身心、生死八字,而因果實為人生之主要,善惡苦樂身心生死隨之轉變。人生無非依因感果,無因必不成果,譬如世間無有種子,那得結實,必先種其因,然後收其果,人生之定理,亦復如是。任從那種學說,不能推翻因果,若撥無因果,即是外道論議,世間邪說,違背正理。
按佛教以惑業為因,苦報為果,惑即迷惑,如貪瞋癡等心,業即依貪等所造之業,如殺盜淫等,此惑業二者為因,依業因必定招感苦果。試舉一例,若有一人,存貪財之迷惑心,不了愛財須當取之有道,必定依著貪財之第六意識而指揮眼根,去看那裡有財,再指揮身根,去竊取或搶劫,此即依惑造業,因也。若被人發覺,報告官府,被捕治罪,而受苦報,果也。此即人生不出因果之明證。
上約苦因苦果,而論人生,若善因善果,可以類推。更有進者,此約現世因果論,尚有隔世因果,不可不知,試問我們現前身心,即是人生果報,畢竟因從何來?若謂從父精母血,結合所成,此即不明人生之來源。要知我此身心之苦果,乃從前世惑業之苦因,所受之報,由夙生自己業緣,與父緣母緣三緣結合,而得受生,非僅父母精血而已。若是執精血所成,世間許多無子之人,豈無精血耶?以此推究自明。更復當知人生苦樂窮通壽夭得失,並非有那個可以主宰,完全由自己業因使然;「楞嚴經」云:「循業發現」是也。若明此理,對人生之境遇,可以隨緣而安,對人生行為,自能謹慎,集中一種心力,造成一種殊勝業力,招感將來殊勝之人生樂果,自是可能之事完矣。倘有疏忽之處,惟希見諒!
佛法之精神
今日承蒙諸君過愛,開會歡迎,圓瑛自愧德薄才庸,實不敢當。惟是大家有緣一堂聚會,很是一種良好機會,可作為一番佛教之討論。
夫佛教應行討論之點,不一而足,今天不妨把佛教是消極不是消極,是厭世不是厭世,這問題先來解決;這個問題解決之後,即能解釋世人種種之誤會。因世人多以佛教為消極,為厭世,不生信仰,故印度為佛教之祖國,流傳二千餘年,現在幾乎無有佛教。即東流中國,千有餘載,而今猶未普及,究其原因,不出三種:一、佛教經書義理深奧,未易領解,由難解故,人多不看,所以不知佛教之精華與佛教之利益。二、佛教徒輩不事宣傳,即有一二窮經明理之士,亦多蘊匵而藏,不行法施,所以餒人少聞佛法,聞既不聞,信仰何自而生?三、法門廣大,龍蛇混雜,凡聖交參,賢善之士,遁跡山林,韜光匿采,人多不見,不肖之流,偏在社會,出頭露角,人多輕慢,因不信僧界,併不信佛教。有此三種原因,故佛教不得昌明於世界。現因物質文明之失敗,哲學進步之趨勢,人心漸漸趨向於佛教,其間更有許多仍以佛教為消極,為厭世,而觀望不前者。圓瑛少安儒業,冠入空門,研究教典,垂三十年,深信佛教,實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是救世的,不是厭世。敢大聲疾呼,而告於我僑胞;試分三部討論:
一、就佛教本身而論:釋迦降生中印度,為淨飯王太子,因觀老病死苦,大生感觸,人生斯世,而有如是三事,無論何人,皆不能免,即發勝心,欲求一種方法解脫眾苦。如是可見最初發心即是為眾,不是為己。至十九歲出家,捨皇宮樂,棄輪王位,難捨能捨;學比丘法,修頭陀行,難行能行;著敝垢衣,行平等乞,循方乞食,難忍能忍。乃至坐菩提樹下,發廣大誓,謂:「不成佛道,不起此座。」此皆大精進,大勇猛,其中具四宏誓願:誓度無邊之眾生,誓斷無盡之煩惱,誓學無量之法門,誓成無上之佛道。此種宏願,完全是積極的,救世的,不可以其出家,遂謂為消極厭世。譬如世界學者要學一種學術,研究多年,放棄諸事,對其放棄方面觀之,近似消極,對其研究之方面觀之,正是積極,其目的,在犧牲個人,利益群眾,待學成之後,將其所學術,貢獻世界,利樂眾生;佛亦如是,豈可謂為消極厭世者乎?
二、就佛之字義而論:梵語「佛陀」,華譯「覺者」,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一切諸法,無所不知,無所不識。對宇宙人生二者論之,覺悟茫茫世間,芸芸眾生,無非業感。世界,乃眾生同業所感,共同依止,同得受用。眾生,即個人別業所感,苦樂果報,各別不同。細分之,同業之中,亦有別業,別業之中,亦有同業,一一皆由迷惑妄心所造,依惑造業,依業受報。世界之與眾生,皆屬果報,世界為依報,眾生依止,眾生為正報,正受苦樂。逆推之,果報由於業方,業力由於妄惑,妄惑不出眾生之心,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如是,則可證明世界皆是眾生業力造成,譬如世人,欲造一座房屋,亦皆由其心力,欲造幾層,便成幾層;則以小例大,心造世界,決定無疑。
試問:而今世界,是何世界?是不是人慾橫流之世界,是不是修羅爭鬥之世界,此種世界,皆由眾生貪瞋癡慢嫉妒種種惡心造成,這種惡現象,人心日積月漓,世道愈趨愈下,我愛群愛國之同胞,無一不抱救世之思想。亦有一般人,欲以鎗砲為救世具,思藉武力創造和平,此乃夢想顛倒,以殺伐因,求和平果,斷不能的。現欲救世,如炙病者,須得其穴,在愚見看來,有欲挽回世道,必定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宏揚佛教,此非圓瑛身為佛教徒,偏於佞佛也。因我佛自己覺悟,一切世界,都由心造,眾生以清淨心,造成清淨世界,以惡濁心,造成惡濁世界,故自覺之後,而行覺他,說法四十九年,說出種種法藥,救治眾生惡濁之心病。
今但舉「無我觀」之法藥,對治眾生「我執」之心病,先覺此身,乃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和合而有,離卻四大,無我可得,千萬不可認作實我,而起貪瞋癡慢嫉妒等心。世界上人,個個能修「無我觀」,能將這個「我執」打得破,則貪等諸惡濁心,自然息滅,惡濁心滅,清淨心生,不難轉惡濁世界而成清淨世界。佛欲喚醒世界眾生,共嘗法藥,祛除心病,經歷五時,循循善誘,自覺覺他,歷久不倦,豈可謂非積極者乎?
三、就佛之宗旨而論:佛以慈悲為本,慈者 ,與一切眾生之樂;悲者,拔一切眾生之苦。眾生未出輪迴,備受諸苦煎迫,如來因興無緣大悲(無緣者,無所不緣),運同體大悲,為說諸法,普令離苦得樂。而如來慈悲,視大地眾生,皆如一子,冤親平等,一視同仁,不生分別。如是看來,則如來慈悲,更有過於父母,父母慈悲,止於現世,如來度生,若眾生此世不受教,不得度,來世仍欲度之,必令離苦得樂方慰其心。又世之父母,若生多子,則心有分別,愛有厚薄,而如來則盡大地眾生,皆如一子,無不普教,不獨法施救護,倘若應以身命布施,而得救護者,亦欣然布施,而救護之,又不獨對同類之人如是,乃至異類之眾生,無不如是。
佛教有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菩薩救度眾生,常向異類中行(即變畜生等),試舉釋迦過去行菩薩道,有一世憐憫畜生,恆遭殘殺食噉之苦,有欲救護,乃變作鹿王,管五百鹿眾,彼時提婆達多(佛之堂弟)亦作鹿王,亦管五百鹿眾。一日,國王起兵圍獵,將那座大山重重圍繞,時釋迦鹿王,念眾生命頃刻,即思救護,乃語鄰群鹿王言:「汝我當為眾生,而作救護,同策喚王請願,求其解圍,自後,汝我每日輪流進貢一鹿,與王食之。」商量已訖,即詣王所,以作人言,謂:「小鹿今日為眾請願,求王解圍,王若行獵,食必不及,一二日其肉必腐,其味必變,不如不獵,小鹿願每日進貢一鹿,與王充饍,恆得食鮮,永不斷絕。」王見鹿知請願,又能作人語,心大奇之,乃許。後二群鹿,每日輪派一鹿進貢。一日,鄰郡鹿王派一母鹿進貢,而母鹿腹孕小鹿,三日可生,乃與王求請先派他鹿,待其字生,乃往進貢,王不許。而母鹿知釋迦鹿王有道,乃往求之,具訴其情。釋迦鹿王意想若派他鹿代死,心必不甘,誰願先死,若不允其請,則辜負所求,即以自身代往就死。即到王所,王問:何以自來?乃將其事一一告白於王,王聞之,大生慚愧,何以人而不如獸乎?即說偈曰:「汝是鹿頭人,我是人頭鹿,我從今日後,不食眾生肉。」遣鹿還山,王自此持齋,禁止全國,不許畋獵,由其捨一己之身命,救護無量眾生之身命,消弭無量眾生之殺業,佛教救護眾生,乃至捨頭目腦髓而不吝惜,豈可謂非積極救世者乎?
總上而論,佛教既是積極救世的,則與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係。凡抱愛群愛國思想家,皆當極方提倡,極力研究,極力宣傳,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殺機於無形,化戰器為無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個個皆存慈悲之心,則世界全無苦境,盡成樂觀,豈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圓瑛欲學佛教慈悲之道,所以前在寧波倡辦佛教孤兒院,迄今九週紀念。前歲,又同本教轉道和尚,及其師弟轉物三人,發願重興泉州開元寺,創辦開元慈兒院,教養兼施,定額一百二十名,已歷一載。自愧不能與一切人生之樂,拔一切眾生之苦,對此少數至窮苦而無告之孤兒,應盡佛子之天職,與以教養之樂,拔其飢寒之苦。此次來南洋也是代孤兒請願,籌集基金,今日迺蒙諸君開會歡迎,慚愧交併,不善言詞,統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