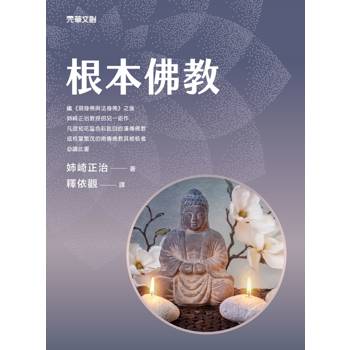【第一篇 總論】
Mahāparinibbāna-s. l. 34.
Ye taranti aṇṇavaṃ saraṃ setuṃ katvāna visajja pallalāni, kullaṃ jano ca bandhati, tiṇṇā medhāvino janā ’ti.
長阿含.遊行經
佛為海船師,法橋渡河津;大乘道之輿,一切渡天人。
亦為自解結,渡岸得昇仙;都使諸弟子,縛解得涅槃。
佛教的地位
佛教是宗教,雖為構築其宗教信行而包容及發表各種哲學思辨、理論概念,然此等思辨及概念實是其宗教信行之附屬,此具有生命力的宗教遂被視為是理論性的。亦即古印度婆羅門階層崛起之所以,是因彼等能透過奧義書(Upaniṣad)哲學精鍊其知識,才能擅長理論及冥想,所以佛教的歷代祖師,於信行的實行之外,為扶植出佛教的一流勢力,也不得不同樣重視思想的組織與鍛鍊。此種情況,如同起始以實行為其特徵的基督教,於其興起之後,亦不得不納入哲學性的考察而與靈知派的思辨等希臘思想有所接觸,故於組織其宗教之外,也同樣具有哲學的架構。
若純粹就哲學的理論論之,佛教所述未必優於婆羅門,其大致的宇宙觀不出於奧義書所述。但若論及作為宗教,其風靡人心的勢力,或社會人文受其感化所影響之力,可以說佛教實較印度任何宗教優秀。婆羅門教其哲學思想雖然深遠,但實際的感化,只侷限在擁有四姓制度與吠陀祭祀的印度國境內。反之,佛教的感化及於四方,在各種方面皆有自由的發展,據此看來,其宗教的感化實具有宏大遍通的根本原動力。
受此現實有限的生命所制的人心,希望觸及無限超越的生命,且意圖於現實中求之,宗教的產生在於此。故就理想而言,任何宗教皆具有無制限的勢力,但受限於現實,人心並不容易掙脫其束縛。如此的束縛或作為天然物質之力而糾纏人生;或作為家族種族制度而制裁人生。而人心則希冀有一超越此等制限的某物存在,故宗教或呈現為崇拜自然或與社會制度相串聯,意圖於其中訂定其神聖的終局目的。
例如儒教特將天體運行或四季循環視為天道啟示,此外,又於其家族主義的社會道德中,追求人道之理想,指出天人兩道合一。猶太教則將一切萬物視為皆隸屬於一創造及主宰之神,而此主宰神又是特為寵愛自己民族之神,由此發展出視其民族所傳法律為唯一神聖神法的宗教。而印度人亦不遑多讓,將太陽風雲等一切自然力雄大的呈現都視為神,進而將以祭祀諸神的司祭為中心的社會制度以及古來的道德視為宗教要件。
此等天然崇拜與社會的宗教,皆是應其國、其時及人心所需,出自社會發展所要求,其勢力之感化當然與宗教的職分相應。
雖然如此,但偏倚於外物勢力的宗教終究無法滿足意圖自我實現無限生命的人心。將社會制度以及古來道德視為唯一最上目標的宗教,終將只是拘泥於古來制度,不能完成其自由發展。
當人心開始內省,其自覺被喚起時,崇拜自然的宗教遂被發現有所不足,因此,轉而趨向以自己為本位的道德,同此,當發現社會制度的束縛過重,其神聖性也被懷疑時,超越此等現實規定或固定的道德,乃至心靈自由的欲求,由此產生。
約莫西元前六世紀,不約而同的,東西方的人們開始發展其心靈上的自覺。老子提出於仁義忠孝之上,更有所謂的大道。瑣羅亞斯德(Zarathustra)將自然所存的清濁之爭,提高為道德性的,又在以司祭為中心的宗教中,加入心靈的要求;猶太教的預言者以賽亞(Isaiah)等意圖超越祭祀與法律,僅以依賴神而獲得不疲之力,凡此大抵皆出現於同一時期。
而蘇格拉底意圖於自律的道德上,發揮人心之威嚴,為此,遂與在來的信仰發生衝突,觸犯社會忌諱等等,此又是西洋思想上劃時代之舉,其過世是在西元前399年。簡言之,社會本位的道德轉為以個人為本位,法律制度的宗教被心靈的甦醒摧破,東西方不約而同的,大抵都是發生於此前後的二百年之間。
而於此人心之大革命中,樹起其特別之旗幟的,實是佛陀(Buddha),晚五百年才出現的基督除外,可以說佛陀是當時世界宗教的最大明星。基於「我是一切知者,是一切勝者」之自覺,以相應其自覺的人格之力,化導眾生,意圖於人心開啟其心靈自覺之種的,即是佛陀,因其眼中不存在自然紛紛之威力,又能超越社會與神法之威權。
反之,猶太的預言者尚未完全擺脫其以民族為中心的觀念,至於老子,雖宣揚大道,然尚未親自體現之時,佛陀早已宣布其超越神法之法音,自己又作為大法之權化,亦即作為如來(Tathāgata)而教化世人。又當瑣羅亞斯德猶拘泥於祭祀行法時,佛陀早已棄捨一切祭祀。當蘇格拉底方始於人心種下知見之種,佛陀早已綻放其教法之華,且頒布其果實於人間。
至少其他諸賢尚未臻於此心靈的自覺之時,佛陀已有此自信,又具有令信者真心相信之力。相對現實的束縛,佛陀主張心靈的自由,而其人則親身體現最普遍的理想。亦即佛陀的宗教其主力在於佛陀本身,而其勢力則及於心靈的自由之境。
佛陀的宗教是應人類心靈要求,相對於以司祭為中心的社會宗教而興起的。就其興隆之跡看來,恰似一種社會改革,亦即無視於四姓制度而傳達其平等的福音,但如此的社會福音是心靈宗教的結果,並不是其感化力之根本或出發點。其原動力在於佛陀的心靈自覺,其興隆出自佛陀人格的勢力。大抵而言,人格的勢力是活生生的事實,理論概念只是次要事項。為此,佛陀為宣揚其心靈自覺的內容,直接勸誡的採用較多於理論證明。
佛陀說法時,雖也採用分析性的解釋,然其目的不在於宣明其哲理,而是為給予對方對於修行具有必要的領解。作為佛教的根本,且其信念及世界觀可說最為簡明的苦集滅道四諦,其性質與其說是經由考察思辨所得,不如說是依其直接經驗而體得的直觀。又佛陀宣說此四諦的目的並非只是為令吾等觀察世相,更是為資助吾等道行。
世界是苦之說,並不是考察之結果,而是吾等可直接的經驗。求其苦因,所提出的集諦,並不是為知識而探其原因,而是為滅其原因而除苦。至於其理想之滅,也不是以言說揭示,而是以令吾等依內觀而證悟為主。相信佛陀的人尊仰佛陀為師主,既以佛陀為師主,又如其人依內觀思惟而得最深之法,隨順其教示,與信行相應,自己亦能獲得其所得證悟。
其修行目的,消極而言,雖是解脫生死,然此解脫生死在於開發己心永遠的光明。此信行之保證完全在於佛陀的人格,如同佛陀脫離迷情,成為正覺之如來,我等亦應以正覺作為理想,而最後可到達的信仰則是佛道修行的原動力。
佛陀以三世諸佛同一成道作為眾生成佛的保證,直至後世,佛教徒仍然相信「佛本是凡夫,我等終將成佛」,其因在此。而實行此信仰理想的方法,是依循師主教示守戒、修定及開啟智慧。不只是佛教徒修持佛陀所揭示的戒定慧,佛陀自己亦依修此可到達正覺的同一乘之戒定慧。
此一理想、此一保證、此一方法皆以佛陀的人格為中心。就一切信仰皆集中於師主的人格,以師主為歸依而言,可以說佛教完全是信賴的宗教。一聲「隨我來」而歸依正覺佛陀的直傳弟子的述懷,所呈現的佛陀化導事蹟,以及上座弟子的述懷之所呈現,乃至後世佛教雖分成多種門派,但仍可看出其中心點皆出自對於佛陀的信仰,以及以與此有關的考察為主要。
雖然如此,若就內容而言,佛教可說是心靈自覺之宗教。佛教徒並不只是崇拜佛陀而已,而是以開發己心的佛性為其理想。就此而言,戒定慧正是到達此一目的的方法,而作為師主的佛陀亦非其信賴之究竟目的,而是其信行之導師或修道之橋梁。「佛是船師,自度至彼岸,又度人至彼岸。佛是法橋,是渡河津之大道」。
因此,佛陀於其入滅之前,告誡弟子:師主入滅之後,勿嗟嘆師主已不存,應各自為己之燈明,應自歸依,應精進不退。亦即佛教是信賴的宗教,同時又是自律之宗教,其行是聖道之修行。後世佛教所產生的他力信仰,是從信賴的方面發展所成,但佛教實以聖道修行,亦即以自心成佛為其本義。
此恰如同基督教。基督作為天父之子而來此世間,而其宗教是主張我等亦應如天父之完美無缺,一如基督是神子,我等亦為神子。然隨著歲月推移,其教徒於信基督之餘,加上恐懼神罰之情,基督遂被視為是神罰的代替者而受崇拜。此係基於人格的信仰所致,是應其要求而產生,然此並非出自基督意願。如同說為例外可以證明規則,此二種宗教於後世雖開發出他力信仰,但也足以得知其教主的人格勢力是何等宏大。
要言之,佛陀的宗教淵源自佛陀本身,是以其人之信仰證悟作為生命。佛教的感化是以佛陀為其出發點,以涅槃的理想為其所規。雖然如此,但對於今日意圖研究佛教者而言,並無法直接觸及佛陀本人,吾等所知的,只是其感化事跡、其所宣示的教法乃至其教法發展等事後現象。亦即吾等的研究既然是仰賴於材料,首先則必須從佛陀所悟得之法探究,進而於其法之中探索其人。此恰如光線本體雖有波動,然其研究須從於光之強弱、色之種類開始而溯及本體,亦即須以佛陀教法的內容為發端而活化其教法,進而溯及作為其感化之中心的人格。
Mahāparinibbāna-s. l. 34.
Ye taranti aṇṇavaṃ saraṃ setuṃ katvāna visajja pallalāni, kullaṃ jano ca bandhati, tiṇṇā medhāvino janā ’ti.
長阿含.遊行經
佛為海船師,法橋渡河津;大乘道之輿,一切渡天人。
亦為自解結,渡岸得昇仙;都使諸弟子,縛解得涅槃。
佛教的地位
佛教是宗教,雖為構築其宗教信行而包容及發表各種哲學思辨、理論概念,然此等思辨及概念實是其宗教信行之附屬,此具有生命力的宗教遂被視為是理論性的。亦即古印度婆羅門階層崛起之所以,是因彼等能透過奧義書(Upaniṣad)哲學精鍊其知識,才能擅長理論及冥想,所以佛教的歷代祖師,於信行的實行之外,為扶植出佛教的一流勢力,也不得不同樣重視思想的組織與鍛鍊。此種情況,如同起始以實行為其特徵的基督教,於其興起之後,亦不得不納入哲學性的考察而與靈知派的思辨等希臘思想有所接觸,故於組織其宗教之外,也同樣具有哲學的架構。
若純粹就哲學的理論論之,佛教所述未必優於婆羅門,其大致的宇宙觀不出於奧義書所述。但若論及作為宗教,其風靡人心的勢力,或社會人文受其感化所影響之力,可以說佛教實較印度任何宗教優秀。婆羅門教其哲學思想雖然深遠,但實際的感化,只侷限在擁有四姓制度與吠陀祭祀的印度國境內。反之,佛教的感化及於四方,在各種方面皆有自由的發展,據此看來,其宗教的感化實具有宏大遍通的根本原動力。
受此現實有限的生命所制的人心,希望觸及無限超越的生命,且意圖於現實中求之,宗教的產生在於此。故就理想而言,任何宗教皆具有無制限的勢力,但受限於現實,人心並不容易掙脫其束縛。如此的束縛或作為天然物質之力而糾纏人生;或作為家族種族制度而制裁人生。而人心則希冀有一超越此等制限的某物存在,故宗教或呈現為崇拜自然或與社會制度相串聯,意圖於其中訂定其神聖的終局目的。
例如儒教特將天體運行或四季循環視為天道啟示,此外,又於其家族主義的社會道德中,追求人道之理想,指出天人兩道合一。猶太教則將一切萬物視為皆隸屬於一創造及主宰之神,而此主宰神又是特為寵愛自己民族之神,由此發展出視其民族所傳法律為唯一神聖神法的宗教。而印度人亦不遑多讓,將太陽風雲等一切自然力雄大的呈現都視為神,進而將以祭祀諸神的司祭為中心的社會制度以及古來的道德視為宗教要件。
此等天然崇拜與社會的宗教,皆是應其國、其時及人心所需,出自社會發展所要求,其勢力之感化當然與宗教的職分相應。
雖然如此,但偏倚於外物勢力的宗教終究無法滿足意圖自我實現無限生命的人心。將社會制度以及古來道德視為唯一最上目標的宗教,終將只是拘泥於古來制度,不能完成其自由發展。
當人心開始內省,其自覺被喚起時,崇拜自然的宗教遂被發現有所不足,因此,轉而趨向以自己為本位的道德,同此,當發現社會制度的束縛過重,其神聖性也被懷疑時,超越此等現實規定或固定的道德,乃至心靈自由的欲求,由此產生。
約莫西元前六世紀,不約而同的,東西方的人們開始發展其心靈上的自覺。老子提出於仁義忠孝之上,更有所謂的大道。瑣羅亞斯德(Zarathustra)將自然所存的清濁之爭,提高為道德性的,又在以司祭為中心的宗教中,加入心靈的要求;猶太教的預言者以賽亞(Isaiah)等意圖超越祭祀與法律,僅以依賴神而獲得不疲之力,凡此大抵皆出現於同一時期。
而蘇格拉底意圖於自律的道德上,發揮人心之威嚴,為此,遂與在來的信仰發生衝突,觸犯社會忌諱等等,此又是西洋思想上劃時代之舉,其過世是在西元前399年。簡言之,社會本位的道德轉為以個人為本位,法律制度的宗教被心靈的甦醒摧破,東西方不約而同的,大抵都是發生於此前後的二百年之間。
而於此人心之大革命中,樹起其特別之旗幟的,實是佛陀(Buddha),晚五百年才出現的基督除外,可以說佛陀是當時世界宗教的最大明星。基於「我是一切知者,是一切勝者」之自覺,以相應其自覺的人格之力,化導眾生,意圖於人心開啟其心靈自覺之種的,即是佛陀,因其眼中不存在自然紛紛之威力,又能超越社會與神法之威權。
反之,猶太的預言者尚未完全擺脫其以民族為中心的觀念,至於老子,雖宣揚大道,然尚未親自體現之時,佛陀早已宣布其超越神法之法音,自己又作為大法之權化,亦即作為如來(Tathāgata)而教化世人。又當瑣羅亞斯德猶拘泥於祭祀行法時,佛陀早已棄捨一切祭祀。當蘇格拉底方始於人心種下知見之種,佛陀早已綻放其教法之華,且頒布其果實於人間。
至少其他諸賢尚未臻於此心靈的自覺之時,佛陀已有此自信,又具有令信者真心相信之力。相對現實的束縛,佛陀主張心靈的自由,而其人則親身體現最普遍的理想。亦即佛陀的宗教其主力在於佛陀本身,而其勢力則及於心靈的自由之境。
佛陀的宗教是應人類心靈要求,相對於以司祭為中心的社會宗教而興起的。就其興隆之跡看來,恰似一種社會改革,亦即無視於四姓制度而傳達其平等的福音,但如此的社會福音是心靈宗教的結果,並不是其感化力之根本或出發點。其原動力在於佛陀的心靈自覺,其興隆出自佛陀人格的勢力。大抵而言,人格的勢力是活生生的事實,理論概念只是次要事項。為此,佛陀為宣揚其心靈自覺的內容,直接勸誡的採用較多於理論證明。
佛陀說法時,雖也採用分析性的解釋,然其目的不在於宣明其哲理,而是為給予對方對於修行具有必要的領解。作為佛教的根本,且其信念及世界觀可說最為簡明的苦集滅道四諦,其性質與其說是經由考察思辨所得,不如說是依其直接經驗而體得的直觀。又佛陀宣說此四諦的目的並非只是為令吾等觀察世相,更是為資助吾等道行。
世界是苦之說,並不是考察之結果,而是吾等可直接的經驗。求其苦因,所提出的集諦,並不是為知識而探其原因,而是為滅其原因而除苦。至於其理想之滅,也不是以言說揭示,而是以令吾等依內觀而證悟為主。相信佛陀的人尊仰佛陀為師主,既以佛陀為師主,又如其人依內觀思惟而得最深之法,隨順其教示,與信行相應,自己亦能獲得其所得證悟。
其修行目的,消極而言,雖是解脫生死,然此解脫生死在於開發己心永遠的光明。此信行之保證完全在於佛陀的人格,如同佛陀脫離迷情,成為正覺之如來,我等亦應以正覺作為理想,而最後可到達的信仰則是佛道修行的原動力。
佛陀以三世諸佛同一成道作為眾生成佛的保證,直至後世,佛教徒仍然相信「佛本是凡夫,我等終將成佛」,其因在此。而實行此信仰理想的方法,是依循師主教示守戒、修定及開啟智慧。不只是佛教徒修持佛陀所揭示的戒定慧,佛陀自己亦依修此可到達正覺的同一乘之戒定慧。
此一理想、此一保證、此一方法皆以佛陀的人格為中心。就一切信仰皆集中於師主的人格,以師主為歸依而言,可以說佛教完全是信賴的宗教。一聲「隨我來」而歸依正覺佛陀的直傳弟子的述懷,所呈現的佛陀化導事蹟,以及上座弟子的述懷之所呈現,乃至後世佛教雖分成多種門派,但仍可看出其中心點皆出自對於佛陀的信仰,以及以與此有關的考察為主要。
雖然如此,若就內容而言,佛教可說是心靈自覺之宗教。佛教徒並不只是崇拜佛陀而已,而是以開發己心的佛性為其理想。就此而言,戒定慧正是到達此一目的的方法,而作為師主的佛陀亦非其信賴之究竟目的,而是其信行之導師或修道之橋梁。「佛是船師,自度至彼岸,又度人至彼岸。佛是法橋,是渡河津之大道」。
因此,佛陀於其入滅之前,告誡弟子:師主入滅之後,勿嗟嘆師主已不存,應各自為己之燈明,應自歸依,應精進不退。亦即佛教是信賴的宗教,同時又是自律之宗教,其行是聖道之修行。後世佛教所產生的他力信仰,是從信賴的方面發展所成,但佛教實以聖道修行,亦即以自心成佛為其本義。
此恰如同基督教。基督作為天父之子而來此世間,而其宗教是主張我等亦應如天父之完美無缺,一如基督是神子,我等亦為神子。然隨著歲月推移,其教徒於信基督之餘,加上恐懼神罰之情,基督遂被視為是神罰的代替者而受崇拜。此係基於人格的信仰所致,是應其要求而產生,然此並非出自基督意願。如同說為例外可以證明規則,此二種宗教於後世雖開發出他力信仰,但也足以得知其教主的人格勢力是何等宏大。
要言之,佛陀的宗教淵源自佛陀本身,是以其人之信仰證悟作為生命。佛教的感化是以佛陀為其出發點,以涅槃的理想為其所規。雖然如此,但對於今日意圖研究佛教者而言,並無法直接觸及佛陀本人,吾等所知的,只是其感化事跡、其所宣示的教法乃至其教法發展等事後現象。亦即吾等的研究既然是仰賴於材料,首先則必須從佛陀所悟得之法探究,進而於其法之中探索其人。此恰如光線本體雖有波動,然其研究須從於光之強弱、色之種類開始而溯及本體,亦即須以佛陀教法的內容為發端而活化其教法,進而溯及作為其感化之中心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