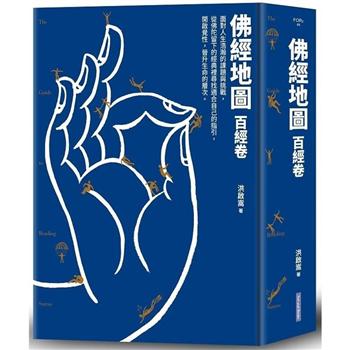佛經是用哪種語言、又由哪些人所說
早期的經、律,只用口傳並未形諸文字。佛陀開許所有的人,用各自的母語、方法傳法。如《四分律》卷第五十二載:「佛言:『聽隨國俗言音所解,誦習佛經。』」也就是說,只要不違佛意,是允許佛弟子用各自慣用的語言來誦讀、學習佛經,或是傳法的。所以《五分律》卷第二十六:「佛言:『聽隨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所謂「偷蘭遮」為巴利語thullaccaya 的音譯,在《善見律毗婆沙》卷九解釋「偷蘭遮」是大罪的意思。因此,用哪種語言說法、學習佛法都是可以的,重點是不能違背佛陀所教授的法義。
在這些佛典中,並不只包含佛的直接說法,同時還包含一些出家與在家的佛弟子、仙人、梵天與帝釋等神祇、夜叉、鬼神乃至幻化人等等所說的法。如《大智度論》卷二云:「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而這些佛陀之外天人等眾生所說的法,必須經過佛陀的印可證明,是正確的教法,如此也可以視之為佛說。
佛經是如何集結出來的
口誦佛經結集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並不曾親手將自己的教說寫成經典,當時的弟子依印度習慣也沒有用文字將教法紀錄下來,都是憑記憶與理解口耳相傳。
佛陀入滅之後,對僧團造成極大的衝擊,隨著佛陀離世,全憑個人記憶、師徒間口誦耳傳的教法,本就容易出現錯謬疏漏。因此,隨著教團的發展,確實需要對教法作有系統的分類、整理、統一。這使得僧團中的長老意識到必須將佛陀教法結集、統整,作為後世學人依止於是以摩訶迦葉為上首,召集了佛弟子中五百位開悟的大阿羅漢,進行佛陀遺教的結集,也就是佛經的結集。
結集是「合誦」或「會誦」的意思,也就是集合僧眾,誦出佛陀遺教,並加以審訂、編次的集會,又稱「集法」、「集法藏」、「結經」。佛陀滅度以後,諸弟子以集會,各誦出其所親聞之教法的方式,甄別異同,辨明邪正,以集成佛所說之法藏,如此一方面可防止遺教之散失,互補各自受學記憶校正,又可確立教權。
結集的過程,大致經過以下三個階段來審定:
誦出:由聖弟子就其記憶所及誦出教法。
共同審定:將誦出的文句,經與會大眾共同審定,以判定是否為佛陀所說,是否為合乎佛法。阿難在參與結集的過程中,曾如是對大眾說:「對我所誦出的佛陀教法,若是如法者願大眾隨喜,若不如法,應當遮除,若不相應也當遮除,千萬不要因為敬重我而不遮除,我所誦出之法,是否合乎法義,願諸位長老告知。」
編成次第:經過大眾的審定之後,再將佛陀所說的教法分成說法的「經」及戒律的「律」兩大部分,即將誦出的經與律,分為部類,編成次第,甚至結為「溫柁南」(即所謂的「偈頌」,十句經為一偈)以便記憶奉持。
歷史上佛經結集大致上有四次。
第一次結集是在佛陀入滅之後,在阿闍世王的護持之下舉行。當時五百阿羅漢會集於摩揭陀國王舍城外的七葉窟,以摩訶迦葉為上首,由多聞第一的阿難誦出經藏,持戒第一的優婆離誦出律藏。此次結集又稱「五百集法」、「五百結集」、「五百出」。《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記載有當時結集的情形。
第二次結集,是在佛滅百年時,毗舍離附近的跋耆族比丘就戒律事與耶舍長老產生異見,為此,七百比丘集會於毗舍離城,以耶舍為上首而舉行結集,就十事進行討論是否合於戒法,以維護戒法的清靜與正確性;後經代表表決認為「十事非法」不應做。此次結集稱為「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
第三次結集,相傳係於佛陀滅度之後的二三六年舉行。當時由於阿育王的護持,一千比丘會集於摩揭陀國波吒釐子城阿育僧伽藍,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然而此次結集,僅記載於南方所傳的經典。
第四次結集,相傳是在佛陀入滅後四百年舉行。在迦膩色迦王護持下,會集迦濕彌羅國之五百阿羅漢,以脇尊者、世友二人為上首,共同結集三藏,並附加解釋。當時所集論藏的解釋即現存的《大毗婆沙論》,所以又稱之為「婆沙結集」。在玄奘《大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中記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
除了第四次集結的經過有文字記載,前三次都僅是口誦耳傳。
文字經典形成
佛陀一生的教法,在佛滅度後雖然經過弟子們結集,陸續形成經、律、論三藏的型態,但仍是以口耳教授傳承,尚未形成以文字記錄的佛經型態。直到西元前後,才逐漸開始用文字記錄佛法。在毘普拉瓦佛塔遺址發現的舍利容器,由上面的銘文,可證明久遠以前即有文字。至今發現最早佛教文獻乃是以犍陀羅語書寫佛教文本。在一九九四年,大英圖書館獲得八份從一世紀到二世紀的犍陀羅語原稿。原稿以犍陀羅語佉盧文書寫在樺樹樹皮及泥陶罐上。目前陸續發現了約七十七份,分藏於大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國巴黎、俄國聖彼得堡等地。到了阿育王時代雖然曾下令以梵書體和佉盧虱底體,將法敕刻在摩崖及石柱上,但此時仍未發現有用文字記錄佛典的跡象。殊勝的佛典,仍完全由嚴謹的長老口傳弟子,這是中印度的傳統精神。
然而南方佛教,傳說在西元前一世紀,也就是錫蘭阿跋耶婆荼迦摩尼王時,已開始用巴利語(受摩揭陀語影響)記錄佛典,這是南方上座部教團用巴利語記錄三藏的起源。北方的佛教,到第二世紀的迦膩色迦王時代,則有《大毘婆沙論》的結集。據傳,他們將此經文錄刻在紅銅片上面,並放在石函中。這雖然不是佛典紀錄的起源,但由以上各點,可以推知印度佛教到西元前後,可能是由邊境地帶的教團,開始用文字記錄佛法。
由於阿育王以後,佛教已傳遍印度全土;隨著教團的社會性發展,波斯人、希臘人等國人也皈依佛教,參加教團。尤其,西北印度的邊境地帶已成為印度佛教的一個中心,該地新製作佛像、新紀錄經典的工作,不久就越過國境,而有向國外發展的前兆與趨勢。佛陀教法從口耳相授到形成文字紀錄,可以說是佛教廣大傳布到世界各地的重要因素。
早期的經、律,只用口傳並未形諸文字。佛陀開許所有的人,用各自的母語、方法傳法。如《四分律》卷第五十二載:「佛言:『聽隨國俗言音所解,誦習佛經。』」也就是說,只要不違佛意,是允許佛弟子用各自慣用的語言來誦讀、學習佛經,或是傳法的。所以《五分律》卷第二十六:「佛言:『聽隨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所謂「偷蘭遮」為巴利語thullaccaya 的音譯,在《善見律毗婆沙》卷九解釋「偷蘭遮」是大罪的意思。因此,用哪種語言說法、學習佛法都是可以的,重點是不能違背佛陀所教授的法義。
在這些佛典中,並不只包含佛的直接說法,同時還包含一些出家與在家的佛弟子、仙人、梵天與帝釋等神祇、夜叉、鬼神乃至幻化人等等所說的法。如《大智度論》卷二云:「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而這些佛陀之外天人等眾生所說的法,必須經過佛陀的印可證明,是正確的教法,如此也可以視之為佛說。
佛經是如何集結出來的
口誦佛經結集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並不曾親手將自己的教說寫成經典,當時的弟子依印度習慣也沒有用文字將教法紀錄下來,都是憑記憶與理解口耳相傳。
佛陀入滅之後,對僧團造成極大的衝擊,隨著佛陀離世,全憑個人記憶、師徒間口誦耳傳的教法,本就容易出現錯謬疏漏。因此,隨著教團的發展,確實需要對教法作有系統的分類、整理、統一。這使得僧團中的長老意識到必須將佛陀教法結集、統整,作為後世學人依止於是以摩訶迦葉為上首,召集了佛弟子中五百位開悟的大阿羅漢,進行佛陀遺教的結集,也就是佛經的結集。
結集是「合誦」或「會誦」的意思,也就是集合僧眾,誦出佛陀遺教,並加以審訂、編次的集會,又稱「集法」、「集法藏」、「結經」。佛陀滅度以後,諸弟子以集會,各誦出其所親聞之教法的方式,甄別異同,辨明邪正,以集成佛所說之法藏,如此一方面可防止遺教之散失,互補各自受學記憶校正,又可確立教權。
結集的過程,大致經過以下三個階段來審定:
誦出:由聖弟子就其記憶所及誦出教法。
共同審定:將誦出的文句,經與會大眾共同審定,以判定是否為佛陀所說,是否為合乎佛法。阿難在參與結集的過程中,曾如是對大眾說:「對我所誦出的佛陀教法,若是如法者願大眾隨喜,若不如法,應當遮除,若不相應也當遮除,千萬不要因為敬重我而不遮除,我所誦出之法,是否合乎法義,願諸位長老告知。」
編成次第:經過大眾的審定之後,再將佛陀所說的教法分成說法的「經」及戒律的「律」兩大部分,即將誦出的經與律,分為部類,編成次第,甚至結為「溫柁南」(即所謂的「偈頌」,十句經為一偈)以便記憶奉持。
歷史上佛經結集大致上有四次。
第一次結集是在佛陀入滅之後,在阿闍世王的護持之下舉行。當時五百阿羅漢會集於摩揭陀國王舍城外的七葉窟,以摩訶迦葉為上首,由多聞第一的阿難誦出經藏,持戒第一的優婆離誦出律藏。此次結集又稱「五百集法」、「五百結集」、「五百出」。《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記載有當時結集的情形。
第二次結集,是在佛滅百年時,毗舍離附近的跋耆族比丘就戒律事與耶舍長老產生異見,為此,七百比丘集會於毗舍離城,以耶舍為上首而舉行結集,就十事進行討論是否合於戒法,以維護戒法的清靜與正確性;後經代表表決認為「十事非法」不應做。此次結集稱為「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
第三次結集,相傳係於佛陀滅度之後的二三六年舉行。當時由於阿育王的護持,一千比丘會集於摩揭陀國波吒釐子城阿育僧伽藍,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然而此次結集,僅記載於南方所傳的經典。
第四次結集,相傳是在佛陀入滅後四百年舉行。在迦膩色迦王護持下,會集迦濕彌羅國之五百阿羅漢,以脇尊者、世友二人為上首,共同結集三藏,並附加解釋。當時所集論藏的解釋即現存的《大毗婆沙論》,所以又稱之為「婆沙結集」。在玄奘《大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中記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
除了第四次集結的經過有文字記載,前三次都僅是口誦耳傳。
文字經典形成
佛陀一生的教法,在佛滅度後雖然經過弟子們結集,陸續形成經、律、論三藏的型態,但仍是以口耳教授傳承,尚未形成以文字記錄的佛經型態。直到西元前後,才逐漸開始用文字記錄佛法。在毘普拉瓦佛塔遺址發現的舍利容器,由上面的銘文,可證明久遠以前即有文字。至今發現最早佛教文獻乃是以犍陀羅語書寫佛教文本。在一九九四年,大英圖書館獲得八份從一世紀到二世紀的犍陀羅語原稿。原稿以犍陀羅語佉盧文書寫在樺樹樹皮及泥陶罐上。目前陸續發現了約七十七份,分藏於大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國巴黎、俄國聖彼得堡等地。到了阿育王時代雖然曾下令以梵書體和佉盧虱底體,將法敕刻在摩崖及石柱上,但此時仍未發現有用文字記錄佛典的跡象。殊勝的佛典,仍完全由嚴謹的長老口傳弟子,這是中印度的傳統精神。
然而南方佛教,傳說在西元前一世紀,也就是錫蘭阿跋耶婆荼迦摩尼王時,已開始用巴利語(受摩揭陀語影響)記錄佛典,這是南方上座部教團用巴利語記錄三藏的起源。北方的佛教,到第二世紀的迦膩色迦王時代,則有《大毘婆沙論》的結集。據傳,他們將此經文錄刻在紅銅片上面,並放在石函中。這雖然不是佛典紀錄的起源,但由以上各點,可以推知印度佛教到西元前後,可能是由邊境地帶的教團,開始用文字記錄佛法。
由於阿育王以後,佛教已傳遍印度全土;隨著教團的社會性發展,波斯人、希臘人等國人也皈依佛教,參加教團。尤其,西北印度的邊境地帶已成為印度佛教的一個中心,該地新製作佛像、新紀錄經典的工作,不久就越過國境,而有向國外發展的前兆與趨勢。佛陀教法從口耳相授到形成文字紀錄,可以說是佛教廣大傳布到世界各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