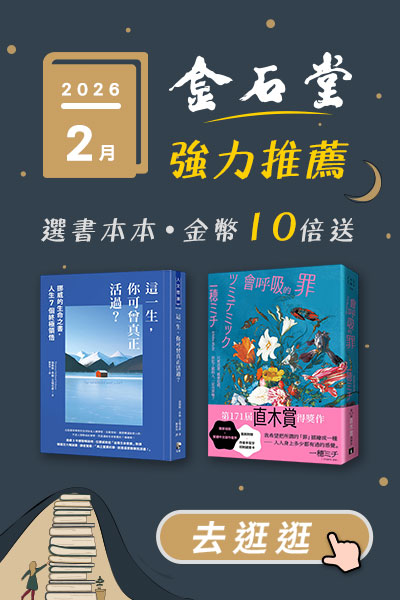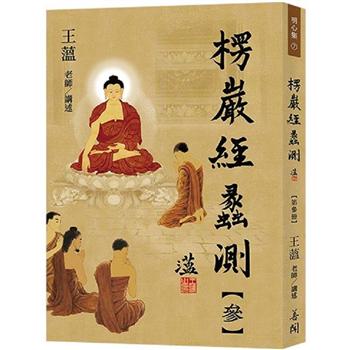由於張老居士兩代一家法眷對慈航法師的信仰,而慈航法師一生中最受影響的又屬於太虛大師的佛學思想,晚期慈航法師曾多次向張居士論及要多讀《楞嚴經》,尤其是太虛大師所曾經開示過的一切《楞嚴經》法教。張老居士由於家學的緣故,自幼熟識漢文,又曾受日本教育,其日文程度連教他的日本老師都讚嘆有加,在那個時代裡,日文幾乎成了他的母語,我也曾從他處獲得了幾本他所贈送的日本和尚所講的淨土諸經和禪宗相關的源流經典,但張老居士還是依舊稱賞不置者為《首楞嚴經》,我相信這是源自於慈航法師影響所及,慈航大師對於《楞嚴經》的一切教理也都是源自於太虛大師。
一回,我應張老居士之託,幫他帶了一套明代交光法師的《楞嚴正脈疏》,他說他原來的那一套被基隆某佛學院借走了,希望能幫他再找一套。這套《楞嚴正脈疏》幾乎是近代各大禪林都奉為首要依據之參考書籍,我也曾多次從默如老和尚和戒德上人處聽聞《正脈疏》的重要性,戒德老和尚曾說在過去常州天寧寺參禪的老參,幾乎沒有人不是從交光法師這套新註解的《楞嚴正脈疏》獲得好處。這套新註的特點是在於交光法師有別於過去唐、宋、元各代楞嚴大家所著,不依循天台,有自己宗下獨特之見解,過去《楞嚴經》諸多註解都是依照宋代的長水法師所註為主。交光大師是了不起的大和尚,雖然他精通《楞嚴》,但是他的本業仍然是以念佛為主,他在註解這套《楞嚴正脈疏》的時候,原來他的陽壽將盡,很多次都感到阿彌陀佛要來接引他,但是他認為中土的眾生對於《楞嚴經》需要有一套更完整的註解本傳世,所以他發願要把自己個人所得註解下來,於是他就向阿彌陀佛祈求,等待他把這套《楞嚴正脈疏》交代清楚之後再往生。
近代有禪學巨擘圓瑛大師者,乃清代以降,民初至今對於教證最有實入之一人,尤其是對於《楞嚴經》的用心近代少有。大師曾經自己自述過,在他年輕聽聞《楞嚴經》的時候,由於發心專研此經,但苦無太多參考之資料,當時大師對於《楞嚴經》之殷切求知的心情,就如同枯苗望雨一般,可惜在當時坊間可以參考的註釋雖多,但卻各有用詞,種類繁多,大師為此曾經於研究經文時,用心腦過度,導致心火旺盛而患了血疾,但大師卻沒有因此而有所退失,反而越遭逢挫折,越激發信解,於是就在佛前發願,希望藉由佛力的加被感悟楞嚴大義,並且也能夠迅速停止血疾,在此之後,遂有感應,有化人示現為老婦狀來告訴圓瑛法師藥方。這老婦人跟圓瑛法師說:「現在病體的狀況,可以用白杜鵑花燉冰糖服用,一定可以迅速地好轉。」當這位老婦人把藥方口述之後,圓瑛法師回過頭來尋著音聲來處張望,卻看不到任何人影,大師雖然心裡覺得訝異,但也不疑有他,之後便依老婦人所言服用了三次之後,血便停止。從這件事情之後,圓瑛法師知道有佛菩薩的加持,便更加地有信心,歷經十年苦心鑽研《楞嚴經》,幾乎是孜孜矻矻,抱經不懈,焚膏繼晷,兀兀不斷,夜以繼日,無一稍歇。在這期間大師只要稍微有看到經文中不解或稍難之處,他便把這些字句逐句抄寫下來,變成書籤模狀,一張一張地貼黏在牆壁上,不敢或忘,有時一日之中無數回的參詳,有時便閉目苦思,靜坐參究,直到了解奧義為止。只要有一條明白之後,便除卻壁中之紙一張,如此不知不覺之中,竟也經過了八年的時光,才把滿屋子的紙條撕卻,這種用心嘆未曾有,這種精神簡直是觀止之嘆,也值得後學效法。雖然如此,大師仍然小心翼翼地不敢把所言講義即刻披露傳印。法師自述在每一次的講演《楞嚴經》便有旁通之義產生,因此,更覺精進不少,甚至於想要閉關專注《楞嚴》,如此直至大師六十八歲,深覺人之身軀受四大之干擾形同風前殘燭一般,他體悟到如此的桑榆暮景,人生無常,如果不迅速地把多年來所整理累積之《楞嚴》心得傳講演示,豈不可惜?在這之後便創立了楞嚴學院,自己每天親自講經,講經之餘便編寫講義,每天都到凌晨一點,如此年邁之年加上心腦使用過度,最後在講經中突犯風症⋯⋯此後經過醫治,仍然未放棄繼續編著《楞嚴經講義》,有感於《楞嚴經講義》志業未成,便繼續編寫直到大師七十四歲那年的夏天終於圓滿,總計有二十四卷。這其中的精義展讀再三,便會覺得乃是此末世中可以依靠此講義一窺首楞嚴三眛重要之津梁所在。
我會深入地研讀圓瑛法師所著的《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也是因為禪宗家師影響所介,第一套《楞嚴經講義》也是老和尚所親贈,裡面充滿了密密麻麻的朱字批註,幾乎布滿章章頁頁,這對我研讀此講義也有莫大的指引。由於過去自己也曾經覽讀過交光法師的《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脈疏》、溥畹《大佛頂首楞嚴經寶鏡疏懸談》和長水子璿法師的《首楞嚴義疏注經》……及當代多位法師的註釋參考多年。但此後自從仔細讀獲圓瑛大師的《楞嚴經講義》之後,深覺更能融會貫通,因此,只要讀誦本文時遇有任何疑惑處,旋即便可解惑,於是我在不同的書齋處都各自備有一套《楞嚴經講義》。
「內守幽閒。猶是法塵分別影事」這句話佛在《楞嚴經》初期就提醒,為什麼?許許多多的修行人參禪者,剛開始在沒有真正了悟真心之前,都很容易會守在這個狀態中,他們也認為一念清淨,煩惱不生就是證道了,事實上,去道甚遠。許多道家和金剛乘的瑜伽士也很容易進入這個狀態,並且以為這就對了!事實上這些充其量也都只是一種分別心所產生的意識境界,所以才說是法塵,這些都不是常住真心,因為不是真心的緣故,如果有任何的生滅變化,那我們的心到那個時候就如同龜毛兔角一般。從這裡就必須了解一切萬法都是唯心所現,就如同鏡子裡面所收受的意識一樣,所以外面的色、聲、香、味、觸,它就如同鏡子裡面的形體一般,我們的心因為有分別的緣故,所以看到的都只是影像,影像的來源是因為有外境,外境的來源是因為我們的心受到了六塵的影響,這些都只能說是分別影事。所以說「內守幽閒」雖然也是一種境界,但是也不過是心的影子而已,還有所執著於識的緣故,所以根本不是本覺真心。如果修行未體悟到真心,那根本離清淨心還非常地遙遠,《楞嚴經》佛所說的妙明真心,它是確實可以證得離一切分別的境界,這個心無任何的染著,才能稱做清淨,即便有任何外境的污染,但其心也是入一切雜染而不受其染,這種境界才可以稱為妙淨。
在此處《楞嚴經》佛胸前所放射出來的佛光,它代表的意思是表示如如不動的意思,也表示寂而常照的意思,也表示十方周遍的意思,也象徵真心實相的意思,更是用此來比喻所有的眾生十法界中一切凡聖同體,本自有與生俱來的妙明真如、常住真心,只不過一時迷卻罷了!這也是佛在菩提樹下所悟得的光明本體,並且還告諸眾生所有的眾生都有佛性,只不過妄想和執著的因素而迷卻於輪迴之中,所以佛在這段裡面所要講的,所謂為了一切的眾生樹立大法幢,這大法幢在這裡所講的就是要阿難能夠了解到吾人本自俱足的寂常自心。這個心俱足體相用,這就是每個人都俱足的寂妙本心,佛所要闡釋的、讓大眾全部明瞭的就是這個大法,這就如同在我們眼前樹立了大法幢一般,這個法幢就是大法,佛所要開示的大法。這個大法也不是獨獨只有傳給阿難等與會大眾菩薩,同時佛也希望可以令十方法界眾生都可以聽聞到這個大法,獲得解脫,所以文中所講的建大法幢是這個意思。下面有一句話是這段文中最主要的密義,就是要眾生獲得「妙微密性淨明心」,雖然只有幾個字,但是意境非常地高遠。要達到妙的境界,非得要證入寂照不二的境界。那什麼又是寂照等同之境呢?先講寂,寂是指我們每個眾生本自就有的不生不滅它的本體,眾生和佛的差別便是在這裡,佛早就證得了這不生不滅的心性,但是凡夫眾生每每都是活在生滅輪迴之中。光是有寂還不行,還要能照,照的解釋也是我們需要俱足了了常知,才知道照的意思,這種境界也只有如同當日達摩給慧可印證時的境界差不多。當時慧可因為參透了達摩所傳心法,去找達摩印證,當時達摩問他的便是在於有沒有斷滅心,慧可回答達摩時所說的一句話便可以確定,慧可當時說:「了了常知。」
這時候達摩心中便很清楚地確定慧可所悟的沒有錯,因此他印證對他說:「這個是十方諸佛所傳、所證、所得之心印,你一旦獲得,從此不可再有懷疑。」
這點和金剛乘的大圓滿非常地像。上師在灌頂的時候,就用種種的色、香、觸、味,讓受灌頂者去體會,在各自不同的境界中,去尋找心在哪裡?有時候會問你,是在身體嗎?還是在心裡面?那如果是心裡面,它又是長得如何?它的顏色和大小又是如何......就這樣子一邊口傳,一邊灌頂,一邊指引,這和《楞嚴經》佛現在在指引阿難大同小異。例如在西藏傳統的大圓滿灌頂有關於指引看光的部分,這裡面打坐的方法也有一定的規矩,身體的姿態如何,這個牽扯到氣脈,心和氣如果不能配合,眼睛也無法看到任何所指示的各式各樣不同的光。比較特別的是心愈是不執著、不在意,愈鬆坦,那所看的光就會更清楚,這種指引的方法在大圓滿裡面叫做「托嘎」,「托嘎」裡邊所指示的外境,其實也都是行者自己本身心的實相。而所修的六種境界其實都是幻化境,並不是真正的實體境界,這是行者透過自己色身內的氣和脈,透過和心的實境反射出種種的光,其實這些也都是吾人的真心所變現出來的,所以這個法的名稱翻譯得特別好,叫做「本覺智慧」,這其中有種種的細節,未經過大灌頂和上師的指引是無法可以了解的。
從〈第一卷〉最先開始直至前面重點提到的〈第四卷〉之間,一路下來《楞嚴經》中所講的重點只有一個——破除妄想,顯示真心,這也是研讀《楞嚴》最重要的核心,是在於修正心裡的迷思,不要走入修行的誤區。許多人修禪都明白目的都是為了要返向自心,因此都是在專一性上多做參究,直到證悟到所謂沒有差別,沒有思量,遠離能所,無識無智,心行俱滅,自性獨標,才能說是徹底地脫出陷阱,可受鉗鎚。許許多多的修行人錯解四禪八定,神通妙用,晨禪昏淨,宴坐行香,機鋒千轉,當作修行解脫之路徑,實際上很容易偏邪空亡,成為附佛外道。事實上,如何才可以免於勞形易道,遠離無謂諍論,研習《楞嚴》便是最正確的道路,無論修禪、修淨、修密皆是匯歸要領,若要趨入真如法性,直探真心,也只有《楞嚴》。就如同佛在《楞嚴經・第一卷》阿難向佛請法,佛便很清楚地說:「所有的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為何不斷地輪流相轉於生死,並且難以出期,相續不斷,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不知道妙明真心它的重要性,都是因為充滿無量無盡的妄想執著,所以便成為六道輪迴的主要原因。」因此如果真正可以了悟到一真即是一切真,真真之中直透妙如真心,到了那種境界,自然一切現成,不假方便,每個當下皆是在禪的境界中來說,了解了這片真心,所謂的無論境界萬千,只需胸懷一片,便是如此的風光。一旦獲得妙明真心,修行無須任何次第,不增不減,無修無證,無漸無頓。
一回,我應張老居士之託,幫他帶了一套明代交光法師的《楞嚴正脈疏》,他說他原來的那一套被基隆某佛學院借走了,希望能幫他再找一套。這套《楞嚴正脈疏》幾乎是近代各大禪林都奉為首要依據之參考書籍,我也曾多次從默如老和尚和戒德上人處聽聞《正脈疏》的重要性,戒德老和尚曾說在過去常州天寧寺參禪的老參,幾乎沒有人不是從交光法師這套新註解的《楞嚴正脈疏》獲得好處。這套新註的特點是在於交光法師有別於過去唐、宋、元各代楞嚴大家所著,不依循天台,有自己宗下獨特之見解,過去《楞嚴經》諸多註解都是依照宋代的長水法師所註為主。交光大師是了不起的大和尚,雖然他精通《楞嚴》,但是他的本業仍然是以念佛為主,他在註解這套《楞嚴正脈疏》的時候,原來他的陽壽將盡,很多次都感到阿彌陀佛要來接引他,但是他認為中土的眾生對於《楞嚴經》需要有一套更完整的註解本傳世,所以他發願要把自己個人所得註解下來,於是他就向阿彌陀佛祈求,等待他把這套《楞嚴正脈疏》交代清楚之後再往生。
近代有禪學巨擘圓瑛大師者,乃清代以降,民初至今對於教證最有實入之一人,尤其是對於《楞嚴經》的用心近代少有。大師曾經自己自述過,在他年輕聽聞《楞嚴經》的時候,由於發心專研此經,但苦無太多參考之資料,當時大師對於《楞嚴經》之殷切求知的心情,就如同枯苗望雨一般,可惜在當時坊間可以參考的註釋雖多,但卻各有用詞,種類繁多,大師為此曾經於研究經文時,用心腦過度,導致心火旺盛而患了血疾,但大師卻沒有因此而有所退失,反而越遭逢挫折,越激發信解,於是就在佛前發願,希望藉由佛力的加被感悟楞嚴大義,並且也能夠迅速停止血疾,在此之後,遂有感應,有化人示現為老婦狀來告訴圓瑛法師藥方。這老婦人跟圓瑛法師說:「現在病體的狀況,可以用白杜鵑花燉冰糖服用,一定可以迅速地好轉。」當這位老婦人把藥方口述之後,圓瑛法師回過頭來尋著音聲來處張望,卻看不到任何人影,大師雖然心裡覺得訝異,但也不疑有他,之後便依老婦人所言服用了三次之後,血便停止。從這件事情之後,圓瑛法師知道有佛菩薩的加持,便更加地有信心,歷經十年苦心鑽研《楞嚴經》,幾乎是孜孜矻矻,抱經不懈,焚膏繼晷,兀兀不斷,夜以繼日,無一稍歇。在這期間大師只要稍微有看到經文中不解或稍難之處,他便把這些字句逐句抄寫下來,變成書籤模狀,一張一張地貼黏在牆壁上,不敢或忘,有時一日之中無數回的參詳,有時便閉目苦思,靜坐參究,直到了解奧義為止。只要有一條明白之後,便除卻壁中之紙一張,如此不知不覺之中,竟也經過了八年的時光,才把滿屋子的紙條撕卻,這種用心嘆未曾有,這種精神簡直是觀止之嘆,也值得後學效法。雖然如此,大師仍然小心翼翼地不敢把所言講義即刻披露傳印。法師自述在每一次的講演《楞嚴經》便有旁通之義產生,因此,更覺精進不少,甚至於想要閉關專注《楞嚴》,如此直至大師六十八歲,深覺人之身軀受四大之干擾形同風前殘燭一般,他體悟到如此的桑榆暮景,人生無常,如果不迅速地把多年來所整理累積之《楞嚴》心得傳講演示,豈不可惜?在這之後便創立了楞嚴學院,自己每天親自講經,講經之餘便編寫講義,每天都到凌晨一點,如此年邁之年加上心腦使用過度,最後在講經中突犯風症⋯⋯此後經過醫治,仍然未放棄繼續編著《楞嚴經講義》,有感於《楞嚴經講義》志業未成,便繼續編寫直到大師七十四歲那年的夏天終於圓滿,總計有二十四卷。這其中的精義展讀再三,便會覺得乃是此末世中可以依靠此講義一窺首楞嚴三眛重要之津梁所在。
我會深入地研讀圓瑛法師所著的《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也是因為禪宗家師影響所介,第一套《楞嚴經講義》也是老和尚所親贈,裡面充滿了密密麻麻的朱字批註,幾乎布滿章章頁頁,這對我研讀此講義也有莫大的指引。由於過去自己也曾經覽讀過交光法師的《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脈疏》、溥畹《大佛頂首楞嚴經寶鏡疏懸談》和長水子璿法師的《首楞嚴義疏注經》……及當代多位法師的註釋參考多年。但此後自從仔細讀獲圓瑛大師的《楞嚴經講義》之後,深覺更能融會貫通,因此,只要讀誦本文時遇有任何疑惑處,旋即便可解惑,於是我在不同的書齋處都各自備有一套《楞嚴經講義》。
「內守幽閒。猶是法塵分別影事」這句話佛在《楞嚴經》初期就提醒,為什麼?許許多多的修行人參禪者,剛開始在沒有真正了悟真心之前,都很容易會守在這個狀態中,他們也認為一念清淨,煩惱不生就是證道了,事實上,去道甚遠。許多道家和金剛乘的瑜伽士也很容易進入這個狀態,並且以為這就對了!事實上這些充其量也都只是一種分別心所產生的意識境界,所以才說是法塵,這些都不是常住真心,因為不是真心的緣故,如果有任何的生滅變化,那我們的心到那個時候就如同龜毛兔角一般。從這裡就必須了解一切萬法都是唯心所現,就如同鏡子裡面所收受的意識一樣,所以外面的色、聲、香、味、觸,它就如同鏡子裡面的形體一般,我們的心因為有分別的緣故,所以看到的都只是影像,影像的來源是因為有外境,外境的來源是因為我們的心受到了六塵的影響,這些都只能說是分別影事。所以說「內守幽閒」雖然也是一種境界,但是也不過是心的影子而已,還有所執著於識的緣故,所以根本不是本覺真心。如果修行未體悟到真心,那根本離清淨心還非常地遙遠,《楞嚴經》佛所說的妙明真心,它是確實可以證得離一切分別的境界,這個心無任何的染著,才能稱做清淨,即便有任何外境的污染,但其心也是入一切雜染而不受其染,這種境界才可以稱為妙淨。
在此處《楞嚴經》佛胸前所放射出來的佛光,它代表的意思是表示如如不動的意思,也表示寂而常照的意思,也表示十方周遍的意思,也象徵真心實相的意思,更是用此來比喻所有的眾生十法界中一切凡聖同體,本自有與生俱來的妙明真如、常住真心,只不過一時迷卻罷了!這也是佛在菩提樹下所悟得的光明本體,並且還告諸眾生所有的眾生都有佛性,只不過妄想和執著的因素而迷卻於輪迴之中,所以佛在這段裡面所要講的,所謂為了一切的眾生樹立大法幢,這大法幢在這裡所講的就是要阿難能夠了解到吾人本自俱足的寂常自心。這個心俱足體相用,這就是每個人都俱足的寂妙本心,佛所要闡釋的、讓大眾全部明瞭的就是這個大法,這就如同在我們眼前樹立了大法幢一般,這個法幢就是大法,佛所要開示的大法。這個大法也不是獨獨只有傳給阿難等與會大眾菩薩,同時佛也希望可以令十方法界眾生都可以聽聞到這個大法,獲得解脫,所以文中所講的建大法幢是這個意思。下面有一句話是這段文中最主要的密義,就是要眾生獲得「妙微密性淨明心」,雖然只有幾個字,但是意境非常地高遠。要達到妙的境界,非得要證入寂照不二的境界。那什麼又是寂照等同之境呢?先講寂,寂是指我們每個眾生本自就有的不生不滅它的本體,眾生和佛的差別便是在這裡,佛早就證得了這不生不滅的心性,但是凡夫眾生每每都是活在生滅輪迴之中。光是有寂還不行,還要能照,照的解釋也是我們需要俱足了了常知,才知道照的意思,這種境界也只有如同當日達摩給慧可印證時的境界差不多。當時慧可因為參透了達摩所傳心法,去找達摩印證,當時達摩問他的便是在於有沒有斷滅心,慧可回答達摩時所說的一句話便可以確定,慧可當時說:「了了常知。」
這時候達摩心中便很清楚地確定慧可所悟的沒有錯,因此他印證對他說:「這個是十方諸佛所傳、所證、所得之心印,你一旦獲得,從此不可再有懷疑。」
這點和金剛乘的大圓滿非常地像。上師在灌頂的時候,就用種種的色、香、觸、味,讓受灌頂者去體會,在各自不同的境界中,去尋找心在哪裡?有時候會問你,是在身體嗎?還是在心裡面?那如果是心裡面,它又是長得如何?它的顏色和大小又是如何......就這樣子一邊口傳,一邊灌頂,一邊指引,這和《楞嚴經》佛現在在指引阿難大同小異。例如在西藏傳統的大圓滿灌頂有關於指引看光的部分,這裡面打坐的方法也有一定的規矩,身體的姿態如何,這個牽扯到氣脈,心和氣如果不能配合,眼睛也無法看到任何所指示的各式各樣不同的光。比較特別的是心愈是不執著、不在意,愈鬆坦,那所看的光就會更清楚,這種指引的方法在大圓滿裡面叫做「托嘎」,「托嘎」裡邊所指示的外境,其實也都是行者自己本身心的實相。而所修的六種境界其實都是幻化境,並不是真正的實體境界,這是行者透過自己色身內的氣和脈,透過和心的實境反射出種種的光,其實這些也都是吾人的真心所變現出來的,所以這個法的名稱翻譯得特別好,叫做「本覺智慧」,這其中有種種的細節,未經過大灌頂和上師的指引是無法可以了解的。
從〈第一卷〉最先開始直至前面重點提到的〈第四卷〉之間,一路下來《楞嚴經》中所講的重點只有一個——破除妄想,顯示真心,這也是研讀《楞嚴》最重要的核心,是在於修正心裡的迷思,不要走入修行的誤區。許多人修禪都明白目的都是為了要返向自心,因此都是在專一性上多做參究,直到證悟到所謂沒有差別,沒有思量,遠離能所,無識無智,心行俱滅,自性獨標,才能說是徹底地脫出陷阱,可受鉗鎚。許許多多的修行人錯解四禪八定,神通妙用,晨禪昏淨,宴坐行香,機鋒千轉,當作修行解脫之路徑,實際上很容易偏邪空亡,成為附佛外道。事實上,如何才可以免於勞形易道,遠離無謂諍論,研習《楞嚴》便是最正確的道路,無論修禪、修淨、修密皆是匯歸要領,若要趨入真如法性,直探真心,也只有《楞嚴》。就如同佛在《楞嚴經・第一卷》阿難向佛請法,佛便很清楚地說:「所有的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為何不斷地輪流相轉於生死,並且難以出期,相續不斷,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不知道妙明真心它的重要性,都是因為充滿無量無盡的妄想執著,所以便成為六道輪迴的主要原因。」因此如果真正可以了悟到一真即是一切真,真真之中直透妙如真心,到了那種境界,自然一切現成,不假方便,每個當下皆是在禪的境界中來說,了解了這片真心,所謂的無論境界萬千,只需胸懷一片,便是如此的風光。一旦獲得妙明真心,修行無須任何次第,不增不減,無修無證,無漸無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