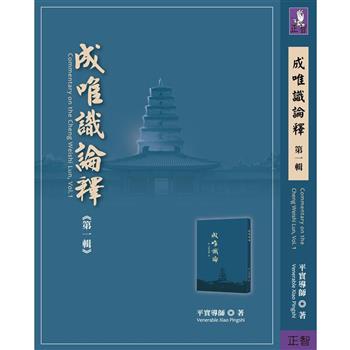第三目 緒說造論之緣由
論文:「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障俱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真解脫;由斷礙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又為開示謬執我法迷唯識者,令達二空,於唯識理如實知故。」
語譯:【如今造作這一部論典,是為了想要使對於人空與法空有迷惑而產生虛謬見解的人,可以出生正確理解的緣故;幫助他們生起正確理解,則是為了想要幫他們斷除煩惱障與所知障等二種重大障礙的緣故。由於有情同有我執與法執等二種遮障同時生起,若是能證得人空與法空等二空,他們的我執與法執等二障就會隨之斷除;而斷除這二障之目的是為了要幫他們證得解脫果與佛菩提果等二種殊勝果報的緣故。由於斷除相續而生的煩惱遮障的緣故,能斷此障而證得我空的人便可以證得真正的解脫;由於斷除對所知障內涵無知的障礙而理解所知障內涵的緣故,便能證得大菩提。又為了打開及顯示正理而使錯謬地執著有我有法的迷惑唯識性的人,教令他們通達我空與法空,對於唯識性的正理能如實了知的緣故。】
釋義:「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為斷二重障故。」「今造此論」:玄奘始從天竺投生於中國前,以曾三世為護法故而為國王,以致失去往世已有之神通與意生身故有胎昧;然於西行天竺取經之前,已經恢復往昔天竺時所證之解脫果及證真如與眼見佛性之智慧,當時已成為慧解脫及實證真如與佛性之菩薩,已有如幻觀的現量;依菩薩願不捨眾生,及為求具足而完整的成佛之道聖教得以弘傳於中國,廣利華夏學人,方始發願前往天竺而不顧禁令與安危,西行求經;返回大唐之後廣譯諸經,又造此論,成佛之道的完整內容方得弘揚於中國,成為中國至今傲視全球的文化瑰寶,譯經之後不久,禪宗之證悟明心,因有諸經之護持而得以廣弘。
對於返回中土已經通達真如的玄奘菩薩而言,是已經入地的聖者,證得多種現觀;而他對於三界愛的現行已經斷除,因此證得阿羅漢果而解脫於我執、我所執;並已斷除習氣種子隨眠,兼有深妙的無生法忍,是故玄奘造作此論時絕非為自身名聞或利養,純粹為了利他而造論。
「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玄奘造作此論所欲利益的對象,若能如實證解此論,將會有兩種利益:第一是以前對於我空與法空有迷惑以及誤解的人,可以因為如實證解此論中闡釋的唯識性、相等正義,理解先前對於我空與法空的誤解,由此而斷除我見,乃至斷除我所執與我執,證得解脫果的人我空,成為慧解脫的聖者;再者也可以由此論而如實現觀蘊處界等一切法莫非是空性心第八識——五陰自始至終都在第八識空性心中生住異滅、循環不已,本來即應攝歸第八識空性;由此現觀而深入觀察,終能現觀非安立諦等三品心而加以內遣(後述,此不預說),通達初地真如而證得法我空。
如是,一般學人本來雖於人空及法空有所迷謬,以致錯認邪說為正說的人,若能經由此論法義的如實證解而親證人我空與法我空,對二空便有正確的理解與實證,由是遠離對於二空產生迷謬之無明,永遠不墮於空有之爭中,跳脫於其外而得真如實智,發起實相般若。
二空是生空及法空;生空或名我空,是於眾生分上的五陰等法無有所知,執為真實不壞之自我時,若能現觀其為無我,名為證得生空或我空。法空,是指有人對於蘊處界,亦即是對於十二處、六入、十八界、心所……等諸法中所觀見的無數法,認定其全部或局部真實有我恆存,是常住法,名為法我;若於如是法我,能觀察其為生滅不住之有生法,並無一法之中有真實我,名為證得法空。如是二空滅除無明,即是此論所欲說明之正理。
迷與謬是二種人,如《成唯識論述記》卷一云:「一切異生諸外道等,此愚癡類,彼於二空全不解了,名為迷者;聲聞、獨覺及惡取空,邪解空理,分有智故,名為謬者。不解、邪解,合名迷謬。或但不解,無明名迷;若不正解,邪見名謬。癡、邪見人,名迷、謬者。」
「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然而對《成唯識論》的正確理解,可以使行者斷除二種重大的遮障,這二種重障是指煩惱障與所知障;若是錯解此論之人,則不能斷除絲毫。云何煩惱障與所知障名為重障?煩惱障對菩薩們的遮障,是障礙菩薩們無法證得解脫果,無法出離三界生死中的種種苦。既無法出離三界生死中的種種苦,便也同時遮障了更進一步修證佛菩提道的可能性;因為「證真如」而生起實相般若以前,必須先斷我見;若不先斷我見,永無可能「證真如」,必墮蘊處界我之中故;或是「證真如」後仍將退轉,以其我見未能先行斷除故。以是緣故說煩惱障中的我見、我所執、我執等,必致有情沈墮生死中;或是由於這二障會遮障有情證悟真如故,都屬於重障。
又煩惱障之重者,例如修證佛菩提道的第一大阿僧祇劫最末位的十迴向位,轉入初地之前必須斷除分段生死——斷盡三界愛的現行而證阿羅漢果;隨後轉入第二大阿僧祇劫的地後修道過程中,還必須斷除煩惱障所攝的三界愛習氣種子隨眠,才能進入八地起的第三大阿僧祇劫修行過程。以如是煩惱障極難斷除而致諸大阿羅漢之習氣種子隨眠尚難除盡故,說此煩惱障為重障。
所知障更屬重障,以其深奧微細而難破,若不證第八識真如即無法打破所知障;此是一切不迴心之三明六通大阿羅漢所不能破,更不能斷,故此所知障名為重障。又因所知障內涵深廣而難以除盡故,也函蓋煩惱障故,七地滿心已斷盡煩惱障所攝習氣種子隨眠者,轉入八地初心以後,方能開始專門斷除變易生死異熟法種,尚需一大阿僧祇劫精勤修行方能除盡,故名重障。
窺基法師對於重障的解釋非常好,《成唯識論述記》卷一說:「由煩惱障障大涅槃流轉生死,由所知障障大菩提不悟大覺;一者猶如金剛難可斷故,二者擔此難越生死流故,三者押溺有情處四生故,四者墮墜有情沒三界故;此上四義毀責過失故名為重,通二障解。五者或二障中我法二執為障根本,生餘障類,但說二執名為重障;我法執之餘末,障皆輕故。」
然而〈唯識三十頌〉及此論中,對於成佛之道的內容,基於所度對象是娑婆世界此際的五濁惡世有情,則以大乘見道之通達入地為偏重內容,是故此句中「斷二重障」之意涵,以見道通達位轉入初地時所必須斷除的二種障的障礙與開解為主。
對於此論闡述的大乘見道有如實證解的菩薩們,在「證真如」而心得決定,轉依成功而不退轉以後,依此論的解說而如實修證慧觀、定力、解脫、廣大福德、增上意樂以後,可以超越第一大阿僧祇劫,是因為此論中已經說明,在悟後的三賢位中必須修證非安立諦的三品心:內遣有情假緣智、內遣諸法假緣智、遍遣一切有情諸法假緣智;再加上「相見道」位的最後部分,即是安立諦十六品及九品心;由如是「真見道」及「相見道」的智慧與真如心平等平等故,能通達初地入地心真如的解脫與實相智慧,名為分證初地真如。
若能配合其他應有的條件 而發起對十無盡願的增上意樂,日日發願俟其增上意樂得清淨時便能入地,此時有佛加持而證明之,證得「大乘照明三昧」,即得完成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證過程與內涵。這便顯示此論的實修,對於佛菩提道的見道通達位中所應斷除的二種重大遮障|煩惱障與所知障|都能如實斷除,是由實證而得切實出生勝解的緣故,才說「生解為斷二重障故」。
「由我法執,二障俱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由我法執,二障俱生」:我執是執著五陰假我為實有,法執是執著諸法中的某法為實有之我,或如執有外六塵被自己所見知者亦名法執;然而二執皆妄,因為蘊處界等我皆非實有,依蘊處界而生的諸法亦非實有,是故應斷。所以上來勝解重障之義已,以下說明二種重障其實唯有二執:我執與法執。我執是煩惱障所攝,法執是所知障所攝。煩惱障的品類眾多,而法執中的品類更多,所以法執更加深廣難斷。我執亦因眾生所不知的法執而生,故說我執只是法執中的局部,法執函蓋我執。
若是具足我執與法執的人,正是被煩惱障及所知障雙雙遮障的凡夫異生,因此先打破二障即是學佛人的要務;是故若依大乘法能斷我見而斷除三縛結,薩迦耶見已除,便能對我執斷除第一分,煩惱障的遮障便減掉一分。若能「證真如」而觀察能取的覺知心等見分,以及所取的色身五根與六塵境界相分,現觀此二分都是空性如來藏中的一部分——能取所取空,轉依成功而能成就佛菩提中的「真見道」功德,根本無分別智生起了,實相般若在胸,法執便斷除了第一分,所知障便滅掉了第一分。然而煩惱障與所知障的由來,正是我執與法執,所以說,「由我法執,二障俱生」。
若斷不了煩惱障的影響,即是我見及我執深重,所以貪、瞋或愚癡深重者,「真見道」以後遇到事相上的事情不如意時,也會受煩惱障所攝的貪、瞋或愚癡所影響,失去轉依的功德,二障相應的煩惱便會繼續生起;甚至因此而推翻以前的所悟,只因自認一悟即入初地,而自己所悟並未擁有初地的功德,以此為由而否定善知識所授為非真悟,不接受證悟之時只是第七住位,企求初地功德;於是造謠抵制正法而作故謗善知識等大惡業。這在平實將近三十年的弘法過程中,再三、再四證明此一事實,學人於此不可不慎,若究其實,都是源於煩惱障的深重所致。
「若證二空,彼障隨斷」,若能具足證得人我空——詳細將我所執、我執全部滅除,煩惱障的現行便全部滅除,雖仍有煩惱障相應的習氣種子隨眠現行,亦能成就出離三界生死苦的果報,位在阿羅漢果,獲得解脫果的殊勝果報。
若能詳細將大乘見道通達位中應該全部滅除的法我執滅除,具足證得「相見道」位的法我空,見道位現行的所知障便全部滅除,成就了見道「通達位」的無生法忍——具足見道位應有的法空觀,位在初地聖果,即是獲得佛菩提果的殊勝果報;然而推究所知障與煩惱障的由來,全都源於我執與法執,因此玄奘大師說「由我法執,二障俱生」。意謂若非有我執與法執,就不會有煩惱障與所知障——二障俱生的緣由即是我執與法執等二種遮障;以是緣故,「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意謂菩薩若能依解脫道具足實證人我空,使煩惱障的現行滅除;也依佛菩提道具足實證見道「通達位」中應實證的法我空,斷除了「通達位」所知障的現行,對於佛菩提道二種見道位中所應斷除的煩惱障與所知障,便能隨之斷除,則入初地。
若未證二空,則二障不斷,異生性必定會再生起,即是沒有轉依成功,方又再度造作二障相應的種種惡行等作為,發起異生性,所以窺基法師於《成唯識論述記》卷一說:「問:『煩惱障中品類非一,可言本斷、餘惑不生。所知障中唯有法執,殊無品類,何法為流,言根斷時莖葉亦盡?』答:六識執外五識等中法、愛、恚等,異熟生攝;定下劣性,能障定者。法執等流,所知障攝,故說根斷莖葉亦除。」道理亦然,所以斷除根本煩惱才是最重要的事,若是根本的我執法執都未斷除,只斷二障等枝葉,久後又從根本再生枝葉,終究未能斷除二障。由是可知,斷薩迦耶見及「證真如」轉依才是根本。若對薩迦耶見藕斷絲連,久後遇緣又復再生,所斷的二節斷藕又連在一起,異生性又復生起而現行,於是破法及毀謗賢聖等業,恣意造之無所忌憚,即是顯示二障所依的根本(我執與法執)尚未斷其少分。
若對「證真如」心中有疑,未能剎那剎那心得決定,或如主張外於第八識心體而有真如可證者,即是所知障之根本未斷——法執具足存在,轉依不成功,久後遇緣又復生起所知障而轉生煩惱障,復造惡業。若是薩迦耶見藕斷絲連,於事相上有不如意時,我執與我見隨即復生,又對正法大造惡業。如是二障俱皆障礙學人進修佛菩提道,此亦是佛世以來的常態,直至如今更加彰顯。
問:「為何求斷二障?」答:「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為何說解脫果與佛菩提果是勝果?因為這二種殊勝的果報中,斷煩惱障是一切世間的天、人、阿修羅所不能證的緣故,名之為勝,三惡道即無論矣!至於斷除所知障、證佛菩提果後,位在賢位或聖位之事,亦非二乘聖者之所能,唯有菩薩歷經久劫方能具足證得故,外道與凡夫更無論矣!當然更可名之為「勝果」。
如是因地分斷我執(註)法執而打破二障,即能證得解脫於分段生死及證得實相法界的殊勝果報。若想要進而斷除二障的其他隨煩惱,還得轉入第二大阿僧祇劫中,繼續斷除煩惱障中的習氣種子隨眠,不以斷除現行為足。若是想要進而分斷所知障中修道所應斷的「上煩惱」隨眠,同樣皆屬於進入初地開始修道位中所應修者;滿足七地心以後,進入第三大阿僧祇劫中繼續斷除所知障中的種子異熟,永離變易生死,方能獲得解脫道及佛菩提道的究竟勝果,則是諸菩薩之所努力進求者。所以佛地斷盡二障時說是殊勝果,容後卷九、卷十再說。以是故說,斷除成佛之道中的這二種重大遮障,其目的是為了要獲得解脫果與佛菩提果這二種殊勝而究竟的果報之故,所以說:「斷障為得二勝果故。」(註:佛菩提道中所說的我執函蓋習氣種子隨眠,故曰分斷。)
問:「為何斷此二障得名勝果?」答:
「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真解脫;」由於斷除前後連續出生的煩惱障故,便可以證得「真解脫」。佛出世間之前,每有外道自稱已得解脫、已證涅槃;如是類人之中,有宣稱自己是阿羅漢者,也有宣稱自己是如來者,其實全部非真。今我 釋迦文佛出世宣說的解脫,方名「真解脫」,然後度諸外道已證禪定而宣稱證阿羅漢或證得如來果者,實證阿羅漢以後方有真阿羅漢及諸菩薩,以及 釋迦世尊所示現的真實如來,是故《成唯識論述記》卷一說:「解謂離縛,脫謂自在;障即煩惱,名煩惱障。此持業釋,障蔽涅槃令不趣證。凡夫所修諸行暫滅,外道苦行計證涅槃,乃至有頂諸惑暫斷(應為暫伏),所顯之理執為圓寂。今說彼是彼分涅槃,雖理名真,種不斷故非真解脫。」由生死苦的現行與習氣種子悉皆未斷故,非真解脫。
又如不迴心大乘的二乘聖者,未證第八識如來藏而未曾證得真如,無能現觀死後所入的無餘涅槃中的本際,故其所證的解脫並非真實解脫。何以故?皆因二乘聖者所證的解脫是方便施設,世尊依如來藏不生不滅說有解脫,然二乘聖人未曾實證第八識如來藏,不能現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故其解脫並不真實,即非「真解脫」。
是故二乘聖者生前所住的有餘依涅槃,並不了知將來捨壽以後「不受後有」時,迥無來世五蘊或四蘊的涅槃解脫境界是什麼;而他們捨壽後入了無餘依涅槃時,又沒有五蘊、四蘊之我存在而成為「不受後有」的無我狀態,當然也沒有五蘊等自我可以了知無餘涅槃中無有境界的解脫境界,因此二乘聖者以及外道的解脫,玄奘、窺基皆說為「非真解脫」,只是 世尊依第八識如來藏而方便施設,令彼等畏懼生死苦的不迴心二乘聖人、暫得遠離生死流轉。
唯有諸地菩薩所證之解脫方是「真解脫」,因為諸地菩薩世世捨壽時皆有能力入無餘涅槃,只是因為無止盡的十大悲願所持,故不取無餘涅槃而繼續受生於人間或色界、或兜率天的內院中;但在捨壽前仍然住世弘法的任何時刻,都能現觀阿羅漢與緣覺們,捨棄五蘊之後所取無餘涅槃中的境界,其實便是如來藏捨離五蘊、十八界後的無境界的本來解脫生死境界;而這種解脫生死的無生無死境界,其實是在捨壽之前便已本來存在著,即是第八識獨存而名為「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無境界境界,所以諸地菩薩所證的解脫境界才是「真解脫」。
論文:「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障俱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真解脫;由斷礙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又為開示謬執我法迷唯識者,令達二空,於唯識理如實知故。」
語譯:【如今造作這一部論典,是為了想要使對於人空與法空有迷惑而產生虛謬見解的人,可以出生正確理解的緣故;幫助他們生起正確理解,則是為了想要幫他們斷除煩惱障與所知障等二種重大障礙的緣故。由於有情同有我執與法執等二種遮障同時生起,若是能證得人空與法空等二空,他們的我執與法執等二障就會隨之斷除;而斷除這二障之目的是為了要幫他們證得解脫果與佛菩提果等二種殊勝果報的緣故。由於斷除相續而生的煩惱遮障的緣故,能斷此障而證得我空的人便可以證得真正的解脫;由於斷除對所知障內涵無知的障礙而理解所知障內涵的緣故,便能證得大菩提。又為了打開及顯示正理而使錯謬地執著有我有法的迷惑唯識性的人,教令他們通達我空與法空,對於唯識性的正理能如實了知的緣故。】
釋義:「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為斷二重障故。」「今造此論」:玄奘始從天竺投生於中國前,以曾三世為護法故而為國王,以致失去往世已有之神通與意生身故有胎昧;然於西行天竺取經之前,已經恢復往昔天竺時所證之解脫果及證真如與眼見佛性之智慧,當時已成為慧解脫及實證真如與佛性之菩薩,已有如幻觀的現量;依菩薩願不捨眾生,及為求具足而完整的成佛之道聖教得以弘傳於中國,廣利華夏學人,方始發願前往天竺而不顧禁令與安危,西行求經;返回大唐之後廣譯諸經,又造此論,成佛之道的完整內容方得弘揚於中國,成為中國至今傲視全球的文化瑰寶,譯經之後不久,禪宗之證悟明心,因有諸經之護持而得以廣弘。
對於返回中土已經通達真如的玄奘菩薩而言,是已經入地的聖者,證得多種現觀;而他對於三界愛的現行已經斷除,因此證得阿羅漢果而解脫於我執、我所執;並已斷除習氣種子隨眠,兼有深妙的無生法忍,是故玄奘造作此論時絕非為自身名聞或利養,純粹為了利他而造論。
「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玄奘造作此論所欲利益的對象,若能如實證解此論,將會有兩種利益:第一是以前對於我空與法空有迷惑以及誤解的人,可以因為如實證解此論中闡釋的唯識性、相等正義,理解先前對於我空與法空的誤解,由此而斷除我見,乃至斷除我所執與我執,證得解脫果的人我空,成為慧解脫的聖者;再者也可以由此論而如實現觀蘊處界等一切法莫非是空性心第八識——五陰自始至終都在第八識空性心中生住異滅、循環不已,本來即應攝歸第八識空性;由此現觀而深入觀察,終能現觀非安立諦等三品心而加以內遣(後述,此不預說),通達初地真如而證得法我空。
如是,一般學人本來雖於人空及法空有所迷謬,以致錯認邪說為正說的人,若能經由此論法義的如實證解而親證人我空與法我空,對二空便有正確的理解與實證,由是遠離對於二空產生迷謬之無明,永遠不墮於空有之爭中,跳脫於其外而得真如實智,發起實相般若。
二空是生空及法空;生空或名我空,是於眾生分上的五陰等法無有所知,執為真實不壞之自我時,若能現觀其為無我,名為證得生空或我空。法空,是指有人對於蘊處界,亦即是對於十二處、六入、十八界、心所……等諸法中所觀見的無數法,認定其全部或局部真實有我恆存,是常住法,名為法我;若於如是法我,能觀察其為生滅不住之有生法,並無一法之中有真實我,名為證得法空。如是二空滅除無明,即是此論所欲說明之正理。
迷與謬是二種人,如《成唯識論述記》卷一云:「一切異生諸外道等,此愚癡類,彼於二空全不解了,名為迷者;聲聞、獨覺及惡取空,邪解空理,分有智故,名為謬者。不解、邪解,合名迷謬。或但不解,無明名迷;若不正解,邪見名謬。癡、邪見人,名迷、謬者。」
「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然而對《成唯識論》的正確理解,可以使行者斷除二種重大的遮障,這二種重障是指煩惱障與所知障;若是錯解此論之人,則不能斷除絲毫。云何煩惱障與所知障名為重障?煩惱障對菩薩們的遮障,是障礙菩薩們無法證得解脫果,無法出離三界生死中的種種苦。既無法出離三界生死中的種種苦,便也同時遮障了更進一步修證佛菩提道的可能性;因為「證真如」而生起實相般若以前,必須先斷我見;若不先斷我見,永無可能「證真如」,必墮蘊處界我之中故;或是「證真如」後仍將退轉,以其我見未能先行斷除故。以是緣故說煩惱障中的我見、我所執、我執等,必致有情沈墮生死中;或是由於這二障會遮障有情證悟真如故,都屬於重障。
又煩惱障之重者,例如修證佛菩提道的第一大阿僧祇劫最末位的十迴向位,轉入初地之前必須斷除分段生死——斷盡三界愛的現行而證阿羅漢果;隨後轉入第二大阿僧祇劫的地後修道過程中,還必須斷除煩惱障所攝的三界愛習氣種子隨眠,才能進入八地起的第三大阿僧祇劫修行過程。以如是煩惱障極難斷除而致諸大阿羅漢之習氣種子隨眠尚難除盡故,說此煩惱障為重障。
所知障更屬重障,以其深奧微細而難破,若不證第八識真如即無法打破所知障;此是一切不迴心之三明六通大阿羅漢所不能破,更不能斷,故此所知障名為重障。又因所知障內涵深廣而難以除盡故,也函蓋煩惱障故,七地滿心已斷盡煩惱障所攝習氣種子隨眠者,轉入八地初心以後,方能開始專門斷除變易生死異熟法種,尚需一大阿僧祇劫精勤修行方能除盡,故名重障。
窺基法師對於重障的解釋非常好,《成唯識論述記》卷一說:「由煩惱障障大涅槃流轉生死,由所知障障大菩提不悟大覺;一者猶如金剛難可斷故,二者擔此難越生死流故,三者押溺有情處四生故,四者墮墜有情沒三界故;此上四義毀責過失故名為重,通二障解。五者或二障中我法二執為障根本,生餘障類,但說二執名為重障;我法執之餘末,障皆輕故。」
然而〈唯識三十頌〉及此論中,對於成佛之道的內容,基於所度對象是娑婆世界此際的五濁惡世有情,則以大乘見道之通達入地為偏重內容,是故此句中「斷二重障」之意涵,以見道通達位轉入初地時所必須斷除的二種障的障礙與開解為主。
對於此論闡述的大乘見道有如實證解的菩薩們,在「證真如」而心得決定,轉依成功而不退轉以後,依此論的解說而如實修證慧觀、定力、解脫、廣大福德、增上意樂以後,可以超越第一大阿僧祇劫,是因為此論中已經說明,在悟後的三賢位中必須修證非安立諦的三品心:內遣有情假緣智、內遣諸法假緣智、遍遣一切有情諸法假緣智;再加上「相見道」位的最後部分,即是安立諦十六品及九品心;由如是「真見道」及「相見道」的智慧與真如心平等平等故,能通達初地入地心真如的解脫與實相智慧,名為分證初地真如。
若能配合其他應有的條件 而發起對十無盡願的增上意樂,日日發願俟其增上意樂得清淨時便能入地,此時有佛加持而證明之,證得「大乘照明三昧」,即得完成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證過程與內涵。這便顯示此論的實修,對於佛菩提道的見道通達位中所應斷除的二種重大遮障|煩惱障與所知障|都能如實斷除,是由實證而得切實出生勝解的緣故,才說「生解為斷二重障故」。
「由我法執,二障俱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由我法執,二障俱生」:我執是執著五陰假我為實有,法執是執著諸法中的某法為實有之我,或如執有外六塵被自己所見知者亦名法執;然而二執皆妄,因為蘊處界等我皆非實有,依蘊處界而生的諸法亦非實有,是故應斷。所以上來勝解重障之義已,以下說明二種重障其實唯有二執:我執與法執。我執是煩惱障所攝,法執是所知障所攝。煩惱障的品類眾多,而法執中的品類更多,所以法執更加深廣難斷。我執亦因眾生所不知的法執而生,故說我執只是法執中的局部,法執函蓋我執。
若是具足我執與法執的人,正是被煩惱障及所知障雙雙遮障的凡夫異生,因此先打破二障即是學佛人的要務;是故若依大乘法能斷我見而斷除三縛結,薩迦耶見已除,便能對我執斷除第一分,煩惱障的遮障便減掉一分。若能「證真如」而觀察能取的覺知心等見分,以及所取的色身五根與六塵境界相分,現觀此二分都是空性如來藏中的一部分——能取所取空,轉依成功而能成就佛菩提中的「真見道」功德,根本無分別智生起了,實相般若在胸,法執便斷除了第一分,所知障便滅掉了第一分。然而煩惱障與所知障的由來,正是我執與法執,所以說,「由我法執,二障俱生」。
若斷不了煩惱障的影響,即是我見及我執深重,所以貪、瞋或愚癡深重者,「真見道」以後遇到事相上的事情不如意時,也會受煩惱障所攝的貪、瞋或愚癡所影響,失去轉依的功德,二障相應的煩惱便會繼續生起;甚至因此而推翻以前的所悟,只因自認一悟即入初地,而自己所悟並未擁有初地的功德,以此為由而否定善知識所授為非真悟,不接受證悟之時只是第七住位,企求初地功德;於是造謠抵制正法而作故謗善知識等大惡業。這在平實將近三十年的弘法過程中,再三、再四證明此一事實,學人於此不可不慎,若究其實,都是源於煩惱障的深重所致。
「若證二空,彼障隨斷」,若能具足證得人我空——詳細將我所執、我執全部滅除,煩惱障的現行便全部滅除,雖仍有煩惱障相應的習氣種子隨眠現行,亦能成就出離三界生死苦的果報,位在阿羅漢果,獲得解脫果的殊勝果報。
若能詳細將大乘見道通達位中應該全部滅除的法我執滅除,具足證得「相見道」位的法我空,見道位現行的所知障便全部滅除,成就了見道「通達位」的無生法忍——具足見道位應有的法空觀,位在初地聖果,即是獲得佛菩提果的殊勝果報;然而推究所知障與煩惱障的由來,全都源於我執與法執,因此玄奘大師說「由我法執,二障俱生」。意謂若非有我執與法執,就不會有煩惱障與所知障——二障俱生的緣由即是我執與法執等二種遮障;以是緣故,「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意謂菩薩若能依解脫道具足實證人我空,使煩惱障的現行滅除;也依佛菩提道具足實證見道「通達位」中應實證的法我空,斷除了「通達位」所知障的現行,對於佛菩提道二種見道位中所應斷除的煩惱障與所知障,便能隨之斷除,則入初地。
若未證二空,則二障不斷,異生性必定會再生起,即是沒有轉依成功,方又再度造作二障相應的種種惡行等作為,發起異生性,所以窺基法師於《成唯識論述記》卷一說:「問:『煩惱障中品類非一,可言本斷、餘惑不生。所知障中唯有法執,殊無品類,何法為流,言根斷時莖葉亦盡?』答:六識執外五識等中法、愛、恚等,異熟生攝;定下劣性,能障定者。法執等流,所知障攝,故說根斷莖葉亦除。」道理亦然,所以斷除根本煩惱才是最重要的事,若是根本的我執法執都未斷除,只斷二障等枝葉,久後又從根本再生枝葉,終究未能斷除二障。由是可知,斷薩迦耶見及「證真如」轉依才是根本。若對薩迦耶見藕斷絲連,久後遇緣又復再生,所斷的二節斷藕又連在一起,異生性又復生起而現行,於是破法及毀謗賢聖等業,恣意造之無所忌憚,即是顯示二障所依的根本(我執與法執)尚未斷其少分。
若對「證真如」心中有疑,未能剎那剎那心得決定,或如主張外於第八識心體而有真如可證者,即是所知障之根本未斷——法執具足存在,轉依不成功,久後遇緣又復生起所知障而轉生煩惱障,復造惡業。若是薩迦耶見藕斷絲連,於事相上有不如意時,我執與我見隨即復生,又對正法大造惡業。如是二障俱皆障礙學人進修佛菩提道,此亦是佛世以來的常態,直至如今更加彰顯。
問:「為何求斷二障?」答:「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為何說解脫果與佛菩提果是勝果?因為這二種殊勝的果報中,斷煩惱障是一切世間的天、人、阿修羅所不能證的緣故,名之為勝,三惡道即無論矣!至於斷除所知障、證佛菩提果後,位在賢位或聖位之事,亦非二乘聖者之所能,唯有菩薩歷經久劫方能具足證得故,外道與凡夫更無論矣!當然更可名之為「勝果」。
如是因地分斷我執(註)法執而打破二障,即能證得解脫於分段生死及證得實相法界的殊勝果報。若想要進而斷除二障的其他隨煩惱,還得轉入第二大阿僧祇劫中,繼續斷除煩惱障中的習氣種子隨眠,不以斷除現行為足。若是想要進而分斷所知障中修道所應斷的「上煩惱」隨眠,同樣皆屬於進入初地開始修道位中所應修者;滿足七地心以後,進入第三大阿僧祇劫中繼續斷除所知障中的種子異熟,永離變易生死,方能獲得解脫道及佛菩提道的究竟勝果,則是諸菩薩之所努力進求者。所以佛地斷盡二障時說是殊勝果,容後卷九、卷十再說。以是故說,斷除成佛之道中的這二種重大遮障,其目的是為了要獲得解脫果與佛菩提果這二種殊勝而究竟的果報之故,所以說:「斷障為得二勝果故。」(註:佛菩提道中所說的我執函蓋習氣種子隨眠,故曰分斷。)
問:「為何斷此二障得名勝果?」答:
「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真解脫;」由於斷除前後連續出生的煩惱障故,便可以證得「真解脫」。佛出世間之前,每有外道自稱已得解脫、已證涅槃;如是類人之中,有宣稱自己是阿羅漢者,也有宣稱自己是如來者,其實全部非真。今我 釋迦文佛出世宣說的解脫,方名「真解脫」,然後度諸外道已證禪定而宣稱證阿羅漢或證得如來果者,實證阿羅漢以後方有真阿羅漢及諸菩薩,以及 釋迦世尊所示現的真實如來,是故《成唯識論述記》卷一說:「解謂離縛,脫謂自在;障即煩惱,名煩惱障。此持業釋,障蔽涅槃令不趣證。凡夫所修諸行暫滅,外道苦行計證涅槃,乃至有頂諸惑暫斷(應為暫伏),所顯之理執為圓寂。今說彼是彼分涅槃,雖理名真,種不斷故非真解脫。」由生死苦的現行與習氣種子悉皆未斷故,非真解脫。
又如不迴心大乘的二乘聖者,未證第八識如來藏而未曾證得真如,無能現觀死後所入的無餘涅槃中的本際,故其所證的解脫並非真實解脫。何以故?皆因二乘聖者所證的解脫是方便施設,世尊依如來藏不生不滅說有解脫,然二乘聖人未曾實證第八識如來藏,不能現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故其解脫並不真實,即非「真解脫」。
是故二乘聖者生前所住的有餘依涅槃,並不了知將來捨壽以後「不受後有」時,迥無來世五蘊或四蘊的涅槃解脫境界是什麼;而他們捨壽後入了無餘依涅槃時,又沒有五蘊、四蘊之我存在而成為「不受後有」的無我狀態,當然也沒有五蘊等自我可以了知無餘涅槃中無有境界的解脫境界,因此二乘聖者以及外道的解脫,玄奘、窺基皆說為「非真解脫」,只是 世尊依第八識如來藏而方便施設,令彼等畏懼生死苦的不迴心二乘聖人、暫得遠離生死流轉。
唯有諸地菩薩所證之解脫方是「真解脫」,因為諸地菩薩世世捨壽時皆有能力入無餘涅槃,只是因為無止盡的十大悲願所持,故不取無餘涅槃而繼續受生於人間或色界、或兜率天的內院中;但在捨壽前仍然住世弘法的任何時刻,都能現觀阿羅漢與緣覺們,捨棄五蘊之後所取無餘涅槃中的境界,其實便是如來藏捨離五蘊、十八界後的無境界的本來解脫生死境界;而這種解脫生死的無生無死境界,其實是在捨壽之前便已本來存在著,即是第八識獨存而名為「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無境界境界,所以諸地菩薩所證的解脫境界才是「真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