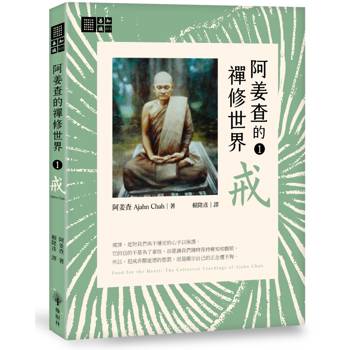【第三章】感官接觸——智慧的泉源
真正的平靜在我們內心
為了找到平靜,我們已下定決心成為佛教中的比丘和沙彌。那麼,什麼是真正的平靜呢?
佛陀說,真正的平靜並不遠——它就在我們的內心!但我們卻長久忽視它。人們渴望獲得平靜,卻始終感到迷妄和不安。他們一直對自己缺乏信心,且無法從修行中獲得滿足。猶如我們離家四處旅行,但只要還未回家,就不會感到滿足,而仍有未完成的事需要費心。這是因為旅程還未結束,我們尚未到達最後的目的地。
所有比丘與沙彌,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平靜。當我年輕時,四處尋找它,無論到哪裡都無法滿足。我進入森林行腳,參訪各類老師聆聽開示,都無法從中獲得滿足。
為何會如此?我們在極少接觸色、聲、香、味的環境尋找平靜,相信安靜地生活能令我們滿意。但事實上,若我們在不受干擾的地方,非常安靜地生活,能生起智慧嗎?我們能覺知到什麼?仔細想想,若眼不見色,那會是什麼情況?若鼻不嗅香,舌不嘗味,身無觸受,那會是什麼情況?那情況就如盲、聾之人,鼻子與舌頭失靈,且身體完全麻痺失去知覺。那裡有任何東西存在嗎?然而人們卻還固執地認為,只要到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的地方,就能找到平靜。
放下不是什麼都不做
當我還是個年輕比丘,剛開始修行時,坐禪便會受到聲音干擾,我自問:「該怎麼做才能讓心平靜下來?」於是我拿了一些蜜蠟將耳朵塞起來,如此就聽不到任何聲音,只剩下嗡嗡嗡的殘響。我以為那樣會比較平靜,但並非如此,所有的思考與迷妄根本不是從耳朵生起,而是從心生起,那才是找尋平靜的地方。
換句話說,無論待在哪裡,你都不想做任何事,因為那會妨礙修行。你不想掃地或做任何工作,只想坐著不動來尋找平靜。老師要求你幫忙做些雜務或日常執事,你並不用心,因為覺得那些都只是外在的事。
我有個弟子,他真的很努力「放下」以追求平靜。我曾教導「要放下」,他認為只要放下一切事物,便可獲得平靜。從來這裡的那天起,他就不想做任何事,即使大風吹走他茅篷的半邊屋頂,也絲毫不在意。他認為那只是外在的事,因此不想費心修理,當陽光或雨滴從一邊灑進來時,就挪到另一邊去。他唯一關心的是讓心平靜,其他的事都只會讓他分心。
有天我經過那裡,看見傾頹的屋頂。「咦?這是誰的茅篷?」我問。有人告訴我是他的,我心想:「嗯!奇怪。」因此便找他談話,對他解釋許多事,如「屋舍儀法」(senāsanavatta)——比丘對住處的相關義務。「我們必須有個住處,且必須照顧它。『放下』並非如此,它不是要逃避我們的責任,那是愚蠢的行為。雨從這邊下來,你就移到另一邊,陽光照進來時,你又再移回這邊,為什麼要這樣?你為什麼不乾脆連那裡也放下?」我在這上面為他上了頗長的一課。
當我結束時,他說:「哦!隆波!有時你教我執著,有時又教我放下,不曉得你到底要我怎麼做。甚至當屋頂塌了,我都能放下到這種程度,你還是說這樣不對,可是你教我們要放下啊!我不知道你還指望我怎麼做。」
有些人就是可以如此愚蠢!
每件事物皆可用來修行
若我們如實覺知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麼它們都是生起智慧可用的素材。若我們無法如實覺知它們,就會否定它們,宣稱不想見色或聞聲,因我們會受到干擾。若切斷了這些因緣,我們要憑藉什麼進行思惟呢?
因此,佛陀教導我們要防護,防護即是「戒」。有防護感官的戒——眼、耳、鼻、舌、身、意——這些都是我們的戒和定。
想想舍利弗的故事,在他成為比丘之前,有次看見馬勝(Assaji,音譯為「阿說示」,五比丘之一)長老正在托缽,心想:「這出家人如此不凡,走路不疾不徐,衣著整潔,威儀莊嚴。」舍利弗受到鼓舞,趨上前去致敬並問道:「抱歉,長者!請問你是誰?」
「我是一位沙門。」
「你的老師是誰?」
「我的老師是喬達摩尊者。」
「喬達摩尊者教導什麼?」
「他教導一切事物都從因緣生,當因緣滅時,就隨之息滅。」
當舍利弗問法時,馬勝比丘給了他這簡短的關於因果的解釋。「諸法因緣生,有因才有果;若是果息滅,必是因先滅。」
他雖然只說了這些,但對舍利弗而言已經足夠。
這是一個佛法生起的因,那時舍利弗六根具足,擁有眼、耳、鼻、舌、身、意,若無感官,他會有足夠的因以生起智慧嗎?能覺知任何事嗎?但多數人都害怕感官接觸,無論害怕或喜歡,我們都未從中發展出智慧,反而透過這六根放縱自己,貪圖感官享受並迷失於其中。這六根可能誘使我們享樂與放縱,也可能引導我們獲得知識與智慧。
因此,我們應該把每件事物都拿來修行,即使是不好的事。當談到修行時,我們不只針對美好或令人愉悅的事,修行並非如此。在這個世上,有些事物我們喜歡,有些則否,通常我們想要喜歡的,即使對同修的比丘與沙彌也一樣。我們不想和不喜歡的比丘或沙彌交往,只想和喜歡的人在一起。你了解嗎?這是依自己的喜好在做選擇。通常只要是不喜歡的,就不想看見或了解, 但佛陀希望我們去體驗這些事,「世間解」——看著這世間並清楚地覺知它。
若無法清楚覺知世間的實相,我們將無處可去。活在這世上,就必須了解這世間,包括佛陀在內的過去的聖者,都與這些事物一起生活。他們活在這個世上,在凡夫之中,就在這裡達到實相,而不在他處。但他們有智慧,能防護六根。
一直逃避智慧無從生起
防護並非意指不看、不聽、不聞、不嘗、不觸或不想任何事,若行者不了解這點,一旦見聞到什麼,就退縮逃避,以為只要這麼做,那件事最後就會喪失控制的力量,然後他們就能超越它。但往往事與願違,他們根本無法超越任何事。若他們逃避而未了知實相,相同的事不久仍會生起,一樣得再面對。
例如,那些永不滿足的行者,在寺院、森林或山中受持頭陀支(Dhutanga),他們到處行腳,東看看、西瞧瞧,認為如此就能獲得滿足。他們努力爬上山頂:「啊!就是這裡,現在我沒問題了。」感到幾天的平靜後,就對它厭煩了。「哦,好吧!下山到海邊去。」「啊!這裡既舒適又涼快,在這裡修行一定很好。」不久後,他又對海邊感到厭倦。對森林、山頂、海邊厭倦,對一切厭倦。這並非正見,不是厭離的正確意義,而僅僅是感到乏味,是一種邪見。
當他們回到寺院:「現在,我該怎麼做?每個地方都去過了,卻一無所獲。」因此他們棄缽、卸袍而還俗去了。為何要還俗?因為他們不了解修行,不曉得還有什麼事可做。他們去南方、北方、海邊、山頂、森林,仍不了解任何事,因此結束一切,他們便「死」了。事情的演變就是如此,因為他們一直逃避事物,智慧便無從生起。
從心裡跳脫不是逃避面對事情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假設有個比丘,下定決心不逃避事物,要勇敢面對它們。他照顧自己,並了解自己和他人,持續努力地解決各種問題。假設他是位住持,經常得不斷面對需要注意的事物,人們一直來詢問,因此必須時常保持覺醒。在可以打瞌睡之前,他們就會再用另一個問題喚醒你。這讓你能思惟、了解所面對的事物,你變得會以各種的善巧方式處理自己與別人的問題。
這技巧從接觸、面對、處理與不逃避事情中生起,我們不是以身體逃避,而是使用智慧,從心裡跳脫,靠當下的智慧而了解,不逃避任何事。
這是智慧的源頭,每個人都必須工作,必須和其他事物聯繫。例如,住在大寺院中都必須幫忙處理事情,從某個角度看它,你可能會說那些都是煩惱。和許多比丘、比丘尼、沙彌住在一起,在家眾來來去去,可能會生出許多煩惱。但為了增長智慧、斷除愚痴,我們必須如此生活。我們要選擇哪一條路?是為了消除愚痴,或為了增加它而生活?
真正的平靜在我們內心
為了找到平靜,我們已下定決心成為佛教中的比丘和沙彌。那麼,什麼是真正的平靜呢?
佛陀說,真正的平靜並不遠——它就在我們的內心!但我們卻長久忽視它。人們渴望獲得平靜,卻始終感到迷妄和不安。他們一直對自己缺乏信心,且無法從修行中獲得滿足。猶如我們離家四處旅行,但只要還未回家,就不會感到滿足,而仍有未完成的事需要費心。這是因為旅程還未結束,我們尚未到達最後的目的地。
所有比丘與沙彌,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平靜。當我年輕時,四處尋找它,無論到哪裡都無法滿足。我進入森林行腳,參訪各類老師聆聽開示,都無法從中獲得滿足。
為何會如此?我們在極少接觸色、聲、香、味的環境尋找平靜,相信安靜地生活能令我們滿意。但事實上,若我們在不受干擾的地方,非常安靜地生活,能生起智慧嗎?我們能覺知到什麼?仔細想想,若眼不見色,那會是什麼情況?若鼻不嗅香,舌不嘗味,身無觸受,那會是什麼情況?那情況就如盲、聾之人,鼻子與舌頭失靈,且身體完全麻痺失去知覺。那裡有任何東西存在嗎?然而人們卻還固執地認為,只要到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的地方,就能找到平靜。
放下不是什麼都不做
當我還是個年輕比丘,剛開始修行時,坐禪便會受到聲音干擾,我自問:「該怎麼做才能讓心平靜下來?」於是我拿了一些蜜蠟將耳朵塞起來,如此就聽不到任何聲音,只剩下嗡嗡嗡的殘響。我以為那樣會比較平靜,但並非如此,所有的思考與迷妄根本不是從耳朵生起,而是從心生起,那才是找尋平靜的地方。
換句話說,無論待在哪裡,你都不想做任何事,因為那會妨礙修行。你不想掃地或做任何工作,只想坐著不動來尋找平靜。老師要求你幫忙做些雜務或日常執事,你並不用心,因為覺得那些都只是外在的事。
我有個弟子,他真的很努力「放下」以追求平靜。我曾教導「要放下」,他認為只要放下一切事物,便可獲得平靜。從來這裡的那天起,他就不想做任何事,即使大風吹走他茅篷的半邊屋頂,也絲毫不在意。他認為那只是外在的事,因此不想費心修理,當陽光或雨滴從一邊灑進來時,就挪到另一邊去。他唯一關心的是讓心平靜,其他的事都只會讓他分心。
有天我經過那裡,看見傾頹的屋頂。「咦?這是誰的茅篷?」我問。有人告訴我是他的,我心想:「嗯!奇怪。」因此便找他談話,對他解釋許多事,如「屋舍儀法」(senāsanavatta)——比丘對住處的相關義務。「我們必須有個住處,且必須照顧它。『放下』並非如此,它不是要逃避我們的責任,那是愚蠢的行為。雨從這邊下來,你就移到另一邊,陽光照進來時,你又再移回這邊,為什麼要這樣?你為什麼不乾脆連那裡也放下?」我在這上面為他上了頗長的一課。
當我結束時,他說:「哦!隆波!有時你教我執著,有時又教我放下,不曉得你到底要我怎麼做。甚至當屋頂塌了,我都能放下到這種程度,你還是說這樣不對,可是你教我們要放下啊!我不知道你還指望我怎麼做。」
有些人就是可以如此愚蠢!
每件事物皆可用來修行
若我們如實覺知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麼它們都是生起智慧可用的素材。若我們無法如實覺知它們,就會否定它們,宣稱不想見色或聞聲,因我們會受到干擾。若切斷了這些因緣,我們要憑藉什麼進行思惟呢?
因此,佛陀教導我們要防護,防護即是「戒」。有防護感官的戒——眼、耳、鼻、舌、身、意——這些都是我們的戒和定。
想想舍利弗的故事,在他成為比丘之前,有次看見馬勝(Assaji,音譯為「阿說示」,五比丘之一)長老正在托缽,心想:「這出家人如此不凡,走路不疾不徐,衣著整潔,威儀莊嚴。」舍利弗受到鼓舞,趨上前去致敬並問道:「抱歉,長者!請問你是誰?」
「我是一位沙門。」
「你的老師是誰?」
「我的老師是喬達摩尊者。」
「喬達摩尊者教導什麼?」
「他教導一切事物都從因緣生,當因緣滅時,就隨之息滅。」
當舍利弗問法時,馬勝比丘給了他這簡短的關於因果的解釋。「諸法因緣生,有因才有果;若是果息滅,必是因先滅。」
他雖然只說了這些,但對舍利弗而言已經足夠。
這是一個佛法生起的因,那時舍利弗六根具足,擁有眼、耳、鼻、舌、身、意,若無感官,他會有足夠的因以生起智慧嗎?能覺知任何事嗎?但多數人都害怕感官接觸,無論害怕或喜歡,我們都未從中發展出智慧,反而透過這六根放縱自己,貪圖感官享受並迷失於其中。這六根可能誘使我們享樂與放縱,也可能引導我們獲得知識與智慧。
因此,我們應該把每件事物都拿來修行,即使是不好的事。當談到修行時,我們不只針對美好或令人愉悅的事,修行並非如此。在這個世上,有些事物我們喜歡,有些則否,通常我們想要喜歡的,即使對同修的比丘與沙彌也一樣。我們不想和不喜歡的比丘或沙彌交往,只想和喜歡的人在一起。你了解嗎?這是依自己的喜好在做選擇。通常只要是不喜歡的,就不想看見或了解, 但佛陀希望我們去體驗這些事,「世間解」——看著這世間並清楚地覺知它。
若無法清楚覺知世間的實相,我們將無處可去。活在這世上,就必須了解這世間,包括佛陀在內的過去的聖者,都與這些事物一起生活。他們活在這個世上,在凡夫之中,就在這裡達到實相,而不在他處。但他們有智慧,能防護六根。
一直逃避智慧無從生起
防護並非意指不看、不聽、不聞、不嘗、不觸或不想任何事,若行者不了解這點,一旦見聞到什麼,就退縮逃避,以為只要這麼做,那件事最後就會喪失控制的力量,然後他們就能超越它。但往往事與願違,他們根本無法超越任何事。若他們逃避而未了知實相,相同的事不久仍會生起,一樣得再面對。
例如,那些永不滿足的行者,在寺院、森林或山中受持頭陀支(Dhutanga),他們到處行腳,東看看、西瞧瞧,認為如此就能獲得滿足。他們努力爬上山頂:「啊!就是這裡,現在我沒問題了。」感到幾天的平靜後,就對它厭煩了。「哦,好吧!下山到海邊去。」「啊!這裡既舒適又涼快,在這裡修行一定很好。」不久後,他又對海邊感到厭倦。對森林、山頂、海邊厭倦,對一切厭倦。這並非正見,不是厭離的正確意義,而僅僅是感到乏味,是一種邪見。
當他們回到寺院:「現在,我該怎麼做?每個地方都去過了,卻一無所獲。」因此他們棄缽、卸袍而還俗去了。為何要還俗?因為他們不了解修行,不曉得還有什麼事可做。他們去南方、北方、海邊、山頂、森林,仍不了解任何事,因此結束一切,他們便「死」了。事情的演變就是如此,因為他們一直逃避事物,智慧便無從生起。
從心裡跳脫不是逃避面對事情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假設有個比丘,下定決心不逃避事物,要勇敢面對它們。他照顧自己,並了解自己和他人,持續努力地解決各種問題。假設他是位住持,經常得不斷面對需要注意的事物,人們一直來詢問,因此必須時常保持覺醒。在可以打瞌睡之前,他們就會再用另一個問題喚醒你。這讓你能思惟、了解所面對的事物,你變得會以各種的善巧方式處理自己與別人的問題。
這技巧從接觸、面對、處理與不逃避事情中生起,我們不是以身體逃避,而是使用智慧,從心裡跳脫,靠當下的智慧而了解,不逃避任何事。
這是智慧的源頭,每個人都必須工作,必須和其他事物聯繫。例如,住在大寺院中都必須幫忙處理事情,從某個角度看它,你可能會說那些都是煩惱。和許多比丘、比丘尼、沙彌住在一起,在家眾來來去去,可能會生出許多煩惱。但為了增長智慧、斷除愚痴,我們必須如此生活。我們要選擇哪一條路?是為了消除愚痴,或為了增加它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