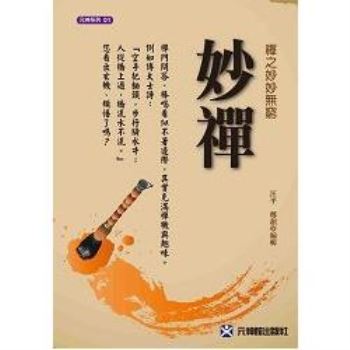禪八講目錄夾雜英文有噱頭
如前所述,鈴木大拙的著作大多從其英文講義中翻譯而來,而禪本不立文字,其言語又充滿禪機,難以用常理推斷;要將禪的意涵用英文如實表達已經不容易,再翻成中文或其母語日文也不容易,因而出現目錄中夾雜英文的特殊現象。例如:
第一部:最終講義----禪讓通過不可得的方法進行自證的人開悟(Zen Opens Our Eyes to Self which is Altogether Unattainably Attainable)。第二部:鈴木大拙說禪的世界----(序)佛教到底是什麼?(What is Buddhism?)(第一章)禪與心理學(Zen and Psychology)。(第二章)佛教禪與藝術(Zen Buddhism and the Arts)。(第三章)活在佛教禪的戒律中(Living by the Precepts of Zen Buddhism)。(第四章)佛教與倫理(Buddhism and Ethics)。(第五章)佛教的神秘主義(Buddhism Mysticism)。(第六章)佛教禪的哲學(Philosophy of Zen Buddhism)。
不過如果細看其目錄英文,其實文字很簡單,章節也無特殊性,噱頭多於必要性,其目的可能是在吸引讀者的目光吧!何況就編輯而言,此種「後發先至」、近期文稿放前面,早年文稿放後面,可能會讓人有時空錯置的感覺。為了便於讀者理解起見,以下特別挑出重點,點出「最後禪八講」的特色:
第一講:什麼是「禪」
主要是記錄鈴木大拙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在夏威夷演講的二十九項要旨。其中雖未明確記錄演講會場及時間,但從其內容可知,演講會場是夏威夷東本願寺別院的成道會,從下午2點開始,持續了約1個小時。
第二講:禪說「真我」
在這次演講中,大拙說:心理學中的「真我」一詞,經常和個人連結使用,甚至可以說,「真我」本來就是從心理學發展而來;宇宙的真我可以和非宇宙的真我相連接。他認為,初學佛的人大概都無法理解,甚至有點排斥,為何要以「梵(阿特曼)」來代表真我。大拙甚至將成為佛性根據的「真我」,作為「無欲的修行者」,以引出唐代末期禪師的理念。因此必要時可參看宋代禪師的公案。第三講:禪與藝術
根據鈴木大拙的說法,所謂「佛教禪與藝術」,是指禪與藝術不管是在主觀或客觀上都能達到完美一致,禪就像宇宙之魂深處的物質,而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來展示,那既是藝術的起源,也是真正的藝術。在那種情況下,表現者和表現的媒介融為一體,而且自己可以意識到這種一體化,這就是禪的真我意識。他以日本有名的俳句「千代女」與「芭蕉」等具體的例子來做說明。例如:「嬌豔牽牛花,紫露晶瑩縈清井,惜花借水去」(千代女),「閑寂古池旁,青蛙跳進水中央,撲通一聲響」(芭蕉);還有鏡清的《雨滴聲》問答,仔細描寫雪寶問答的頌語,以此來說明日式禪所具有的藝術之美。
第四講:修禪戒律
在談到「佛教禪戒律」時,鈴木大拙提到,修禪、談禪說法時通常有三種戒律,那就是:「不肯定什麼是什麼」、「不否定什麼不是什麼」,以及成為那個「什麼」本身。他認為在宗教生活中,只要謹守這三個戒律,就能在生的本身中找出生的意義;非出家眾如能在日常活中把握這三個戒律,結果會更加美好;就如同他盛讚千代女所寫的「牽牛花」詩,就頗具淨土宗經典所描寫的「安樂國淨土」之美。
就禪宗或禪學而言,雖然說共有三個戒律,其實歸結到最後不過是「道一句」,也就是一句話、言語道斷的意思。為了說明三戒律與生的關係,鈴木大拙特別介紹了一則禪宗唐朝在有名的公案「南泉斬貓」:唐朝時,南泉普願禪師修行的禪堂出現了一隻貓,眾僧為了「貓有沒有佛性」而爭論不休,甚至因此而造成對立。南泉普願禪師走出禪堂,要求眾僧「道一句」,亦即說出貓到底有沒有佛性的道理;如果說不出,則爭論無易,就殺了爭論的源頭「貓」。結果因為沒有人回答得出,南泉就命人斬殺了那隻貓。
不久,南泉最信賴的弟子趙州和尚從外面勞作回來,南泉把經過說給他聽,問他會怎麼做?趙州禪師聽了之後什麼都沒說,就脫下腳上穿的草鞋,頂在頭上走了出去。南泉看了嘆道:「剛才如果你在場,那隻貓兒就得救了。」自古以來,這則「南泉斬貓」公案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引起很多討論,鈴木大拙自己也認為很難明確表達這則公案的整體內涵。不過他也認為,「修禪三原則」終究勝過當時西方世界流行的「新正統派基督教世界觀」,以及薩特所代表、主張虛無的存在主義。基督教是把現實的「生(命)」本身,當作沒有意義的東西;而將神的恩惠、恩寵視為「生」的外部力量。薩特的存在主義則認為,不論是「生」的內部或外部,其實都是虛無的,包括生命與生活都是虛無的,必須重新定位存在的意義。可是依據禪雖然不直觀地否定或不否定什麼,但認為宇宙充滿生機,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只要經過指引,找出那個可能性,就是頓悟,就能海闊天空、心無罣礙,過有意義的人生。
大拙禪風具有五大特色
禪文化聯繫了古代與現代,跨越了東方與西方文化的為哩,形成一條寬廣深邃的溝通渠道。雖然禪宗與禪學興盛於中土,但不可諱言,二十世紀初期將禪文化帶入西方社會,且引起重視的應該是日本人,其中以鈴木大拙最投入、最有心,而且獲得最多回響。尤其是他晚年多場演講結集而成的「最後禪八講」,最近又引起討論的話題。
其實鈴木大拙在西方說禪,不像我國傳統的禪宗大師或其解讀者一樣,往往先談禪宗的發展史,再提具有代表性的公案。他雖以中國禪、日本禪為立論基本,卻用西方哲學的觀點來解說禪,這是它的特點,也是成功之處。大拙說禪可大致歸納出幾個重點與特色:
一、以西方哲學語言說禪,故能引起興趣
或許是受到其同鄉兼好友、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影響,鈴木大拙談禪「多從理論上下功夫」,而且用的是西方人容易懂的語言和文字,因此能激起西方人對東方禪文化的好奇,達到他「盡量讓普通的讀者能多了解禪、更加親近禪,即使多少犧牲了一點禪的正確性」也可以理解。但以哲學或西方語言說禪,再翻譯成東方文字時,可能有無法完全達意的情況,尤其禪宗公案的引述,就顯得虛無飄渺,沒有原先文字那麼簡潔而意境高遠。二、強調「靈性的直覺」
雖然鈴木大拙長年待在西方社會,但其思考模式、對禪的觀念還是非常傳統的,他對《華嚴經》有深入研究,也體會到「明心見性」、「頓悟」的奇妙。據說他在以「真我」為前提的修習過程中,二十五歲時體驗到「靈性的直覺」,明心見性而「開悟」;此後均以心靈本能的直覺,即禪之體驗,作為禪思想的主幹(大前提),從此始終一貫,從未改變。
他認為宇宙中的一切現象,彼此之間有多重至無限的關係,即使只是是一個現象,比如心理上的微小波動,或一粒微塵,其中都包含了宇宙整體的影像,即所謂「一沙一世界」、「絕對的一點蘊含三千個大千世界,絕對的現在包含永遠的過去和永遠的未來。」這種「為一切眾生,神變不可思議」的體驗,只有回歸真我,靠「靈性的直覺」才能頓悟。
三、禪不能以常情看待、常理推測
「禪超越了言語和理智,不像哲學那樣,依循規定的思想和行為發展。」鈴木大拙強調,只有「修行」才是明心見性的捷徑。他引日本曹洞禪創始人道元和尚的話說:「我空手還鄉,在中國學到的只不過是眼橫鼻直而已。」意思是雖然到在禪門重地修行,每天的生活都一樣,看到的人也都長得差不多,無法給予什麼高深的理論,也不談玄說裡,就像每個人的長相都是眼睛橫著長、鼻子是值得那麼平常。禪門中人的言行舉止也無法以理智探討,更無法系統化表述;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行」,就是觀察、思索與體會。禪的修行沒有適當、合理的知解形式,但也不能完全沒有知解;「有知解而無修行則弱,只修行而無知解則盲」,比較起來,知識、理解還不如「老實念佛(修行)」容易禪悟。
談禪的性格、方法與途徑
常言道「知易行難」,就禪而言,「知」的工夫並不難,難的是如何達到真正的「知」,以接近禪的本質。畢竟禪是一種洞徹的智慧,其本質在於「真實在」,正如鈴木所言:「禪給了我們看透世界的眼睛,其範圍遍及三千大千世界,而且還要超越。」因此鈴木大拙說禪,談的是禪的性格,禪是什麼、不是什麼;禪的方法、路徑,禪如何看世界、如何思考;最後才談到修禪的目的和意義。他談禪宗與東西方宗教的異同、禪與審美的關係等等,無非想廓清世俗(特別是西方世界)對禪錯誤或粗淺概念,掃去陰霾,以回復本來面目。星雲法師在『禪學與淨土』系列演講集的序中,談到什麼是禪、修禪或學禪有什麼作用時說:「禪是什麼呢?據青原禪師說:禪就是我們的「心」。唐朝的百丈禪師最提倡生活化的禪,他說挑柴擔水、衣食住行,無一不是禪,所謂翠竹黃花,一切的生活都是禪。」又說:「我們生活在人間,人間有男女老少,人間有五欲六塵,人間有生老病死,人間有悲歡離合。在缺憾的世間裡,我們如何獲得歡喜自在?如何發揮生命的價值?如何擁有安樂的生活?這是我們要探討的課題。」他說,禪可以開拓我們的心靈,啟發我們的智慧,引導我們進入更超脫的自由世界,可以說是探討生命學、生死學與生活學的法門,打開天人之門的鑰匙。換句話說,就是:以生命為 「體」,生死為「相」,生活是「用」,生命從生到死,其中的食衣住行、言行舉止、身心活動等等,無一不是生命的作用。因此,體、相、用,三者密不可分。所謂戒定慧,即由戒生定,由定發慧,由慧趣入解脫,需要斷除煩惱才能獲得究竟的妙智,才能自在悠遊於人間!
但「禪是需要去實踐的,而不是在嘴上談論的」;所謂「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地用功夫;若要紙上談人我,筆影蘸乾洞庭湖。」禪是言語道斷、不立文字的;是心行處滅,與思維言說的層次不同的。禪不好講、不能談,也不易懂。所以古代禪師用「棒喝」、用看似不合常理的言語、文字來讓地子頓悟;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來參禪(就是生活禪);甚至如「趙州八十行腳」一樣地修禪。
話雖如此,禪畢竟不容易入門,所謂「妙高頂上,不可言傳;第二峰頭,略容話會」。禪雖然不容易了解,雖然以「言語道斷、不立文字」為戒律,為了普及禪知識,還是要藉言語、jp6y4來說明。禪八講雖各有主題,但是每講內容實則包含了多個子目標,切題並擴題,顯得廣闊無邊。本書採用主題方式,重新呈現禪八講。閱讀起來輕鬆活潑,禪味不失,請讀者慢慢體會禪言之妙。
以下即以其所提的公案來作分析,請讀者多加體會。
一、論佛姓
公案:本有說不得
松山和尚和龐居士喝茶。居士說:「人人均有佛性,為什麼說不出來?」
松山道:「因為人人本有,故說不得!」
居士又問:「但有時聽你說此本有(佛性),這又是為何?」
和尚答:「你總不能叫我不說話吧!」公案:喝茶為和要寒喧
唐代禪匠松山(馬祖道一門下)與龐居士喝茶。居士拿起茶碟,問:「茶碟人人知,卻沒有人解釋它究為何物,這是為何?」
松山禪師回答:「人人皆知,所以誰也無法解釋。」
龐居士進一步追問:「那麼如何才算是巧妙的說明呢?」
松山回答道:「無法保持沉默的時候。」並喝了一口茶碟上的茶。
龐居士緊迫追問:「喝茶的時候,為什麼要先對客人寒暄呢?」
松山詫異的問道:「對誰?」
龐居士接著說:「對姓龐的老人啊。」
「老人,需要寒暄嗎?」
◆ 解讀
龐居士和松山的問答就這樣結束了。初次接觸學學的人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事實上,禪不是哲學,也無法說理,但禪者間的問答卻充滿了哲學意味。對多數人來說,禪者間的對話不著邊際,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教誨。龐居士所問、松山和尚所答,都不是茶碟的外在,而是有情或無情究極的實在。在「禪問答」之間,確實有不可思議的一面。禪並非全是抽象的觀念,身旁觸手可及的茶碟也蘊含著禪的道理。松山和尚所言「無法保持沉默的時候」,意指不得不表達自我的時候,其內心早已浮現闡述禪的道路。禪匠所關切的,也是每一個人都關心的。這就是禪。
初次接觸禪的人都說禪難以把握、甚至讓人困惑,這是基於以下事實:不可得的東西就像是圓心在任何地方的圓,正因為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以得到,所以才不可得。它不在任何地方,所以無所不在;它隨處都有,卻又是哪裡都沒有。
我們再看看雪峯義存的公案,也許就可以帶來啟示。
第三章 禪到底是什麼?
看了那麼多禪宗公案,究竟有多少人知道:禪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佛學提倡解行並重,尤其是禪,更注重實踐的功夫。唯有透過實踐,才能把握到禪的風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古德說:搬柴運水無非是禪。在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面,穿衣吃飯可以參禪,走路睡覺可以參禪,甚至於上廁所都可以參禪。一、禪最自然,無關美醜
什麼是道?「雲在青天水在瓶」、「青青翠竹,無非般若;鬱鬱黃花,皆是妙諦」。
未悟道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悟道後,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日月,寒盡不知年」、「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禪」就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滌心靈的塵埃;禪,如天上的白雲,任運逍遙,不滯不礙。
公案:好醜起於心
雙峯道信禪師(五八○~六五一)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禪宗特別重視內心的淨化,強調要認識內心世界的真面貌。
在諸多花卉中,最富禪意的是在清晨開放的牽牛花,其絢爛之美常於瞬間爆發、達到頂峰。牽牛花能夠長到二十公分,甚至更大,有各種顏色。雖然無法經受長時間的陽光照射,但花朵總在夏日清晨的清爽空氣中綻放,堪稱「無瑕」;無論是何種色調,若有輕盈的朝露加被,便顯現出鮮活生機,十分清雅動人。
日本德川幕府時代末期(十八世紀後半葉),有一位頗具才華的女俳人千代,她創作了許多十七音節的俳句,其中就有牽牛花。有一天她在清早起床後,準備從廚房旁邊的水井打水,忽然發現牽牛花的藤蔓纏繞著水桶,竟然開花。她被花的美麗強烈打動,不忍觸碰,保持著花的原樣,轉而去鄰居家取水。同時寫下:
朝顏藤蔓生,縈繞輕纏井邊瓶,但汲鄰家水。
千代俳句中的「朝顏」,英語稱之為「清晨的榮耀」。從「朝顏藤蔓生」這五個字,即能體會牽牛花在早晨清爽的空氣中綻放,夏日的大自然在黎明之光中蘇醒;既美麗又充滿生意。
世人對花各有所愛,例如印度人偏愛蓮花的潔淨;中國人愛牡丹,象徵富貴;日本人則醉心於菊花,代表高潔;還有蓮花與牡丹,惟獨夏日清晨的牽牛花,其美無可匹敵。
同樣在德川幕府時期,中後段班的俳聖芭蕉,也有類似俳句:
閑寂古池旁,青蛙躍進水中央,撲通一聲響。
在原始的寂靜森林中,青蛙激起的水聲凸顯了環境的靜謐氣氛,以及大自然的深沉神秘,無須多言。
兩人的俳句雖然未觸及禪意,卻充滿禪機,讓禪與藝術巧妙結合,躍然紙上。第四章 有關禪與佛的吉光片羽---大拙觀點
讀完鈴木大拙最後的禪八講,感覺體例不是那麼完整,論述也不是那麼周延,畢竟那是多年前、多場演講的勉強合集。不過其中有些論點較少受到注意,這裡特別將其拾綴起來,就當作有關禪與佛的吉光片羽,供有興趣者參考。
一、佛教到底是什麼?
有些人說不能理解佛教,雖然有時可以這麼說,但要徹底理解確實並不容易,必須經過多年潛心研究才能有些進境。但換個角度看,在這個世界上好像沒有比佛教更易懂的了。
佛教並不是說舉起一指,世界就誕生,咳嗽一聲所有的一切全部消失,或唸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就能立即被迎入淨土,當然沒有那麼簡單。熟悉四諦、十二因緣、八正道也無法一窺堂奧;鈴木大拙認為佛教是經驗的宗教,並不是說教或講道理就能解決,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還是必要的;最容易的可能是從開悟經驗來分析,包括佛陀的經驗。他自承經過六年的冥想和思索,才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以形而上學的形式做不成熟解釋」。
如前所述,鈴木大拙的著作大多從其英文講義中翻譯而來,而禪本不立文字,其言語又充滿禪機,難以用常理推斷;要將禪的意涵用英文如實表達已經不容易,再翻成中文或其母語日文也不容易,因而出現目錄中夾雜英文的特殊現象。例如:
第一部:最終講義----禪讓通過不可得的方法進行自證的人開悟(Zen Opens Our Eyes to Self which is Altogether Unattainably Attainable)。第二部:鈴木大拙說禪的世界----(序)佛教到底是什麼?(What is Buddhism?)(第一章)禪與心理學(Zen and Psychology)。(第二章)佛教禪與藝術(Zen Buddhism and the Arts)。(第三章)活在佛教禪的戒律中(Living by the Precepts of Zen Buddhism)。(第四章)佛教與倫理(Buddhism and Ethics)。(第五章)佛教的神秘主義(Buddhism Mysticism)。(第六章)佛教禪的哲學(Philosophy of Zen Buddhism)。
不過如果細看其目錄英文,其實文字很簡單,章節也無特殊性,噱頭多於必要性,其目的可能是在吸引讀者的目光吧!何況就編輯而言,此種「後發先至」、近期文稿放前面,早年文稿放後面,可能會讓人有時空錯置的感覺。為了便於讀者理解起見,以下特別挑出重點,點出「最後禪八講」的特色:
第一講:什麼是「禪」
主要是記錄鈴木大拙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在夏威夷演講的二十九項要旨。其中雖未明確記錄演講會場及時間,但從其內容可知,演講會場是夏威夷東本願寺別院的成道會,從下午2點開始,持續了約1個小時。
第二講:禪說「真我」
在這次演講中,大拙說:心理學中的「真我」一詞,經常和個人連結使用,甚至可以說,「真我」本來就是從心理學發展而來;宇宙的真我可以和非宇宙的真我相連接。他認為,初學佛的人大概都無法理解,甚至有點排斥,為何要以「梵(阿特曼)」來代表真我。大拙甚至將成為佛性根據的「真我」,作為「無欲的修行者」,以引出唐代末期禪師的理念。因此必要時可參看宋代禪師的公案。第三講:禪與藝術
根據鈴木大拙的說法,所謂「佛教禪與藝術」,是指禪與藝術不管是在主觀或客觀上都能達到完美一致,禪就像宇宙之魂深處的物質,而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來展示,那既是藝術的起源,也是真正的藝術。在那種情況下,表現者和表現的媒介融為一體,而且自己可以意識到這種一體化,這就是禪的真我意識。他以日本有名的俳句「千代女」與「芭蕉」等具體的例子來做說明。例如:「嬌豔牽牛花,紫露晶瑩縈清井,惜花借水去」(千代女),「閑寂古池旁,青蛙跳進水中央,撲通一聲響」(芭蕉);還有鏡清的《雨滴聲》問答,仔細描寫雪寶問答的頌語,以此來說明日式禪所具有的藝術之美。
第四講:修禪戒律
在談到「佛教禪戒律」時,鈴木大拙提到,修禪、談禪說法時通常有三種戒律,那就是:「不肯定什麼是什麼」、「不否定什麼不是什麼」,以及成為那個「什麼」本身。他認為在宗教生活中,只要謹守這三個戒律,就能在生的本身中找出生的意義;非出家眾如能在日常活中把握這三個戒律,結果會更加美好;就如同他盛讚千代女所寫的「牽牛花」詩,就頗具淨土宗經典所描寫的「安樂國淨土」之美。
就禪宗或禪學而言,雖然說共有三個戒律,其實歸結到最後不過是「道一句」,也就是一句話、言語道斷的意思。為了說明三戒律與生的關係,鈴木大拙特別介紹了一則禪宗唐朝在有名的公案「南泉斬貓」:唐朝時,南泉普願禪師修行的禪堂出現了一隻貓,眾僧為了「貓有沒有佛性」而爭論不休,甚至因此而造成對立。南泉普願禪師走出禪堂,要求眾僧「道一句」,亦即說出貓到底有沒有佛性的道理;如果說不出,則爭論無易,就殺了爭論的源頭「貓」。結果因為沒有人回答得出,南泉就命人斬殺了那隻貓。
不久,南泉最信賴的弟子趙州和尚從外面勞作回來,南泉把經過說給他聽,問他會怎麼做?趙州禪師聽了之後什麼都沒說,就脫下腳上穿的草鞋,頂在頭上走了出去。南泉看了嘆道:「剛才如果你在場,那隻貓兒就得救了。」自古以來,這則「南泉斬貓」公案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引起很多討論,鈴木大拙自己也認為很難明確表達這則公案的整體內涵。不過他也認為,「修禪三原則」終究勝過當時西方世界流行的「新正統派基督教世界觀」,以及薩特所代表、主張虛無的存在主義。基督教是把現實的「生(命)」本身,當作沒有意義的東西;而將神的恩惠、恩寵視為「生」的外部力量。薩特的存在主義則認為,不論是「生」的內部或外部,其實都是虛無的,包括生命與生活都是虛無的,必須重新定位存在的意義。可是依據禪雖然不直觀地否定或不否定什麼,但認為宇宙充滿生機,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只要經過指引,找出那個可能性,就是頓悟,就能海闊天空、心無罣礙,過有意義的人生。
大拙禪風具有五大特色
禪文化聯繫了古代與現代,跨越了東方與西方文化的為哩,形成一條寬廣深邃的溝通渠道。雖然禪宗與禪學興盛於中土,但不可諱言,二十世紀初期將禪文化帶入西方社會,且引起重視的應該是日本人,其中以鈴木大拙最投入、最有心,而且獲得最多回響。尤其是他晚年多場演講結集而成的「最後禪八講」,最近又引起討論的話題。
其實鈴木大拙在西方說禪,不像我國傳統的禪宗大師或其解讀者一樣,往往先談禪宗的發展史,再提具有代表性的公案。他雖以中國禪、日本禪為立論基本,卻用西方哲學的觀點來解說禪,這是它的特點,也是成功之處。大拙說禪可大致歸納出幾個重點與特色:
一、以西方哲學語言說禪,故能引起興趣
或許是受到其同鄉兼好友、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影響,鈴木大拙談禪「多從理論上下功夫」,而且用的是西方人容易懂的語言和文字,因此能激起西方人對東方禪文化的好奇,達到他「盡量讓普通的讀者能多了解禪、更加親近禪,即使多少犧牲了一點禪的正確性」也可以理解。但以哲學或西方語言說禪,再翻譯成東方文字時,可能有無法完全達意的情況,尤其禪宗公案的引述,就顯得虛無飄渺,沒有原先文字那麼簡潔而意境高遠。二、強調「靈性的直覺」
雖然鈴木大拙長年待在西方社會,但其思考模式、對禪的觀念還是非常傳統的,他對《華嚴經》有深入研究,也體會到「明心見性」、「頓悟」的奇妙。據說他在以「真我」為前提的修習過程中,二十五歲時體驗到「靈性的直覺」,明心見性而「開悟」;此後均以心靈本能的直覺,即禪之體驗,作為禪思想的主幹(大前提),從此始終一貫,從未改變。
他認為宇宙中的一切現象,彼此之間有多重至無限的關係,即使只是是一個現象,比如心理上的微小波動,或一粒微塵,其中都包含了宇宙整體的影像,即所謂「一沙一世界」、「絕對的一點蘊含三千個大千世界,絕對的現在包含永遠的過去和永遠的未來。」這種「為一切眾生,神變不可思議」的體驗,只有回歸真我,靠「靈性的直覺」才能頓悟。
三、禪不能以常情看待、常理推測
「禪超越了言語和理智,不像哲學那樣,依循規定的思想和行為發展。」鈴木大拙強調,只有「修行」才是明心見性的捷徑。他引日本曹洞禪創始人道元和尚的話說:「我空手還鄉,在中國學到的只不過是眼橫鼻直而已。」意思是雖然到在禪門重地修行,每天的生活都一樣,看到的人也都長得差不多,無法給予什麼高深的理論,也不談玄說裡,就像每個人的長相都是眼睛橫著長、鼻子是值得那麼平常。禪門中人的言行舉止也無法以理智探討,更無法系統化表述;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行」,就是觀察、思索與體會。禪的修行沒有適當、合理的知解形式,但也不能完全沒有知解;「有知解而無修行則弱,只修行而無知解則盲」,比較起來,知識、理解還不如「老實念佛(修行)」容易禪悟。
談禪的性格、方法與途徑
常言道「知易行難」,就禪而言,「知」的工夫並不難,難的是如何達到真正的「知」,以接近禪的本質。畢竟禪是一種洞徹的智慧,其本質在於「真實在」,正如鈴木所言:「禪給了我們看透世界的眼睛,其範圍遍及三千大千世界,而且還要超越。」因此鈴木大拙說禪,談的是禪的性格,禪是什麼、不是什麼;禪的方法、路徑,禪如何看世界、如何思考;最後才談到修禪的目的和意義。他談禪宗與東西方宗教的異同、禪與審美的關係等等,無非想廓清世俗(特別是西方世界)對禪錯誤或粗淺概念,掃去陰霾,以回復本來面目。星雲法師在『禪學與淨土』系列演講集的序中,談到什麼是禪、修禪或學禪有什麼作用時說:「禪是什麼呢?據青原禪師說:禪就是我們的「心」。唐朝的百丈禪師最提倡生活化的禪,他說挑柴擔水、衣食住行,無一不是禪,所謂翠竹黃花,一切的生活都是禪。」又說:「我們生活在人間,人間有男女老少,人間有五欲六塵,人間有生老病死,人間有悲歡離合。在缺憾的世間裡,我們如何獲得歡喜自在?如何發揮生命的價值?如何擁有安樂的生活?這是我們要探討的課題。」他說,禪可以開拓我們的心靈,啟發我們的智慧,引導我們進入更超脫的自由世界,可以說是探討生命學、生死學與生活學的法門,打開天人之門的鑰匙。換句話說,就是:以生命為 「體」,生死為「相」,生活是「用」,生命從生到死,其中的食衣住行、言行舉止、身心活動等等,無一不是生命的作用。因此,體、相、用,三者密不可分。所謂戒定慧,即由戒生定,由定發慧,由慧趣入解脫,需要斷除煩惱才能獲得究竟的妙智,才能自在悠遊於人間!
但「禪是需要去實踐的,而不是在嘴上談論的」;所謂「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地用功夫;若要紙上談人我,筆影蘸乾洞庭湖。」禪是言語道斷、不立文字的;是心行處滅,與思維言說的層次不同的。禪不好講、不能談,也不易懂。所以古代禪師用「棒喝」、用看似不合常理的言語、文字來讓地子頓悟;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來參禪(就是生活禪);甚至如「趙州八十行腳」一樣地修禪。
話雖如此,禪畢竟不容易入門,所謂「妙高頂上,不可言傳;第二峰頭,略容話會」。禪雖然不容易了解,雖然以「言語道斷、不立文字」為戒律,為了普及禪知識,還是要藉言語、jp6y4來說明。禪八講雖各有主題,但是每講內容實則包含了多個子目標,切題並擴題,顯得廣闊無邊。本書採用主題方式,重新呈現禪八講。閱讀起來輕鬆活潑,禪味不失,請讀者慢慢體會禪言之妙。
以下即以其所提的公案來作分析,請讀者多加體會。
一、論佛姓
公案:本有說不得
松山和尚和龐居士喝茶。居士說:「人人均有佛性,為什麼說不出來?」
松山道:「因為人人本有,故說不得!」
居士又問:「但有時聽你說此本有(佛性),這又是為何?」
和尚答:「你總不能叫我不說話吧!」公案:喝茶為和要寒喧
唐代禪匠松山(馬祖道一門下)與龐居士喝茶。居士拿起茶碟,問:「茶碟人人知,卻沒有人解釋它究為何物,這是為何?」
松山禪師回答:「人人皆知,所以誰也無法解釋。」
龐居士進一步追問:「那麼如何才算是巧妙的說明呢?」
松山回答道:「無法保持沉默的時候。」並喝了一口茶碟上的茶。
龐居士緊迫追問:「喝茶的時候,為什麼要先對客人寒暄呢?」
松山詫異的問道:「對誰?」
龐居士接著說:「對姓龐的老人啊。」
「老人,需要寒暄嗎?」
◆ 解讀
龐居士和松山的問答就這樣結束了。初次接觸學學的人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事實上,禪不是哲學,也無法說理,但禪者間的問答卻充滿了哲學意味。對多數人來說,禪者間的對話不著邊際,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教誨。龐居士所問、松山和尚所答,都不是茶碟的外在,而是有情或無情究極的實在。在「禪問答」之間,確實有不可思議的一面。禪並非全是抽象的觀念,身旁觸手可及的茶碟也蘊含著禪的道理。松山和尚所言「無法保持沉默的時候」,意指不得不表達自我的時候,其內心早已浮現闡述禪的道路。禪匠所關切的,也是每一個人都關心的。這就是禪。
初次接觸禪的人都說禪難以把握、甚至讓人困惑,這是基於以下事實:不可得的東西就像是圓心在任何地方的圓,正因為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以得到,所以才不可得。它不在任何地方,所以無所不在;它隨處都有,卻又是哪裡都沒有。
我們再看看雪峯義存的公案,也許就可以帶來啟示。
第三章 禪到底是什麼?
看了那麼多禪宗公案,究竟有多少人知道:禪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佛學提倡解行並重,尤其是禪,更注重實踐的功夫。唯有透過實踐,才能把握到禪的風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古德說:搬柴運水無非是禪。在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面,穿衣吃飯可以參禪,走路睡覺可以參禪,甚至於上廁所都可以參禪。一、禪最自然,無關美醜
什麼是道?「雲在青天水在瓶」、「青青翠竹,無非般若;鬱鬱黃花,皆是妙諦」。
未悟道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悟道後,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日月,寒盡不知年」、「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禪」就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滌心靈的塵埃;禪,如天上的白雲,任運逍遙,不滯不礙。
公案:好醜起於心
雙峯道信禪師(五八○~六五一)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禪宗特別重視內心的淨化,強調要認識內心世界的真面貌。
在諸多花卉中,最富禪意的是在清晨開放的牽牛花,其絢爛之美常於瞬間爆發、達到頂峰。牽牛花能夠長到二十公分,甚至更大,有各種顏色。雖然無法經受長時間的陽光照射,但花朵總在夏日清晨的清爽空氣中綻放,堪稱「無瑕」;無論是何種色調,若有輕盈的朝露加被,便顯現出鮮活生機,十分清雅動人。
日本德川幕府時代末期(十八世紀後半葉),有一位頗具才華的女俳人千代,她創作了許多十七音節的俳句,其中就有牽牛花。有一天她在清早起床後,準備從廚房旁邊的水井打水,忽然發現牽牛花的藤蔓纏繞著水桶,竟然開花。她被花的美麗強烈打動,不忍觸碰,保持著花的原樣,轉而去鄰居家取水。同時寫下:
朝顏藤蔓生,縈繞輕纏井邊瓶,但汲鄰家水。
千代俳句中的「朝顏」,英語稱之為「清晨的榮耀」。從「朝顏藤蔓生」這五個字,即能體會牽牛花在早晨清爽的空氣中綻放,夏日的大自然在黎明之光中蘇醒;既美麗又充滿生意。
世人對花各有所愛,例如印度人偏愛蓮花的潔淨;中國人愛牡丹,象徵富貴;日本人則醉心於菊花,代表高潔;還有蓮花與牡丹,惟獨夏日清晨的牽牛花,其美無可匹敵。
同樣在德川幕府時期,中後段班的俳聖芭蕉,也有類似俳句:
閑寂古池旁,青蛙躍進水中央,撲通一聲響。
在原始的寂靜森林中,青蛙激起的水聲凸顯了環境的靜謐氣氛,以及大自然的深沉神秘,無須多言。
兩人的俳句雖然未觸及禪意,卻充滿禪機,讓禪與藝術巧妙結合,躍然紙上。第四章 有關禪與佛的吉光片羽---大拙觀點
讀完鈴木大拙最後的禪八講,感覺體例不是那麼完整,論述也不是那麼周延,畢竟那是多年前、多場演講的勉強合集。不過其中有些論點較少受到注意,這裡特別將其拾綴起來,就當作有關禪與佛的吉光片羽,供有興趣者參考。
一、佛教到底是什麼?
有些人說不能理解佛教,雖然有時可以這麼說,但要徹底理解確實並不容易,必須經過多年潛心研究才能有些進境。但換個角度看,在這個世界上好像沒有比佛教更易懂的了。
佛教並不是說舉起一指,世界就誕生,咳嗽一聲所有的一切全部消失,或唸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就能立即被迎入淨土,當然沒有那麼簡單。熟悉四諦、十二因緣、八正道也無法一窺堂奧;鈴木大拙認為佛教是經驗的宗教,並不是說教或講道理就能解決,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還是必要的;最容易的可能是從開悟經驗來分析,包括佛陀的經驗。他自承經過六年的冥想和思索,才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以形而上學的形式做不成熟解釋」。